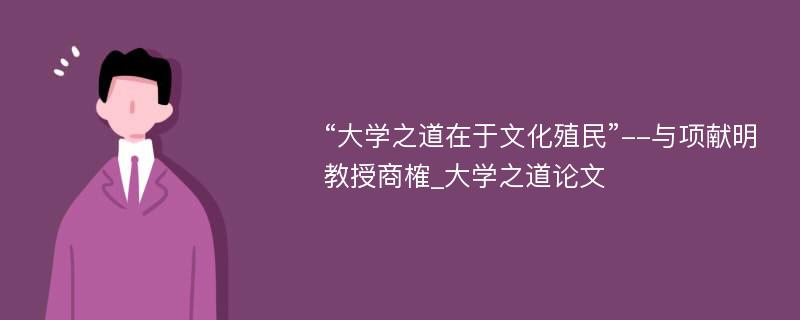
岂能说“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与项贤明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贤明论文,之道论文,教授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2)04-0154-05
读罢《学术界》2002年第1期所刊登的项贤明教授的《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一文,笔者颇有感触,于是想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与项教授商榷其中的一些论点。
首先来看“殖民化”和“文化”问题。殖民化作为一个政治学中的术语,它一般被理解为一个处于强势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军事)的国家,运用它所拥有的强势力量迫使一个处于弱势的国家屈从于它,从而达到剥削、奴役的目的的一个过程。在上面提到的强势状态的因素中,笔者没有谈及文化因素,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对文化所下的定义竟达300种之多。(注: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导言第1页。)当广义的文化概念界定中包含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时,我们可以以这些先进的科技为准来确定文化间的孰优孰劣;当狭义的文化概念仅理解为民族精神时,我们又怎能说哪种文化比哪种文化优势呢?所以,当我们把文化理解为广义的文化时,我们的大学面对来自社会各层面的要求或压力,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世界先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后,难道我们就应以似乎符合逻辑推理的理由,强加给大学一个“在文化殖民”的帽子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话:社会的需求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当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想融入国际社会时,它就要求我们的大学同社会发展保持同向。即使所谓的“文化殖民”能成立的话,那也不是大学本身的错,更何况“文化殖民”这种提法本身就存在是否能成立的问题(稍后再论)。
再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即作为民族精神的文化来考虑“文化殖民”这个问题。民族精神作为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结晶,它具有稳定性、恒久性的特征,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民族精神的存在才保证了一个民族不至于易于“变质”或“消亡”。这一点在我们中华民族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同化力可以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和包融异族外来文化的过程,最终的结局都是丰富和发展了原先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连续几千年的文化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核,经受住了从1840年到1949年这百余年间中华民族衰微时期时外来强势文明的强烈冲击,抗争、探索、适应和同化着外来殖民文明。难道能说这段时期内自从中国有了大学,大学就在“文化殖民”着中国?显然不能。相反倒是我们对那个时期内的大学对我们民族的复兴作出的贡献应给予认可。这里我们还要与项教授讨论另一个论点,即“精英文化层面的殖民化对包括大众文化层面在内的整个民族文化体系都有着十分锐利的侵蚀作用”。项教授这一忧国忧民的观点看来会让人们认为完美无缺,我们想问项教授的是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我们的大学所创造的精英文化倒底是一种什么样文化?其二,体现我们民族精英分子思想的精英文化是否已经被殖民化了或着说正在被殖民化?如果回答是肯定,那么这种精英层面的殖民化表现在哪里?对后一个问题,项教授在他的文化里给的回答中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的精英文化已经殖民化了,很危险,表现在对大众文化的冲击方面,并以社会中的一小撮青年雅皮士现象为论据来说明危害,请问项教授这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吗?雅皮士是一个舶来品,是否适合我们的青年呢?据笔者从报纸上所了解的信息,上海这样一个很有“海外”特色的城市中的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念依然符合我们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这似乎可以说项教授有些过分担心我们的青年一代会被“殖民化”吧。其实是我们对今天的青年给予的否定太多,而实际上今天的青年一代是很有思想和见识的,他们积极进取,崇尚民主和科学,关心时事政治。这些我们可以从2001年中国青年中间最为流行的10个词语,即“9·11”、“本·拉登”、“申奥成功”、“入世”、"WTO"、“翠花上酸菜”、“出线”、"QQ"、“反恐”、"flash"。(注:《生活周刊》,青年报社主办,2002年5月2日-8日,第2版。)它们以强烈的世界意识、广泛的祖国关怀、入时的娱乐需求,特征性地勾画出我们的青年群体。我们的青年是有希望的青年,能以此称他们为“雅皮士”吗?应当肯定我们的青年人,以他们的理智水平来看,不可能至少不易于被“殖民化”。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在这样一个文明相互激荡的时代,社会上或大学中多了些异于传统的新东西,这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甚至警惕心,支持或反对。笔者想对此警惕是应该的,毕竟我们特别珍视我们的传统,而且在百年的屈辱史中,中华民族已成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受到创伤的民族,伤口直到今天还未愈合。从这种背景出发我们当然要理解像项教授的忧虑,但存在的事物有其合理性或必然性(只要条件具备),因此,我们不应该用“殖民化”这顶帽子将大学充满活力的“头”笼住,使其惧怕而趋向保守,最终无所适从。或许当大学失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或愿望时,大学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也就在这时候,一个民族有了被“殖民化”的危险。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不可能被项教授所认为的那种“强势西方文化”所“化掉”,相反,中华文化在异质的外来文化相互激荡中会更加充实、丰富发展。我们应少一些担心而要多一些信心,不要惧怕“文化殖民”。笔者向来坚信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激荡是客观的,两种异质的文化之间只能是一个冲突、融合且会保持各自特质的过程。这可从我国周边几个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的历史发展来说明,日本在古代历史上面对我国唐朝的强盛文化优势时,积极学习、吸收,甚至连汉字也加以引进并经改造后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化、文明的发展,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到了近代,日本被迫开关后,处于优势的西方文明对于封建落后的日本的冲击不可谓不大,结果又怎样呢?日本人不畏“殖民化”,勇于吸收借鉴西方文明,创造性发展了日本文明并胜过西方。日本文明显然没有被殖民化。再看印度这个国家,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多年后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文化传统,像社会等级现象等,这个民族的语言消失了吗?显然也没有。印度虽有英国的殖民烙印,但更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存在着。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殖民化”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似乎不能用于文化领域,至少不能用于像中国这样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中。项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我国中小学也成为我们从内部进行自我殖民的一种文化殖民机构了。对于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言重了吧,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正“风声正紧”,大多数国家对基础教育非常重视,我国更是如此。因此,紧跟世界先进教育改革潮流,吸收其中的先进经验来改革我国基础教育就成为我们一种自学的选择。我们进行基础教育改革就应当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基本的教育理念进行创新,吸收国外先进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创新,形成自己的东西。没有这几年教育改革力度,我们能将教学内容中那些陈旧的东西删去吗?没有吸收外来的先进经验和理念,我们能像今天这样特别关注教育中的“人”的成长吗?对学生发展的关注,人民大众的觉悟提高,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基础教育在吸收了外来先进思想后开始进步了。尽管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还有大量的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项教授如此将我国中小学教育定位在“成为一种文化殖民机构”,这有点像是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出发而得出的一个固执观点,这是在否定我们的教育改革,否定我们为此做的努力探索。
与上面的论断相对应,为了证明他的结论的正确性,项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接着谈到文化交流和西式学校教育的传入两者的区别,并认为文化交流后传入我国的文化是作为“文化因素”传入的,所以这个“文化因素”不会导致多大的危害;而西式学校教育则不仅仅是作为“文化现象”传入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机制”传入我国的,因此,西式学校教育会传承西方的话语和价值,于是成为一种“文化殖民机构”了。笔者想项教授对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认清,有些简单化了,其一:我们今天的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引进西式学校教育的一些东西,并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相反,我们是主动出击,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其二:我们不是全盘照搬西式学校教育,我们学的是西方最先进的东西,而且我们对这些外来东西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我国的国情,此外,我国中小学也一直在强调传统文化,思想、情感、价值观的教育。由此看来,项教授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呢。
20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三个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国际性。强调高等教育间的沟通与交流是各国所认同的,邓小平曾经说过,认识到落后,我们就会努力赶超世界先进,这就是一种进步。我们的大学水平整体落后于西方,我们重视吸收和改造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是一种理性化的明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许多学院(College)急于改为大学(University),有些大学硬性规定以英语授课的课程必须占多少比例,这些做法当然是不合理的,但至少在教师和学生英语水平过关的大学里,我们应当提倡用英语讲课,这难道也是一种“殖民化”的表现?当大学和大学中的人用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并得到我们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时,我们为什么非要用一个“殖民心态”来贬低他们呢?如果非要说是他们的殖民心态的话,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强调外语教学呢?难道是国家在助长这种所谓的“殖民心态”?与项教授的这种民族保守主义情结相反,同是比较教育博士的薛理银先生在他的博士文化中提出了如下观点:“比较教育的研究活动(或流派)分为四类:第一,民族中心主义,它以本文化的思维模式、概念系统和价值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客文化的教育;第二,科学主义,它假定认识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第三,相对主义,它以客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来认识和评价客文化的教育现象;第四,国际主义,它假定存在一个国际公认的认识方式、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并以此作为分析(主)客文化的教育现象。……并提倡能把民族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统一起来的‘国际主义’观点。”(注:薛理银著:《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内容提要第2-3页。)与此观点相对应的是,现实当中,我们的关注点就在于“国际交流”的加强。在国际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一个富有根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各国指导各自教育行动的依据。在这样一个五洲相互激荡的时代里,开放的心态对我们的社会是何等重要。“中国人越是自信,就越没有理由害怕合作可能造成依赖”。(注:〔加〕许美德,〔法〕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因此,我们有必要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德洛尔的新教育哲学观,即“首先,我对教育的信仰是教育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我对国际组织的作用的信仰是它们可以把最值得称颂的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人民的意识中,不断地向理解他人的方向迈进。”(注:赵中建选编:《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九十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36页。)
项教授在他的文章最后指出了如何做到“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他在对“本土化”和“化本土”的批判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大学的“本土生长”。倘若项教授不是在用新术语来给他人一种新鲜感的话,请问“化本土”和“本土生长”又有何区别?“本土生长”一定比“化本土”更高明?依笔者之浅见,“化本土”之后就是为了“本土生长”,从而达到大学的优化和超越,我们怎能饮水不思源,否定“化本土”呢?著名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为了反驳“全球文化正在走向同质化”的观点,而提出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意思是指“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因而他赞成全球文化正以“越来越大的多样性和差异为标志”的观点。(注:〔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由此可见,我们的民族文化从来就没有被“化”过,且一直在“本土生长”着,项教授又怎能从我们的民族文化已经在被殖民化的前提出发,来得出一个似乎前无古人的观点,即要“本土生长”呢?
在我国近代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的衰落和为探索民族复兴道路而走过的曲折历程,使得我们的国人很容易将引入外来教育因素视为奴化或奴役过程,看来在今天中华民族开始腾飞的时候,面对外来的强大力量,我们的国人又开始重复我们先人的道路,视大学之道在奴化中华民族了。是以积极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还是以心存余悸或防范之心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大学之道,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为了进一步明确笔者的“大学之道不在文化殖民”观点,还是让我们以鲁迅的一段话来结束吧,“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魅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退缩,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注:何泽福:《看镜有感》,转引自《“开放”与“闭关”》,《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