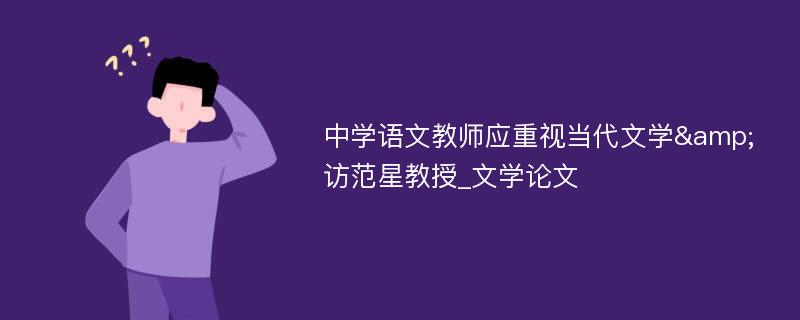
中学语文教师应关注当代文学——樊星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学语文论文,教师应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樊教授,您好。我是《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实习记者。今天我想就中学语文教学的有关问题采访您,可以吗?
樊:好的。我乐意接受采访。
钱:现在中学语文新教材中增加了不少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如《陈奂生上城》、《摆渡》等。那么作为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在讲授当代文学作品时应该采取哪些与讲授其他时代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方法?
樊:在中学语文新教材中增加当代文学名篇,无疑是出于“与时俱进”的考虑。讲授这些作品时,除了常规的人物形象分析、语言风格辨析之外,我认为可以适当加强对作品的“当代性”的分析。
钱:那么这个“当代性”应该如何分析呢,能具体的给我们举例谈谈吗?
樊:那我以《陈奂生上城》为例。其“当代性”至少体现在,可以通过陈奂生与阿Q的性格比较看当代作家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陈奂生被评论界公认为当代的阿Q形象,由此可以引出这样的思考:阿Q的子孙为什么绵绵不绝?其中蕴藏了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之谜?如果没有阿Q精神的支持,陈奂生会怎样?在日常生活中,究竟需不需要一点“阿Q精神”?(顺便提一句:经济学家于光远曾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谈及自己凭着“革命的阿Q主义”在逆境中豁达处世的体会,值得注意。这样的体会显然与鲁迅对阿Q精神的批判不一样,但在我看来,同样深刻。)分析这些问题,可以由此为学生们开出一条重新认识生活、探讨生活的复杂性的思路来;另一方面,作家本人曾经说过“陈奂生就是我”,作品的主题是“农民苦”,这是与评论家的共识颇不相同的另一种思维,它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主题的丰富性。此外,陈奂生与阿Q性格的相似又不尽相同也值得辨析,这种辨析可以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钱:总的来说,这样分析的好处在哪儿呢?
樊:要而言之,通过对当代文学名篇的多角度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理解生活与世界的复杂性的能力。在这方面,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是值得记取的:“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当然,我觉得,在这段话中,“每一部”的后面应该加上一个形容词:“优秀的”,才更准确。
钱:由此看来,中学语文教师要想讲好当代文学作品,需要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樊:是的。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在平时多关心当代文学。这样在讲当代文学的作品时才能对作品有个很好的把握,才能把它讲好。
钱:但现在有这样一种状况,即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部分语文老师不关心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
樊: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比起80年代的文学来,已经普遍失去了“轰动效应”,许多当年的文学爱好者由于种种原因开始远离文学(有的是下海,有的则是因为对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粗鄙化倾向不满,还有的是走向了通俗文学的新天地,也有不少人被“家庭影院”席卷而去),文学的危机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对于中学教师来说,沉重的应试教育负担也迫使他们无暇顾及当代文学。据我有限的了解,中学教师中喜欢文学、关心当代文学的不乏其人,但教学与家务的重负常常使他们抽不出时间去关心当代文学。
钱:这种状况会造成语文教师因为负担过重,极少去阅读课本以外的当代文学作品,使得他们的知识难以得到更新。
樊:是这样。对当代文学的渐渐陌生很可能导致教师人文素质的退化,以致教师们至少难以回答爱好文学的学生们提出的有关问题,而眼下普遍存在的中学生被流行文化牵着走,良莠不辨的问题也会自然加重。有关部门正在呼吁“加强素质教育”,许多大学(包括许多理工科大学)都在开办人文讲座,都表明了问题的迫切性。看来,如何提高中学生的人文素质,事关重大。而这个问题又与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密切相关。不言自明的是,对当代文学的了解与修养是中学语文教师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钱:那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对当代文学日渐陌生的情形?
樊:我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的体制,让教师从繁重的讲课、改本子、阅卷任务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一种“减负”,给教师减负,使他们有一定的时间去读书。在这方面,有一部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利用假期参加专业进修、培训(例如“中学教育硕士学位课程班”)的教师是体会很深的。我曾经不止一次给这样的教师上过课,他们的普遍反映是:继续教育,搞与不搞,感受大不一样。在国外,发达国家的教师也有不断“回炉”、“充电”的机制,行之有效。另一方面,我觉得,只要真的喜爱当代文学,总会想方设法、挤时间去了解当代文学的新动向的。至少,我就接触过一些一边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一边坚持阅读最新文学作品并坚持写作的中学教师。对于他们,这样的阅读和写作显然是非功利的。爱好是最大的动力。爱好就是精神的家园。
钱:是的,要解决中学语文老师对当代文学缺乏关注的问题,需要社会和老师双方面的共同努力。您认为中学语文老师应从哪些方面努力呢,也就是他们应关注当代文学的哪些方面?
樊:我觉得应该主要关注那些个性突出、不随波逐流又具有重要影响的优秀作家作品,例如:那些积极探讨人生哲理的作品(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铁凝的《永远有多远》、阎连科的《年月日》、王小波的杂文等),因为对于中学生,在人生观形成的时候,更需要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与一般性的说教区别开来的积极影响;那些具有深厚古典文化底蕴的作品(像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阿城的《棋王》和李弘的《春江花月夜》等),因为现在的中学生对古典文化已经相当陌生了,而如何从当代生活中发现古典文化底蕴,也直接关系到人文素养的建构;那些具有地域文化气息的作品(从迟子建的《亲亲土豆》、毕飞宇的《玉米》那样的新乡土小说到于坚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昆明记》那样的“新都市文学”、红柯的《跃马天山》那样的新边塞小说),由此培养地域文化意识。因为地域文化永远是文学的富矿,可以常写常新(想想张爱玲、王安忆、朱文颖笔下的上海,老舍、邓友梅、王朔笔下的北京,就可以体会出这一点来)。将上述几个方面拢到一起,既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也有助于培养我们的个性,而个性,不正是创新的源泉么?
钱:听您举了这么多例子,使我感到在当代文学的作品中还有许多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那您认为对当代文学的了解对我们中学的教学有哪些帮助?
樊:可以从两个层面看这个问题:第一,从实用的层面看,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和态势有助于加深对中学语文教材的理解。在讲解那些当代文学的名篇时,要想对作家作品的背景有深入的理解,当然离不了对当代文学发展态势的整体了解。第二,从文学修养的层面看,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也是了解当代文化思潮、当代人价值观念变迁的必需。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意气风发、到80年代社会巨变导致的浮躁情绪的高涨、再到90年代社会平稳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困惑,一切都在文学思潮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在文化思潮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中,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与杂糅,使得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
钱:那了解当代文学对我们中学的作文教学有哪些帮助呢?请跟我们的读者具体谈谈比如新写实主义、新体验、新历史主义等艺术流派对中学生写作的启发作用。
樊:新写实小说的世俗化倾向、冷漠化风格就充分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态。方方、池莉、余华、苏童、刘震云的小说对当代人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他们善于通过鸡毛蒜皮的描写去还原生命体验的写法对于当代中学生模仿港台流行文学的俏皮、花哨风格也许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而这些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文风上的各不相同也昭示了世俗化写作的广阔空间。
所谓“新体验小说”,其实是“纪实小说”的另一个说法。当代许多作家直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文学作品,使“纪实小说”十分发达。像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老鬼的《血与铁》、林白的《青苔》都因此而给人以强烈的“亲历感”。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些作品的成功也很有启示意义:普通的生活,自己的体验,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学财富。
“新历史主义”重写历史(但与“戏说历史”的媚俗做法很不一样)的尝试也可以给人开启重新审视历史的思路,像格非的《凉州词》、《锦瑟》,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这样的作品就在重写历史中倾注了作家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写出了历史的另一面。在我看来,去年高考作文中那篇不胫而走的,以古文风格重写赤兔马命运的作品《赤兔之死》,就具有“新历史主义”的意味。当然,对上述思潮中的虚无主义倾向,教师也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的职责。
钱:您的谈话一定会给我们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带来不少启发,我的采访就到这里,感谢您拿出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樊:不客气。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