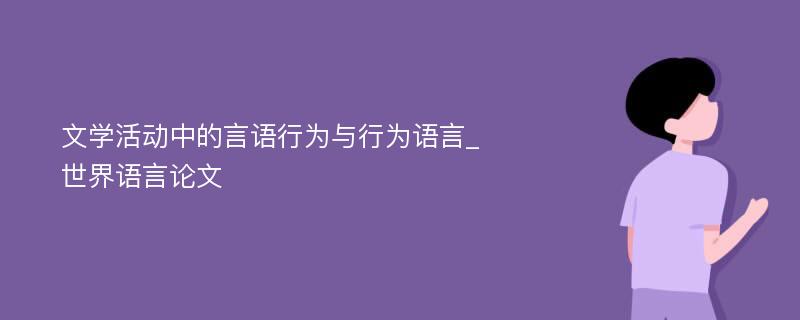
文学活动中的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语论文,语言论文,活动中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言语是一种行为,行为(动作、姿态、表情、装饰等)也是语言。 在俄罗斯导演M.什维茨尔拍摄的影片《复活》中,有一组十分精彩的心理描写镜头。电影没有旁白,镜头也没有对准女主角卡秋莎极富于表现性的面部表情,而是聚焦于门扇上一个扣门的金属搭钩和手掌的背部:就在搭钩附近的门扇上,那只紧张得有些僵硬的年轻女性的手微颤着犹疑地缓缓挪向那个搭钩,渐渐靠近了,近了,又移开了……当手再次靠近搭钩,终于毅然抬起了搭钩。搭钩从门扣上脱出,垂落下来,镜头中只留下搭钩无声地来回摆动——那是卡秋莎的手。她深爱着涅赫柳多夫。当涅赫柳多夫第一次在深夜想进入她的房间,她却犹豫了。她期盼涅赫柳多夫的到来,甚至愿意将整个人都献给他,却又担心两人之间的身份差距,毕竟一个是公爵少爷,而自己却只是个养女、侍女,她朦胧地意识到潜伏着的危机,内心充满矛盾。可是,对于电影艺术来说,这种心理活动必须转换为视觉形象,什维茨尔则敏锐地抓住了这只少女的手。原本不会说话的手,却极其生动、细腻地道出了一个少女内心的动荡,她对性爱既憧憬又恐惧的矛盾。行为就是语言,它甚至比普通语言更富有表现力。 行为是广义的语言,是比普通语言更原初、因而也更基本的语言。在小说《复活》第十二章,托尔斯泰描写了涅赫柳多夫与卡秋莎的初恋,那种少男少女间刚刚萌生的纯真、朦胧的爱情:在他俩当着老女仆玛特廖娜的面谈话时,感到分外轻松愉快。可是,房内只留下他们两人,谈话就比较别扭。“这时候眼睛就开始说话,眼睛说的话与嘴上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而且比嘴上说的重要得多。”①行为语言(眼睛表情和别扭态度)常常比普通语言更为可信,它无意间泄露了真正的自我,更加真实、直白地表达了内心。语言学家韩礼德说:“我们都是通过对个体的表达习惯来认出我们的朋友,这如同通过他们的脸、声音、穿着或行走的方式来了解认识我们的朋友一样。一个人即是他表达的意义。”②行为不仅让我们认出朋友,而且看出他的个性特征,看到他的内心状态,因为行为就是语言,它以最自然的方式表达了个人的独特意义。 康纳顿谈到身体姿态的重要性,并认为权力和等级一般就通过相对于他人的某些姿态来表达。我们可以从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从他们的身体相对于其他人所摆的姿势,推断每个人按规矩拥有或自认为拥有权力的程度。譬如当一个人坐在高处,围绕他的人都站着;当一个人站着,其他所有人都坐着;当某人进来,屋里每个人都起立等等。所有这些姿势都包含着明确的意义。“在所有文化中,对于权威的编排,大多通过身体来表达。在这项编排中,有一整套可辨认的姿势,由此,直立的身姿表现出诸多含义的弯曲,让许多姿势操演变得有意义。”③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拓展了“语言”的外延,把它扩大到普通语言之外。他说:“我们称之为语言的首先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这一工具,我们的语词语言这一工具;然后根据与它的相似性或可比较性才将其他的东西也称为语言。”④当人的行为包含着社会共享的意义和普遍可传达性,并进入人际交流活动,那么,它就是一种“类语言”或“广义语言”。我们以“行为语言”而非“身体语言”来命名,主要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待和解读身体语言。行为语言所强调的是动态的行为,而非静态的符号及其组合或组接。行为固然具有符号学特征,却不仅仅是符号,它首先是不断变化着的身体行为,符号性只是从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特征。同时,身体也不只是行为的载体,不只是行为的发出者和施行者,而是和行为相统一的,是行动着、表演着的身体,它融合、融化在行为之中,成为行为本身和其构成要素。行为才是我们思考的着眼点。 行为作为语言是人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既习得了普通语言,也习得了行为的语言。他逐渐听懂父母所说的话,同时,也逐渐理解父母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可以说,儿童在学会普通语言之前,通过身体接触就能够了解行为语言,行为语言早就刻写在人的身体上了。较之于普通语言,行为语言是更为基础、更为丰富细腻的。对普通语言的理解常常需要行为语言的协助,也就是说,行为语言起着“元语言”的作用。普通语言是和抽象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将现实世界抽象为超越具体时空的概念,由此给人类交流带来极大的方便,将人类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解放出来。而行为语言则是非概念性的,它始终和行为的具体方式密切相关,是对行为模式的识别,对行为形式的整体提取。因此,行为语言是一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抽象,也可以说,它是非抽象、非概念的,但仍然是形象性的。它虽然不是纯粹的形式,却是与行为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具有形式感。舞蹈就是一种行为语言。只是它对日常行为语言进行了提炼和改造,强化了它的形式感、美感,并将其高度仪式化了。舞蹈语言是被高度规范化、程式化、仪式化了的行为语言,是以行为本身作为感受目的的语言,因而也是另一种行为语言。日常的行为语言缺乏这种严格的规定性和自足性,其意义也相对模糊,它是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对行为方式的习得。人从社会生活里不断重复的行为中潜移默化地习得了行为语言,不仅养成了个人应有的行为方式,并且理解了各种行为的意义,掌握了行为语言,这就成为解读行为意义和人际沟通的必要前提。相对于普通语言,人的行为语言要更为古老,它深深植根于人的身体和心灵,成为人最基本的能力,人须臾不能离开行为语言。行为语言甚至可以超越普通语言的民族界限、国家界限,而具有远为广泛的普遍性和可传达能力。 与此相应,人的行为所关涉的情景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对象被人所认知,并不总是直接和语言概念密切相关;同时,情景也不是作为静态的背景与行为相关联,而首先是作为人的行为的直接延伸,被赋予动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形式,并因此被拟人化了。人所活动的世界首先是作为人的行为的一部分而被建构起来,同时也受到语言的重构和拓展。正因如此,人的世界,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都透露出人的气息,流淌着湿漉漉的生命汁液,洋溢着勃勃生机。在谈到对遗迹和景象的感知时,梅洛—庞蒂指出,人们用烟斗吸烟,用羹匙吃饭,用电铃叫人等等,对文化世界的知觉只有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对另一个人的知觉才能得到证实。这就是说,文化世界始终是与人的行为、人的活动密切相连的,它是行为的直接延伸,是人的活动的丰盛成果,因此,它才以人的方式向我们诉说,才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感,才能令人流连忘返。对自然景象的感知也同样如此。“每一个物体都散发出一种人性的气息。”⑤在《艺术作为手法》中,什克洛夫斯基对“识别”与“感觉”做了区分。两者相区别的关键在于:识别活动以区分对象作为目的,它把感觉对象归类于某概念之下,并屈从于概念的权威性;而在感觉活动中,感官感觉本身即目的,它强调感觉的优先性。因此,当识别活动凭借习惯经验,以最少量的感性信息实现区分目的时,它也就舍弃了对象的丰富内涵,使物蜕变为一个空洞概念;只有当物以陌生的方式出现,吸引我们的注意,激起我们的感官活力之时,我们的感官感觉才不再受概念束缚而获得解放,石头才充分展示其感性内涵,才重新成为石头。尽管感觉活动与概念相互关联,难以剥离,但毕竟不能否认感官感觉的重要性,不能否认存在一种强调感官感觉优先性的感觉活动,而这种活动恰恰就是人将对象纳入己身、与行为相连贯的活动。 在谈到绘画时,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画了我称为脸的东西,然后再画一张,与此微有不同,你也立刻知道有差别,识别表情……比如,我谈论微笑:‘它不太真诚。’‘哦,胡说,嘴唇最多不过动了千分之一英寸,能看出来吗?’‘是的。’‘那这就是因为特定的顺序。’但不仅如此,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两张脸可以有同样的表情,可以说它们都难过,但如果我说:‘就是这个表情……’”⑥人对行为语言的感知是极其精细的,哪怕嘴边或眼角一条隐约的皱纹移动,都会被感觉到,其意义也就变化了,它显得“不太真诚”。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脸上认出相同的表情,也可以识别各种不同的表情,如微笑、冷笑、奸笑、讪笑、干笑等等,乃至语词无法分辨的细微差别。譬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人们早已从面部表情看出蒙娜丽莎的微笑不同于一般的微笑,感觉到微笑中还包含着另一种意味,但又无法以言辞表述出来,许许多多的阐释都仍然没有揭示这一神秘的微笑。人对行为(表情)的感知是极其敏锐、细致的,他分明感觉到微笑背后存在着神秘,从这一角度看,行为语言是精细的,然而,却又不能用语言加以明确阐释,因而微笑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从这个角度说,行为语言又是模糊的。 既然行为是语言,它就具有普遍可传达性;又因为它是非概念性的,也就具有模糊、朦胧的特点,并往往不被意识所直接把握,而是处在潜意识层面。在日常生活中,人常常是无意识地习得了种种行为语言,无意识地施行特定的行为方式,并直觉地解读行为之意义⑦。人的潜意识主要是由对行为语言的记忆所构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拉康所说的无意识是一种“语言结构”。在脑裂人(即左右脑半球的大部分常规传导中断)实验中,罗杰·斯佩里发现,假如图片出现在病人的右侧视野,由于人的言语功能局限于左半脑,因此病人可以相当正常地用言语描述图片;如果图片出现在左侧视野,那他就无法用言语描述。由此,斯佩里得出结论说:具有言语功能的左半脑起着“解释者”的作用,“只有这个半脑拥有高级意识,另外一个半脑虽然具有各种技能,但没有真正的意识”⑧。这就意味着语言对于人的意识的重要性,若失去言语作用,单纯的行为语言记忆也只能无声无息地沉淀在潜意识中。同样,弗洛姆也指出语言与人的意识密切关联,他认为:“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囿定在其中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⑨行为语言需要与普通语言相结合,受到语言概念的吸纳、凝聚和塑形,才构成明确的意识。但是,行为语言记忆毕竟是语言,即便处身潜意识,它仍然具有自己的语言结构。这些沉积于人的内心的行为语言,不仅构成个体潜意识,而且由于它是在社会群体中共同形成的,是相互效仿的结果,具有共享性和普遍可传达性,因而,也就是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语言,并构成了这一社会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我们所说的“直觉”能力,其实就是对行为语言的把握能力,是从人的行为中直接看出行为的意义,它不需经过语言概念,也不需经过意识并做出思考和判断,就已经了解对象。因此,我们所说的认识过程“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潜意识的直觉向语言意识过渡,是语言介入和整理的过程,它将潜意识的行为语言翻译为普通语言,并用语言逻辑做梳理和再造,使其变得有条理、明晰,但也因被语言过滤而变得贫乏。 较之于普通语言的抽象性和概念性,行为语言与人的生命及情感有着更加密切、更加直接的关联,譬如人的表情就是内心情感的标记。当我们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待表情,它是一种可传达的行为语言;而当我们把表情与人的内心感受联系在一起,则直接显示了情感,是情感的直接表达。或者可以说,人的行为是以特殊的语言方式表达的生命之形式。 作为语言的行为必须有规则可循,这就是社会规约。由于行为语言是非概念的,缺乏明晰性,因此,对行为语言的习得过程本身就缺乏精确性,每个学习者所习得的行为语言及对行为语言的理解存在个体选择和偏差,这就造成行为方式的偏移和行为语言边界的模糊。但是,人作为社会性的生物,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心理上的,更重要的是行为方式上的。正是认同使得各种偏离得以纠正,不至于漫无边际地变得无法沟通和协调,其中,仪式、习俗、传统则构成行为认同的核心,人类就通过这些活动来规范行为方式,强化对行为语言的感知,凝聚社会群体,社会规约就建立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自我界定是一切文化的活动之一。它有自己的辞藻,有一整套仪式和权威形式(全国性的欢宴、危机时刻、开国元勋、基本的文本等等)及对自身的熟悉。”⑩社会规约既在社会认同过程中形成,反过来,又不断规范社会行为,为社会认同提供依据,维护社会同一性,成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实,语言的特性也决定着社会规约对于人类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行为作为一种语言,就必须具有公共的可传达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社会”的,必然要受到社会规约的限制。 在谈到人脑对情景意义把握的机制时,詹姆斯·保罗·吉指出:从根本上说,大脑是一种熟练的模式识别者和建构者。也就是说,大脑首先主要处理从经验中提取的灵活多变的模式,而不是高度普遍化的或非语境化的规则。因此,“对人类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模式遵循的是一种‘金凤花原理’:它们不太笼统,又不太具体,情景意义是处在笼统与具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模式或概括”(11)。对人的行为语言及其规约的把握也相类似。更确切地说,对行为模式的把握应该是建构与感受、体验、理解的统一,既是建构过程,又是感受、体验、悟解的过程。建构活动以行为语言连接自我与他人,连接人与世界,建立起统一的关系,这也即同情或移情,是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一旦这个过程有语言概念强势介入,统一体就瓦解了,它转化为识别活动和认识活动。同时,社会规约并非某些抽象规则,它不可能被简化为由语言概念构成的条文,而只能是范例性的,和行为方式始终无法剥离开来。它是对行为模式“不太笼统,又不太具体”的概括,也是对原有行为的尊重,对具体行为范例自然而然的遵循,不需要刻意而为。“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12)规约业已融入人的行为,铭刻于人的身体,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的行为方式。即便新的行为可能对旧的行为模式做出这样那样的变更,甚或构成挑战,却仍然围绕着原有规约,以原有行为为参照,也就是说,在社会共同体中,各种不同行为间依然存在着特定的社会规约,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认同。这种既有力制约、规范着社会群体中每一成员的行为方式,又不能被充分意识到的社会规约,就是这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规约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类共性,又不乏特定社会群体的独特性,它塑造着特定群体的行为方式,留下这一群体独有的印记。较之于荣格、弗莱的神话原型,社会规约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既可以涵盖原型理论,以行为语言记忆及行为模式对神话原型做出解释,又可以有效探索各种社会及个体心理,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理论阐释力。也因为人的行为是惯例性的,而非按照抽象化、概念化的规则,所以对行为的判别更适宜依照具体惯例,难以仅仅根据几条规则做出机械的评判,这正是英美等国家的法律采用“判例法”的原因。当然,法律是用来判别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而社会规约则是判别“合适”与“不合适”的界限,同时,也为伦理裁决提供重要依据。 人在社会实践中掌握行为模式,习得行为语言及其规约,这个过程既不可能如同模型浇铸那样完全同一,也不是按照抽象规则建立起来而相互一致,它不能不受到个体生命的影响,是有所选择和重构、各具特征的,人的不同习性就建立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人的行为受到内心欲望的推动,是生命自身的表达;另一方面,社会行为又不能不受到社会规约的规范,因此,行为语言本身是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相互调适、制衡的结果,它身上刻写着生命个体的特征和社会规约打下的印痕。事实上,人的欲望原本只是一种弥漫性的存在,无法被人自身清醒把握,只有当欲望遭遇社会规约——无论是屈从于规约或挑战规约——时,它才成为一种可感觉、可领悟、可展示的语言方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这两者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并被个体独有的行为语言表达出来。因此,所谓个性,正是一个人独有的行为语言,它以个人的方式暗示着个体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间独有的紧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性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而对行为语言的解读,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人的独特个性,同时让我们洞悉社会规约和生命本身,进而了解特定社会对待生命个体的态度和方式。 人们惯常说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包含着很大误解。深入地看,矛盾根源于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间的冲突:欲望迫切地追求自身的满足,按照自然的方式去寻找快乐;而社会规约却告诫他,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方式,这会限制他直接实现自己的欲望。这种由社会规约塑造而成的、对于人应该如何行事的意识,即人们所说的“理智”;对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内在紧张的体验,就产生了情感。这种矛盾在托尔斯泰笔下得到生动的展现。第一次出现在姑妈家的涅赫柳多夫是一位对爱情有着朦胧向往的青年。贵族家庭的教养和校园生活的规训,使得他举止优雅、文质彬彬。重访姑妈庄园时,他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是位军官了。大都市的骄奢淫逸和军旅的放荡无羁又养成他另一种行为方式。在他内心存在着两套相互抵牾的规约和两套行为语言,并且原有的规约已经成为对过去的隐约记忆。当再次面对卡秋莎,那位纯洁、童真的姑娘不能不重新唤醒他对过去那个自我的回忆,令他内心充满矛盾:“涅赫柳多夫像所有人一样,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上的人,这个人寻求的是给别人也带来幸福的那种幸福。还有一个是动物的人,这个人寻求的只是自己个人的幸福,为了这种幸福,他随时可以牺牲天下所有人的幸福。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唤起了他心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在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疯狂时期,他身上的这个动物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完全压制了精神的人。但是见到卡秋莎后,他又产生了昔日对卡秋莎的那种感情,这时候精神的人抬起头来,声明自己的权利。在复活节前这两天中,在涅赫柳多夫身上一刻不停地进行着他本人也未意识到的内心斗争。”(13)面对不同的场域和情境,人享有不同的社会规约,由此造成内心冲突,造成风格迥异又集于一身的行为,显现出人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不仅把人的心理冲突展示得极其真切、细腻,而且对矛盾形成的根源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阐释,塑造出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 由于人的行为语言是在社会生活活动中习得的,因此,与行为语言紧紧依附在一起的社会规约也在此过程中习得了。社会规约持存在文化传统之中,持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处在文化传统与日常交往的交集地。如果说,文化传统维护着社会规约的稳定性,那么,日常交往方式的变动则促使社会规约发生蜕变。社会规约既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暗中操控社会规约,稳固或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稳固或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稳固或改变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行为语言的变化,往往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引起社会规约被改写的结果,因此,人的行为语言里有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印痕。阿尔都塞指出,人的观念即人的物质的行为,它是受到意识形态机器规训的(14)。如果更具体地看,意识形态正是渗透于社会规约之中,以此来规训、控制人的行为并调节社会关系的。“意义是一种社会行为,受社会结构的制约。我们的表达习惯是指与我们自身相似的人群的表达习惯,而这群人则是定义我们符号社会的参考群体。”(15)这种对行为的制约是一种不留痕迹、深入骨髓的掌控,较之于通过话语来宣传意识形态,它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 如今,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正在促使社会规约发生重大蜕变。一是金钱,二是互联网。这两个因素都具有吉登斯所说的巨大的“脱域”功能。金钱作为一种时空延伸的工具,将人从直接的物质交换活动中解脱出来,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分工有了可能,使城市得以集聚和扩张,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导致原有规约解体和新的社会规约重新确立。比较而言,互联网的脱域功能更强大,对社会交往关系的改变更迅速和彻底。金钱仅仅从物质交换角度入手来变更人际交往,一步步地向各个领域渐次拓展这种变化;而互联网则直接从人际关系入手,全面进入所有社会领域,迅速更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除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以间接的乃至虚拟的交往来替代,这将在短时期内扼断对传统的承袭,摧毁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规约,重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种变化也将彻底动摇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及社会规约的操控,反过来将产生出新的意识形态。 文学写作当中一个极其重要而艰难的过程,就是把行为语言转换为言语行为,把非概念语言转换为概念语言。这两者分处于潜意识和意识中,既相通相连,又存在不可通约性。言语行为在生动描摹人之行为的同时,总是无法克服语言自身的限度。康纳顿就把人的行为纳入“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以此同作为“刻写(inscribing)实践”的语言符号相区别,并认为符号不能完全替代身体行为。“有意义的实践并不与符号相合;意义不能被简化为存在于身体活动范围之外,属于另一个‘层面’的符号。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16)然而,作家的写作却无法绕过这一转换过程,作家必须把这种潜在语言转换为普通语言,同时,又能引导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触发对行为语言的记忆。文学语言的生动性、深刻性,就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召唤人重新返归行为语言,了解行为规约。文学作品描绘人物个性是否鲜明、典型,就取决于如何揭示个体独特的行为语言。但是,这种转换翻译常常难以找到适切的语言对等物,难以找到沟通桥梁,以致无法“言说”。这就是语言的困境和痛苦:“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7) 文学写作必须挑战这一困境。马尔库塞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回忆:它欲求达到一种前概念的经验和理解。而这些前概念的东西,又都再现于或相悖于经验和理解的社会功用的框架,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相悖于工具主义的理性和感性。”(18)这种“前概念的经验和理解”正是行为语言记忆。人通过前概念的行为直接和世界相关联,既经验了世界,理解了世界,又构建了自己的内在心灵。行为语言最为鲜活地展示着人的内外两个世界,文学不得不以言语行为来召唤这种前概念的行为语言。于是,当作家在转换过程中遭遇困难,以致无法对等地把行为语言直接翻译为言语行为,他所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强化言语表达过程中的“言外行为”,即一种非措辞、非概念的言语行为,迂回溯之,以此来暗示、逗引、诱发潜意识中积蓄的行为语言。这种言外行为实即“言语建构行为”,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调动人的想象,唤醒人对行为语言的记忆,并在双方相互交织中构建一个虚拟的活动世界。譬如隐喻常常以既言此又言彼、既非此又非彼的言语策略来造成内在紧张,激发人的想象,顿时击穿意识与潜意识间的隔膜,借此来诱引、召唤沉积于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并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造成回响。在言语行为中仍然残留着许多身体行为的印记,语言的旋律、节奏、语调、语气、色彩、质感、结构而非语言概念,同行为语言有着最直接的关联,甚至原本就扎根于行为语言中,因而,对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具有巨大的激发作用,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这一转换过程,在于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所构成的张力,在于言语行为对激发行为语言记忆所具有的冲击力,它使人在瞬息间意识到原本模糊、朦胧的潜意识内容,将那些隐蔽在心灵深处的奥秘揭示出来,深深地撼动人的灵魂乃至身体。 哈布瓦赫曾研究失语症与记忆的关系。他认为,失语症会造成记忆减缩,以致无法向他人成功地传达有关过去的详细看法。在症状稍轻的失语症病例中,患者因缺乏语词而不能讲述他的过去,而且对时间、地点、人物可能只保留了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其原因在于,失语症患者失去了语言能力,也就失去了以集体记忆的框架去回忆过去的能力,因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19)。这就是说,没有语言,就无法唤醒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无法显现人关于过去的记忆。只有在言语行为中给行为语言记忆赋形、定格,行为语言记忆才能明晰地在意识中浮现,并得以言说。这期间,言语习俗或惯例则是不可或缺的记忆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写作就是一个运用言语行为给行为语言记忆重新塑形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语词、语句不只是一个诱因,在它激发出行为语言的记忆之后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是与行为语言相互交织、交相发明、交互推进和深化。言语行为起着逗引、激发、组织、塑形、拓展和深化的作用;行为语言则与之相互呼应,反过来又为言语活动注入丰满的形象性和感性内涵以及新生机、新动力,共同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可以说,人的想象就是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交集的领地,而人们所说的“形象思维”正是两种语言、两种行为相协同、相融合又始终存在无法消弭的紧张的心理过程。这已经不再是对原有行为语言记忆的简单复现,而是重新发现和重新组织,行为语言业已受到叙述结构的再造而整合为连贯的形式,受到语词的吸引而凝结为莹洁的晶体,并以新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融合,因而生成了全新的境界和意义,焕发出奇光异彩。如果说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言语行为与人的现实行为相互交织交缠,共同构建着人的生活世界,并且由于人的现实行为的有限性,这个世界只能是特定的有限世界,那么,在文学活动中,潜意识中积蓄的行为语言记忆是无限的,它随言语行为的激发方式和强度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调动,而且并不局限于原有记忆。作为一种行为之语言,它完全可以重新组合和建构,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并因此构建一个开放的虚构世界,一个昭示着人的内心和外部的虚构世界。这个由行为语言参与构建的虚构世界,也因此体现着人的情感性和生命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也因如此,相对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往往有着明显的暗示性、包容性和丰富性。 萨丕尔说:“可以把语言看成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语言的流动不只和意识的内在内容相平行,并且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和它平行的,这水平面可以低到个别印象所占据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高到注意焦点里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不消说还随着心灵的一般发展而自由变化。”(20)语言同时可以奏出高低各种声部,它虽然无法舍弃概念,总是和概念牵连在一起,却又能超出概念,深入到非概念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到内心的个别印象,调动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我们所说的“语言韵味”,往往就栖息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交接部,是双方的共鸣和交响。它离不开语言又不止于语言,扎根于行为语言记忆又不止于记忆。这种能被意识所感知却又说不明白的“言外之意”,正是由言语行为所激发和照亮的行为语言记忆。由于它本身不是言语行为,因而不能被语言明确地表达;又因它不仅仅是行为语言记忆,而是受到了言语行为的启发,因而才能被意识所感知。当言语行为构筑起一个语义空间,它就为行为语言的出场提供了机缘,与此同时,行为语言则赋予言语行为以光晕和韵味,使它更为充实、丰盈、生动。但是,一旦语言陷入习惯化、自动化、逻辑化,它也就径自流逝而忘却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更丧失了激发行为语言记忆的能力,退化为枯瘦干瘪的概念运作了。 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性,即总是在整体情境中感知对象;二是选择性,即把注意力聚焦于某一对象,其余则作为背景,构成前景/背景关系;三是可转换性,当注意焦点转向另一对象,前景与背景关系就会重新组织。人与语言的关系同样如此。言语行为是运用语言概念的行为,它依赖于概念,离不开概念,却又不止于概念,语言概念并不能穷尽它,在语言的能指层面还存在着诸如旋律、节奏、声韵、质感、语气、语调等感性因素,它们都不能为概念所涵括,因此,言语行为是具有“厚度”的独特现象。而旋律、节奏等感性因素恰恰也是行为语言所共有的,是为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所共享的。在言语指涉行为中,我们着重关注语言概念,突出概念的作用,通过概念来区分对象、识别对象,发现对象的各种特征,了解其内涵,从而认识对象,而旋律、节奏、声韵、语调等感性因素仍然隐蔽在背景中,只能起着辅助性作用。言语建构行为则不同,它是语言整体的活跃状态,并因其整体性和动态,概念的边界被软化和撑破了,概念的地位被弱化了,而旋律、节奏、声韵、语调等感性因素被凸显出来,这同时也就触及了行为语言记忆,并通过这些天然的纽带,将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交织、交融在一起,将意识与潜意识相互沟通,反过来也赋予言语行为以活力和丰厚的涵义。在言语建构过程中,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是相互应和、相互生成、相互融合的,它们相聚合于人的想象之中。言语行为提升了行为语言,以意识照亮行为语言,赋予行为语言以明晰性,使人的行为不仅作为人的体验对象,而且成为可观照、可反思的对象。这不仅把个人的朦胧感觉表达出来,使那些无声无息的记忆找到了名字和定义,而且让原本沉潜着却又不时折磨着人的痛苦经验找到宣泄的出口,甚至让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共同的悲剧经历得到表述。而行为语言在充实言语行为、强化言语行为的整体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生命气息和表演天赋交付给言语行为,双方协同共创一个真切、丰美、生动的世界,一个可以栖居的真正属人的世界。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既有遮蔽性,同时又有敞开性。当人仅仅重视言语的指涉功能时,世界就被遮蔽了,世界被语言概念所分割、分隔和变形,并按照语言秩序来重构世界秩序,使世界成为“世界图像”,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对象,语言自身也因此沦为受人掌控的工具;而当言语处在建构活动中,它又将行为语言召唤出来,将人的活动及与活动密切相关的活生生的世界召唤出来,以人的行为贯通人与世界,构建一个浑整、统一的人的世界,于是,世界被敞开了。世界不再是与人相对而立、相互分隔的世界,语言也不再是工具,它们本身就和人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鱼水相依。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之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相反,唯有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这话说的是:唯在有语言的地方,才有永远变化的关于决断和劳作、关于活动和责任的领域,也才有关于专断和喧嚣、沉沦和混乱的领域。唯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22)从这个角度看,诗歌语言是本真的语言,其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强有力地召唤出行为语言记忆,并协同行为语言让存在出场,让世界敞开,共同创设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 因此,作家和诗人不应该轻视语言,更不应该刻意地去掌控语言,这将窒息语言的活力,而应该尊重语言,去倾听言语底下与言语遥相应和的窃窃私语,那流淌于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把它从隐蔽中召唤出来。也因如此,现代诗歌常常特意拧断语词间的语法关系和逻辑锁链,建立一种跳跃的、奇特的关联,其主要目的在于延滞言语行为,归还语词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凸显语言的感性特征,克服言语行为的自动化,以此去倾听、呼唤和撞击那沉睡着的行为语言,把它召唤出来。这不仅再造了言语行为自身,赋予言语行为以生动活泼的表演性,也重塑了行为语言,改造和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家、诗人甚至还能够创设独特的虚拟情景,一个充满生机的语义空间,诱使人在想象中以新的行为方式去做崭新的体验。 文学写作行为所使用的语言,是作家在日常生活和阅读活动中习得的。在此过程中,作家逐渐把握了文学语言的惯例,这是一种特殊领域中的行为规约,我们称之为“文化惯例”。这种惯例并非语法,无法设立明确、抽象的规则并通过传授规则来获得,而是对言语行为习惯的掌握。这是活生生的、变化多端的言语行为,不可能用死板、抽象的规则来限定,只能通过具体范例,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潜移默化地习得言语行为方式,或者说是领悟文学语言形式惯例。因此,文化惯例本身是不能以任何抽象规则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的,它甚至是不能被“言说”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惯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规则,它是范例性的,而非概念性、抽象性的,是非规则的规则,只能在言语行为的具体实践中加以领悟和把握,就如《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作诗,只能让她通过熟读诗歌来获得,不可能传授几条机械的规则或者写作秘诀。 苏珊·朗格说:“在诗作中见到的这种某一个别成分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多样性联系,就使得诗展示出一种类似有机结构的特征。这就证明,一件艺术品也如一个生物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假如硬是要将它的各构成成分分离开来,它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整个形象也就随之消失了。”(22)文学艺术的有机性源自行为本身所体现的生命性。生命形式的繁复多样,决定着任何抽象规则都不能对它做出限定。因此,对于文学艺术来说,那些抽象规则,诸如格律、对位、和声、透视关系、肌理等等,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格律只是对格律诗做出规定,没有格律,依然可以是好诗。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文学艺术,“游戏”是个蹩脚的比喻。游戏强调抽象规则,可以说,是抽象规则决定了游戏,区分了游戏的性质和类别。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离不开规约或惯例的约束,恰恰有可能脱离种种抽象规则。这些规则只是为文学艺术提出某些暂时性的要求,赋予某一时期、某一类型的文学艺术以特征,却并不能决定文学艺术本身。任何一条抽象规则都潜伏着使文学艺术趋于僵化的危机。规则本应有助于行为语言的表达,有助于生命的表达,而实际上,它却无法避免对千变万化的行为语言和生命形式构成限制,可能因此被抛弃。与“刚性”的抽象规则不同,规约或惯例则因为是范例性的,也就相对柔性和弹性,它赋予文学艺术以可传达性,同时,又使文学艺术葆有行为本身那种生机和活力,维护文学艺术的自由本性。 文学语言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一,也是首要的,是文学经典,包括中西方文学经典,这是读者在阅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习得的,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其二是日常生活,这是在日常会话、日常交流中习得的。这两种资源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交流。一方面,由于文学语言、日常话语这两者分别处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两个不同场域,享有不同的规约。日常话语本身就属于人的日常行为整体,和日常行为遵循同一体系的社会规约;而文学语言则处在一个特殊的场域,承袭了文学自身的传统,其惯例就势必区别于日常话语。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习得的语言经常被用于叙事作品中的对话,作为直接引语出现,虽然需要经过重新铸造才能融入作品整体语境。更重要的是,作家为了实现语言创新,一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从日常话语中汲取营养,以此来打破旧的文化惯例,重造文学语言。由于文学语言将自己分隔于日常生活之外,与日常语言相区别,与行为语言日渐隔膜,慢慢就丧失了对行为语言记忆的召唤能力,丧失了对人的亲和力;日常话语则因和日常行为享有同一体系的规约,和日常行为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一旦经过改造重铸而纳入文学语言,在新的文学语言与行为语言记忆所构成的张力关系的整体背景上,它就成为有效的沟通桥梁,并对行为语言记忆产生更强的召唤力。 由于文学鼓励创新,个体习得语言形式及文化惯例的过程,就具有更多可选择性和创造空间,并且选择和偏移的方向也更多分歧,日积月累,文学也就繁衍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现象。文化惯例则是维系这个“家族”的纽带。文学样式变化多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文化惯例不是抽象规则,它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被仿效、继承和改造,由此生成的新的文学样式尽管不断繁衍、变迁,却由于相互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依然构成一个文学“家族”。与此同时,惯例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处于不断地生成、颓败和分化、迁移的过程。在文化惯例的延续与断裂之间,文学类型的边界就开始形成了,但这种区分又只能是相对的,其边界是模糊的、变化不定的。艺术形式及惯例的习得和演变也应作如是观。 作家个人对文学语言的学习和对文化惯例的习得,受到他的个性的影响。他总是从自己的个性出发,对语言形式及文化惯例做出选择和重塑。由于个性即一个人独特的行为语言,是个体生命与社会规约相互调适的结果,因此,反映在文学语言风格上,即个体生命与社会规约、文化惯例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也即个体生命与社会规约及意识形态、文学传统及文化惯例间的相互作用(23)。文学风格是不能仅仅依据某些语词的使用频率来甄别的,更为重要的是言语行为所体现的特殊“风味”,而这恰恰是由上述三者间的张力所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恩斯坦说:“每种语言都有很多种说话方式和连贯框架,而且……这些说话方式,语言形式或编码本身随着社会关系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24)譬如“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知识者的个性得到解放,旧的社会规约对个体的约束开始被冲决,这也就同时对文学语言提出新的要求:抛弃文言及其惯例,向民间口语寻求更切近生命的表达方式,并因此酿成时代潮流。反过来,一旦文学语言及其惯例遭逢变革,并因此创造出新的语义空间,也将以新的方式召唤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进而造成个体生命与社会规约间新的冲突,使个体生命有机会获得更充分的表达。文学风格、文学形式的生生不息,就源于个体生命、社会规约、文化惯例三者间的张力,是三者关系不断调整的结果。 文学活动离不开体验。我们把参与日常生活活动称为“体验”,同时,也将文学欣赏称为“体验”。其共同之处就在于两者都涉及行为语言,是人的行为在世界中展开,将人与世界紧紧连接在一起,令人融入了世界、理解了世界、建构了世界,并且两者的融入方式和理解方式是相类似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活体验是现实行为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施行过程,而文学体验则是对行为语言记忆的重新唤起,在想象世界中展开虚拟的行为,它因构建了另一个虚构世界并生存于这个虚构世界,从而不能不专注于这个想象世界和行为自身。文学体验的真义就在于文学以言语行为唤醒了人对行为语言的记忆。我们之所以强调体验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之所以强调文学阅读的体验性,就因为它直接关联着对行为语言的把握能力和转换能力。 文学体验即通过阅读作品语言,进而唤起行为之语言,展开想象的过程,是读者调动自己的行为语言记忆,构建并投身虚构世界的过程。他亲身体验到行为的活力,领悟了行为规约,进而领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性特征。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把行为语言转换为言语行为,它揭示行为语言之力度和行为规约之深度,是衡量作品质量的重要尺度。 正如人处身不同境域会自动选择行为模式、调适行为方式,譬如公共空间、职业岗位、家庭、隐私空间、假面舞会、狂欢节广场、骚乱中心等等,个体会随不同场域对各种行为规约做出迥然不同的选择,总是自然地趋向于最少约束的方向,并与规约处于不同的紧张关系中。文学则为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场域,给人以独特的体验。文学体验的独特性在于它以独有的结构特征赋予读者双重态度:一方面,读者会遵循特定社会的行为语言及规约来构想文学的世界,按照行为语言及规约来理解所发生的行为、事件及社会;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世界是虚构的,如同为读者创设了一个私密空间,一切规约都成为虚设而对读者本人失去了规范效力,而使读者的感性生命获得解放。在谈到人的记忆活动时,哈布瓦赫指出:在记忆中,我们不只是能在各种不同的群体间信步漫游,从一个群体走到另一个群体,而且,即便我们在沉思默想中和他们厮守在一起,也不会像现实处境那般强烈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约束。原因就在于,“我们记得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已经或远或近地离开了我们,在我们的眼中,仅仅代表着死去的社会——或者至少是一个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很不相同的社会,这个往日社会里的多数清规戒律如今都已弃置不用了”(25)。如果说,在记忆中清规戒律已经失却对回忆者的规范力量,那么,在文学的想象世界中,那些社会规约只能对作品人物的行为构成约束,是读者想象事件、建构世界的依据和观照、体验、理解的对象,而不能约束读者本身,读者也因此获得新的自由。正是这种解放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人性、更符合生命本然状态的立足点,拉开了读者与作品所揭示的社会规约间的距离。原先在日常生活中业已习惯的规约,如今却凸显在读者面前,与其感性生命构成尖锐对峙,并因此受到审视、揭露和批判,从而为实现诗性正义提供了有效途径。文学阅读是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不断过渡和游移的过程,不断变换的场域致使读者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行为规约,与它们处在不同的紧张关系之中。虚构赋予读者独特的、变幻的活动场域,也赋予读者不断变化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赋予他批判意识形态的独特立场。 在谈到原始民族的诗性智慧时,维柯认为原始人没有推理能力,却浑身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诗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可是文明人不同,这种能力已退化了,其原因在于“使心智脱离感官的就是与我们近代语言中很丰富的那些抽象词相对应的那些抽象思想”(26)。其实,维柯所说的感觉力和想象力就是行为语言能力。对原始人来说,行为语言是更发达、有效的语言,正是行为语言赋予他们以诗性智慧。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抽象思维能力也发展了,行为语言在交流活动中渐渐失去重要性,并且由于它处在辅助地位和潜意识状态,更容易为人所淡忘。唯有文学为了找回语言活力和诗性智慧而始终挂念并热忱召唤着行为语言。 言语即行为,行为即语言。甚至可以说,言语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而行为则是更为基础的语言。言语在成为人的独特行为之时,赢得了自己的自由和深刻性,也因此遗落了原有的切近感和生命感。文学则试图将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结合起来,重新葆有双重优势。文学既离不开言语行为,也离不开行为语言,是两者的交汇融合,因而,它涵容着人及人的世界,涵容着人的全部历史,并让我们站在人类和人性的立场审视、思考这一切。 ①(13)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安东、南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第62页。 ②(15)(24)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阐释》,苗兴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第180页,第22页。 ③(1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第117页。 ④(1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8页,第128页。 ⑤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8页。 ⑥《维特根斯坦论美与美学》,王峰译,王峰《美学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259页。 ⑦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应手状态”与“显现状态”的区别,只有当人处在一个陌生的群体中,这个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此时,他原有的行为方式受到否定,才开始采取有意识的行为方式,同时又感觉到别扭和不适。一个人的局促不安常常根源于他感觉到自己的行为习惯与周围群体的行为存在距离,并因此受到他人的注视,他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却又限于习惯而一时难以弥合其间的裂罅。 ⑧Susan Blackmore,Consciousnes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p.72. 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⑩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页。 (11)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8页。 (14)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17)鲁迅:《野草·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8)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1—172页。 (19)(2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第88—89页。 (20)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 (2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41页。 (22)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54页。 (23)文学语言及其文化惯例本身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由于文学语言是巴赫金所说的“杂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极其复杂,故本文存而不论。 (26)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