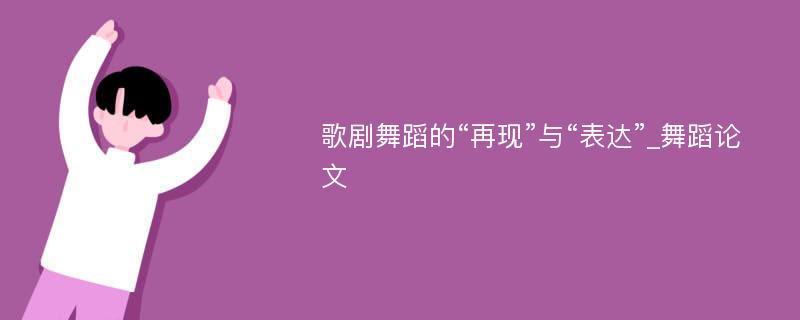
戏曲舞蹈的“再现”与“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舞蹈是人类强烈感情的外化,抒情性是舞蹈艺术内在的本质属性。一般说来,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重于表现,轻于再现。所以在美学理论中,它往往被称为“表现艺术”或者“表现的时间艺术”(参阅全国民族院校《美学十讲》)。而戏剧则不同,它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诗学·诗艺》)。也即是说,它是剧中人在被一定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所制约的一系列事件中所展开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它的本质是行动性。在以写实话剧为代表的摹象戏剧中,这种行动性是以全面摹仿生活的方式出现的,所以是一种再现艺术。
舞蹈和戏剧这种本质上的差异,给舞蹈进入戏剧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话剧舞台上,它常常体现为一种插入式、点缀式的拼贴。
中国戏曲独树一帜,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胆突破摹仿生活的羁绊,以处理舞台时空的极大自由,充分调动唱、念、做、打等各种艺术手段,“把再现方式与表现方式交叉起来,创造了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第三种方式”(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之《中国戏曲通论》第四章)。这种独特的演剧方式为舞蹈进入戏曲拓宽了道路,使其不再是一种拼贴,而是一种综合,一种融化。
但是,戏曲毕竟是戏剧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戏剧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仍然是它的基本职能。所以,“舞蹈进入戏曲后,既要演故事,就难于避免生活动作的表演。……各种艺术既进入戏曲圈子之中,都要多少改变其原来的特性以互相适应而取得协调;更主要的是要受戏剧性的制约。”(张庚《戏曲美学三题》,引自《中国戏剧》,1990年第三期)也就是说,长于抒情的舞蹈艺术,在被“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艺术综合以后,在保留其基本属性的同时,却比一般表现型舞蹈不同地肩负起了更多的描绘生活、叙述故事的责任。这是舞蹈为适应戏曲的戏剧性所发生的必然变异,是舞蹈艺术进入戏曲后由“表现”向“再现加表现”移位的一种体现。
一、戏曲舞蹈的“再现”性
确切地说,舞蹈虽为一种表现艺术,但也并不排斥对客观事物生活情状的描写。这在叙事舞蹈中自不必说;即使在抒情舞蹈中,有时为了具体、形象地抒发舞蹈者的思想感情,也往往采用一定的情节、事件和物态描写。如傣族舞蹈家刀美兰的独舞《水》,人们赞誉象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但整个“诗篇”却是通过对一位傣家少女到江边汲水、戏水、洗发、梳妆等一系列生活动作的描绘来完成的。被称为舞蹈动作诗篇的芭蕾舞片断《天鹅之死》,采用拟人化手法和形象化的舞蹈语汇,对天鹅临终时的各种体态、身姿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从而表现了天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追求。可见即使在抒情性很强的舞蹈作品中,有时也兼有描绘事物的“再现”功能。只不过这种描绘和“再现”,一般说来较为简略和概括,而且要服从于抒情性的“表现”而已。
“戏曲表演中的舞蹈与纯舞蹈的不同之处,在于舞蹈的抒情、造型和描绘等各种功能,统统必须服从戏剧性的要求。”(《中国戏曲通论》第七章)所谓戏剧性的要求,也就是要有助于推进戏剧情节发展,有利于矛盾冲突的展开,从而达到刻画人物的目的。在京剧《乌龙院》“坐楼杀惜”一折中,当宋江发觉招文袋失落后,有这样一段戏:
宋江:(内)啊!(神急气促上)哎呀且住!昨夜偶宿乌龙院中,失落了我的招文袋,内有黄金一锭,书信一封。想这黄金事小,那书信乃是晁大哥所寄,若被旁人捡去倒也还好,若被贱人拾去,我的性命休矣!这,这,这,……也罢!我不免回楼去找。
当宋江意识到这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时,剧中没有采用唱腔或过多的独白来表现他的复杂心态,而是设置了大段舞蹈化的表演:“进院,一路留神寻找,上楼。……进房后四处寻觅,不见袋子。沉思半晌,回忆方才取袋、挟袋、取衣、开门时的动作,肯定了袋子是在开门时遗落的。想到一定是被阎惜姣拾去了,更形焦急。”这段表演以非常形象而生动的舞蹈语汇,描绘了宋江焦急万分、惊恐慌乱的心理动作,为下一步的剧情发展——“从“求惜”到“杀惜”,起到了有力的铺垫作用。这是戏曲舞蹈为戏剧性服务,显示其“再现”功能的成功范例。
为了使舞蹈表演戏剧化,中国戏曲创造了一系列再现生活的规则性动作,即表演程式。它来源于生活,使人们一看便知其特定的指代意义,如开门关门、上楼下楼、穿针引线、走马行船等等;但它又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超越了生活真实的摹仿,使其具有了造型美感、节奏美感等舞蹈特质。如京剧《拾玉镯》中孙玉姣的放鸡、喂鸡、绣花、拾镯等一连串的舞蹈表演,既是生活的,使人倍感亲切;又是艺术的,处处闪射着戏曲程式的韵律之美。
在戏曲表演程式中,除了大量普遍用于指代具体生产内容的动作外,还有一部分高度夸张的技巧性动作,如筋斗、旋子、朝天蹬、铁门槛、卧鱼……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生活动作的提炼,但却跟武术、杂技及古典舞蹈有着不可割离的联系,是社会生活的间接反映。而这些动作一旦跟具体的戏曲内容相结合,就可以起到描物状情的艺术效果。如武打戏里的翻滚跌扑,可以表示战争的紧张激烈;某些戏里的“变脸”、“火功”,可以表示剧中人的神通广大……技巧性程式动作的运用,若能与戏曲情节有机结合,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在昆曲《十五贯》中,当娄阿鼠听到况钟假扮的测字先生道出“老鼠偷油(尤)”而猛然一惊时,扮演娄阿鼠的昆曲名丑王传淞,用了一个从长凳上“倒扎虎”翻下又从凳底下钻出而四处窥视的动作,形象地刻画了娄阿鼠作贼心虚的精神状态;在桂剧《打棍出箱》中,演员运用在大木箱一阖一开的瞬间翻腾出入并变换衣服的高难度技巧,夸张地描绘了范仲禹在遭受巨大打击和惊吓后的疯癫痴狂。
戏曲舞蹈的“再现”与戏剧性的统一,显示了戏曲以歌舞化艺术方法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中国戏曲始终坚持以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牢牢把握戏剧行动的“再现”性,同时在舞台动作的运用上又高度艺术化,在长期的实践中走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二、戏曲舞蹈的“表现”性
戏曲舞蹈在为戏剧性服务,实现了更多的“再现”功能的同时,其作为舞蹈艺术的基本属性——“表现”性,并未因此而消失。在戏剧冲突发展的进程中,有时反而借助于剧情而使人物的情感抒发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戏曲传统剧目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或高潮戏,往往就是人物情感最为激荡饱满的舞蹈场面。如京剧《徐策跑城》,当老臣徐策见到二十年前遭受残害的薛门之后终于重振雄风而兵临城下之时,惊喜若狂,急于禀告朝廷而为薛家平冤。他一边唱着“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一边不顾老迈之躯而奋力奔走。只见那帽翅与白髯共舞,袍带与水袖齐飞,优美的舞蹈把人物兴奋激动的心情渲泄得淋漓尽致。“仿佛一笔大草字,一泻千里”(《周信芳文集》)。
《徐策跑城》里这段精妙绝伦的舞蹈,生动而形象地证明了我国古代所谓“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经·大序》)这一舞蹈生发理论的正确性。中国的文学艺术历来既强调“观物取象”的现实主义原则,又重视“诗言志”这种反映生活的方法。“志也者,情也”(董解元《西厢记》题辞)。言志就是言情,中国戏曲追求“情真”,与中国绘画所讲究的“神似”一样,是艺术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反映,这一点与西方写实话剧所追求的“形真”与“摹仿”不同。正是基于这一点,戏曲舞蹈在展现戏剧冲突、塑造戏剧人物的创造活动中,赢得了广阔而自由的空间。人们在观赏《挑滑车》、《战冀州》这类武戏中蹉步、跳叉、跺子、转体僵尸等武功表演,以及《天女散花》、《贵妃醉酒》中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长绸舞以及下腰、卧鱼等舞台造型时,除了为演员的高深技艺所折服、赞叹外,感受到的是古代武将的英雄气概以及仙女、贵妃的美丽神韵。谁还会去深究这些动作和造型是否合乎生活常规呢?
中国戏曲作为一种“剧诗”,总是带有浓厚的作家主观意志色彩。正如李贽评《西厢记》所言:“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一情,触目兴叹,压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李贽《杂说·焚书》)当然,这种发自戏曲诗人内心的主观情感,除了由古代戏曲中的“副未”登场作直接表白,以及古今通用的帮腔、伴唱等形式进行表现外,更多的却是通过剧中人物的舞台动作(包括心理动作)来完成的。而作为人物心理外化的戏曲舞蹈,便是抒发人物情感、表现作家意志的一种有效手段。晋剧演员田桂兰在《打神告庙》中扮演敫桂英时,利用三尺长的水袖,以冲、抛、抡、打、甩等种种技法,将一个受欺凌女子的绝望、痛苦及火山般迸发而出的愤懑作了尽情的渲染,同时较好地抒发了剧本作者对封建时代妇女命运的同情和感概。这种着力于展示人物内心冲突所引发的戏剧效果,在诸如《琵琶记》里的“描容上路”、《荆钗记》里的“刁窗”、《宝剑记》里的“夜奔”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它虽然不在于描写人物与人物面对面的斗争,但却由于人物心理动作的丰富和抒情效果的浓烈,而达到了完美的戏剧性。
世界著名哲学家、美学理论家黑格尔曾经指出:“真正的戏剧性在于由剧中人物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的分裂之中的心事话。”(《美学》第三卷)戏曲舞蹈,便是说出戏曲人物“心事话”、寄托剧作家主观情志的一种艺术手段,其“表现”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再现”基础上的“表现”
戏曲舞蹈从总体上说,既是戏剧化的,又是抒情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其表现形态又依剧情的需要而又多种多样,其功能也各有侧重。有时它偏于描绘,有时则重于抒发情感。或描绘中见抒情,抒情中带描绘,或两者并重,兼而有之。为了便于分析比较,我们不妨按其侧重点的不同而将其分为以下四种常见类型:
1、生活程式型。这种类型泛指以再现生活动作为主的程式化舞蹈,即以手、眼、身、法、步为基本元素组成的一系列表演符号。它是戏曲表演中最小的单元动作,是生活动作的舞蹈化。在舞台演出中它可以单独成段成块地组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生活内容。如《拾玉镯》以成套的做功来表达男女初恋,《三岔口》以摸黑开打展开一场误会冲突等;但更多的时候它是呈散见状态,与唱、念结合来描绘情节和人物。无论生、旦、净、丑各种行当的戏曲人物,只要往台上一戳一站,或一举手一投足,均带有明显的程式韵律。生活程式型舞蹈可以说是戏曲演出中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见的舞蹈化表演。由于它以描绘事物、叙述生活过程为主,所以更多体现为“再现”性质。
2、技艺表演型。它专指戏曲演出中展示特殊技巧的舞蹈化表演,如种类繁多的毯子功、把子功、水袖功、椅子功、火功……等等。技艺表演型舞蹈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刻画人物、抒发情感服务(如前面提到的《十五贯》、《打神告庙》中技巧性动作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直接服务于观众的技艺欣赏要求。“欣赏戏曲,有一个与欣赏话剧不相同的特点;观众在关心剧中人物命运的同时,还在欣赏演员艺术功力的美,……有时表演有惊人的绝技使一个剧中人产生了迷人的风度。”(张庚《戏曲美学三题》)这是中国戏曲演出和审美活动中一种特殊的现象,是戏曲反映生活而又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感所带来的审美特性。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表演者与两个被表演者”(《论中国人的戏剧》,转引自《中国戏曲通论》第597页)的关系,即演员既扮演角色,又表演自己。技艺表演型舞蹈从展示演员功力、塑造剧中人物这双重职能来看,它既是“表现”的,又是“再现”的,是一种“表现加再现”的舞蹈类型。
3、叙事寓情型。这种类型从形式上看是在描述事物的发展过程,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叙述和交待,而是在描述过程中融入了人物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因而又是抒情的,是寓情于事,以事见情。如《乌龙院》中宋江寻找招文袋一段舞蹈,它是叙事的,所有舞台动作都具有明确的指代意义,形象地描述了宋江“四处寻觅”以及回忆判断的过程;然而它又是抒情的,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宋江意识到大祸将至时的惊恐和焦急。川剧《秋江》的行船舞蹈也可以说是叙事的,生动地再现了剧中人从上舟到追舟的情景,使人如闻其水,如见其舟;然而它又通过大量戏曲化的舞蹈语汇,表现了陈妙常与艄翁两个人纯情与善良、一庄一谐的人物个性以及幽默风趣的喜剧情调。这种舞蹈非常巧妙而有机地把叙事与抒情统一起来,达到了高度的戏剧化,具有“再现加表现”的性质。
4、烘托点缀型。此类舞蹈在戏曲演出中常以独立段落出现,它与剧情和人物的联系较之前面三种要为间接一些。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剧中所要塑造的人物往往并不加入舞蹈行列,而是另由舞队来完成,具有“伴舞”的特质;标志之二是它的戏剧性较弱,甚至使剧情暂时中断而变成几乎是纯粹的舞蹈表演。其作用主要用来烘托气氛,点缀环境,增强舞台色彩。如表现宫廷庆典的仕女舞、出征场面的武士舞、妖魔世界的鬼怪舞,以及形形色色的土风舞、祭祀舞、少数民族舞等等。由于它只作用于渲染气氛和情绪,很少具备描绘事件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属于一种“表现”性质的舞蹈。
中国戏曲常用种类,大抵可以归纳为上述四种类型(个别正在探索中的特殊类型下文将另有阐述)。如果我们将其各自的功能、与生活的关系、戏剧性的强弱以及艺术方法作一番比较,那么大致可以从下面表格中一目了然:
戏曲舞蹈类型比较表
舞蹈形式艺术功能与生活的关系戏剧性艺术方法
生活程式型 描绘生活 直接强 再现
叙述事件
技艺表演型 展示技艺 间接强表现+再现
刻画人物
叙事寓情型 叙述事件 直接强再现+表现
抒发情感
烘托点缀型 烘托气氛 间接弱 表现
通过列表比较不难看出,在戏曲舞蹈诸形态中,大凡具备“再现”性质的舞蹈,如“生活程式型”、“技艺表演型”和“叙事寓情型”,其戏剧性相对较强;反之如“烘托点缀型”一类,由于缺少“再现”性,其戏剧性也相对较弱。——这一有趣的发现使我们涉及到了戏曲艺术方法的实质,即“戏曲所完成的再现与表现的结合,简约地说,就是再现性的舞台行动与表现性的舞台动作的结合。它以再现性的舞台行动为基础,又在这一基础上充分发挥舞台动作的表现技能,实现了再现性基础上的表现这个第三种方式”(《中国戏曲通论》第四章)。对于戏曲舞蹈这种特殊的“舞台动作”而言,虽然它们类型不同,功能也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们的最高宗旨仍然是必须为人物的“舞台行动”——即戏剧情节服务。只有这样,戏曲舞蹈才真正具备了戏剧性,才真正完成了由纯舞蹈向戏曲舞蹈的综合或融化。“再现基础上的表现”这一戏曲艺术方法实质的科学性归纳,象一块明镜,为我们判别戏曲舞蹈的优劣成败提供了借鉴,排除了种种疑虑和纷扰。也为戏曲舞蹈的创作实践及其探索,打开了一道科学之门。
四、戏曲舞蹈在当代戏曲中的运用与发展
中国当代戏曲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的探索过程。这种探索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以及多种文艺形式的竞争,而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特点。但戏曲无论怎样革新,其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征却不会改变,并且在舞台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戏曲舞蹈在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以及整理改编的古代戏剧目中的广泛运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对传统表演程式的利用、改造,以及开拓表现当代生活的戏曲舞蹈新形式两个方面。
传统表演程式对于新编历史剧及整理改编的古代戏而言,由于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与传统戏并无两样,因而运用起来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一点有许多成功的剧目已经作出了范例。如莆仙戏《春草闯堂》中对花旦表演程式的运用,京剧《曹操与杨修》中对花脸表演程式的运用,蒲剧《关公与貂蝉》中对红生表演程式的运用等等。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对旧程式加以改造,使其更加切合剧目内容需要的问题。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三角小眼能洞察细微,歪脖驼背受得住重压,短手短脚可以干出非凡大事”的新丑角形象。但在对传统丑角表演程式的运用上,除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造,还从人物性格出发而增加了许多生活化的表演,因而并不给人以雷同感觉。川剧《芙蓉花仙》能够上演两千多场而饮誉海内外,除了剧目内容以及舞美等因素的吸引力外,恐怕与其在继承川剧传统表演程式和技法的同时,大量吸收融化魔术技巧和现代舞蹈手法分不开的。
在现代题材剧目中,由于所反映的时代不同,人物的装束和生活方式(包括某些行为方式)也不同,对旧的表演程式的利用相对要费劲一些,而且具有更多的创造色彩。据说李少春扮演京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时,起初觉得挪用旧程式很难,他设计的一些动作不是“飘”了就是“溜”了。后来经过认真分析角色,体验情感,终于找到了利用和改造旧程式来表现时代人物的可行路子。不仅使“小滚背”、“小翻身”这些动作真正属于杨白劳,而且在表现杨白劳之死时用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吊毛”动作,既增加了舞台美感,又较好地表现了人物悲愤而死的情感。实践证明,利用和改造旧程式来演出现代戏并非不可行。问题在于我们把目光投向戏曲表演程式的“规范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要求演员在创造角色时,应该从生活出发,对传统程式进行认真的比较、选择和利用,并根据生活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造,甚至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对传统的原样搬演。著名戏曲导演艺术家阿甲说过:“生活总是要冲破程式,程式总是要规范生活。这两者之间,老是打不清的官司。要正确解决这个矛盾,不是互相让步,而是要互相渗透。从程式方面来说……修改自己不合理的规矩,克服自己的凝固性;从生活方面来说,要克服自己散漫无组织的、不突出的自然形态,要学习大雅之堂的斯文驯雅……一句话,就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对待生活和程式的关系,这样才能使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一致起来。”(阿甲《戏曲表演论集》)这可以说是当代戏曲利用和改造传统表演程式的经验之谈。
开拓表现当代生活的戏曲舞蹈新形式,是当代戏曲探索革新中的一大贡献。在传统的表演程式已不能满足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时,许多有志于推进戏曲表演艺术发展的艺术家们作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早在六十年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以一曲旋律奔放、造型优美、动感很强的“滑雪舞”而轰动了京剧舞台。这段舞蹈的基本动律直接从生活中的滑雪动作加以提炼,并使之与戏曲武功相结合;音乐上将创新的旋律与京剧板式、交响乐的和声、织体有机融合,给人以既戏曲化又耳目一新的感觉。八十年代,汉剧《弹吉它的姑娘》又以一曲别开生面的“打电话舞”而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它通过几个人手持听筒边舞边唱,在迪斯科的动律中完成了对话交流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观赏效果和戏剧性。其它再如京剧《药王庙传奇》中的“轮椅舞”,评剧《高山下的花环》的“战斗舞”,以及近年戏曲舞台上频频出现的“自行车舞”“溜冰舞”……等等。这些舞蹈已大大超越了原有程式的羁绊,在源于生活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了当代舞蹈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并使之尽量与戏曲的韵律、风格相结合,拓展了戏曲舞蹈表现当代生活的空间。
这里还需提及,无论在新编历史剧(古代戏)或现代戏的二度创作中,戏曲舞蹈的探索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的。除了前面已进行列表比较的几种常用类型外,还有一种“心理符号型”舞蹈,它在剧中作为一种心理和意念的象征,并常常代表着作者的主观评判。如在桂剧《泥马泪》中,李马撞头而死时,舞台上出现了大批象征马群的白衣人向他冲来,使造神反被神所害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在川剧《红楼惊梦》中,编导者曾让全身披红的演员代表巨大的、难以回避的“红柱子”,到处拦截逃命的瑞珠,象征着封建势力对人的禁锢和迫害。而在云南花灯剧《淡淡的茴香花》中“绣嫁衣”一场戏,流动的舞蹈画面时而组合成女主人公玉秀意念中的石林,时而又变成一幅幅美丽的彝族服饰图案,表现了“但愿他人好花好,抽我心丝绣月圆”的主题意蕴。“心理符号型”舞蹈虽然也具有由专门舞蹈队伴舞并独立成段的特点,但又不同于“烘托点缀型”那样仅用于点缀气氛、色彩,它是人物命运的变形再现,又是剧作家主观情志的浓缩表现,所以是一种特殊的类型。
戏曲舞蹈在当代戏曲中的运用及其探索,总的说来成绩是可观的,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当然,既然是探索,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误,也相对积累了一些失败的教训。首先最明显的例子是,不顾剧情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而无端地增加舞蹈场面,而且大多体现为“烘托点缀型”舞蹈的大量采用。正所谓“戏不够,舞来凑”。殊不知过多表现型舞蹈的填入,往往减弱了戏曲的再现力度,冲淡了戏剧悬念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结果反而更加“没戏”,起到事倍功半或适得其反的效果。更有甚者,有的编导纯属为了展示“阵容”或炫耀“包装”,而苦心编排大量舞蹈场面,把一个本来只需七、八个人或十几个人便可演出的本子,硬弄成几十号、上百人参加演出的大队伍、大装备。这些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为戏增色,却反而既损害剧本,又增加了演出困难,是不可取的。从艺术方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对戏曲舞蹈的性质及功能缺乏全面把握所导致的失误。其次,另一种相反的做法则是“话剧加唱”使戏缺乏歌和舞,客观上却抽掉了戏曲审美的独立品格,失掉了自己存在的根基和竞争优势。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失误,其实质仍然是对戏曲舞蹈功能乃至戏曲艺术歌舞化表演特质认识不足的反映。
戏曲舞蹈在当代戏曲中的运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呈现出多思维、多视角、多形式的异彩纷呈的局面。从它的发展及其经验与教训不难看出,在纷纭复杂的探索现象中,“戏剧性”仍然是戏曲舞蹈所必需遵从的共同要求,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它要求戏曲舞蹈从生活出发,着力于戏剧情节和人物刻画的实际需要,深刻把握“再现基础上的表现”这一戏曲艺术方法的实质,创造出更多生动感人的舞台艺术形象,为中国当代戏曲的发展增光添彩。
标签:舞蹈论文; 戏剧论文; 艺术论文; 京剧演出论文; 再现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京剧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