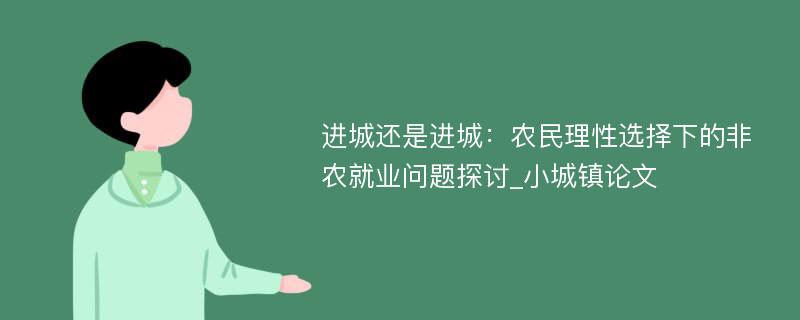
进镇还是进城:农民理性选择下的非农就业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问题论文,非农论文,理性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主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村人口的超大规模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农民先向小城镇转移而后逐步转往小、中、大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方式,可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迫不得已的路径选择。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重要意义也许正在于此。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小城镇建设,已历时近20年。目前学术界在小城镇发展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有人认为,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是以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就地非农化为核心的封闭式城市发展模式,即遵循“乡镇工业→乡村工业化→小城镇→乡镇(人口)城市化”的路经[1]。由此而来问题是,这些建制镇人口少,经济规模净收益小,故非农就业容量不足。另有人指出,小城镇聚集的人口少,不能产生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经济效益,故难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2],我国城镇人口规模偏小的弊端在于城市规模净收益的流失并使我国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3]。还有学者对西部城市周边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实证分析显示,乡—镇与乡—城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民进城或进镇的主要因素[4]。笔者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农村调查中发现,新设置的小城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名无实的“空壳”镇。这些镇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对周边农村要素资源的集聚能力弱,难以发挥吸纳农民入镇定居的功能[5]。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小城镇持肯定意见:李宝库认为,“发展小城镇是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6],董鉴泓认为“小城镇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富余人员,避免盲目流入大城市”[7];高红贵强调,“小城镇建设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客观要求”[8]。目前对有关小城镇问题的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一,对小城镇发展与非农产业、就业之间的关系缺少定量分析[9];其二,有关小城镇的概念比较含混,有的研究未将(作为行政单位的)镇域(实际上包括了镇所辖的乡村和镇所辖的镇区)与建制镇镇区相区别[10],因而导致对小城镇人口和劳动力非农化状况描述地失真;其三,缺乏根据全国普查资料对小城镇(即建制镇镇区)规模与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全面分析及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由于这些欠缺,使人们很难对小城镇建设的成败做出事实的判断。笔者希望通过经验分析弥补不足。本文着重探讨与城镇,特别是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1)城(市)、建制镇人口规模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2)小城镇扩张与其非农第二、三产业变动之间的关系;(3)定量分析全国和区域间非农产业发展与小城镇非农就业的关系。必须着重指出,本文所界定的小城镇是指经国家批准设立的建制镇的镇区而不是作为行政单位的镇域;且文中提及的小城镇、镇均指建制镇的镇区。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1990年第四次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镇、乡村普查登记的人口数(短表)以及城市、镇、乡村抽样调查按行业分类的就业人口数(长表)以及国家统计局、农业部编印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相关社会—经济资料,统计分析的基本单位(case)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表11990年、200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市、镇、乡村就业人口分布比例(%)
┌───┬───────────┬───────────┬───────────┐
│ │市就业人口│镇就业人口│乡村就业人口 │
│ ├─────┬─────┼─────┬─────┼─────┬─────┤
│ │农业 │ 非农业 │ 农业│ 非农业 │ 农业│ 非农业 │
├───┴─────┴─────┴─────┴─────┴─────┴─────┤
│ 1990年
│
├───┬─────┬─────┬─────┬─────┬─────┬─────┤
│ 全国│ 26.18
│73.82 │16.62 │83.38 │89.09 │10.91 │
│ 东部│ 23.68
│76.32 │20.67 │79.33 │84.82 │15.18 │
│ 中部│ 24.37
│75.63 │13.49 │86.51 │85.9 │14.1 │
│ 西部│ 36.79
│63.21 │12.23 │87.77 │93.37 │6.63 │
├───┴─────┴─────┴─────┴─────┴─────┴─────┤
│ 2000年
│
├───┬─────┬─────┬─────┬─────┬─────┬─────┤
│ 全国│14.34 │85.66 │31.88 │68.12 │85.24 │14.76 │
│ 东部│11.67 │88.33 │30.76 │69.24 │77.53 │22.47 │
│ 中部│16.77 │83.23 │32.07 │67.93 │89.03 │10.97 │
│ 西部│19.76 │80.24 │34.55 │65.45 │91.27 │8.73 │
└───┴─────┴─────┴─────┴─────┴─────┴─────┘
本文中关于城市、镇、乡村的界定均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11]为划分标准予以确定,此不一一赘述。另须说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所列城市、镇、乡村按行业分类的就业人口数(即长表4—1a、1b、1c)系9.50%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与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为普查实数是不相同的)。为了便于比较,文中2000年抽样调查数据已按统计学的点估计方法还原为实数。
二、小城镇与城市、乡村非农就业容量变动比较
全国。1990年以来我国镇与城市人口规模都有较大幅度增加,镇由1990年的11329个增加到2000年的19692个,其总人口由8492万增加到16614万,净增95.6%;城市(含大、中、小城市)则由456个增加到659个,其总人口由21122万增加到29263万,净增38.5%;同期乡村总人口由83437万减少到78384万,净减少6.0%。从表面上看,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深入的考察会发现市区、镇区人口规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非农人口,特别是非农就业人口的等速增加。事实上,1990~2000年间全国镇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仅由3818万增加到5763万,净增率为50.9%,城市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由12060万增加到14345万,净增率仅为18.9%,均低于人口规模的增加幅度。如表2所示,全国镇的平均人口规模虽然由1990年的3816人/镇增加到2000年的4296人/镇,但平均每个镇非农就业人数却从3370人/镇降为2972人/镇(平均减少11.8%);我们注意到,1990~2000年间市、镇、乡村净增加的非农就业人口6031万中,乡村非农就业人数净增加了1801万,在总增量中占30%。市、镇、乡村非农就业人数占全国总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1990年分别为49.55%、21.25%和29.19%,若以镇为1,则三者之比为2.33∶1∶1.37;2000年分别为49.0%、22.98%和28.02%,三者之比为2.13∶1∶1.22。(见表3)。
表2200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市、镇平均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人数比较
┌────┬─────────────────────────────────┐
││
市就业人口 │
│├──────┬──────┬────┬──────┬───────┤
││ 地县级市数│ 总人数│ 人/市 │ 非农人数 │ 非农人数/市 │
├────┼──────┼──────┼────┼──────┼───────┤
│ 全国 │659 │ 143450347 │ 217679│ 122881979 │186467│
│ 东部 │293 │ 81139547 │ 276927│71674221│244622│
│ 中部 │265 │ 40415611 │ 152512│33638842│126939│
│ 西部 │134 │ 21895189 │ 163397│17568916│131111│
├────┼──────┴──────┴────┴──────┴───────┤
││镇就业人口│
│├──────┬──────┬────┬──────┬───────┤
││建制镇数│ 总人数│ 人/镇 │ 非农人数 │ 非农人数/镇 │
├────┼──────┼──────┼────┼──────┼───────┤
│ 全国 │19692
│ 84594358 │ 4296 │ 57628063 │2927 │
│ 东部 │8655│ 43407600 │ 5015 │ 30054463 │3473 │
│ 中部 │6000│ 24834316 │ 4139 │ 16870347 │2812 │
│ 西部 │5037│ 16352442 │ 3246 │ 1016809
│2125 │
└────┴──────┴──────┴────┴──────┴───────┘
表31990年、200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市、镇、乡村非农就业人口比例
┌──────────────────────────────┐
│ 1990年│
├─────────────────┬────────────┤
│非农就业比例(%)│镇非农就业=1│
├─────┬─────┬─────┼─────┬──────┤
│市│镇│乡村 │市│乡村│
├─────┼─────┼─────┼─────┼──────┤
│49.55 │21.25 │29.19 │2.33 │1.37│
├─────┼─────┼─────┼─────┼──────┤
│50.56 │18.64 │30.8 │2.71 │1.65│
├─────┼─────┼─────┼─────┼──────┤
│43.88 │19.95 │36.16 │2.2
│1.81│
├─────┼─────┼─────┼─────┼──────┤
│45.53 │26.5 │27.97 │1.72 │1.06│
├─────┴─────┴─────┴─────┴──────┤
│ 2000年│
├─────┬─────┬─────┬─────┬──────┤
│49│22.98 │28.02 │2.13 │1.22│
├─────┼─────┼─────┼─────┼──────┤
│50.31 │21.1 │28.59 │2.38 │1.36│
├─────┼─────┼─────┼─────┼──────┤
│48.61 │24.38 │27.01 │1.99 │1.11│
├─────┼─────┼─────┼─────┼──────┤
│44.92 │27.36 │27.72 │1.64 │1.01│
└─────┴─────┴─────┴─────┴──────┘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10年间的全国城镇化建设主要限于市以及建制镇数量的增多,辖区范围的扩展,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市区、镇区统计范围之内,而每一市、镇容纳非农就业人口的能力并无大的变化。上述统计描述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即此间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撤乡建镇”、“撤县建市”的城镇化活动,具有“外延式”或“圈地型”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从非农就业容量的角度看,此间乡村容纳非农就业总量始终大于建制镇。
大区比较。1990~2000年间,东、中、西部镇数分别增加3136、2009、2548个,净增率分别为56.8%、50.3%、102%;地、县级市分别增加122、74、41个。全国市和镇的总就业人数和非农就业人数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除东部地区外,镇的平均非农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中部平均每镇减少550人,降幅为16.3%;西部平均每镇减少971人,降幅为31.3%;市的降幅则分别为17.9%、7.9%。惟东部地区的镇和市平均非农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83人/镇和2980人/市,其增幅分别为12.4%和13.9%(见表2)。从1990~2000年东、中、西部建制镇、市与乡村农业和非农业就业人口分布(表1)的变化看,镇非农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下降10个、19个和22个百分点;市非农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上升12个、8个和17个百分点;乡村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东、西部分别增加7个、2个百分点,中部则减少4个百分点。故东、中、西部镇、市、乡村的非农就业人口的比例1990年分别为1∶2.71∶1.65,1∶2.20∶1.81,1∶1.72∶1.06;2000年分别为1∶2.38∶1.36,1∶1.99∶1.11,1∶1.64∶1.01(表3)。这些数据反映,10年之间各大区域市、镇、乡村吸纳劳动力非就业的能力和位次并未改变,即城市仍然是非农就业容量之重头,而乡村的非农就业容量仍或约高于镇(表3)。
东、中、西部的镇、市、乡村的非农就业容量之差异是:①东部地、县级市的平均非农就业容量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2000年分别为中、西部的1.23倍和1.63倍),且10年间呈上升趋势,这与中、西部城市容纳非农就业人口的功能弱化形成鲜明对照。②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等省(市)镇的平均非农人口分别为5678人/镇、6306人/镇、4468人/镇和4860人/镇,而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如重庆市、四川、湖北、湖南)镇的平均非农人口一般只有2000人/镇左右。反倒是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边远省(区)镇的平均非农人口达3831~6574人/镇。
形成上述特点和差异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首先,上世纪90年代东部与中、西部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中、西部省份在经济竞争中逐渐“边缘化”(即大量国内外资本不能进入内陆中西部省份,而大批中西部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农村劳动力又不断涌向东部发达省分),造成产业经济,特别是乡镇非农产业经济的弱化;其次,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等省、市地处我国沿海的“长三角”、“京津唐”、“珠三角”等三大产业经济圈,引进外资早,乡镇工业发展基础好。如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大批乡镇是我国最早的“三资”企业生产基地;而浙江的温州、宁波地区则是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到上世纪90年代,这些地区乡镇产业经济发展势头更盛;而中、西部无产业支撑的镇,即使数量增多,但难于聚集“人气”,因而成为“空壳”镇。反观地广人稀的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规划设立的建制镇数目少(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仅有124个建制镇;青海72万平方公里仅有40个;宁夏17万平方公里64个;内蒙古自治区40多万平方公里仅有341个镇),人口多集中在已有商贸、行政基础的(县)城关镇或其他规模较大的镇,反倒能够聚集“人气”,吸纳较多的非农劳动力。
非农就业结构变动比较。在同一统计口径下,1990~2000年间我国建制镇镇区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已有显著变化。从全国看,镇已在非农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上升约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则相应下降同样的百分点)。但从大区看,东、中、西部则各有不同,东部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略有下降(减少约2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均分别增加4和12个百分点。东部与中、西部镇区的非农就业结构变化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经济的扩张使建制镇已在10年间成为工业制造业的集聚之地,这里的镇实际上成为经济圈内从事加工工业的卫星镇(因为镇区和乡村的地价及各种费税一般比城市便宜)。以广东省为例。1990~2000年间,建制镇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由于同样的原因,就连广东省乡村(即镇区以外的乡、集镇)也大量吸纳大批本地和外省农村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业,致使广东成为全国主要的人口流入地。据2000年人口普查,仅四川一省流入广东省的人口就达285万,占四川流往省外人口的41%,占广东省吸纳外来流入总人口的18.9%。仅2000年,广东乡村的第二产业就业比例比1990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达到73.84%。事实上,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1》提供的数据,2000年在该省76.7万个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已达928.3万人,其产值(按当年价计算)为9223.5亿元。与此相对照,中部和西部镇的非农就业结构趋同,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之比均为1∶3。中、西部小城镇这种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非农就业结构特征,可以解释为缺乏东部那样的工业制造业扩张的环境和机遇所致。以西部的四川省为例,1990~2000年间,建制镇镇区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例上升约15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就业则下降同样比例。事实上,四川省2000年乡镇企业产值不到广东省的一半(48%),其中四川乡镇企业工业产值不及广东的1/3(31%)。东部与中、西部镇的劳动力非农就业结构的差异反映出,东部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的扩张是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为基础的实业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的小城镇发展具有较为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不存在中、西部省区小城镇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东部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扩张,使1990~2000年间城市非农就业中第二产业的比例也一直处于上升势头,城市第二产业就业比例2000年比1990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
三、小城镇非农就业的产业基础:相关与回归分析
通过经验观察,我们发现小城镇非农化就业容量与非农产业发展之间某种的关联性。现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对1990~2000年小城镇非农就业及其相关经济因素作统计分析(见表4)。
表41990、2000年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与产业经济因素相关系数比较
┌─────────┬─────────────┬────────┬───────┐
│ │相关系数(R) ││ │
│因变量│ │Sig.
│
样本数(N)│
│ │(自变量:镇非农就业人口)││ │
├─────────┼─────┬───────┼───┬────┼───┬───┤
│ │2000年│1999年│2000年│1999年 │2000年│1999年│
│ ├─────┼───────┼───┼────┼───┼───┤
│镇非农就业人口│1.000 │1.000 │.000 │ .000 │ 31 │ 30 │
│GDP或GNP产│0.870**
│0.865**
│.000 │ .000 │ 31 │ 30 │
│第二、三产业产值 │0.856**
│0.728**
│.000 │ .000 │ 31 │ 30 │
│乡镇非农产值 │0.779**
│0.691**
│.000 │ .000 │ 31 │ 30 │
│乡镇第二产业值│0.780**
│
- │.000 │-
│ 31 │
- │
│乡镇第三产业值│0.472**
│
- │.000 │-
│ 31 │
- │
└─────────┴─────┴───────┴───┴────┴───┴───┘
首先,全国小城镇非农业就业量与GDP的关系。如表4所示,二者之间存在统计显著性和高度地相关性(1990和2000年分别为0.865和0.870)。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小城镇可容纳非农就业的数量愈大。深入地考察它与GDP产值中第二、三产业的相关性,便可发现在同样条件下2000年二者的相关程度比1990年有所增大(1990年R=0.728,2000年R=0.856),换言之,在全国范围内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对第二、三产业的依存度进一步增大。
其次,进一步分析发现,小城镇非农就业的容纳能力实际上更大程度取决于乡镇企业产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如表4所示,镇非农就业量与乡镇企业产值的相关程度2000年已比1990年有较大的提高(1990年R=0.691,2000年R=0.779)。据此可以解释若无乡镇第二、三产业扩张,就不可能有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的增长。换言之,在没有乡镇非农产业的小城镇,劳动力找不到就业机会,“人气”很难集聚。
再其次,深入研究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与乡镇产业经济内部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发现,2000年全国镇的非农就业人口主要与第二产业乡镇企业产值存在高度的相关(R=0.780)而与第三产业的乡镇非农产值低度相关(R=0.472),虽然二者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由此我们推断:到2000年为止,小城镇非农就业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小城镇第二产业,即工业制造业的存在与发展。
最后,根据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并配合经验事实,我们以2000年乡镇第二、三产业产值为自变量,镇非农就业人口为因变量建立如下对数回归模型:
模型中R[2]=0.696,调整后的R[2]=0.674,F=31.985,Sig.=0.000,括弧内为t检验值。上述回归模型的R[2]=0.696,拟合的优度高,其解释力近70%。它表明乡镇第二产业产值每增加1%,则全国建制镇非农就业人数就增加0.17%;乡镇第三产业产值每增加1%,则全国建制镇非农就业人数就增加0.36%。
四、结论与思考
(一)寻求非农充分就业机会是乡——城人口迁移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机制。农民以经济理性选择进城(市)或是进镇或者留在农村,故小城镇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它能为农民提供多少非农就业机会以及农民对就业后净收入的理性预期:当城市就业机会和预期净收入大于小城镇时,农民总是选择进城而不是进镇;人为地“撤乡并镇”或扩大镇区范围,让农民进镇,无异于缘木求鱼。前文有关上世纪90年代农民迁移选择后果的经验分析表明,西方经济学的配弟—克拉克定律[12]对我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人口城镇化的宏观过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以配弟—克拉克定律来评价近20年的我国小城镇建设,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国特殊国情条件(超大规模农村人口,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权宜之计或过渡性措施。从实质看,我国某些地区人为设置的、缺乏非农产业基础的小城镇无非是将城市—乡村二元结构中的乡村一元的边界放大到了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小城镇劳动力分工不明(亦农亦工或非农非工)、镇民身分不清(既非农民又非市民)、其传统行为向现代(市民)行为模式的转化受阻等等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经验性分析已证明,小城镇非农就业容量对乡镇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有很高的依存度:没有镇区工业的存在与发展,“人气”不能聚集,劳动力的分工难以细化,商贸、服务业也很难扩张。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是难以抗拒的,故决定小城镇的生存与发展之核心是其能否不断扩大非农二、三产业的就业容量,从而吸引更多农民进镇定居。用人为“圈地”或行政办法迫使农民集中到小城镇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农化与城镇化。因此,我们必须以尊重农民理性选择的自由为前提,调整现行的城镇化战略,以避免城镇经济要素的资源配置不当和规模不经济。
(二)小城镇对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小城镇非农二、三产业,特别是乡村工业(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只有镇区工业及其商贸、服务业的存在与扩张,才能不断吸引农民进镇从事非农活动;为农民提供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小城镇聚集“人气”的必要条件。
(三)我国东、中、西部各省、市、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小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容量的差异,故不存在全国统一的、均衡的城镇发展模式。不应当一概否定小城镇对我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必须重视经济欠发达省区建制镇的“空壳化”问题,以及就业结构趋同的问题,并从产业发展等深层次方面寻找解决办法。
(四)鉴于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的非均衡特征,可以预期,我国未来将呈现区域人口城镇化发展多样化趋势:①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一元化演变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如全国统一的户籍、就业用工、社会保障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扩大,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非农就业将更多地转到市和镇,2000年市、镇、乡村非农就业为49.0%、22.98%和28.02%之比例分配中乡村份额势必降低。②东部小城镇由于工业制造业扩张的优势,其非农就业量势将进一步增加,“人气”会更旺;部分小城镇可能发展为小城市(如浙江温州市龙港已有20万人口规模)或大、中城市的卫星工业区(如广东中山、东莞附近的许多小城镇);而中、西部省、区多数缺乏产业经济发展优势的小城镇,可能因“空壳化”或撤销或合并;少数小城镇得地利之便(如水陆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旅游点等)将成为以商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体的镇。因此,对中、西部省份而言,小城镇发展选择数量少、规模大、“人气”旺的集约化模式更具生命力。③从总体上看,未来全国小城镇吸引农民非农就业的“拉力”不可能大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拉力”。因此,不宜再提“小城镇,大战略”之类的话语。
我们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引出的政策性思考是:第一,无论东部或是中、西部省份都应把小城镇建设放在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点上,城镇产业“空洞化”和小城镇“空壳化”的问题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在政策层面加以约束;第二,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别是区域产业经济的不同特点,将城市和镇的发展建立在当地比较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防止区域间小城镇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趋同化。第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乡镇企业通过改制都已民营化、股份化。因此,创造宽松的法制环境促进民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对今后城镇产业和就业扩张有重要作用。第四,各地在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时,应当注意因地制宜,使城镇发展模式多样化。具体地说,凡非农产业和就业扩张基础好的地方,都应当允许设镇,扩张条件更好的(如浙江温州市龙港那样)还可以升格为市。最后应当强调,以单纯增加城镇数目来解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相反,某些地区还应当及时纠正小城镇数量盲目扩大的失误,对确实不具备条件的“空壳镇”,可考虑与大镇合并或撤镇归乡。总之,将城镇建设放在能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民充分就业的“市气”(即产业经济)和“人气”(总人口和就业人口的集聚)的基点上,应是我国未来非农化与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标签:小城镇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民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非农数据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第二产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