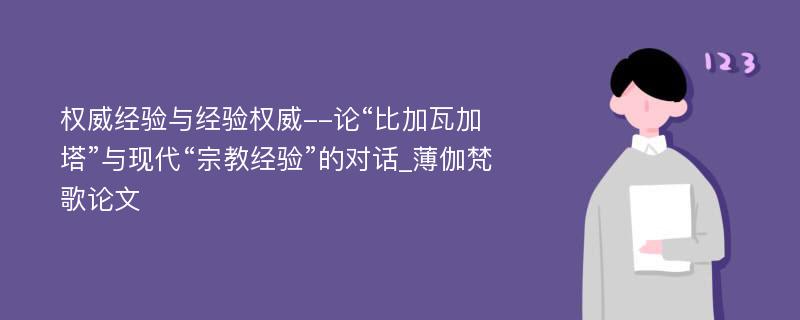
权威的经验与经验的权威——论《薄伽梵歌》与现代“宗教经验”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权威论文,宗教论文,薄伽梵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是古代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一小部分,从18世纪晚期,便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①《薄伽梵歌》的英译,与《圣经》和《道德经》的翻译,被西方文化界公认为最重要的三大翻译作品。1901年至1902年,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吉福德讲座(后来整理出版为名著《宗教经验之种种》)②中曾经引用《薄伽梵歌》,以此考察早期印度典籍如何向它的古代、现代读者与听众提供一种方法,用来有系统地培养现代人所谓的“宗教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宗教经验的渴求,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化信号,在风行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瑜伽练习中随处可见,而这些绝大部分的瑜伽信条都根源于《薄伽梵歌》。或许有人会问,这部前现代的、有着强烈东方色彩的瑜伽典籍,在今天要向我们表达什么?或者,这部典籍的内容,是否有助于阐发或丰富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宗教经验”概念?
而我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力图将《薄伽梵歌》置于后现代重构主义者之中,致力于“捍卫(被后现代解构主义者抛弃的)世界观这一概念,……重构这一概念,并设法避免前现代及现代主义所犯的错误”③。本文只简要阐述了这一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薄伽梵歌》如何理解权威与宗教经验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做这样一番探索的动力,在于权威与经验这对概念之间,存在假定的或真实的张力,就大约是从威廉·詹姆士的时代开始的,现当代关于宗教经验的讨论,被置于掌握宗教权威的宗教机构的对立面。④
实际上,现当代关于宗教经验的讨论,都以宗教权威作为个体的中心,换言之,一个典型的假设是,这些宗教经验的核心是宗教权威,宗教权威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进入个体,被个体所获得。《薄伽梵歌》作为印度教毗湿奴派最重要的哲学/神学典籍,在个体概念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只有个体才能自我修炼,个体经验与被称为终极宗教权威的奎师那(Krishna)相关,而奎师那就是这部典籍的言说者。
虽然现代人关于宗教经验的概念都隶属于个人层面,但是我在本文则要指出,《薄伽梵歌》中的经验有强烈的群体性倾向。它所论述的作为宗教的经验(或经验的宗教),是在其特有的宇宙秩序(法)的观念系统之中的。同时《薄伽梵歌》还坚持这样的一种假设,所有个体通过与无限的“经验者”一如,最终都有获得精神圆满的潜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假设是针对当代读者的,因为它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前现代及现代主义中所蕴涵的价值,消除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所犯的错误”。尽管《薄伽梵歌》显然源自前现代,但它毕竟属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前基督教“轴心时代”,从中我们仍可辨别出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的雏形。⑤
这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讽刺,《薄伽梵歌》对于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是印度人或有印度教背景的人)仍然作为一种修炼宗教经验的权威典籍而起作用。但同时它还提醒我们,典型的(如果不是所有的)宗教经验之所以能产生,都会与(被确信的)一种或者几种被“宗教经验者”的群体视为权威的典籍相关。
在简介《薄伽梵歌》中指称经验的一些方法之后,我将讨论神圣的和个体的权威概念,最后简单阐述这部典籍中的重点“奉爱”(bhakti)即“完全的相互性”(total reciprocity),并以此为视角来讨论《薄伽梵歌》在当代流行的瑜伽文化与后现代重构主义中的作用。
一 三种类型的经验
《薄伽梵歌》巧妙地结合了数论派和吠陀哲学三个本体性概念prakrti(原质,旧译自性)、purusha(神我)以及brahman(梵,终极实在),并主要区分了由这三个概念所产生的普通的经验和超越的经验。普通的经验以二元为特点:作为自我中心的结果,人本身及其境界会用成对的概念来形容,例如喜爱与厌恶、欢喜与悲伤、期待与绝望、荣耀与羞耻等等。⑥这种对立的二元性给个体带来的困扰,在《薄伽梵歌》中得到了戏剧性的夸张,集中体现在人间著名的勇士阿周那(Arjuna)身上,他和他的兄弟们即将同他们的堂兄弟交战,但战争中的职责问题困扰着他。⑦他向自己的朋友、战车的驾驭者奎师那征询意见,后者的回答构成了七百颂的《薄伽梵歌》。
在《薄伽梵歌》中,日常的经验是自我由于疏忽而迷失终极实在后的产物,超越的经验是自我通过瑜伽或“合一的训练”(discipline of yoking)达到自我合一后的产物。瑜伽(yoga)这个术语是与“合一”(yoke)同源的,既包括了英文中“经验”这个词的第一种含义,即(1)通过练习或背诵而拥有的知识或技能,又包括了第二种含义,(2)由外物刺激而主观直接接受的体验。
《薄伽梵歌》中的教导大体上说是致力于引导个体,从暂时的、有限的、二元的、普通的经验,到永久的、自由的、合一的、超越的经验。⑧正如我在前文已经提到的,强调个体的改善与自我修行,是所谓“轴心时代”典籍中展示现代主义雏形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自我修行的精神气质,当然有利于典籍在当代的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普通的经验和超越的经验之外,《薄伽梵歌》还提出了第三种类型的经验,它是由独一至上的有情存在者所享有的经验。《薄伽梵歌》的言说者奎师那,用各种不同的词来定义这独一至上的有情存在:梵(brahman)、最高我(paramatman)、薄伽梵(bhagavan)、无上神我(purusottama)。与个体的普通经验与超越经验不同,这一超凡之我,不受意念、时空的限制,也不局限在个人的身体之中。⑨这就强烈地暗示出它与文本主题的相关性,特别是经验的权威建立在无上的有情存在者的基础之上,个体也参与其中。我们后文还将讨论这一话题。
二 权威、个体以及世界秩序
《薄伽梵歌》教导的中心,是要解决贯穿于《摩诃婆罗多》中两套观念系统里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之间的张力。一个是“此世”中进取的或行动(pravrtti)的观念系统,与之相反的是“彼岸”中超脱的或无为(nivrtti)的观念系统。前者设计了一个由法(dharma)支配的世界,宇宙运行原理的特征,是居于永恒世界规则的中心地位的祭祀(业)的等级结构和规范,并强调每个人在世界规则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于此,经验的物件是欲(kama)、利(artha)和法(dharma)。与此相反,在后一种观念系统(nivrtti)中,将在法(dharmic)规则运行下的暂时的世界视为虚妄,转而屈从于坚定的禁欲主义的生活(sannyasa),这种生活以关于梵、终极至上存在的知识为主导。真正的或超越的宗教经验,在第二种观念系统中,毅然决然地同世界隔绝开来,而导向解脱(moksa)。
这两种观念系统的张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体化的悖论(paradox of individuation)引起。在世间行动,必须完全遵从法,最终排斥掉作为个体的我,而成为与社会协调的理想公民,自我归于消亡。然而出世而追求作为自主存在的我,或许会以获得个性为补偿,但却成为孤独的缺乏活生生面目的存在物:十足的禁欲主义者就是十足的陌生人,他者的身份是完全由他者性构成。⑩或许有人会将最极端形式的行动(pravrtti)观念系统,当做是前现代社会的核心议题,宣称彻底的秩序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而极端形式的无为观念系统与此相反,它是现代社会核心问题的回响,表现为自我的孤芳自赏,以与世隔绝为代价。(11)
《薄伽梵歌》力图解决这一悖论,主要的办法是通过重新定义“等式”(equation)的双方——一方面重新定义法(dharma),另一方面重新定义克己(renunciation);与此相联系的是,宇宙权威从原则(法)复归到终极经验的、关切的神,神成为一切经验的基础(bhoktr)(12)以及世界秩序的创立者(dharma-samsthapaka)。(13)奎师那教导阿周那,法(dharma)要通过行动(业)去认知和执行,行动是依据神的意愿或者说是终极位格化权威来支配(14);克己则被理解为,从人的行动所产生出来的或善或恶的果报中解脱出来的超然态度。这部典籍重新定义了业瑜伽(karma-yoga),即“行为的整合训练”(integrative discipline of action)。《薄伽梵歌》以业瑜伽这个概念为基础,进行了概念重塑,即根据《薄伽梵歌》中最完满正确的概念即奉爱(bhakti),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完满的宗教经验”,重新理解了数论派、瑜伽、吠陀哲学传统中的关键术语。
三 当下的解释学(The Hermeneutic of Immediacy)
通过瑜伽练习,产生与神一如经验的原理,是《薄伽梵歌》反复强调的重点;在简要讨论完下面两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个议题。第一个问题是,《薄伽梵歌》认定个体的不可毁灭性,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薄伽梵歌》“当下的解释学”。第二个问题的一个例证,以及后者如何构成前者的观点,是出自于奎师那关于身体变化的一个有名的比喻,用来证明永恒之我的存在:“如性灵于此身兮,历童年、少、壮、老衰;如是而更得一身兮!智坚定者于斯不疑。”(15)这一论述针对了身体随时间变化的常识(common sense),肯定有事物没有变化。奎师那以全知的权威的论述,总结了由普通(我敢说是普遍)的经验引发的常识,接着还继续讨论了永远不可分割、不可破坏的身体持有者(dehin)。我们知道《薄伽梵歌》这些颂中的教诲,在反佛教论战一开始时便被引用(16);关于诸多永恒的个体经验之“我”的论述,还有利于这部典籍在今日的传播。
“当下的解释学”更明显地表现在《薄伽梵歌》另外几章中,更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它们都采用了简单比喻的形式,从熟悉的事物扩展到不熟悉的事物,让我们领会理解。这种比喻的方法有时会用于教导关于超凡之我的神学抽象概念;也会用于说明瑜伽修炼,通过个体之我的经验,最终与超凡之我融合。例如当乌龟遇到危险时,习惯于将腿缩到壳中——这是任何好奇的男孩都熟知的场景。《薄伽梵歌》用它来说明瑜伽修炼者如何控制感官,“诸根退于根境兮”获得更高境界的瑜伽经验。(17)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薄伽梵歌》借用了数论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常见的比喻形象,即将身体比作“田”(kshetra),并把它与“知田者”(kshetra-jna)区别开来,而且还将它同我区别开来,而关联上超凡之我。超凡之我“遍诸田处”,是经验所有田的知田者。(18)
在《薄伽梵歌》第十章中,奎师那还使用了排比举例,其作用类似于排喻,用来说明超凡之我是如何出现,也就是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的。例如奎师那说:“‘我’是静定位之雪域高峰(Himalaya)”,“诸树中‘我’是菩提树”,“人群中‘我’是皇王”。(19)排喻中表达出来的持久信息:是在此世人类经验到的典型的事物中,卓尔不群的、超越的经验或对象表现;或者是对终极指称物的微言大义。因此,奎师那让他的读者/听众,依据他所谓的超凡至上之我,扪心自问,回味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结论:权威的经验与经验的权威的一如
将普通的经验引入超越的经验之中,是《薄伽梵歌》中的一种技巧,给听众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感官的转化,而且是对超凡之我的直接体验与一如。《薄伽梵歌》第四章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有助于说明上述看法。“人[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如是其就‘我’[超凡之我]兮,‘我’亦如是而佑之;苍生遍是遵‘余’之道兮。”(20)在这里一如是指,个体自由决定了其要选择的或与之互动的特殊道路,而这特殊的道路即是无限互动的终极之我。读者还须注意,《薄伽梵歌》的言说者所谓的“道”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奎师那,神)的。这是一种保证,通过接受各自的责任,人们能够立刻获得个体价值的保证,最终能够进入卓越的非凡之我的非凡经验之中。
最后,回到我们的主题——宗教经验与跨宗教对话。像许多早期梵文哲学作品一样,《薄伽梵歌》向我们呈现的是(奎师那与阿周那)对话形式,引导它的听众,像阿周那那样迫切知道它要讲述的内容。(21)《薄伽梵歌》这部典籍,要让人从个体的经验升华到与超凡之我相关的经验,而典籍本身就是指导人们完成这一经验目标的权威,让读者像阿周那在对话中表现的那样,承认《薄伽梵歌》的权威地位。奎师那告诉阿周那:“尔心独契于‘我’兮,修瑜伽以‘我’为依。”(22)阿周那听到了这部典籍的指示,现代读者也超越时空参与了同样的对话。
再次回到当今面临的问题,如果不是彻底拒绝神圣权威,用内在的宗教经验代替外在的宗教权威;而是认为《薄伽梵歌》强烈地、坚定不移地主张,投入到一位至上的神圣者,一切生命和万物都臣服于其脚下(23),我们就会对《薄伽梵歌》为什么在现代(或后现代)还如此流行产生疑问。我希望本文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从宗教经验的视角切入去探讨《薄伽梵歌》,有助于理解这部典籍如此流行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服务于后现代重构主义的,后现代重构主义与古代印度瑜伽原则是相融的。
注释:
①我非常感谢赖品超和谭伟伦两位教授好意邀请我参加此次学术会议(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比较与对话视野中的宗教经验”学术研讨会)。《薄伽梵歌》首次从梵文翻译为英文是由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完成的,1785年出版。
②詹姆士在他的演讲中只引用了《薄伽梵歌》一次,在第十四讲和第十五讲“论圣徒性之价值”(这两次演讲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合为一章,即“论圣徒性的价值”,《薄伽梵歌》仅在本章中出现过一次。——译者注),用来阐述他的观点:真正的圣人不需要极端禁欲主义的修行实践。“正如《薄伽梵歌》所说的,只有内心还留恋世俗的行为的人才必须舍弃这种事情。假如一个人实在不恋恋于行为的结果,他可以安心地与世人混在一起”。参见James,William,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A Study in Human Nature,New York:Mentor Books,1958,p.280。
③尼古拉斯·吉尔(Nicholas Gier)在他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写作意图,启发我做这种尝试。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印度传统被过于局限在前现代,而我要说《薄伽梵歌》迈出了印度思想中的重要一步,至少显现出了我们称之为“后现代重构主义”的萌芽。参见Gier,Nicholas F.,The Virtue of Nonviolence:From Gautama to Gandhi,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p.44。
④《薄伽梵歌》确实可以被视为早期印度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试图弥合当时社会中的新思潮与婆罗门典籍日益对立(当然也根源于其中)的观点。
⑤Jaspers,Karl,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st ed.),München:Piper Verlag,1949.
⑥例如《薄伽梵歌》2.14;2.45;2.64;7 27。
⑦阿周那面对战争的场面产生了极度的苦恼,见《薄伽梵歌》1.28—2.8。
⑧有几颂中是特别讲述这一要旨的,见《薄伽梵歌》7.1;9.2;14.1—2。
⑨参见《薄伽梵歌》4.5—6;7.26;13.2;13.13;13.22;13.32;15.15。
⑩Olson,Carl,The Indian Renouncer and Postmodern Poison:A Cross-cultural Encounter,New York:Peter Lang,1997,pp.49-71.
(11)Gier,Nicholas F.,Spiritual Titanism:Indian,Chinese,and Western Perspectives,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
(12)《薄伽梵歌》5.29。
(13)《薄伽梵歌》4.8。
(14)《薄伽梵歌》10.8,即“智者殷心如是兮,礼‘我’唯敬念是凭”。
(15)《薄伽梵歌》2.13。
(16)《薄伽梵歌》坚持认为有诸多实体性的“我”永久存在,反对佛教“无我”(anatma-vada)的观点。
(17)《薄伽梵歌》2.58。
(18)《薄伽梵歌》13.2。
(19)《薄伽梵歌》10.25;10.26;10.27。
(20)《薄伽梵歌》4.11。
(21)参见Schweig,Graham M.Bhagavad-Gita:The Beloved Lord's Secret Love Song.New York:Harper San-Francisco,2007,pp.255-256,关于《薄伽梵歌》中对话结构层次的设计。
(22)《薄伽梵歌》7.1。
(23)对于现代听众来说,《薄伽梵歌》还有一个更潜在的“罪过”,即怀疑——经验是更高级真理的基础。不过《薄伽梵歌》交给读者的任务是“奉爱瑜伽”(bhakti-yoga,又译为信瑜伽、敬爱瑜伽),奉爱瑜伽,既意识到了经验的重要性,又具有群体性,而不是个人的、由主观产生的。或许对现代读者信奉《薄伽梵歌》更潜在的危害,不是奎师那说一不二的独断论,而是他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惊人破坏力(见第十一章)。作为受过良好训练的勇士面对巨大的破坏,应该处变不惊,但根据《薄伽梵歌》的描述,甚至勇士阿周那都对此不知所措(这无疑是鲁道夫·奥托“既令人害怕又令人神往的神秘感”这一宗教经验概念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