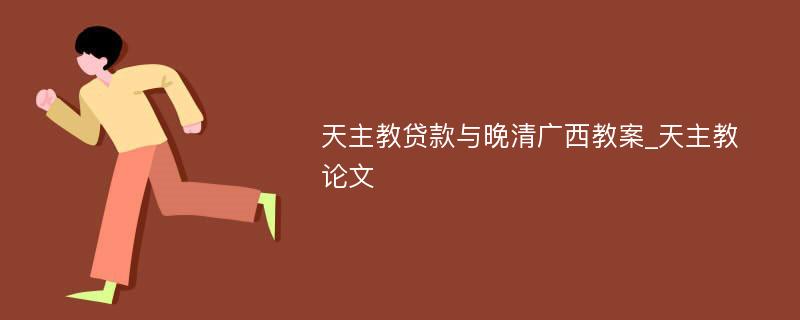
天主教会放贷与清末广西教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会论文,广西论文,清末论文,教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天主教与高利贷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但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学、伦理学等角度对中世纪天主教会高利贷禁令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等进行了研究,而对天主教会自身的高利贷活动考察不多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大量进入广西活动,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以法国武力为后盾,在传教过程中吞并民众财产、霸占土地房产、破坏民间风俗等等,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他们的高利放贷,往往使得民众不满,导致民教冲突发生。但学界对这些问题关注较少,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那么,天主教在清末广西的发展情况如何?其放贷情况怎样?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天主教在清末广西 (一)天主教在广西传播纵览 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开端于明末清初时期。明万历十三年(1585),天主教意大利耶稣会会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由粤来桂,试图展开传教活动,但不久就被驱逐,天主教打入广西的计划受挫。清顺治四年(1647),奥地利耶稣会会士瞿纱微(Andreas Xxvier Koffler)随葡萄牙军队从澳门到达桂林,援助南明永历皇帝,天主教在宫中发展了部分教徒,但清军攻破桂林后,瞿纱微被处死,传教随之中止。随后清朝进入康乾年间的百年禁教时期,天主教更是无法在中国开展正常的传教活动。特别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廷颁布“西洋人立堂设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1717)九卿原议禁止”②谕令以后,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帝进一步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③此后120多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进一步衰落。在广西,此段时间“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教士能够进入广西省”④。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提供了良机。1844年,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其中第17款规定,美国人可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通商口岸“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⑤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可以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⑥清政府被迫颁布洋教弛禁令。根据条约,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只能在5个通商口岸内活动,清廷也多次强调不能“越界传教”⑦,但违规而越界传教者为数众多。特别是中法《天津条约》中“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的规定⑧,为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清政府宗教政策步步松弛,使“西洋教盛行中国,天主、福音等堂几遍天下,虽至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⑨ 天主教在广西的发展晚于其他省份。184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将两广教区划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作为活动范围,并在1852年通过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李莫瓦(Labbe Libois)为两广教区的主教,李莫瓦随即命教士肋诺(Reniu)非法潜入广西,了解桂省宗教活动情况。咸丰四年(1854),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从贵州潜入广西西林县(今田林县,下同)白家寨,并计划到广西省城或其他城市传教。在西林期间,马赖用小恩小惠诱骗群众入教,并与官吏勾结,为非作歹,新任知县张鸣凤于咸丰六年(1856)将马赖及教徒26人逮捕,处决了马赖和两个中国教徒,此即西林教案,又称“马神甫事件”。法国以“保护圣教”为名,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巴黎外方传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取得了“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天主教随之在广西迅速蔓延,据统计,从清咸丰四年(1854)到清宣统三年(1911),法国传教士在广西田林、上思、贵县(今贵港市)、宣化(今属南宁)、凌云、郁林(今玉林市)、柳城、百色、武宣、象州、荔浦、罗城、苍梧、蒙山、平南、桂平、平乐、宁明等地传教,先后活动的传教士有20余人。⑩ (二)天主教传教的经费来源 在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很快。传教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经费,其经费在不同时期的来源有异。 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经费来源,早期主要来自国外,如法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经费主要依靠法国政府和募捐解决,“在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以前,在华遣使会每年从法国在政府领取一万二千法郎,另外还从法国教会募得的捐款中获得一部分接济”(11)。19世纪后,在华法国传教士的经费逐年递增,特别是在广西的传教士获得的经费大量增加。据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2章的统计,巴黎外方传教会于“一八四三年拨给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经费是二十八万法郎,一八四五年是三十万四千万法郎,一八五一年是三十万六千万法郎,一八五四年是三十一万一千万法郎,到一八五九年为了向中国内地特别是沿交趾支那一带的省份扩张势力而猛至五十四万法郎”(12)。 历次教案发生后,列强向清政府勒索到大量赔款,其中的一部分拨给天主教会,使在华天主教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J.M.Mouly)更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稿内私增一项条款:听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3)。此后,传教士遂据此大量霸占田产房舍,扩展教会势力,吸收无地农民入教,其经费来源“逐渐地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接济”(14)。 在广西,这种情况尤为严重。贵县天主教会“常用经费,除罗马宗教酌予津贴外,余仰于教会田租收入”(15)。在西林县,天主教堂在该地大量购买土地,租给教徒和村民耕种,获得巨额收入,仅仅定安、渭各两教堂年收租谷就达4万余斤(16)。清同治年间传教士在象县(今象州县)龙女村建立的教堂,占有土地更多,所收租谷数量惊人,民国《象县志》有载:“外国人之居留象县者,始于清同治间,法人在县属龙女村,建筑天主教堂一所,置有田产,年收租谷二十余万斤。”(17)在大肆购买地产的同时,天主教还向教徒和乡民放贷,获得利息收入,构成其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中法战争前,贵县三板桥教堂“每年收入田租、息谷就达三四百担,佃户、债户遍及附近各村”(18)。 二、天主教会在广西的放贷活动 清末时期,天主教会在其活动区的放贷十分普遍,这种放贷是否属于民间借贷?笔者认为,传教士进入广西后,其在传教活动中的放贷目的是为了解决传教经费和吸引群众入教,用于放贷的资金也不一定来自外国,这种放贷行为是非政府性的,属于宗教机构的放贷。因此,笔者在此将传教士和教堂放贷视为民间借贷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为教会所控制的高利贷资本进入借贷领域,使得广西民间借贷具有了新的内容。 (一)放贷对象 天主教在广西取得一定发展后,为扩大传教经费,发展教徒,教会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传教区进行放贷。根据对有关资料的分析,天主教会放贷的对象主要有以下三种人。 1.教徒 教堂对信教民众的放贷很常见,主要是针对经济上较为贫困的教徒。教会放贷给教徒,除了赚取利息用于传教外,一方面是在经济上救济教徒,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教徒的宗教信仰,让他们享受教堂的恩惠和入教的好处,并通过他们影响教外群众,以吸引更多的人信教。在贵县,天主教堂早在中法战争前就放高利贷,教堂“先是租借给教徒,利息和租金也略低于本地地主”(19)。贵县三板桥教堂“当青黄不接和荒年,神父也开仓借谷给教徒,每百斤收利息五十斤,俗称放青苗”(20)。 除了教堂的放贷外,一些地区的教徒还在教会支持下,成立借贷互助组织,教内群众可以借贷,同时亦对教外民众放贷。如在象州龙女村,天主教大约于19世纪末传入该地,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他们有信天主教的,据说在三四十年前,已有天主教传入,现时他们的村里,有几处还有教堂,虽说十分卑陋,然外力之传播可见一般了”(21)。19世纪90年代,传教士苏安宁(Mathieu Bertholet)在该地“成立了婚嫁协会,提供资金给准备准备建立新家庭的青年,并通过盈利使资本适度增长,在短短几年内,解决许多年轻人因婚姻缺乏资金的困难”(22)。据国内有关资料记载,该婚嫁协会亦名“结婚会”,是教堂拨出专款设立的,经济困难的教徒及其子女在办婚事上有困难时,可以向“结婚会”借贷,不收利息,三年还清(23)。 教会对教徒的放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教徒的经济困难。在广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巴赞写到:“马赖先生死后……在继此之后的战争和饥饿年代,异教徒们被成百地饿死,而基督徒们却从未缺乏过生活必需品,他们甚至还成功地设法勾销了几笔债务”(24)。但因大部分属于高利贷,这就加重了教徒经济负担,加深了他们对教堂的依附,导致他们在经济和人身上受到教堂控制。 2.一般非信教民众 教堂和传教士放贷给这部分人主要是为了赢得民心,吸引群众入教,并获得利息收入,用于教堂开支。在西林县定安圩,“教外的人经过教徒介绍和担保,也可以向教堂租借……传教士见向他租田、借债的人多了,就逐步提高租谷和利息,和本村财主佬差不多”(25)。西林县乐里圩,“法国传教士……大量买田出租和放债”(26)。上思县“天主教……放债拉拢穷人”(27)。 教堂对非信教贫困群众的放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部分民众为了得到救助,纷纷入教。20世纪60年代,调查组在西林县调查时,群众说:“在这里不奉教又没有田地种,借也无法借,所以后来我也入教了”(28)。亦有人说:“法国神甫好,有饭给我们吃饱”(29)。该县“常井全村四十多家的人都信奉天主教,种教堂的田,有的人帮教堂做事,没吃的向教堂借”(30)。在梧州,天主教初入该地时,“首先在某些堂区购买土地,以低租解决贫农生活上的困难,或低息贷款给他们……以种种方式接近农民,和他们建立感情,在他们中间传教,吸收信徒”(31)。贵县三板桥“当时穷人去信教是出于不得已的,入教是为了多一条借债、租田的门路”(32)。 3.其他阶层 除了教徒和一般群众外,教会还放贷给地方的一些不务正业者,这些人主要依靠敲诈勒索维持生活,在地方上具有相当的势力,群众比较畏惧他们,他们得到教会的恩惠后,就威逼或诱骗民众入教。因此,教会以较为优惠的条件对他们放贷,不但可以避免勒索,而且可以利用其势力为传教服务。如天主教初入西林县时,“对一些流氓则用金钱收买。神甫借钱给他们去赌博或搞投机生意;……还不还也不追讨。如此一个引一个,村寨上的居民入天主教的逐渐多起来”(33)。 一些传教士还利用放贷勾引妇女,败坏社会风气。如在西林县,“神甫……借钱给一些好用钱的妇女,一百几十块法光(法国银币)在所不惜;还不还也不追讨”(34)。传统的中国乡村极重礼教,“男女授受不亲”观念在士民中根深蒂固,传教士对妇女的经济诱惑,有违中国风俗,极易伤害民众感情,引发士民反感。 除了上述几种类型债户外,一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租入教堂土地耕种,向教堂缴纳地租,一旦他们不能及时缴租,地租就转化为高利贷,这也是导致民众对教堂负债的一个原因。 (二)放贷利息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无论是对教徒还是非信教民众,传教士放贷的利息都很高。贵县天主教堂“出租耕牛、农具等。黄牛每头收120斤租谷,水牛每头收150斤”(35)。西林县“定安教堂放债,教徒借债100斤谷,利息只要50斤。非教徒借100斤,利息是100斤”(36)。借钱的利息也很高,在西林县,“向教堂借10块法光,一个月收利息一角”(37)。 传教士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利润,“在付款方式上,又故意玩弄花招,克扣农民。本来是借谷子,教堂却用银子,法光支付,在折价时扣除一、二成。归还时也照样从中盘剥债户。当债户用银子还债时,教堂却要用法光折价,当债户用法光还债时,教堂却用法纸折价。教堂支付时,总要加水一二成,收入时又扣水一二成……借一元只得九角八分,不到两月,却要还一元二角二分多”(38)。 除了放贷的利息较高外,债户还须付出额外开支。如贵县三板桥“教堂定的利息、田租和本地财主定的差不多,但除交租之外,还时常被叫去帮教堂做工,一年之中做三五十天不等,只供吃饭,不付工钱。谁人不去或者去了不卖力,教堂就借故抽佃、逼债、不帮医病”(39)。 因利息高昂,很多人还债的本利往往超过本金数倍,给债户造成沉重负担。西林县白卜顺借教堂100斤谷,年底还200斤,因无谷偿还,次年还400斤,他家有一年收获1000多斤谷,全部拿去还教堂的债。(40) 放贷成为部分教徒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教会贷款的发放,大多是由传教士信任的教徒负责,他们常常利用权力,欺上瞒下,提高利率,很多人因此获利丰厚。如贵县有教徒因利用教堂的钱放债而致富,“庆丰的黄五福,大圩的温亚四、李石生,三板桥的江春荣,附城的李永泰等,都是这样从一般教徒而变成大地主的”(41)。 (三)放贷性质 天主教会在广西的放贷大多属于抵押借贷,他们在放贷时,一般要考虑到对方的偿还能力,若借贷者有田地、山林或固定收入,借贷就相对容易。民众在向教堂借贷多需要抵押品,若到期不能偿还债款,抵押物就为教堂侵占。西林县定安教堂“借钱也和借谷一样,先了解借贷人有无能力还债才决定借或不借……银钱多借给有铺号的,或者先了解其社会关系、经济来源才借”。“借贷有限借给教徒。借钱也和借谷一样,先了解借贷人有无能力还债才决定借或不借”(42)。苏安宁在象县设立的“结婚会”,教徒在借贷时,尽管不须支付利息,但“必须有房屋、用产作抵押,到期无法还清,便将这些抵押品卖断抵债”(43)。 由于教会放贷的利息较高,很多债户借入后无法偿还,因而抵押的土地或山林被掠夺,导致民众对教会不满。20世纪60年代,调查者在贵县调查时,当地群众说到:“外国人到我们村来抢购田地,放债剥削,心里是不满的”(44)。天主教在贵县“有田、塘、宅地1238丘,面积约七百五十多亩。这些田地除部分是教会用钱买的外,绝大部分是因穷人向教会借钱无力归还而被夺去的”(45)。西林县“群众借神甫的钱,利息很高,年息达50%,起初神甫不催还,后来债务也就越来越重了。因此就只好把田地卖给他抵债”(46)。该县央荣屯“有一片很宽的山地(10多里)当给教堂,后来陆卜沙、陆卜夫亲自到教堂去赎三次,神甫都不给,并说不见文凭不能赎了。这一大片的山地就这样由教堂霸占了”(47)。 三、高利贷视角下的广西教案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天主教在广西的放贷活动,大部分属于高利贷,利息极高,借贷条件苛刻,很多债户因借入教堂的债而付出惨重代价。 心理学家指出,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弹性和韧性是有“度”的,这种“度”是指人们的心理一般具有承受相应的社会刺激而又不出现异常反应的界限,即“阈限值”。社会刺激若低于“阈限值”,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若超过“阈限值”,则使人们产生心理压力,出现异常心理反应。(48)当借贷的利息极其高昂、借贷条件十分苛刻、催债手段极度残忍而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后,民众就会选择一些较为极端的方式来应对高利贷。这种极端心理既有个人的心理想法,也有社会民众集体的共识。社会心理学认为,当群体对某一对象在思想上或原则上有对抗、反抗和抵制时,他们就会采取敌视和憎恨的态度对待这一对象,这种社会情绪可称为集体敌视。(49)清末时期的广西也正处于利益分化、矛盾突发阶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众容易产生极端心理,他们或在高利贷面前失去了常态而走向极端,或表现极其脆弱与消极悲观,这些问题的演变和激化往往导致群体的极端心理。同样,教会对群众的放贷,利率高昂,条件苛刻,并利用放贷吞并群众的土地山林,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再加上传教士欺压百姓,横行乡里,诸种因素使得民教矛盾十分尖锐,冲突不断。除咸丰4年(1856)的西林教案外,自中法战争前夕至清末,广西发生规模较大的反对天主教的教案有四次,即三板桥教案、上思教案、乐里教案、永安(今蒙山)教案,其中有三起与高利贷有关。 (一)三板桥教案 贵县三板桥是天主教在广西的一个重要传教基地。同治十四年(1875),富于道(Foucard)在此开始传教,后由司立修(Chouzy)负责传教事务。传教士伯业(人称李神甫)主持三板桥教务期间,教会在该地大量购买土地出租,并放高利贷,并“借口经费困难,决定提高地租和债息,而且规定教堂的地租是‘铁租’,不管天灾人祸,都要如数交足,不得拖欠分文。他还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大放青苗,等到一个多月禾熟后,往往获利数倍”(50)。他们还无视当地风俗,阻碍教徒祭祀祖先、强行参与民众的民俗仪式。三板桥“每逢村上死了人,天主教的神父来搞什么念圣经祷告,道公也来打醮超度,而群众是反对天主教的,只是顾虑要租教堂的田种,不敢公开反对”(51)。诸种因素导致民众与教堂的关系日趋紧张。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九月五日(1883年10月5日),三板桥部分汉、壮族青年教徒准备应募从军,而传教士伯业却百般阻拦,并严厉斥责这些青年的带头人江三开,还威胁“要收回佃田,限期清偿债务”(52)。江三开等愤于传教士高价出租教会田地、重利剥削民众及暴力催债等行径,在开拔前夕,与传教士发生冲突,群众冲进教堂后,“发现大厅内摆着的帐本、契约、借据、催交欠债名单等物件”(53),极为愤慨,遂“烧毁了教会的帐簿、借据,又开仓分粮,拆毁教堂,并将李神甫绑送县衙”(54)。 (二)乐里教案 乐里在清代属西林县,民国初中期由凌云县管辖,后划归田西县,今属田林县。关于乐里教案的情况,不同资料记载有出入。民国《田西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游匪尤维翰杀传教士于乐里……有法传教士一人到乐里,意在宣传教义,甫至,尤愤恨杀之”(55)。该记载只是粗略指出游勇杀传教士是出于“愤恨”,具体原因则没有写出,该时间亦有误,应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曾为天主教修女的卢玉贞认为是游勇觊觎传教士财物,遂杀而掠之。根据从她母亲那里得来的消息,她说是有人看到传教士有财物而报告游勇,游勇遂杀害传教士和教徒,将财物分给众人。(56)该说法值得质疑,一则卢是听人述说,这导致资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二则卢为教徒,有为传教士辩护的可能。由其所述的游勇在事后将财物分给群众而不是据为己有可以看出,游勇也不完全是为了贪财而杀传教士。 关于乐里传教士的死因,笔者认为是因催租逼债被杀,死后财物被掠夺。乐里是南宁、百色通往西林的必经之地,传教士在此开设教堂,购置田地和山场,出租给教徒或群众耕种,并大放高利贷,佃户若无法交租或偿债,其田地往往被教堂占去。教会所放的高利贷,“利率超过本地财主,而且绝对不能拖延”,乐里人称其为“讨命债”(57)。1960年广西通志馆调查组在乐里调查时,该地老人雷达廷(时年78岁)说:“法国传教士在我们乐里建教堂传教,大量买田出租和放债,调戏妇女,还挖走我们不少宝贝。老百姓个个痛恨,但敌不过他,只好忍气吞声”(58)。传教士还“不准教徒与异教徒结婚,干涉人们婚姻。借入教‘洗礼’之机,奸淫妇女,制造了许多家庭纠纷。不准入教者祭奉祖先,干涉民族风俗习惯……法国神甫还自以为高人一等,对群众趾高气扬,态度粗暴”(59)。这些行径使得民众与教堂关系日趋紧张。有关乐里教案的过程,据虞裕良考证,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3月29日),传教士马仙(Mazel,当地人称邓神父)由百色回西林,路宿乐里,得悉教堂租谷、债钱尚未收完,于是严令佃户、债户3天内交清,并采取暴力手段威逼债户偿还。时值春荒时节,佃户、债户难以按时还清,感到灾祸临头,便求助于游勇首领游维翰,游维翰对传教士的劣端十分愤慨,率众赴教堂与传教士论理。马仙初将他们拒之门外,继而开枪射击,游勇还击,将马仙等3人击毙,并开仓分谷给民众以度春荒。(60)权威工具书亦同意虞裕良的观点(61)。这也与《田西县志》所载游勇因“愤恨杀之”一致。传统的中国乡村民间借贷多是春借秋还,一般债主在春荒很少催债,即使催债也效果甚微,而传教士的威逼行为却把债户逼上绝路,因而导致教案发生。 (三)永安教案 光绪15年(1889),伯多利受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委派来广西传教,光绪二十年(1894)进入贵县,后担任象州龙女教堂本堂神父,监管象州、柳城、修仁、永福、永安(今蒙山)等地的传教事务。为便于接近当地民众,因当地民众苏姓较多,特改名为苏安宁。苏安宁在传教时对贫困民众施以小恩小惠,逐渐取得信任,信教者日多。 在当地站稳脚跟后,为增辟财源,苏安宁遂“提高教堂的田租和利息,甚至向教徒摊派捐款”,甚至干涉地方政务,私设监狱,还在民众与教徒之间的债务冲突中包庇教民,当地“望教村老农民覃恒信,在一次赌博中和一个输了钱想赖账的教徒发生争吵,覃恒信就牵这个教徒的耕牛抵账。苏安宁闻知后,不经过地方当局的审理,便派江飞祥等人把覃恒信抓来教堂审问,然后将他套上一个特制的大木枷,使他的手脚不能动弹,任由打手们用劲抽打,强迫覃恒信承认错误,赔偿损失”(62)。前述苏安宁成立的“结婚会”,尽管属无息借贷,但附有苛刻的条件,“结婚的男女双方都必须奉教,而教徒结婚又必须到教堂做弥撒,在神父面前办告解”(63)。这有违当地的婚姻风俗,导致教外民众和乡绅反感。这些因素使得当地士民对苏安宁十分愤恨。光绪二十四年(1898),苏安宁等三个传教士及十几个教徒又到永安传教,并收罗无赖教民,欺压乡民,进而引起当地士民公愤,群众奋起而击杀三名传教士。 上述三起教案的发生,有相同的原因,三板桥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即与教堂暴力催债引起民众公愤有关;传教士在乐里为游勇所杀,他们蛮横的逼债行为起了导火线作用;永安教案的发生,亦与传教士的高利放贷、干涉民教债务纠纷及利用放贷干涉地方婚姻习俗有一定联系。 教案是民教冲突的最高形式,是民众与教会各方面矛盾激化的结果。长期以来,天主教在传教时不断侵犯民众利益,反对民众的祖先崇拜,破坏民间风俗,争端时有发生,但清廷因惧怕列强武力,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往往偏袒教堂而打压百姓,致使民众冤屈长期不得伸张,积怨过多,民愤极大,而传教士在放贷中的不端行为,进一步破坏了极其脆弱的民教关系,难以忍受的民众终于群起攻击传教士,从而引发教案。 四、余论 在清末广西民间借贷领域中,引发债主与债户冲突的原因很多,如债户的赖债和逃债行为、债主的暴力催债和重复催债、利率高昂等等,这种纠纷不但使得民众之间人际关系紧张,而且增大了社会动乱的风险和社会发展环境的失衡,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天主教的放贷活动,是清末广西民间借贷中出现的新现象,使得借贷体系中除了传统借贷方式外,还增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无可否认,这种放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贫困民众的燃眉之急,但由于利息极高,债户一旦借入,若不能及时偿还,则利滚利计算,数目越积越大,给债户造成巨大压力。对债户来说,借入教会钱粮解困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果极其严重。传教士凭借其政治、经济等优势凌驾于众人之上,他们在放贷、收债等过程中的种种不端行径和利用放贷兼并民众土地财产等行为,不但使民众对教堂产生愤恨,也使得一些地方头面人物对教会反感,极易引发教案,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导致外交风波。民国以后,天主教的手段稍为收敛,民众的极端行为日渐减少,民教之间冲突渐微。 综上所述,天主教在广西的高利贷活动,是导致诸起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为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观测清末教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在清末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是广西地区的特性?还是具有普遍性?在其他省份是否有这种情况?更进一步来说,法国传教士在世界其他国家传教过程中与民众的冲突,是否也与高利贷有关?等等问题,都有待学人更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黄振南教授的悉心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参见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赵立行:《论中世纪高利贷禁令及其社会基础》,《历史教学》2001年第10期;孙诗锦、龙秀清:《试论中世纪天主教会高利贷观念的嬗变》,《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②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6,圣祖康熙四十六年起——世宗雍正元年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5页。 ③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96页。 ④⑩(5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宗教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4、78页。 ⑤⑥褚德新等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100页。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2页。 ⑧(1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2、147页。 ⑨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332页。 (11)(12)(1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102、103页。 (15)(26)(35)(39)(41)庾裕良等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8、286、11、272、12页。 (16)(28)(29)(33)(34)(36)(37)(40)(42)(46)(47)(56)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田林县天主教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64年,第20、4、24、3、3、22、22、22、22、19、19、16页。 (17)吴克宽、梁方津修,刘策群纂:《象县志》,第二编社会,第二项种族,1948年。 (18)(50)(52)(53)甘相茂:《八塘人民怒毁三板桥洋教堂》,政协贵港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第18辑,1992年,第115、115、116、119页。 (19)(20)(25)(27)(30)(32)(44)(51)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82、271、282、275、285、271、271、270-271页。 (21)赵希超:《桂瑶》,《史地丛刊》1933年第1卷第2期。第2页。 (22)Notice biographique and Notice nécrologique,Bertholet Mathieu(1865-1898),见巴黎外方传教会官方网站传教士个人索引,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necrologiques/bertholet-1865-1898。 (23)(38)(43)(63)庾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65、50-51、65、65页。 (24)《广西传教区日志摘录》,陈增辉主编,耿升、杨佩纯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4册,法文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9页。 (31)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梧州市志》(文化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59页。 (45)徐如璋:《贵县天主教、基督教发展情况》,政协广西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县文史资料》,第8辑,1987年,第46-47页。 (48)张大均:《关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 (49)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55)黄旭初修、岑启沃纂:《田西县志》,第七编,前事,兵革,政治,灾异,1938年,第188页。 (57)同23,第50页 (58)黄立志:《“乐里教案”概况》,政治田林县委员会编:《田林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24页。 (59)黄毅:《法国天主教在乐里》,政治田林县委员会编:《田林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24页。 (60)虞裕良:《游维翰和乐里教案》,见莫乃群主编:《广西历史人物传》第6辑,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地方史志研究组编印,1984年,第219-221页。 (61)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壮族百科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62)广西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广西人民反帝风云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