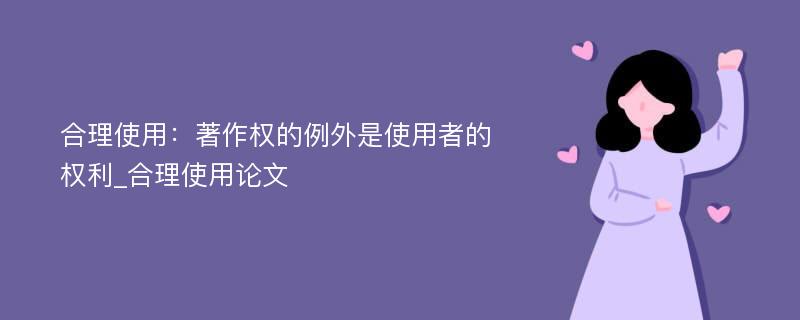
合理使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使用者的权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用者论文,著作权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解决了作品的使用者在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时与作品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合理使用的性质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以确定它是作者著作权的例外还是使用者的权利,对于作品的作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根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和法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结合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学界诸仁。
一、有关合理使用性质的争论
关于合理使用的性质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吴汉东博士将各种观点总结为“权利限制”说、“侵权阻却”说和“使用者权利”说三种不同的学说。(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28~131页。)
将合理使用理解为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这是知识产权法学界的通说,而且得到许多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的支持。(伯尔尼公约没有使用“对著作权的限制”,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合理使用是著作权保护的限制,国内学者也大都持此种观点;1996年12月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0条的标题是“限制和例外”,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107条的标题是“专有权的限制:合理使用”,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是“权利的限制”,这都表明合理使用是对著作权的限制。)郑成思先生认为合理使用是对版权的权利限制,它“本来是版权人的专有领域的东西,被使用(未经许可)而应属侵权行为。但由于法律在使用条件及(或)方式上划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从而排除了对该行为侵权的认定。”(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保护实务全书》,中国言实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89页。)从郑成思先生的论述来看, 合理使用实际上是在发生侵害著作权之诉时被告的一种抗辩理由,被告如能证实自己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就可以免除侵权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权利限制”说也好,“侵权阻却”说也好,都是将“合理使用”作为作者著作权的一种例外。
“使用者权利”说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依此说,合理使用“乃是使用者依法享有利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一项权益”。(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30、139页。)基于这种学说,著作权人负有相应的义务,即“服从使用者的意思而进行的作为或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不加禁止与干涉他人合理使用不作为)”。(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30、139页。)
“权利限制”说和“侵权阻却”说认为合理使用只是著作权的例外,是对侵权指控的一种抗辩理由;而“使用者权利”说则认为合理使用并不是对著作权的限制或者例外,而是作品使用者的一项独立的权利。两者的分歧在于,合理使用是一种权利还是一项例外?这并不仅仅是思考或考察角度不同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合理使用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作品的传播与使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对这一问题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如果说合理使用是作品使用者的一项权利,法律就应保障此项权利的实现,著作权人则负有某种义务以便使用者能够对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由此在使用者和著作权人之间产生了权利义务关系,作品的使用者是权利人,著作权人则是义务人。使用者的权利应该是在法律规定的合理的范围内,自由地使用作品;而著作权人则负有不妨碍使用者权利实现的义务,他不得采取任何妨碍使用者合理使用作品的措施,否则使用者可以要求排除妨碍。如果说合理使用只是作者著作权的例外,则意味着著作权不及于属于合理使用的行为的范围,使用者的合理使用行为不会被法律追究为侵权行为。也就是说,著作权人对使用者并不负有任何义务,使用者也不能向著作权人主张其“合理使用权”。著作权人为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他人未经其许可而使用,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妨碍了使用者的合理使用,也不认为非法。这一点在数字化传播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之背景下特别有意义。
合理使用作为一种权利还是一项例外,不仅表现为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同,而且在程序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合理使用是一种权利,则使用者应享有诉权;而作为一项例外,使用者没有诉权,相反,著作权人对于那些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行为仍拥有诉权,只是因法定抗辩理由的存在不能胜诉。另外,在具体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因是权利还是例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若是权利,则著作权人需要否认这种权利才能胜诉;若为例外,则使用者需要证明其使用为合理使用方能胜诉。
吴汉东博士是“使用者权利”的提倡者,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一书中对使用者权利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吴博士首先分辩了合理使用的对象,继而对私法上合理使用的一般情形进行考察,然后讨论了著作财产权的实现途径,最后得出了合理使用是使用者权利的结论。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论述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下面我们仅就合理使用的对象是作品还是权利这一问题及合理使用作为一种权利的欠缺进行探讨,以期对合理使用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二、合理使用的对象
依吴博士观点,合理使用实质上是对作者的“专有使用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无偿利用”,(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14页。)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合理使用的对象是作者的财产权利,而不是作者享有财产权利的作品。
如果说合理使用的对象是作者的财产权利,那么使用者利用了作者的财产权利而不构成侵权,事实上就是在行使这种财产权利。使用者在行使这种权利时并未得到权利所有人同意,显然不是以所有人的名义利用权利的,而只能以自己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使用者实际上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或许是使用者权利说的一个立论依据。
既然合理使用是使用者利用了作者的专有使用权利,我们就有必要讨论清楚这种专有使用权利是如何被使用的。依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其中著作财产权又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这里的使用权,是指“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使用者权利”说所声称的专有使用权利显然就是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以各种方式使用作品和许可他人使用作品的权利。依“使用者权利”说,合理使用的对象就是这种使用作品和许可他人使用作品的权利,这就是说,使用者有权利用著作权人的这些权利,即行使这些权利。如果使用者能够使用这些权利,就意味着使用者也能够“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用”。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使用者岂不成为了著作权人?这种使用还能是合理使用吗?显然,合理使用并未走得如此之远。在我国,使用者只能以著作权法第22条所规定的12种方式使用作品才构成合理使用。那么,能不能说合理使用所利用的是作者使用权的一部分呢?对作者的使用权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就会发现,使用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为使用者所利用。我国著作权法学界对使用权往往是按照著作权法第10条的表述方式来解释。(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93年6 月版。)这种解释方法特别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对一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复制就是行使了复制权。著作权人复制作品是在行使复制权,使用者复制岂不也是行使复制权?其实不然。让我们来看一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如何对复制权进行解释的就可以明确这个问题。
“版权所有人禁止其他人制作其受保护作品的复制品的权利,是知识产权的这个分支中最基本的权利,制作受保护作品的复制品属于出版商的行为,他希望把作品销售给公众,因此,控制这种行为的权利,是版权所有者和出版商之间签订的出版受保护作品协议的法律基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知识产权纵横谈》,张寅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19页。)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复制权是著作权人禁止其他人制作其受保护作品的复制品的权利,是控制复制行为的权利。(我国著作权立法和理论中的“专有权”一词来源于“exclusiveright”,在英文中,“exclusive”是排除他人的意思,“exclusive right”也就是排除他人的权利。著作人对作品享有专有使用权, 本身就意味着排除他人使用,也就是禁止他人使用。)因此,著作权人许可或者禁止他人复制其受保护的作品才是行使其复制权的行为。
在合理使用之下,使用者虽然可以复制作品,但无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复制作品。因此,使用者是不可能行使或者利用著作权人的权利的,这就说明,合理使用的对象并不是作者的专有使用权。既然合理使用的对象不是作者的专有使用权,那就只能是作品了。事实上,合理使用只是一些具体的使用行为,这些使用行为只能直接指向作品。因此,只有作品才是合理使用的对象。
当然,如果从一种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合理使用制度所指向的对象就是作者的专有使用权,因为合理使用制度是对著作权的一种制约,是直接指向著作权的。不过,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使用者来说,合理使用只是一些具体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法律制度。作为制度的对象是专有使用权,而作为具体行为的对象则是作品。
在著作权法上,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与合理使用都是一种建立在非著作权人同意的基础上的使用。从表面上看,这与合理使用极为相似。但是,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与合理使用却有本质的区别。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下的使用虽然不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但其实质仍然是许可,亦即授权。通过授权,被授权者获得行使某些原本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虽无权禁止他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但对于其使用行为的产物(实际上是作品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则享有控制权,(我国著作权法关于表演、录音录像、播放的规定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这种控制权是本应属于著作权人的;在合理使用之下,使用者对作品本身无任何权利,对使用行为的产物也无任何属于著作权范畴的权利。因此,法定许可与强制许可才是以著作权人的专有使用权为对象的。
事实上,将合理使用的对象界定为著作权而不是作品,并不能对“使用者权利”说提供任何理论上的依据。在合理使用下,使用者虽然可以使用或者复制作品,但不享有作者对作品所享有的权利。而依“使用者权利”说,使用者可以“使用”或者“利用”著作权人的著作财产权利,而对著作权的“使用”或者“利用”只能是“使用”或者“利用”著作权的权能。我们在上述分析中已经阐明,著作权中的任何部分权能并不能被使用者行使。因此,使用者有权“利用”或者“使用”著作权,却不能行使著作权的权能,这在逻辑上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
三、合理使用作为使用者权利的欠缺
如果说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权利,那么在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关系。对于这种法律关系,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基本问题是不容回避的:这种法律关系的产生依据是什么?这种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什么?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围绕合理使用而存在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按照民法理论,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依据是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两大类。(参见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年7 月版, 第120页。)对于合理使用, 哪些法律事实产生了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呢?
合理使用本身是一种行为,由于使用而在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过这种法律关系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在实施合理使用的行为之前,使用者(严格来讲是潜在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使用者有权实施属于合理使用的行为,显然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也不是因为第三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更不是出于客观现象。产生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只能是著作权人的行为。也就是说,由于著作权人自己的行为而在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产生了合理使用的法律关系。正是由于著作权人自己的行为,使用者才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著作权人自己则承担了义务。著作权人自己的行为主要是创作作品的行为和传播作品的行为,产生合理使用权的依据只能是这两种行为中的一种。通过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考察,我们发现,只有传播作品的行为才是合理使用权产生的依据。这意味着,只要著作权人传播其作品,使用者就享有了合理使用权。这种合理使用权是使用者实际使用之前就存在的,由于这种权利的存在才使其有权使用作品(或者著作权),任何妨碍其使用的行为均侵害其权利。但是,在著作权法上,构成合理使用是有条件的。(美国版权法第107 条规定了在确定合理使用时的四个因素:(1)使用行为的目的和特征;(2)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性质;(3 )被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及其在享有著作权作品中的重要性;(4)使用行为对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在实施具体的使用行为之前,合理使用者无法向著作权人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因为判断构成合理使用的标准必须在实施合理使用行为之后才有意义。在使用者具体实施使用行为之前,其将来的使用行为是否“合理”尚在未知之中,何来“合理”使用的权利?
合理使用关系与相邻关系明显不同。(吴汉东博士将相邻关系作为私法上合理使用的一种情形来论证合理使用是对著作权的利用。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15~116页。)抛开相邻关系的性质不论,相邻关系的产生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动产毗邻。没有相邻的不动产,没有对相邻的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根本谈不上什么相邻关系。而在合理使用关系中,这一切都不存在。合理使用所指向的只是著作权人的作品,而没有使用者的作品,使用者也不享有任何与著作权在性质上相同的权利。用相邻关系来说明合理使用关系,实在过于勉强。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导致合理使用关系产生的依据并不存在。
即使我们不考虑合理使用关系的产生依据,通过对合理使用关系的内容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使用者的“权利”也是不存在的。依民法原理,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法律关系就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主体享受权利,义务主体承担义务。在考察合理使用的权利义务关系时,我们必须从权利义务的主体和内容两个方面出发。在合理使用关系中,使用者是权利人,而著作权人是义务人。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规则,同一个客体的权利主体应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则可以是不特定的。而在合理使用关系中,我们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个特定的义务主体面对众多不特定的权利主体。
不论合理使用的对象是著作权还是作品,作品的著作权人总是特定的,而作品的潜在使用者(或者著作财产权的使用者)却是不特定的,除了著作权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作品的使用者。他们都是对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的同一作品(或者著作权本身)享有合理使用权的权利主体,也就是说,对同一个客体存在着事实上无法统计的各自独立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的义务主体却是同一个人。从现有的民法中是找不出这种奇特的权利的。果真要著作权人面对如此众多的、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权利主体,他最初的选择恐怕只有一个:不创作任何作品以避免这无数个义务。
在合理使用关系中,使用者自己的作为对其权利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关键在于著作权人所承担的义务。没有著作权人的义务,也就没有使用者的权利。著作权人的义务是“服从使用者的意思而进行的作为或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不加禁止与干涉他人合理使用的不作为)”。(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39页。)著作权人如果实施了禁止或者干涉行为, 即违反其义务,构成对使用者权利的妨碍,使用者因此而产生了请求权,得请求排除著作权人的妨碍。但就笔者所了解的范围,尚无使用者请求排除妨碍的实例。从笔者所接触的美国有关判例来看,使用者均在被控侵权时以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理由。从使用者权利角度来考虑,只能说这是权利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如此众多的权利人(可以说是所有的权利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行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不能不让人费解。此外,还有一个用“使用者权利”说难以解释的现象:在著作权丧失之后,合理使用权也随之消灭,原著作权人自然无需承担什么义务了,如果原著作权人采取了某种技术措施使他人无法对其作品进行合理使用,并不构成对其义务的违反;在他享有著作权的时候如果采取这种措施,却违反其义务,这不能不说是非常荒谬的吧?
因此,我认为,合理使用并不是使用者的一项民事权利,而是对著作权人主张著作权的一种限制。当使用者实施了属于合理使用的行为时,他的行为不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使用者无权也不可能向著作权人提出什么主张,只是在著作权人指控使用者侵权时,使用者可以将其使用属于合理使用作为一种抗辩理由。
我否认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民事权利,并不等于不承认合理使用的权利性质。民法和知识产权法通说认为,著作权法具有双重目的:其一,保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作品的作者因其创作活动而应享有的权利和传播者因传播活动而应享有的权利;其二,促进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著作权法所要实现的双重目的,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从一致性上看,著作权法通过授予作者对其作品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即著作权)而保护了作者的利益,并将这种保护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作者的智力创作活动都是在继承和吸收了前人的智力成果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完成的,是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延续和发展,而不仅仅属于作者个人,其成果应由全人类分享。
著作权法要实现其双重目的,就必须在垄断与分享之间创设并维持一种平衡,也就是“各种冲突因素处于相互协调之中的和谐状态,它包括著作权人权利义务的平衡,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3页。)合理使用制度正是体现了垄断与分享之间的平衡,合理使用虽然规定在著作权法上,但它并不是著作权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对著作权所施加的限制。这种限制的直接法律依据就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因此,我认为,合理使用就是言论自由在著作权领域中的延伸。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合理使用确实是社会公共所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承认合理使用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意义并不在于某个特定的使用者可以要求著作权人如何如何,而在于国家不得取消或者不合理地限制合理使用制度。在美国,合理使用制度是通过判例法确立的,最终得到1976年著作权法的确认。近年来数个与著作权有关的重要法案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些法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版权保护法案》(Nii Copyright Protection Act of 1995)和《1996年数据库投资与制止盗用知识产权法案》(H.R.3531:Database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这两个法案均强化了权利人的独占权,而对使用者的合理使用却规定不多,由此而招致美国公众的普遍反对。)对合理使用这样一项宪法权利的忽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过,为了保障言论自由而创设的合理使用制度为使用者创设一项民事权利。而且,在涉及言论自由与著作权的关系时,法院也并不总是倾向于言论自由。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在一份判决中写道:“我们承认,就公众获取(新闻)的权利而言,公众对‘使电视广播更能为其利用’享有有限的利益。如果WXIA(本案原告)完全拒绝准许公众观看其广播的录像带或者记录稿,则公众的这种利益或许受到威胁。但如同最高法院在Sony案中清楚指出的,公众利用广播的利益并不对每一个使更多观众观看电视广播的行为都提供保护。”(Pacific & SouthernCo.V.Duncan(744F,2d 1490)案的法官意见。)法官通常是在著作权与言论自由中间找出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来兼顾各方利益。
四、数字化与合理使用
在数字化传播技术之下,作品(包括表演、广播电视节目)均可用数字“0”和“1”的系列编码体现出来,所有数字化作品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处理和存储。作品数字化使其权利人更难以控制作品的使用,日本东京大学的中山信弘教授精辟地指出,在作品的使用过程中,“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并没有被一根无形的绳子联系起来”,“音乐的著作权人,对于收听者的录音,事实上是无法控制的”,不过,因音质的劣化,“无限制的录音因此而受到阻止”,“但在数字时代由于复制不会引起音质的劣化,原件与复制品之间在品质上并无差异,所以上述障碍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日]中山信弘:《数字时代著作权法的变化》,《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此外,在数字化时代, 作品的复制成本的降低和复制速度的提高,作品的权利人根本无法以法律控制对其作品的使用。
面对此种局面,著作权人无法从法律上得到更多的保护,只能在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对作品的复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加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使他人无法对作品进行复制。这种做法在计算机软件行业和新兴的DVD制作业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著作权人的这种做法并不是直接针对合理使用者的,而是针对非法盗版者的。但是,“加密”使得使用者所要进行的“合理使用”无法实现。若依“使用者权利”说,著作权人的这种做法显然侵害了使用者的权利,应负有排除妨碍之责。从积极的方面讲,使用者为了实施其合理使用权,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解密”。
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加密”是著作权人实现其著作权的一种方式,使用者无权要求著作权人不进行“加密”或“解密”。至于使用者的“解密”行为,现在虽然没有见到禁止的明文规定,但从有关法律和条约的精神来看,通常也是不允许的。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1996年12月20日通过,尚未生效。该条约第11条的标题为“有关技术措施的义务”。)第11条的规定,对于那些阻碍为实施著作权而由作者采取的技术措施以及为限制未经作者许可或法律准许的行为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行为,缔约方应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在条约的草案中,该条原有三款,其中第一款要求,各缔约方将那些明知或应知将用于破坏保护的设施的进口、制造或销售,以及提供或演示那些具有同样破坏保护的效果的服务,确定为非法;第二款要求各缔约方应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救济以制止第一款中所提及的非法行为;第三款则对“破坏保护的设施”进行了定义,凡主要目的或主要效果在于使那些限制或禁止本条约授予的权利所涉及的行为的任何过程、处理方法、构造或系统不能发挥作用的任何设施、产品或结合于设施或产品中的部件,均为“破坏保护的设施”。
结合条约和草案的精神,我们认为,使用者为了实施其合理使用的行为而自行“解密”,法律并未予以禁止。但是,任何有助于“解密”的工具的制造或销售以及提供“解密”服务,除非这些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合理使用或法律所允许的其他行为,否则就是非法的。
另外,在随数字化而出现的网络环境中,使用者的合理使用受到更多的限制。比如,在通常情况下,使用者为个人学习目的复制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但在网络环境中,如果将这种复制品置于网络上,则不再是合理使用。由此可见,随着作品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了保障著作权的实现,总的趋势是对合理使用进行必要的限制。
五、结论
通过以上各个方面的论述,我的结论是,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中为平衡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是对著作权进行限制,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不及于的例外的范围,而不是授予使用者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使用者基于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条件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使用,但使用者无权要求著作权人为或不为任何行为。对著作权的这种限制本身必须是合理的,一旦技术的发展使这种限制不合理,就必须予以适当调整,对这种限制措施加以限制,以确保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