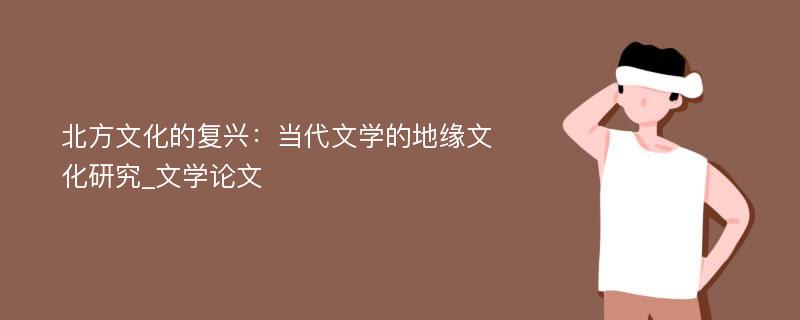
北方文化的复兴——当代文学的地缘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地缘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方文化在衰落吗?
北方——黄河流域,从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朝代都建在北方——周、秦、汉、唐、宋……然而,也许是应了“有兴就有衰”的老话,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从沿海登陆,东南沿海地区成了现代化的前沿,而北方却显然落后了。对此,当代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曾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做过评说:“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中心,大体沿着自东向西,继之又由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转移。”[①a]他还引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关于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总趋势是“由北而南”的论述,描绘出中国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壮阔图景,并进一步揭示出“近代科学、近代政治运动连同近代工商业在东南诸省兴起后,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内地延伸、发展,形成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运动方向,这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迁徙方向恰好相反”[②a]的历史走势。
当代作家中,也有几位注意到了“北方文化的衰落”这一现象——
例如“寻根派”李杭育就曾在1985年将中国文化分成“规范”文化和“规范之外”的文化两类。他认为,“中原文化便是中国文化之规范”,而“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那便是“绚丽多彩的楚文化”、“吴越的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的开放、坦荡”、“老庄的深邃”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那“原始、古朴的风韵”……[③a]这位浙江作家寻吴越文化之魂,意在张扬浪漫古魂、民间精魂,意在反“规范”、反“传统”。
又如北京作家张承志也曾在198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西省暗杀考》中记录下西省回民的叹息:“……以后的事,海边热闹多旱地消息少。……英雄志士轮到南方人里出;陕西迤西好像给人忘了,无声无息。”为什么复仇的口唤就是不来?为什么奇迹就是不肯降临?”人怎么不能如愿,养育的主啊……”于是,作家也浩叹道:“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你这广阔无垠的西省大地,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悲鸣,一位热血男儿的浩叹。
再如陕西作家贾平凹,也在谈及《废都》的主题创意时说:“‘废都’两字最早起源于我对西安的认识。西安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但已在很早很早的时代里这里就不再成为国都了,作为西安人虽所处的城市早就败落,但潜意识里其曾是十三个王朝之都的自豪得意并未消尽,甚至更强烈,随着时代的前进,别的城市突飞猛进,西安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已无什么优势,这对西安人是一个悲哀,由此滋生出了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的放达和一种尴尬的焦虑。西安这种古都——故都——废都的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的心态也恰是中国人的心态”[①b]。——一个“废”字,浸透了荒凉、颓唐、绝望的意味,也表达了贾平凹这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淫得比一般同龄人要多一点点”[②b]的奇人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绝望之情。
如果说,南方作家李杭育宣告中原文化之根的枯死还可以看作是南方文化向北方文化的挑战,那末,北方作家张承志、贾平凹悲叹北方文化的衰落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直面文化的悲剧?意味着北方文化无力回应南方文化的挑战?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另一面:
北方在经济上是不如南方,但北方文化却并不因此而黯然失色。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北方文化精神的一次次大放光芒?
1976年清明节,是北京民众自发掀起的“四五运动”率先敲响了极左暴政的丧钟;1977年底,是北京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率先举起了“伤痕文学”的旗帜,复兴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改革文学”的主将蒋子龙、张洁、柯云路、陈冲都是北方作家;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王蒙、马原、刘索拉、徐星、莫言、张承志、史铁生也是北方人;八十年代的“寻根派”中,贾平凹、郑义、阿城、莫言也是北方人,其中,贾平凹赞美商州的淳朴民风、郑义讴歌老井村人的坚韧民魂、阿城谱写了平民百姓以柔克刚的风骨、莫言张扬高密东北乡的酒神精神,都极富凛然正气或生命激情,毫无颓败气息;八十年代后期,“新写实”崛起,刘恒、刘震云、王朔等北京作家都是风云人物;九十年代初,北京作家张承志、史铁生几乎同时发表了高扬人文精神的名篇《心灵史》、《我与地坛》,在文坛上再次鼓起了理想主义的风帆;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程海以各自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热爱命运》汇成了“陕军东征”的威武阵势,开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热”的新风;山东作家张炜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柏慧》、《家族》,讴歌民魂、批判现实、反思历史,每一部都产生了“轰动效应”,张炜也因此成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镇;另一位山东作家刘玉堂不断谱写着温馨的民风消解政治运动毒素的美好篇章,被公认为“新乡土文学”的主将;东北地区的三家当代文学评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文艺争鸣》)在当代文论界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文论不景气、文论刊物难办的当代文论界,创造了一个奇迹;东北作家马原、洪峰、阿成、迟子建、述平、刁斗也都显示出雄厚的创作实力和令人刮目相看的锐意求新求变的充沛活力……
匆匆一瞥,好不壮观!如此说来,又怎能过于武断地下“北方文化已经衰落”的断言?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的社会发展规律,早为人所共知。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大潮汹涌,激活了当代人的生命热情。北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刚烈之魂、豪放之气、壮美之情也深深融入一代又一代北方人的血液中——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它异化为造神的狂热、党同伐异的偏狭;到了思想解放的岁月,它升华为生命的呐喊、创造的激情、慷慨的壮歌。
写到这儿,耳边又响起《黄河大合唱》那激动人心的旋律,响起八十年代末歌坛“西北风”的高亢、炽烈的歌声,响起“京城摇滚人”生命呐喊激起的一阵阵热潮,响起亚运会开幕式上那响彻云天的北方鼓声……一切,都是北方豪情的见证,北方生命热情高扬的象征!
而当北方作家梁晓声在他那篇《龙年一九八八》的著名文章中写下“文学绝对地需要一种文化的传统和氛围来养育。深圳它太新了,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中国’两个字”,“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这样一些警世的句子时,当北方作家张承志在他的小说《胡涂乱抹》(尽管此篇发表于1985年,早于《西省暗杀考》四年)中讴歌“伟大的北京城,伟大的中国年轻人,其伟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渴望一场胡涂乱抹。他们讨厌公允和平庸……北京真是座奇异的城。它不会永远忍受庸俗,它常常在不觉之间就掀起一股热情的风,养育出一群活泼的儿女”时,他们都显示出了北方的自尊和北方的豪情。
是的,北方自有北方的豪情。——它不会被时光销蚀,不会被柔情化解,它是民族精魂的命脉所系,是人文精神的根系所在;它还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象征,是人不甘平庸、不堪沉沦、不甘异化的血性的证明。
北方:苦难成全了坚忍
北方的自然条件比南方严酷。中国历代的战乱又主要集中在北方。因此,北方比南方多苦多难。苦难消磨了多少生命热情,同时又砥砺出多少英雄豪气!
1979年,在控诉极左暴政的怒潮中,河南作家李准却发表了风格淳厚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志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①c]。——这一番话,在一片悲凉之雾中呼唤出一轮红日:它放射出“文化寻根”的最早曙光,也发散着在“信仰危机”的寒雾中“重建人文精神”的热能。顽强的生命意志,真挚的伦理柔情,机智的生存策略,是黄泛区人民抗御天灾人祸的立足基石。
在北方,有很多这样的生命礼赞、文化颂歌——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天狗》是淳朴民风的赞美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朴实民魂的颂歌;矫健的《河魂》塑造了一群忍受着苦难又抗拒着苦难的胶东人,在反思历史的悲剧时别开生面地发现:“人类竟这般地奇妙,一代一代的人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联系起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化教养如何差异,它总是潜伏在人的心灵里,暗中规定着你的行为。家族就是这样组成的,村庄就是这样组成的,民族也是这样组成的”;郑义的《老井》也塑造了一群忍受着苦难(缺水)又抗拒着苦难(打井)的山西人,“纵然万般缺水,但老井人绝不背井离乡”,打井“打到十八层地狱,我顶上一颗人头”——这又是怎样的民风民魂!还有张承志《心灵史》中那些“可以活在穷乡僻壤可以一贫如洗,却坚持一个心灵世界的人道精神”,“如一片岩石森林般的人民”;还有苗长水笔下那些“至真至诚,情感笃深”的沂蒙山人(《犁越芳冢》),他们忍受了多少苦难,却一直保持了朴实、厚道、仁义的古风……许多动人的故事,都使人想到那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面对那些在苦难中沉沦的人们,许多作家写下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力作。而面对这些在苦难中抗争的人们,作家们唱出了一曲曲崇敬、赞美的歌:坚忍不是麻木,不是懦弱——
有时,坚忍显示为一种刚强:“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得刚强地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总有转变的时候。”“我们穷人家老坟里不长弯腰树,就是磨扇压在身上也不会弯腰。……我这个人是苦水里泡大的,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人,什么苦也吃过,什么罪也受过,什么心也操过,什么气也装过!”(《黄河东流去》中李麦的话)——其中有古老民族生命崇拜的遗风,有对命运轮回的乐观解释,还有“曾经沦海难为水”的豪放气概。中国人历来崇拜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英雄,崇拜“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壮士,也许正是出于一种“苦难崇拜”的文化心态?
有时,坚忍升华为一种豁达:中国人多信“知足常乐”,会“苦中作乐”。阿城在《棋王》中写道:“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惟有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连“家破人亡”、“每日荷锄”都不怕,还有什么能奈他何?以豁达化解忧患,以淡泊轻视苦难:这是道家文化的精髓所在。有了这样的胸怀,就能以柔克刚。
有时,坚忍还养育了美。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记述了这样的人生体验:“‘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到了《插队的故事》,史铁生再次写到了陕北民歌:“不过像全力挣扎中的呼喊,不过像疲劳寂寞时的长叹。……歌声在天地间飘荡,沉重得像要把人间捧入天堂。其中有顽强也有祈望,顽强唱给自己,祈望是对着苍天。”张承志也在《黑骏马》的开篇讲述了“蒙古民歌的起源”——“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劝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荷。”——悠扬的陕北民歌、高亢悲怆的蒙古民歌凭什么叩人心弦?凭对苦涩人生的感悟,也凭化苦涩为抒情的人生的灵性。因此,民歌也成了超越苦难的方舟。
北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也就富有了格外感人的坚忍品格。
北方:刚烈的自由魂
北方自古多豪杰。史书上记载着“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仇也”[①d]。也记载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山东出将”的奇观。艰苦的自然环境得凭刚勇去征服,尖锐的社会矛盾要待刚烈去克服。而一代代英雄豪杰的慷慨悲歌、不朽业绩也凝聚成伟大的自由魂,充溢天地间,感召后来人。
于是,你不难发现:北方作家中,有那么多热血男儿——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都是九死不悔追求壮美理想的奏鸣曲、交响乐,都曾在文坛上、在青年中鼓动起壮美的激情:“我们开始承认了人情和世俗的强大……我们仍然时时发现自己的血液里奔涌着一股力量,那是一种不可制服的自由激烈的神力。”(《金牧场》)正是凭着那神力,他在世纪末的世俗化大潮中岿然不动,谱写出激烈反世俗化的壮美诗篇;还有梁晓声,也在忧患地“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同时,敲响警世的洪钟:“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迷乱、癫狂、咽泣、呓语、呐喊、吼叫、呻吟、低述……是时代本身的情绪”。“自我正在死亡”(《龙年一九八八》)。“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张承志、梁晓声,都是知青出身的作家,愤世嫉俗的热血男儿,勇猛刚烈的北方斗士。当然不能忘了张炜这位山东汉子,当他在《柏慧》中写下“这个不让人喘息一下的时代啊,对于好人,它的心肠是硬的”,“我的全部狂热和焦灼都是从一个点上派生出来的,它简直有着巨大的、无法抵御的能量”。“血脉把一个生命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让其一生都无法挣脱”。“由于我的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血脉,我一直铭心刻骨地记住了:永远也不要背叛和伤害,永远也不要对丑恶妥协”。为此,他宁可愤怒也“绝不宽容”。张炜的愤怒与抗争也显示了北方的良知与血性。
是的,自由意味着高傲,意味着抗争,意味着决不随波逐流的悲壮,还意味着固守精神家园的决绝。
于是,你还可以注意到:正是在礼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北方,却涌现出一批讴歌“酒神精神”的作家,屹立起一群至情至性、敢做敢当的刚烈男儿形象——莫言以《红高粱》中余占鳌的英雄业绩照出了当代“种的退化”的悲剧,贾平凹的《五魁》、《美穴地》、《白朗》塑造出一个个热情似火的土匪形象,他们多被厄运逼入绿林,而一旦走上土匪之路,他们便卸下了循规蹈矩的重负,在杀富济贫的生涯中尽情挥洒自由的豪情;河南作家阎连科的《鲁耀》写活了一个“乐哉游哉,洒洒脱脱”,“人活一世,‘快活’二字”,“为人之所不敢为,道人之所不敢道”的“杠头”形象,意在表明:“我们的祖先中有的人并不挣扎在泥潭里……”[①e]——这些率性而活、痛快一生的艺术形象,足以开拓我们对民族性的新认识:中国百姓从来就有酷爱自由的传统,有蔑视礼教的豪情,有敢做敢当的烈性。“温柔敦厚”、“勤劳善良”或者“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之类一般性说法并不能概括中国民族性的全部。
就是那些朴实、憨厚的农民,平时活得坚忍,坚忍中也积聚起不可思议的炽烈之情,关键时刻喷发出万丈豪情:矫健笔下的天良忍无可忍之时,会走上决死抗争之路(《天良》);王冠笔下的黑衣鼓手们为鼓而生,为鼓而死,那情那义,能惊天地,能泣鬼神(《黑衣鼓手》);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出身贫贱却心比天高,“他性格中有一种冒险精神”,不甘心在土里刨挖一生,虽最终碰壁而终显示出不认命的骨气(《人生》);贾平凹笔下的金狗也不安平庸,立誓“要穿就穿皮袄,不穿就光身子!”他浮躁不安地干出了一番事业,显示了新农民的精神(《浮躁》)……不论成败,不计荣辱,只要争那口气,只要尽那份心——就凭这心劲,北方就有复兴的希望。
甚至那些柔情似水的女性,血管里也奔涌着滚烫的激情——张贤亮笔下的“风流种子”韩玉梅(《河的子孙》)、马缨花(《绿化树》)、黄香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贾平凹笔下的黑氏(《黑氏》)、烟峰(《鸡窝洼的人家》),周大新笔下的汉家女(《汉家女》)、邹艾(《走出盆地》),李准笔下的李麦、雪梅(《黄河东流去》),张石山笔下的甜苣儿(《甜苣儿》)、莫言笔下的九儿(《红高粱》)、上官鲁氏、孙大姑、来弟、招弟、领弟、想弟……(《丰乳肥臀》),苗长水笔下的月梅、素盈(《犁越芳冢》),刘玉堂笔下的刘玉贞(《温暖的冬天》)、张立萍(《温柔之乡》),刘绍棠笔下的红兜肚儿(《红兜肚儿》),李佩甫笔下的李满凤(《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匆匆一瞥:竟有这么多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倔强泼辣、叱咤风云的刚烈女子形象!她们有柔情,更有刚性。她们的夺目光彩足以使传统意义上的“温柔贤惠”、“三从四德”黯然失色。她们以率性而活、尽情而活的动人事迹实现了妇女解放的人生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女性文化的认识。甚至觉得:世纪末中国社会上有目共睹的“阴盛阳衰”现象决非空穴来风,其源头早就在中国女性长期反抗封建礼教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关于穆桂英、花木兰、樊梨花、杜十娘、梁红玉……的动人传统中。
就这样,刚烈的自由魂一直在北方的大地上飘荡。这实在是文化的奇观:“根深蒂固的礼教为什么就是窒息不了自由的精魂、刚烈的民性?反过来说:自由的精魂、刚烈的民性又是怎样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瓦解了礼教的网罗的?如果我们可以把一部中世纪史看作一部人俗与天理交战的历史,那么,人欲的最终获胜又向我们昭示了怎样的历史定律、文化奥秘?
北方人的刚烈性情使得北方文学也天然富有了阳刚之气。至少,在上面列举的那些作品中,我们感受不到北方文化“衰败”的气息。诚然,在《废都》、《橡皮人》、《伏羲伏羲》、《故乡天下黄花》、《私刑》、《黄尘》这样一些作品中,弥漫出一片“衰败”的气息,可《红高粱》、《九月寓言》、《北方的河》、《绿化树》、《黑衣鼓手》、《白鹿原》这些作品都充溢着阳刚正气。我愿意把“衰败”与“复兴”看作一对并峙的文化主题,一个北方文化在天翻地覆的世纪里蜕变的痛苦象征。具体地说,“衰败”的是那些注定要衰败的文化(那些僵化的礼教、那些垂死的疯狂、那些无可救药的麻木、那些病入膏肓的痼疾),而“复兴”的则是永远的生命意志,永远的创造激情,永远的自由渴望,永远的纯洁真情。
而且,北方的刚烈气质注定要在世道巨变、文化转型的世纪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北方作家群英杰辈出,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北京作家群自“文化大革命”前就一直是文坛关注的热点,一直以朴实、浑厚的文化品格为世人所看重;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河北作家群在八九十年代的崛起,也显示出或豪放、或朴实的北方品格;八十年代中,在现代派文学大潮汹涌之际,北方作家麦天枢、贾鲁生、赵瑜却掀动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大潮,北方作家王蒙、刘心武也针对“文学失重”现象敲响了警钟,北方作家张承志、史铁生则同时开始了叩问宗教的神圣事业——一切都不谋而合,不正昭示了北方的精神么?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新写实”的冷漠之风和“王朔热”的玩世之风盛极一时,甚至连一些一贯张扬正气的著名作家也随风转向了,又是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横空出世,升起了九十年代高扬人文精神的第一轮朝阳,梁晓声的《浮城》、张炜的《柏慧》忧患深重,再度燃烧起批判时弊的激情……。北方作家就这样几度在文学失重的危机中以阳刚之气充沛的一篇篇力作,维系了文坛的平衡,展示了北方精魂古风常在的强大魅力。
人类永远离不了崇高的理想,离不了刚烈的心性,它们将成为批判时弊的武器,成为超越现实的力量。——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北方文化精神不可能衰亡,甚至注定会永放光芒。
北方:涌动的新潮
中国在发生着巨变。北方涌起了一阵阵新潮。在新潮跃动的深处,我们可以感觉出北方文化新生的活力。北方的刚烈古魂是怎样包容现代新潮的呢?北方的文化新潮又是如何为刚烈古魂注入新鲜活力的呢?
早在1985年“新潮文学”以前,北京作家王蒙就于1979年发表了“意识流”小说《夜的眼》,以后又发表出《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相见时难》……一批“新潮小说”,令人刮目相看。有人在抱怨王蒙偏离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写实路子的同时,却忽略了王蒙“新潮小说”的民族特色、当代品格——上述作品中,除《夜的眼》以外,哪一篇没有浸透作家对历史、对民族、对革命、对理想的深沉之思?当作家写下“政治关系着的是亿万人民的命运”(《相见时难》),“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薄,更永远不会中断”(《海的梦》)这样一些深沉感人的句子时,我们便感受到了北方的使命感、北方的激情。
在1985年的文学新潮中,马原、莫言、刘索拉、徐星、张承志、史铁生这些北方作家都显示出非同一般的魅力。马原的西藏探险故事展示出浪漫气质,莫言的故乡记忆燃烧着灼人的激情,刘索拉和徐星的荒诞之作表示出叛逆的意志,张承志的草原故事和黄土高原故事奏响了理想主义的旋律,史铁生的人生沉思也涌动着圣洁的情思……在多元思潮碰撞的文坛上,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激情与冷漠的对比、浪漫热血与荒诞意识的交锋、宗教情感与浮躁心绪的争鸣……一切的一切,汇成了北方文化充满活力的交响曲。
甚至在偏远、闭塞的晋北地区,也产生了吕新那样的新潮作家。他的《农眼》、《雨季之瓮》、《黑手高悬》、《抚摸》都极富现代性,极具博尔赫斯小说意味,尽管如此,小说中对晋北山区苍黄风景的神奇描绘,对“土里土外热烈地泛着一种血腥气”、“流油不止的晋北山区啊热烈无度的晋北山区”的渲染,对晋北农民想“看看我们的户口”的请求的着力刻画(《农眼》),依然使人强烈感受到浓郁的北方气息。因此,尽管吕新在谈及自己的文学观时只说:“一个小说家应该找到与自己的声音相吻合的那种说话的方式与精神内涵,找到那种隐藏动作与感觉中的真正的主题”,小说中那些富于晋北山区特色的风景和人生印象,依然打上了深刻的北方农村印记。在一贯以写实功力深厚著称的山西作家群中,也终于产生了吕新这样的新潮作家,不能不说是北方文学复兴的又一象征。
陕西也一直是写实传统深厚之地。到了贾平凹,也拿出了新潮的奇文:这位一贯写实的作家在1986年患病住院后,发表了一系列风格诡异的魔幻之作——《龙卷风》、《瘪家沟》、《太白山记》、《白朗》、《烟》……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写得亦真亦幻(如《龙卷风》、《瘪家沟》),或写得荒诞不经(如《太白山记》、《白朗》、《烟》),都意在展示神秘文化心态的深不可测,寄寓高深玄奥的禅机、佛理[①f]。在当代中国的“新潮文学”中,贾平凹的魔幻之作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不同于那些或多或少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的作品,贾平凹直接从民间文化中汲取素材,写成极具神秘意味的当代志怪,堪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派文学”(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话题,容另文论述)。
——就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却以文学新变的大潮显示了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勃勃朝气。北方的“新潮文学”、“新潮艺术”与北方的“传统文学”、“传统艺术”因此而各显异彩,向我们展示了北方文化裂变的壮阔景观。
北方是传统根基深厚之地。但北方也早有容纳“新潮”的传统。钱穆先生就曾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①g]“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②g]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品格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化命脉能历尽劫难而几度涅盘,与此很有关系。在历史上,中国容纳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匈奴、鲜卑、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满、回、藏、苗……各民族,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宗教;近代以来,中国又容纳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种胸怀本身就显示了一种活泼、健康的生命力。如此,又何从说起“衰亡”二字?
有些东西在衰亡;有些东西在新生;有的衰亡于此时,又复兴于彼时(如孔家店在“五四”时期被摧毁,几十年后又重建起辉煌的殿堂);也有的崛兴于一时,转眼又成过眼云烟(例如“五四”时期、六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中期三度大起大落的“反传统”偏激思潮)……历史变迁的风云常常出人意料。狡黠的理性就这样不断捉弄着自以为是的人们。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太武断地宣告北方文化的“衰亡”?
在八十年代的浮躁之潮过后,九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正在趋向沉静——一切都是必然的:冲动过后是平静;破坏过后是建设。而北方文化根深蒂固的坚忍之魂、刚烈之魂、博大之魂也必将在建设的年代里再放光芒。
南方的经济奇迹与北方的文化奇迹相映生辉,成为世纪末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到下个世纪,南北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交流会最终谱写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格局中政治、经济、文化之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吗?
未来会回答我们的。
注释:
①a②a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第43页、第48—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a 《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①b②b 治玲:《〈废都〉几乎忘了贾平凹》,《今日名流》1994年第2期。
①c 李准:《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第2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①d 引自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七,第3页、第41页。广益书局1923年版。
①e 《“活”乱弹》,《中篇小说选刊》1990年第1期。
①f 笔者曾撰文《贾平凹:走向神秘》,载《文学议论》1992年第5期,可参看。
①g 《中国文化精神》第51页,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
②g 《中华文化史导论》第12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
标签:文学论文; 张承志论文; 贾平凹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文学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黄河东流去论文; 读书论文; 红高粱论文; 白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