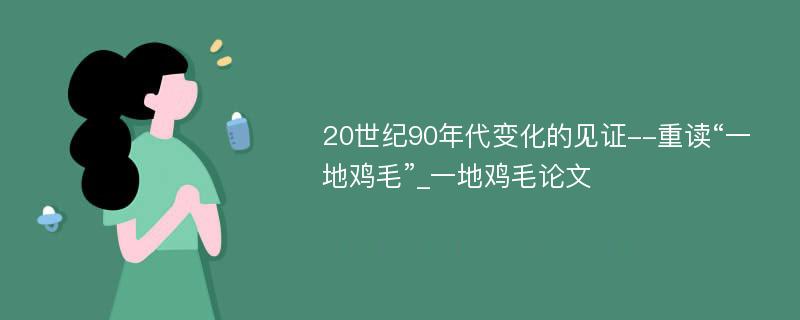
80—90年代转变的证词——重读《一地鸡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词论文,鸡毛论文,一地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作家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县一个农民家庭,15岁参军到部队。1978年复员后到一个中学当老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农民日报》工作。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以现实为题材的《塔铺》、《新兵连》、《单位》等,也有“故乡”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近年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可谓多产作家。其作品多次获奖,在当代文坛中享有一定的赞誉,王朔称为“当代小说里真正能够对我构成威胁的一个”,[1](P69)他的《一地鸡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小说家》,后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通过重新审视这部作品及关于它的各种评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80—90年代转变的切入口。
一、80、90年代之交的生活感觉
作品大致写成于1990年前后,这可以看作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主人公小林经历了双重变化:就个人而言,是从学校走向社会(《单位》中写他1984年毕业);就社会而言,是经济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以此为背景展开的人物生活场景描述了他所面对的各种日常琐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80、90年代之交生活感觉的参照物。
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地位、思想的变化无疑是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大学生曾是天之骄子,被冠以各种光环和期望,作品通过小林夫妇和“小李白”的变化来表征8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历程。在上大学时,“小李白”和小林“都喜欢写诗,一块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那时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而且“‘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对文学、文化和各种思想的关注与喜好是当时的时代主潮。“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李陀在回顾80年代时指出:“80年代一个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抱负。……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就从这里开始/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这是江河的几句诗,很能反映那时候人们的情绪。”[2]占据时代中心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大学校园、在街头、在广场,他们都成为受人欢迎、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一时风头之劲,比起现在的传媒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今天的明星是很世俗的,而当时的‘文化英雄’却带有一种神圣化的理想光环”。[3](P35)
但伴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现实发生了逆转,“中国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笑话:80年代,有人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80年代末,变成了在街上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经理”。[4](P5)经商成为时代的热潮,因而不难理解作品中人物前后巨大的转变。小林问“小李白”现在还写诗吗,“小李白”以极端的方式给予了否定:“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小林夫妇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生活被各种具体的琐事填充,“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这种重复性否定了先前对生活的设想:“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话语流露出无奈,现实生活自有其逻辑和规则,单纯的理想追求现在被物质利益的纠葛和关注所代替。
当个人生活从宏大动员中抽身而出之后,个人开始切实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感觉。“现代生活,要求每个个体去独立地寻找中道,而不再有那么一个现成的过法”,“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人们必须直接面对‘过日子’本身……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的‘理’”。[5]“烦恼”是新写实小说中人物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词,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作家们对这一话题的青睐及有意铺陈、渲染;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情节取向。要处理诸如对付保姆、孩子看病、入幼儿园等事情,需要依靠心机、或利益的交换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心烦和难以应对。小林夫妇带着感冒的女儿去看病,感慨“现在给孩子看一次病,出手就要二三十;不该化验的化验,不该开的药乱开。小林觉得,别人不诚实可以,连医生都这么不诚实了,这还叫人怎么活?……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小林和老婆都觉得是来上当”。这一生活感觉可以套用社会学上的术语“相对剥夺感”,它是“由美国社会学家S.A.斯托弗等人提出,是指剥夺是相对的,人们对其处境感到怨恨或不满,未必是在绝对意义上被剥夺,而是与某种标准相比感到被剥夺了。……美国社会学家Robert.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相对剥夺感理论,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6]作品中还有很多情节传达出人物的这种感觉,如小林为了帮老婆调动工作给人送礼,结果被拒,“尴了半天,两人才缓过劲儿来。小林将箱子摔在楼梯上:‘×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又埋怨老婆:‘我说不要送吧,你非要送,看这礼送的,丢人不丢人!’”小林家的保姆任由小林的女儿玩凉水,结果引发了感冒,小林怕引起风波没有告诉妻子。小林老婆的单位开通了班车,“原来以为坐班车是公平合理,单位头头的关心”,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领导老婆的妹妹,她“马上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的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小林的女儿靠邻居的帮忙上了自己中意的幼儿园,但后来才发现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和打算,小林老婆对小林说:“他们孩子哭闹,去幼儿园不顺利,这才拉上咱们孩子给他陪读”。“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这种个人生活中的相对剥夺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了当时的现实形势,改革开放在80年代初曾给人们带来希望,“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整个社会的主流情绪还是乐观积极和昂扬的”;[7](P231)而之后形势的发展无疑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生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们其心情是沉重的,这是一段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巨大转折且折角最尖锐的时期。……物质的贫乏和生活的困窘在短暂的缓和之后一下子又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8](P279)“1988年我们曾对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三个群体进行调查,几乎所有群体都认为自己与其他群体相比地位是最低的,……那么到底是谁‘赚了’呢?或者说,社会上得到实惠最多的又是谁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的群体都会指向其他群体,并且认为自己得到的实惠很少”。[9]有资料显示:“1988年中国社会持续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完成了其最初的生产刺激后越来越走向迷惘。其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它所滋生的官僚腐败行为,某些方面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和宣泄,使得当时的民众怨气于心。”[10]小林夫妇和其他普通人一样承担着改革的负面结果:医生诚信、利益交换、人际交往的实用化……
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个首要现实问题是物价上涨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情况是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的,“1988年市场物价更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高幅度上涨,全年上涨18.5%,其中12月比上年同月上涨26.7%”,[11](P8)这“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12](P330)可见当时的情况是较为严重的。将作品中的情节置于这一语境之中,或许可以理解小林夫妇对经济开支的重视,带来烦恼的是它,带来幸福感的也是它。小林老婆为一块豆腐大发脾气,二人吵架也都离不开经济损失,如打碎暖水壶、花瓶。再如他们带女儿去看完病后,小林老婆说自己上次“感冒从单位拿的药还没吃完,让她吃点不就行了?大不了就是‘先锋’、‘冲剂’、退烧片之类,再花钱也不是这个”!“小林觉得老婆的办法也可试一试。……孩子的病也确诊了,老婆想出办法,看病又省下四五十块钱,这不等于白白收入?大家心情更开朗”,两人挑选礼物也同样是基于价格考虑。这些细节不断重复出现在文本之中,显然是在有意提醒我们经济的得失对于个人生活感觉的切实影响,而这种生活感觉无疑是对80、90年代之交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
二、从身份到契约:“经济人”的形成
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社会逐渐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人的心态在这一过程中也随之发生改变。作品中小林和“小李白”的不同处境是当时社会阶层重新分化、组合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度设计的思路是“通过单位制和身份制,把个人都纳入行政框架,使人成为高度的‘组织人’”。[13](P207)同时,“国家全面控制单位,单位高度依附于国家。……单位实际上成为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和附属物”。[14]单位主要通过资源配置、身份确认等方式和手段来承担起连接个人和国家的功能。在作品中,小林夫妇都处于单位制度的体系当中。“小李白”这种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的人群的出现显然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时一些人从事个体经营是出于生计的考量抑或无奈,“小李白”毕业后“分到一个国家机关。后来……辞职跑到一个公司去了”,再后来“公司倒闭了,就当上了个体户”,他对小林说:“不卖鸭子成吗?家里五六张嘴等着吃食哩!”而有些是因为被单位制度所排拒,“‘为何要当个体户?’王朔的回答是‘被逼的’。……复员后分配在一家医药公司当药品推销员。由于种种原因,他辞了职。……‘当时如果有个单位收留,我也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15]其中一些成功者在经济收入上可以自足,甚至超过薪资阶层。1988年时,“一些小道消息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着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要知道,那年首都北京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16]
但就社会制度的施行效果而言,显然单位体制内的人能得到更多的保障,不仅是经济上、生活上的,也包括身份。对多数人而言,放弃单位制度给予的身份确认而“下海”并非一个好的选择,“离开单位,放弃单位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丧失一切……城市居民同单位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17]而现代经济时代恰恰是要实现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8](P97)小林和“小李白”处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他们的身份因此有着不小的差距。当时对个体经营者的成见是较为深固的,小林帮“小李白”卖鸭子时碰到处长老关,便解释说自己碰巧遇见同学,“觉得好玩,就穿上同学的围裙坐那里试了一试,喊了两嗓子,纯粹是闹着玩……他并没有卖鸭子,给单位丢名誉”。老关说:“我说呢,堂堂一个国家干部,你也不至于卖鸭子!”阿城回忆说:“80年代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工人还好。他们甚至看私营小贩倒卖牛仔裤的笑话:你蹦跶吧你!有俩糟钱儿敢下馆子,你有退休金吗?摔个马趴,你有医疗公费吗你?幸灾乐祸。”[19](P30)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小李白”说服小林帮忙时劝他不必太“要面子”,而小林“一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穿上白围裙,就不敢抬眼睛,不敢看买鸭子的是谁,生怕碰到熟人”,这些都说明身份确认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小林在这件事情上前后心态的变化其实也反映出经济时代对于个人思想转变的影响,“下班挣个零花钱有什么不可以?有钱到底过得愉快,九天挣了一百八,给老婆添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五斤重的大哈密瓜,大家都喜笑颜开。这与面子、与挨领导两句批评相比,面子和批评实在不算什么”。“小李白”给他报酬并说以后还会请他帮忙时,他“这时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声音很大地答应:‘以后需要我帮忙,你尽管言声!’”这种心态的变化也暗示着“新人”的出现,如果借经济学上的概念,可以把小林夫妇思想的变化概括为“经济人”的形成过程,这是与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的时代语境密不可分的。系统论述过“经济人”思想的亚当·斯密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怀有“自利的打算”,即“利己心”或“自爱心”,[20]他举例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1](P13)
这种新人的出现与当时经济时代的热潮密不可分。现实迫使人们逐渐变成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交换的原则开始被人们接受,并且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人际交往、情感付出等),成为现实生活的处事方式和逻辑。李陀说:“卢卡奇有一个洞见,说,商品形式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近二十年中国来了个‘大跃进’,不过是建设市场经济的大跃进,其中一个重要改造,就是对契约关系的建设。……很多人都没注意,商业契约的原则,现在已经渗入商业活动以外的我们日常生活里……你给我什么好处,我给你什么好处,都是无形的契约。”[19](P268)
“经济人”必须要懂得各种操作规则而且善于处理各种事情,否则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小林夫妇便经历了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小林老婆想换工作单位,一开始找了不止一人帮忙,结果“犯了路线性错误。……找的人多了,大家都不会出力”,最终没调动成。小林想送女儿去外单位的幼儿园,却发现“人家名额限制得也很死,没有过硬的关系,想进去比登天还难”,他本来想“直接把困难向人家说一下,看能否引起人家的同情”,去了“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天真”。园长说如果“能帮他们搞到一个基建指标,就可以收下小林的孩子”。因为这两次失败经历,小林老婆抱怨小林“没本事”,他也为此而自责,其实他们抱怨的是没有可用来交换的资源。而后来,当看水表的老头求小林帮忙处理当地的一个批文时,“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小林此时显然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运用规则,事后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老头送的微波炉,“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
“经济人”在个人生活中把对生活的需求精细化,并且追求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如小林老婆嫌单位太远而想要调动工作,他们想让女儿上最好的幼儿园。“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22](P358)小林夫妇在开支上精打细算,“等孩子入托,辞了保姆,一个月省下这么多钱,家里生活肯定能改善,前途还是光明的”。这种精细化也被运用到感情的付出上,曾经救过小林一命的老师来北京看病,他一开始很高兴,但随后意识到自己无力帮忙,便产生了负疚感。送老师走时,他“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悼念文章:“说大领导生前如何尊师爱教,曾把他过去少年时代仅存的两个老师接到北京,住在最好的地方,逛了整个北京。小林本来对这位死去的大领导印象不错,现在也禁不住骂道:‘谁不想尊师重教?我也想让老师住最好的地方,逛整个北京,可得有这条件!’”如果说这是源于经济和现实局限而带来的无奈,那么他在对待老家人态度的前后转变则有主动的意味,小林老家经常来人,“往往吃过饭,他们还要交代许多事让小林办。……一开始小林爱面子,总觉得如说自己什么都不能办,也让家乡人看不起,就答应试一试,但往往试一试也是白试……后来渐渐学聪明了,学会了说‘不,这事我办不了!’”小林一开始在招待上热心周到,后来发现“你越热情,来的人越多,小林学聪明了,就不再热情。不热情怠慢人家,人家就不高兴,回去说你忘本。但忘本也就忘本,这个本有什么可留恋的!”可见,利害关系的考量逐渐成为感情付出的准绳。
在作品最后,小林夫妇终于熟练掌握了操作规则,主动给幼儿园老师送去炭火,“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所谓的“道理”对应着经济时代的各种观念和规则,虽然其中或许带有源于现实的无奈感,但毕竟主人公顺应了这种“道理”而转变成为了“经济人”。
三、进入90年代的方式
当时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命名大致有:“新写实小说”(丁帆、徐兆淮)、“新写实主义”(雷达)、“后现实主义”(王干)、“现代现实主义”(陈骏涛)这几种。[23]《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说:它“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上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当时有评论家认为,新写实小说不再遵循塑造典型化人物的创作规范,是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和突破,而另一些评论家则反对这种以碎片化形式呈现的日常生活描写。
相比之下,评论家们更多地关注作品表达的思想及作家的姿态等问题。从这些迥异的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80年代的共识已经破裂,这背后展现出理解、进入90年代的不同方式。
知识分子在面对90年代时大都体验过困惑、迷茫,“80年代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24]王晓明说:“进入90年代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困惑: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那以后接着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说80年代知识分子鼓吹‘现代化’,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我在90年代亲见的这种种变化,实在和80年代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25](P4)在面对现实时的无奈感上,作家和批评家是相通的。王安忆说:“日常生活是很有力量的,现实生活实践着因果关系,所有因果关系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检验,逃不过去。”[26](P309)池莉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自我设计这词很流行很时髦,但也只有顺应现实它才能获得有限的收效。常常是这样:理想还没形成,就被现实所替代。……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27]在《一地鸡毛》中,如“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是用反语的方式来表达无奈和沮丧。再如“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从这种近乎调侃的语调中,我们不难读出作者的困惑和无奈。刘震云在《磨损与丧失》一文中将这种沮丧、疲惫感倾泻无遗,“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为“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刀山火海还要让人发怵。因为每一件事都得与人打交道。刀山火海并不可怕,我们有能力像愚公一样搬掉它,像精卫一样填平它。但是我们怕人”。结果,“生活固然使我们一天天成熟,但它也使我们一天天变老、变假,一天天远离‘我们’自身。成熟固然意味着收获,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成熟不也意味着遗忘和丧失吗?”[28]正是基于这种表述,陈思和认为这种写作并未放弃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藏在民众中间,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态度来表现难以表述的时代真相的认识。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得更加含蓄更加宽阔”。[29]
批评该作品的评论家或许并未注意到作家的这种无奈感,他们认为作家采取了背弃启蒙话语、向现实生活妥协的创作姿态、立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出现,表明了作家精神上的困窘状态”。[30]这些批评站在启蒙话语的立场指责日常生活造成理想的失落、异化、扭曲等,“历史被阉割了,剩下的只有油盐酱醋,吃喝拉撒。……理想主义便不得不从现实中默默遁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存在哲学——活命哲学”。具体到《一地鸡毛》,金惠敏认为它“所指示的是如何做一个庸俗的小市民:得便宜不要脸面,行贿心安,受贿理得,随波逐流”。[31]还有评论说:“刘震云的小说具有共同的意象系列——将实存世界最鄙俗、最污秽、最卑贱的物象供奉在艺术世界最重要最显眼的位置上。刘震云独特的感受生活的方式——从每个细节看出生活的糜烂和人性的耻辱——由此得到了强化。”[32]该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权力崇拜、物质崇拜”,“无论是机关小说还是历史小说,无论是权力的奴隶还是物质的奴隶,刘震云笔下的人物都是这种昧于理性和良知的奴隶”。[33]这些指责表明了批评者坚持以知识分子立场来否定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排拒经济时代所带来的一切。
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写实小说对知识分子话语的部分疏离也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理解和肯定,陈晓明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为卑琐的日常小事压得透不过气来,文学怎么可能超越这个卑琐的生存境遇呢?它无疑非常恰当而有效地表达了我们时代生活的这一方面。”[31]“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紧张冲突被自然化解,生活本身并没有作出关于‘幸福的承诺’,生活的事实倔强而傲然地存在,那些由‘父法’(历史法则或权威话语),由集体的乌托邦统治的想象关系也就自行崩溃。”[34](P71)蔡翔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心态源自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正是在80年代,对人的存在的理想与憧憬被张扬到极致,因此反而造成价值——事实之间的辽阔距离。在这种时候,普通的日常性的生活经验起到了有效的抵制作用,甚至开始怀疑‘启蒙’的价值系统。”[35]另有一些评论持较中立的态度,“‘新写实’亦可看作是青年一代作家告别英雄主义的仪式……‘新写实’作家就其心态来说,显然是在寻找一种与社会的调适方式,而不再以抗争的情绪对之施以报复”,“它不再讲述集体的故事和想象,它更关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并小心翼翼地述说着庸常生活的伤害与痛苦”。[36](P290-291)这些评论背后或许隐含着他们对知识分子话语的限度及实现的可能性等问题的反思。
如果说80年代知识界普遍坚持知识分子立场、视角来观照现实的话,那么这种共识显然在90年代被打破。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理解、进入90年代的方式:是继续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宣扬启蒙话语,还是开始承认日常生活的自足性乃至主体性,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分歧。而作家本人关于《一地鸡毛》前后不断变化的言说也更为充分地表征了80—90年代的变化。针对有人批评《一地鸡毛》会压垮人的精神,刘震云说:“这是没看懂我的作品。……人们的生活虽然非常琐碎、重复,但的确有一种趣味感,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情感。比如在菜市场上,买卖双方之间讨价还价,往往为几分钱喋喋不休,但最后他们谈成了,获胜了,于是就在这几分钱中,体现出他们活着的趣味。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一种生命的辉煌。我觉得我找到了生命的支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地鸡毛’叫作‘一地阳光’也未尝不可。”[37]这里已经没有《磨损与丧失》中的无奈、失落感,90年代之后经济时代已是主潮,知识分子话语被不断挤压、边缘化,作家显然也有意顺应时代来调整叙述的口吻。他无须再为作品人物身上曾经被冠以的“庸俗”、“堕落”等名号进行辩解,时代背景的转换反倒使人物变成了“英雄”:“小林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卑下,他的见识相当了不起,我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写的。小林认为他们家一块豆腐馊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38]同时,作家有意强调与知识分子话语的不同之处:“我对他们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我觉得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新写实’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中在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39]当然,作家此时的诸多言说显然是时过境迁的重新叙述,从这当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90年代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在此时均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面对关于这部小说(以及其他新写实小说)的诸多评论,或许可以借用程光炜教授一篇评述当时评论家批评张辛欣、刘索拉小说的文章来总结:“缺乏现代生活切身经验的批评家只能从对传统生活的了解入手来观察小说主人公近乎超前的想法和举止。由于批评家缺乏现代生活的资源,所以他们的批评活动实际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批评的文学人物。”[40]反观当时的种种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选择进入90年代的不同路径和方式。而这些也和文本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理解80—90年代转变的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