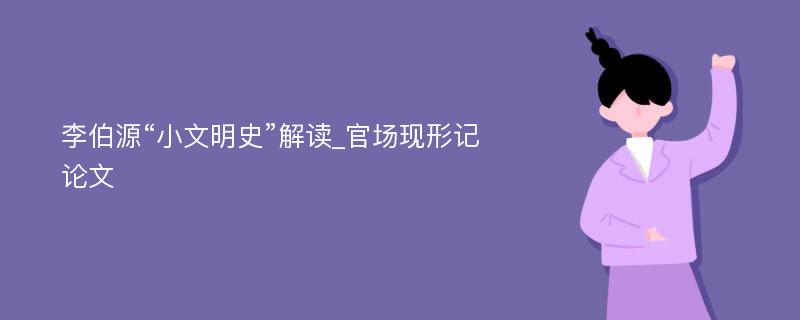
李伯元《文明小史》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伯元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明小史》是被研究者忽略了的一部作品。同《官场现形记》一样,《文明小史》(注:本文引用《文明小史》依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2版。)也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名噪一时的长篇谴责小说。小说共六十回,最初在1903年5月至1905年9月连载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同时刊出的还有署名“自在山民”的评论(注:“自在山民”评语系转引自《李伯元研究资料》149-179页,下文引用时标明回数,不另注。),为以后的版本所无,实际上也是研究这部小说的绝好材料。
从《文明小史》与《官场现形记》创作时间相近、作品风格相似,以及作品内容相关联来看,两部作品几乎可以说是孪生子。但从研究的历史看,《文明小史》则明显受到冷落。鲁迅、胡适一代学者,“大概因为难于访求的原故,《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只用很少几个字带过,《中国小说史略》一样的止于提到”(注:阿英著《晚清小说史》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北京新一版。)。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官场现形记》。后来虽有阿英在《晚清小说史》里极力推重《文明小史》,但并未扭转业已形成的研究格局。
实际上,《文明小史》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开先河的作品,在它之后,有不少以讨论中国维新改革方案和道路为主题的作品。《文明小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且,由于《文明小史》比《官场现形记》复杂,经由对它的研究,我们对李伯元的创作观念及创作风格会有更加深切的把握。
《文明小史》比《官场现形记》复杂,是由这部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这部小说主要反映清政府1901年开始的各种政治制度改革,也涉及戊戌变法中的人物和“革命党人”方面的情况。“文明”指的是这一改革过程中输入的西方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等,但作者使用“文明”作标题时,显然有怀疑和嘲讽的意味在里面。
对于这场改革,用文学的形式作出判断,也许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的推动者(政府)和参与者(吏民)的动机和能力,参与者或旁观者对改革的不同态度,……这些都是复杂多变的,给小说的表现和判断增加了困难。对于这样一部题材复杂的作品,我们的许多研究仍停留在泛泛谈论它的“谴责”上,而未能触及更深入的问题:作者谴责了什么?作者用什么作为谴责的标准?作者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进行谴责?一句话,李伯元视野中的晚清改革运动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观?本文试图经由对《文明小史》结构、情节和人物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先讨论作品的楔子。
楔子与尾声是章回小说沿用的说书人技巧。“楔子与尾声构成了正文的框架,同时,由于引导读者理解故事的意图,它们也执行阐释的功能。”(注:M·D-维林吉诺娃主编《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第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文明小史》楔子的叙述者把中国的现状比作日出前的晨曦,风雨欲来的天空,中国的未来由“潮”和“风”兆示着。叙述者叙述:一次,“我”坐了火轮船在大海里行走,“偶至船顶,四下观望,但见水连天,天连水,白茫茫一望无边,正不知我走到那里去了。……忽然东方海面上出现一片红光,随潮上下,虽是波涛汹涌,却照耀得远近通明……潮水一分,太阳果然出来了。”“记得又一年,正是夏天……虽然赤日当空,流金铄石,全不觉半点歊热,也忘记什么时候了。……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乌云,隐隐有雷声响动,霎时电光闪烁,狂风怒号……一家的人,关窗的关窗,掇椅的掇椅,都忙个不了。不消一刻,风声一定,大雨果然下来了。”(注:《文明小史》第1页。)这里,潮水显示太阳要出,风声显示大雨将下,但“太阳”与“大雨”两个意象显然有不同的情感指向:太阳象征着光明的未来,而大雨似乎预示着灾难性的后果,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对“大雨”的描写中透露出一种阴森的气氛,它的到来并不是消除炎热,而只是增添了忙乱。这两种寓意相反的意象的并置,暗示出叙述者对于改革运动后果的不安和茫然。“正不知我走到那里去了”和“也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它们作为一种修辞的技巧,起着强化这种不安和茫然情绪的作用。叙述者似乎感到这两种比喻还不够明确,又直接出来解释:
做书的人,因此两番经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何以见得?你看这几年的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的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地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注:《文明小史》第2页。)
叙述者对中国既非老大,亦非幼稚的看法,印证了“太阳”与“大雨”意象的对立。如果这两个意象寓意一致,则表明叙述者不是同意“老大帝国,未必还老转童”的悲观论调,就是同意“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的乐观论点。
叙述者的语气,一方面肯定了“文明”维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表明对于维新现状的不安和焦虑,因为它的结果既可能是迎来太阳,也可能是招致大雨。这种不安和焦虑来自维新改革运动中的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参与者“为公为私,是真是假”鱼龙混杂。为公为私,侧重从参与维新者的动机上来说;是真是假,既包括参与者为公为私的动机问题,更指参与者对“文明”的认知问题,涉及他们推行的“文明”是真文明还是假文明的问题。叙述者要把这一干人,“不管是公是私,是真是假”,都“表扬一番”,这自然是反讽的语气。
以往的研究,对于楔子中意象的含义、叙述者的语气,缺乏准确的把握,因而失去了准确理解《文明小史》全书的一把钥匙。从楔子表明的情况看,作品描写的主要是维新运动中的混乱情况,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对“文明”的错误理解和参与利用“文明”之名,谋个人利益上。
二
全书的情节结构和人物是本文的解读重点。
M·D-维林吉诺娃在《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学》一文中,针对晚清小说情节似乎松散,似乎缺少剪裁的情况时说道:“对晚情小说情节结构认识的不足必然导致对于小说意义的肤浅理解和主观评价。因为如果不能确定一部小说统一的情节或主题,对于小说的判断就往往只能依据小说中个别人物的言谈或对个别插曲的不适当强调,以此作为整个小说的代表”。(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第3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在这篇文章中,《官场现形记》被归为“环型情节小说”一类,这种看法可供我们借鉴。
我们可以用“史化叙述”来描述《文明小史》的一些特点。首先,作品所描写的是一个国家的改革。晚清改革的主要方面,小说基本都涉及到了,只不过有详略的不同而已。其次是人物的不断转换,没有固定的主人公。第三是地点的不断转移,从闭塞的内地到上海的“夷场”,从京城到地方。阿英称此书“全面的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的那个时代”,而胡适对于《官场现形记》的评论——“是一部社会资料”——也完全可以移用于《文明小史》。在这种宏大的、松散的、充满“插曲”的情节结构中,到底有没有统一的语义原则呢?我们认为,这个统一的原则就是:“文明”的被扭曲、被利用,即“神奇”被化为“腐朽”。情节的张力来自“文明”的真实内涵与对文明的错误理解,推行“文明”的行动与推行“文明”的动机之间的对立。
如果对作品的这一潜在结构不清楚,就会对作品描写内容的杂乱感到迷惘。
表面看来,《文明小史》与其他几部宣扬改革方案的小说,如《新石头记》、《新三国》、《黄绣球》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一种明晰的结构,以理想化的方式展现了改革目标和方案,而《文明小史》则缺乏一种结构,作者关于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是混乱的。
一般的小说,即使是纪实性非常强的,其中的细节或情节往往经过裁剪,它们之间的对比照应关系,使丰富的内容组成一个清晰易辨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每一个侧面,与某种情感或观念对应着。而《文明小史》的细节和情节的安排,似乎是未经裁剪的、“原生”的生活素材,给人杂乱的感觉,而叙事者的评论,似乎也出现自身矛盾的情况。我们试以第二、第三回写湖南永顺县童生聚众追打洋矿师、围攻府衙门一案中对武童一方面的情况为例,来说明意义相反的细节,态度相反的评论同时共存的现象:
①武童为考试延误而不满;武童所考试的射箭等技术已经无补于时。
②武童认为知府巴结外国人而增加不满;武童大都游手好闲,少年喜事之人居多。
③武童听说知府把山卖给外国人而议论纷纷;武童仅是误信人言。
④武童议论开矿将使自己的田产、祖坟受到破坏;武童议论开矿会坏了“风水”。
⑤武童被黄举人一番慷慨激昂的话鼓动;黄举人专喜包揽词讼,名声甚臭。
⑥武童在茶店和明伦堂议事,要打死外国人,绝了祸根;武童等一哄而散,茶店没收到茶钱,茶碗反打碎不少。
⑦武童到高升店追打洋矿师;武童没有搜出洋矿师,顺手抢了不少东西。
⑧武童等攻打府衙门;武童等听到绿营兵来,齐想一哄而散。
对武童的描写评论经常出现相反态度并置的情况。在这些描写里,包括叙述者的评论里,我们看到,如果强调前一种内容,那么,武童的行动就被描绘成正义的;如果强调后一种内容,武童的行为就完全变成无理取闹。把两种内容并置在一起,就造成印象上的混乱和判断上的困难。
武童的大闹,使得永顺勘踏矿苗一事归于流产。这似乎可以作为小说内容的预示:在反对者一方面,对待改革态度上的盲目性(缺乏智识)与虚伪性(缺乏诚意),是造成混乱的原因。
在表面上推动或实行“文明”维新的方面,人物的思想行动也一样显得混乱无序。以全书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新学”这一环节来说,第十八回写到上海的学堂只是为了赚钱;第二十一回写到杨编修到学堂任职只是为了束修,并借机重返仕途;第二十四回写到王文藻至山东担任学堂总教,自己于西学时务一窍不通,居然受命课选教员;第四十一、二回写到南京的康太尊一边开设新学堂,一边禁书,而且自己的儿子死了,还让学堂师生为其子送殡……这些人物未必没有冠冕堂皇的议论,未必没有貌似“文明”维新的举动,但他们身上,却体现着对“文明”的扭曲。整个“文明”界,各色人物或者互相吹捧,或者互相倾轧,使“文明”毫无希望。
《文明小史》第二回叙述,店小二打碎洋矿师一个磁碗,柳知府深恐引起交涉,极力巴结洋人,随行的金委员说:“同外国人打交道,亦只好适可而止。他们这些人,是得寸进尺,越扶越醉,不必过于迁就他们。”这番话对于柳知府的媚外,无疑是对症下药。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金委员却为谋取私利,不惜怂恿洋人,挟制柳知府,以索取贿赂。金委员的一番议论,有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表明柳知府在对外交往中“智识”的不足,智识不足正是改革中混乱的原因之一;其次,表明金委员本人虽有从事外交的智识,却无至诚为公的动机,这种缺乏正确动机的情况,是引起混乱的另一种原因;最后,这种安排从总体上表明智识与动机的不正确是“文明”事业陷入混乱的原因。
《文明小史》中类似金委员这种人物正不在少数,他们此一时仿佛“正面人物”,彼一时又仿佛成了“反面人物”。此一时,他们代表叙述者执行批判的功能;彼一时,他们又被另一代表叙述者执行批判功能的人物所攻击。柳知府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描写的,在这里他被金委员批评,而在下一个场景中,他又成为金委员的批判者。小说中的人物,随着叙述者描写和评论他们的语气不断变化,他们在不同的情节、场景中,执行着不同的功能。作品本身以“文明”事业被误解扭曲,即改革者智识动机与改革的真实目标、内容的错位为统一的语义核心,因此,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适合于表现这种“错位”的。
三
《文明小史》以表现晚清改革中的种种混乱为内容,留下了当时社会的生动资料。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小说的叙写方式同样也是一种社会资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小说中所叙的混乱,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为公为私混杂,一是真假难辨。后一个方面,西方文明的真假问题,实际上涉及中西文明关系以及引进西方文明的重点和限度。真文明是什么?虽然作者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他所描绘的“假文明”中反推其大致轮廊。
小说中对湖广总督的赞赏,在全书中显得非常特殊。他显然是影射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一向以他的“中体西用”观点闻名。而在近代非常活跃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本书中,作者用安绍山、颜轶回的形象来影射,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这一安排,倒可以提醒晚清文学的研究者:不少人谈到晚清小说的繁荣,提到谴责小说,总是把它们与梁启超的文学(小说)理论联系起来,这是否过于简单,是否在梁氏的提倡之外,它们另有一种生发的力量?这或许是另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小说以立宪结尾,暗示出作者认为改革的政治目标是止于君主立宪,这并未超出当时主导改革者的意图。在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观念指导下,小说在批评“假文明”的理路上也与政府改革者如出一辙:
(清政府)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讲“平等”、“自由”、“民权”等,有潜在的超出改革极限的危险,在小说中,讲“平等”、“自由”的人就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些人被描写成肤浅的,只知摭拾西方的半面之词,丧失了中国固有的美德。如:第十九回写到刘学深(“留学生”的谐音)讲“自由”,目的仿佛是为和妓女相好作论证,他反对女人缠足,却又忘乎所以地称赞野鸡的小脚,他设坛演说,只是为了聚敛钱财。第二十一回写一位出身学堂的秀才何祖黄,学了一年西文,可以译些粗浅的书,别人劝他不要打野鸡,他反说别人是“压制”他的“国民资格”。第二十五回写到讲西学的瞿先生和王济川师徒,老师讲的“尽是一派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说得天花乱坠”,却以开办女学堂为由骗了学生家里二千五百块钱。第十六回写一个叫广东阿二的女人,“十三岁上曾在学堂里读过一年外国书,……竟其改变了脾气”,专门“轧姘头、吊膀子”,叙述者且有意无意地把“外国婚烟自由的道理”等同于上海的一种“轧姘头拆姘头的名目”。第四十四回写南京一位机户人家的女儿,入过学堂,有些“开化”“文明”气息,“但是过于自由,自己选过几个女婿,招了回来,多是半途而废的”。
作家并未正面展示对于平等、自由的看法,但书中不仅常用“无非是平等、自由一类的话头”表示蔑视,还通过戏谑化的手法刻画出讲“平等、自由”的人的不堪,而暗示出“平等、自由”的主张的可怕后果。
作者把当时的出身学堂、留过洋的一个圈子的活动,写成了一部新的《儒林外史》,与作者在批评大小官吏时所使用的细节、素材又大同小异,从而使本书在整体上与《官场现形记》显得雷同。
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里说:“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穷困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用不着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博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注:转引自《李伯元研究资料》第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他的话,还需要稍作补充:对于维新改革作全景式的反映,本身是需要“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的,这是《文明小史》显然区别于《官场现形记》的地方;但我们的确可以说,作家由于自身的缺陷,未能写出“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思想”,而只是写出了当时公认的罪恶,甚至是以公认的罪恶加于西方文明的倡导者之上。
胡适对于谴责小说作者人格的批评,自然有些武断,但是,对于李伯元,他的意见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