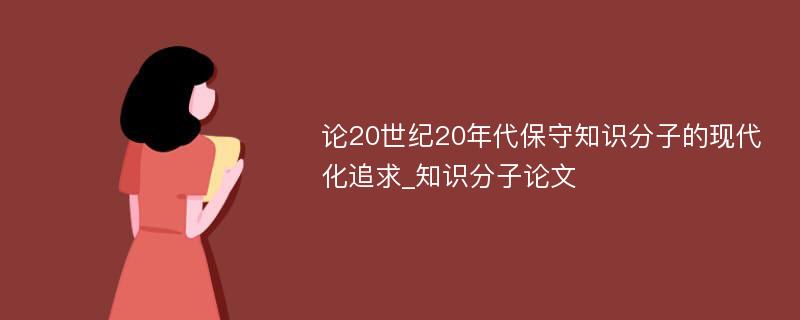
论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保守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2001)01-0041-05
一
在1917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知识界,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照的,是以杜亚泉、张元济、吴宓等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或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激进知识分子扫荡传统已成时代主流之际,毅然挺身而出,捍卫传统文明,光大传统文化。人们以往总是认为他们是与中国现代性进程背道而驰的,将他们纳入“反现代性”的框架。而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却发现中国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推进现代性进程作出了努力。只不过与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推进现代性的资源,更多地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他们的努力更多地体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中国保守主义的生发基础,主要在于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与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一方面,辛亥革命使古典王权政治秩序走向了崩溃,也摧毁了儒学长期依赖的制度基础,从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与价值危机。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更将现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危机推向了极致。中国传统文化大厦已经坍塌轰毁,成为一片文化的废墟与精神的荒原。这种价值的迷失与意义的危机,引发了中国文化深刻的认同危机,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欧战所引发西方文化危机又进一步为其提供了契机。以巴黎和会观察员身份旅欧考察的梁启超,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幻灭,返国后发表《欧游心影录》,大力宣扬西方科学文明的破产和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这种传统危厄和西方困境的双重危机,顺理成章地成为保守主义崛起的催化剂。梁漱溟率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儒家人生理念批评西方近代世俗工具理性的非价值性,力倡儒家文化的复兴。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则以古典人文主义衡估新文化运动,批评其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反传统主义倾向。而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强调科学理性之于人生信仰的限度,以及宋明理学之超越西方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因此,保守主义作为中西文化双重危机与现代中国认同危机的反应,是对激进知识分子全盘性传统和西方化倾向的某种反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新文化启蒙运动退潮后的思想真空。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了一批以杜亚泉、刘师培、黄侃、张元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为代表的以批评西方文化、护卫中国传统为职责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等。《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严格说来并不应划到“保守”的阵营。事实上,在本世纪初它为传播西方文化、开启民智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只不过由于杜亚泉1911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对它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因而在那段时间带上较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保守派刊物则首推北京大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它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表现了它批评西化主义和护卫东方人文传统的鲜明主题。而在整个20年代,最具声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是以吴宓和《学衡》为中心的学衡派知识分子群体。
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们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曰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中固然有极少数的“国粹派”,但大部分人并不是抱残守缺的文化遗老,恰恰相反,他们中有很多人曾游学欧美,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化训练,在西方文化的引进上也颇多贡献。他们之所以被归为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立场上的不同。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传统的奇理斯玛权威土崩瓦解,社会道德政治秩序失去原有和谐,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已成为一种与社会政治形式相剥离的价值观念。激进知识分子以某种现实功利需要作为评判文化的态度,对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以及作为文化代表的道德伦理秩序进行全盘性反叛。而在保守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瓦解,已经使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支撑构架,现在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进一步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如何利用西方现代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利质素,来重新构架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系统。对他们来说,这种文化价值系统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一旦也遭到全盘性的否定,那知识分子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所适从。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文化的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而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不仅要在文化层面上摧毁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且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达到对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重构。这就使得保守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两大群体的冲突与对峙,成为20年代知识界的一大景观。
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表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更多地诉诸于价值理性,要求把价值的立场与功用的立场分开,在纯粹知识和文化的层面上,“审文明真价之所在”。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着力挖掘中西文化中超越现实功利的人文价值,重建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比如伧父就认为西方重竞争,东方重自然,西方动的文明引向物质生活的富裕,东方静的文明注重精神生活的和谐。从价值上看,不能以绝对肯定一方而绝对否定另一方来解决。因此,两种文明应当互补,主张“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1]可见,无论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工具理性,还是保守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近代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又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必然要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量,以致常常不自觉地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地拥护工具理性;而保守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理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而且东西方的价值理性传统并无古今高下之分,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尊严和地位。[2]显然,保守主义的价值理性与激进主义的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正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内在紧张的必然表现,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推进现代性进程的不同取向的必然结果。
二
以吴宓为中心的学衡派是20年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声势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从1922年1月创刊,到1933年停刊,《学衡》前后支撑了11年,集中了一批以学问为自我中心价值、以思想文化评论为时代使命的知识分子,除了吴宓、胡先骕、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外,还集中了刘伯明、楼光来、缪凤林、景昌极、刘永济、林宰平等人,形成了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志向与文化精神的学衡派知识分子群体。
作为20年代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主体的学衡派,既有着容纳中西的文化胸襟,又对新文化运动充满了难以化解的偏见;既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念,又与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理解与把握学衡派知识分子,有必要论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衡派知识分子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二是学衡派知识分子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
《学衡》创刊伊始,就在《学衡杂志简章》中定下了自己的办刊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翻一翻《学衡》杂志,不难看出他们的确是希望在中西文化的宏阔背景下,论究学术,阐求真理,以一种超然独立的态度,追求终极的价值理性。《学衡》的栏目有“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占主体部分的是“通论”和“述学”。他们热衷于引进代表西方文化精粹的大家学说,除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外,还有《葛兰西论新》、《西洋文学精要书目》、《希腊之精神》等等大量论文。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学衡》创刊号的卷首插图就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像,在以后的各期中,每期中都有中西方哲人学者作家的画像,如莎士比亚、弥尔顿、迭更司、沙雷克、耶稣、威至威斯(华兹华斯)、辜律己(柯勒律治)、托尔斯泰、彭士(斯)、哈第(代)、劳伦斯等等。这些大家,成为学衡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将中西文化相提并论的主观意图。仅仅曰此观之,我们不能不说学衡派诸位的确是有着融化中西的胸襟和实力的。另一方面,“通论”、“述学”、“文苑”中的主要篇幅还是大量对中国传统文化纯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兼及教育、道德、社会诸问题,甚至还有不少旧体诗作。这些论述似乎都在努力体现它昌明国粹,不激不随,论究学术,阐明真理的主观愿望。在一个思想相对和平稳定知识语境中,《学衡》这种对文化终极价值理性的追求,无疑是无可厚非的,可以说还是每个知识分子所必须依循的规则和一个文化赖以传承的基础。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那样的特殊时代语境中,它就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尤其是学衡派诸位还想依循自己的文化理念对当下的新文化运动说三道四,这就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尤其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所不容了,并招来了此后几十年备受指责和冷落的历史命运。其实,仅仅从几十期的《学衡》杂志来看,是看不出多少对新文化运动的“恶毒攻击”的,除了一些纯学理的研究外,涉及现实文化的一些文章也大都持兼容中和之态度,真正集中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只有廖廖可数的几篇,即第一期上海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的《评〈尝试集〉》,第四期上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等。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只有这么几篇,但已集中体现了学衡派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深深的陈见和不满,再考虑到当时新旧交替的时代大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衡派知识分子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从现在披露的资料来看,在吴宓等人的内心深处的确对新文化运动充满了深深的难以化解的偏见。吴宓在1917年以后的《日记》中曾多次对所谓的“新文学”大加痛斥。他说,所谓“新文学”,“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3]甚至认为,“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吴宓始终认为,“救世救国,惟在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惟道德之增进,为真正之改革。此外之所谓革命,皆不过此仆彼兴,攘夺利己而已。”“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余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忧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而已。”[3]因此,对国内的新文化运动真诚地感到忧心如焚。“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俗人固不可与道,即同心知友,偶见面谈及,亦只楚囚对泣,惨然无欢。”[3]这种相当深刻的隔阂,既是他们身处国外而生的一种强烈的爱国之忱的表露,也是他们文化观念的严重对立。
学衡派知识分子把全国“震撼动摇、相激相攻、纷纷扰攘之状况”的原因,概括为“新旧思想之冲突”。并且认定,“此冲突盖中国文化估定价值之关头,亦即中国文化之生死关头”[4],因此,在新旧剧烈冲突的激流中,《学衡》试图超越新旧之争,强调“事物之价值在其本身之良否,而无与于新旧”[5],用另一种姿态为中国文化发展开辟“第三条路向”,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旧冲突的样态也在发生变化,《学衡》尽可申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亦可期望“国粹不失,欧化亦成”融化东西文明的新文化,可这种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同样会与新文化不可避免地构成新与旧的冲突。激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社会的革命与文化的重塑,而不再强调旧传统的根基。学衡派在旧传统基础上所构想的融化中西的理想,对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过于遥远。在特定的新文化运动语境中,要么是新,要么是旧,试图超越新旧之争的种种姿态,其实也是新旧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学衡派试图解脱新旧缠绕处境的努力注定是不可能的。这种新旧冲突的严重隔阂和深刻对立,成为我们理解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评〈尝试集〉》、吴宓《论新文化运动》等文章的重要基础。
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所采取的理性态度,使他们在批判或维护传统文化方面颇具保守色彩。这里的“保守”并不是传统概念中的贬义词汇,而是一个中性词汇。我们所使用的“保守”、“保守主义”基本上都属于一种中性词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学衡派知识分子的“保守”,并非出于对现代性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反感,也并非纯粹对“旧”事物的迷恋,恰恰相反,他们对中西文化抱有宽容的心态与融汇的胸襟,企求由此创造出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融化西方精髓的新文化。他们所取的是一种开明审慎的文化态度,而不是激进派那种否定一切的情感渲泄。吴宓和学衡派知识分子的这种新文化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美国导师、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他们不仅在美国留学时亲受白璧德的教导,甚至在回国以后,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将白氏的学说奉为圭臬。吴宓看来,白璧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他的学说远承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精义微言,近接文艺复兴诸贤及英国约翰生、安诺德等人之遗绪,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卓然而成一家之言。他对自己能在白璧德身边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而深感荣幸。[6]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也就成为他们当然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理想。他们试图以人文主义的文化发展的承继性和规范性,来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沦丧。人文主义成为学衡派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道”,《学衡》也因此成为他们“论道”的人文主义堡垒。
三
林毓生先生曾指出:“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提供有力条件”。以此质之《学衡》及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倒是颇多启示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想化认识虽然不足取,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态度与中庸的价值取向恰恰正是“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只不过他们的努力缺少了“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而导致了历史的误构。如今回过头来思考,他们的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对于保守知识分子来说,“中庸”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而且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这种理性而中庸的文化态度正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尽管当时的主流话语是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话语,但并不能因此排斥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它同样具有自己参与历史对话的资格。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理性而中庸的价值取向,贯穿于保守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之中。既反对激进的革命,也反对复古的倒退,主张在基本保持既定文化秩序的基础上,吸引中西文化的精髓,对传统文化加以现代性的转换。
这就涉及到新文化论争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重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如胡适所说,是要“重估一切价值”,以批判的精神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这也是启蒙运动的精神。但是思想文化的“价值重估”不应当导致价值虚无,也不应当把封建纲常伦理当成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全部。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重估,离不开“承传”与“创造”的二元统一。只有处理好“承传”与“传统”的关系,才能形成一种具有弹性的、稳定的价值取向。“承传”与“创造”是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相互依赖的两个重要因素,两者的有效互动才有可能使传统文化成为洞察当今现实的思想资源,才有可能产生最富创见性的新文化理念。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其实都属于“承传”与“创造”的范畴。激进主义者把新与旧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忽略了“创造”新文化所必须的“承传”基础;而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注重传统的“承传”,却未能将社会政治剧烈变革与人文传统的绵延连续有效区分。因此,从中西传统文化资源中提取符合现代观念的要素,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合法性地位,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或许有人会认为,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这种依恋传统、固守价值理性的态度,是否应视作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大阻碍。因为一般而言,现代性是与当下的物质现实功效紧紧相联的,与传统精神学问似乎并不密切。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现代性恰恰与传统、与价值理性密不可分。这就为文化保守主义所推进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援。如果象激进派那样完全与传统断裂,那么不仅“现代”与“现代性”失去了一定的解释标准,陷于一片混乱,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现代性”本身的危机。因此,为了实现现代性的理性重构,我们离不开在自身传统的理性资源中发掘和建立规范,而不是纯粹地借用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或以西方文化价值系统取代中国固有文明。这一点也正是保守派与激进派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根本冲突。因此,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以抽象的理念来整体性地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可能会人为地摧毁与破坏现存秩序,并带来事与愿违的历史后果,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制内的生长,可能更是实现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早期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表面上似乎是处于现代性进程之外,甚至是反现代性的,但他们作为现代性的对照物,同样对现代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后起的吴宓、杜亚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始终是处在现代进程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的现代性思路与西方的现代性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呈现出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三派互动的多元发展趋势。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群体,主张彻底反叛传统,拥抱现代文明,甚至企图通过激进的手段彻底改造社会现存体制和文化观念,从而将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蔡元培、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群体,以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为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尤其是胡适等人试图立足现实社会,探讨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秩序之路。与此相呼应的就是以吴宓、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群体,以文化守成为现代性价值取向,力主肯定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积极作用,并思考引入西方现代文明,以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来融贯中西,以达到昌明国粹,重铸文明的目的。三派并存,都是在危机中寻找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为中国文化寻找自己的归宿,为现实社会政治寻找新的秩序。因此,以学衡派为主体的20年代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收搞日期:2000-07-10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现代性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价值理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吴宓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学衡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