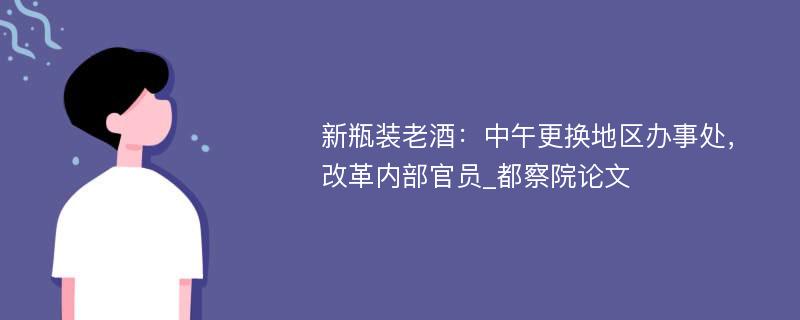
新瓶装旧酒:改设政务处与丙午内官改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瓶装旧酒论文,政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9-0104-12
清末新政开始后,朝廷为“专责成而絜纲领”,特设督办政务处为“统汇之区”,计划将各项新政事宜的因革损益交由该处审定,分别缓急,次第施行。[1](P1583-1588)1905年1月《会议政务章程》颁布,政务处的议政职能得到加强。①时论认为,“各衙门堂司各员即可照章入政务处参议政务。善哉,此美举也,诚可为立宪之先声矣”。[2]随着立宪声浪的高涨,政务处将改为议院的消息屡见报端。但是,丙午内官改制的结果,政务处并未循着原有轨迹和人们的预期发展,而是出人意料地改为会议政务处。改设后的政务处不仅名称改变,机构性质和功能也较前差异甚大,实际上演变为责任内阁的替代品。
细读相关史料,可知在政务处更名之前,有关改设意见就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趋向,不仅促成了丙午改官制前政务处职能的变化,也影响了编纂官制王大臣对政务处改设方案的选择。在官制改革中,政务处的改设过程极为复杂,与其他机构牵扯很多。以往的研究由于侧重的不同和材料的纷繁,关于政务处的改设仅依据典章条文略加陈述,②亦有学者注意到政务处改设前后的差异。③但是,关于改设的因由和过程,以及给整个内官改制尤其是中枢行政所带来的影响,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丙午官制改革是近代中国制度转型的重要一环,其背后交织着新旧中西的不同观念。在宪政改革的大背景下,官制的变动既受西方宪政思潮的影响,又受清朝固有体制的牵制。时人容易将中外不同政体的相似机构进行简单类比,既忽略了清代设官分职的主旨,也混淆了立宪政体的概念。同时,参与官制改革之人取向各异,都希望通过官制改革达到各自目的。由内官改制尤其是中枢机构变动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改革方案几经争论,多次修改。最高统治者举棋不定,最终选择将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的稳妥方案来平衡各方的政治诉求。这一偶然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整体改革的走向与进程。因缘政务处的改设过程,可窥见内官改制的曲折复杂及中枢机构的变动,西方宪政体制与清朝固有体制的冲突由此凸显。
一、两可之间
五大臣出洋前后,行将立宪并改革官制的消息在京中已是沸沸扬扬,内官制的变动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报载,“政府王大臣近日屡次会议改定官制、裁并衙署各节”。[3]有消息说,“那中堂创议,将内阁改为内部。以后,政务处为立法官,内部为行法官。某邸甚以为然,不久即见明文矣”,[4]又谓“政府因内阁事务清闲,各大学士均系备员,有拟即行裁撤之意,所有事宜归并政务处。政务处之名目亦拟改定。又闻有归军机处、内阁、政务处为一处之说,或总名枢密院,或仍名内阁。各军机大臣现正议商,尚未决定”。[5]
外界虽然众说纷纭,而朝中大老的实际步伐显然与之不合符节。1905年11月27日,商部尚书载振上折条陈改官制。折中称,“我朝设官分职,大都沿明代旧制,故有旧政既废,官位尚存,寝至名实不符”,[6]由此而官制事权不一,责任不专。其弊有二:一曰推诿,“盖责任不属于一人,则纲领便无由提挈,国家遇有大事,此部推诸彼部,甲权诿为乙权,或明知其事之非,而不肯出一言以立断”。二曰牵掣,“各堂官既众,意见不无参差,往往提议一事,议论经年,终归搁置,所谓筑室道谋,不溃于成”。因此,他认为当此时局艰难之际,旧有官制不能与之因应,建议“宜仿各国专任之例,将中央官制改弦而更张,庶有以植新政之初基,而可自立于竞争之世”,并提出了一整套官制改革的方案。其中,“内阁大学士不兼部务者,同内阁学士等官,事务稀简,几等闲曹,于国家体制,名实太不相符,或可将近设政务处,归入内阁办理”,而“都察院系建言论事之地”,“未可轻议裁撤”。上奏之前,载振特地致函瞿鸿禨,并将疏稿见呈,望瞿氏入对之余,“赞成一切,俾可见之施行”。[7](P59)不难看出,载振所奏与此前外界传闻差距不小。折中虽然提出宜仿照各国“专任之例”,但并未涉及立宪政体改革,而是在原有体制内进行“祛冗滥、专责成”的调整,意在“维政体”,而非“改政体”。不过,折中也提到“日本明治变法之初,亦先改定官制”,隐含为立宪准备,似又不便明言。实则载振此奏另有隐情,“闻振贝子此折夏秋之间即已具稿,是时贝子适在极力运动立宪,欲俟立宪事成,然后请更官制。不料立宪事,外议略有异同。刻下未能遽行,遂将此折递上。又闻此折原稿其官制全仿外国制度,后与朝中大老细商,知中国此时程度未能及此,且今日仓卒之间亦万办不到,乃降格为此,实有不得已之隐衷”。[8]此言并非虚妄,“(载)泽未行时,(载)振即告以非立宪不可,兄出去一看,便明此理云云”。[9](P837)可见此时朝中亲贵对于立宪仍在游移之间,又未能与中枢大老就官制改革达成共识,故此折虽发交政务处议奏,但阻力重重。政务处各堂“议及政务处归并内阁一事。某大臣谓以现在改良政治不厌求详,内阁为各衙门总汇之区,而政务处交议折奏事务尤属繁冗。若经归并,难免有疎略之虞。此举暂可从缓,俟有妥实办法再议”。[10]有消息称,“议覆振贝子变通官制折”,“欲俟五大臣回国后始行发表”。[11]
虽然如此,舆论却并未丧失信心。《时报》发文称,“风闻朝廷因振贝子之奏,将大改官制。比虽未奉明谕,然以近政而论,此举固在意中。且窥朝廷之意,将非如前者枝枝节节之为,而确有整齐全局之想”,并提醒当政者“定制之初,虽未能一扫旧规,然统辖联属之间,必宜特参新制。如司法、行政之分立,中央、地方之相联。凡可为立宪之基而文明官制所必然者,皆宜先引其端”。[12]
1906年3月,任满回国的驻法公使孙宝琦于奏对之际“历陈各国政治,并请速定立宪以慰天下臣民之望”,[13]又提出应仿照列国制度,扩充内阁权限,“将军机处、政务处请旨裁撤,一切军国重事、内政外交事宜均归内阁总辖,以划一事权而整齐政务”。[14]据悉,孙宝琦连日与政务处王大臣会商,“请先设考察政治馆于政务处,凡有通达东西各邦宪法人员及程度最高之留学生,由王大臣随时保奏,调充考察政治馆之议员。王大臣均以为然”。[15]作为驻外钦使,孙宝琦对时局有相当清醒的认识。1904年,他就曾“上书政务处,请定立宪政体,广开议会,以振全国之精神,以新天下之耳目”,并致函端方,希望其能与张之洞“将立宪之意合疏上陈”。[16](P195)但“枢府中多不赞成”,[17]最终石沉大海。任满回国之初,他又电称“非此(立宪)不足扶危局,恳早颁明谕,定为帝国立宪政体,慰天下人民之望”。[18]或许是时势使然,孙宝琦此次的主张得到军机大臣们的认可,因而“枢眷甚好”。[19](P25)然孙宝琦变革政体、扩充内阁的建议一经提出,朝中随即引发关于重组中枢机构的争论,尤其对于政务处的变动意见不一。据媒体披露,方案大致有二:其一,拟“将内阁、军机处归并,改为内部”,“政务处改为上议院,另订设官章程,以作立宪之根据”。[20]其二,则如孙宝琦所请,“将军机、政务二处奏请归并内阁,仍用内阁名目。所有全国行政事宜,均归内阁统辖”。[21]两种方案虽然意见不同,但都旨在建设立宪政体。政务处在立宪政体中的去向,则或归并于内阁,抑或改设为议院,意见截然两分。
将政务处改为议院的意见由来已久。1903年七八月间,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便奏称宜仿效外国议院,将政务处酌量变通。[22]而自《会议政务章程》出台后,外间更以为“政府有组织立宪之意,拟以政务处为上议院,以都察院为下议院,凡侍郎以上各大员皆令充当议员”。[23]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时人将形似西方议院的政务处简单类比为立宪政体下的立法机构,实际上是意欲沟通中外政体,使固有机构与宪政机构实现顺利对接,从而平稳地实现政体变更。但此举既忽略了政务处设立的本意与清代设官分职的主旨,又混淆了立宪政体的概念。在外人看来,对此消息不免“讪笑,以为驴非驴,马非马”。[24]
日人服部宇之吉在介绍清朝政治机构时,虽把政务处列入“议政机关”的行列,但也明确指出,“此处所称之议政机关,乃对受天子之命议论政务之所给予之假定名称。其中有纯粹的顾问府,亦有行政机关等,在某种情况下亦可成为议政机关,其内容不一。虽定名为议政机关,但与外国之立法部等不可相比。”[25](P98)服部宇之吉意识到清朝的衙署往往身兼议政与行政两任,无法与外国官制一一对应,强行比附,难免格格不入。而织田万从行政法的角度,“考察政务处开设之实情,其所主职权盖在审议新政之方针乎?或目为我往时所谓制度取调局之类,亦似无不可”,[26](P206)显然不了解清朝设官分职中分权制衡的特点,因此对政务处的认识模糊不清。时人大多对此并不深究,而孙宝琦任满归来后,于中西政体的差异应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故其回国后对政务处的改设意见与此前截然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朝廷有意将政务处改为议院,此时亦纠葛较多,尤其是都察院同样具有改为议院的可能性。坊间早已传言,“政府议商拟将都察院改为议院,俾御史中之才干者充作议员”,[27]1906年初,都察院各堂官奏请裁减科道员缺,立即引来一片反对之声。翰林院编修刘廷琛上折反对裁减科道,认为“谨按会典,科道稽查各部院及各省事宜,曲折钩稽,周详妥备。现虽奉行故事,早失其职,犹可想见祖宗立法精意,至为深远”,“比岁朝廷加意维新,盖以法之弊者不能不改弦更张,以适时变。浅识者不深维其意,往往藉变法之名,徇一隅之见。于各国要政之精神命脉未窥真际,而吾固有之良法美意,已渐坠坏于冥昧之中。深可惜也。”况且,“东西各国,幅员较我为狭,然欲宣达民隐,其议员率数百人。中国二十一行省,纵横数万里,仅恃此科道数十员具疏言事,耳目已恐难周,岂可复减省人数”。[28]在刘廷琛看来,主张裁减科道之人不识都察院设官之精神,于外国要政之精髓又未深悉,企图削足适履,变更祖制,因而大加反对。不过,刘廷琛显然未雨绸缪,提出“征诸各国官制,(都察院)亦实兼议法、立法两部之任”,留有以待。相比之下,《时报》的论说则比刘廷琛更进一步。《时报》称,“都察院与议院,诚不可相提并论。第天下事有精神不同,而形式尚可比附者。存其形式,即可预为改易精神之地。今都察院之职,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虽权力远非议院之比,而所为之事则与议院不甚相远”。[29]也就是说,都察院的设官立意虽然与议院不可相提并论,但形式和职能都与西方议院相似,将来改为议院亦属可行。由此可见,朝廷一旦实行立宪官制,若将政务处改为议院,则都察院势难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以都察院改为议院,政务处仍可归并于“行政机关”之中。因此,在立宪改革的大势之下,出于自身得失考虑,台谏中人可能更倾向于后一种方案。
此外,将政务处归并于“行政机关”也并非水到渠成,尚有两种取径。其一,如孙宝琦提出的“将军机、政务二处奏请归并内阁,仍用内阁名目。所有全国行政事宜均归内阁统辖”;[21]其二,则是并入内部。考察政治大臣载泽“以为非立宪无以救国”,“极愿归后有所建白”,[9](P837)其“自外洋回京之时,即面奏两宫请将政务处、内阁归并改为内务部,为全国行政总机关”。[30]但不久又传出其于召见之时面奏两宫,“将内阁、军机处归并为内务部,并请将吏部并入此部,总理全国机务。仿照日本内务省办法,简亲王总理,其余派重臣四人为内务大臣,另派协办内务大臣二人”。[31]报道虽前后不一,载泽试图设立内务部的主张却基本能确定。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设立内务部,以载泽对各国内务部的考察,应该深知内务部并非能“总理全国机务”。[32](P597-600)之所以虚晃一枪,其意应在避免各军机大臣的反对。若以军机处并入内部,则立宪政体下内部与其他各部平行,各有专司,原有的军机大臣必定事权尽失,而政务处尚可改为议院;若以政务处并入,军机处仍有存在的空间,军机大臣依旧将有每日入对、“总理全国机务”的可能。据说,“直、鄂二宫保皆以政务处改为上议院极为合宜”,[33]而军机大臣意在“将内阁、政务处并为内部,以大学士领内部”,而“军机处仍照旧,吏部亦从缓更动”。[34]由此可见,立宪政体能否实现,关键在变更官制后军机处的去留,而政务处亦尚在议政机构与行政机构的两可之间,去向不定。
二、方案变动
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并决定从改定官制入手。随后,派载泽等人共同编纂新官制,又派庆亲王、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35](P5563-5565)在内官制的讨论中,责任内阁的成立与否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关键所在,④政务处的改设方案也一度随之变动。
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和端方在回国之初即奏请立宪,并毫不讳言“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36](P367-383)强调“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折中提出,应“略仿责任内阁之制”,“以军机处归并内阁,而置总理大臣一人兼充大学士”,“置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兼充协办大学士”,“以求中央行政之统一也”。另“请改都察院为集议院”,“凡各省外县所陈利病得失,皆上达政府,以备采择而定从违,亦准建议条陈,兼通舆论情,而觇众见。至于财政之预算,亦必属之”,待“将来程度日高,可由国会立法,自可与以立法之权,另行组织”,而政务处“似可仿日本之制改名枢密院”。此外,改礼部为典礼院,吏部待各部制度完备后再行裁撤,将原有各部归并为九部,⑤改大理寺为都裁判厅,增设会计审计院与行政裁判院等。戴、端此折出自梁启超之手笔,⑥意在合并旧内阁与军机处而组织责任内阁,改都察院为预备国会,以政务处为纯粹的顾问机构,退出行政部门的行列,并位置裁缺人员。三者之规制,多仿自日本不同时期的相关制度。如责任内阁“置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即略采日本明治二年“于太政大臣外,增设左右两大臣”之意;集议院之设,亦“考日本历设公议所、待诏局,皆使臣庶尽言,以为国会基础”;枢密院则“有类于各国之枢密顾问府”,与日本枢密院如出一辙。[37](P19)
尽管如伊藤博文所说,“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32](P579)但在将清朝固有机构对应立宪机构时,则难免不相凿枘,需要有所取舍。例如在集议院的模仿上,该折明显有所保留。一方面,日本帝国议会为两院制,分贵族院与众议院,而集议院为一院制,其议员由宗室、世爵勋裔、七品以上京官和各省督抚及驻外公使保荐之人组成。[38]另一方面,据穗积八束介绍,日本“国会之权限仅在于决议立法与预算二事,而不得干预行政。政府大臣之进退,则属于君主之大权,与英法诸邦议院政治大有所异”。[39]也就是说,日本君权具有独尊位置,“并非三权分立”。[40](P208)而集议院之权限仅在“觇众见”与“财政之预算”,至于其与行政之关系则避而不谈。较之日本国会,该折所提出的方案中君权比日本更加独尊。之所以如此设计,或可由于中国程度不及,“现在如遽行立宪制度,亦不足以举实”。
至于以政务处改枢密院,则是因其“系属新设,职权本未分明,然会议大政以待圣裁,本有类于各国之枢密顾问府,法良意美,允宜保存”,其人员“以原有大学士及各裁缺之大员特旨简任,十日一值,以备顾问,惟不入内阁,不受行政责成”。1906年9月11日《时报》就曾刊登所谓《拟定官制大纲》,其大旨便是按照戴鸿慈与端方的方案所拟,其中即以政务处改枢密院,“为最高顾问之地,以原有大学士及各部裁缺之大员特旨简放”。
如前所述,都察院有改设为议院的可能性,戴鸿慈、端方即如此提议,袁世凯亦表示赞同。⑦袁世凯最初欲裁撤都察院,经人劝阻后,才同意将都察院纳入集议院中。据杨寿枏说,“袁项城议裁都察院,余力争曰:台谏之职,总司风宪,纠察官邪,实为汉唐以来之善制,似宜保存。泽公亦语项城,曰:台官弹劾不避权贵,我辈不宜轻。议乃止。”[41](P659-660)报道亦称,“初时袁、端之意,主以都察院并入集议院,将其名目消灭。泽公则主张存留,谓各国政治家均谓都察院为中国专制政体中极有补救之一良法。今议院未成立,骤然废言官,必令行政者肆无忌惮。惟须设法改良其组织耳”。[42]更为重要的是,此前“袁宫保创议,凡宗室王公贝子将军等,无行政之责任者,别设一勋贵院以置之,非奉旨派有差缺,不得干预行政事件。以此大触宗室王公之忌,怂恿小醇邸出与为难”,[43]故而“筹预防之策,议先设上议院以皇室中之王公、贝子、贝勒等充当议员”。[44]
官制改革正式启动后,编纂官制王大臣“所会议者,大率皆本端午帅之原奏”。[45]但在对于政务处的意见上,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中外日报》专电称,“新内阁已议定,设两副理大臣,将军机处及政务处一律并入,日内即将入奏”。[46]陶湘致盛宣怀密函中亦称,“第一次编纂处议上时,系内阁、军机、政务大臣皆归并,改为总理一人,副理二人,并设资政、集贤两院”。[19](P30)现收入《光绪朝朱批奏折》中的《谨拟内阁官制初议草案》即“以内阁、军机处、政务处改并”而组成新内阁。[47](第33辑,P57)可见,此草案为编纂官制王大臣最初时所拟议。其中,以政务处归并于内阁,而都察院改设集议院。此草案似曾拟为大纲,于9月18日编纂官制王大臣奏陈《厘定官制宗旨大略折》时一并进呈过。据恽毓鼎9月20日所记,“议新政大臣奏陈改定官制大纲,留中不下,盖圣意犹欲审慎而后出也”。[48](P324)《申报》9月27日对此大纲有所披露,“内阁,总理全国一切政务,如日本之内阁然。将军机处、政务处并入。设总理大臣一员,副总理大臣四员……集议院,如各国上议院。以都察院并入”。[49]《时报》随后亦称“议定改官制之折已于本月初二日由王大臣会衔递上,当时留中,至今尚未发出”。[50]但是,以都察院改设集议院,立即招致反对之声。陆宝忠于9月15日为王宝田、李经野等人所上封事致函瞿鸿禨,希望瞿氏“造膝时,能为略伸其意”,并云“近日厘定官制,乃朝廷变法自强、实事求是之至意,预议诸臣,苟出以公心,酌古准今,和衷商榷,何尝不可推行。乃倡议者不学无术,又辅之以三五嗜进喜事少年,逞其私见,任意去留,几欲举祖宗成法扫除而更张之,以致人心愤怒,举国哗然”。[51](P20)而王宝田等人之折即大力反对裁改都察院,称“今之议者乃欲去都察院,未知考察诸臣果何所据,要其平日所为必有不堪告人者,故大懼诸御史之多言而发其奸也”。[36](P159)陈田亦称,“改都察院为议院,只得议政不得上封事,此尤蔽塞朝廷耳目之私意也”。[47](第22辑,P779)此外,又有“某大臣封奏,集议之员须另行选派,以符名实。诚恐御史等非尽合程度也”。[52]加之“庆邸亦深以不改动为然,恐言官因此疑忌或至鼓噪。两宫圣意亦欲保存衙门,故决议不提议。袁宫保召见时亦奏明不改都察院”。[42]由此,都察院的裁改暂且搁置下来。
与此同时,政务处的去向也随之发生变化。据报道,“政务处拟改为集议院,为上议院之基础”,而“内阁即系以军机处及旧内阁两处合并而成”。[53]这一变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保存都察院而引起的方案调整,另一方面则是考察政治馆此时已成为预备立宪的重要机构,[54]“拟改为法制调查局”,“亦隶于内阁”,[53]大有取政务处而代之之势。以政务处改集议院,对集议院而言并无多大影响,当道诸公仍“以缩小其权力为宗旨,盖恐因此而张大民权也”。[55]然而,“恐因此而张大民权”只不过是搪塞之词,在“君权不可侵损”宗旨下,[51](P21)其实际目的应是建立“无监督之责任内阁”。其间,集议院之名迭经更换,因“庆邸极不愿意议院二字,故不得已改为集贤院”,[56]嗣又屡经会议,“以资政院带集议之性质”。[57]揆诸《资政院官制草案》第14条称,“资政院所陈事件由总裁、副总裁咨送内阁,请旨施行。若内阁总理大臣以为不可行,须临本院或派员陈明己见,本院不得强政府施行”;第26条称,“资政院参议员如原有专折奏事之权,于本院现行开议之事,不得陈奏”。[58](P59-60)资政院既然不能强制政府施行,则“无监督之责任内阁”昭然若揭。袁世凯如此一箭双雕之设计,既可“借此以保其后来”,[19](P28)又可防止资政院掣肘行政。故而铁良才有“如乃公(注:袁世凯)所谓立宪,实与立宪之本旨不合”等语。[19](P29)
此时内官制的讨论已进入白热化,各大臣之间明争暗斗,“各树党援,互相挤排,台谏上书亦党同伐异”。[41](P660)“铁(良)自揣总理必归庆邸,若自己要户部,则失副总理,若要副总理,则失户部。盖现下军机、兵权、财政握于一人之手,若实行改变,则自己止可得一而必失二,于是极力与庆、袁反对,实自计利害之心过胜耳”。[59]荣庆、铁良等人对成立责任内阁表示反对,又“授意陆宝忠运动许珏、文海、周克宽、刘汝骥、柯劭忞、王步瀛、张瑞荫、杜本崇、蔡金台等交章弹劾”。[60]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御史刘汝骥、王步瀛、张瑞荫,翰林院侍读柯劭忞,吏部主事胡思敬,皆认为设立责任内阁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权臣窃弄政柄的恶果”。[61]如周克宽称,“今议并军机、政务于内阁,而设三大臣以担全国之责成,官少事烦,恐虽才力兼人,亦未易愉快胜任”。[36](P419-420)王步瀛称,“若号为内阁总理,不过近支王公,或者不明无断,名实相违,似转不若现设军机三五臣工参酌办理之为得”。[36](P427)
而“赵炳麟、蔡金台、石长信、王诚羲、史履晋等之反对马上设立责任内阁,却是另外一种情况”。[62](P63)如御史蔡金台称,“各国之臣权百倍于我,而绝无内重外重之弊者,则民选议院之效也。臣愚以为此时仿办,但可狭其范围,不可误其宗旨,但可暂以此权付之与民相近之士,断不可误以此权属之势莫与京之官”。[36](P412-413)御史石长信称,“今下议院未兴,国民程度不及,不能保荐即不能持其进退,而集重权于一人,幸公忠自矢,已不免专擅之嫌,倘私意偶蒙,恐流为僭窃之渐,征诸泰西,似有未协。”[36](P431)御史王诚羲亦称,“各国政府责任虽重,而内无专擅之嫌,外无藩镇之祸者,恃有议院以持其后也。……假令各国并无议院之助,其设官必不尽如今日之制,断可知矣。”[36](P451)史履晋更明确指出,议院为立法之地,而政府为行政、司法之地,议院可以监督政府,使政府有所顾忌,此为“宪法之精意”。“倘未立议院,先立内阁,举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握于三数人,则政府之权愈尊,而民气不得伸”,“不但立宪各国无此成法,亦大失谕旨庶政公诸舆论之本意矣”。[36](P461)
赵炳麟将《内阁官制草案》逐条批驳,强调“政府钳制议院,议院亦监督政府”,“固非一任政府操无上之权而莫之或问也”。“我国教育未兴,率有私党而无公党,原无政界思想,只以富贵相求”,“故在朝只有私党之营,在野决无政党之固,上下议院不克成立者以此,责任政府不能仿行者亦以此。若贸然为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遽立此无监督之责任政府,恐患气之乘不在敌国外忧,而在邦域之内也。”此外,他进一步指出,官制局所拟定之行政法规草案,是“立法、行政直出一人”。且官制草案中“政府交集议院公议之法律草案,开阁议决之,以总理大臣为议长”,⑧是“自行交议,又自行议决,而自作议长,是总理大臣非特上对君主代付行政之全权,并下代议院兼操立法之实际,而集议院徒作赘疣”。[36](P441-442)显而易见,赵炳麟等人反对的,一方面是责任内阁权力过大,与清朝历来体制固不相符,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尚不完备,无法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胡思敬就尖锐地提出,之所以成立资政院,乃“士气渐嚣,外省呈电沓至,欲以一院当舆论之冲。使政府得安行其政策。本固拒而云周谘,欲盖弥彰”。[63](P1447)孙宝瑄也认为,“下议院之在国家,如人身中命门之火也!有此火之炽盛,则百骸润,脑力强;反是,则无生理。今变法而不知从事于此,纷纷厘定官制,更易名称,徒然也。”[64](P934)此外,“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袁世凯如芒在背,“北洋旧人如唐君绍仪、梁君敦彦力劝项城出京,乃乘彰德大操,以钦派阅军为名,自京往彰德”。[65](P45)
面对朝中针对官制草案的交相攻讦,载泽于10月21日特上《申明厘定官制要旨折》,[47](第33辑,P52)希望挽回局面,说服慈禧太后。折中称,⑨“此次厘定官制,无非恪遵睿训,参酌旧章,但期收整齐画一之规,原非为扫除更张之计。言者不悟圣哲因时制宜之妙,而斤斤以变更祖制为疑”,“今总理大臣之设,不过正其名位,以副中外之具瞻。若夫国家大政出自亲裁,彼固不得而擅之也。部院大臣皆由特简,彼固不得而私之也。犹虑其权之太重也,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督内阁。”[66](P144-147)然而上意已变,慈禧非但不愿召见载泽,并告庆亲王,“从前我看载泽甚好,不料此次出洋被人愚弄”。[67]至11月2日,庆亲王奕劻等将内官制各草案进呈御览。其中,拟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设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等十一部,并“设集贤院以昭恩礼”,“改政务处为资政院,以彰公溥”,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大理院、军谘府等以次成立,都察院“原缺职掌与新拟部院官制参差重复者,当略加厘正,以归画一”。[36](P469-471)
三、新瓶旧酒
有学者认为,对于奕劻等人进呈的官制改革方案,慈禧“害怕责任内阁成立后君权潜移,疑忌袁世凯权势过重,不同意设立,对奕劻等提出的改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的方案也仅接受了一半”。[62](P63)然而细读奕劻等人所上《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则可发现该折实际蕴含两套方案:第一套是责任内阁,第二套是变通军机处。该折称:“若是者(责任内阁制),责成既已明定,积弊庶可廓清。宪政规模,实肇于此。如以议院甫有萌芽,骤难成立,所以监督行政者尚未完全,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行政机关屹然已定,宪政官制确有始基矣。”[36](P465)言外之意,如果成立责任内阁,则设立资政院以为议院之预备,势在必行。而如果认为设资政院的条件尚不成熟,则亦可变通军机处,内阁仍旧,使“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消息灵通的报界似乎对这一言外之意了然于胸。《时报》于官制草案进呈的次日即刊出电报,称“编纂官制大臣十六日将议定官制具奏。内阁之名或改为政务处,设总理大臣一员,副总理大臣二员。初议之资政、行政裁判诸院一概作罢”。[68]几日后,该报又披露,“总司核定处于原议草案中颇有更改……内阁则拟用内阁及政务处两名,请旨候朱笔圈出用。将来不过将军机处换一名目而已。如圈出内阁,则总理一席即名为内阁总理大臣;圈出政务处,则名为总理政务处大臣。”[69]《中外日报》亦有专电,称“内阁总理大臣现又议改为政务大臣,其旧有之内阁则仍如故”。[70]正如前引《时报》消息所揭示,奕劻等人进呈的官制方案乃是总司核定大臣对原议草案进行修改后的结果,⑩而主其事者则为瞿鸿禨。瞿鸿禨对于将官制全盘更动一事并不赞成,所谓“敝不在法,而在行法之人”,“今日之当改者,自应因时变通,特宜循序渐进,不在一切纷更,顾力行何如耳”。[71](P35)因此,在官制改革的讨论中,“善化(注:瞿鸿禨)朝夕持《会典》详核,稍事更动”。[19](P30)另据报章披露,“反对官制,固疑荣铁二人,然荣与铁无大机智。惟瞿则变化百出,善于操纵。彼第一以利用庆王,第二则操纵孙中堂。端午帅正在会议官制,忽然出督两江,亦彼运动使去。取敬远之主义,以孤袁宫保之势力。一面运动南城御史等,纷纷具折弹劾,极力阻挠改革官制。至以孙中堂为议官制之首,亦彼之策。盖彼最畏清议,而能外饰文明。以孙为傀儡,置于首要之地,万一改革派构难生事,即将责任推诿于孙,与己无关。其机敏如是,他人诚不可及云。”[72]
对于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瞿鸿禨亦表示反对。其在《复核官制说帖》(11)中指出,军机处因雍正时军务机要而设,“相承至今不改,实以地依禁,每日承旨办事,无少稽留,一洗从前内阁之旧习”,且其“立法精密,实为前古所无。日本以内阁居首,亦采中制”。同时,“欧洲各国不名内阁,其以一员总理,则同我朝以军机处为行政总汇,其义亦未尝不同军机处”。他特别强调,军机处之印文“向称办理”,似旨在反驳认为军机处“对于上则仅备顾问,对于下则未受责成”[36](P368)的看法。而设置总理大臣,瞿鸿禨则举乾隆朝故事,认为“总理政事之名,虽亲贤有所不敢居也”,但是,瞿氏并不敢公开反对改制。他本着上谕中“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73](P129)的宗旨,提出“近年奉旨设政务处矣,如以军机名称宜改,不若易为政务处,其办事大臣即名政务大臣,似为名正言顺。其余各部大臣本会合行政,即名参预政务大臣,亦与统称政府之义相□合”。如此,则“内阁一切职掌,仍从其旧,无庸移并。原拟五局,亦无庸设”。所以,《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中的第二套方案必然为瞿鸿禨之意。(12)
这一变通方案,新瓶装旧酒。立宪政体下的责任内阁,“凡循例无甚关于重要之件,即执定法以行之,或由行政上便宜处分,无所不可”,“各国现例,凡阁议,非有要事不开”;而军机处则仰承旨意,“一切例定事项,皆须一一入告”。[51](P41)若仅将军机处改名为政务处,各部大臣为参预政务大臣,所谓“会合行政”貌似“与统称政府之义相□合”,实则与原有规制并无二致,“仍以各部轮班值日,伺候召对,有事则会议”,故瞿鸿禨认为此举亦“名正言顺”。瞿鸿禨之所以反对,大致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扼定上稽成法、酌古准今、折衷至当数语”,其核心是旧有体制不应大变,君权必须独尊,民权不能扩张。与此相应,则军机处关系君权,不能裁撤,资政院关系民权,理当制约。无独有偶,御史张瑞荫此前就奏称,“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不过遇事请旨耳,视前明之内阁票拟何异。若谓大权仍不下移,其谁信之”,故建议“如必须事归内阁,则政务处可以归并,军机处自宜并存,以分其势。大致如宋之枢密主兵权,中书主内治,汉之丞相秉政,太尉典兵,事有攸分,权无偏重”。[36](P430)此外,瞿鸿禨认为,“今中国官民程度俱有未及,议院未能遽立,地方未能自治,而先行立宪之官制,其势必多扞格”,故将资政院加以限定,仅在“博选通才,集思广益,为采舆论、通下情起见,裁缺之员亦不至尽置闲散”。可见,瞿氏所能接受的资政院,只是“采舆论、通下情”之地,与议院之宗旨泾渭分明,且需身兼集贤院之任,安置裁缺人员,不另设集贤院。另一方面,瞿鸿禨深知,“内阁者,各部之总汇也,改各部不改内阁,犹以旧锅炉运新汽机,必无指臂相使之效”。[7](P58)但总理大臣之位非己所有,而军机大臣既能“每日承旨办事”,且“有事无不总汇”。(13)所以,尽管袁世凯“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9](P951)而瞿鸿禨仍旧提出仅将军机处改名,既不用设立总理大臣,又可保留其“每日承旨办事”之权力,作为一变相之内阁。张之洞所谓“默运挽回,功在社稷”,[51](P33)应即指此。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总司核定大臣之一,庆亲王奕劻对瞿鸿禨之修改内容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丁士源就曾向他言及,“由各部大臣会议所在即系内阁,与现时政务处会议相似”。[74](P443)然庆王在外人看来“向来无可无不可,故一切均九公(注:瞿鸿禨)专主”。[19](P30)据鹿传霖说,“邸无定见,初亦为人惑,近稍悟。至立宪不能遽行之意,则均同也”。[75](丙午七月十七日京鹿尚书来电,P322)至于孙家鼐,其在官制讨论之初就曾表示“不以改官制为然,大意以为官之不职,择人可也,何必更动旧制”,[76]“在振百司之精神,不在新天下之耳目”,[75](丙午九月初七、十三日京陈道来电.P306)且“多集干员在府中将官制草案逐条签驳”。[77]
官制草案进呈后,慈禧太后思量再三,最终完全接受了瞿鸿禨的建议,“军机处拟改为办理政务处,军机大臣拟改为办理政务大臣,内阁如旧制”,“资政院采群言拟设”,[47](第33辑,P62-63)并一度就此草拟了谕旨。草谕中称,“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其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名曰办理政务处。办事大臣即授为办理政务大臣,至总理名目,仍候特旨简派,不为常例。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原设之政务处即行裁撤……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查核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原拟各部院等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名缺,仍著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政务大臣奏明办理。”[47](第33辑,P54-55)也就是说,将军机处改名为办理政务处,而非归并内阁,军机大臣改为政务大臣,总理大臣不常设,同时裁撤原设之政务处,资政院等依次设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变动也带来不小的麻烦。旧的内阁不归并,则原草案中计划接收旧内阁事务的衙门势必作出相应的调整。此外,按此草谕之意,以军机处改名为办理政务处,原设之政务处即行裁撤,则原本“以政务处改设”的资政院将成无本之木,进退失据,不免前后冲突。故而在正式颁布前,对此草谕又进行了删改。
比较草谕与颁谕,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改动痕迹。第一,调整衙门班次与行文语序,增加遗漏的衙门。如在毋庸更改的衙门中,将銮仪卫调至内务府之前,在顺天府之后增加仓场衙门。将“除外务部堂官员缺仍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一句调至“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之后。第二,删改自相矛盾之处,务求前后一致。如删去了“名曰办理政务处。办事大臣即授为办理政务大臣,至总理名目,仍候特旨简派,不为常例”与“原设之政务处即行裁撤”两句,将“会同政务大臣奏明办理”改为“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14)因此,在颁布的谕旨中,不仅未改变军机处原有的名目,亦不增设总理大臣,但仍增加各部尚书为参预政务大臣。
然而,此一删改的上谕,文气既欠通顺,内容也有相当大的疏漏。既然军机处不更名,则政务处自然依据官制草案改为资政院,那么谕旨中各部尚书充“参预政务大臣”又成为无的放矢。这一纰漏,直到三天之后才被发现。或许为了照顾朝廷体面,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政务处著改为会议政务处”,[73](P209)既无改设因由,又无权限职能,实际上成了折衷妥协的替代品。(15)而迟至1908年7月方才订定院章的资政院,则不再提及由政务处改设的问题。[78]袁世凯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曾拟遵二十日谕旨,‘体察情形,随时修改’之意,设法补救,大致欲合军机于政务处,以复阁议,附编制、统计两局于该处,以重事权。商诸育周(载振)、菊人(徐世昌)两尚书,俱以从缓为宜,缘是暂不饶舌”。[79](P171)大江东去,圣眷已衰。外界称,“虽袁督之权势声望与力图革新,亦无奈何”。[80]
改设之后,会议政务处“拟仿内阁会议办法,各部尚书每五日与军机大臣会议一次”。[81]其原有工作,经政府王大臣会议,“寻常交议折奏及日行公文均由政治馆办理”,“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均兼考查政治馆差使”。[82](P584)由此可见,会议政务处除名称上的延续性外,与原有的政务处相比,其性质已大相径庭,“具有向责任内阁过渡的性质”。[83](P228)至此,政务处完成了向会议政务处的改设,丙午内官制改革也随之草草收场。
围绕清末政务处改设所产生的争论与方案以及最后的选择,不难看出丙午内官制改革的复杂和曲折,亦可反映出清末朝野上下在政体改革问题上的观念差异与利益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宪政体制的关照下,时人容易忽视清朝固有政治机构的设官本意,以之与宪政体制下的相关机构进行简单比附。一旦改革深入,必定不相凿枘。此外,不同机构为了在改革后保留位置,获得适合的发展空间,亦必造成改革的复杂与分歧,矛盾重重。政务处的改设方向之所以在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摇摆不定,即有此种因素的影响。在立宪的招牌下,各方的改革要求各有异同,互相冲突,最高统治者为平衡各派的政治诉求,采取平衡牵制,使得官制改革有名无实,也加深了各方之间的矛盾。政务处虽经改设成类似责任内阁的机构,在制度上规定了枢臣与部臣的“会合行政”,实则并未改变原有的中枢行政体制,反成叠床架屋之势,(16)丙午改制效果甚微。同时,也未能平息各派的纷争。“孝钦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世凯大失望,益衔鸿禨”。[84](P125)随后而来的丁未政潮,即是丙午改制中政治斗争的延续。(17)
注释:
①文中“政务处”均为“督办政务处”的简称。
②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修订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等。
③王立诚、楼劲认为,政务处在改设之后,“天下政治之管辖”的地位为考察政治馆及其改设的宪政编查馆所取代。而负责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宜,则成了会议政务处的主要职责(《政务处与清末政局》,上海市历史学会编:《中国史论集》,内部发行,1986年11月)。关晓红指出,丙午改制后,“军机处侧重于军事与外交,各部所管新政事物则主要由内阁会议政务处审议。除外务部外,各部尚书退出军机处而仍充会议政务大臣,至少是减轻军机处的事权,增加政务处的权限”,且“具有向责任内阁过渡的性质”(《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彭剑注意到《内阁官制草案》前后关于政务处去留的不同,惜未予深究(《宪政本土化中的集团政治——基于清季宪政编查馆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2007年6月,第116-119页)。
④参见李细珠:《丙午官制改革与责任内阁制的命运: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32页。
⑤此九部分别是内务部、财政部、外务部、军部、法部、学部、商部、交通部、殖务部。
⑥参见夏晓红:《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现代中国》第11辑;[日]狭间直树:《清朝的立宪准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徐洪兴、小岛毅等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18页。
⑦据胡思敬记,“五大臣归,至天津,世凯劳以酒,曰:‘此行良苦,将何以报命?’皆愕然,莫会其意。世凯出疏稿示之,曰:‘我筹之久矣,此宜可用。’遂上之。”见《大盗窃国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445),第1351页。
⑧赵炳麟所称“集议院”,当时已改为“资政院”。
⑨此折为杨寿枏所代拟,正式上奏时有较大删节。
⑩彭剑提到了官制草案的定稿问题,并找到了经总司核定大臣定稿的《内阁官制清单》(彭剑:《宪政本土化中的集团政治——基于清季宪政编查馆的研究》,第116页)。
(11)李振武曾对该说帖的上奏时间提出质疑,认为应在11月6日以后(李振武:《〈瞿鸿禨复核官制说帖〉考略》,《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但是,该说帖如果晚于11月6日(九月廿日),则根本无法说明该说帖与草拟谕旨中文字上的基本相同。
(12)另据刘厚生说,“我在长沙《瞿氏家谱》中,搜集材料后,而加以推测,似乎瞿鸿禨之说动那拉氏,另有一种微妙的措词。他大概这末说吧:责任内阁制度是立宪国一定不易之常规,是无可反对的。责任内阁成立之后,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开会决定,决定之后,再请谕旨宣布施行,此与军机处事前请旨的情形,完全不同。……大概保存军机处内阁,那几句扼要的上谕,完全是鸿禨的主张,并且是鸿禨的手笔。”(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张国淦也有此种说法(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13)参见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1967年版,第492-500页。
(14)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96-197页。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所引该上谕,一处标点似可商榷,其标点为“军机处为行政总汇,本由内阁分设……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该谕后文又称,“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均著毋庸更改”。如此,则同一上谕中对内阁的情况进行两次交代,似属不妥。故前一处标点可改为“军机处为行政总汇,本由内阁分设……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所谓“复改内阁”,意为军机处不须改归内阁,“复”字乃是针对前文“本由内阁分设”而言。
(15)此变动,时人亦未深究。因此,刘锦藻仍然认为资政院为政务处所改(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63、8765页)。
(16)有消息称,“从前内外大小臣工所递封奏条陈均交政务处核议施行。顷因设立政治馆以来,一切折奏俱交该馆核办,而政务处遂无核议事权,颇有闲散废弛之像云”。(《政务处已成闲曹》,《盛京时报》1907年1月22日,第2版)
(17)参见周育民:《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
标签:都察院论文; 日本首相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历史论文; 孙宝琦论文; 王大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