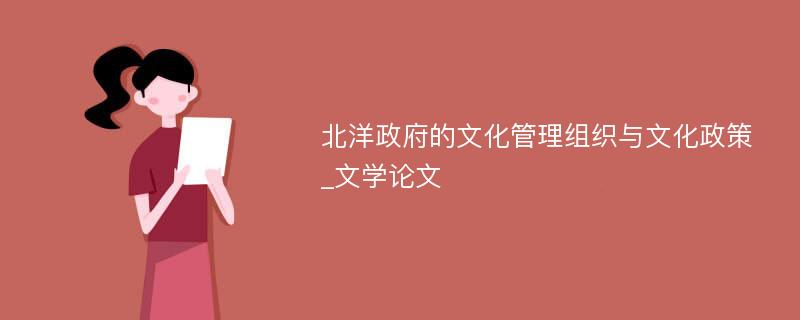
北洋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与文化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文化论文,管理机构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并无余裕顾及文化事业,仓促之间公布的“暂行报律”因有“钳制舆论”的嫌疑且程序不合法,受到“全国报界俱进会”的质疑和反对①,旋生旋灭,几乎没有影响。北洋政府时期,《出版法》(1914年12月)、《著作权法》(1915年11月)陆续颁行,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也在两法的施行过程中逐渐明确,并在此后陆续推出了若干具体的管理规则、章程、办法,一套趋新且不乏本土色彩的外部干预机制由此进入新的文学体制之中,并逐渐发展成为文学制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补充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实权人物对文学的偶发性干预又是频繁出现的,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这一点无疑也是文学制度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北洋政府的文化、文学理念基本停留在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文学移风易俗的层次,较多的管制往往指向所谓有伤风化的通俗作品,而对新文学并没有太多介入。②从“临时约法时期”到北伐落幕,北洋政府的文化管理及政策的变迁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临时约法时期”和“新约法时期”(1912-1916)即袁世凯当政时期初步确立文化管理的格局,内务部、教育部特别是前者扮演了重要角色;“法统争执时期”(1916-1924)出台若干文化管理细则,形成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导与京师警察厅查禁两种手段、方式交相为用的管理制度;“法统放弃时期”(1924-1928)即段祺瑞执政和北京军政府时期,常规的文化管理几乎不复存在,这时实权人物的个性、好恶等不确定因素起到了较多作用。③总体说来,在新文学生产、传播和相应的文化市场尚未展开之时,北洋政府的文化管理也是比较粗疏的,一个常规性的管理机构,是教育部的“通俗教育研究会”。 一 教育部与通俗教育研究会 教育部分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此后几经改制而结构不变,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是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是首任总长蔡元培有鉴于西方国家社会教育之发达而增设的,下设图书博物科与通俗科,主要职责是施行民众教育。最广为人知的事实,是鲁迅曾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即图书博物科科长。鲁迅所作之《儗播布美术意见书》第四方面的内容“播布美术之方”,所涉种种几乎是该科具体事务的最赅要的说明④,而他负责的若干工作,如迁移京师图书馆、筹办历史博物馆、与内务部交涉文津阁《四库全书》等,即为该科之具体职能。通俗科的职能与图书博物科有交叉之处,而与现实中的文化活动关系更为直接、密切。晚清以来,小说、戏曲等传统民间文学样式的重要作用逐渐得到舆论认可,士人的“观风俗”与民众的“听故事”产生交集⑤,催生了大量通俗作品,其中就包含了众多“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⑥的所谓“不良”作品。通俗科的职责是全面评估这种状况,并负责提出处理办法,像《教育部禁止出版伤风败俗小说杂志的通告》(1915年1月)即是其具体行为。不过,通俗科乃至社会教育司的工作,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被1915年9月6日成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所取代。 1915年7月16日,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呈文,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⑦,两日后大总统即批复“准如所拟办理”,并拨出15400元作为开办和活动经费。不同于此前的中国通俗教育会的是,通俗教育研究会隶属于教育部,会长由教育部次长兼任,会员则由京师各有关机构选派,是一个正式的官方行政机构。该会下设小说、戏曲、讲演三股,讲演股以法律、卫生、教育等为内容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主题演讲,向民众(主要是市民)宣传现代社会常识,承担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教育的最主要工作;而小说、戏曲二股则主要负责小说、戏曲、评书等新旧文学的审核、奖掖、劝导、改良、查禁等工作,与文学最为相关。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性质、宗旨、职能看,“这个名为研究‘通俗教育’的官方组织,实际上有点类似一个图书杂志审查机关,不过其职权范围比后者要大得多”⑧,下面即按照其关涉文学的上述几种最重要的职能分述之。 第一,审核。鲁迅在1915年8月3日和教育部同僚共二十九人奉部命加入通俗教育研究会,且在同年的9月1日指定担任小说股主任,后于次年2月底辞去主任职务,改任审核干事。在鲁迅主持小说股期间,讨论通过了小说股进行办法、办事细则以及《审核小说之标准》《编译小说标准》《奖励小说章程》《查禁小说议案》等。根据小说股第一次会议所载,小说分教育、政事、哲学与宗教、历史地理、实质科学、社会情况、寓言及谐语、杂记八类,按一定的标准分三等,“上等之小说宜设法提倡;中等者宜听任;下等者宜设法限制或禁止之”⑨。据正式章程,区分的标准是,“宗旨纯正,有益于国家社会者;思想优美,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灌输科学知识,有益于文化发达者;文词优美,宗旨平正者”为上等,宜提倡、奖励;“宗旨乖谬,妨碍公共秩序者;词意淫邪,违反良风善俗者;思想偏激,危害国家安全者”为下等,宜限制、禁止。⑩参照《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戏剧章程》的审核标准,大体而言,小说、戏剧的奖励标准并无不妥,而从之后的图书、杂志的查禁事实来看,禁止的标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至于审核的程序和办法,小说股基本采用鲁迅的意见:其一,“先由通俗图书馆之小说着手,由第一号起陆续审核”,“一方就由图书馆已经取来登簿之小说审核,再将图书馆新买尚未编号之小说审核,双方并进”,分员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其二,因为“报纸所载小说为多,即不妨先就报纸设法禁止”,具体方法“宜分两项:一为书肆发行及贩售之禁止;一为报纸登载之禁止”。(11) 第二,奖掖。《奖励小说章程》提出:“自撰之小说经本会审核认为有裨益于人心风俗者,得受领甲种褒状;迻译外国人旧著或新撰之著名小说,经本会审核认为可补助我国人之道德智识者,得受领乙种褒状;采辑古今中外之杂事琐闻汇为一书,有类札记,经本会审核认为有益于社会者得受领丙种褒状。”(12)经小说股审核,教育部以部令的形式先后公布百余种小说予以褒奖,且发出咨文,推荐各级图书馆、学校广为采购。这批受到褒奖的小说,如《块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冰雪因缘》《鲁滨逊漂流记》等林译小说,绝大部分属于乙种,而从中表现出对妇女、儿童、黑奴弱势群体苦难处境和奋斗精神的揄扬,可以看到民国成立以后,政治主流和行政主体对人道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想的肯定和接纳。 第三,劝导与改良。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宗旨即在于“改良社会,普及教育”,对符合这一宗旨的带文学性质的著述本有褒扬、提倡的职责,劝导与改良不过是沿袭文学移风易俗的古典传统并受晚清以来文坛舆论影响而顺理成章产生的一种举措,如《通俗教育研究会改良戏剧议案》认为戏剧对社会风化至关重要,“故在今日,欲改良社会,非改良戏剧不为功”(13)。问题在于,来自于当政者主观意图的劝导有否效力实在成问题。《通俗教育研究会关于不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致作家函》《通俗教育研究会关于编写提倡勤朴艰苦美德小说致作家函》等函告,良苦用心一望可知,但日益受读者趣味左右的作家总能找到最贴合市场选择的路径,民初鸳鸯蝴蝶派的流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当然,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往往受部、司主脑人物的政治立场和主观倾向的影响。张一麐1915年10月接任教育总长,在通俗研究会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演说,认为“中国社会自游牧时代进入宗法时代,而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之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且要求“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望“本会会员”“戮力同心,进行不懈”。(14)就事情本身来看,张一麐的这番言论不过是民国老派政治人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重复,但在客观上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舆论导向相贴合,虽然他与那些迎合袁世凯而鼓吹“忠君”、“尊孔”的一班人不无区别。 第四,查禁。北洋政府《出版法》沿袭此前公布的“命令式之法律”《报纸条例》的精神,第十一条对查禁内容作如下规定: 文书图画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出版: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 张静庐作为亲身经历者,指出第十一条“与报纸最有关系,动辄得咎,非常危险”(15)。其中与通俗教育研究会最有关系的一点,即所谓“败坏风俗者”。 这里的“败坏风俗”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有损社会道德基准的内容,如《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戏剧章程》载明查禁的内容,“一、情节淫秽,有伤风化者;二、凶暴悖乱,足以影响人心风俗者;三、剧情荒谬,显悖人伦道德者;四、倡论邪说,意图煽惑者”(16),凡此种种,无不对正常社会应有的良风善俗造成恶的影响,所以对这一类书刊的查禁是合理的(其实,在对人性有更多、更深了解的今天,对此相对宽容,虽非全面禁止,但也限制分级)。北洋政府时期,列为“下等”而遭到查禁的文学类书刊,基本属于这一类,就此而论,通俗文学研究会是极为中正地履行了自己的职权。 举一书一刊为例。1916年9月7日,小说杂志《眉语》被禁。《眉语》1914年创刊,以文化消遣、娱乐为宗旨,是较早的鸳鸯蝴蝶类刊物。其所刊载的小说,在卿卿我我之外,其实不乏宣扬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之作,但为了吸引注意往往加倍夸饰,所以劝百讽一,几乎全为“眩惑”之作,比如主编高剑华就曾特意选取《裸体美人语》这种耸人耳目的题名。所以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咨文称,“经本会查得有《眉语》一种,其措辞命意,几若专以抉破道德藩篱,损害社会风纪为目的,在各种小说杂志中实为流弊最大……亟应设法查禁……并令停止出版,似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17),实在不为无因。1923年,《通俗教育丛刊》第18辑载有57种小说的审查意见,其中列为下等应予查禁的有22种,其中包括《荷花大少爷》。通俗教育研究会对此书的具体意见是:“是书自序谓惟荷花大少爷不独不受妓愚,反能赖妓之债,且能使之无从索讨,其手段又高出妓女一筹矣云云,因而历述其手段,不啻以欺诈之术导人,且专以欺诈之术施之妓女,直是下流无行矣。”这一评判极为中肯。 其二,主要针对“淆乱治安”、“妨害治安”的“过激主义”书刊,它们主要由内务部和京师警察厅负责,而通俗文学研究会呈报查禁的书刊(18),则基本不涉及这一类。 从上述通俗研究会及教育部相关部门的结构、组织、权限、行为来看,北洋政府设置的这一文学监管、审查部门所制定的褒奖惩处的标准的确体现了政府对文学移风易俗的良好主观期待,而从查禁事实来看,也主要指向那些在当时看来有伤风化的书刊。此外,小说股、戏剧股成员均为兼任,个人精力有限,所以审核的范围其实相当有限,因而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宜夸大。1923年,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无形停顿,北洋政府时期常规的文学管理亦不复存在。 二 内务部与京师警察厅 北洋政府时期,通俗文学研究会审核列为下等的书刊,需经教育部核准,然后咨行内务部,并由其下辖的警政司批转京师警察厅及各地方警察厅予以查禁。而从现象上看,与文学相关的书刊审核、评骘、查禁等事宜也均与内务部下属的京师警察厅相关:其一,通俗文学研究会系政府各机构抽调人员组成,警察厅也在其中,因之决策固然包含了警察厅的若干主张;其二,凡有书刊查禁,经常是以京师警察厅的名义发布公告,因而舆论不免将之认作“元凶”。当然,社会舆论的看法其来有自。在官方的通俗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京师警察厅不止一次地单独查禁了一批带有文学性质的书刊。据《京师警察厅为请转咨查禁不良小说致内务部呈》(1916年5月8日)所载,京师警察厅呈报内务部转咨教育部的这一呈文列出业已查禁的小说达63种之多。(19)虽然这批小说绝大部分是淫秽的低俗作品,如《风流太守》《妻妾吃醋》《姐夫戏小姨》《房中奇术》《灯草和尚》之类,的确应予查禁,但京师警察厅毕竟有违背程序之嫌,以致通俗文学研究会通过教育部、内务部向其索要查禁书目,委婉地表达了一种不满。其实,京师警察厅虽然常常以主体身份发布公告,但不过是接受内务部及其他上级部门的指令行事,一般不作为行政主体制订有关管理条例。(20)它作为北洋政府社会管理可以凭借的常规强制力量,主要是一个执行机关。从北洋政府的组织架构看,文学管理的真正常设机构是内务部。 通俗教育研究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代行内务部的文学管理职权,但由于其系各相关机构选派人员兼职组建,各成员自有本职工作,事权集中的优势便为人员分散、各不相属的组织劣势所抵销,事实上效率并不高。而且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它虽然负责常规的文学管理,其实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增设机构,内务部只要觉得有必要,就有足够的法理依据绕开它而指令京师警察厅单独行事。 内务部是与社会各方面关系最为密切的行政部门,虽然后来机构屡有调整,而职能基本不变,大体相当于清末的民政部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内政部。就总体状况而言,内务部和京师警察厅一般不直接插手纯粹的文学事务,它们重点关注的是上引《出版法》第十一条前两项的内容——“淆乱政体”和“妨害治安”——这类与现实政治相关且可能对执政基础形成冲击的书、报、刊。 1915年9月,内务部以“妨害治安”为名查禁《甲寅》《正谊》两种杂志。章士钊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避居日本,于1914年5月创立《甲寅》月刊,在日本共出4期,屡有脱期,第二年5月起改在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至第10期遭禁。《甲寅》以政论为主,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及复辟帝制活动多有批评,更重要的是它在知识人中间激起较为广泛的共鸣(21),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于是被禁。其实,《甲寅》第10期被正式取缔之前,第9期因发表《帝政驳议》,邮局已经停止寄送。与《甲寅》一样,《正谊》亦以政论为主,其《发刊词》申明刊物宗旨,对政府是“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22),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发生冲突,以至于1915年6月即被迫停刊。两份刊物被禁以后,两位主编章士钊、谷钟秀也遭政府通缉。(23) 如果说《甲寅》《正谊》是因其主编及各撰稿人涉及实际的政治活动从而遭禁,是打击政治敌对面,那么差不多同时其他文化、文学类书刊被禁的名目,诸如“诬诋政府”、“妨害治安”、“与时局甚有妨害”、“宗旨悖谬”、“宣传过激”等,无一不与民国成立以来在知识界获得愈来愈多认同的新思潮有关,个中关键,也在于是否与反对当时政府的实际活动相关。因为牵涉到实际政治,所以不仅内务部和京师警察厅,而且国务院及其他相关各部门,如交通部、邮政总局,都不免参与其中。在1924年以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是新思潮书刊、社团受到压制较为集中的两个时期,尤以后者为甚。 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内务部以“与现时风潮大有关系”为名查禁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直隶省长公署以“与时局甚有妨害”为名查禁了《北京女高师半月刊》。此外,《进化》月刊在1919年5月被交通部查禁,名目是“鼓吹无政府主义”。“进化社”是民声社、实社、平社、群社等四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联合而成,根据《进化》月刊首期看法的宣言,是追求“从根本上”“扫除”包括“现在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资本家”等在内的所有“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各种“强权”,所以主张“革命”(24),虽然只是纸面的主张,但以无政府主义在“五四”前后的声势,自然不能为政府容情。此后,京师警察厅也以同样的名义查禁了《光明》杂志。 这些查禁行为有时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1920年9月6日,京师警察厅查禁了北京师范学校一些学生组织的社团“觉社”出版的半月刊《觉社新刊》。此前北京市行政处给上级的呈文称:“查《新刊》内容主张改革社会、妇女解放、铲除阶级等,其《磨面的工人》一诗尤近煽惑劳工,拟查禁。”觉社成立于1920年初,宗旨是“本互助精神,研究学术,做实现真理社会的运动”,发表言论的标准,“趋重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志在实行工读以推广国民教育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目的的学生团体。(25)以师范生即一般中学生的眼光打量“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并提出改造办法,其实是极为平和的。像白涤洲,其时在校就读并为觉社的骨干分子,是一个“很精明,但不掏出手段;他很会办事,多一半是因为肯办,肯认真办”(26)的人,主张“工学主义”:“照这样实行起来,由于工作的生产,便可以与家庭脱离经济的关系。再发达起来,生产完全能抵补消费,便连公费都不用,完全自食其力,营独立的生活。然后更普及到各学校,普及到社会,人人作工,人人求学。那么,‘工学主义’普遍实现的希望便可以达到,人生最快乐的生活也可以出现了。”(27)这种民间自发改造社会的动向其实并不触及政权基础,却很少为当权者接受。《觉社新刊》遭查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煽惑劳工”之嫌的《磨面的工人》。其诗如下: 穿着破烂的衣裳,吸着不洁的空气! 为养那不劳而食的寄生虫,没昼没夜的拼命做活计! 可能养你的父母、妻子、姊妹、兄弟? 你做出来的面本是雪白的,为什么反吃那粗劣的棒子面? 你曾想到:吃你磨的面的人,不知你的饭粗、衣烂、工作不得闲? 就是知道、看见,也不过像“过眼云烟”? 这首诗与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比较,不过是在模拟的基础上增添了反问,是否这就是“煽惑”不得而知,但的确可以照见北洋政府草木皆兵的心态。 总之,以政权稳定为目的,内务部为首的北洋政府相关部门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管理难免杯弓蛇影,而作为中央政府的文化分管机关,内务部还是注重社会舆论的,总的行事原则在于师出有名,很少捕风捉影。相形之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其主脑人物就很少这方面的顾虑了。 三 行政长官的意志 民初主持新式文化事业(如报馆、出版社)的多为晚清以来的高层开明士人,他们受西方民主社会观念的影响,又有相当的声名、地位和社会资源,对相关律令中不合理的部分往往能够据理力争,如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因多设禁忌遭报界抗议,不久即废止。但在更多时候,行政当局首脑因为拥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他们的个人意志往往占据上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官、民对立情形反映了民国以后“由开明人士转型而来的自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由士绅支撑的正统秩序始终无法谐和,只好再度竞逐较量”的“新知识界与旧士绅的分离对立倾向”。(28)北洋政府时期有关文化、文学的重要事件,其实都有这一社会背景,而地方实权人物的横加干涉虽然并不能算多,但无疑加大了这一裂痕,以至于新文化界相信“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29),形成了“走向政治的趋势:他们因主张文学的表述形式与思想社会有关,就走向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因假想对立面有政治背景,也就越来越往政治方面着眼”(30)。 举两个1924年之前的例子。早在民国建国之初的1912年1月始,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就因报纸登载裁撤民军的消息先后查禁《国事报》《总商会报》《公言报》和《陀城日日新闻》,主持报纸的陈听香后来也被陆军法务局以军法条例判处死刑。陈炯明力主枪毙陈听香,事实是后者涉及为非作歹的民军叛逆之事(31),在当时虽得到士绅的普遍支持,但被报界渲染为压制舆论。今天看来,这一段历史公案的是非曲直已经清楚,问题在于陈炯明是否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报纸业已查封,相关人等也已控制起来,是否有必要采取极端手段? 1919年12月初,国务院下令查封《浙江新潮》,“立予禁止刷印邮寄,毋俾滋蔓,以遏乱萌”(32)。《浙江新潮》周刊的前身是《双十》半月刊,是浙江一师等在杭数个中等学校学生联合组织的杂志社所创办的刊物,志趣在于介绍新思潮,所以第三期起改名,而改为周刊之后,施存统在第二期上发表了《非孝》一文,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务院通令全国“随时严密查察”,实是源于浙省首脑人物的呈文。时任浙江督军的卢永祥、省长齐耀珊此前密电北京中央政府云: 近来杭州发现一种周刊报纸,初名《双十》,改名《浙江新潮》,通讯处为第一师范黄宗正。大致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其贻害秩序,败坏风俗,明目张胆,毫无忌惮。稍有知识者,莫不发指背裂。已令警务处禁止刷印邮寄,并饬教育厅查明通讯之人于该学校有无关系,呈复核办……惟查谬论流传,本非始于浙省,以全国推仰之北京大学,尚有《新潮》杂志专肆鼓簧;此外如《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惘……若辈违心背谬,自外生成,敢为叛道之莠言,即是人类之公敌。此等书报,有在内地发行及在租界外转售者,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乞训示遵行。(33) 这份电文汇集了文化守旧者的意见,此外亦有省议会多名议员联名致电大总统请予严办,不过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代表士绅阶层的浙省当局。“五四运动”以后,在校长经亨颐的主持下,“一师请来了几位新教师,其中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原有的夏丏尊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34),且定下了两种改革方针,“一种是文学改革,一种是学生自治”,后来“学生差不多全体都用白话作文”,“学生自治会也成立了”(35),学校于是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也正因为如此,也招来守旧派的敌视和当局的不满,而后者正要寻找机会改变局面。虽然后来“一师易长风潮”的结果尚属差强人意,但实权人物的强力干预,毕竟改变了文化格局,影响到了卷入其中的施存统、沈乃熙(夏衍)、宣钟华(宣中华)、赵平复(柔石)等人后来的政治选择、文学选择。 以上两例,一个涉及军事,一个涉及社会,都很难说是涉事行政首脑的政治选择,但都产生了实际的政治后果,足以影响文化、文学的走向。反倒是真正的政治行为,如对中共相关报刊的查禁,而因为限于政治,所以在社会上的震动不大——起码不像后来共产党人的回忆所描述的那样。北洋时期武夫当国,许多人其实修养不错,再不济也讲究个江湖义气,所以真正胡来的情况比较少见,但问题在于眼界不高,所以这些实权人物的主观意志、态度、倾向、行为之于文学发展虽然是偶然的、间歇的,但若干起事件层累叠加,居然形成了影响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方式,进而波及文学发展方向的长时段稳定力量,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从文学制度的角度看,它要比那些成文的制度构成要素重要得多。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惨案固然事出有因(36),但执政府屠杀学生毕竟削弱了政权的道义基础,同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份约五十人的名单(37),加深了知识界的恐慌。而执政府倒台后,奉系控制了北京并在其后成立了军政府,期间邵飘萍、林白水被杀,情形更趋严峻。在此背景下,知识界人士纷纷南下,至此中国的文化格局开始重组,重心也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地区。 北洋政府的文化、文学管理举措,是以内务部这一政府部门为常设总理机构,教育部从旁作业务辅助,而以二部人员为主要分子组成通俗文学研究会对文化、文学事业进行常规管理,遇有需强制执行的事项,则由京师警察厅按照指令照办的一个系统。从实际效果看,这套系统运行不够流畅,结果也与预期相差甚远,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文化转型之功。 ①(15)《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325,326、330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北洋政府查禁了较多与“过激主义”相关的书报,而所谓“过激主义”的认定,则以实际政治的需要为转移。“过激主义”显然与新文学、新思想有相当多的交叉,这就涉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过此处难以全面展开,只在必要时涉及。 ③这里的时期划分和命名采自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⑤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⑦此前的“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有时亦称“通俗教育研究会”)1912年4月28日成立于南京,是一个旨在灌输常识、培养公德的民间团体。由于参加者往往是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地方实力派,故经常影响到教育部以及社会教育的决策和行为,后出于人员流动、经费支绌等原因,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很快无形中湮灭。参见施克灿、李凯一《江湖与庙堂: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路径选择——以通俗教育研究会为考察对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⑧(12)(14)沈鹏年:《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关于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一段史实》,《学术月刊》1963年第6期。 ⑨(11)《小说股股员会议事录(一)》,《教育杂志》第7卷第12期,1915年12月15日。 ⑩《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杂志条例、标准与奖励章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3)《通俗教育研究会改良戏剧议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16)《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戏剧章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17)《教育公报》第3年第11期,转引自沈鹏年《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关于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一段史实》,《学术月刊》1963年第6期。 (18)参见吴效刚《民国时期查禁文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3、221~227页。 (19)《京师警察厅为请转咨查禁不良小说致内务部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194页。 (20)这当然不是绝对的,比如1925年4月曾有《京师警察厅公布管理新闻营业规则令》。 (21)参见孟庆澍《〈甲寅〉杂志略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该文考察杂志的销量时提及:“除了京津沪等各大商埠,《甲寅》还可以顺利发行到中国腹地,无论是湖南长沙还是四川成都,一个月内都可以看到东京出版的《甲寅》。” (22)谷钟秀:《发刊词》,《正谊》第1卷第1号,1914年1月15日。 (23)《吴虞日记》1915年10月22日记载:“晚马光瓒来谈,言《国民公报》登有政事堂来电,通饬缉捕章士钊、谷钟秀,谓其莠言乱政也。”参见吴虞《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24)凌霜:《本志宣言》,《进化》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20日。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5页。 (25)《发刊的旨趣》,《觉社新刊》第1期,1920年4月15日。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 (26)老舍:《哭白涤洲》,《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27)涤洲:《实行“工学主义”与师范生》,《觉社新刊》第1期,1920年4月15日。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9页。 (28)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5页。 (29)周作人:《现代散文选序》,《苦茶随笔》,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06页。 (30)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31)参见赵立人《泼向陈炯明的污水》(上),《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20日。 (32)《国务院致各省密电稿》(1919年12月2日),《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3页。 (33)《卢永祥致大总统等密电》(1919年11月27日),《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2~143页。 (34)傅彬然:《回忆浙江新潮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 (35)《〈浙江新潮〉被禁之由来》,《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8日。 (36)参见邵建《重勘“三一八”》,《温故》(之七),刘瑞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参见鲁迅《大衍发微》,《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