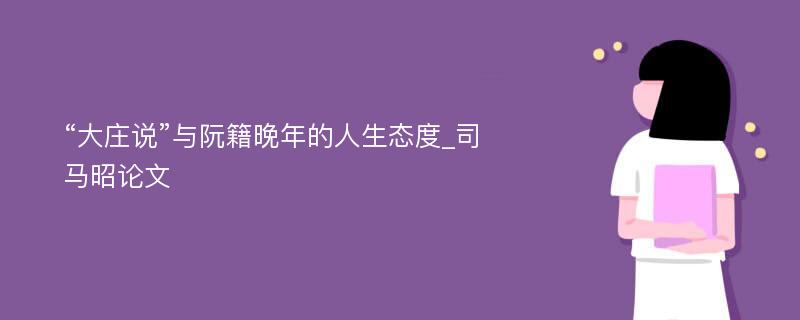
《达庄论》与阮籍后期的人生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人生态度论文,阮籍论文,达庄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阮籍《达庄论》不仅是研究阮籍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探讨阮籍散文创作特色不可忽略的代表性作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阮步兵集题辞》说:“嗣宗论乐,史迁不如,《通易》、《达庄》,则王弼、郭象二注,皆其环内也。以此三论,垂诸艺文,六家指要,网罗精阔。”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也评论说:“其见于明人所刻《阮集》者,有《通易论》、《达庄论》、《乐论》三篇。《通易》综贯全经之义,以推论世变之由,其文体奇偶相成,间用韵语;《达庄论》亦多韵语,然词必对偶,以气骋词;《乐论》文尤繁富,辅以壮丽之词。阮氏之文,盖以此数篇为至美。”②但阮籍《达庄论》究竟写作于何时,具体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其思想旨趣,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给以较圆满的解决。本文拟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达庄论》写作时间辨析
关于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意见,即正始九年(248年)说、嘉平五年(253年)说和景元元年(260年)说,这三种说法所对应的阮籍写作《达庄论》时的年龄分别为39岁、44岁和51岁。
1.嘉平五年说
该说较早的提出者是丁冠之先生。丁冠之认为,正始以前阮籍思想以儒学为主;正始以后,阮籍鄙弃礼法,推崇庄子。丁冠之对阮籍《达庄论》写作年代的界定即是以此为依据的。他根据《达庄论》同阮籍的另一名作《大人先生传》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从而推断《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应基本与《大人先生传》同时或略早。阮籍《大人先生传》,丁冠之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的考证,认为约作于正元二年(255年)至甘露三年(258年)之间。所以,丁冠之认为《达庄论》的写作不会晚于此时间,应是嘉平(249-253)、正元(254-256)之际的作品③。高晨阳先生在丁冠之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推断,认为《达庄论》应该写作于嘉平五年。高晨阳指出:
《达庄论》的撰作时间当略早于《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对君臣上下制度尚未彻底否定,而《大人先生传》则对之持完全批判的立场。从逻辑上说,从前者到后者表现为一个思想发展过程。但《达庄论》最早也不得作于正始时期,或说早于《通老论》,很可能是在竹林七贤“并居山阳”后回到洛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即在魏嘉平五年(253)前后。据刘汝霖考证,嵇康与向秀锻铁于洛邑约在嘉平五年。又据《向秀别传》载,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作《庄子注》,“妙析奇趣,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在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据上推测,向秀注《庄》有可能是在与嵇康、吕安在洛阳相交一段时间。阮籍的《达庄论》不必是向秀《庄子注》影响的产物,反过来说,《庄子注》也不必是《达庄论》影响的产物。但由此可以说明,当时思想界的学术倾向已由老学转向庄学,由于学人的鼓动、张扬,遂开庄学一代学风。由此推断,阮籍撰作《达庄论》于此时,其可能性极大④。
高晨阳《阮籍评传》后所附《阮籍年表》即将阮籍《达庄论》系于嘉平五年。由于丁、高之说年代界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将此看法概括为“嘉平五年”说。
2.正始九年说
此说最早由董众在其所编《阮步兵年谱》中提出⑤。其根据是阮籍《达庄论》开头一段话: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弅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洲。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⑥。
“单阏”、“执徐”是我国古代的太岁纪年法。《尔雅·释天》曰:“大(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⑦董氏据此推断此文应写作于正始九年阮籍39岁之时。韩传达《阮籍评传》也同意董众的说法,并说:“阮籍作论之时,曹氏与司马氏斗争胜败之势已成,阮籍也已看到世不可为的苗头,因而处世态度已开始由入世到遁世的转变,思想上也已开始从服膺儒学转为好谈庄、老之学。《达庄论》之作于此时(指正始九年),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⑧王晓毅也认为阮籍《达庄论》作于“正始八九年(247-248年),即正始之音的高潮中,似乎更合理”⑨。
3.景元元年说
沿董氏思路而下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看法的是陈伯君和郭光。陈伯君在其《阮籍集校注》的《达庄论》注中,也依据上述材料推断说:“阮籍在生之年,凡五遇卯、辰之岁:一、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十七年(壬辰),时年二、三岁。二、魏文帝黄初四年(癸卯)、五年(甲辰),时年十四、五岁,三、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四年(丙辰),时年二十六、七岁。四、魏齐王芳正始八年(丁卯)、九年(戊辰),时年三十八、九岁。五、魏高贵乡公髦甘露四年(己卯)、五年(庚辰),时年五十、五十一岁。高贵乡公于甘露五年五月被害,而观此文首段忧来无端,无可奈何之情绪,今假定系作于最后之一个辰年,或不远于事实。”⑩与陈伯君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郭光的《阮籍集校注》。其在《达庄论》注释中说“魏少帝奂景元元年(按,甘露五年六月,改元景元)为庚辰年,辰岁当指是年”,并认为《达庄论》写阮籍“景元元年五月高贵乡公被弑后的怅然无乐的心情”(11)。陈、郭之说我们概括为“景元元年”说。
检讨上述三种关于阮籍《达庄论》写作时间的看法,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都意在对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给出明确的判断,但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嘉平五年说”基本没有考虑《达庄论》文中的“内证”,更多的是结合“阮籍的思想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及社会思潮”来分析的;而“正始九年说”、“景元元年说”虽然结论不一致,但除了结合时代学术、政治环境和阮籍生活思想变化外,均考虑到了文章本身的时间提示即“内证”。因此,前者我们可称为“外证”论;后者我们可称为“内外结合”论。
这就遇到一个问题,考订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其作品本身提供的“内证”,是否可以作为判断其作品写作年代的基本依据?
要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先对阮籍现存作品进行分析。在阮籍今存作品中,有明确系年的只有《首阳山赋》一篇,据此赋前的“序”我们知道此文作于“正元元年”的秋冬之际(12)。另外,《鸠赋》据其“序”,知其写作应在“嘉平中”之后(13),具体时间不能确定。阮籍作品除此两篇外,其他均没有明确的时间提示。但阮籍《首阳山赋》的系年,对我们了解阮籍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心理动机确实又非常重要。“正元元年”正是司马师密谋废曹芳,曹魏政治动荡不安之际,《首阳山赋》就写作于司马师废曹芳不久。关于《首阳山赋》的写作背景和内在思想蕴含,笔者已著文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此不再赘述(14)。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他并不回避自己在特殊时期的思想感受,甚至可以说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特殊时期思想感受的变迁的。由此可见,阮籍《首阳山赋》的时间系年决非率意而为,自有其深意所在,只不过采用了具有符号暗示性的瞒天过海的障眼法罢了。验之《首阳山赋》的时间提示,再看阮籍《达庄论》中明确写到“先生”的活动时间,可以想见恐怕也不会是率意为之的。在笔者看来,阮籍此处的年代提示同《首阳山赋》一样本身也具有某种暗示性。结合对《首阳山赋》(包括《鸠赋》)时间提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阮籍《达庄论》里的时间提示是虚构的情况下,将其作为阮籍《达庄论》写作时间唯一可以依据的“内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判断。
通过上述检讨分析,笔者认为,就《达庄论》的写作年代而言,“内外结合”、兼顾的研究方法应是考订其写作时间最可取的方法。也就是说,阮籍的《达庄论》必是卯、辰之年的作品,而不可能是其他时间创作的。
这样,关于阮籍《达庄论》写作年代的界定就只有两个最可能的时间,即正始九年和景元元年。那么,阮籍的《达庄论》究竟是作于正始九年还是景元元年?诚如丁冠之、高晨阳等先生所指出的,阮籍思想性格的发展的确存在由崇儒到慕道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由现实政治局势和学术思潮的相互刺激和激荡得以完成的。但具体到阮籍个人而言,如何面对现实政治危恶环境的挤压,如何解决生命生存问题,才是他“心焦”、“忧虑”的头等大事。所以,考察阮籍《达庄论》的写作年代,既不能完全离开阮籍生活的时代的政治局势、学术思潮,也不能完全忽视阮籍作为自我存在的主体心灵的幽微变化,甚至是阮籍在政治苦局面前的机变和“远识”。因此,综合阮籍的时代环境、仕宦生活、人生处境、生命幽思等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陈伯君、郭光景元元年的推断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即《达庄论》不可能作于正始九年,而只能作于景元元年。
二 《达庄论》与阮籍后期的生存处境
《达庄论》重点描写了“先生”与“缙绅好事之徒”的一场论辩驳难,在结构上采用的是“问答之体,与《解嘲》、《客难》略相似”(15)。但细读阮籍《达庄论》,可以发现,其“问答之体”的运用决非仅仅是结构文章的一种形式,或对前贤“设论”文体的简单模仿。作为“有意味的形式”,阮籍《达庄论》的“问答之体”实际反映和折射了阮籍后期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一点对我们考订阮籍《达庄论》的写作年代和写作背景极富启示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阮籍的生活仕历来考察其论辩驳难可能发生的环境,并进而确定《达庄论》的写作年代及其背后蕴藏的现实因素。
据《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最早的仕宦生活是正始三年(242年)左右被蒋济征辟作掾属。但从他给蒋济的《奏记》中的话看,“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16),这时的阮籍对仕途并不热心,相反,他基本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蒋济征辟阮籍的正始前期,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矛盾还处于酝酿阶段,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总的来讲,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风平浪静的。所以,此时的阮籍不可能视仕途为畏途而回避之。阮籍辞蒋济征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阮籍自己说的身体“疲病,足力不强”,而且有“耕于东皋之阳”,“以避当途者之路”的隐逸之想。这与阮籍“时人多谓之痴”(17)的内向性格应该有很大关系。到正始后期曹爽召阮籍为参军时,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司马氏集团与曹爽集团的矛盾已显露天下。这时,有一定鉴识的士人均意识到形势的危恶,甚至权力中心的人物也产生了人生危殆的幽思之叹。前者如山涛,后者如何晏。《世说新语·政事》刘注引虞预《晋书》曰:“(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踏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世说新语·规箴》刘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18)此时的阮籍对形势的认识也是清醒的。《晋书》本传说:“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19)这里明确说在形势最危急时刻阮籍“屏于田里”,自然就不可能与“缙绅好事之徒”频繁交往。而且从《晋书》的话来看,似乎阮籍就没有赴曹爽的召任。可以说,正始九年前后,天下矛盾一触即发,多数士人都持徘徊观望的态度,视仕途为畏途,在此屏心敛气、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阮籍既不可能有与人争辩的心情,也不可能有与礼法之士驳难的机会。要之,结合《晋书·阮籍传》和其他材料,正始年间的阮籍走的是即仕即隐的道路,因此,是不具备写作《达庄论》的条件和环境的。
但高平陵之变后,阮籍的人生境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被司马懿征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又为司马师从事中郎;司马昭当政后,阮籍曾拜东平相,但“旬日而还”,又为司马昭从事中郎;后求为步兵校尉,直至终老逝世。也就是说,高平陵之变后,阮籍几乎没有离开过官场,而且一直浪迹司马氏之门。正如《晋书》本传所说:“(籍)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20)此处所说的“府”,即司马昭大将军府。阮籍与礼法之士、缙绅之徒的频繁接触主要在司马昭时期,其中,他与礼法之士钟会、何曾的关系颇值得我们注意。
钟会在风云变幻的魏晋之际,扮演了司马氏爪牙的角色。虽然钟会的人生结局令人可哀,但在司马氏剪除异己的过程中,钟会之“功”则是有案可查的。钟会陷害嵇康之事人人皆知,钟会在政治生活中也曾挑衅过阮籍。据《晋书》阮籍本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何曾对阮籍的态度与钟会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激烈严厉。《晋书·何曾传》记载: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可见,在司马昭当政期间,尽管阮籍与司马昭过从甚密,并不时受到司马昭的庇护,但在礼法之士如钟会、何曾等眼中,阮籍始终是被作为异己受排斥挤兑的。
随着“淮南三叛”(21)的平定,天下大势分晓已明,魏晋鼎革只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这时对垒的双方虽还存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但力量悬殊已不可同日而语,曹魏皇室已完全控于司马昭之手,其反抗不过是作困兽斗。所以,司马氏集团要防范的已不是曹魏皇室,而是社会舆论导向和士人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如嵇康、阮籍。因此,司马昭时期的政治策略同乃父、乃兄已大不同,主要采取的是宽容与打压相结合方法。而这一策略的实施,在司马昭霸府里又具体体现在司马昭和礼法之士对名士的不同态度上。可以说,司马昭与钟会、何曾之流在这一策略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果说司马昭对异己名士的异常表现还有一定的容忍和宽容的话,而钟会、何曾等则处处与他们为敌,时时提醒他们自己的处境。在这方面,司马昭与礼法之士之间的配合可谓相当默契。所以,从生存处境看,后期阮籍面对的真正敌人是礼法之士。当然,如果阮籍的言行超越了司马昭的政治容忍限度,司马昭也是不会姑息的。《晋书·阮籍传》就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按即司马昭)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孝的具体体现即是敬父,而阮籍公然倡导杀父,自然同司马氏的政治策略发生了悖逆,因此,阮籍的“失言”才会招致司马昭的厉声呵斥。好在阮籍以机智之语躲过了一次劫难。这说明,司马昭之时,阮籍与礼法之士在司马昭“府”上是经常会面并不时发生舌口之争的。总之,后期的阮籍无时不处在礼法之士的监视和围攻下,阮籍也是在与礼法之士的不断交锋中进行生存突围的。
明白阮籍后期的生存处境,我们就可以知道《达庄论》展现的论辩情景正是后期阮籍真实生存处境的写照。如果不考虑阮籍前后期具体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仅仅依据学术思潮的变迁来推断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很可能陷入只知其“世”而不知其“人”的误解。
三 《达庄论》与魏末政治形势
那么,阮籍《达庄论》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的?背后蕴含着阮籍怎样的生活影像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景元元年前后的政治形势进行梳理和分析。
“魏氏之亡,始于曹爽之诛,而终于齐王之废及高贵乡公之弑”(22)。景元元年在曹魏历史上是继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曹芳事件后又一个悲慨凄惨且荡气回肠的年份。正元元年,司马师废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面对司马氏的淫威和野心,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欲作最后的一拼。甘露五年(260年)五月戊子夜,曹髦“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并发誓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但在此关键时刻,王沈、王业临阵变卦,奔告司马昭。无奈,曹髦亲“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司马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23)。可怜年轻的曹髦就这样死于乱臣贼子之手。《魏氏春秋》说是夜“暴雨雷霆,晦冥”(24)。高贵乡公被杀后,司马昭等奏请太后“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25)。据《汉晋春秋》记载,高贵乡公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26)。六月甲寅,司马昭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改元景元。
少帝曹髦被杀,在当时朝野曾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据《三国志·陈泰传》裴注引干宝《晋纪》记载,事后司马昭征询陈泰如何处理后事,陈泰直对说:“诛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问有没有其他办法,陈泰厉声说:“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甚至晋朝建立后,当时士人提起此事,还常常耿耿于怀。《晋书·庾纯传》记载,贾充与庾纯在一次酒会上发生冲突,庾纯骂贾充“天下汹汹,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汹汹?’纯曰:‘高贵乡公何在?’”又据《世说新语·尤悔》载:“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由此可以想见,高贵乡公被杀在当时及两晋士人心中留下的伤害和深深印痕。而阮籍《达庄论》则作于此年“季秋”,正是高贵乡公尸骨未寒之时,政治动荡甫定之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参照阮籍《首阳山赋》的写作动机和背景,可以肯定,阮籍《达庄论》回应的也正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
高贵乡公被杀之时,阮籍任步兵校尉,正在京师,这一惊心动魄又悲惨的一幕他是亲眼目睹的。而且这一时期也是阮籍与司马昭过从甚密,“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的一段时光。作为当时名士的领军人物,著名的“问题”士人,在如此关乎司马氏人心向背的“时事”面前,司马氏及其党羽钟会、何曾之流不可能不关注阮籍的政治态度和表现。特殊的身份和关系,使阮籍必然成为司马氏集团重要的防范和审查对象;而特殊的事件和影响又使司马氏集团必然顾及和在意当时士人的态度和反应。所以,在这朝野震荡,人心骚动的紧要关口,对于像阮籍这样的名士来说,政治表态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这与稍后不久发生的嵇康、向秀之事颇相类似。嵇康被杀后,向秀被荐举入洛,诚如徐公持先生所说,向秀“此行的实际意义绝非一般性人才荐举,而是强迫他向司马昭当面作出政治表态”(27)。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法了解当时发生的真实情景,但可以想见,风雨过后,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阮籍与礼法之士、“缙绅好事之徒”发生像贾充、庾纯那样的碰头机会应该是极可能的。在这种场合下,自然也会涉及这令人尴尬的话题。但信守“尊卑有分,上下有等”,深恶“弃父子之礼,驰君臣之制”(28)的阮籍,面对如此大逆不道、肆意妄为之事,他又能如何呢!曹芳被废之时,阮籍的精神世界已几近崩溃,“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29)。而今,司马氏又由废君进而弑君,所谓的“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30)的和谐的天地社会秩序已荡然无存,而活跃在他面前的不是道貌岸然、雄心勃勃的野心家,就是“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31),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却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小人。所以,面对司马昭的政治欲望,面对礼法之士的威逼、挤兑,“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32),身处重围又生性至慎的阮籍不可能发出“峻切”的声音,做出什么激烈的动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发言玄远”的方式,来传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对“时事”的看法,又不致被司马氏及其鹰犬爪牙抓住把柄。阮籍《达庄论》就是此高压气氛下不得已的产物。所以,《达庄论》中描绘的“先生”与“缙绅好事之徒”辩难的场景绝不是空穴来风的文学描写,实际是阮籍后期生活危苦处境的艺术化再现,是他与礼法之士正面交锋的曲折隐晦的生活记录。
要之,阮籍《达庄论》真实记录了阮籍特殊时期特殊情境下的内心感受,隐含着阮籍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影像和生平情貌,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
四 《达庄论》寓意的人生态度
关于《达庄论》的思想倾向,王晓毅认为与《大人先生传》的思想大相径庭,“《达庄论》的内容是道家‘先生’与儒家‘缙绅’之间关于《庄子》与儒家思想异同的辩论”,“阮籍在儒道关系上,是强调两者的同一而不是对立。他认为《庄子》与儒家名教之间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儒家探讨的是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庄子研究的是宇宙运动规律,而两者的目的却是相同的”(33)。王晓毅对《达庄论》思想意旨的概括,笔者深表赞同。
不过,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阮籍的“达庄”即崇尚庄学精神的《达庄论》为何要调和儒道?其真实的目的何在?
以往的研究者,认为《达庄论》是阮籍思想崇尚老庄的“转折的标志”,是阮籍玄学思想的代表作。不可否认,阮籍《达庄论》带有鲜明的玄学色彩,但也正如上文已分析的,阮籍《达庄论》同样也具有深刻的现实因素。我们不能因为其充满浓郁的玄学色彩就忽视了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的现实影像。所以,笔者以为,阮籍《达庄论》虽蒙有浓郁的玄学色彩,但未必是一篇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充满浪漫和玄思色彩的生活记录,是阮籍在政治危苦的特殊处境下被逼无奈而作出的带有政治表态性质的思想自白,其现实精神远远大于玄学观念。只有围绕这一写作目的,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和认识阮籍《达庄论》调和儒道的真正用意。质言之,阮籍《达庄论》是采用超以象外的写作方法,来回应特殊政治情势下礼法之士的围攻和责难,以表白自己人生态度,既具有深刻现实性又充满玄学思辨性的一篇文章。
司马氏打的旗号是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的纲常伦理。“人伦有礼,朝廷有法”(34),阮籍对此心知肚明。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35),结果夕阳鸣琴,命归黄泉。阮籍在实际生活中是聪智的,他意识到了自己叛逆的限度,虽然常有悖“礼”的行为,但他“至性过人,与物无伤”(36),虽有违“礼”之行,却无违“法”之实。阮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生活层面而没有触及到政治原则问题。这不仅是司马氏庇护阮籍的原因,也是阮籍得以寿终的“聪明”所在。阮籍《达庄论》的调和儒道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他无奈下的“聪明”选择。
《达庄论》首先是从宇宙意识入手进行讨论的。他认为,宇宙世界作为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首先具有的是“一体”性特征,但同时它又呈现出“殊物”性特征。如土,“平谓之土,积谓之山”,水,“通谓之川,回谓之渊”(37),是“一体”与“殊物”的互存关系,而礼法之士则硬将二者分开看待,结果导致“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所以,在《达庄论》中,阮籍从“万物一体”的宇宙意识的高度对儒道存在形态进行了论述。首先,在宇宙和谐本体层面上强调二者之“一体”性;其次,在世俗观念层面也即从礼法之士的认识层面批判其思维定势的“殊物”性。而这两个层面恰好构成“虚实”“本末”的相辅相成关系,对应的正是他要回答的现实政治时事的两个问题。
首先,阮籍要回答的是对司马昭杀曹髦之事的态度和自己的立场。文中“客曰”的“今庄周”暗指的就是阮籍。所以,阮籍必须对曹髦事件和礼法之士的指责作出正面回应。但阮籍的“聪明”在于他避实就虚,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借调和儒道的话头表明了自己对“时事”的态度,也阐明了自己的人生立场。阮籍认为司马氏以“儒”杀曹髦,自己以“道”行世界,二者虽然表现形态完全不同,但在本体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于此,阮籍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消弭了在礼法之士看来水火不容的两种态度,既巧妙表现了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又申述了自己的人生立场。“客”把阮籍比作今日之“庄周”,而阮籍认为,自己的人生存在方式是“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完全是个体心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同庄子没有关系,“客”把自己“同古”庄周,是“客”心守其成的虚妄指责。这样,阮籍不仅虚应了现实政治敏感问题,回应了礼法之士对自己的指责,而且也辩解了自己人生存在方式的“合法性”和“自然性”。阮籍既承认儒家“分处之教”的合理性存在,又承认道家庄周“致意之辞”的合理性存在,认为他们在最根本上是同一的,实际在说自己的行为与司马氏的行为并不冲突矛盾。应该说,这才是阮籍《达庄论》调和儒道的真正用意和目的所在。由此也可看出,阮籍的“达庄”并不是真正“达”历史上的庄子,而是现实中“形神在我而道德成”的自我,实际是在变相张扬自我的人生信念。阮籍采用调和儒道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政治的棘手问题同向秀借巢许和尧事回答司马昭一样,虽巧妙玄远,都实属无奈之举(38)。而这无奈的回答,不仅表现了阮籍临场的“聪明”,同时也证明了阮籍深厚的玄学素养。
其次,阮籍要对礼法之士的丑恶行径进行痛击。相对而言,阮籍《达庄论》对礼法之士“结徒聚党,辩说相侵”,兴师问罪的描述要比第一层面显豁得多,因为他面对的礼法之士,正是事端的挑起者,是自己现实生活的真正敌人。阮籍对礼法之士的痛击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浪漫气质,文学才华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风格,不仅生动描写了“缙绅”礼法之士“怒目击势而大言”,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得意忘形的丑恶嘴脸,也揭露了他们在阮籍宏言慷慨面前“丧气而惭愧”的卑琐丑态。至此,阮籍《达庄论》以有形含无形,张末而应本的特殊方法化解了自己的一场人生危机,也在对礼法之士的无情揭露中张扬和捍卫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可见,阮籍的《达庄论》实际是“达我”论,是阮籍面对危恶复杂的政治情势,张扬自我个性的宣言。这也许才是阮籍《达庄论》的真实意旨所在。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可概括如下:阮籍《达庄论》作于景元元年司马昭杀曹髦不久的“季秋”时节,其写作的直接原因是面对司马氏的政治重压和礼法之士的围攻责难,不得已对眼前发生的政治事态而作出的政治表态。《达庄论》调和儒道,是现实胁迫下的无奈选择,有其深刻的现实政治背景和指向。阮籍《达庄论》显露了阮籍在政治危恶面前的妥协性,同时,也张扬了阮籍人生选择的坚定性。《达庄论》畅神肆意,挥洒自如的浪漫文字背后,隐含着阮籍大哀无形的痛苦。《达庄论》的现实因素弥补了阮籍研究史料的不足,是研究后期阮籍人生态度的重要文献。
注释:
①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9页。
②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③丁冠之:《阮籍》,见方立天、于首奎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④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
⑤董众:《阮步兵年谱》,《东北丛刊》第三期,1931年沈阳出版。
⑥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3页。略有校改。
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⑧韩传达:《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⑨王晓毅:《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⑩(12)(13)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134、25、47页。
(11)郭光:《阮籍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4)参见拙作:《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5)李兆洛评语,李兆洛编,殷海国、殷海安校点:《骈体文钞》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16)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61页。
(17)《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9页。
(1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553页。
(19)(20)《晋书·阮籍传》,第1360页。
(21)“淮南三叛”指正元元年(254年)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甘露二年(257年)继毌丘俭为镇东大将军的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事。历史上将“毌丘俭、文钦以及诸葛诞在淮南发动的反对司马氏的军事行动”,称为“淮南三叛”。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2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夏侯玄传附许允王经”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23)(26)《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9、110页。
(24)《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第109页。
(25)《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109页。
(27)徐公持:《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
(28)《乐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82页。
(29)《首阳山赋》,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6页。
(30)《乐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79页。
(31)《咏怀诗》其六十七,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77页。
(32)《咏怀诗》其三十三,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12页。
(33)王晓毅:《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34)(35)(36)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9、122、118页。
(37)《达庄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以下引文均据此,不一一标注。
(38)《晋书·向秀传》:“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第1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