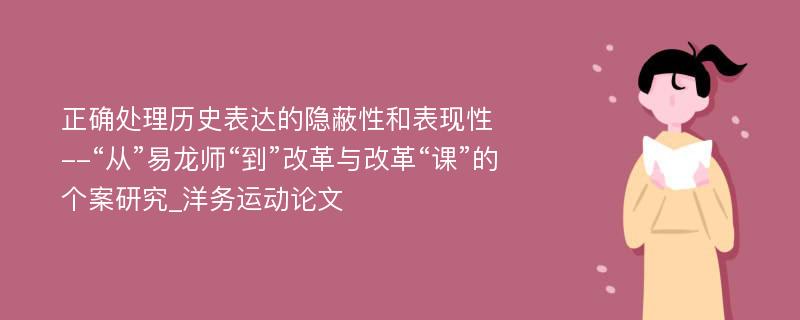
应恰当处理历史表达的隐与显——以人教版“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一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以人论文,恰当论文,一课论文,教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自鸦片战争至维新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潮澎湃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会通异常剧烈,因而人们对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把握往往存在一定的难度。笔者认为,由于受篇幅所限,人教版“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一课的编写,过于言简意赅,这也造成了有些材料在选择与编译过程中存在语义上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本解读是课堂教学的前提。惟其如此,文本表达本身就颇显重要,而文本在表达历史时怎样处理隐与显的关系,就更显重要。 隐与显,或谓隐与秀。古人早就注意到二者关系的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隐秀”专篇论之,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刘勰是在艺术境界高度强调文本表达的,历史教科书不必有那么高要求,但有一点却是值得借鉴的,那就是文本可以、也应该“有秀有隐”,但这“隐秀”关系一定要处理恰当才好,“隐”不是隐没,而是“义生文外”,当需要表达的意义有被隐没之虞,那就要设法用“秀”来显露之。 本文在辨证教科书所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就历史教科书文本表达的隐与显问题谈点粗浅认识,同时对此课文本中被“隐”去的历史做某些“沿隐以至显”的尝试,以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此课内容。 一、“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及其“厄运” “确切”与“严谨”是历史教科书语言的基本特点[1],带着这一认识检视教科书,虽有吹毛求疵之嫌,却毕竟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关于教科书“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表述,笔者更愿意认为这是史学界对林则徐历史地位的一种赞扬与认可。要知道,在一个视了解“夷情”为“以夷变夏”的时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因此,或许在这一表述前,加上“史学界认为”会比较合适。 教科书在表述“开眼看世界”的背景时说:“当英国鸦片走私船开始频繁出没于中国东南海域的时候,清朝君臣只是习惯地称他们为‘岛夷’,对岛夷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这一表达存在语法和语义双重问题。就语法而言,按照教科书的表述,“他们”当指“英国鸦片走私船”,而非英国鸦片商贩,意即“走私船”是“岛夷”,存在混淆主语的语病。就语义而言,其一,究竟是英国鸦片商贩是岛夷,英国人是岛夷,还是笼统地说西方人是岛夷?至少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是有区分的。其二,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岛夷的情况真的“一无所知”吗?有人撰文指出:“鸦片战争前的清廷已经对西方有所了解,这些对西方的认知中往往夹杂着想象、臆测和偏见,而且了解也并不是很多,但也不能以‘一团漆黑’概之。”[3] 教科书在“历史纵横”中称:“林则徐建议朝廷用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炮船,以抵抗英国侵略者。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建议的朱批是:‘无理!可恶!’‘一派胡言’。”以此说明“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事实真的如此吗?经查,林则徐的此次上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底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该折称: “惟其虚骄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贴然俛伏。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 此后朱批:“汝云英夷试其恫吓,是汝亦欲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 “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 此后朱批:“一片胡言。”[4]429-430 从原文可见,“无理!可恶!”与“一片胡言”均非针对林则徐“用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炮船,以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建议而言,奏折中甚至没有正面提及这一建议。原文“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与建议“用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炮船”的意思大相径庭。教科书的表述截取了林则徐奏折的部分语句和道光帝的朱批,似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来新夏先生认为:“道光帝训斥林则徐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抵抗派不敢再有所申辩和争论,从而剥夺了抵抗派对局势的发言权。”[4]430如果联系鸦片战争过程中道光帝的态度和林则徐的遭遇,笔者认为,林则徐遭到训斥的真正原因应当是道光帝已经对其失去信任,他准备以惩戒林则徐来平息战争。问题在于,无论何种解读,这则材料并不足以说明“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这一结论,倒可以认为是林则徐政治生涯“厄运”的开始。 二、“中体西用”与救亡图存 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科书寥寥数语,语焉不详,尤其难以表述清楚发展着的“中体西用”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何谓“中学”、何谓“西学”呢?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6]“中学”姑且笼统地称作“纲常伦理”之学,但“西学”实际上至少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分。历史学科讲求时空观念,就时间观念而言,“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的,“西学”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虽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性思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体西用”思想是超越洋务运动的。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就将“西学”由表及里地概述为五个方面,充分说明了“西学”内涵的丰富以及时人对“西学”认识的渐进过程[7]。大致可以说,“西学”在洋务运动时期侧重于西方自然科学,在戊戌维新时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因此,当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著述《劝学篇》时,“西学”为“西政、西艺、西史”等社会科学。李鸿章在担任江苏巡抚上书总理衙门时,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乃不能及”,强调的是军事技术背后的自然科学。如果不能准确地以唯物史观来揭示“中体西用”思想的变化发展趋势,那就不得不说是某种缺憾了。 教科书行文中还屡有“洋务派”的表述,前文与后文还有“顽固派”的表述。问题是,所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和前文所举琦善等“封建顽固派”与后文所举荣禄等“顽固派”并不是对应关系。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哪怕是同一个人也可能被划分到不同的派别中,因为“有时候会使历史人物本来的复杂多态溢出历史分类后来为他们设定的界域”[8]64。因此,尤须注意教科书表述前后应一致。这或许也可以作为要以变化发展的眼光把握历史的例证。 同时,教科书还称,洋务运动“目的是挽救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但也“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笔者认为,如不应过分强调“洋务派”“顽固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界定一样,评价洋务运动也应该尽量跳出阶级属性的划分,多一些“民族复兴视野”[9]或近代化视野的考量。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纲常伦理”始终是“中学”的核心内容,封建统治是“中体西用”思想或洋务运动赖以生存的土壤,洋务官员更是脱胎于传统伦理法则与君主专制制度,其尽忠职守就是“肯定封建制度”,“挽救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从近代化视野来说,中国近代史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的历史”[10]。自鸦片战争以来,会通中西、救亡图存是无数中国仁人志士的历史使命。“中体西用”思想是心怀天下、洞察时势的知识分子提出并逐渐完善起来的思辨性理论,洋务运动是精干有为的督抚要员实践“中体西用”思想的近代化抉择。因此,洋务运动的目的首先是救亡图存,即挽救被列强欺侮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由此而言,无论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在与列强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还是康梁维新变法,都是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以挽救国家,即通过近代化以救亡图存。当然,近代化和封建统治从本质上是不相融的,近代化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封建统治的崩溃。这个过程,饱含着文人的义理情怀、官场的利益权衡、时局的血泪压迫,很难以成败利钝来简单评价个人是否爱国。有人就认为:“‘从爱国主义走向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中体西用’思想也具有这样的特点。”[11]因此,中肯地说:“李鸿章也是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12]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不能以近代化史观来把握历史,则又是一种缺憾。 总之,如果说君主专制制度是“自私”的总根源,那么,可以用这句话来作为洋务运动的辩证性评价:“这种矛盾和同一,使这些人为私利而助成过近代化,也使这些人为私利而蛀蠹了近代化。”[8]72只是“私利”的理解应当更为宏富。 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外 《新学伪经考》成书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孔子改制考》较为系统的编纂始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问世。这两部著作均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均从经学出发,在理论上奠定了维新变法的基础,影响甚大。然而,教科书叙述仅限于此,则似乎显得不够全面。戊戌维新时期(1895年至1898年)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时期。可以说,在政治实践的推动中,代表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文章与著作还包括“七上皇帝书”、《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和一系列代人草拟的奏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由总理衙门代递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通称《上清帝第六书》。重新补缀的《戊戌奏稿》辑有《应诏统筹全局折》,即指此折。 在这一时期,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更具政治性和实践性。他试图借助西方三权分立和代议制的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做法,全面改革政治制度,倡导“选通才于左右,以备顾问;开制度局于宫中,以筹全局”[13]388。虽然他在语言上进行了不同的描述,但他强调制度局可以“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13]14,是维新变法的领导机构。并建策设立十二局作为执行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康有为在相关论述中也采用“议会”“议院”的表述,在《戊戌奏稿》中更改写为“立宪法”,但“制度局”的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尚有距离。茅海建引用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议郎”的叙述,认为:“康有为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与议会制度还有隔阂,仅形似而未得其真意。”[14]100孔祥吉也认为:“二者均不否定皇权,虽曰取法泰西议院之名称,而毕竟与西方议院不同。”[15]萧公权更直截了当地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立法机构或议会,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机关。”[16]但不能否认的是,尝试引进西方政治思想并开始应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 对此,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的一段文字概括得更为恰当与全面(只是其中的《戊戌奏稿》已经过学者考证大部分存在“作伪”嫌疑):“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以及《戊戌奏稿》;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和其他文章,集中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维新派论变的哲学。”[7]180 此外,在维新变法思想的实践中,教科书在“历史纵横”中选取并编译了一则颇具戏剧性的材料。材料中,“顽固派重臣荣禄气势汹汹地教训康有为说:‘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和康有为“时代变了,祖宗之法非变不可!”等语句生动形象地塑造了“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对立。最终,“荣禄被驳得哑口无言”,表明维新变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不可战胜的。 然而,越具戏剧性的材料往往离历史事实越远。这则材料出自何处?历史上真的有这场争论吗?荣禄真的被驳得哑口无言吗?经查,这则材料源自康有为《我史》(习称《康南海自编年谱》)。根据《我史》记载[17]: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总理衙门总办来书,告初三日三下钟王大臣约见。至时李中堂鸿章、翁中堂同龢、荣中堂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相见于西花厅,待以宾礼,问变法之宜。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至昏乃散,荣禄先行。 可见,原文并无“荣禄被驳得哑口无言”的语句或意思,此语当属主观臆断。原文确有这场争论的记载。那么,是否说明历史上确有这场争论呢?《我史》系当事人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1月)流亡日本时所撰。大胆假设,如果说康有为流亡海外,基于扩大政治宣传的目的,回忆一年前的这件曾经是康有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心情激动,言语夸饰,也是符合情理的。实际上,茅海建在《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推论,认为:“康说似可以怀疑。此时康尚未大用,正谋求前程,即便与荣禄意见不一,也未必当面露出锋芒……荣处世为人甚精密,似不会去主动攻康,提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命题,更何况荣本人还是此期军事变革的倡导者。”[14]291-292由此可见,这一戏剧性的争论也未必属实,且很有可能是当事人夸饰或作伪的。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用于历史教学的材料亦当忠于事实、小心抉择。 综上所述,为“隐”去的历史“补白”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有助于历史教学工作者弥补因史观或视角不同而造成的缺憾之“白”,因史料加工而造成的语义误解之“白”,因语言简练而造成的表述不全面之“白”。历史观念决定了历史材料的选取,而历史材料离不开历史语言的表述,这一过程均需要始终坚持“确切”“严谨”的学科特点与要求。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的境地,无论隐,抑或显,都服务于表达真实历史的需要,恢复历史本有的生命力。标签:洋务运动论文; 康有为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清朝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孔子改制考论文; 林则徐论文; 中体西用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中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