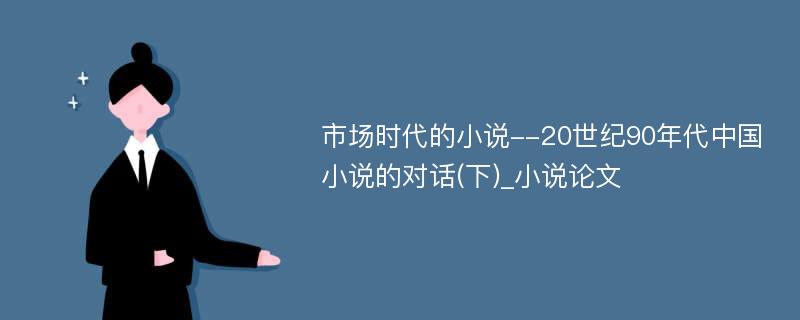
市场时代的小说——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对话(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时代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性趣盎然的写作
荒林:我还想谈谈90年代的性话语。当然这不只是现代才有的话题,而是自古以来便有的。离开物质不可以谈人,离开性其实也不可以谈人。简单说来我们就是由性创造的人,所以离开性不能谈论我们的问题,性在今天是前所未有地浮现出来。就像物质成为商品一样。九十年代的小说写作中,性的姿态比八十年代不知要突出多少。在八十年代,性以爱的包装,爱的寓言的形式来呈现,然后由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是政治关系、理想关系。在九十年代性就是性,它不是别的东西。所以说关于性的关系的探讨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它包括了哪几方面呢?男女两性之间性的较量,同性之间性的可能性,还有包括物质的性的探讨。我并不说立场问题,只说性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言说姿态,关于性的探讨的复杂性已经到了无所遮拦的层面。比如男女之间、同性之间、性和物质之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一种空间的生长。这是一种触觉的展开。过去当然也谈论性的,但是不是以性的形式,比如说以爱情、以理想的形式,以政治的形式来言说,它是一种压抑的形式,而现在是一种敞开的形式,比如说《蝴蝶的尖叫》,是写一个女孩子跟一个有妇之夫的爱情关系,就在夫妻合影照下面那个女孩子跟那个有妇之夫发生性关系。这种场面只有在九十年代小说中才会如此凸现出来。因为,这个女孩子不会觉得那里面有什么道德,有什么伦理,也有什么家庭存在。她没有这种观念。因为性就成了第一位的。作家之所以如此地表述性,是因为性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语话。这个女孩之所以跟那个人发生性关系,它里面就代表物质的意图,而性在今天成为交换的意图的表述,在无数的小说中得到体现。比如林白很早时写的小说,写一个女孩赴幽会,她之所以跟那个男人约会,仅仅是为得到一张房产住房证。还有比如我的朋友在国外写的留学生小说,一个女人之所以要跟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就是为了出国留学,为了得一个学位等等。性的较量就如争夺一个商品,就用这个形式呈现。虽然张爱玲时代性也被作为一种较量,但是还比较含蓄,最终她会转到《倾城之恋》这样,可能还会产生爱情,但是在90年代的性关系的叙述中,很可能不懂得爱情,它仅仅就是性,性就成了交换的商品,所以我觉得九十年代小说如果不谈到性的关系的这种呈现,也是不全面的。我觉得女性小说的先锋性就从这儿呈现出来。它揭露了性的关系只不过是物质关系,一种交换关系,一种权力关系,与爱情未必有多少关系。上海批评家陈惠芬一篇评论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她认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能够在物质关系中游刃。女性主义作家并不是解构爱情,而是要解构性的关系,说性就是一种政治,也就是一种物质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谈陈染,比如她的《私人生活》,前面她跟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后面她跟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它就是一种性的较量,在性的较量里,她没有体验到一定是爱情或者是什么,因为爱某种程序上和这种性的关系发生一种分离。
郑国庆:我觉得性它如果是跟商品、跟社会联系起来,最终还是引向了社会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说通过它能够真正地去探讨灵与肉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如果你一直探讨下去,那我倒觉得有可能会拓出一条新路出来的。
王光明:那么你说的这种性描写,跟《肉蒲团》、《金瓶梅》,有什么不同?
荒林: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应该承认它们是市民阶层意识的反映。
南帆: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一些异议,其实文学跟性的关系比你说的要复杂。包括《肉蒲团》、《金瓶梅》,这种作品有很多主题范畴,中国的性有同房中术的关系,跟以往的禁欲的关系。二三十年代以来性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与革命的关系,茅盾的多篇小说里,一边非常革命,另一边性关系是非常混乱的,这里有一个倾向就是性的能量跟革命的能量是一致的,然而,奇怪的是革命后来又跟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
孙绍振:先是革命加恋爱,但有了革命后就不能恋爱。赵树理的作品出来后,革命就取消了爱情,到了五十年代,就是奖章加爱情,如著名的《天山牧歌》,为什么爱上你?因为你有个劳动奖章。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就变成与革命迭在一起,就是林道静的道路,如果这个人有了问题,那就跟他决裂,所以革命压倒一切,是这么一个脉络。那么到了样板戏阶段,就没有爱情,没有性,所以《红灯记》里边家里都是没有亲人的、李玉和没有老婆,李奶奶没有丈夫,李铁梅没有父亲,没对象,江水英没有老公,韩英也没老公。
南帆:我想弄清楚的问题是,革命和性之间如何由同构呼应关系转向排斥关系的。
孙绍振:它是异构的、冲突的。革命的时候追求社会解放,恋爱的时候追求个性解放。
南帆:我想到的是,革命发生之初,需要冲劲,与解放、个性同属一个利比多,但革命进入纵深后,这些东西恰好成了阻碍了,包括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妨碍了革命的透明性,因此总想把它拿掉。
孙绍振:对,郭小川的叙事诗《深深的山谷》写的就是这个过程,一对革命恋人从上海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女的很快融入了延安的集体生活,而男的对集体生活感到非常不适,于是两人感情发生分裂,男的就从山谷上跳下来自杀了,这就是革命和恋爱的冲突,因为恋爱是个人的,革命是民族的,恋爱是渺小,革命是伟大的。集体的实用价值取消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两性描写在新时期不过是重新恢复而已。到了八十年代,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成了一个主题,人成了一个主题,性饥饿在《绿化树》中就有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如《早安朋友》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是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我们可以跟苏联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相比,我们比起来是比较严酷的,我们到了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老婆的程度,苏联还没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革命和恋爱冲突了以后,人家怎么处理的?
荒林: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作家的素质。
孙绍振:还有整个民族的素质问题,国家的一种机制问题,我们民族传统的力量不足以抗衡这种国家话语或革命要求、现实要求,也许是我们民族的解放要求特别高的缘故。虽然我们的文艺政策来自苏联的体制,可我们加进去的东西比苏联严酷,加上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本来就现代意识不足,所以不足以抗衡,个人的情感空间、生活空间就给取消掉了。苏联的爱情描写不像我们取消得那么彻底,赵树理的方向已开始认同这种彻底,到了浩然的《艳阳天》已比较完整,爱情跟社会的关系,跟社会价值的关系、法律的关系,完全是一致的,西方不是这样的,俄国首先不是这样,我们不但看到了像肖霍洛夫这样的作品,阿·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是这样。还是有个人空间的。苏联解冻以后就不用讲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经典作品,也是拥护合作化,可是人家写性不是这样写的,达维道夫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爱上了集体农庄主席拉波洛夫的老婆,然而这个女人却不爱达维道夫,她爱上了富农的儿子,一个反革命。另一个真正喜欢达维道夫的女孩子,达维道夫却一点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就很糟糕,你去看赵树理,你去看《艳阳天》,没有这样的人性的东西,没什么“性”的感觉。我们是完全《西游记》的传统,或者是《水浒传》的传统,是没有“性”的,都是武松那样的英雄,看见女人是不动声色的,没有利比多的,这是非常悲哀的。
荒林:你的这些比较道出中国文学中性政治的严酷程度,中国这种性别体制对于人的压迫主要是通过这种性的压抑来实现的,所以说中国文学是缺乏这样一种性自由的传统,所以说中国作家必须经过一场性政治的革命才行。你说到从张贤亮开始,性的解放是个人解放开始,但张贤亮同样是把性活语当作一次大叙事来言说的,他把他的女主人公象征为土地啊、绿化树呵,其实还是集体的男性意识形态,根本没有个人的存在,爱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因此依然是中国文学话语中的一种性话语,一种大叙事,所以这之后有王安忆《叔叔的故事》,来解构张贤亮这种性话语。叔叔所遇到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一次性的艳遇,而这个艳遇中,这个叔叔是极其性无能的,就说他根本都没有真正的人性的觉醒和性的觉醒。
王光明:90年代的确有一些小说文本是性趣盎然的,但将性话语、性自由视为个人觉醒、解放和现代性的标志,却值得我们认真检讨。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性话题被广泛谈论意味着什么?那些小说家是怎样谈论性的?是否真的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和美学的视野?关于第一点,我认为福柯的《性史》值得注意,他在回答性话题为什么被广泛谈论这个问题时,追溯了“不合法”的性如何被迁谪进妓院和精神病院的过程。他注意到,只有当性欲即弗洛伊德所言的利比多被压抑时,才会有性欲自由的要求,性欲才被作为代表解放的参数。就是说,一旦性被打入冷宫,那么仅仅因为谈到这一点,就给谈论者染上越轨的色彩,具有反叛和颠覆意味。但福科同时又看到,从不许谈论性到性被广泛谈论,从性压抑到性自由,并不意味一种由压抑到自由的社会改变,而是表现为权力通过性的关注而运作,可以让人看到明显的社会权力架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认为,性不过是权力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权力架构的一个影子,这一点我们甚至用不着深奥的理论,从电视播放的大量“成功人士”的广告中,就可以看到,性是如何同汽车、别墅、手提电话一起塑造了今天的市场意识形态。因此,需要在政治权力、时代风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关系中观察性话语的生产与消费,在九十年代中国,性话语与理想、颓废、政治、经济等话语复杂纠缠在一起。作为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与忘却作出反应的一种特殊话语方式,处于历史的道德排拒与人性向往的张力场中,这种话语既可用来进行文化批判,也很容易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总是有办法把各种不同的声音纳入自己的系统,性话语同样可以成为他们庞大市场促销的一种手段。这样,面对90年代小说的性话语,值得关注的,不是性被带进了公共话语空间,而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想象性、描写性。当我们从不准谈性,或像韩侍桁批评茅盾《子夜》简单地把性派给资产阶级,到可以在文学公共空间合法地谈论性之后,性话语是否就是“现代性”标志,是否就是个性、自由、解放的指标?是否可以将当代小说对性描写的回避归结为缺少性自由的传统,甚至认为提高中国作家的素质,得经过一场性革命才行。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怎么谈论性与否就像谈论女性主义和种族一样,成了政治上正确不正确的指标。显然,这里存在着以西方现代观念作背景的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想象,这些言说者心目中首先有一个“想象的读者群”,这些中国读者生活在“前现代”社会,是“落后”、“保守”、“素质”上有问题的,因而需要“启蒙”、“解放”,以使他们摆脱“传统”,获得“自由”,实现“现代化”。事实上,进行这种言说的大多是些自我感觉良好,把社会革命和艺术想象混为一谈的新潮一族,他们把谈论、描写性作为“开放”和优越文化阶层的标记,其中不少似是而非的性言说,既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又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当然,也有一些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性话语是女性主体建构一条通道,比如林白、陈染的“成长小说”就把性经历作为女性主体成长的必修课。然而,无论是把性作为符码,想象男性暴刀对女性身体、青春资源的掠夺的作品也好,或是兑换其它东西的货币也好,都很容易陷入某种迷思。以性来建构主体比较典型,并被个别女性主义批评家激赏的文本,一个是台湾女作家李元贞的《爱情私语》,一是北京女作家陈染的《私人生活》,这两个女作家一个共同的之处是,都强调身体的主权,并把性的自由支配作为自由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前者把自我与性等同,认为性的觉醒就是女性主体意识和权力的觉醒,而一旦获得这种权力,并有足够的性知识和性技巧,就不但有生命的快乐,而且能通过征服男人去征服世界。后者有一个情节曾被女性主义批评一再诠释发挥,女主角在一间仓库里诱导一个大学生进入了自己的身体,这次性的主动出击,不仅使她摆脱了性的被虐心理,而且由于那个大学生正受通辑,她还获得了献身于某种事业的自豪感,因为在他流亡异域之前,她让他记住了她的身体。像这样的女性主体性建构,究竟建立的是真正的女性主体,还是从西方早期女权主义中“借来的主体”?哪怕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也是落入了男性意识形态的陷阱。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要写性,相反,正如本雅明所说,身体、性欲从来就是构思社会问题和文化想象的宝贝清单,性欲,甚至色情,不仅可以利用来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潜质,关键是你怎样写它。就我读到的小说而言,我还是比较欣赏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玫瑰门》那样的写法,她们所写的性,既有历史的具体性,又处在比较真实的两性关系中,既从美学的立场僭越了陈旧的道德规范,又不回避男女欲望追逐中胜负难辨的灰色地带。
四、从“大说”走向“小说”
黄洪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走向了市场经济,而思想文化界则在激情受挫以后走向了保守主义,包括创作和学术都是如此,文学创新的势头整个跌落下来,最明显的是先锋的转向,这批作家已经没有了前卫的锐气,也不再热心于技巧的试验。许多作家都与市场经济妥协了、和解了,尽管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如新生AI写作城市生活与人的关系,呈现出“欲拒还迎”的姿态;陕军东征则表现出明显的商业炒作倾向,更不用说“布老虎丛书”了,尽管罗织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无论题材、写法、发行都是商业规则运作的。九十年代小说没有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没有过去那种激情、理想,关注的都是身边的凡人小事,它好像失去了大气,缺乏大的历史关怀和伦理关怀。
王光明:洪旺说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我不想从道德、历史的角度去谈它,更愿意从小说本身的特点去谈它。这就是为什么开头我说九十年代小说老让我想起晚清民初小说的原因。在给研究生上课时我们讨论过“small narrative”和“grand narrative”。黄子平则提出晚清小说有一个从“小说”走向“大说”的过程。中国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是身份卑微的,处于历史话语秩序的边缘,然而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又拼命挤向中心,要承担“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大使命,甚至抱有“补正史之遗”的野心。因此,到了严复和梁启超,靠着社会转型的背景,小说被抬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承担起了“新一国之民、新一国之政治”的重大使命,直至鲁迅把它当作“改造国民灵魂”的工具。在晚清文学中,小说写作的语境受制于两种表面矛盾而内在相通的因素:一是基于民族落后对发展的深重忧虑,这是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精神,一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商业利益的驱动,这两者都参与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社会政治关怀与商业利益共同推动了小说生产与消费的新型态。政治要求利用并改造了文学大传统中的教育功能,因此有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社会小说”或“谴责小说”的热闹,以峻急的调子和深重的忧郁描写社会的病痛,秉承《儒林外史》,以“天下第一伤心人”的心情写社会的腐败(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或表达政治幻想(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是由“小说”到“大说”的转变。而在社会改良的幻想受挫和沦为一套陈词滥调后,又从启蒙心态走向了言情和通俗,将社会和人生的失意与幻想寄之于勾栏,于是有市井言情小说的勃兴并产生了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小说继承的是宋元明以来中国小说的小传统,可说是从“大说”回归“小说”。这个世纪中国的小说,主流文学一直在追求“大说”,但“小说”也未曾中断。进入90年代后、小说似乎已收回了“大说”的野心,更认同“小说”的路数,退向边缘作游戏状,有意无意地调侃、戏谑“大说”的虚妄。
南帆:“小说”与“大说”的问题,我觉得很值得谈一谈,但是我不太赞成这个事情发生在晚清。我觉得我们中国目前的小说有两种源头。在西方的小说,早先有一个史学的传统,荷马史诗的传统,长篇是最经典的小说。在瓦特《小说的兴起》里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原先《荷马史诗》基本是叙述一种历史现状,到后来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后如《鲁宾逊漂流记》等要叙述的是个人的事情,这时候从思想看恰好是个人主义的崛起。个人的崛起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一个人又是什么关系?于是后来探讨个人跟普遍的关系,包括典型理论等等。这是西方小说史上的一个转换。在中国小说史上也一样有一个史传的传统,但应该说它更多是本于《史记》这个传统。我们认为以前没有史诗,所以叙事文学不太成熟,但史传这个传统到晚清小说中间有很多话本。从史传的传统转向叙事个人人情的传统并不是发生在晚清,早就有了,比如说《金瓶梅》的出现,小说史上称之为人情小说,已经进入了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像梁启超当时提出那种观点,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王光明:我插一句。小说本身其实都是站在个人的边缘的立场,它本身并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为什么站在历史的边缘,我认为写作者是从边缘观看历史,并不承担主流历史的叙述功能。然而晚清恰恰出现了这种倾向,就使小说变成了大说。
南帆:对。晚清把小说变成了大说是另一个问题,包括梁启超提出的那个观点,它赋予小说很高的价值,但是梁启超这个观念,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的,是他从西方看到小说有这么大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如此。
王光明:这就是承担政治功能了。包括鲁迅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改造国民灵魂的传统。
南帆:对。但是从小说史线索下来还是很复杂的,包括梁启超本人欣赏的小说跟他所谈论的小说似乎又不一样,这是我看到的海外一篇论文里谈到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证过我也不大清楚。但梁启超当时无疑是把小说甚至把整个文学提升到了社会改制的高度。
王光明:强化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功能。
南帆:我想说以前的史传文学是回溯历史,后来把它改造为政治想象,强调的是政治功能。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说九十年代以后,在很多小说里面,既不像古代史传小说那样阐述一段历史,包括阐述历史的愿望,像《红旗谱》、《创业史》,九十年代小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批人是没有这个愿望的,他们的小说阐述的是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刚才荒林所说的两种倾向我认为是存在的,第一是人与物质的关系,尽管被孙老师挑剔了一下,但它确是90年代小说所处理的问题。另一个是人跟性话语的关系,包括性关系与性话语,也是90年代小说的新倾向。这些都与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无关。
王光明:小说走向“大说”的深层动力是晚清那批志士仁人社会变革的激情,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病痛的深切关怀,但是作为审美想象的小说是否承担得起这么重大的时代历史使命?我们看到的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随着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小说一下从社会解构和政治乌托邦想象的云端跌进了勾栏酒肆,从社会战场转向到情场的想象,变得风流香艳、感伤颓废。九十年代小说启蒙主义激情的消退,它的平庸、琐碎、性趣盎然能否与晚清民初的小说构成比较?它是否也有一个从“大说”走向“小说”的过程?无论如何,文学是随着电视剧《渴望》、王朔的小说,汪国真的通俗诗进入90年代的,那时虽然也出版了张承志的《心灵史》这样有血性和激情的作品,其中对弱势边民与“公家”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表述,但它来自一种宗教信仰的激情,而我们看到得更多的,是《一地鸡毛》那样描述平凡人生的小说大量出现。这些小说让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即使始终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即反映色彩比较强的小说,也只在一些表面形态上保留了过去的东西,而诸如典型、环境等原则,就变得难以坚持。现实主义方法的叙述立场,现实主义的坚信和叙事态度等已变得非常混乱,《废都》、《白鹿原》,这样一些所谓现实主义小说,思想上、写法上都与过去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废都》是揭示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被世纪末所废,只能在与许许多多的女人的交往中寻求暂时的安宁,让人想到晚清的狎邪小说,是颓废的。对于《白鹿原》我很欣赏南帆讲的一句,“思想的混乱又带来了叙事的混乱”,我觉得在家族争斗和儒家思想之间,作家无法平衡,找到统一的叙述观点。还有大量的现实主义小说,包括现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对当代文坛构成了冲击,还是被现在的社会语境所冲击?也许不是它冲击了现在的许许多多的小说,而是现实主义在种种的冲击面前变得没有叙述的信仰、叙述信心,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叙述观点。包括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看了以后我特别不舒服,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神话,他认为个人都是无所谓的。如同孙老师80年代批判的“大我”是重要的,“小我”是不重要的理论,“小我”甚至应该连受法律保护的权力也放弃,忍受强暴,仅仅是强暴者会办养殖场,有钱,这分享的是谁家的艰难?不是在纵恶吗?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叙述观点,连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不管《白鹿原》也好,还是《大厂》《分享艰难》也好,虽也描写一些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但是在叙述观点和叙述立场上他们是非常混乱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也缺乏统一的叙述观点,缺乏叙事信心,所以面对这一切,包括荒林谈的物质性和性描写的热情,是否可以说“大说”正在瓦解、隐退,而“小说”正在浮出,正由过去关心国家、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走向更关心个人或个人领域生活的想象?它带着市场经济时代物质性的光泽,性的香艳,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以及《废都》式空几十字的策略和《白鹿原》式“主人公一出场就干倒七个女人”的噱头,宣告了后现代叙事风格的降临。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同是由“大说”走向“小说”,九十年代小说与晚清小说又是不同的,晚清是解构社会的叙事,90年代小说则在现代语境中连主体性也解构了。小说本来是一种文化想象,追求文化价值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语境,变成了“为什么要那么好,难道不能次一些”的自我质疑,这种价值质疑包括体现在写作态度上,普遍的不愿在文本形式、结构、语言上下功夫,因为不相信永恒的价值,也就干脆放弃了永恒的追求。九十年代小说确确实实没有什么经典,价值虚无与写作心态的浮躁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90年代的小说,可以解读我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但这样一些现象也是需要反思的。当小说变成“大说”,国家意识形态的叙述变成一种体制时候,没有好小说,一旦这些东西真正流入一种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没有自己的叙事观点和价值坚信的时候,能不能出现好小说呢?刚才国庆提到小说中有虚无情绪,那么,当虚无也变得体制化的时候,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商品,同样被资本主义市场收容整编了?
孙绍振:对小说从“大说”到“小说”的转变,我同意光明这个想法。如果说小说里追求绝对小的“小说”,是不是就一定是好事?小说走向某种程度的“大说”,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我曾经认真读过光明的《艰难的指向》,追求一种个人话语,我当时比较怀疑,因为绝对的个人话语可能比较困难,个人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关系很复杂,我们吃了国家话语的亏以后,是绝对走向个人话语,还是寻求一种调和?我觉得不仅仅是小说,还包括诗歌,诗歌现在被我骂了一顿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王光明:我的意思既不是重回“大说”,也不是寻求两者的调和。从根本上看,小说从“大说”回到“小说”,是回到它本身的位置,是好事,因为它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强加的重负卸下了,回到了它个人的、边缘的、审美想象的本性上。对于90年代小说,我忧虑的问题是,回到“小说”,回到个人后,须要有坚实的生命和美学的价值感支撑,以虚无解构历史的庞然大物是不能奏效的,价值真空像权力真空一样可怕,小说毕竟是以语言和想象来探寻文化价值的,在市场也成为垄断、化约一切“大说”的时候,小说将怎样以自己的价值与它展开对话?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金瓶梅论文; 废都论文; 梁启超论文; 王光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