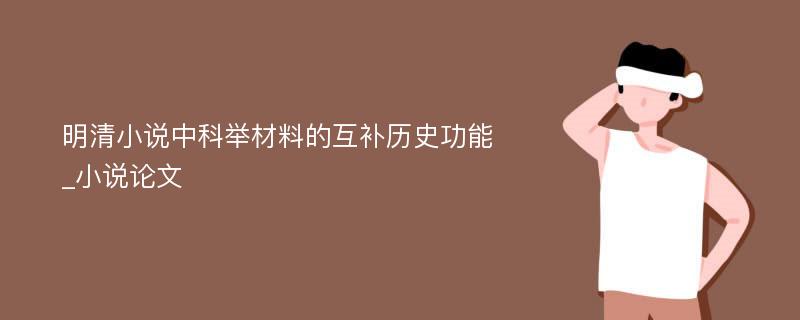
明清小说所含科举资料的补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明清论文,所含论文,作用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0)12-0155-03
科举文献记载的明清科举制度,无论如何完备都有局限之处。其局限表现在制度化、原则化和机械化等特点上,它不像文人小说和笔记,对历时两个朝代的科举制度的细节要求、执行情况、前后变化,对科举考试中出现的偶然事件,以及与规制不符的特例,作出虽然不成系统却更近事实的描述。总览明清时期的科举文献与小说,在系统性上,科举文献远远优于小说,在具体性和生动性上,小说又远胜于科举文献。从众多的明清小说中还可以发现正史偶有遗漏的科举资料,这些内容正是小说作为科举资料储备的可贵之处。
一、科举文献的制度化与小说的具体化
正史中的明清科举文献首先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如《明会典》《皇明贡举考》《明史·选举志》《清史稿·选举志》《钦定科场条例》《续增科场条例》等,诸种文献均是如此,它们由史官编撰,必须按一定的体例和要求记录相关制度和规定。然而,明清小说中的科举资料与之不同,其中涉及的科举制度不需要像正史一样用陈述的方式来条列,它用小说家的语言来表现,小说作者可以对他们感兴趣的方面加以细致描述。相比之下,小说中所写的科举制度更加具体化。
正史记载的明清科举文献以客观记述为主。《钦定科场条例》之类的史料将科举制度分条陈列,每项规定以交待清楚为宗旨,它们没有必要,也不能加以更多的描写和修饰。因此,这些正统史料文献简洁明了,同时具有强烈的制度化特征。如《钦定大清会典》中对科考进场有载:“是日,应试者由贡院东西门鱼贯序进,听唱名、搜检、入大门、给卷,各归号舍。试日,五鼓内簾出题纸。”[1]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的考前进场,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环节,进场对于应试举子来说,不仅需要的时间长,而且准备的事情也很多,他们要于子时就早早地在贡院前等待点名、领签进场,之后经历重重严格的搜检,接续下来的给卷、归号都各有规定。仅就搜检一项而言,其严格的程度和具体情形,从科举文献中无从得知。
明清小说涉及这一内容时,与科举文献有着天壤之别,进场的各项进程都可以成为小说的题材,其中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有具体描写。仍就搜检而言,小说中的描述详备之至。《儿女英雄传》中借安公子的所见写道:
公子因见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才待放下考篮,忽听那老头儿说道:“罢了。不必解衣裳了。(举场东门外砖门)这道门的搜检不过是奉行功令的一桩事,到了贡院门还得搜检一次呢。”……顺天府五城青衣,都揎拳捋袖的在那里搜检。被搜检的那些士子也有解开衣裳敞胸露怀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满身上混掏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当,他就提着那条卖估衣的嗓子,高喊一声“搜过”,便催快走。那班士子一个个掩着衣襟,挽着褡包,背上行李,挎上考篮,那只手还得攥上那根照入签,再加上烟荷包、烟袋,这才迈着那大高的门槛儿进去,看着实在受累之至。公子有些心怯。[2]
明清科举的搜检,历史文献中有所提及,至于搜检官的粗暴和举子们的苦楚却仅仅一笔带过而已,对具体情形的详细描绘就要借助于小说。乡会试的搜检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在点名、领签之后的“砖门”处,《续红楼梦新编》也曾提到:“(芝哥儿)拿根签就到搜检砖门边来。”[3]“砖门”在举场的东门外,是最外一层的搜检,第二层搜检才是在贡院门口。两次搜检的严格程度不同,第一次较为宽松,并不仔细翻查,搜检官吏不过应付了事。第二次就不同了,搜检官吏“揎拳捋袖”、高声呵斥,与市井粗俗之人无异,搜检全不顾及读书人的体面,使得应试举子备受辱没,应接不暇。举子们表现为另一番情态,他们“掩着衣襟”、“挽着搭包”,不仅苦不堪言,甚至令读书人对此十分心怯。将小说与历史文献对比,孰详孰简,一目了然,小说中的记述比历史文献中制度化、程式化的记载要具体,为我们了解明清科举的实行情况也提供了一个参考。
科举文献对乡会试的时间、场规有明确载录,从入场到出场都有相关的条例,但是对于举子们在规定的时间和制度内,如何进行考试,在考场中怎么度过,时间充裕还是紧张等诸多问题,则较少涉及。小说作者从应试举子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详述。《儿女英雄传》写安公子应乡试首场时道:
看了看墙上挂的那个表,已经丑正了,便要水擦了擦脸,又叫那号军熬了粥。才待收拾完毕,号口边值号的委员早已喊接题纸。少时,那号军便给他送了一张来。……才得辰刻,头篇文章合那首诗早已告成,便催着号军给煮好了饭,胡乱吃了一碗。天生的世家公子哥儿,会拿甜饽饽解饿!又吃了些杏仁干粮油糕之类,也就饱了。便把第二三篇作起来,只在日偏西些都得了,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看天气尚早,便吃过晚饭,上起卷子来。他的那笔小楷又写的飞快,不曾继烛,添注涂改,点句勾股都已完毕,连草都补齐了。点起灯来,自己又低低的吟哦了一遍,随即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卷袋里。闲暇无事,……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那个老号军便帮他来把东西归着清楚,交卷领签,赶头排便出了场。[4]
从小说中可以了解举子们在乡试首场中的具体情形。应试举子为了对时间有所把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带表进场。经过点名、搜检、找号舍和安顿之后,已经是丑正时分,即凌晨2点,此时稍加洗漱,交待号军准备些饭食,略吃些东西,待收拾完毕,盖已近寅时,即凌晨3点,此时题纸发下,开始答题,因天色尚暗,故有“灯下一看”之举。这一阶段是进入号舍到正式答题之前的过程。小说中的安公子平时习业颇精,对举业较为熟悉,至辰时,即上午10点左右,头篇八股文和诗题均已写好,此时又由号军准备早饭,再吃些自带的甜点,之后继续写作第二、三篇八股文;在“日偏西些”,约傍晚时分,试题就已做好,再吃过晚饭,将草稿誊写至试卷上,加以涂改、点句、分股,天色未黑,便已将首场试题全部答完,这一阶段是举子的答题过程。安公子写好试卷后便无他事,睡到天明,次早交卷领签,头排出场,这是第三个阶段,对于答题较快者来说,要做的事情只是等待出场。
从上段叙述,可以对举子在考场中的饮食起居和相关制度大体了解。如号军不仅防止作弊的情况,还要负责举子的饭食,对他们提供帮助。就考试时间来看,虽然考试时间是三天,其实满算起来只有两天,第一天只是子时开始点名进场,进场后算起已是第二天了。举业精熟者考试题目一天即可完成,时间比较充裕,第三天一早便可交卷出场,实际在考场的时间只有一天多。当然,小说叙写清代之事,从考试内容上来看,应是乾隆四十七年之后,所以我们只能就此了解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然而从安公子的答题时间来看,却可以理解明朝初定乡会试仅考一天的原因,虽然时间紧迫,但对有准备的考生而言,一天足够答完试题。
明清小说涉及的此类科举制度可以信手拈来,它们的可贵之处绝不仅仅在于描述的具体性上。科举文献记载的很多简括的条令性制度不容易明白和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明清小说作者以其亲身经历,用最详细也最贴近现实的笔墨,将这些规制详细述说出来,很多时候会成为我们理解科举制度的重要途径。
二、科举文献的机械化与小说的生动化
明清科举文献的第二个特征是机械化。科举文献的记载简省、明晰,一般在形式上比较拘泥且无变化,显得呆板、不灵活。科举文献的可信度最高,但是作为制度的条陈,不能让人了解到明清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的现实情况。这一点小说与之迥异,小说家善于描摹物态,对于他们熟知的科举制度,更能够在其笔下发挥得游刃有余,从而使科举资料的机械记载,变成小说中的生动描述。
科举文献的机械化与小说的生动化是二者的不同记述方式使然。史官的责任是记载,小说家的任务是创作;史官的记载讲求秉笔直书,小说家的创作注重形象生动。基于这两点不同,科举文献与小说在涉及科举制度时,也相应的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我们对明清科举制度的了解,大多是从科举文献中所得,科举考试的时间、内容、场规以及中式后的各项事宜,科举文献都有程式化的记载,确凿地记录了相关规制。我们从科举文献中看到的明清科举,都属制度介绍一类,转观明清小说,它却是当时科举制度的生动再现。
如科考阅卷要求严格,一般科举文献多记录从房考、副主考到主考,一级一级的评阅过程,重在指明阅卷的程序和相关规定,至于如何评阅、因何取中,不会加以说明。明清小说作者把科举阅卷的过程搬入作品中,经过一番加工摹绘,不但使考官的阅卷程序一目了然,对去取的原则和其中备卷的作用也有详解。《儿女英雄传》中描述:
(娄主政)重新把安公子那本卷子加起圈来,重新加了批语,打了荐条。……主考接过来,不看文章,先看了看是本汉军旗卷,便道:“这卷不消讲了,汉军卷子已经取中得满了额了。”那娄主政见不中他那本卷子,那里肯依?便再三力争,不肯下堂。把三位主考磨得没法了,大主考方公说道:“既如此,这本只得算个备卷罢。”说着,提起笔来在卷面上写了“备中”两个字。……[5]
这段话重点叙述了科举的阅卷过程和取中的“备卷”。科举考试分十八房,每房的房考先阅本房试卷,在试卷中加上圈点和批语,将取中的写上“荐”字,荐至副主考和主考处,副主考和主考再从中挑选较好者分别写上“取”和“中”字,试卷才真正被取中。小说中的娄主政是因为在交上荐卷之后,重新审阅安公子的试卷,故此加个“荐条”,每科取中的名额有限,考官往往在取中定额后,不再接纳其他的试卷,因此,出现了娄主政极力推荐的情节。由于房考强烈推荐,主考被“磨得没法”,方得在试卷上写一个“备”字,作为定额外的“备”卷之用。这一荐卷过程反映了考官因为取中定额的限制,不一定将全部举子的试卷一一评阅,录取额满后,对于好的试卷也不再取中,这正是科举阅卷环节的不公正之处。娄主政的荐卷与之相反,他不想遗落人才,故此“再三力争,不肯下堂”,安公子的试卷才被批为“备卷”,虽然不是正式取中,但总算还有中式的机会。后面写到填榜时,第一名因为诗题没押官韵,考官们又不想依次改动上面的名次,故“向这备卷中对天暗卜一卷”,可见,取中者的试卷出现了问题,备卷中便有人可以得到入选的机会,不致名落孙山。作者不但详述了试卷的去取过程,还揭示了科举能否取中与考官的关系,尤其娄主政极力荐卷一幕,除小说之外,科举文献是不会载录的。
小说对科举内容表现的生动之处,更在于它可以将严肃、刻板的科举制度,以饶有趣味的笔墨描绘出来。仍就上述“备卷”来说,作者对备卷作一番解释之后,还引用譬喻,以结胎、弄璋、弄瓦、半产来形容科举中各种类型的试卷。“他把房官荐卷比作‘结胎’;主考取中比作‘弄璋’;中了副榜比作‘弄瓦’;到了留作备卷,到头来依然不中,便比作个‘半产’。”[6]房考荐卷之后还需主考评阅,有待时日,故称“结胎”;弄璋与弄瓦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璋指圭璧,臣之职,后引申生男为“弄璋”;瓦指纺砖,后引申生女为“弄瓦”;备卷终未选中的则称作“半产”。依此比喻评阅的各类试卷倒也符合人们的心理,十分贴切。小说作者在前面对备卷解释之后,再加此譬喻,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将本来自己“先原也不懂”的抽象的规制,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类似的描写在《女开科传》中也有:“由此推之,则分明以棘院为场圃,以士子为谷种,以分房为此疆彼界,以阅卷为耕耘锄植。翰林金马诸公,都是些荷锄负畚,与耕牛为伍的农夫田畯。到后来的拜认师生,银壶金爵,无非是芳塘绿亩之遗弃滞穗。”[7]岐山左臣将科举比作农耕,从贡院、分房,到举子、考官,都一一与农耕关联起来,不但比喻别致,而且将严肃的科举以这样游戏口吻写出,也表明作者对科举的鄙薄态度。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将秀才入闱比作七似: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他将举子入闱、搜检到出场、未中等一系列情形作了巧妙的比喻,刻画入里,对举子的心理变化有所揭示,对科场的唱名、归号诸项也有描摹。将抽象的规则和制度化为形象的描述,既符合科举的历史真实,又使人容易理解科举文献中的记载,小说的功用正体现于此。
三、科举文献的普遍化与小说的个别化
明清科举文献中史料的第三个特征是普遍化。科举文献记载的科举制度必定是常规性的,具有可以实施的普遍性。历时两朝的科举制度,拥有庞大的应试群体,实行过程中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难免遇到特殊的情况,正史对这些特殊情况的载录并不全面。这些在科举中发生过的特例,很多都可以散见于各类文人笔记和文学作品,明清小说中当然也不乏这类个别化的科举资料。
明清科举本身在很多方面都有特殊的个案发生,如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致使考试日期变更;科举三场的考试内容偶有变换;举子在考试答卷时将五经试题全部写出,本应按违式处理,却仍有得以中式的特例。这些方面科举文献有载,小说中也有叙述,如《五色石》中写:“光阴荏苒,看看过了八月场期,各直省都放过乡榜,只有陕西因贡院被火焚烧,重新建造,改期十月中乡试,其他各处试卷,俱陆续解到礼部。”[8]乡试因为贡院火灾而推迟场期,史实上也曾发生。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统计,其中因火灾、水患均有过乡试改期之例,虽然小说中的叙述不能与科举文献所记的某一次进行核对,但此类事件确实存在过,这表明小说中出现的个别化案例并不是虚构。
这些方面从科举文献中还可略见,更多的情况是科举文献未曾记载或仅仅略有迹象的,有关明清科考官吏的任派即如此。按科举制度的规定,考官是由朝廷选任具有科名、官职或一定学识者,但是从小说中我们得知,在现实的科举考试中还曾存在非朝廷官员,没有学问之人,甚至宦官充任考官的情况。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述:“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初五日入闱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继之,带了家人王富,同到公堂(试院的正堂,应是至公堂)伺候。行礼已毕,便随着继之入了内帘。”其中作者没有官职,不是朝廷官员,虽然通晓文理,按照科举制度规定也不能于考场内任职,而他之所以得以进入内帘担任考官,并帮助批阅试卷,是由于与继之关系密切,受继之的请托。更有宦官主试之例,《鼓掌绝尘》中记:“这魏太监一个个考选过,毕竟是生员比监生通得些。”这里的“考选”是指科举而言,由宦官主持科举未免太过戏谑,小说所述看似夸张,实际上,查找文人笔记,在明代后期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宦官参与科举考试并且掌握中式与否的权利,此事确实不虚。
与科举文献的普遍化特征比较,小说资料的个别化尤显鲜明,其原因之一是小说家对常规性的事情并不乐于记述。他们的创作讲究新奇,而科举作为文人喜欢谈及的话题,发生在制度之外的情形更能得到小说家们的青睐,并且他们笔下的人物凭借常规之外的方式得以荣身,如采用五经中式、录遗选取等,也是众多科举失利的小说作者们所希望和幻想的。更重要的是,明清小说对科举制度中特殊情况的记述,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科举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式。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明清小说中涉及的很多科举内容,确实起到了补足正史之阙的作用,其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10-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