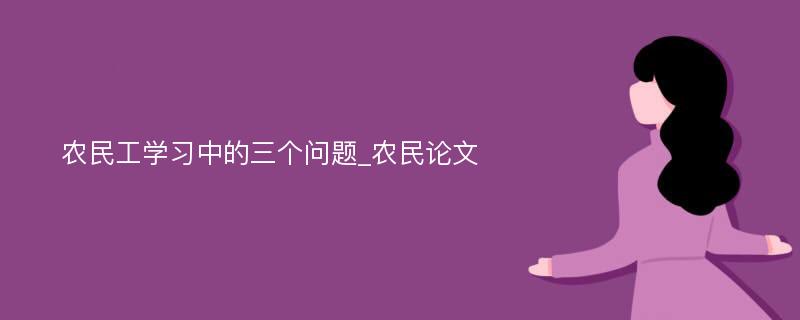
农民工问题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04)08-0053-03
一、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是市场经济“铁律”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很大,但人多地少,属于世界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改革前,受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束缚,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沉淀”在土地上,农业低效,农村贫困。改革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使土地上隐性的过剩劳动力迅速显现,同时农民有了择业的自由,通过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或者是“离土离乡”到城市打工谋生。然而,不稳定的就业和低收入迫使大量进城农民工回流,或者滞留在城市但不得其用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直是全社会沉重的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跃跃欲试”,引人关注。
很多人赞同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从人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城乡居民应当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笔者对此并不反对。但是,一些人可能暗含“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怜悯”,因为农民工的境遇实在是太苦太苦。一些反对的人则认为工资应当遵循市场经济“铁律”,如果农民工太多以致于“无限供给”,市场经济的法则必然是供过于求要素的价格(工资)低落。因此,本文要申明和讨论两个观点,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一个保护农民,但实际上也同时保护城市的制度,因为不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也将受害;工资决定的市场经济规律包含最低收入保障,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并非无视“历史和道德的因素”。
第一,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1954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首创二元结构分析(他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指出,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存在“二元经济”,先进但弱小的现代工业部门与庞大但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改变这种二元结构,扩张现代工业部门,而传统农业部门则可以为此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并因转移剩余劳动力而获得效率。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经济和管理体制,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城乡二元格局被强化了,农业低效,农村贫困,而城市则因为农产品供给匮乏而陷入萧条。这就是城乡二元格局的实质。由此可见,给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以最低收入保障,促使数量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推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改变,它不仅对农民有利,因为可以提高农业的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也对城市有利,因为城市可以获得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第二,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否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他们的工资怎样决定?正是开创二元结构分析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由于农业中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所谓“零值劳动力”,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这种生存收入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界限。后来,另外两名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其称为“不变制度工资”。刘易斯认为,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的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会完全等同于农村的生存收入,而会比后者稍高一些,他估计约高30%左右。这是因为,第一,城市生活费用比农村高,需要支付较高的水电、房租和交通费用;第二,农业劳动者习惯于乡村的散漫和自由,应该有一部分收入用于弥补他们迁入城市后置身于高节奏的“心理成本”;第三,为了引诱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还必须有一部分额外的净收入作为刺激;最后,城市工业部门工会的力量也有可能使工资水平上升,但刘易斯又说,即使没有工会,工农业收入的差别仍然是存在的。
其实,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在130多年前分析资本主义工资时已经指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它包含三个部分:劳动者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所必需的学习和训练费用。马克思特别指出,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不同,工资决定包含着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即要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或者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这注解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何存在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但是,尽管如此,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劳动者维持自身及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从而其工资水平也是可以大致确定的。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历改革以来20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农民工最低收入保障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难道还嫌早了吗?
二、城乡统筹培育大容量就业载体
据有关权威研究,改革20多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量约1.5-2亿,但其中有较稳定就业机会和收入的仅仅约占一半。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约5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已由改革初期的70%下降到50%,但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需要转移。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改变过去的转移定式,站在国民经济的高度,城乡统筹,培育大容量的就业载体。
第一,改善城市结构和城市功能。城市化是城乡统筹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机制。一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是生产力在空间转移和聚集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化提供规模和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奉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和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模式,这虽有历史合理性,暴露日甚的弊端是小工业、小城镇“遍地开花”,割断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城市化严重滞后,延缓了农村和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落后不仅表现在城市分散和规模小,还表现在城市的层级结构不合理,缺少相互联系。由于大、中、小城市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应当形成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的多元化城市体系。调整城市功能结构的多元化城市建设将营造大容量的就业载体,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第二,乡镇企业的结构优化。相当一段时期,乡镇企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然而,近10年来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90年代末甚至出现负增长。今后,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必须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特别地,一是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农业产值不到80%,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4倍。二是优化乡镇企业的布局。乡镇企业的布局改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要与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连片集中,通过聚集效应拓展就业空间。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门槛低,容量大,是大规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优化农业资源利用结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我国正在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农业资源的利用结构,可以拓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调整农业结构应与发挥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我国土地资源短缺,大量耗费土地的农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应当大力发展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以劳动置换土地。
第四,加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力度。从客观需要和主观能力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我国必须加大水利、交通、通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此举可以达到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多赢”局面。
第五,境外转移。应当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拓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国外转移的渠道。
需要指出,城乡统筹培育大容量的就业载体,只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大容量的就业载体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仅是数量的,而且尤其是质量的。这需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农村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育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
三、走出外来工身份城市化的误区
从2003年11月起,深圳市对原不属于特区的宝安和龙岗两个区进行城市化改造,将原属于农村集体的土地收归国有,原农村集体财产改变为股份制经济,27万本地村民转为深圳城市居民。一旦宝安和龙岗城市化改造完成,深圳将成为全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宝安和龙岗的城市化改造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宝安和龙岗两个区有450万外来工,他们在数量上是本地人的好多倍,他们应该搭上城市化的车也转变为深圳城市户口,把外来工排斥在外不能够真正实现城市化。简言之,外来工“进城”是城市化的关键(注:谢孝国、宋毅、何书彬:《深圳农村城市化进程再思考》,《羊城晚报》2003年11月20日,21日)。
我认为,此言差矣,差在不明白城市化的真谛。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是生产力由农村向城市在空间转移和聚集的结果。同时,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规模和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工业化发展。就像广义的工业化意味发展和现代化,广义的城市化也是经济和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变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地域不断扩大,农村地域不断缩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商业劳动者,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实质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是城市化的真谛。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横亘着一个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与户籍制度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由于存在着这个差别,农村人口难以城市化,外来工难以本土化。所以,改革城乡分割、地区歧视的户籍制度,一直是人们强烈的呼声。但是,最艰难的改变就是利益的改变,户籍制度的改革说了一、二十年,“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没有什么重大进展。这说明,必须换一种思维,改革应当逐渐淡化并最终消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从而使户口失去意义。换言之,只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了,农村人口就真正转变为城市人口。到那时,有没有城市户口,并不重要。就像我国城市居民曾经使用的粮本,当市场上到处都能够买到比国家粮店更好、也不昂贵的口粮时,粮本就失去了意义。
主张外来工城市化的错误就在于,它还“陷”在“身份城市化”的认识误区里,它看重的正是现存的城乡、地区利益差别,它善良却是幼稚地希望将其一笔勾销或是一视同仁。殊不知,这是现阶段根本做不到的。明知一件事做不到,却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个事情上来,岂不是作茧自缚,自扰?说得直白一点,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有点像一个国家的国籍,你拥有这个国家的国籍,你就拥有该国赋予本国国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并不妨碍外国人来此地工作和生活。外国人在此工作和生活虽不享受该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也受该国法律的保护。每个国家对外国人加入本国国籍都有严格的审批制度,但不妨碍在此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照样可以安居乐业。任何比喻的说明都是有限的,这个比喻可能还“残酷”了一点。但是,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没有条件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背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时,城市化的策略是不要把思路定格在身份城市化上。恰恰相反,应当淡化与身份连在一起的城乡、地区利益差别,使身份失去实质性的意义。城市化应当使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也能在本地安居乐业。至于他们是否要本地化,前提是他们自愿,并有能力,而不是赋予他们本地城市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