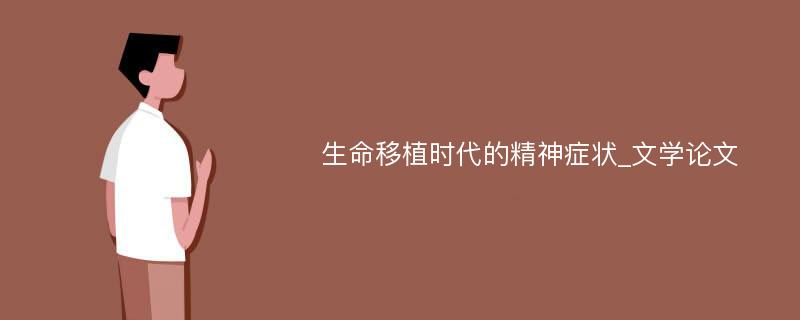
生命移植的时代精神症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症候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一光2009年从武汉移居到深圳,成为这座移民城市的移民作家。移民的根在原居地,不在移居地。移居地是经济社会之地,而不是感情和心灵的所在。作家往往会把故乡看作创作的主要灵感、生活基地、地缘和血缘的纽带。然而,邓一光来到深圳后,在创作上并没有回望故乡,而是把创作的源泉锁定在了这座移居地,与他早期的创作是楚河汉界。当然,邓一光会说,“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好作家总在颠覆前经验,包括个人的写作经验,改变是作家的常态”,①“‘原乡’情结不是作家独有的,优秀的作家会走出‘原乡’情结,而不是依赖它,从而建设一个独特的,同时又属于全人类的精神家园。”② 在短短几年的移民时间里,他创作出了和深圳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的17部短篇小说和1部中篇小说,构成了“深圳系列小说”,这里密密麻麻写满了深圳。光从小说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到深圳的角角落落,“红树林”、“市民中心”、“梧桐山”、“万象城”、“龙华”、“罗湖”、“仙湖”、“北环路”、“前海”、“莲花山”、“关外”、“梅林”、“杨梅坑”、“欢乐谷”、“欢乐海岸”,这些都是深圳的真实地名,也是深圳人最熟悉的地方。当然,并不是写此类深圳地标才是深圳文学,关键是深圳这座城市在作家心里及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呈现出独特的都市经验和精神气质。从小说的人物形象上看,也是包罗各个阶层和各色人等,有在底层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有高学历的博士、硕士,有大龄的剩男、剩女,有没钱买房的人,有工作压力过大的人,有过年回不去老家的人,等等。他们都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移民,他们是“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全部神经,因此是惊人的敏感”③,这时的邓一光仿佛从作家变成了一位医生,邓一光的笔,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游走于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培的生命个体,理性而智慧地解剖着因为移植而带来的根与土壤冲突的痛苦的躯体。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书写的是这座移民城市中被移植后的生命的时代精神症候。 一 “你不是深圳人” 深圳是座口号之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口号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为中国大众广为熟知。还有另外一句口号,叫做“来了,就是深圳人”,但并不是那样耳熟能详。实际上,“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是一种呼喊,一种荣耀,是一种精神,一种激励。可是在邓一光的笔下,却很煞风景地告诉你,“你不是深圳人”。是的,从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为了寻梦而移居深圳的人,他们到底是哪里人?深圳诗人一回的诗《你是哪里人》也许给予了最好的诠释: 明天,我要到广州去 广州人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我是深圳人 深圳人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我是湖北人 在湖北,湖北人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我是赤壁人 以前叫蒲圻 赤壁人又问我 你是哪里人 在别人眼里 我仿佛是一个永远无家可归的人 只有回到家里 家里人不再问我 你是哪里人 当移居到一座新的城市时,却发现这里并不是心灵的归所,故乡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远方,而自己却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这样的心情,鲁迅在《在酒楼上》早有提到,“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故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鲁迅生动地写出了移民矛盾与无奈的心情。“而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诗人田地的诗歌把这种矛盾与无奈更加放大。 在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中,“你不是深圳人”屡屡被提到。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出现了男孩这样的诉说,“如果可能,我会放弃做一个人。我是说,不是吸烟的人,也不是深圳人,是人——如果我能做一枚砗螺,或者一丛三角藻的话。”在这里,似乎是男孩宁可成为砗螺、三角藻,也不肯成为深圳人。而实际上,男孩不是不想成为深圳人,不是对深圳的不认同,而是无法被深圳认同,故事情节中已经有了交代,“深圳的房子太贵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办二代身份证,可这太难了,”,“谁也没有两个身份”。男孩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不是深圳人,因为他没有深圳的身份证,而故乡也是回不去了的故乡,漂泊感与悬浮感油然而生。身份证,象征着一个人身份归属的证明,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物质的属性,而是一种精神属性,这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一个是你是否认同这个身份,另一个是你是否被文化身份所认同。 “你不是深圳人”在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又被高调地提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这一观念在作家的心中由来已久,所以会不时地闪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好像是作家的无意识,但它是作家思考已久,却终将无解的问题。小说中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作为博士的他和作为硕士的她终于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的地方租住了房子,她为此而狂喜,甚至“眼圈红了,哽咽着说不出话。”因为市民中心就是市政府,习惯中一律叫政府大院,是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深圳的CBD,是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大客厅。用她的话说,这里才是“高贵的深圳”。住进去之后,她每天都沉浸在这种“高贵的”喜悦之中,甚至想到市民大厅里办一场隆重的婚礼。可是她发现工作在市民广场的保洁工一次也没走进过市民大厅,在她的一再追问下,“为什么一次也没有走进市民大厅,因为那里是深圳市民的大厅啊”,保洁工说出了掷地有声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像保洁工这样居住在深圳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不是深圳人,他们的故乡也回不去了。那么,他们到底是哪里人。回答是,他们是移民。移民才是他们最真实的身份。什么是移民?“移民,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的移植。移植的痛苦首先来自于根与土壤的冲突。在新的土壤中,敏感的根才会全然裸露。与此同时,在时空的切换中,根的自然伸展也必然对新鲜的土壤进行吐故纳新。”④这里就涉及到了移民文学的问题,邓一光作为移民作家,他的深圳系列小说,都可以归为移民文学的类型,可以在移民文学的范畴里进行讨论。 移民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寻找身份的焦虑。前故乡身份在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或者已经褪去了昔日的光环,或者比前身份更加黯淡无光。因为移民就意味着前身份被打散了,须要重新聚拢来,形成一个新的身份。重新的聚拢需要更多时间的磨砺,新身份的确立须要经历更多的坎坷与煎熬。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太多的可能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就提出了寻找文化身份与认同危机的问题。那么,在移民城市的人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的文化身份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移民浪潮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不仅仅单纯是“你不是深圳人”的问题,而是“你不是纽约人”,“你不是巴黎人”,“你不是东京人”,“你不是伦敦人”等等的全球化的问题。所以,对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不能不参照国际文化的背景与框架,对于关于深圳文学创作的关注,就不能仅仅限定在深圳这个地方区域内,对于身份的定位自然应该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那么,《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的男孩、《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的保洁工的身份问题,就不仅仅是他们一个人的问题,恐怕对于身份的寻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人需要的是归属,他须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自己属于哪个族群,只有明确这个问题,心灵才不会流浪,身心才会彻底能安顿下来,才会获得马斯洛的人的心理需求中的最高层次的安全感。然而,这又的确是无法立即得出答案的问题,也许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 在现代性的悖论中,谁也无法阻止人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的大型迁移,这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问题。那么,如何在这过程中,去缓解寻找身份的焦虑,也许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可以从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一些端倪。如果把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整个看做一个大的文本的话,那么,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唯一的一个中篇《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成为浮躁而慌乱的漂泊生活中最为温情而有亮色的部分,这也是这部作品的极为精彩之处。它对如何缓解焦虑这个问题,给出了紧绷的神经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答案。小说这样写: 一个14岁的女生,她有一个因为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的路上的父亲,一个总是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是的,她该怎么办?这个倒霉的移民孩子。且慢,邓一光给她了一个暂时的特殊身份,她是百合合唱团的成员,不仅如此,她还在国际比赛中作为合唱团的指挥获得了大奖,因此与势不两立的父母产生了和解。这是这个作品中最为温暖的地方,使得所有的焦虑有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当然,哪怕这是暂时的,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二 “今夜深圳无眠” 深圳也许最应该书写的,是它的夜晚。不是因为它的五光十色,也不是因为它的灯红酒绿。这是因为,“今夜深圳无眠”。无眠的深圳折射出了太多现代性的问题。这也是作家邓一光的不厌其烦地书写无眠的深圳的一个偏爱,他的质疑精神、批判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构成了深圳系列小说的核心。在小说《深圳在北纬22°27′~22°52′》、《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抱抱那些爱你的人》、《要橘子还是梅林》等中都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甚至反复出现了深圳无眠的描写。 《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的没有深圳身份证的男孩、《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的走不进市民大厅的保洁工以及《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的在重重生活重压下的14岁女生兰小柯,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底层,也许你会问,《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的男博士与女硕士因为他们的高学历,是这座城市的中上层,应该在这座城市里完成了他们的身份确认并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了吧?否。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之间有互文和佐证的效果,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你可以找到《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的男博士和女硕士的影子,他们在这里变成了男监理工程师与女瑜伽教练,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可以说,《深圳在北纬22°27′~22°52′》是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中最为优秀和精致的一篇。就如同他所说的一样,“好的小说,一定能经得住三方面的追问,是否具有发人深思和有别于社会主流历史观的个人生命经验;对现实尽可能超越的程度;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⑤这三方面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现,短短的一部短篇小说,承载了非常重的分量。 《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监理工程师,工作压力非常大,他时常在夜里醒来,作品中有多处这样醒来的描写,例如,“最近他老是在半夜里醒来。有时候是凌晨。如果不想什么,大多时候他可以接着睡,到早上再醒”。“他安顿她重新睡下,为她盖好被单,关上床头灯。她很快睡着了……” “他没有睡,完全清醒了,睡不着了”,类似的描写,比比皆是。在极短的篇幅中,反复出现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叠章复唱的修辞格,起到反复渲染与加深重点的作用。而实际上,作家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失眠背后的东西,失眠只是一种表征。为什么会失眠,这应该已经不是一个生命个体的睡眠障碍的问题,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时代与城市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我们都是时代与历史的产物,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只能徒劳无功地在命运中自我挣扎。 《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是一部很有趣的小说,因为它之中有一点小小的悬疑色彩在里面,故事角色中只有他与她,她在梧桐山下租了一套民居,是个幽静的度假村,他急急忙忙赶到她那里,与她共同生活了四天,这四天,他们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亲昵接触,一次也没有。故事交代的是他们做不到,想做,但做不到。随着故事的结束,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对已经离了婚的夫妻,女人就要住到山顶上的豪宅里,而男人,并没有遵照女人的要求,告诉他们的孩子,妈妈已经死了的谎言,这是一个很简短的小故事。但是,故事中令人瞩目的对话是这样的: “昨晚熬夜了?”她问。 “没熬。睡了五个钟头。”他老实承认,“没睡着。想今天睡。” “还失眠?”她问。 “好些了。”他说,“大多时候睡不着。” “眼圈都是黑的。”她说,“你瘦了。” “他们都这么说。”他说。 类似的描写在《要橘子还是梅林》中也可以看到:“刚搬到梅林那几天,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夜里睡不着,连续好几天没去单位上班。人力资源部一个家伙给我打电话,让我看看《劳动合同法》的有关条文”。这里的“我”是一名雇员,专门负责接受网络售假投诉的工作,这当然是一项很好的工作,并且他们局的LOGO都是由两颗心组成,代表关爱民生,与消费者心连心,但是这项有爱心的工作也不能治愈“我”的失眠症,相反,“我的失眠症明显加重了,两点到四五点那段时间,我会非常兴奋,老有一种冲动,想学着某种动物的样子引颈长啸。我知道这样不好,可就是忍不住。” 相对于因为失眠的煎熬几乎想变成动物不同的是,《抱抱那些爱你的人》中的“我”对于失眠是另一种淡漠或者说是百无聊赖的反应:“我睡不着,起身去冲凉。我想象自己淋了一场没来由的大雨,关上龙头,水立刻没有了。我再打开龙头,再关上。”“我”的另外一次失眠的描写也是同样无聊,“我睡不着,心里惦记着什么。我悄无声息地从床上起来,去了淋浴房。我在那里研究了一会儿花洒,又玩了一阵浴盐,然后离开淋浴房,去了户外。” 对于失眠的描写,作家在每一个人物上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他们在睡不着的时候,或者百无聊赖,或者想变成一个动物。无论是怎么样的表现,都是生命个体的煎熬。失眠是一种现代病,是一种自我无法控制,依靠药物和心理干预得以缓解的现代病,有轻与重不同的症状,严重时还可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并诱发一些心身性疾病。这也许就是移民与社会转型之于我们的意义。 睡眠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要橘子还是梅林》、《抱抱那些爱你的人》中角色的一种奢望,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烦恼,但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监理工程师当然他也有睡着的时候,可是睡着甚至比睡不着更令人烦恼,因为睡着时全是梦,而且梦境很逼真,梦的内容也很清晰,梦到自己是一匹马,一匹“黑色皮毛四蹄雪白的马”,“他兴奋地奔跑着,快速超过几头慌里慌张的灰毛猞猁,一群目中无人的野骆驼和一队傲慢的丹顶鹤”,“他就是一匹马,撒着欢,无拘无束。”不仅如此,透过监理工程师的眼睛,我们获悉,虽然睡在他身边的做瑜伽教练的女友是睡着了,没有失眠,但是她却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她在热带雨林里快乐地飞翔,没想到遭遇上劈头盖脸的雨。”更有甚者,监理工程师白天坐在车里看到了穿过马路的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但他看到的不是头发蓬松的男孩,而是一只展开双翅掠地而过的稻田苇莺”。他变成了马,女友变成了蝴蝶,男孩变成了苇莺。从人到动物,之间有多远的距离?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作家独特的想象力,可以认为他把这部小说刻画成了一部精致的艺术品。可是,这只是表层。真正深刻的东西是从人到动物,这其中难道仅仅是睡眠不足的恍惚吗?否。这是一种人的异化。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有许许多多有待于剖析:“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主体并没有直接变成另外一种生物,它可以说是《变形记》的前史:因为还差那么一点点,变形就没有彻底地发生……区别在于,卡夫卡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来展示其对现代性的彻底绝望,而邓一光,还没有绝望到这个程度,因为在现代性的展开之际,对于深圳——同时也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呈现出了更多重的面孔:既有创造的力量,也有异化的悲剧;既有一切消失的恐慌,也有再造一切的激动;既有旧的主体的迷惘、失措和逃避,同时又有新主体的新生、成长和对世界的渴望。”⑥ 是的,邓一光笔下的人变成生物只是在梦境中或者视觉中,而卡夫卡笔下的人真正地变成了动物。其实在深圳系列小说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佐证,邓一光这种多面的呈现也可以看到,即“既有创造的力量,也有异化的悲剧”。一方面他失望与无奈,一方面他又充满了信心,这是一种最真实的表达:例如,在《出梅林关》中,作家直接站出来讲,“高速经济社会让所有的人都变得疯狂,要治愈这个疯狂得花掉两代人的代价吧”,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在《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他却这样说,“海风小了一些。我点着了香烟,看咫尺外磷火辉煌的巨蟒。我知道我身在的这座城市,它在奋起直追,可能有希望成为另一条巨蟒,我被这样的念头鼓舞着,一时心花怒放。”可以看出来,在深圳海边看到的巨蟒,显然指的是香港。他对移民城市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希望。 三 “我没有朋友” 身份无法确认的漂泊感以及人被异化的痛苦,是移民城市的症候,它的另一个症候是孤独。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痛苦。在深圳的漂泊者,当初为了追求自由与梦想,“脚底生风”般地逃离令他们“厌倦”的故乡,到深圳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实现他们的梦想。然而,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这些对独立个体的追求欲望反而使他们堕入了孤独的深渊。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了人类从史前时期开始就已经有孤独感了。他分析了现代人孤独感的来源:自由一方面给现代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另一方面又使现代人陷入了孤独。人或许能忍受诸如饥饿或者压迫等各种痛苦,但却很难忍受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孤独,是一种难以被他人理解、接受或认同的感觉,是在虚无与痛苦中一种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孤独已经由来已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孤独,但是移民城市里的孤独,无疑更应该是雪上加霜。 在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的写作中,孤独被书写得是那么令人触目惊心:“我并不认识她,她是陌生人,我也是,是她的陌生人。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须要杀出一条血路才能彼此认识,并且为自己建立起一座全新的城市。”这是小说《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中“我”对孤独的体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多么遥远和艰难,须要去“杀出一条血路”,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认识,暂时摆脱片刻的孤独。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设计在酒吧里,主人公“我”从监狱里出来,女友把“我”抛弃了,只有朋友侯夕照来接我,为了排遣“我”的孤独,侯夕照把“我”带到了酒吧。场景的设计非常合适,因为酒吧里充满了孤独与寂寞,有许许多多孤独的人为了摆脱孤独来到这里,希望与人建立起联系,然而,结果是他们收获的是更多的孤独。在酒吧里,“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目光迷茫,落落寡欢,“我”看见有两个男人过去搭讪,但都遭到了姑娘的拒绝。于是“我”端着酒杯走过去,“我”与姑娘开始了交谈,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同时也就结束了。因为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络,孤独的人还继续孤独着。这是一篇简短的小说,但是整个故事里弥漫的气氛是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一种孤独。仿佛空气里、酒杯里都是满满的孤独,谁也无法挣脱,同时谁也无法走近对方。 分析在都市里产生孤独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孤独源自社会价值观的断裂。在传统社会中,一切价值观都是有序的,善与恶的标准也是清晰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价值观却是无序、暧昧与断裂的,为了逃避这种不确定性,结果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隔阂,孤独由此产生,在这座移民城市里,这种对立与隔阂只能更甚。 《北环路空无一人》对孤独的书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写了人的孤独,还写了狗的孤独。主人公“我”有一个朋友,叫个色,因为他的女朋友失踪了,他要去寻找,但是他还养了一条狗,叫皮卡,他必须把皮卡托付给“我”照顾三四天,这引起了“我”的极大不快,但又无法拒绝,所以在与皮卡相处的这几天里,故事就发生了。因为“我”是一个孤独久了的人,根本无法和另外一个生命体同在一个空间里相处,哪怕它是一只狗,所以“我”给狗做了很多限制,总之,“我”是极其排斥这条狗的。因为狗侵占了“我”的空间,所以“我”开始“憎恨”起狗的主人来。这里有一段关于孤独的描写:“皮卡不是科学家,它的主人已经废了。那个叫个色的家伙,他根本没有什么女朋友。他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他就从来没有女朋友。他只是在不断寻找想象中的某个人。在灯火辉煌的深圳,他连觉都不敢睡,不敢在屋里睡,只能把被子抱到阳台上,在那里抱着被子的一角悄悄哭泣,然后爬起来,回屋里喝一杯水,再去四处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人。他就像一粒空壳的谷粒,白生长在金黄色的稻田里了。”这段描写令人泪流满面。实际上,个色根本不是去找什么朋友,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朋友,他只是一个说辞,与他相依为命的只有一条狗,人与狗都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他孤独地抱着被子角哭泣,这里的书写非常有力量。那么狗离开了主人怎么样呢,也有一段关于孤独的描写,同样是非常震撼心灵,“天黑之后,月亮升起来。我来到窗前,朝楼下看。我看到了皮卡。它在裙楼的中央草地上,就它一个……偌大的草地上只有它。它站在那里,仰着脑袋,一动不动地看着天空中的那轮月亮。月光如洒,看不清它有多么肮脏,它就像一尊雕塑,只是一尊雕塑。”这只寄人篱下的狗,实际是一个隐喻,暗指人。狗与他的主人一样,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他们彼此失去,又彼此分开。邓一光采用了隐晦,虚构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曲折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突出和放大了人的孤独。 关于孤独主题的书写,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毕生钟情于孤独的主体,他有意无意把自己的孤独的感觉倾注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在拉丁美洲,孤独意味着落后、原始与孤立无援。马尔克斯所要做的,是想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帮助拉美人民摆脱沉重的民族孤独意识,走向新生。孤独有许多种,《百年孤独》中的生存的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爱情的孤独,《族长的没落》中的权力的孤独,无论是哪种孤独,马尔克斯都是批判的态度,这是一种从反面写爱的方式。爱,就意味着沟通和交流、理解和信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同情与悲悯,只有爱才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真正正面回答,只有爱才能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才能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才能满足人内心最强烈的共同追求。实际上,马尔克斯的这种批判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邓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也有体现。 如果直接写爱的方式,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反过来写孤独,那么它的力量的巨大的,可以震撼心灵。这是一种反其道而为之的方法。被邓一光运用起来可谓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比如说他在小说《你可以看见前海的灯光》中写道:“我能说什么?深圳根本就没有朋友这种东西。但我不能这么说。我不能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说出来,那会让很多人不高兴。”深圳没有朋友,对于许多移民来说,都会产生共鸣。这种孤独不仅仅表现在没有朋友这么简单上,这座移民城市仿佛是一座丛林,必须遵守的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包括在爱情上也是如此。《一直走到莲花山》写的是大龄女孩相亲的故事,相亲的地点是莲花山。可是,“女孩在男人的丛林中一路磕磕碰碰走来,碰得自伤自恋,至今仍是孤芳一株,咎由自取”,女孩在经历了无数的相亲失败后,仍旧是孤家寡人。但是她还是不肯放弃,一直向莲花山走去。 在现代的移民都市里,没有身份也罢,无眠异化也罢,孤独难耐也罢,这是现代性的多样面孔,这是移民城市的时代精神症候。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通道、缓解症状、向着健康的方向进发,缓解是一个关键词。缓解也是一个医学术语。有些疾病是不能完全治愈的,只能缓解病情。移民文学中的伤痛是无法根治的,只能得到暂时的缓解,这是它的宿命。挥之不去的伤感美,成就了移民文学独特的美学特征。萨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精彩的阐释,“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既然症候不能得到根治,那么,这时候也许只有选择逃离。但是逃离到哪里去呢?已经无法回到最初的原点,因为人生是不可逆的,只有向前走。 ①《深圳还给文坛一个新的邓一光》,《深圳晚报》,2012年10月24日。 ②《邓一光:作家关注的是无所不在的可能性》,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2/11/04/007515105.shtml。 ③严歌苓:《论严歌苓的海外小说》,载《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宁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 ④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⑤《邓一光:好小说一定经得住追问》,《深圳商报》,2011年9月21日。 ⑥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文学评论》201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