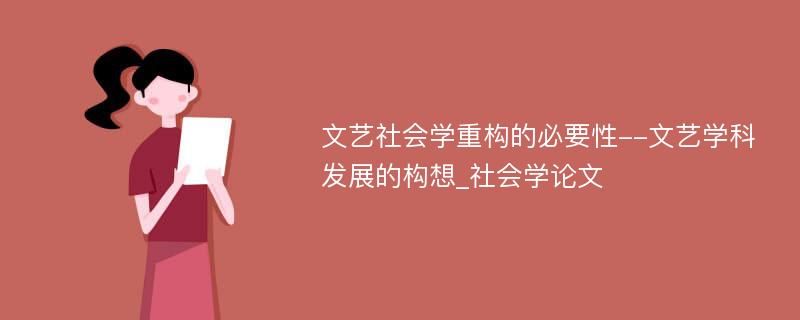
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文艺学学科发展的一种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社会学论文,学科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4)01-0122-06
近年来,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势劲头,“转向”说、“跟风”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1],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学/文艺/文化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一 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与文化诗学的关系
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在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对此有过清晰论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2-3]。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内。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亦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或趣味发展史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3](412、406页)
文化研究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家又如何见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类型: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其中的作家社会学和公众社会学研究。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并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同样被他当作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
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学科史视角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与相互交织,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所谓“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命名。尽管这种文化诗学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文化诗学固然重视“文本”的阐释,不过,其阐释的重心并不在于“审美”与“诗意”,而在于“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4]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是基于有意识地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4](前言)而这,恰恰也正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立场与目标之一。可以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针对文化研究将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与无限度地扩张,以至于威胁到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危险之弊端,童庆炳先生等一批学者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其旨趣,在于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强调既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又超越现实,反思现实。因此,这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富于针对性和建设意义的。
文学界对文化研究最大的不满,主要就在于它“泛学科”、“非学科”,甚至“反学科”倾向。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文化化”倾向,已成为当前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5]。的确,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2](23页)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一个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6],应该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做“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基本思路和关于必须重视“文艺评论”的理论主张的。同时,这也与“泛文本化”的文化研究划清了界限。不过,如前所述,文学社会学包括作家/作品/公众研究三方面,而定位于“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正因为文化诗学定位于“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要比这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文学文本”,而且也包括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功能、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其中有些研究与“文学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尽管这种“非文本”研究,包括其中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可能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它就是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惟其如此,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的同时,还赞同有必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二 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无高下之分
如上所述,倡导“文化诗学”是适时的,但以“文化研究”、“文化诗学”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匪夷所思。
的确,新兴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7]。但,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此其一(关于这一点,童先生早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8]中便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其二,如果说“不同”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差异,即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脱离文本空发议论。因而在“视界融合”中诠释文本和问题,便构成了“文化诗学”所追求的“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7](40页)。那么,我想要补充的是,这种开放的“视界融合”的方法,同样表现在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以“原来的”或“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来反衬“文化诗学”方法的优越性所可能造成的“遮蔽”,是不言而喻的。
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理查德·霍加特曾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了不同性质/类型的文学社会学:“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像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3](44页)
上述区分是重要的。毫无疑问,“审美”或“语言”“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惟其如此,发生学结构主义学派的戈德曼,才将其方法概括为“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和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9]。经验实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埃斯卡皮,其实也并不忽略形式主义所标榜的“文学性”。他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是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而已。在他看来,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这也就是所谓“背叛的能力”或“创造性的背叛”,即“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2](《文学社会学》,17页)而具有这种“重新阐释”的无限可能性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经典”。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更是谋求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或“原来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的文学批评和经验技术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本文社会学”批评模式。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10]。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又强调社会意识形态意义揭示的批评方法,与霍加特倡导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或文化诗学标举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6],其实并无二致。
1980年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不但文艺学“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就是文艺“新学科”,也是满天开花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仅1988年出版的《文艺新学科手册》,收录、介绍的文艺“新学科”便达145个)。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文艺学学科的“不成熟”性。有学者认为: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文艺学存在着学科定位不甚清晰、研究领域比较模糊的问题,许多方面还表现出不成熟。比如,对文献和学术资源的依赖性不够,问题意识和学理意识不强,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不严,过于热衷于追逐时尚和标新立异等等,这诸多方面都将严重阻碍文艺学的学科建设[11]。有论者更是批评了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现象[12]。话虽尖锐,却发人深省。
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主张“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但1987-1997年10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目标,尚有相当距离。早在1920-1930年,欧美、日本、苏俄的文艺社会学便有大量译介。到了19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与“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近20年来却相对“沉寂”了(童庆炳语)。据1998年在北图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书名的比例差之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形态的单一性。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文艺社会学在中国创建于何时,学界有不同意见。多数意见认为,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但我认为,不会晚于1930年。故在《文艺社会学史纲》书稿中,我将国内1980-19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今提“重建”,当为继续1980年代以来的未竟事业。因为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似乎突然被悬置、中止了。当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文艺社会学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受益者。尽管这种受益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不排除为文艺社会学“正名”之愿,或者说,仅图个“虚名”而已。
三 重建文艺社会学的三条路径
2001年4月,陶东风在扬州会议上提出了“重建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必须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13]。尽管这一基本构想,并未超出其身体力行的文化研究之旨趣,但提出“重建”本身,以及在方法论中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互为主客体辩证关系之强调,值得关注。
长期以来,在国内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主张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属罕见。其实,这也就涉及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等。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的定位,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还有不同的学派。其分歧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14]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惯例和约定俗成,无论是社会学分支还是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应该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其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或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属于一般的文化研究而非文艺社会学研究。而这种研究的或“有诗意”或“无诗意”或“反诗意”,是不能构成方法论上的孰优孰劣问题的。
其次,在两大分支内,还应该重视不同流派和学派的建设与发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多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尤·H·达维多夫);以及“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埃斯卡皮)等等。而“经验的实证的”和“理论的批判的”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技术的”和“批判的”两大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主要特点,在于坚持技术主义路线,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与之相对立的,是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坚持“批判的理论”和“否定的美学”的阿多诺,便曾经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代理商的技术”[15]。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年)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年),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路径,才导致了花建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研究,而姚文放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国内文艺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如果把“技术的”,理解为支持的是工具-目的合理性,指的是当社会行为的规范化目标确立之后,为获得特定结果对最优工具所做的合理化选择(哈贝马斯);或者所有批判性知识的可能性,都由于对“处方性知识”的需要而被放弃(吉姆·麦克奎甘)。而把“批判的”,理解为吉姆·麦克奎甘所言的:这是一种学术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使其工作本身所发生的语境与任何直接的实践的结果相分离;或者说,他们在一种语境下可能的批判性反思机会的获得,是以丧失任何直接的实践有效性为代价的[16]。那么,我认为文艺社会学除了上述“技术的”和“批判的”两大流派之外,我们还应该重视融“经验的实证的”和“理论的批判的”为一体的第三种流派。1970年代初,尤·H·达维多夫在为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文艺社会学》词条曾指出:在“基础理论性的”研究和“实证应用性”研究的结合中,有可能产生出“第三种流派”。对于这一流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的”。实践的文艺社会学,应该是在“新理性”精神指导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功能和批判功能、实证方法和理论方法、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的辩证综合。
就当下而言,面对现代高科技的复制技术、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对艺术、艺术生产、艺术消费方式和过程的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所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制品的大举入侵与倾销,无论是立足于国家意识形态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立场,如何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都是一个迫在眉睫极需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性意义。而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市场、文艺体制、文艺政策,以及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等诸多领域,正是“实践的”文艺社会学的用武之地。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三个“文化产业”项目。这三个项目,无一例外全都在“中国文学”学科内。它表明,“文学研究”之介入“文化产业”研究,已成为国家学术体制和学科建制的一种需要与现实。而这,也为“实践的”文艺社会学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