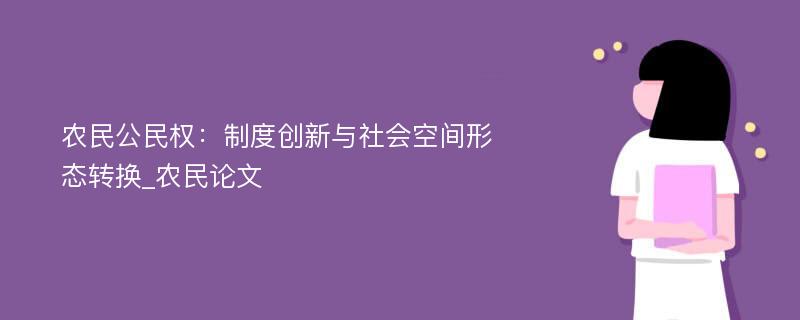
农民市民化:制度创新与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创新论文,形态论文,市民论文,农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随着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一些地区已经部分地出现了片面追求空间景观城市化的倾向,相对忽视了地域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城市化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对此,有学者提出“假性城市化”的概念,强调应积极发挥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以克服这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误区(注:郑也夫:《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07-113页。)。但有的甚至进而认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是分离的,或者说两者并不相关。
诚然,农民市民化与空间景观的城市化可能具有时序先后的差别,一味追求空间景观的建设未必就能直接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但倘若将两者某些相脱离的表象错当相分离的实质,误以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不相关,恐怕颇为不妥。且不说上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已经充分认识到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空间景观的密切关系,现今中国城市中所存在的为数众多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独特景观。再有,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双重作用,共同构成了当前城乡一体化的丰富内容,而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性正体现为一系列崭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农民市民化作为城市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相关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而这一制度安排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内容。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约束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农民市民化始终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贯穿其中,并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中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将空间维度的分析引入相关制度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更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注入更为丰富的社会发展内容,从而提升我国城市化的品质。
一、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
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使大中城市郊外的农村与城市,缺乏城乡一体化的有机的空间联系,致使集镇与集镇之间未能形成与城市相衔接的资源合理配置的空间体系,乡村社会的空间格局反而呈现出相当分散的空间布局状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制乡、建制镇更使这种分散状态获得了行政区划的体制支撑。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当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农村非农经济的快步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与地域背景下展开的。的确,乡镇企业在当时的积极贡献尽人皆知,1978至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2%,年均就业总量为670多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但乡镇企业自身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特征,以及乡、镇政府的深度介入,致使我国不自觉地走上了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村发展道路(注: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5-99页。)。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村村像镇,镇镇像村”可谓是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形象表述。而与此相关的正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不同程度地受阻:一是农民向非农产业进一步转移发生了困难,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的趋势,1992年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平均每年仅260万人左右,此时,农民不仅兼业现象普遍存存,而且原来已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口甚至出现回潮的趋势。二是分散城市化又导致了作为城镇重要作用的规模效应未能形成,1997年的统计表明,从已形成的小城镇来看,平均建成面积0.39平方公里,非农人口城关镇2.6万人,建制镇2700人。加之资源配置的城乡落差,城镇的生活环境未能形成重大的根本性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转变尚难以形成(注:袁以星、冯小敏主编:《上海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8-134页。)。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不少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并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构筑城镇体系,从而大力推进城市空间形态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首先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形成,其次是各城市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加强,再次是各城市群体在中心城市辐射的地域范围内与中心镇、小城镇乃至广大农村构成一个经济综合体,从而逐步形成一个有层次、有职能分工的地域体系,而城镇在整个地域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和补充功能。与此同时,围绕城镇建设进行乡镇区划调整,适度扩大中心镇的政区规模,并适时推进土地、户籍、就业、规划、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创新,确保城镇体系有序、快速地形成。实际上,城镇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镇发展的高级地域组合形式;也正是依托这一城镇体系的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将逐步得以形成。
就农民市民化进程而言,城镇体系的构筑这一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农民职业构成模式的转变。城镇体系所需要的产业支撑,是由城市工业向郊区扩散和原乡村积累转向对非农产业的投入两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故而城镇的新型产业不仅已经超越了原有乡镇非农产业的范畴,而且具有现代城市工业乃至服务业的内涵;这不仅意味着农民就业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更意味着农民将在大量的新型产业寻求就业空间,形成职业构成模式的多样化,从而融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与此同时,目前原有城乡分割状态下限制农民就业范围的所谓“自然就业”政策已被突破,进一步扩大农民就业范围的制度创新正逐步形成。不仅如此,新型产业不再是分散布局,而是以强有力的政策导向推进城镇工业园区集聚,这又将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的形成提供必要的产业空间基础。二是农民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缩小城乡差别并不是将城市与农村生活条件低水平地“拉平”,而是通过多层次城镇体系的建立,带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而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传播具有层次性的鲜明特征,与城市经济辐射的基本路径相似,是通过有机组合的城镇体系,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中心镇—小城镇逐层地影响农村的。城乡融合的新型生活方式将率先出现在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域社会实体——城镇之中。小城市或中心镇将成为新型城镇社会空间体系的“龙头”,而小城镇将构成其主体,至于那些工业化或贸工农一体化的超级村庄则成为其重要组成部份。当然,这种城镇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同样是在土地利用、户籍管理、城镇规划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中,在城镇体系日臻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构筑城镇体系进一步的制席安排中,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的衔接、城镇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等等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内容。
二、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
如果说,职业分化使农民离土离农,是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前提,生活方式的变革构成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基础,那么,社会空间流动则是促进农民认同城市文明、共享城市文明、融入城市文明的关键环节。倘若缺乏这一关键环节,即便是那些犹如镶嵌在都市汪洋大海中一座座孤岛的“城中村”,村民们已经没有了耕地,也大多不在村落中就业,但周围的都市世界却似乎依然是陌生的,他们在心理认同、生活情感上对自己的村落仍然拥有相当强的依赖感,仍然“坚守”着村落共同体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注: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尽管美国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已关注到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或基层集镇(standard town)作为传统农村基本功能单位的空间纽带作用(注:[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40、41页。),但是,长期的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以及城镇的分散布局,致使城郊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多局限于社区内部空间,即所谓“熟人社会”,从而产生社会交往中特有的地域凝固,难以形成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以乡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非农经济发展,曾极大地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它们长期在农民基层行政体制的约束中,难以使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的地域凝固状态得以根本改变。乡镇企业大多是在乡村两级组织深度介入下形成的,乡镇企业在资金方面主要来自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也包括本地农民的部分集资,初期很少有外来资金;在经营方面,厂地选择一般不考虑原材料产地、消费者所在地等空间因素,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主要以本地域为建厂地址,乡办企业建在乡,村办企业建在村;产品营销则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为主;而劳动力吸收则以本地为主,当本地劳动力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时,才会适当吸收外来人员。至于乡镇个体企业,则具有独户和联户两种形式,在劳动力方面更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有限的雇工多是亲属、朋友,具有明显的家族亲缘特征,在企业的选址上有些企业甚至将生产用房和家庭生活用房合为一体(注:张晓山、胡必亮主编:《小城镇与区域一体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88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在“家庭—乡村”的地域单元中展开的。加之村落管理制度、集体产权的作用以及当时对“农民工”的体制排斥,更强化农民社会空间流动的凝固状态。
然而,城乡一体化发展正逐步使农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向空间开放悄然转变,并集中体现在活动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变化上。对于活动空间来说,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使农民社会活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与城区的交往联系活动日趋频繁。据笔者关于上海的相关调查表明,上海郊区农民活动的空间范围已突破所居住的乡村或县城的局限,向城区不断扩展。在上海远郊抽样调查的500人中,2003年农民出访城区的频率较1998年提高了5倍;而上海近郊抽样调查的500人中,2003年较1998年提高了8倍(注:林拓:“上海郊区城镇发展功能定位与开发区体制关系研究”,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课题(2002-R-14-A)。)。不仅如此,当前上海郊区农民出访城区正逐步由节庆型向日常型转变,其中城乡交通系统的完善是促使上海郊区农民活动空间扩展加速的重要因素,而农民活动空间的城乡一体化趋向无疑直接有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对于居住空间来说,一方面,农村居民逐渐摆脱原有依附父系家庭、村落集中居住的格局,呈现出从集中到分散,再向城镇集中的流动变化趋势。城镇新型工业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是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业生产方式代替以家庭或逐步乡村地域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它不仅促使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且社会的行业和职业趋于复杂。而与之相伴的是个人收入独立,家庭控制逐步削弱,家庭成员就业提供大量机会,自主选择生活方式以及居住空间;家庭结构模式逐步以空巢、核心和主干家庭结构为主,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又有利于城市化。更应该指出的是,其中以乡镇企业的改制和转制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企业制度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海郊区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为例,1980年代上海农村劳动力的迅速非农化大转移,很大程度上是以乡镇集体为单位,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渠道的单一性转移。1980至1986年,上海郊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仅上升不到1个百分点,1986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仅1990年平均每户新建住房0.31间,但基本上仍然是非城镇化集中的分散建房;而1990年至1996年平均每年上升达1.7个百分点,1996至1998年年均上升幅度则达2.2个百分点,此后逐年快速提升。正是1992年以来上海郊区以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乡镇企业的改制和转制;同时率先在郊区建立“私营经济区”,促进非公经济加速发展。到1997年,全郊1.9万多家乡镇企业已有73%完成改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已达10.9万和6.2万户,非公经济日益成为郊区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此外,三资企业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郊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97年郊区集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产值比例已由1992年的86∶12∶2转变为60∶25∶15,基本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不仅近郊地区如此,而且远郊地区城镇集中的进程也在加快。城镇人口机械增长与乡村人口机械变动减少的相对比值,已由1980—1986年的63.8%上升到1986—1990年的79.3%和1990—1996年的85.7%,说明远郊地区乡村人口向远郊地区本身城镇集中的进程正趋于加速(注:朱宝树主编:《城市化再推进和劳动力再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40页。)。与之相关的是,城镇土地制度等的创新诱发了农民在购房置业的积极性,也相应在拓宽了城市建设的投资渠道。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颁布以后,更加快了这一进程。
另一方面,城区居民向郊区流动、扩散也正在逐步加强郊区居住空间的开放性,从而改变郊区居民以本地农民为主的单一性格局。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在上海近郊地区的不少城镇,吸收来自市区的人口已经占到相当高的比重。例如,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在宝山区的月浦、盛桥和杨行三个镇的人口中,1985年时常住地为城市街道的人口所占比重达45%,奉贤西渡小区,1996年已有8300多套住房被市区居民购买,占购房总数的70%;入住家庭6500多户,占总数的50%以上。宝山顾村、嘉定江桥、闵行莘庄等地新建居住小区内,来自市区的普通居民也已占4成以上(注:朱宝树主编:《城市化再推进和劳动力再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40页。)。据统计,城郊已售出的别墅和公寓房中,有近三成买主来自城区。随着城区人口的不断导入,原有城镇居民的构成发生变化,城市生活方式也被带入城镇社会,社区风尚将相应产生一系列转变;而农民与市民在特定空间的社会整合过程,也正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逐步融合的进程。近些年来上海城乡居住出现明显的双向流动趋势,农村人口进城住商品房,城区人下乡购小别墅。实际上,城乡居民这种双向流动的趋势,在全国不少大中城市已经相当明显,而在它的催化下所形成的居住空间的开放性,其本身不仅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生活环境等逐步趋于均衡的必然结果,是城乡居民双向认同的重要反映,更是农民市民化转型的关键途径之一。
三、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
既然社会空间格局的变化引发农民的职业分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空间流动又促进城乡文明的融合,那么,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整体进程来说,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势必要求社会空间治理模式产生相应的转变,而现代社会空间治理的基本特征正是突破行政区域的狭隘局限,形成跨区域的协调与互动,其转变的基本前提之一则在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更新,以及各种新型社会公共或私人部门的产生。
在这里,我们应先考察现代行政体制在我国乡村社会的确立状况。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专业化为基本标志,以现代财政制度为保障,是适应社会专业化事务的不断涌现而形成的。我国虽然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集权制官僚国家体系,但在乡村基层却是“皇权不下县”(注: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9、92页。),其县令既是行政首长,又是法庭判官,往往一身多任,权力相当集中。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可能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确立起来。建国以后,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量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各种机构,不仅有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分设,而且行政机关内部还设立了大量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委办局,这些专业分工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在县以下的乡镇相应设立各种代理机构,即后来发展为乡镇一级“七站八所”的那些机构。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农业型地区现代行政体制努力的成果并不明显(注:贺雪峰:《当前县乡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6期。)。究其原因,一是在行政体制形成的基础上,以农户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事务相对简单,现代行政体制所需要的专业化分工尚未真正形成;二是在行政体制运行的成本上,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收入有限,而以之为来源的相应有限的基层政府财政,难以支撑昂贵的现代体制运行所需要的行政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地区,社会事务不断趋向复杂与细化,财税收入也相应扩大,现代行政体制确立的迫切性和实效性日益突出。但乡镇企业的地缘性特征使之与乡、村两级组织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而乡、村两级组织的经济来源又多依赖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时排斥可能来自其他行政区域内乡镇企业的竞争(注: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78页。);加之社会空间流动的地域凝结,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管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视野投向其他行政区域,故而长期以来乡村基层社会管理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以行政区划为空间分割的鲜明特征。至于村级组织作为行政村区域内部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更具有类似的空间分割特征。不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正不断地促使乡村社会治理突破政区分割,进而向区域联动转变。
近年来,农村乡村治理的研究日渐引起重视,并已取得众多重要成果。大致地讲,目前的相关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这样的认识前提,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促使农村经济社会秩序解构—重组的主要力量,一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诚然,上述两种力量的决定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乡村治理进程的加快更在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正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导致了产业多元化、居民多样化、建设集约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变,进一步催化农村社会关系与网络发生新的调整,进而全面催生乡村社会资本的更新,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家族关系及家庭功能的变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随着城镇新型产业的发展,农民逐步融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个人选择职业、配偶及生活方式的自主空间将不断扩大。目前农村的家族婚姻正向城市的个人婚姻转变,亲属关系交往的比例已经呈现出城镇小于农村的状况。很明显,家庭亲属的作用正在减弱,许多家庭功能逐步被新型社会组织所代替,这将为各种社会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产生提供广阔的空间。
其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村级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的变化,并集中体现在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变化上。原有村级组织网络关系大多仅涉及行政村内部成员的这一闭合性特征是众所周知的(注: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但随着企业改制及现代产权制度的逐步确立,当前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大致说来,己经形成三种新的基本关系类型:一是附生型关系,即由村级自治组织直接行使管理决策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包括村办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股份合作企业、村办合作基金会等等,在现有体制背景下,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等三个正规组织的活动是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该合作经济组织兼具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和社区稳定等多重职能,它基本上由行政村内部成员所构成。二是衍生型关系,即管理决策权与生产经营权归属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非自然人,这类组织在乡镇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成立的农村基金会以及依托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所建立的专业协会中普遍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管理决策的行政控制性,往往根据政府意志而非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利益进行管理决策。它具有两个双重性,第一个是在管理决策与成员利益上既有统一又有冲突,第二个是在组织构建与参与广度上既开放又相对封闭,表面上对组织成员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定,具有一定的乡村社会公共部门的色彩,但实际上仍未脱开原有村庄关系及行政区域的限制。三是新生型关系,即管理决策权和生产经营权集中于大股东或专业大户。在这类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中原有的村庄关系已产生相当大程度的改变,大股东或专业大户的角色作用已不在于村庄内部关系网络中的辈份与资历,而在于新生经济组织网络中的实际地位,还在于个人的才干、声望及与之相关的个人权威等无形资产;至于这类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有的村庄关系而处于动态的伸缩变化之中。对于社会公共部门的催生来说,这类组织的作用将最为直接。尽管上述关系类型的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已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对其最终走向尚难作出明确判断,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实质正是社会资本的更新,众多社会公共部门将孕育其中,它必然使基层社会空间治理逐步突破行政村的政区分割,进而向区域性联动迈进(注:林拓:《城市化进程中乡镇治理与社会资本更新》,《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2002年,第121、123页。)。当然,在村级自洽组织中,部分农民转为居民户口以后,原有村民自治由于选民性质的变化,使选举的合法性基础发生相应的变更(注:何泽中:《当代中国村民自治》,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56页。)。不仅如此,目前在不少大中城市的近郊,许多村民委员会已转为居民委员会,并逐步融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
再次是乡镇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的变化。政社分设以后,乡镇作为一级政权组织,自成体系;作为一级财政,长期以来是镇属经济为财政收入来源,除了上缴部分利税之外,均用于本镇范围相关的行政支出,圆融自足;因此,作为一级管理主体,加之原有村级组织网络关系的闭合性特征,乡镇管理的空间是相对封闭的(注:林拓:《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政区改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但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使乡镇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从镇属经济到镇域经济的转变,笔者在上海、苏州、宁波等市抽样调查的30个镇级工业园区中外来企业户数均占30%以上,有的高达80%,而原镇属企业外迁者也屡见不鲜;目前乡镇财政收入也已不再是通过政府深度介入来获得镇属企业产值利润的上缴,而是依靠镇域经济的利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注:高培勇、温来成:《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与此同时,在镇域范围内也已相继出现相当数量的行业协会、专业基金会等各种民间组织,而这些民间组织中有不少是跨镇域、跨县域甚至是跨市域的区域性组织,仅仅拘泥于镇级政区内部的管理明显难以适应新的需要。不仅如此,目前镇域发展的实际绩效也已不再仅仅取决于镇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是与周边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联。今后在我国不少地区即将试行的,乡镇一级由政权型组织向代理型机构的转变,正是为了适应乡镇治理新要求而作出的努力。
简言之,从家族关系网络到村级组织的关系网络,再到乡镇组织的关系网络,这一层层递进的乡村社会的关系链正处于重大的变化调整之中;而乡村社会资本更新的同时,己使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这一模式转换的主线日渐明朗。应该说,在制度创新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与农民市民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社会空间格局、社会空间流动和社会空间治理这几个方面,但他们却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面。实际上,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空间过程,更是相关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三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倘若没有制度创新,难以引发社会进步与相关的空间形态变迁;倘若没有社会进步,相关的空间形态也无从谈起;倘若缺乏必要的空间基础,社会进步也将相应变得迟缓。
标签:农民论文; 空间形态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