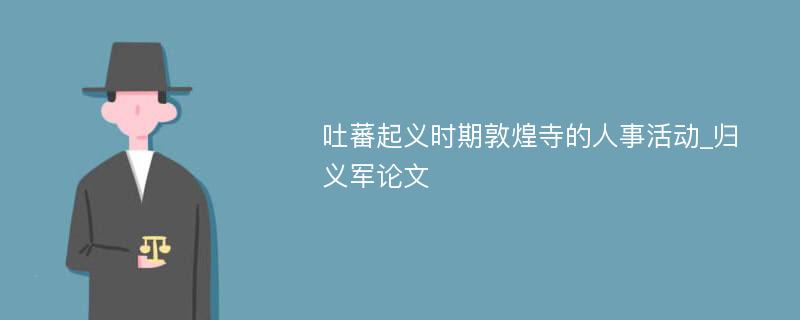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人事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敦煌论文,寺院论文,义军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收支中有一类特殊的项目,名曰“人事”。关于“人事”一词,从古至今有着诸多含义,①其含义之一即是指赠送的礼物或酬物。如韩愈《奏韩弘人事物表》云:“右臣先奉恩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缘圣恩以碑本赐韩弘等;今韩弘寄绢五百匹与臣充人事,未敢受领,谨录奏闻,伏听进上。谨奏。”②但是,在不同时期,“人事”又成为因升迁而进行讨好贿赂的行为,如《后汉书·黄琬传》记载:“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甚至发展到唐代,在诸道州府的非财政支出中就有一项名为“人事用度”。据李锦绣先生的研究,“人事支出成为唐代地方固定支出项目,为唐后期财政史上的独特现象。人事支用应始于肃代之际。”而且,“长庆之后,人事风气愈演愈烈,中央不但允许人事存在,还颁令定额,力求限制。”③正是由于人事风气的泛滥,从而导致了其性质的变异,故《唐会要》卷七九中对“人事”做了如是解释:“如闻朝臣出使外藩,皆有遗赂,是修敬上之心,或少或多,号为人事。”④这里的人事即为贿赂,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礼物或酬物的范畴。作为“礼物或酬物”意义上的人事行为不仅盛行于上层社会,而且普遍存在于民间;不仅中原地区,而且流行于边远地区,甚至渗透于脱离尘世的佛教界。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保存下来的诸多寺院人事收支账目即为我们认识唐宋之际民间人事活动及敦煌佛教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利用这些资料对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二、寺院人事收支类别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人事收支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庆贺
首先是庆寺。P.3763V《年代不明(10世纪)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第3-4行记载:“又布壹拾贰疋,起寺设时官私及诸寺人事入。”P.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中第44-45行载:“生绢贰疋,大云、永安庆寺人事用。”又50行载:“绵绫壹疋,圣光寺庆钟用。”又第51-52行载:“绵绫壹疋,安国寺庆寺人事用。”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第94行记载:“绁破:官布壹疋,高孔目起兰若人事用。”又243行载:“粟柒斗,卧酒乾元寺冩钟人事用。”又第496-503行载:“布入:……布壹疋,大众起钟楼人事入。布壹疋,官家人事入。布壹疋,杨孔目人事入。布贰拾尺,索校拣人事入……布壹疋,三界寺人事入。”又第506-508行载:“绁入:……细绁贰拾伍尺,粗绁伍拾尺,大众起钟楼人事入。粗绁贰拾伍尺,莲台寺人事入。粗绁贰仗伍尺,报恩寺人事入”又509-510行载:“褐贰仗伍尺,大众人事入。褐贰丈,安生人事入。”P.3234V(7)《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第24-25行记载:“官布壹疋,乾元寺冩钟人事用。”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第197-198行记载:“粟柒斗卧酒,官布壹疋,莲台寺起钟楼人事用。”又第395-396行载:“面肆斗,造蒸饼,粟壹石壹斗沽酒,粗绁壹疋,报恩寺起幡设人事用。”从这些记载来看,庆寺不只是在修建新的寺院或兰若时进行,但凡寺院内部的建造如修造钟楼、鼓楼等均属于庆贺的对象。由于建造寺院以及寺院中的钟楼、鼓楼等均是一种功德,其他寺院或个人一般要进行庆贺,故寺院关于这方面的收支记载亦较多。
其次是庆婚嫁与生育。婚嫁与生育是人生中的重大喜事,故敦煌文书中亦有对此等事宜进行庆祝的记载,不但世俗人乐此不疲,而且佛教界亦加入其中。如P.2638中第45-46行载:“又生绢贰疋,郎君小娘子会亲人事用。”又第51-61行载:“绵绫壹疋,开元寺南殿上梁用。绵绫壹疋,甘州天公主满月人事用……细绁壹拾柒疋,天公主满月及三年中间诸处人事等用。粗绁伍拾柒疋,三年中间诸处人事、七月十五日赏乐人、二月八日赏法师禅僧衣直、诸寺兰若庆阳等用。布贰仟柒伯壹拾尺,三年中间沿僧门、八日法师、七月十五日设乐三窟禅僧衣直布萨庆阳吊孝等用。”此件文书所记载的是儭司的人事活动,但因僦儭司与寺院均属佛教教团,故实际上亦反映了寺院在该方面进行的人事活动。
最后是上梁。P.2638中第51行载:“绵绫壹疋,开元寺南殿上梁用。”又第49行载“生绢壹疋,天公主上梁人事用。”P.2040V中第238行记载:“粟柒斗,卧酒宋都押窟上梁人事用。”P.3234V(7)中第23-24行载:“布壹疋,宋都押窟上梁人事用。”P.2032V中第119-120行载:“布壹疋,水官上梁人事用。”上梁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盛行的一种风俗,是在修建房屋和开凿洞窟上大梁时举行的一种驱邪求吉的民俗。上梁时亲戚朋友亦要对建造者行人事以示庆祝。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几件上梁文如S.3905《唐天复元年辛酉岁一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P.3302《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等对当时的上梁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⑤
从以上资料来看,庆贺人事所用物品一般皆为织物,即使食物出现亦是与织物同时出现的,这一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敦煌民间庆贺的习俗。
(二)送路人事
“送路”在古代文献是较为常见的一项活动,近似于我们今天的饯行、送行。但当时的送路又似乎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故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李侍御送路物:少吴绫十疋、檀香木一、檀龛像两种、和香一瓷瓶、银五股、拔折罗一、毡毛帽两顶、银字《金刚经》一卷(见内里物也)、软鞋一量、钱二贯文、数在别纸也。”同书又载:“刺使施绢两疋,诸人皆云:‘此处是两京大路,乞客浩汗,行人事不辨,若不是大官,是寻常衣冠措大来,极是殷勤者,即得一疋两疋,和尚得两疋,是刺使殷重深也。’”⑥可见,送路人事是以赠送礼物为前提的,而且礼物的多寡、是否行人事等均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等。送路的物品亦可以称之为“信物”,如“八月九日,得张大使送路信物,数在别。”⑦
敦煌文书特别是寺院经济文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迎送活动的资料。寺院的迎送对象主要为往来外地的使客、统治阶层及其家族、僧官与寺院高层等三类人,迎送支出亦成为寺院支出中的一部分,尽管迎送支出在寺院诸多支出项目中所占数量很小,但出现频率则相对地高,更重要的是寺院送往迎来所发挥的功能及代表的意义却很大。⑧其中迎送活动中有一项称之为送路人事,如P.2912《丑年正月已后入破历稿》(二)记载:
1,四月已后,儭家缘大众要送路人事及都头用使破历。
2,五月十五日,上宋 教授柒综布壹拾伍疋。
3,十七日,瓜州论乞林没热儭绢一疋,慈灯收领。
4,廿四日,奉 教授处分,付都头慈灯柒综布拾疋。
5,奉教授处分,送路宋国宁两疋,
6,[大]云寺主都师布二疋出福渐下。
7,□教授送路布十五疋,准麦六十七石五斗。都头分付
8,[慈]灯布十疋,准麦四十五石。与宋国宁布两疋。
9,[准]麦九石。都计一百廿一石五斗。
(后略)
本件文书是吐蕃时期儭司的账目记录。第一行为布的支出原因,第2~6行为布的实际支出数,第7行后为布折合成小麦的数目。从前后记录来看,“送路人事”或称之为“送路”,或称之为“人事”,这说明“送路人事”可以简称为“送路”。
但是,我们同时又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寺院在送路时一般以食物(包括酒)为主,只有偶尔才会出现以织物送路的现象。罗彤华先生对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P.3763V《净土寺壬寅年(942)入破历算会稿》和P.3234V(9)《癸卯年(943)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广进面破》四件文书中的迎送支出做了统计,结果表明四件文书中麦的支出数共有55笔,粟211笔,油108笔,面227笔,而织物中仅有绁,且仅有一笔(共26尺)。⑨这种现象可能与出行信仰有关,因为唐宋之际敦煌人在出行前往往要通过写经、道场施舍、设斋等诸多方式来祈福。⑩正是由于这些出行者可能在出行前到寺院祈求佛神保佑自己出行顺愿、平安归来,故寺院同时用食物为之招待送行。但这种仅用食物的“送路”与附送织物等的“送路人事”是否性质相同呢?对此我们难以给予明确的答案。或许将送有礼物的送路可以称之为“送路人事”,简称为“送路”,但不是所有的送路均可称之为“送路人事”。
(三)其它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还有一些关于人事收支的记载,但其性质暂时难以确定,这里只好姑且将其归入此类。
首先是句意不明或难解。如P.2642《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中第5~7行记载:“七日,粟壹硕贰斗沽酒梁和尚旋车人事用……十六日粟壹硕贰豆斗沽酒衙内人事用。”衙内即归义军节度使衙。P.3490《辛巳年(921或981)某寺诸色斛斗破历》中第4~5行记载:“油贰胜泛法律起衣人事用。面肆斗泛法律起衣人事用。”P.2049V中第256~257行载:“粟柒斗,吴法律旋车人事用。”P.2032V中第119-120行记载:“粟柒斗卧酒,安平水举发人事用。”第309-310行“吴僧统和尚收灰骨人事用。粟柒斗,高□□上席人事用。”又第818-819行载:“面伍斗,造蒸饼,高法律上席延局人事用。”又第852行“面二升,造高法律人事蒸饼时女人用。”P.4957《申年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中第30-32行记载:“荜豆贰升,煮粥参瓮,内一瓮王阇梨亡日人事(用),两充官灵真及索帐人事用。”其中“旋车”、“起衣”、“举发”等不知何意。
其次是与招待有关。P.2049V《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第231-232行载:“粟壹硕壹斗,莲台寺设人事用。”P.2040V中510行记载:“褐捌尺,看卜师人事入。”设、看、迎、供、屈等词在敦煌文书中有招待之意,(11)故这些人事支出应为寺院招待时的费用支出。
最后是与劳作有关。如P.2049V中第230-231行载:“粟壹硕壹斗,报恩寺垒北园墙沽酒人事用。”P.2040V第290-291行记载:“油叁升,报恩寺垒园人事用。”P.2032V中第811-812行载:“面柒斗,报恩寺垒园时人事用。”又第848行载:“面壹斗,荣报恩寺垒园时人事女人用。”
总之,这类人事似乎可以看做是劳作时的人力或费用支出,但我们亦可以理解为这是敦煌民间人事活动的另一种含义,因为这些支出均非本寺院劳作时的支出,而是针对其他寺院或个人事务的支出,故它可能反映了当时敦煌民间因贫困而注重人事实用性的一面,亦即“资助”。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论述。
以上我们对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所记载的人事收支项目进行了分类梳理,从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均是寺院与敦煌社会各阶层,包括佛教界、官府、上层社会、普通民众间的人事往来。寺院的人事收支所用的物品主要有两类:食物(包括酒)与织物。它们的数量似乎并不是很大,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寺院财产收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人事性质的再认识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人事活动记载是认识古代民间人事性质的重要资料,它既有与传统史料记载的官府上层人事性质相同的一面,但同时又具有民间人事活动注重现实性的一面。下面我们结合敦煌文书的相关记载对人事性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与敦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人事往来是一种礼仪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要赠与对方诸如褐、绫、绁、布之类的织物作为礼品,故这时的人事应与前面所述以赠送礼物为出发点的人事性质是一致的。
但是,这种具有礼仪性质的人事活动又有其特殊性。由于人事较之其它礼仪行为似乎有自己的特殊性,故在敦煌文书中记载到其它礼仪活动如吊孝时,二者往往是分别记载的。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记载了大量寺院进行吊孝时的财产支出,(12)但其与人事活动似乎有所不同。如前引文书P.3234V(7)《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就对因各种人事及吊孝活动而破用布、绁的情况进行了记载,集中体现了二者的不同。如载:“布破:布尺五吊祥会弟亡用,布壹疋宋都衙窟上梁人事用,官布一疋乾元寺写锤人事用,布二尺吊保应父亡时用,布二尺高法律大阿娘亡吊用,熟布一疋送路高法律张阇梨东行用,布贰尺五寸王僧政兄亡吊用,布二尺梁户郭怀义妻亡吊用。计一百三十尺。绁破:立绁一疋送路官家用……”这种现象在其它文书中屡有反映,如P.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记载:“右通前件三年中间,沿众诸色出唱人事、吊孝赏设破除及见在,一一诣实如前,谨录状上,伏请处分。”S.2472V《辛巳年(981)十月三日勘算州司仓公廨斛斗前后主持者交过分付状稿》云:“辛巳年十月三日,算会州司仓公廨斛斗……内除一周年迎候阿郎、娘子及诸处人事、吊孝买布、拜节、贴设肉价并修仓供工匠,计用得麦叁拾伍硕肆斗柒升、粟肆拾肆硕叁斗。”从礼仪的角度来讲,吊孝亦可称之为人事,但这里明确将二者独自并列记录,说明他们在性质上是不一致的。从前面我们所征引的事例来看,人事一般针对的是喜庆之事,而吊孝活动恰好相反。
其次,我们既可以把敦煌文书中的人事认为是一种庆贺活动,又可以视为是一种资助行为。正因为如此,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还经常有“人助”的记载。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记载:“八月六日,显德寺人助酒壹瓮……十七日,酒壹瓮,安国寺人助用。”“廿二日,酒壹瓮,酒壹瓮,翟家人助用。”P.2930(1)《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破用历》记载:“绍建麦伍斗,粟柒斗,沽酒乾元寺起钟楼日人助用。”S.4120《壬戌年——甲子年(962-964)某寺布褐等破历》记载:“昌褐壹疋李僧政造车人助用。”“昌褐壹疋,李集子男修新妇人助用。”S.6981《年代不明诸色斛斗破历》记载:“面伍斗,乾元寺上梁人助用。”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载:“粟柒斗,亦与马家付本卧酒报恩寺起钟楼人助用。”P.3763V《年代不明(10世纪)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粟柒斗卧酒,高孔目起经楼人助用。”从这些材料来看,“人助”的内容与“人事”基本一致,两者均含有造寺、修钟楼、鼓楼、上梁、嫁娶等事项。这说明人事具有资助性质,故“人事”有时亦被称做“人助”。
人事活动所用的物品主要是食物与织物,特别是食物的频繁运用于人事亦说明了其资助性质。而人事的这种性质亦正是民间人事活动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点在敦煌民间结社的情况中得到印证。S.6537V《拾伍人结社社条》载:
(前略)若有立庄修舍,要众共成。各各一心,阙者帖助。更有荣就,男女人事,合行事不在三官之中,众社思寸(忖)。若有东西出使,远近一般,去送来迎,各自总有……(13)
从本社条来看,社人之间的互相帮助、社人出使时的去送来迎与人事是不同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社官组织下社员必须要尽的义务,而后者为社员的自愿行为,社官不予干预,即“男女人事,合行不在三官之中”。但是,当修建与送路时的资助为自愿行为时,它们之间则似乎没有区别,均可以称之为“人事”,这正是我们在前述寺院账目中将相关活动称之为“人事”的原因。
四、结语
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不仅与佛教界、而且与世俗社会之间保持有频繁的具有庆贺与资助性质的人事关系。这种人事活动告诉我们:当时的敦煌佛教界并不是一心拜佛而不问尘事的,相反,他们在积极与世俗社会进行礼仪往来。
敦煌寺院的人事活动不仅反映了寺院与僧俗两界之间的人事往来,而且反映了整个敦煌社会的人事活动,因为这种人事活动在敦煌地区普遍存在,故归义军官府的支出资料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如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中第93-94行记载:“(九月)十六日,支都头泛善恩家人助酒壹瓮。”第95-96行记载:“(九月十八日)押衙曹富德家人事酒壹瓮。廿日,泛郎起舍人助酒壹瓮。”第100-101行记载:“(十月十日)支马保盈人事酒壹瓮。”
尽管寺院经济文书中记载了一些与归义军上层人物(如节度使、天公主、归义军各级官员等)有关的人事活动,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将这些活动视为是敦煌民间社会中的人事活动(当然,我们亦不能排除与官方交往中的人事活动有讨好的意图),这种人事活动不同于唐代地方财政支出中以贿赂等为目的的人事活动,它主要是人们为了庆贺与资助而进行的一种行为,特别是具有资助性质的人事活动,它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民间人事活动的性质,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地了解人事的含义。同时,我们亦可以将敦煌寺院的这种人事活动视为是当时我国民间普遍存在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与资助活动,而并不拘泥于敦煌一地。
注释:
①《汉语大词典》释之为:人之所为;人力所能及的事;人情事理;人世间事;人为的动乱;指仕途;说情请托,交际应酬;指赠送的礼品;男女间情欲之事;官员的任免升降等事宜;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辞海》(语言分册)解释类似。
②《谢许受韩弘人事物状》、《谢进王用碑文状》、《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等均有“人事”的记载。见[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点校:《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2~333页。
③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6~1118页。
④《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大中三年四月敕文。
⑤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33~442页。
⑥[日]圆仁著,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6~188页。
⑦[日]圆仁著,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第202页。
⑧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第193-223页。
⑨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第216-218页。
⑩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0-354页。
(11)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51页。
(12)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吊孝活动》,《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第145~152页。
(13)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