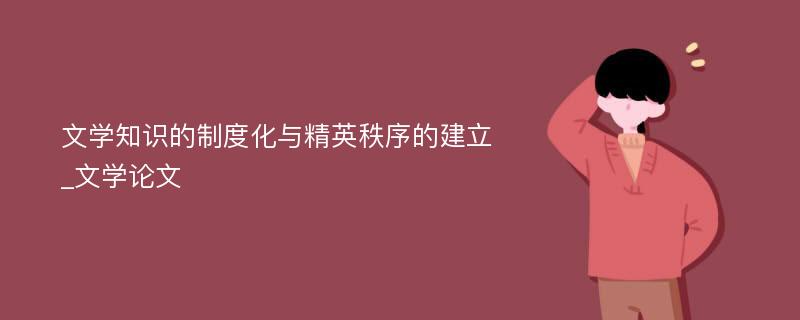
文学知识的制度化与精英秩序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秩序论文,精英论文,制度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6)030104—06
“制度”或曰“体制”(system或institution),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根据自己的理念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体系。《高级汉语大辞典》对“制度”还有这样的定义:“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我们这里强调“一定历史条件”和“构建”这两个关键词,就使得关于制度的讨论不再停留在抽象的理论的层面,而被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这样,它的可变异性也才可能被呈现出来。关于制度的可变异性,王国维曾有很清晰精彩的论述。他在《殷周制度论》曾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过于殷周之际。”① 接着,王国维以“政治与文化之标征”的“都邑”的变迁为例,说明周以前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朝崛起于“西土”,都“丰镐”凡11世。但换代易姓与都城的迁移,都只是表面的现象。最关键的问题,乃是新旧“制度”更替和新旧文化的变革。王国维指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王国维特别标举的“制度文物”与“立制之本意”,包括“制度”的“硬件”部分与“软件”部分,确是区别新旧社会、新旧文化、新旧时代的重要标志。因此,“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思想资源,才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王国维把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人者,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王国维说:“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② 现在看来,周公所立之制,至少在王国维所认为重要的上述三个部分,早已失去其价值与意义:立子立嫡之制已被民主政治制度所取代;庙数之制,亦已被废除;至于同姓不婚之制,对于许多人而言,都失去了意义。从历史角度说,从周朝建立直至晚清为止,中国社会的制度——特别是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着内在的、恒久的关联,晚清以后,这种制度始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而渐渐瓦解。1911年辛亥革命,则基本上推翻了原有的表面的政治制度,但宗法制则以民俗的形式保留在民间。1949年的革命和各项新制度的建设,方才从各个层面动摇了旧有的制度,包括遗留于民间的宗法制度。制度的历史性和建构性,都从制度的建构与瓦解中得到清晰的说明。
为了切题,本文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20世纪(在讨论早期的制度时,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向19世纪做一些延伸,以便厘清某些制度建立的缘起),而且主要涉及与“文学”有关的制度。制度或体制的“构建”的性质,使我们注意到“制度”或“体制”的“非本质主义”特征,它的历史性也为后来“后现代”的瓦解或“解构”留下了各种缝隙。
1922年,31岁的胡适为纪念上海《申报》创刊50周年,撰写了《五十年代中国之文学》,1923年3月他为该文的日译本作序时说:“我的目的只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以备一个时代的掌故。”这篇不到千字的短序特别为这篇文章补充了三份材料:一是王闿运、朱祖谋等人所提倡的“词学”;二是王国维等人对于元人的曲于和戏曲、明人的杂剧传奇的研究成果;三是《宣和遗事》等古小说的发现和印行。③ 胡适在他的文章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申报》诞生以来5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大势,分别介绍了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散文)、王闿运和金和的旧体诗、严复和林纾对西洋思想和文学的翻译、梁启超的时务文章(新民体散文)、黄遵宪的新体诗、章炳麟的述学文章、章士钊、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等人的政论文章、50年来的白话小说以及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距1917年胡适公开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近现代文学发展的文章,也是把古文的死亡和白话文的诞生“文学史”化——从而建立新的文学史秩序的一个令人注意的开端。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及《申报》问世的一年(1872)正是曾国藩死的一年。他指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政治上的中兴事业“虽然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满清国运,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国室的灭亡。他的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癖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但曾国藩一死之后,古文的运命又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更成了‘强弩之末’了。……这一段古文末运史,是这五十年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④
这是一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简史,它相当质朴、直觉而如实地描述了胡适眼里的中国文学从“古文”走向“白话文”的过程。不独如此,它透露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和观念:一、古文的所谓“中兴”和终于走向末运并死亡的历史,不仅与清王朝在政治上的“中兴”和终于走向末运并死亡相始终,也是新的现代制度之一的《申报》从诞生走向发展的过程,是“白话文”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二、胡适所叙述的“文学简史”,其时间跨越了两个政治时期,即晚清与民国,但胡适并没有把“政治”的变革放在他叙述的主线,而更着意于文学内部的变迁;三、胡适所叙述的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并没有出现突然断裂的情况,文学革命前的文学,例如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谭嗣同、梁启超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和章士钊的政论文章,都是从古文体制里发展出来的变种,都被胡适放在文学史的“重要的地位”来加以论说;四、“史”的叙述的必要性,源于对后来成为主流的“白话文”文学的“合法性”的内在需要。也就是说,新的“文学史”叙述与“白话文”的合法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新兴的、自觉的“白话文”文学,在胡适这位当事人的手里,第一次被纳入新的文学史秩序之中——但由于它并没有进入当时大学的建制,也就是说,没有成为大学的教科书,因此,它还是可以在体制外游动的,如此方得以免去许多非文学体制给它造成的无形压力。
在胡适的上述文章发表后十年,即1932~1934年,45岁的钱基博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开始反省胡适已经梳理过的文学史的脉络。与胡适不同的是,钱基博并没有把“现代中国文学史”叙述为“古文”走向末运和“白话文”走向新生的过程。他在为何而治文学史的解释中说,“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来”,“而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他批评“民国”建立以来出现的两种弊端,一是“执古”,二是“鹜外”。执古者食古不化,“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而“鹜外”者“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因此举凡“衡政论学,必准诸欧”,往往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可知他的立场介于二者之间。钱基博关于“现代”的概念也不同于后来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概念,他所限定的时间是1912年民国纪元开始到1930年这一段时间。但对何以没有用“民国文学史”而用“现代中国文学史”,他有一个简洁的界定和说明:“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⑤ 钱基博对政治上“不愿奉民国之正朔”这一现象给予理解,他认为,“政治认同”的障碍无妨文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因此,在他的书里,尽量兼顾“古文学”和“新文学”,实际上,对前者给了更大的篇幅。在上编的“古文学”中,“文”则分述王闿运、章炳麟、苏曼殊等人的“魏晋文”,马其昶、林纾等人的散文;“诗”则分论樊增祥、易顺鼎等人的“中晚唐”诗,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人的“宋诗”;“词”则介绍朱祖谋、况周颐等人的作品,“曲”则介绍王国维、吴梅等人的研究等;下编“新文学”,他则置小说于不顾,只谈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体”,严复、章士钊等人的“逻辑文”和胡适、黄远庸、周树人、徐志摩等人的“白话文”。这是一部独特的“现代文学史”,他叙述或构建出来的“秩序”,迥异于知识背景不同的胡适和其他各种“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
在以“新文学”命名的相关著述中,只有与钱基博的书几乎同时问世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才去关注白话文以前的“古文”甚至“八股文”。而周作人以“言志”和“载道”为两个主要潮流的起伏交替更新为线索,上溯至晚周、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的脉络梳理,特别是对清代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的清理,无非是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作铺垫,而周作人的著述与钱基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周作人最独特的地方,是对清代“制艺”(八股文)的解剖。他比较了八股文、古文、骈文和新文学这几种文学体制的差别:
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而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以形式和思想平重的。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而也是稍偏于形式方面。以感情和形式平重的,则是这时期以后的新文学。……后来反对桐城派和八股文,可走的路径,不走向骈文的路便走向新文学的路。而骈文在清代的势力,本极微弱,于是便只有走向新文学这方面了。⑥
他认为“新文学”的反叛都与八股文有内在的关联,这是因为八股文规则繁琐,形式复杂,从思想上到形式上,都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⑦ 周作人宣告了八股文整体的死亡,却又警告说,“它那一块一块的却活着”,它残留在汉字上,残留在长期的专制给人们的思想造成的奴性上,而且,还在新的洋八股上,比如“策论”这种文体,就是八股文的借尸还魂。⑧
钱基博的文学史著述是为大学教育所用的,⑨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最初也是为辅仁大学的学生所作的讲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知识建构的密切关系。这里,我们还要简略提及也是出现在30年代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这部著作,据作者的自序,也是为了应付他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新文学教学的需要而编成。⑩ 从王哲甫的这部著作开始,出现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上编“古文学”中的几乎所有作家(除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几乎都消失了。“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开始建立他的领地和秩序。王哲甫特别强调,“文学本没有新旧之别,所谓新文学的‘新’字,乃是重新估定价值的新,不是通常所谓新旧的‘新’”。(11) 他综合了胡适的历史观念论和“国语文学”说、陈独秀的“国民的”、“写实的”及“社会的”文学说、茅盾的“社会工具”及“平民文学”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说、胡行之的“死文学”与“活文学”说、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说、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说等等,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新文学”观念。王哲甫叙述出来的“新文学”运动史,以为该运动发动的“远因”是“民间文学的演进”、“佛教之传入”、“海禁开放后外来之刺激”、“废除科举”;其“近因”则是“西洋文化的输入”、“国语统一运动”、“留洋生的派遣”和“外国书籍之翻译”。他叙述了运动发生的经过,把15年来的中国文坛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至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第二期是1925年五卅惨案后至1933年作者写作的时候。看来,王哲甫没法像钱基博把“文学”的立场一以贯之地进行到底,他断代的方法,既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而这种既是“文学”,又是“政治”的思考,也许正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特征。
如果不把胡适的文章包括在内,那么以上三种“文学史”或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述,都恰好出现在1930年代初差不多同一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式大学教育,已经需要把当下的文学发展转化为教育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文学知识的资源。但从这些观点、视野、立场、知识背景都不太一样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著述,到底还是个人行为。如果需要考察这个时期的文学史有何“集体行动”的话,就需要特别提及1934年底由赵家璧策划主编、1935年10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10年(1917~1927)的理论和作品的选集,第一次由现代出版机构来组织、由参与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来亲自担任各个分卷的主编并以“导言”的形式对之作出梳理和总结的文学大系,丛书囊括了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散文、诗、戏剧和史料等新文学的各个方面。这种分类已经把新文学从传统文学中彻底划分了出来。
以上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新文学”发展到了1920~1930年代,已经开始稳步地纳入新的文学体制和文学秩序之中。如果说,胡适的文章还不算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催生的产物,那么,其他三种文学史实际上都与大学的文学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胡适的文章原是为纪念《申报》的诞生而写,“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是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影响下问世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与现代媒体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言自明。作为一种非常明显的“现代事件”,现代文学经由文学史叙述之后,已经被“制度化”了,与此相关,新的精英也从新的文学史秩序中诞生了。(12)
对这一新鲜年幼现代制度的诞生及其影响的评估,无论如何都不会显得过高,因为这是晚清以来一系列“新”思想——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之后——的制度化的必然结果。晚清在变乱的时局中构建起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0年,咸丰10年),专门负责翻译外国各类书籍的“同文馆”(1862年,同治元年),废除八股文(1901年,光绪27年),废除科举(1906年,光绪32年),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现代报纸和出版业的发达,各种学会、社团的建立,文学市场的形成,审查制度和出版法律的制定等等,无不有助于一个新的文学制度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这种“新的文学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我们看到了“作家”身份的戏剧性转换,譬如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身份的变化,使他们非常明显地区分于此前的晚清重要的作者,例如身兼政治家和文人的曾国藩和湘乡派,奔走于政客幕府的经今文学派的学者龚自珍、魏源,以及诸如冯桂芬之类的士人。在日本创办报纸的梁启超开始脱去其“逋臣”的身份,也不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效忠清王朝,而力图借助西方和东洋的新思想,重新建构“新”的国家认同,这个时候的梁启超既是现代报人,也是政治活动家、政论家,章太炎也是如此。他们都不像以前的士人那样流动于官僚的幕府之中,其人身和社会地位都不再依赖于旧有的体制(康有为的保皇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从摆脱幕府、政府、衙门的束缚而独立写作这点来看,在康梁流亡之前的王韬,就应该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作家。王韬出国旅游以及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都是个人行为,正由于这样,王韬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政论,才更具有启蒙性的“现代意义”。在王韬之后,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的身份开始转变,这种转变应以维新失败后的流亡为界限。
自由作家的出现与“文学市场”的形成,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人们一厢情愿的是“纯文学”问题。到了1930年代,这个过程就算是结束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被“新文学史”所叙述的,或者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作家们,都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作家”,这些史的论述和“大系”的编纂,使他们进入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文苑传”的新秩序,他们的作品有了被“经典化”的可能性。制度化之后的思想和秩序显然深刻影响到了对文学经验的解读和感受,有这个秩序和没有这个秩序,对他们的作品的意义的解读,对他们所提供的“现代文学经验”或“文学经验”的现代性的认知,是不太一样了。
1935年的赵家璧在这个新的文学体制和精英秩序构建之始,就表达了他充满希望的预言。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前言中说:
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时间,比起我国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来,当然短促值不得一提,可是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正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一切新的开始。它所结的果实,也许及不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盛美满,可是这一群先驱者们开辟荒芜的精神,至今还可以当做我们年青人的模范,而他们所产生的一点珍贵的作品,更是新文化史上的至宝。(13)
只要把这些作品当作“新文化史的至宝”来看待,就奠定了它区别于那些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典”作品的价值,这是“新文学”经由现代教育、出版、编辑、传播的方式被经典化的开端。
至此,我们已经有条件对我们所谓的“制度”概念再作一些解释。显然,它指的是各种“机构”的编制,这些机构的成立也是据“法”而行,譬如近代影响最大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乃是因事而立,而此“事”乃典型的现代性事件,迥异于古代的事。在总署下面成立的“同文馆”及其所具有的传播现代知识的功能,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因为它对西方诸国、东洋日本等新兴强国书籍的翻译研究,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文学观。从晚清到民国,官方的同文馆,民间新兴的书院(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书院),报馆,这三个制度化的机构,是三个很关键的“现代性思想制度传播”机构。
但这还只是我们所谓的“制度”的“硬件”部分,“制度”的“软件”部分,是使得“硬件”得以运行起来的关键。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形式的部分,即新的文学形式,包括语言变革和新的文体;二是内容的部分,包括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早期的官方知识分子(自“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传教士和民间知识分子(从崩溃了的“科举制度”中逃离的“革命派”和后来各种左翼、右翼的思想、政治派别)所传播的价值观念都属于这个范围。在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文章”体式的变迁。我们把“文章”也看作是一种制度,最典型的就是格式化的“八股文”,它是文言文的最典型的一种制度,因为撰写八股文,必须要遵守八股文所制定的内部标准。周作人写于1930年5月的《论八股文》说:“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14) 桐城派所制定的文章制度——“古文”也是一种“文章制度”。“最后的桐城派”严复、林纾,用桐城古文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作品,完成了一次“静悄悄”的革命。这次“革命”既让读者在现有的“制度”下最大可能地接触到了异域的思想,也促使人们起来打破他们所据以奠定英名的“制度”——因为那真实的异域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无法用桐城文章来表达。这是“五四”发起白话文运动的契机。因此,“白话文”运动就是一场在“文章”制度内的革命。采用白话文,并进一步完善白话文,才算是初步完成了这一场“革命”。
注释:
①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2页。
②王国维,前揭文,第2~3页。
③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④胡适,前揭文,第1~2页。
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9页。
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⑦周作人:《论八股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附录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⑧参见周作人写于1936年1月的《谈策论》,收入《风雨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2页。
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最早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出版,次年9月方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
⑩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自序”,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初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11)王哲甫,前揭书,第1章,第13页。
(12)本章不再花费篇幅去分析1949年以后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是,即使是个人化的文学史著述,1949年以后的同类文学史著作,已经基本自觉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导思想来分析1917年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13)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史大系》“前言”,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版。
(14)周作人:《看云集》,第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白话文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申报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王国维论文; 钱基博论文; 八股文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