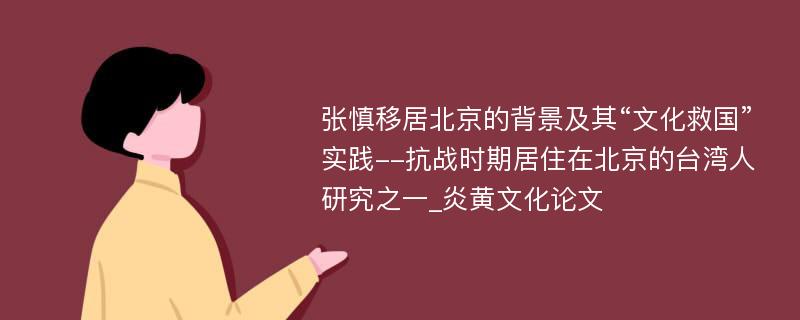
张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国”实践——抗战时期居京台籍文化人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文化人论文,深切论文,北京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2-0080-09
近代台湾被日本占领长达50年。这期间,台湾虽与祖国分离,但与大陆、特别是大陆的沦陷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使得在殖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文化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交叉纠结,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定性判断就能够厘清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考察日本侵华时期台湾人的文化认同,不能不注意到沦陷区背景。本文尝试在简析不同沦陷区特点的基础上,以台湾作家张深切在七七事变后从台湾移居北京之举为中心,对抗战时期沦陷区中国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作一历时的个案考察。
一、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三种殖民形态
日本19世纪末开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形成了一个个迥异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的独立区划。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语境各不相同。日本的殖民形式大体上分为台湾、东北和内地三种。台湾于1895年沦陷,实施日人直接统治的总督制。东北于1931年沦陷,1932年成立由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先后出任执政、皇帝的“满洲国”,在形式上既独立于日本也独立于中国。① 内地沦陷区域,1937年前后陆续成立由附逆的原中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国民政府(华中)等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以中国合法政府自居,企图僭越正统、混淆视听。
这三种殖民地域之间从政治到军事、经济、文化都是分离的,按“国”与“国”的关系行事,人员流动要办理“护照”。就日本最高决策者而言,这是分而治之的侵华殖民政策的结果。从日伪政权方面来说,各地的实权人物竭力维护各自的利益。从时局方面来说,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地方政权以及各种抗日力量的正面对抗和地下斗争持续不断,政局和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之中,日本殖民当局也无力把如此广阔的区域统一起来。体制上的这种新变化,使得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地的类型格局发生改变,大大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更使得不同沦陷区民众的身份认同生发出质的差异,对沦陷区的社会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了将占领区永远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同时,不懈地推行文化殖民,其中,用日语取代汉语的语言殖民在殖民同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如何坚守汉语、抵制普及国语(日语)、延续汉语书写本身,成为沦陷区作家对抗日本殖民同化的重要行为。在不同的沦陷区,日本实施语言殖民的力度各不相同。在各个沦陷区的不同时期,语言殖民的政策和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这种不同和变化给不同地区的生存环境带来改变,影响到沦陷区文化人的流向。台湾在实施42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公然废止中文,强行把日语定为“国语”,清洗和隔离中华文化。汉语表达形式退出主流。伪满洲国旨在最终割裂和脱离中国主体的文化控制,也在不断强化。日语读物的引进量和出版量逐年增加,很快超过汉语读物,大大缩小了中文的表达空间。② 而内地各沦陷区在名义上没有与中国分离,日本无法有效地实施文化和语言的殖民化,殖民统治相对薄弱。这样,或出于殖民当局宣传策略上的需要,或由于具有有限话语权的中国文化人的操守和智慧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内地沦陷区占压倒地位的奴化宣传中,中华文化仍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汉语一直是表达和书写的主流语言。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遗产在沦陷期延绵不绝,甚至依然是日伪官方的招牌。特别是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厚重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族群身份认同资源,仍具有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和感召力量。这是大批台湾、东北作家流向北京沦陷区的重要人文地缘条件。尽管是在日本占领区范围内流动,但对于那些感时忧国之士来说,来到北京已是“回归”和“寻根”之旅。③ 因此,对各沦陷区作家作品进行描述时,不宜简单地用“沦陷区/汉奸文学”模式一味作道德批判,而是需要从各地的实际状况出发,把考察对象,包括人与文两个方面,置于共时环境中作背景和文化身份认同取向的分析。
二、张深切早期的时代背景和经历
张深切(1904-1965),字南翔,笔名楚女、者也等。台湾南投人。在台湾、日本接受初等、中等教育。1923年首次来到祖国大陆。
身处沦陷区的中国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民族国家认同,即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所谓文化身份,系指建立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和集体记忆基础上的民族文化特征,主要包括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等方面。文化不同,文化身份也就不同。在常态下,文化身份是相对稳定的。而旨在灭亡中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沦陷区异质文化间突发性的全方位杂处和错位,中国作家的现实身份危机,对其文化身份造成巨大冲击。身份危机感的指向和程度,与入侵者殖民统治的力度和长度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一方面,或出于本能或出于自觉,中国作家竭力维系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抵御被外来殖民者文化淹没的可能和危险;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违心地屈就于既存殖民文化体制。两种不同文化的种种因素常常集于一身。两者之间会有交叉,但更多的是抵触与冲突。由于中国各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存在着悬殊的差异,这就为一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能在沦陷区域内追寻最佳文化身份认同场所的中国作家,提供了选择。而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状况,往往对他们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中所达到的高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台湾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建立起面向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两个不同教育系统。台湾人就读的公学校削减知识教育,以学习所谓国语即日语为主,在校园内严禁讲汉语,六年的课程量低于日本人就读的小学校五年的课程量。这样,台湾中国人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难度要比日本人学生大得多,从而确保了日本人和日本语言文化的支配地位。④ 台湾传统的启蒙教育形式汉文书房,即学习中文、阅读古典文学的私塾,则游离于正规的初等教育系统之外,逐步萎缩。张深切出生时,台湾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近十年。他于1913年入公学校,接受日式教育。1917年因在校期间违规说汉语被告发,受到留校清扫的处罚。对此,时年14岁的张深切反应强烈,矛头直指日本的语言殖民:“我知道为什么不能讲台湾话的理由了,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的领土,所以我们要受他们管。将来要是我们征服了日本,拿日本来做殖民地的时候,我们不但禁止日本人在校里讲日本话,连在学校外面也非禁止不可!”⑤ 由于坚持台湾人讲台湾话是台湾人的权利,张深切最终被校方开除。家里安排他去了日本,转传通院砾川小学校继续读五年级。毕业后先后进入丰山中学、东京府立化学工业学校、青山学院中学部学习。反抗语言殖民的结果,反而是提前进入日本本土,在宗主国接受教育。这看似颇具反讽意味。其实不然。
日本文化既是灭绝中华文化的殖民文化,也是日据时期台湾人了解世界的高位文化,而且几乎是当时台湾与外界沟通的主要的跨文化通道。正是台湾、日本之间的这种殖民地/宗主国关系,使得日本成为台湾青年深造的最便捷的流向之一:语言、文化以及手续上的障碍少一些。张深切在日本的六年,正值大正民主时期。日本西化后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他对日本产生好感和崇拜,逐渐淡忘了自己的炎黄子孙身份:“觉悟我应该做日本国民,说日本话,读日本书,学习日本人的民情风俗习惯。”⑥ 另一方面,深入接触日本先进文化的结果,激发了台湾留学生的民族解放意识和变革图强热情;殖民地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反而肇始于与外界和大陆的接触机会更多的宗主国日本。⑦ 《台湾青年》、《台湾民报》等先后在东京问世。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张深切在日本期间萌生了革命思想,同时也结识了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留日台湾青年,为重新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命运做了准备。
偶然契机对张深切的人生轨迹产生影响。有一次,他因击剑与日本老师发生龃龉。老师那“支那人”、“清国奴”的辱骂,唤醒了他在台湾曾被开除学籍、曾被唤作“清国奴”的少年记忆,痛切地感受到亡国之民的悲哀:“你既然是亡国奴,你就是征服者的奴隶,无论你有什么经天纬地的绝才,或出类拔萃的学识,都没有用。亡国奴不应该和有国家的国民平等,奴隶不应该和主人站在同一的地位,一希望要平等,一想要同一地位,就是叛逆。”⑧ 而使他获得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一认识的媒介,恰恰是他在日本中学里学习的东洋史课程:
我读了祖国的历史,好像见着了未曾见面的亲生父母,血液为之沸腾,漠然的民族意识,变为鲜明的民族思想。⑨
民族屈辱和民族认同的结合,使张深切认识到,只有中国强大才能改变台湾人的亡国奴地位。于是,他中止了在日本的断断续续的学业,决心回归母体。
这是台湾许多先觉青年所经历过的心路历程。1920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成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新思潮的风行,以及台湾中国人以推进文化启蒙为目的的文学社团活动的蓬勃开展,促使关心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求学,特别是国际都市上海、国民革命重镇广州、文化古城北京、海峡对岸的厦门。据有关统计,早期台湾中国人赴日留学以接受中等教育为主,1918年以后,进入大专以上院校的比率逐年增加,到1934年,已超过半数。以留日为主流的台湾海外教育所培养的知识分子,在人数上超过台岛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的六倍以上。⑩ 其中的进步分子,在经历了痛苦的中国——日本——中国文化认同转换过程之后,即迷失于日本帝国文化,感受到低人一等的切肤之辱,和确立起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之后,往往成为坚持民族自主权的反日人士,张深切就是其中之一。
1923年张深切来到上海。第二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国语师范学校学习,并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加入台湾自治协会,组织炎峰青年会演剧团。1926年经商失败后,转往广州,担任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委员。第二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法科政治系。担任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宣传部长。同年回台湾,因涉嫌鼓动台中一中罢课遭拘捕,后因“广东事件”最终被惩役两年。1930年,组织台湾演剧研究会。1934年担任《台中新报》记者兼编辑。在同年召开的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举为委员长,创办并主编《台湾文艺》杂志(第二年停刊)。他创作的小说《鸭母》和剧本《落荫》,是台湾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在实际参与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社会运动之后,张深切进一步确立了国家民族高于主义思想的信念,决心作一个“孤独的”斗士,“去和真实为国家民族尽力的人共同奋斗”。(11)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深切只身从台湾来到北京定居,正是身体力行这一信念。
三、促使张深切移居北京的环境因素
1938年3月,张深切移居被日本占领的北京,促使张深切来到北京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环境方面的因素是,台湾的殖民体制发生重大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割占中国的澎湖列岛和台湾。日本帝国政府在台湾设立总督府,从法律上规定,台湾总督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直接实施独裁制的总督统治。到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查禁汉文书房,(12) 禁止台语广播,禁演台湾戏剧,推广上演所谓的“改良戏”即使用日语的戏剧节目。9月,又根据日本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施行“皇民化运动”:给台湾人强加上日本国籍,把日语定为“国语”,开展要求台湾人学习日语的“国语普及运动”,不但学校、机关禁用汉文,就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要使用日语,企图借此使“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台内一如’的境地”,(13) 把台湾人改造成“顺良日本人”,变成与日本“利害与共的日本国民”。“皇民化”是日本对华同化政策中最具杀伤力的举措。其直接结果是,台湾人同日本人一样,受制于日本《国民总动员法》(1938)和《国民征用令》(1939),台湾人入伍编入日本军队。
从长远来看,“皇民化运动”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灭绝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代之以日本文化。其表象是改变语言习惯和接受日人身份,其深层影响是动摇台湾人的汉(中华)民族意识。皇民化及日语普及运动进一步压制台湾本土文化,使台湾新文学进入凋零期。此外,张深切回台后虽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一直受到专门对付思想犯的特别高等警察的监视。七七事变后,台湾殖民当局取缔台湾人文化活动的趋向日趋强化,进一步限制了张深切的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所有这些,使得张深切失却了作为一个民族作家的活动空间,加剧了他的身份危机意识。离开台湾成为张深切摆脱行动和思想双重困境的最佳选择。
促使张深切移居北京的第二个环境方面的因素是,北京发生了剧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仅使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1937年7月29日,日军进入北京城,立即组织成立治安维持会,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6日,伪“北平市政府”成立,江朝宗任市长。从即日起,感到回天无望的北京数万名大学师生开始陆续经天津转往内地。随着机构和人员的撤离,历时二十多年的北京新文化活动戛然而止。北京一沦陷,日本方面立即实施分裂中国,对华北进行殖民统治的方案。1937年12月14日,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出笼,辖北平、天津、青岛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汤尔和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之后,既是“翼赞”华北伪政权的“教化”机构,又是实施各项政令的政治团体新民会,迅即于24日成立,并在北京设立中央指导部。次年1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从天津迁至北京。5月4日,成立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操纵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殖民统治体制基本确立。内地大片领土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这种局面,张深切深感忧虑:“眼见日军在大陆的占领区日日扩大,身为汉民族的一员,殊难忍看江山沉沦。”在他看来,家乡台湾的命运是与大陆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14) 张深切到过南京、苏州、厦门、广州、北京等内地许多地方,对于大陆种种落后、愚昧以及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深感失望和伤心,但对于集中体现中国和中国传统的北京则一往情深:一看到紫禁城,不禁“触景热血沸腾,流出激动的眼泪。”(15) 在张深切的心中,北京是中国的象征。救北京即救中国,救中国(大陆)即救台湾。于是,他抱着“到沦陷区尽点义务”的决心,办好护照来到被日本占领的文化古城北京,实施他的文化救国理念。
促使张深切移居北京的第三个环境方面的因素是,在中国各沦陷区域中,北京沦陷区的就业状况相对好一些。
随着“皇民化”的实施,台岛的就业机会日益不足、子女的教育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日益明显。躲避日军兵役也是台湾役龄人很现实的考虑。因此,离开台湾到内地求发展,成为一些有条件的文化人的选择。当华北战局基本稳定之后,北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很快运转起来。(16) 由于七七事变前后大批北京人躲避兵灾出走,北京的专业人员缺乏。以报刊为例,随着第一种官办报纸《新民报》(1938年1月1日)和第一家民办杂志《沙漠画报》(4月16日)的创刊,华北的报刊呈兴盛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10月,杂志已有五十余种,1940年底,近七十种,1941年为高峰期,多达一百余种。各级学校教育或仍在继续或很快恢复。同时,殖民统治刺激了对日语的需求。这就为文化人、特别是懂日文的文化人提供了在北京就业的机会。台湾人1937年后变成日本国籍,在日本统治的区域内流动相对容易一些。他们一般熟悉中日两种文化,能熟练运用日语,在北京谋生较为容易。除在各文教机构任职外,他们多经商和行医。其中,文化界最知名者除在北京居住有年的张我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洪炎秋(北京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柯政和(北师大音乐系主任)、林海音等外,(17) 就是北京沦陷后来京的张深切、江文也(著名作曲家,艺专和北师大音乐系教授)、郭柏川(艺专美术系教授)、张秋海(北师大美术系教授)、林朝权(北师大体育系主任)、林朝棨(北师大地质系教授,林朝权之弟)、郭德钦(艺专)、王庆勋(北师大教授,中华口琴会创始人)、萧正谊(燕京大学教授)、苏子蘅(北京大学理工学院副教授,几年前逝世的前台盟中央主席)、徐牧生(北大法学院副教授)等。
四、在北京实践“文化救国”
1938年3月,台籍张深切从台湾移居北京。北京时期的张深切开展弘扬中华文化的活动,为华北地区文坛从死寂到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有理想、有奋斗、有挫折,也遭遇到被处死的威胁,在北京沦陷区留下了一个不屈服的反日志士的奋斗痕迹。
沦陷时期,居京台湾人的身份是“日本帝国臣民”,由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监督管理。(18)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1940年出版的《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一书,附有“文化学术界名人录”。其中,台湾人既没有归入“日人之部”,也没有单列,而是将他们的籍贯改写成内地,与其他内地人按姓氏笔画混编。比如“张深切”条称:“福建漳县人,现年三十五岁,广东中山大学法政科政治部毕业,曾任大阪朝日调查部记者,东亚新报编辑长,江南正报文艺部主任,现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员兼训育组主任,担任日文课程。”(19) 江文也、柯政和、郭柏川、张我军、洪槱(洪炎秋)等其他台湾人,也是这样处理的。“日人之部”、“满人之部”、“欧美人之部”则单列。“满人之部”反而排在“日人之部”的后面。列入所谓“满人之部”的,是些原籍东北的北京人,如王静远、溥心畬等。该书编者之一武田熙在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任调查官。(20) 显然,北京日本殖民当局刻意找出一些在东北出生的人士,把他们当作“满洲国”在京侨民看待,以宣示东北是独立“国家”这个既成事实。对于台湾人,则有意遮掩他们的台湾人身份。因此,居京台湾人表面上是中国人,内里被当作日本人来管理。张深切就是在这种境遇中开始他在北京的生活的。
在谋生职业方面,张深切起初任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1939年10月间,因奔父丧短期返台。(21) 1940年8月,张深切被迫退出他一手创办的中国文艺社。(22) 此后,他辞去艺术专科学校的教职,携眷返台。在台湾,日本宪兵仍对张深切防范有加。他不得不再次从台湾移居北京,经由原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同事桥川时雄(23) 的介绍,在新民印书馆谋得编辑一职。在筹办由新民印书馆出版的《艺文杂志》(1943年7月创刊)的过程中,张深切在刊物主编权的问题上与来防的日本文学者报国会代表林房雄、北大教授沈启无闹翻,引起伪政权高官周作人的误会和不满。(24) 从个人前途考虑,张深切退出了艺文杂志社,并辞去新民印书馆编辑一职,与北京文坛彻底疏离,被迫终结了在北京殖民地展开的文化救国之旅。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曾通令北京各文教机关不得录用张深切。在沦陷期最后两年,他转而经商。(25)
张深切一如既往地热心社会活动,关注在京台湾人的生存状态。1939年11月,他担任台人旅平同乡会会长。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加快扩军步伐。他利用会长身份竭力阻挠日军征用华北台湾人参战。1945年4月,终因涉嫌反日活动遭逮捕,并以颠覆罪被判处死刑,后由于日本战败才得以幸免。(26) 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协助滞留北京的台籍日本军人返台。第二年,他本人也举家返台,离开了他奋斗、生活了八年的北京城。
张深切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创办并主编大型月刊《中国文艺》(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参与筹办中国文化振兴会并担任常任理事(1942年1月)。(27) 在著述方面,著有《日本语要领》(1941),编译有《现代日本短篇名作集》(1942),收他翻译的《秋》(横光利一)以及洪芸苏、张我军、苏民生、尤炳圻、张绍昌五人的译品五篇,均由新民印书馆出版。此外,还编有《儿童新文库》四册(1941)、《十三作家短篇名作集》(1942年7月)等,也是新民印书馆印行的。后者所收作品均选自他任主编时期的《中国文艺》,并特别标出由中国文化振兴会出版。
初到北京,有感于殖民统治下北京文化界的颓废与媚日,(28) 张深切决心以文化扶正压邪。在新结识的华北最高指挥部参谋堂胁光雄中佐的帮助下,他得以成功创办《中国文艺》,由民营人人书店总代销。他明确提出四项办刊要求:编辑方针和内容不受任何干涉;杂志里绝对不刊登任何宣传标语;保持纯文艺杂志的形态,不作主义思想的宣传;不加入其他新闻杂志社结成的团体做政治活动。急于让北京尽快恢复正常的堂胁光雄予以认可。这样,就使得《中国文艺》在殖民环境中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与此同时,张深切还积极谋划组织类似台湾文艺联盟那样的文艺团体,但未获准。他特意公开说明:“因有事情决定展期”。(29)
在《中国文艺》创刊号上,张深切大胆表露抗日救国精神:“吾人不怕国家的变革,只怕人心的死灭,苟人心不死,何愁国家的命脉会至于危险,民族会至于沦亡?”(30) 他的挽救国家之道,是坚守和高扬民族文化:
国可破,党可灭,恶可除,文化不可灭亡也。我们可以一日无国家,不可一日无文化,因为文化是国家的命脉,是人类的精神食粮。
因此,该刊的《创刊词》回避伪政权的宣传方针,大谈文化。张深切特别指出,欧洲各国各民族接触繁密,文化发展快,而“我国屹立于东亚,且其环居的民族,因文化较为低劣,虽有接触的机会,却未得有利于模仿的条件,遂造成中国文化落后的最大原因”。对中国旧文化进行“研究、整理、批评、淘汰、拔萃并将其系统接合于新文化”,这样“才能展开其新生面,同时也才能保持其绵远的生命。”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日本文化优越论,即,大和民族是“天之子孙”,高于其他民族,日本文化以“言灵”为中心,优于其他民族文化。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张深切公然把日本鼓吹的“东方唯一的高文化”——“大和民族”文化归入“低劣”之列。这显然是在抵制日本的殖民文化政策和宣传纲领,反映出编者意在通过完善中国文化而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立场。
此外,尽管张深切本人对沦陷区文化界的颓靡状态忧心忡忡,但对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学的贬损,却不以为然:“据说最近我国的文艺都带有一种淫逸性和颓废的趋向,这是日本的评论家给我们的一个冷烈的批评,我们虽然不愿意否定他们的见解,但是这无疑的是一鳞片的皮相之见,还未可以说是看透了我们的实在情态”。这不可不谓针锋相对了。于是,在创刊号中,出现了署名木活的文言短文《记梦》:
有大平原,积雪没胫。四望无垠,惟余独处。忽见骏马狂奔,猛不可当。虑其猝然触己,急思趋避。俄而马失所在,徐前查之,见坑深数仞,坑底有水,而马已仰卧波间矣。余深冀其翻然决起,而挽救乏术。方焦灼间,己身已危。盖余坐石之一端,石已徐徐有倾坠坑下之势,他端且翘起。殆哉,余之命运也。是时一碧眼高颧之人,立余旁,状甚闲逸。余处此危局,已千钧一发,身莫敢动,口不能言,意其必能稍加援乎也,以目示意者再,而竟不获一顾。惶怵汗下,始觉为梦。石冥山人曰,马之肆行无忌,宜其危矣。余之仰仗他人,亦必殆也。以小喻大,可不惧哉,可不勉哉。
编者在编后记还特别强调该文“文短意长,颇耐玩味”。如果把文中的“马”和梦者看作中国军民,把“碧眼高颧之人”看作欧美列强,那么,作者、编者意在提醒中国人在挽救国家的斗争中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文艺》历时一年、出满两卷后,张深切自己突然宣布:“我要离开‘中国文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如果一言以蔽之,即曰思无邪而已……我没有私心,只感觉力量不足,就把这个事业让给人家了。”(31) 这一变故的起因,是有人向殖民当局密告,《中国文艺》的内容违反了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此时,堂胁光雄已调回东京参谋总部。统管华北出版界事务的日人山家亨强迫张深切辞去《中国文艺》主编一职,由武德报社接管。(32) 从3卷1期(1940年9月)开始,主编易人。张深切一年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一打击异常沉重。(33)
张深切主编时期的《中国文艺》,主要刊登文学,包括小说、散文、短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艺术,包括绘画、电影、戏剧、音乐以及艺术理论、漫画作品;杂俎,包括科学新闻、名人传记、生活常识、学术界艺术界动态以及读者通讯等。尽管内容庞杂,但公开配合日伪宣传的文字比较少。作品以阐扬中华文化为主,如周作人的《汉文学的传统》(2卷3期)、《关于阿Q》(2卷1期)、《记蔡孑民先生的事》(2卷2期),谢刚主的《明季释乘传记题跋》(创刊号)、《太平天国时代之文人生活》(1卷3期)、《书境》(1卷5期),蒋兆和的《阿桂与阿Q》(2卷2期)、《自述拙作》(1卷2期),石挥的《为什么在现社会下演〈日出〉》(1卷6期)等文章,谈史说文,各有特点。一些青年作者如程心枌、王石子、张金寿、毕基初、曹原、林栖、芦沙、侯北子、孙羽(孙道临)、公孙嬿、慕容慧文、吴兴华、何漫、白金等,有些后来颇有文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中共地下活动的毕基初,他的小说《青龙剑》,公开颂扬用鲜血和生命伸张民族“大义”,就发表在2卷3期上。至于文学评论,其中有不少文章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艺术家为批评对象,包括鲁迅(《鲁迅的印象》,1卷3期;《鲁迅和梦》,1卷5期)、曹禺(《曹禺的三部曲及其演出》,1卷2期;《评曹禺的〈原野〉》,1卷3期;《〈雷雨〉的年龄问题》,2卷4期)、老舍(《谈老舍作风的由来和美点》,1卷4期;《评〈骆驼祥子〉》,1卷6期)以及茅盾、巴金、张天翼、王独清、卞之琳、萧乾、徐懋庸、蒋兆和、朱湘、陈梦家等(2卷1期、2期、3期、5期,1卷4期、5期),孜孜于中国新文学遗产的整理和阐扬。这表明,张深切时期的《中国文艺》坚守了他身体力行文化救国的初衷。(34)
北京时期的张深切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弘扬中华文化的活动,为华北地区文坛从死寂到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试图重返《中国文艺》未果,由他主编新刊物《艺文杂志》的计划又落空。他不向当局妥协,转而经商,赔钱失业在家。他仍坚持写作,发表了一批论述哲学的文章。(35) 尽管他对时局存有模糊的认识,(36) 但总的来说,他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明确,并具有大无畏的实践精神,利用自己的台湾人的身份,在北京沦陷区留下了一个不屈服的反日志士有理想也有挫折的奋斗痕迹。张深切无疑是了解近代台湾人文化身份认同状况的一个窗口。
注释:
①1937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由多个伪政权合并而成的“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它同后来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一样,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伪国民政府。就日本殖民当局而言,实际上更想以满洲国的模式来控制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②到1941年,日本向满洲国出口图书达3440万册,超过该年度东北中文图书出版量的总和。东北本土的出版情况更糟。以1941年7月份为例,出版日文图书112种,中文仅6种。参见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③比如东北作家梁山丁回忆说,他是打通关系办理了“出国证”才得以于1943年年9月30日乘夜车离开东北,到达北京的。对于身为“满洲国”国民的山丁来说,置身于北京,使他有了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情绪”。山丁1991年6月25日致笔者的信。
④见黄大受《台湾史纲》,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251至255页;杨碧川《简明台湾史》,高雄:第一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⑤参见张深切《里程碑(上)》,《张深切全集》第1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81页。张深切的自传《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阳》,曾于1961年12月分4册由台中圣工出版社出版。
⑥(11)参见张深切《我与我的思想》,《张深切全集》第3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73页,第79页。
⑦比如,中国留学生较为集中的寄宿地高砂寮,聚集了一群台湾有为青年。他们经常组织集会演讲、抗议示威等活动,高砂寮因此被视为“台湾文化运动摇篮”。张深切曾是那里的激进分子之一。
⑧参见张深切《里程碑(下)》,《张深切全集》第2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76页。
⑨张深切《里程碑(上)》,《张深切全集》第1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⑩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118-125页。
(12)书房即汉文私塾。它是台湾传统的启蒙教育形式,在学习中文、接触古典文学、传播汉文化和中国人认同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张我军,就受益于早年的书房教育。
(13)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14)(15)张深切《里程碑(下)》,《张深切全集》第2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632-633页,642页。
(16)作家冰心形象记述了这一转折过程。沦陷初期,在故宫、北海、颐和园,作家冰心“只听见橐橐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恨得溜走了。”可不久却发现,“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了木门,挂上了布帘,无线电里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冰心《回忆“七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纪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17)对于40年代前期北京的台湾人之多,后来成名的林海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1959年10月23日致钟理和的信中说:“您曾旅居北平,是客家人,就给我更多的亲切感。因为我想,在北平应当是我认识的,但是您来信说的时期是民国30年至36年,那时本省人到北平去的非常非常之多,而那时我已结婚,不在妈妈面前,就少见到许多同乡了。”见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第7章《联副十年》,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0年版。
(18)兴亚院成立于1939年3月11日,隶属日本内阁,在各个日本占领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统筹以“建设新东亚秩序”为招牌的殖民事宜。1942年11月1日,日本成立取代兴亚院的大东亚省。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遂解散。
(19)李文裿、武田熙合编《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北京:新民印书馆,1940年版。第329页。
(20)在出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官之前,武田熙供职于“军特务部文教室”,是谙熟北京文教界的中国通。见安藤德器编《北京文化便览》,东京:生活社,1938年版。第4页。
(21)张深切短期离开北京期间,曾委托张我军代他编一期《中国文艺》。见张我军《代庖者语》,《中国文艺》1卷3期(1930年11月1日)。
(22)对于这个事件的内幕,洪炎秋的回忆文章有记载:“后来经人告密,认为该志时有违碍的文字出现,迹近‘反动’,张君屡被传讯,终于为敌军的报道部所查封,派由他们的武德报社接收续办……”洪炎秋《闲人闲话·小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3页。
(23)桥川时雄当时是东方文化事业会的成员。见安藤德器编《北京文化便览》,东京:生活社,1938年版。第4页。
(24)周作人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时间虽不长,只有两年多(1940年12月19日到1943年2月4日),但一直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11日,汪精卫又增补他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
(25)张深切回忆说:“日人当然重视周而不重视我”,“若不及时躲开,只有付出重大牺牲,断送自己的前途。”见张深切《里程碑(下)》,见《张深切全集》第2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724页。
(26)转引自E.Gunn,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276.
(27)这里提请注意,诸如“中国文艺”、“中国文化振兴会”这样的文化指向明确的语汇,在台湾和东北都是“非法”的,但在日本人控制的内地沦陷区,则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原因参见如本文第一节的简述。造成这一差别的语境因素,在沦陷区研究中是不容忽略的。
(28)初到北京的张深切,对北京文化界的印象是:“已陷于极端纷乱,满目尽是淫书、桃色新闻,和颓唐悲观的论调;所有言论若不是谄媚日本,便是赞扬新民主主义的八股文章。汉奸、流氓、地痞藉日本势力乘机打劫,横行无忌;下流的政客跳梁跋扈,卖身卖国,恬不知耻;陷害忠良,压迫百姓,习以为常。恐怖空气笼罩着故都,这是内地后方所不能想象的悲惨情形。”参见《张深切与他的时代(影集)》,《张深切全集》第12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139页。
(29)《中国文艺》1卷4期(1939年12月)。第88页。
(30)张深切《编后记》,《中国文艺》1卷1期(1939年9月)。
(31)者也《废言废语》,《中国文艺》2卷6期(1940年8月)。同期的《编后记》重申,原先的一系列计划,“却为了社务变更的关系,结果,都变成了幻想而归于泡影了。对这些事情,我现在无心辩解,只愿率直地说一句——我已无力维持下去了。”
(32)对于这个事件的内幕,洪炎秋的回忆文章有记载:“后来经人告密,认为该志时有违碍的文字出现,迹近‘反动’,张君屡被传讯,终于为敌军的报道部所查封,派由他们的武德报社接收续办……”。洪炎秋《闲人闲话·小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3页。
(33)张深切在回忆录里写道:“断送了《中国文艺》这部杂志,我比受任何打击还要难过。”“我未尝受过这么大的侮辱,咬紧牙根忍着,怅然退出……山家这家伙,竟视中国人不如殖民地人民,殊堪痛恨。”见张深切《里程碑(下)》,见《张深切全集》第2卷,台北:文经社,1998年版。第688页。
(34)局外人和后来者不知晓张深切在北京进行文化反抗的危险,也不理解其文化身份认同历程的艰难,对他编的刊物多有误解。比如,有台湾学者将其界定为文化汉奸、落水作家:“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他以者也的笔名,在每一期的‘随便谈谈’和‘编后记’里,都有替敌伪政策宣传的话,可见他是时时刻刻在为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做工作的。”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73页。
(35)如在《华文大阪每日》上发表了《点、线、面的关系》(10卷6期,1943年3月15日)、《理性与批判》(10卷12期,1943年6月15日)、《中国哲学的线路——老子哲学概论》(13卷5期,1945年5月)等。
(36)比如张深切认为,对于战争的性质,“现在已无议论的余地”。见《卷头言》,《中国文艺》1卷第2期(1939年10月)。还说过不必“执拗抗战彻底”,相信“和平是建国的唯一方略。”见《战争与和平》,《中国文艺》2卷3期(1940年5月)。历史地看,北京沦陷区言说的自由度毕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长期置身于沦陷区一隅,无疑也会使人们的视野受到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