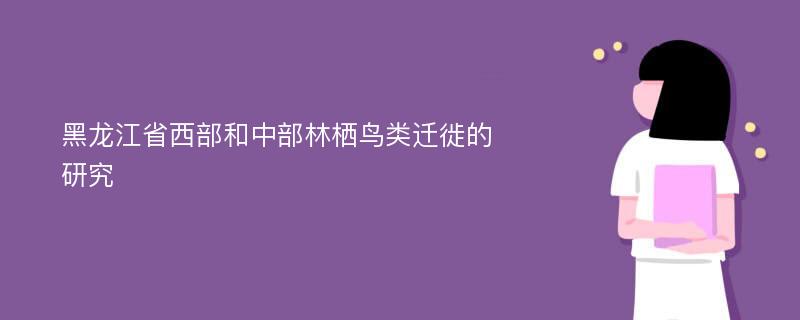
郭玉民[1]2002年在《黑龙江省西部和中部林栖鸟类迁徙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西部高峰鸟站(49°06′N,125°15′E)和中部帽儿山鸟站(45°25′N,127°34′E)两个环志站的环志数据的整理和总结,对两地的林栖鸟类迁徙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工作时间为每年春季在2月末到5月末、秋季从8月末到11月末鸟类迁徙期。每年工作时间约6个月。本文以新近的2001年的数据作重点进行分析。当年其环忐了142种、61443只。实验结果如下: (1)环志的非雀形目种类中雀鹰(Accipiter nisus)和松雀鹰(A.virgatus)在西部远多于中部,这与两地的开阔程度和植被密度相关。在西部同于在捕食上的竞争,春季雀鹰比松雀鹰早到30天。当松雀鹰迁到时雀鹰迁徙已近结束。秋季由于食物远比春季丰富,雀鹰和松雀鹰则同期出现。可见食物直接影响它们的迁徙时间和次序。 (2)蓝尾鸲(rarsiger cyanurus)在所有的鸲类中数量最多,但回收个体极少,说明其种群基数较大且平均寿命较短。此外,原地回收率也较低,这可能与蓝尾鸲不在环志地繁殖有关。 (3)柳莺属(Phylloscopus sp.)鸟类迁到时间较晚、迁离时间较早,这恰与当地的植物物候期和气温等因素一致。归根结底还是纬度不同造成的。 (4)鹀亚科的鸟类是迁徙鸟类中最多的类群。两地在鹀亚科鸟类构成上大体相似,但数量上差异极大。在中部以黄喉鹀(Emberiza elegans)、灰头鹀(E.spodocephnla)和白眉鹀(E.tristrami)为主。西部则以小鹀(E.pusilla)、栗鹀(E.rutila)和黄眉鹀(E.chrysophrys)为主。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繁殖地、越冬地有差异,从而导致迁徙路线的差异。田鹀(E.rustica)在两地都较多。栗耳鹀(E.fucata)、叁道眉草鹀(E.cioides)以及白头鹀(E.leucocephala)在两地都比较少见。此外,环志地点的生境不同也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 (5)两地物候期的差异一般在3-15天左右。早春和晚秋差异大,晚春和早秋差异小。 (6)通过实验数据和相关资料的总结,提出关于迁徙鸟类的两个假说“屏障回避假说”和“栖址优选假说” (7)在2000-2002年的环志过程中,在西部的高峰鸟站获得红腹红尾鸲(Phoenicurus ervthrogaster)、褐岩鹨(Prunella fulvescens)、极北朱顶雀(Carduelis hornemanni)、黄鹀(Emheriza citrinella)和栗头鹟莺(Soicercus castaniceps)等5种黑龙江省鸟类新分布种。此外尚有一种鹨和一种伯劳正在鉴定之中。这些新分布多为蒙新区物种,而高峰鸟站恰处于东北区靠近蒙新区的边缘。这里可能还将发现区系上更多的渗透。
郭玉民, 常家传, 刘晓龙[2]2000年在《黑龙江省东部和西部春季林栖雀形目迁徙鸟类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8年和1999年的两个春季,我们分别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和西部两个环志站点,共环志鸟类71种,6882只.通过比较分析表明:东部林栖雀形目迁徙鸟类种类组成的多样性远大于西部;东部与西部迁徙鸟类的主体上有明显差别:东部以黄喉鹀及灰头鹀为主,西部以小鹀和黄眉鹀为主;一些鸟类的始见日在两地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正反映了两地物候上的差异.
肖静[3]2004年在《我国重要珍稀濒危物种与类群的地理分布格局及保护现状评价》文中提出本研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构建了我国重要珍稀濒危物种与类群(大熊猫、朱鹮、虎、金丝猴、藏羚羊、扬子鳄、亚洲象、长臂猿、麝、普氏原羚、野生鹿类、鹤类、野生雉类、兰科植物、苏铁)的空间分布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物种与类群的地理分布特征,并按科、属、种不同层次的分类阶元提取了这15物种与类群在全国的主要地理分布中心。结合人口、气温、海拔等人文和自然因素探讨了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从保护现状、保护全面性、保护有效性和保护空缺四方面评价了各类群目前的保护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15物种与类群的地理分布中心主要在横断山区,秦岭山地和西双版纳地区,这与全国热点地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影响这些物种分布的主要因素包括地质过程、地形气候条件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横断山区在第四世纪基本无大面积冰川,又未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剧烈影响,人类干扰相对较少,成为这些物种的“避难所”。西双版纳境内丘陵,发育与保存了季节性雨林和山地常绿阔叶林,为树栖类物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秦岭山地在动物和植物区系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是兰科植物、大熊猫、金丝猴和朱鹮的主要分布区。 2.15物种与类群的分布呈现局部分布和间断分布特征。15物种与类群中有不少是局限性分布的特有种,如大熊猫、四川山鹧鸪、普氏原羚和多数兰科植物,呈间断分布的有扬子鳄、金丝猴、白冠长尾雉、攀枝花苏铁和闽粤苏铁。 3.从物种保护来看,35.77%物种没有得到保护,主要集中在兰科植物、苏铁和雉科。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四:(1)我国目前对于这叁大类群的野外考察活动开展较少,其分布地和数量还不清楚。(2)我国是世界上这叁大类群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国家,但是对这叁大类群的法律保护体系却不完善。(3)兰科植物和稚类在我国的分布较为广泛。(4)我国苏铁新物种不断发现,新分布不断记录。 4.从保护区域来看,67.94%分布区没有得到保护。这些空白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南部的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和广西,东北部的黑龙江。除黑龙江、广西和贵州外,这些空白区域位于这15物种与类群的地理分布中心。 5.从保护的全面性来看,大熊猫、扬子鳄和亚洲象的保护现状较好,而兰科和苏铁类的保护现状较差。从保护的有效性来看,每个类群的制约因素不同,管理人员的素质为共同的制约因素,全国涉及到这15物种与类群的自然保护区中专业管理人员只占5.46%。其次是有效保护面积,有效保护面积仅为保护总面积的33.33%。 6.为了加强对于这15物种与类群的保护,建议采取如下对策:新建和扩建一批自然保护区,主要集中在15物种与类群的地理分布中心横断山区、秦岭山地和西双版纳地区,优先考虑四川、云南、西藏这些物种多样性高,分布点多而保护空白区也多的地区;加快尚未受到保护的7属44种物种的保护,尤其是兰科、苏铁和雉类。对于兰科和苏铁,由于它们的分布呈零星状,数量少,可以先建立保护站或自然保护小区;加强已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侧重于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加紧保护区的规划,扩大核心区的面积。
汤卓炜[4]200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西南部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地关系发展阶段的量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环境考古的视角,通过大量古环境、考古学研究资料的环境考古信息提取,经过系统归纳总结、对比分析,以定量、半定量的创新性量化研究方法开展了有重要考古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东北地区西南部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地关系发展阶段的环境考古研究,并获得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趋势推动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考古学领域的密切结合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环境考古学,它在解决现代考古学有关古代人地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考古学问题中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考古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既有利于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也将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地关系哲学反思的启示。人地关系发展阶段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以气候条件为主的环境较明显变化,人类自然属性的降低与社会属性的提高主要以技术进步为前提,以资源环境作保障。人类所处生存环境的低压态势是诱发人类通过文化适应获得进步的动因。人地关系发展阶段量化研究有力地推动环境考古学的进步。古环境评价具有考古学意义和实际研究工作的可操作性。可视化研究成果的展示将有利于揭示更多环境考古现象和规律。建立在人地关系量化研究、古环境质量评价和可视化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遗址预测更具有科学性,将很好地服务于区域考古调查与研究。考古学文化及其地方类型的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环境背景条件有很强的相关性,重要矿冶遗址的分布往往与该类型矿产的空间分布向一致。石器原料的选择性和利用能力影响到石质工具的功效,进而影响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类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因素的文化适应能力。除了对辽西地区的环境考古研究的系统总结和较详尽的细化研究之外,还对以往环境考古研究的空白区下辽河区及辽东区进行了初步的人地关系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形态的确立,生业模式的选择与当时、当地所处气候为主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空间配置有密切关系。在论文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围绕东北地区环境考古工作成果的综述性研究,发现今后开展工作的新生长点,使东北地区未来环境考古工作的发展方向更明确。
曹志红[5]2010年在《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本选题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中有关食物链顶端的亚洲(主要是中国境内)特有种一一虎的记录,对中国不同地理单元的虎种群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复原,恢复其过去的生活史、时空分布变化、数量变化及人虎之间的关系。结合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展开,探讨土地开发、日常社会生活需要、虎贸易利益驱动等人文因素导致的人虎冲突、政府打虎活动对虎历史变迁的影响,揭示人虎关系演变的历程。本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新疆、陕南、福建、江西、湖南、东北六个区域的虎资源变迁及人虎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虎产品利用史、虎产品贸易史进行勾勒,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打虎活动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全文共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也是第1章的内容。主要介绍本研究的主旨和全文结构,勾勒研究简史,介绍研究方法。本研究主旨在于在古动物到现代动物演变之间,补充学术界较为缺乏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内容,通过对典型动物虎的研究,将动物的环境指示意义、动物与人的关系研究推进到历史时期。丰富和完善历史地理、动物地理、环境变迁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第二部分是区域虎历史变迁专题研究,包括第2-7章。第2章对新疆虎的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新疆虎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和研究难度,有关新疆虎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动物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状态。本章充分利用岩画、地志、文集和探险考察游记等资料,对历史上的新疆虎进行调查确认与研究:新疆地区至少在距今1-1.5万年前即有虎分布,以后持续不断;其地理分布涉及天山南北,沿水源(河湖)分布于山间谷地、河流绿洲及山前冲积扇地带;其具体生境以芦苇、胡桐树木(胡杨林)等植被为主,具有足供捕食的食物。至清光绪前期新疆虎依然多见,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1899-1916)开始锐减。人类活动迭加的自然环境演化是影响新疆虎变迁的主要因素。生物链偶然因素的参与(肉食性蚂蚁威胁虎的繁殖)也起到了可能的影响作用。第3章以陕南为专题,着重探讨特定时空条件下典型动物资源变迁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明清时期是陕南地区移民、开发的高潮时期,历史记录显示,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全面展开和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虎资源出现明显的变迁,人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以乾嘉时期为时间断限,虎的栖息领域出现阶段性萎缩,第一阶段涉及南郑、城固、沔县叁地,第二阶段则开始大范围萎缩。人虎冲突逐渐加剧,除一般性人虎冲突事件外,激烈的虎患和打虎活动频繁发生,成为人虎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有计划、有组织、高奖励、高力度的政府性防虎、驱虎、打虎活动开始展开,最终导致虎数量剧减,分布范围显着萎缩,栖息地向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森林资源保存较为完好的高海拔山地后退。第4-6章对华南的叁个地区(福建、江西、湖南)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复原了虎的时空分布变迁和数量变化过程,着重分析了虎患现象,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分析其发生的时空特征、烈度等级、原因和应对措施。得出结论:在进入人类文明阶段后,华南地区老虎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都呈逐渐缩小之势,总的来说人类干扰和捕杀是主要因素。在华南地区,虎的栖息地除了森林山地之外,平原地区也曾有虎分布,因为当时的环境条件满足了虎生存所需的植被、水和食物叁要素,比现在优越。虎患是华南地区的典型和突出现象,虎患烈度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的应对措施也因而出现了官方捕虎、民间打虎、军队猎杀、官民结合猎捕等形式。明清时期是南方地区历史上人虎冲突最剧烈,人类对华南虎影响最显着的一个时期,是华南虎生存出现危机的一个阶段。第7章对东北地区的虎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讨论了东北地区虎的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猎虎活动和虎产品利用情况,探讨东北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即该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特点和人类开发进程分散性、断续性的特点,为虎的生存赢得了一线生机。近代东北开禁后,东北虎的生存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冲击。第叁部分是虎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第8-9章的内容。第8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的勾勒,讨论了虎的药用、食用历史,勾勒出了虎产品贸易的发展过程。第9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打虎活动的讨论,指出打虎活动从史前到1970年代一直存在,明清时期是第一个打虎高潮时期,将虎的分布从平原和低山区推向中山和高山区,但并未对种群的数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真正起到灭绝性影响的是建国后50-70年代的除害兽运动。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第10章内容。本文的突破性结论体现在几个方面,即填补新疆虎和虎产品利用和贸易史研究空白、丰富和补充动物学对于虎的栖息地选择、生活习性的认识、提出中国打虎活动的概念。最后,本研究阐明了历史环境变迁中人文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为特有动物种群变迁研究、濒危动物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 黑龙江省西部和中部林栖鸟类迁徙的研究[D]. 郭玉民. 东北林业大学. 2002
[2]. 黑龙江省东部和西部春季林栖雀形目迁徙鸟类比较[C]. 郭玉民, 常家传, 刘晓龙. 中国鸟类学研究——第四届海峡两岸鸟类学术研讨会文集. 2000
[3]. 我国重要珍稀濒危物种与类群的地理分布格局及保护现状评价[D]. 肖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04
[4]. 中国东北地区西南部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地关系发展阶段的量化研究[D]. 汤卓炜. 吉林大学. 2004
[5]. 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D]. 曹志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