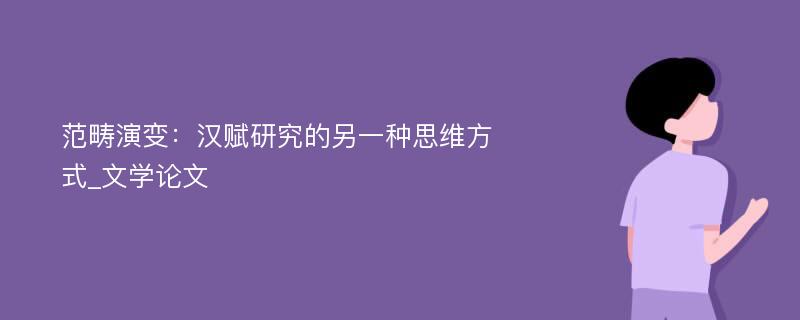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思路论文,类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7-0187-04
关于汉赋发展的描述,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常常是以时间为纵向的“线”,以具体赋家为横向的“点”,并结合汉赋发展过程中先后呈现出的骚体赋、大赋以及抒情小赋这样三种阶段性的体式特征展开论述。这种描述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对一个赋家的全部创作进行充分的评介,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使读者对一种汉赋体式的前后发展变化形成清晰的认识,并误认为以上三种汉赋体式是按照从前往后、由此及彼的顺序来发展,而这与汉赋发展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所以这就给汉赋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来描述汉赋的发展?什么样的描述方式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和展现汉赋发展的全貌?
因为实际上,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并不是在西汉初年和东汉后期才出现的,它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同一种汉赋体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也就是说从贾谊到赵壹,汉代的抒情言志赋一直有条未曾间断的发展线索,而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和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分别处于汉代抒情言志赋发展脉络上的两端,这其间还经历了西汉答难体的言志赋、两汉之际的纪行赋以及东汉初年言志赋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抒情言志赋表现出一些大致相似的共性特征,即它们多以个人身世之感、时事生存之惑努力贯穿全篇,细腻熨帖地展现了汉代文士的性情世界,所以千古之下最能打动人心,也因此成为我们了解和体会汉代文士生存环境、内心世界以及创作心态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所以沿着这条感情的线索,我们看到的是汉代士人志不获伸、意不得抒的“不遇”情结。当然有汉四百年间抒情言志赋中对“士不遇”主题的吟咏又因时代及赋家思想、经历、性情的不同而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点。比如西汉时期的抒情赋与答难体言志赋主要是通过怀悼屈原或是自我伤悼来对大一统专制政体下的君臣关系进行检讨,既然是检讨就不免要比较,在比较之中战国时期那种君主礼贤成风、君臣亦师亦友的风貌则成为当下社会主上威势腾驾于群臣之上的吊诡。所以在西汉赋家悯时伤己的愁肠中普遍有一种制度性的焦虑,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寻找内心的理想情境来平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解脱之道除了坚持个人的德行操守之外,还多多少少表现出安时处顺、与道逍遥的思想与意愿,并以著述之业为寄托。到了两汉之际,赋家的不遇情结中则因战乱平添了身世飘零之苦、悲悯苍生之愁,所以儒道绌补的人生哲学继续成为这一时期赋家思想的主导。至于到了政治相对清明治平的东汉前期,以班固、崔骃为代表的赋家则以完善个人节行操守和重视著书立说的心态来承认当前际遇的合理性,并表示出努力顺应时代变化的意愿。然而赋家心态的变化总是与时代的变化相始终。在东汉后期衰敝的浊流中,儒家的“志”与道家的“遁”使张衡陷于朝隐与归隐的矛盾当中,虽然其最终仍是以“遁”殉“志”;赵壹、祢衡等人是以狂狷之气声讨社会的黑暗腐朽;蔡邕的人生形态则是介于张衡与赵壹之间,他强调应于细端之中预见、辩识祸福吉凶的征兆,懂得避祸全身。可见东汉末期的文士已经萌发了珍爱个体生命之念想,但混乱的浊世却根本不可能提供相应的保障,来自皇权或者权臣的任何威压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一个个生命摧折。所幸的是有这些文字可以留传,我们因此在正史之外多了一条探寻汉代文士思想变化的途径,这也许正是汉代抒情言志赋最大的价值所在。所以总体来说,汉代的抒情言志赋记录的是赋家在制度和规范下的心态、情态与形态,从而以一种内在性的体察与抒写成为苑猎京都大赋历史观照视野的良好补充,在汉代思想史和文学史记中亦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艺术手法上来说,与苑猎京都大赋的散体形式相比,汉代的抒情言志之作基本上是以骚体赋为主,篇幅相对短小,多叙述而少描写,多用典而少想像,而且赋作的骈偶化色彩日趋显著。而且它们无一不以赋家的个人身世入赋,没有矫情,没有夸饰,或是沉郁顿挫,或是朴实流畅,或是自然清新,或是慷慨激昂,细腻熨帖地记录和展现了赋家个人的性情世界与思想经历,这又与苑猎京都大赋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所以,如果说“体国经野”的苑猎京都大赋表现的是汉代赋家的才情的话,那么“述行序志”的抒情言志赋展示的则是他们的心情。而且有意味的是,汉代的大赋作者在写作煌煌大赋之余都还无一例外地用短章小制或抒情或言志或述行,表达着他们在制度和规范下的喜怒与哀乐。所以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苑猎京都大赋是以宏大的叙述模式呈现出对社会的历史观照,而抒情言志赋则是以感性的内在表达展现着赋家个体的心灵世界。
当然,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出盛汉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最主要的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虽然在对它们的具体描绘中夹杂着许多想像和夸张的成份,但虚实相生之间我们却不难看出汉代人对当代社会的观照角度与描述方式。当我们借助于想像的翅膀,连缀起文字的片段,仿佛依稀可见当年那些喧嚣飞腾的历史影像。所以,如果说历史是以一种严谨求实的方式记录着从前,那么文学则是过往时代最生动的录影者,因为它不仅于方寸之间再现了过去的山川风物、琼楼玉宇,而且还比较逼真地复制出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甚至包括那些早已为人们所淡忘的生动细节——一种比地方志更为细腻的风俗记录。代表着权力话语的汉代苑猎京都大赋也因此成为我们体察汉代社会的一条“正途”。
也许对于汉代的赋家来说,苑猎京都大赋多是在田猎、游乐、观赏的时候应君王的要求而作,虽然东汉京都大赋的创作由于赋家的议政意识而带有更大的主动性,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用于呈送、供奉人主的目的与用途。所以这就对汉大赋的内容与形式有了必然的要求,内容上自然是“体国经野”,以展现大汉帝国的声威与君主的德行。形式上则是要“好看”,这不仅是指以囊括四海之意、包举宇宙之心来铺排夸张,而且还要达到“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效果,在君主娱乐性的感观享受与满足之外又加入了一点讽谏的意义。所以苑猎京都大赋主要展现的是赋家“才智深美”的一面,而这种“命赋”的写作方式又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因此以宏大的叙述模式和超凡的想像夸张来展现琳琅满目的汉代社会生活图景是我们所看到的苑猎京都大赋的基本主题。当然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到张衡的《二京赋》,由于赋家的思想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各有不同,因此赋作中对现实政治的观照角度与描述方式亦有差异。比如说,虽然同样是处于国势上升时期,但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展现的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而班固《东都赋》所颂美的则是人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又比如,扬雄和张衡的大赋都因时代的凋敝而增强了讽谏的内容,但扬雄大赋中的讽谏手法比较含蓄诡谲,而张衡大赋则以议论出之,显得相对直白一些。总之,各个时期不同赋家的苑猎京都大赋虽然在摄取现实社会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它们终始是与时代精神相互契合发展,因而在文学价值之外还生发出一层历史意义。而这种对“话语权”的掌握与苑猎京都大赋在汉赋发展史中的地位亦相符契。
此外,在有汉四百年间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同样保持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其实从广义的范围来看,在苑猎京都大赋中赋家以自己的目之所及、足之所历、心之所想已经对都市宫殿、园林苑囿、山川风物、鸟兽虫鱼等物象进行了大量的铺陈与描绘,可谓是“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文选》序)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汉代那些由赋家有感于物,吟咏于物,并以物之个体为篇名的赋怍。以此狭义的标准来衡量,汉代咏物赋今见于目并署作者名的共有80余篇。其中目前仍保存完整的有44篇,残篇25篇,佚篇12篇。倘若再加上《汉书·艺文志》“杂赋”所录“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就有140篇之多。这在前代文学中是没有的,而在汉赋总目中则约占1/3还多。从时间断限上来看,汉代咏物赋亦是横跨两汉,在今见于目的73篇中西汉有27篇,东汉有54篇,从中可见咏物赋渐趋增多的情况。从题材上来看,汉代咏物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涉及到的咏物题材共十九种,除服饰、舟车两类外,其余十七类都录有汉代的咏物赋,由此可见咏物题材在汉代已经大体齐备。
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汉代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浓郁的比附颂德的特点,这不同于屈辞中的香草美人之喻,因为西汉时期的咏物赋更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这种情形在东汉时期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作品是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因此带有浓厚抒情或说理的意味,从某种角度来说将其视为抒情言志赋亦未尝不可。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内心的体察以及物象之特性巨细无遗的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言志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代的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和咏物赋在四百年间一直保持着均衡的发展势头。这里“均衡”的意思是就以上三种汉赋体式在汉代的总体发展状况而言,而不是说其中的某种体式在汉代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平稳态势。因为事实上每一种汉赋体式都是随着时代的盛衰起落和赋家个体的际遇偃蹇而繁盛消歇,所以这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还关涉到有关汉赋的文化品格以及赋家的创作心态等一系列问题。一般来说,有关汉赋的品格定位常常是与“宫廷文学”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囿于其基本的写作方式属于自上而下的“命题作文”,主要的写作内容是围绕着帝王生活来展开,主要的传播范围也是处于宫廷和上层社会之间。但这样的概括并不完全,因为在汉赋发展史上那些以抒发个人心志为主题的抒情言志赋和以日常物象为吟咏对象的咏物小赋都展现了汉赋于“宫廷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品貌。而且颇有意味的是,汉代赋家常选择不同的汉赋体式来抒发其不同的感情需要,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汉赋体式的不同品格风貌和功能用途,以及赋家游刃于各体式之间的心态。特别是赋家用不同体式的赋作来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这一点尤值得我们深味。
因此,就汉赋发展的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从题材内容上将其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是言之成理的;从体裁形式上来说,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咏物赋以小赋为主。另外,前面也已经说过,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和咏物赋这三种汉赋体式在汉代各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但它们并不是按着由此及彼的顺序来发展,相反,这三条线索几乎是同时发生、演进与变化的,所以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而且不同的汉赋体式具有不同的创作来源,进而导致其作品风格、思想倾向、创作意图、写作方式以及赋作用途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在汉赋研究中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并且还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同一个赋家对不同体式赋作的创作实践。所以,我们设想有这样一本著作,它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发展,具体而言是以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和咏物赋为三条纵向的“线”,以各体发展中的重要作家、作品为横向的“点”。一方面对这三种汉赋体式的创作源头、写作方式、创作意图、作品风格、思想倾向以及赋作用途分别进行描述,并顾及一种汉赋体式的前后变化。另一方面在具体叙述则尽可能地挖掘和揭示他们——赋家、它们——赋作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赋家游刃于不同体式之间的创作心态。这或许可以作为描述汉赋发展的另一种尝试。
导师荐语:
汉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别的文学体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蒋文燕同志的《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一文以汉斌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传统文学史和赋史著作中对于汉赋发展的描述方式提出了异议。文中所言应“线”、“点”结合,即以汉大赋、抒情言志赋和咏物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并由此揭示赋家藉不同体式所表达出的不同的创作心态。这种思路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勇于提出新见,不囿于成说,又持之有故,在当前的汉赋研究中可成一家之言,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