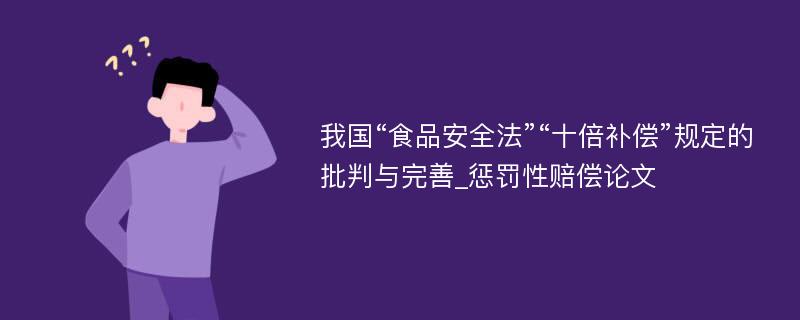
我国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规定之批判与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法论文,我国论文,食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6月1日对每一位中国消费者来说都是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大家翘首以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终于生效施行。虽然对于近些年来已饱受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三聚氰胺之苦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部姗姗来迟的《食品安全法》只能算是迟来的正义,但毕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法》到底能不能承载大家的厚望,成为老百姓们餐桌上食品安全的保护神?
翻开这部号称横跨三年且历经四审才最终出炉的《食品安全法》,我们的确能够从中发现不少新意,如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取消食品免检制度、对问题食品实行召回制度等。在这些新制度中,最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莫过于《食品安全法》第96条关于消费者可索取“十倍赔偿”的规定了。《食品安全法》生效不久,消费者们就跃跃欲试,依据该法的有关规定在全国各地提起了多起向食品厂商索赔的诉讼,①并被媒体宣传为在我国民事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更有甚者称其为中国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成功实践,进行无限拔高。②
一、“十倍赔偿”规定:制度溯源与理论反思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食品厂商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以下简称“十倍赔偿”规定)。这条“新规”虽然在媒体舆论不吝溢美之词的渲染下有如神兵天降一般让原本霸道蛮横的商家现在都成了一戳就破的纸老虎,但其实这种让侵权者向受害者支付超过实际损害数额赔偿金的做法,在英美诸国早已是至少有了两百年历史的成例,即便在国内的立法实践当中也难谓首创。
追根溯源,“十倍赔偿”规定显然脱胎于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是指当被告所实施之侵权行为带有放任、故意或欺诈等恶劣性质时,法官会在原告所遭受实际损失之外,另行判处被告偿付给他一笔额外赔偿金,以求实现惩罚被告、震慑恶行与抚慰原告等多重目的。对于原告来说,惩罚性赔偿可以用来弥补补偿性赔偿可能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当他遭受的损失难以精确量化的时候;对于被告来说,惩罚性赔偿则带有非常强烈的惩戒意味,以剥夺财产的方式遏制其再犯的冲动;同时对于社会其他成员来说,惩罚性赔偿在威慑与教育方面的作用也功不可没。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国外最常被用于产品责任领域当中,这不仅是由于产品质量与每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产品责任案件往往黑幕重重,只有借助惩罚性赔偿所特有的雷霆万钧的威力,才可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至于重演。而基本目的又反过来决定了制度的根本性质,像“十倍赔偿”规定这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足点,就在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如果行为人只是犯有过失哪怕较为严重,也达不到采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因为防范和惩戒功能在此已无用武之地。只有当行为人所为之故意侵权行为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足够恶劣的程度,如已构成了欺诈、胁迫或完全罔顾他人人身安全时,惩罚性赔偿方能发挥其巨大作用。
作为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较为广泛的国家,美国已经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总结出了一整套非常成熟有效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判处原则。通常说来,法官除了会从法律要件的角度推断被告究竟是在何种主观心态驱使下做出了如此令人深恶痛绝之行为外,同时也会从政策效果的角度来思索若是给予此被告严厉惩处将会给社会风气以及所在行业造成何种影响,当然在很多时候原告所遭受的损害后果也会被法官作为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考量因素。这种慎之又慎的态度无疑提醒我们,惩罚性赔偿无论如何都绝非一个常规的选项。
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总是能够赢得一边倒的赞美,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了它的一系列弊端,如这笔数额庞大的赔偿对原告来说实属不义之财、对被告实施过重惩罚有趁火打劫之嫌以及逼得企业走投无路乃至破产对社会总体福利并无益处,等等。面对这些并非妄加的指责,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一直处于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二:一是对惩罚性赔偿金额规定上限,如将惩罚性赔偿金额与补偿性赔偿金额或被告的净资产以一定比例挂钩;二是通过改进诉讼程序让法官对惩罚性赔偿的判处有更多掌控,如规定惩罚性赔偿相关事项必须分案审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效果就如一把双刃剑,如果在没有严谨设计与周密安排的情况下仓皇设立,其后果反而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③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国外的蓬勃发展早就引起了国内法律界的关注与效仿,只不过限于学理上的门户之见,我国的“侵权行为法始终坚持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偿原则,坚持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反对在侵权行为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金”,④因此中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存在于合同法领域。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消费者可对产品与服务欺诈要求两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89条规定的双倍返还定金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某些双倍返还的赔偿责任。在侵权法领域,除了产品责任以外便再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⑤因此,“十倍赔偿”规定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在试图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道路上的又一次尝试,只不过这次尝试却难言事毕功成。
二、“十倍赔偿”规定的立法设计批判: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相关参与立法的专家在解析《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时称:“(该条款的)目的,一是补偿受害者,二是制裁加害者,三是教育其他公众。惩罚性赔偿能够很好地补偿受害者,让违法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感觉疼痛难忍,还让整个社会公众受到震撼。”⑥
由此可见,这条所谓中国版惩罚性赔偿规定的主旨在于,通过“十倍赔偿”的手段来达到补偿、制裁加震慑的三重目的。这种借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来实现一石三鸟的设想固然美妙,却难免让笔者产生直观的疑问,就这样一项字不满百的条款能够达成如此复杂的目的吗?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威力不足、形重实轻
立法者赋予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以震慑的使命,但问题在于价款的十倍赔偿到底能震慑得了谁?
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⑦这难道不正是当今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真实写照吗?当乳制品企业将三聚氰胺加入牛奶,当肉制品企业用敌敌畏来加工火腿,当一些乡镇企业用苏丹红来炮制咸鸭蛋的时候,他们难道不清楚这样做有可能给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从而将导致自己触犯刑律遭受制裁吗?这些民间的“化学大师们”虽然知道自己不法行为的危害及后果,但之所以仍然敢铤而走险,是因为追逐超额利润的本性已使他们陷入彻底的疯狂,甚至到了罔顾他人与自己生死的地步。显而易见,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连走上绞刑台都毫不畏惧的无良商家,会怕你开出的区区十倍的赔偿吗?就以三鹿集团为例,对于这样一个年产值上百亿元的企业来说,区区几块钱(一袋牛奶的价钱)十倍的赔偿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从现实来看,自从《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运用“十倍赔偿”规定成功索赔的案例,如有呼和浩特的消费者获3元价款的十倍赔偿共计30元,⑧有南京的消费者获11.2元价款的十倍赔偿共计112元,⑨有武汉的消费者获9.3元价款的十倍赔偿共计93元。⑩从这些案例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食品安全事件的一个规律,即绝大多数都仅是几块钱或十几块钱的小额消费,鲜有货物能值上成千上万者,故而即便乘以十倍后数额也只能算作“毛毛雨”,并不足以达到立法所追求的让违法者感到疼痛难忍的地步,很多时候连隔靴搔痒的效果也算不上。上述这些案例中的消费者基本上能够不费周折地获得十倍赔偿,笔者想大概与赔偿数额无足轻重有很大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商品生产、销售企业并不怎么在乎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赔偿。
倘若以上分析还不足以让大家感受到“十倍赔偿”威力不足的话,笔者可以再举出更加直观的例子加以横向比较。在德国,亨特格尔公司曾被查出其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奶粉中含有“坂歧氏肠杆菌”,结果向消费者支付高达1 000万欧元的赔偿金;(11)在美国,麦当劳公司因为其出售的咖啡温度过高导致消费者被烫伤,因此向一位老太太赔偿了270万美元;(12)在日本,雪印乳制品公司由于生产出来的牛奶含有“黄色葡萄球菌”而会导致中毒现象,因而不得不借钱赔偿给受害者29亿日元。(13)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规定的“十倍赔偿”看似要把无良商家高高举起,实则却会轻轻放下,这样的处理是根本不可能形成任何震慑力的。如果不把“十倍赔偿”看作下限而当成上限的话,笔者断言,威力不足将会构成今后中国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致命缺陷。
(二)刚性有余、灵活不足
姑且不论这“十倍赔偿”多少的话题,因为多少的评价完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非常好奇这十倍的数目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以至于又能被认为属于合理的倍数?
既不清楚立法者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不知道有没有经过科学的测算,《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就这样给中国版的惩罚性赔偿确定了一个固定的乘数比率,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倍赔偿”规定。换言之,只要出现了制假售假的情况,无论生产经营者的动机怎样、财力如何、规模大小、责任多少,也不管消费者的受伤状况、贻害程度、求偿成本、境况遭遇,更无所谓波及社会公众的范围、影响烈度、负面情绪、后果深远,法官所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连小学生都会做的算术题,把价款乘以10即得出惩罚性赔偿数额。一分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
作出这样一种机械死板却毫无回旋余地规定的最大好处在于替法官免去了思考的痛苦,最直接的坏处却在于使赔偿丧失了应有之义。对于惩罚性赔偿而言,与实际损害相差悬殊的巨额赔偿看似是对受惩罚者的不公,其实却蕴含着实质性的公平,目的在于以儆效尤。然而,钉死于十倍的赔偿却根本地违背了这一精神,无端创造出许多的不公平,以至于无法实现惩戒警示的目的。假设一个人吃了一根价款为1元钱的有毒油条致死,而另一个人买了一盒价款为1000元的不合格燕窝未启封即索赔,于是前者只能获赔10元而后者可获赔10000元,这能称得上公平吗?假设一家企业利欲熏心故意用致癌物来制作食品,而另一家企业仅仅由于某位员工的疏忽在食品的外包装上出了些许差错,虽不符合标准却不会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任何损害,却由于前者产品的价款要远小于后者,以至于乘以10后的赔偿金额更是差距惊人,这又能称得上公平吗?假设一家跨国公司仗着自己财大气粗根本不把消费者放在眼里,屡屡有生产不合格产品的不良历史记录,而另一家私人作坊尽管一直谨小慎微、苦心经营,偶尔有一次因为纯粹技术问题而导致产品未能合格,同样处以10倍赔偿对前者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对后者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了,这还能称得上公平吗?在这么多活生生的不公平面前,立法者对“十倍赔偿”规定寄予的教育功能的期望无疑是苍白无力的。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不公平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关于赔偿倍数的规定过于刚性,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没有任何灵活性可言。这使得法官不能根据每一起案件的独特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合理解决问题。
(三)面目模糊、性质含混
《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看上去像是一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专家也将其解释为中国版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笔者的疑惑恰恰由此而生,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共有的鲜明特点,在我国的“十倍赔偿”规定身上都找不到呢?
惩罚性赔偿被公认为一种特殊的赔偿制度,有着一些自身独到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赔偿的数额很高、适用案件的数量很少、适用案件的条件很严格。在此不妨以美国为例加以说明。首先,惩罚性赔偿之所以会被冠以“惩罚”之名,不仅仅因为其与补偿性赔偿迥然有别,更是因为这种赔偿的数额往往异常巨大,形成了对被告浓厚的警醒、惩戒色彩。有美国学者曾统计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斯州、纽约州这四州法院在1988年至1991年间所判处惩罚性赔偿的平均金额为778 000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赔偿的判决也并不鲜见。(14)其次,正是由于惩罚性赔偿对被告的制裁力度极大,因此美国法官对于这种赔偿方式的运用非常审慎,而绝不会轻举妄动、滥加惩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在全美各州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只有不到6%的原告能够成功获得惩罚性赔偿,如果是在没有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情况下,这个成功的比例又会进一步下降到4%。(15)最后,美国有不少法院都对惩罚性赔偿的判处设置了堪称苛刻的条件,不仅设计出了别致的诉讼程序来不断考验原告的耐心,而且在证明要件方面也大大加深了对被告主观恶意的要求,甚至还把相应证明标准提升到了仅次于刑事案件的高度。哪怕你成功地跨越了这些障碍,法官们也总会以挑剔怀疑的目光来对赔偿金额加以审视,更加让你沮丧的消息还包括,这笔获赔金额不但不免税,有些州政府还要拿走其中的70%以上。(16)
反观《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上述这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显著特点不仅在“十倍赔偿”规定当中无一呈现,反而给人一种南辕北辙的感觉:(1)我国的赔偿数额普遍很低。从新闻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各地已实现的赔偿数额竟鲜有超过人民币百元的,按照一成不变的价款乘以10的算法,在食品价格一般比较低廉的情况下,将来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天文数字的判决出现。如果尽是这些几十、几百元钱的赔偿也能被称为惩罚性赔偿的话,真是会让人哑然失笑,不知“惩罚”这两个字如何名至实归?(2)我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应会很多。按照新闻媒体对各地索赔过程的报道,消费者基本上是无往而不胜,只需费些口舌而不用诉诸法院就能让商家乖乖掏钱认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想并非是中国的商家特别通情达理,而是因为适用“十倍赔偿”的门槛过低,以致适用范围过于宽泛。本应该是一个高不可攀、难以企及的稀罕玩意,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唾手可得、见者有份的寻常之物。让人纳闷的是,这还是惩罚性赔偿吗?(3)我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过于宽松。法律既不要求不合格食品的生产者具备故意或过失的心态,也不要求被告在行为上有除简单违法性外,还应具有道德层面的强烈可谴责性以致于达到了社会难以容忍的程度,更不要求消费者是否遭受了实际伤害。有人也许会问,这不就是把保护的天平倾向了消费者一边,难道这样不好吗?当然不好,消费者可不总是纯洁无助的羔羊,事实上,市场上形成了一股竞相争购劣质食品的风潮。(17)虽然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但看到这样对劣质食品趋之若鹜的景象,还是认为惩罚性赔偿不应该是大家可以排着队到商店去领的奖金、补贴,因为如此一来惩罚性赔偿就失去了应有之义。
除此以外,类似浮现在笔者心头的不解谜团还有很多,如既然消费者获得“十倍赔偿”无需以受到伤害为前提,那么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功能又如何体现?在食品的价款偏低以至于赔偿数额总体不高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的震慑功能又如何体现?由于获赔几乎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那么在“十倍赔偿”眼看就要成为形形色色“王海”们的牟利工具时,惩罚性赔偿的教育功能又如何体现?又如,为什么“十倍赔偿”规定没有采取外国通行的以原告所遭受实际损失为参考基数的做法,而是非常罕见地规定了以他所支付的价款作为乘以10倍的基数?如此一来,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与价款之间究竟存在着逻辑上的什么内在联系?这是不是意味着哪怕原告受到的身心伤害极其严重,但由于他当初支付的价款不多,就理所应当地不该获得比另外一个支付价款较高却未受任何伤害的人更多的惩罚性赔偿?
总而言之,把《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十倍赔偿”规定称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不由得不给人一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
三、“十倍赔偿”规定的司法适用批判:细节缺位,难以操作
除了立法上存在问题外,“十倍赔偿”规定由于细节缺位,因而存在难以操作的弊病,从而导致了根本不可能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被妥当运用。除此之外,在适用时还有《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竞合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两者从表面上看的确存在着竞合,但这种竞合在具体实践中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其具体理由在于:一是两者的立法角度与适用范围是不同的;二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新法与旧法以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三是即便发生竞合也可通过原告选择适用的方式加以解决。
出于常理,“十倍赔偿”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被大范围地推广、落实之前,至少有下列细节问题是《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不清楚却必须弄明白的:(1)生产者在承担“十倍赔偿”责任前,需不需要先有将食品投放贸易流通领域的行为?换言之,一待生产者把不合格食品制造出来,这种“十倍赔偿”责任就已经成立了吗?(2)销售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须以“明知”为前提,那么什么叫做销售者“明知”呢?“明知”是指确实知道、应当知道还是推定知道?对不同业态、规模、渠道与地位的销售者是否应不同对待?(3)数个被告之间的责任应该如何划分?他们之间有相互追偿的权利吗?原料供应商、初级加工商、成品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如果要划分责任,是以各自过错的大小为基础吗?既然“十倍赔偿”不需要证明过错,那么根据过错来划分责任有道理吗?(4)个人之间从事非经营性的食品买卖交换是否适用“十倍赔偿”规定,如社区内部的赈灾义卖活动?(5)价款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吃了一桌子菜,其中有一道变质了,那价款是指这一道菜的价钱,还是指整桌菜的价钱?又如,我的食物中毒是累积性的,那价款是指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价值,还是指全部食品的价值?(6)如果我获得食品时未支付价款,如在街头随手拿的赠品,或者只支付了部分价款,如只交了一部分订金,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无法获得或只能部分获得“十倍赔偿”?(7)不符合安全标准是获得“十倍赔偿”的必要要件,那么如果相关领域内的安全标准缺失,而消费者已受到严重伤害怎么办,典型的例子就如高热量的垃圾食品?(8)符合安全标准是不是就意味着“十倍赔偿”绝对不会启动,即便销售者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如存在欺诈性宣传?(9)食品的特点是不易保存,当一样食品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子或是无法保持当初状态的时候,消费者如何举证?是否适用“不证自明之理”原则(res ipsa loquitor)?(18)(10)虽然食品不合格,但由于事故并非是由食品的不合格所引起的,因此不合格食品与消费者受损之间不存在事实因果关系,那有没有可能消费者无法获得补偿性赔偿,却可以获得“十倍赔偿”?法律因果关系不存在,如原告并非是食品的购买者时,又该如何处理?(11)如果“十倍赔偿”的金额总是低于补偿性赔偿的金额,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现象?(12)消费者在没有遭受任何伤害的情况下,为了证明食品不合格而花去的调查取证等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与“十倍赔偿”是一种什么关系?(13)这种“十倍赔偿”的责任究竟是一种严格责任还是一种绝对责任,被告的抗辩理由与免责事由又有哪些有特殊之处?(14)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的判断应该以何时为准,是以脱离商家控制为准,还是以消费者食用为准?如果因消费者的储存、加工、食用而使得食品的质量状况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时,又该如何处理?(15)召回制度与“十倍赔偿”规定之间是一种替代还是并存的关系,我可不可以在得知商家采取召回行动后,购买少量不合格食品以便牟利?(16)赔偿的倍数是不是只能为十,如果明知商家无力赔付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况时,消费者有没有选择权,可不可以只向法院要求其他倍数的赔偿?(17)在通过网络购买食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物流企业应否认定为食品的销售者?如果食品在物流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十倍赔偿”规定能否继续适用?(18)在赔偿数额不高的情况下,如何阻止商家通过把赔款计入成本从而转嫁给消费者?(19)与索要“十倍赔偿”诉讼相配套的民事诉讼制度是否已经建立,是否完善?这会不会导致相关诉讼像洪水一样涌入法院?
立法总是应该追求精细、缜密的目标,特别是在建立“十倍赔偿”规定这样万众瞩目的法律制度时,更加需要尽可能地把立法者的意图表达清楚;否则,难免会出现因为大家各自理解不同而造成适用不统一的状况。
四、“十倍赔偿”规定的比较法批判:以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例
无可否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纯熟的国家。两百多年来(19)的思考沉淀与判例积累,使得美国法院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异常深刻的理解与丰富的实践,值得成为我们在建立本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学习的对象。
美国运用惩罚性赔偿的经验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因为它早年的那段几乎是被“逼上梁山”的出台背景,这与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有着身临其境般的惊人相似。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仅仅在20世纪前期,美国食品安全状况的糟糕程度简直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甚至比当今中国的食品安全糟糕情况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揭露那段时期美国肉制品加工业内幕的著名小说——《丛林》——(20)至今读来仍令人作呕。迫于民众压力的美国政府,随即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对食品安全进行整治,其中一项便是原本多适用于合同欺诈或普通侵权案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始被大规模地引入产品责任诉讼当中。随着一张张巨额赔偿单的开出,(21)美国食品市场的风气终于焕然一新。这一段从大乱到大治的经历,会令当今的中国消费者神往,希望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同样能带领我们走出食品安全的泥淖。
相较《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它作为一个体系的严谨周密与无微不至上。例如,对惩罚性赔偿触发机制的严格限定,美国大多数州都明确要求只有当卖家的主观过错达到故意、莽撞、恶性、放任、压迫或欺诈的程度时,以至于构成了对消费者的安危罔顾漠视时,才有可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如,对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证明标准的清晰界定,该标准应该高于普通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标准,而必须达到“清楚无疑且令人信服”的水平。再如,对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细密指导,法官此时至少应该考量包括原告的诉讼费用开销、不当行为给被告带来的好处、被告的财产状况与承受能力、社会公众遭受的危害、被告参与的广泛程度、被告是否表现出了悔意、被告是否试图掩盖、被告是否采取过补救措施以及被告可能遭受的其他处罚这9项因素。(22)尽管不同法系间法律传统与文化的差异,使得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难于为我国整体引进,但这却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其中处处体现出先进理念的具体制度设计。
先进的制度设计自然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如果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效果,那正是“狠、准、稳”三个字。所谓“狠”字,是指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制裁力度方面真正表现出了国之重典的风范,不动则已,一动则雷霆万钧。百万美元级的只能说是家常便饭,成千上亿美元的判罚也不鲜见,一定要罚到被告永生难忘为止。(23)而“准”字,是指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对象方面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精确性。通过采用让罔顾消费者安全的行为变得异常昂贵的办法,不动刀兵却能切中唯利是图的不良商家的要害,惩前毖后的效果十分突出。至于“稳”字,则是指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执行得非常稳健,详尽齐备的操作标准使得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判处及金额多寡都有章可循,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人而异的波动使其威信蒙尘,又使得原本的双刃剑变成了法官手中贯彻司法政策、驯服不良商家的利器。
通过上述比较,笔者更加迫切地感到在我国尽早建立真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否则,在世界各国竞相提高对本国消费者保护水平的大背景下,中国却何以要自降门槛以至沦为食品安全防控领域内的一块“洼地”。要知道在食品行业中的跨国巨头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食品出现了安全问题,在外国消费者可以获得巨额赔偿或迅速达成送上门来的和解之时,限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保守、落后,中国消费者却只能得到一丁点可怜的赔偿,而且还得看它们一副态度倨傲的冷脸,这种天壤之别才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有些人担心,将严厉的美式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我国,可能会导致中国的食品企业大面积的倒闭,进而使得众多工人失业以至影响社会稳定。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难道为了就业就可以罔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零容忍”政策;而且这样的担心也是多余的,森林法则告诉我们,在无良企业倒闭之后,自然会有新企业茁壮成长起来。
况且按照笔者的想法,中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不能够仅仅局限于食品安全,而应该覆盖凡属产品责任的所有领域,甚至可以扩展到更多类型的违约与侵权诉讼当中。因此,我们必须在《食品安全法》之外另行制定一部新法,来规范、统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五、“十倍赔偿”规定的立法完善:代结论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对一国国民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食品安全法》的施行无疑为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安全增加了一层厚重的保障。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样一部新法在试图革除旧弊建立新政的时候,难免会存在一些瑕疵。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创新就欠周详,无论在定性、定位还是定量上都存在严重偏差,虽有惩罚性赔偿之形,却无惩罚性赔偿之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笔者看来,“唯用重典,才有安全”。要想扭转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严峻局势,靠“十倍赔偿”规定这种外强中干的花招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只有把原汁原味的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以严刑峻法对抗利欲熏心,把胆敢以身试法的无良商家一次就罚到倾家荡产,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概言之,包括《食品安全法》在内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应予改进、完善。
具体说来,笔者设想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至少需要包括以下核心内容:(1)定义项,对恶意、明知、欺诈、放任、可谴责性等概念进行定义;(2)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可参考《布莱克法律辞典》或《模范惩罚性赔偿法案》(24)的定义;(3)宗旨与基本原则,可考虑设置审慎与最小限度等原则;(4)适用范围,以采用描述而非列举的立法技术为宜;(5)审判组织与流程,不妨设计一些诸如认定责任与确定数额必须分开审理或强制代理这样的特殊程序,以提高对被告的保障水平;(6)构成要件,即主观上存在恶意、行为兼具违法性与可谴责性、存在损害后果;(7)判处赔偿金额时应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包括被告行为的性质、造成伤害的程度、被告的经济实力等;(8)抗辩理由或免责特权,如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公共制药公司可以享有某些特权;(9)证明标准,应高于“优势证据”标准且低于“超越一切合理怀疑”标准;(10)最高数额限定,要么是一个固定数额、要么是补偿性赔偿的倍数、要么是被告净资产的某个百分比;(11)责任承担,应确定不同被告间责任分配的方法;(12)上诉及其审查标准,仅以审查初审法官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限;(13)赔偿款的缴纳,强调在执行环节严格把关,防止被告拖欠赔偿款项;(14)原告与国家在惩罚性赔偿金额上的分成比例,三七开可能是一个较为妥当的比例;(15)惩罚性赔偿金的纳税问题,明确这笔赔偿为应税所得;(16)各种专用诉讼文本的格式模板,像对被告的权利告知书,等等。
至于《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笔者建议改为:“如果消费者能够证明自己所受之伤害乃食品经营者漠视不顾消费者的安全健康所致,法院可准许他获得惩罚性赔偿,但其数额不应超过他所被判予补偿性赔偿的X倍。”
注释:
①此种案例于2009年6月初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生,主流新闻媒体也多有报道。参见甘慧茵:《女子买到问题鱼获十倍赔偿,食品安全法实施》,http://news.zhnews.net/glnews/2009/0602/article_9507.html;蒋德:《南京食品安全法维权第一案,适用十倍赔偿》;孔维薇:《消费者获十倍赔偿,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塘沽首例》,http://WWW.022net.com/2009/6-10/494866202753048.html;李贾、朱敏:《食品安全法实施后芜湖出现首例十倍赔偿案》,http://WWW.wuhunews.cn/whnews/200906/183676.html。
②参见劳力:《保障食品安全更需“损一赔十”》,《信息时报》2009年2月25日。
③(16)(22)参见李响:《美国产品责任法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第388-389页,第390页。
④杨立新:《对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探讨》,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earch/..%5Cshtm1%5C20090907-221228.htm。
⑤参见王晓明:《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改革评述》,http://sybarite.fyfz.cn/blog/sybarite/index.aspx?blogid=509889。
⑥王义杰:《等待食品安全法》,《方圆法治》2009年2月12日。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9页。但是,近来亦有人考证出这段话并非马克思所说。参见赵刚;《被张冠李戴的马克思名言》,《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13日。此观点真伪概莫能辨,笔者故而暂从旧说。
⑧参见刘欣荣、胡红波、鄂迎春:《食品安全法实施第4天,呼和浩特首例10倍赔偿》,http://WWW.northnews.cn/news/2009/200906/2009-06-09/208550.html。
⑨参见蒋德:《南京食品安全法维权第一案,适用十倍赔偿》,http://law.cyol.com/content/2009-06/03/content_2693182.htm。
⑩参见甘慧茵:《女子买到问题鱼获十倍赔偿,食品安全法实施》,http://news.zhnews.net/glnews/2009/0602/article_9507.html。
(11)参见李忠东:《从德国面包看食品安全管理》,《浙江工商》2008年第9期。
(12)参见李响:《美国侵权法原理及案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3)参见于清、管克江:《牛奶中毒震动日本》,《人民日报》2000年7月10日。
(14)参见杨瑞英:《初探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环境侵权中的适用》,http://WWW.enlaw.org/jc11/200606/t20060607_6876.htm。
(15)参见董春华:《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
(17)参见冯炜程:《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引发竞买劣质食品潮》,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6/02/content_11473896.htm。
(18)这是英美法系侵权法上的一个术语,大致指在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如被告不能提供相反的佐证,则可直接认定原告的请求成立。参见李响:《美国侵权法原理及案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19)美国最早一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例通常被认为是1784年的“几内诉诺斯(Genay v.Norris)案”。See Genay v.Norris,1 S.C.L.3,1 Bay6(1784).
(20)《丛林》(The Jungle)是美国著名纪实作家辛克莱尔的代表作,讲述了20世纪初期美国肉制品加工业的肮脏内幕。See Upton Sinclair,The Jungl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21)与此相关的一个数据是,美国旧金山各法院在1965年到1984年间,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增加了3倍。参见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
(23)虽然也有人对这些天文数字提出过异议,但仍然无法撼动支持巨额赔偿的主流意见。典型的例子为,美国国会曾于1994年通过了一部侵权法改革法案(The Common Sense Product Liability Legal Reform Act of 1994),其中第108节(Uniform Standards for Award of Punitive Damages)旨在对惩罚性赔偿的判罚标准与金额予以限制,但该法案遭到了克林顿总统的否决,理由为其与美国法律强调保护消费者的一贯方针不相符合。
(24)《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定义是:“当被告的行为存在放任、恶意或欺诈情节时,原告可以获得超出实际损害以外的赔偿。”Bryan A.Garner(Editor-in-chief),Black's Law Dictionary,8th ed.,West,2004,p.1027.而美国《模范惩罚性赔偿法案》的定义则是:“给予原告的一笔金钱赔偿以实现惩罚或威慑的目的。”See Model Punitive Damages Act 1996(draft),Section 1(2):"Punitive damages" means an award of money made to a claimant solely to punish or deter a defendant or to deter 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