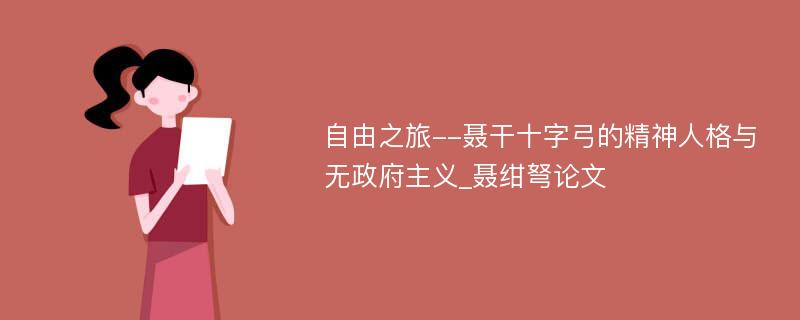
自由的行旅——聂绀弩的精神个性与无政府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旅论文,无政府主义论文,精神论文,自由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17(2006)01-0073-05
聂绀弩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多种创作都风格独特。30年代中期,他的杂文以冷峻峭拔、酣畅淋漓的笔墨初显锋芒;40年代,是他杂文创作的成熟期和丰收期,多种形式的杂文精品使他登上了杂文家的首席宝座。同时,他在小说、散文、新诗等诸多创作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晚年旧体诗的出版使人们像发掘出大汶口石器一般,向他投注惊诧、探询的目光,纷纷感慨万千地发出“奇”的呼声。更为重要的是,他孤羁不群、独行的精神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风帜独标,具有精神范式的价值与作用,因而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与此相对照的是,目前聂绀弩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奇人奇事”这个热点,以及他的杂文和旧体诗的创作上,而对其思想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聂绀弩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方面来把握聂绀弩的思想与精神个性,为聂绀弩研究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对任何一个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童年时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聂绀弩也不例外。关于他的童年情结,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 此处不再赘言。此外,走入社会第一步时的精神遭遇也是极为关键的,因为作为成年人,独立的个体主要用理性来思考人生、认识社会,而摆脱了童年时以感情为主来判断外在世界的幼稚阶段,因此这时的影响可能波及一生。恰恰在这时候,聂绀弩在思想上接受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说:“你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吗?那浅薄的理论,多么适合那时的一个幼稚的孩子的口味。刘师复先生,就这样,成为在思想上,对于我发生影响的第一人,他的影响支配着我,差不多有十年之久!”[2] (P114)具体分析,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造成他个性中的孤傲心理和思维判断的特异倾向,这些异端色彩又使他遭受现实的排斥和攻击,最终经由苦闷的媒介缔结了他与文学的联姻。因此,作为文学家的聂绀弩,与无政府主义有千丝万缕的、摆脱不掉的牵连。
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这种思想,早在190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历经传入、扩散、泛滥、衰落几个阶段。聂绀弩阅读《无政府主义讨论集》的20年代初,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期。在聂绀弩尊崇的刘师复笔下,无政府主义“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丰乐”。[3] (P305)它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没有强权压迫、没有经济侵略、没有行政裁判、没有伦理束缚的完全自由、自主的人间乐园,它像陶渊明“发明”的桃花源一样充满了平等友爱、自由和祥的空气,同时它也如一张白纸,给人们任意遐想、放任自我、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绘制最美丽的画图的心理空间。无疑,它对青年最具有吸引力,因为青年正处在一个向外进行力量扩张以显示自我存在的心理阶段。空荡荡、毫无阻碍的无政府主义王国正满足了青年人那种冲破一切栅栏、肆意驰骋、不计后果的心理冲动。并且,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如日中天、正处于巅峰状态,成为当时的三大思想派别之一。青年趋之若鹜,也正是追赶时代潮流的表现。因此,与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共生的虚幻性和简单化就被青年们轻易忽略了。究其实质,“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4] (P218)此处的“个人主义”,列宁所指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极端的个人主义与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不正有貌合神离的相似性吗?在青年们还来不及细嚼慢咽、深刻领会各种思潮的真谛时,极端的个人主义很可能被他们当作一种时代精神奉为圭臬。聂绀弩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一员,他接受无政府主义具有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共同特性,但具体而言,聂绀弩与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契合,又带有哪些个人因素呢?
聂绀弩自小家庭经济困窘,对贫富差别的感受就特别深,对与此相关的不平等现象也入眼入心。但年幼的绀弩,还不具备对之进行理性分析、评判的能力,乃至走出山城,也没有深厚的新知识储备;而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压迫、贫富不均等不合理现象的解释又是这样简单明了、切中肯綮,因此聂绀弩就很容易被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教打动。无政府主义者“万物为万人所有”、废绝财产私有权的主张也自然会赢得聂绀弩的赞同。其次,无政府主义取消家长权威、废除婚姻制度,以达到男女自由结合之目的,一定使聂绀弩获得了一种类似走出监禁、恢复自由的大快感。因为就是在离开家乡之前,母亲不顾绀弩的极力反对,为他娶了一个素不相识、彼此毫无感情可言的姑娘。绀弩对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痛恨至极,对母亲的专制亦早已反感,取消家长专制与婚姻制度正道出了他的心声。同时,它也为绀弩抛别孤寡妻母的“忤逆行为”找到了开罪的理论依托,使他得到了适度的心理解脱。毕竟,聂绀弩对母与妻有甩不掉的责任感。在泉州国民党东路讨贼军作录事的几个月中,聂绀弩看到军队所到之处就是赌博、娼妓、鸦片猖獗之所,军队的腐败、糜烂集中透视出政府的堕落和官员的昏庸,聂绀弩自然对之心存不满。无政府主义要消灭国家政府的宣传如及时雨润泽了他的心怀,无政府主义的两大理想——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也从此成为了绀弩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
作为思想领域的一种思想学说,常常并不主要依靠其真理性、完备性和可实践性,而要看它与个体碰撞之后是否产生相契、相投的精神现象。在恰当的时候,若某种思想的重点内容恰好击中了个体的心灵敏感点,且它的宣传方式、活动影响带给人信服感、可依托感,它的理论深浅度也正在个体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甚至它为个体留出自我营运的空白空间,那么,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极大,它和个体之间就可能形成一对相契合的成功碰撞体。对个体而言,他从此拥有了一种新的思想范式。聂绀弩正是在如此情境下接受无政府主义并长久地受它影响。
另外,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大胆的猜测:母爱的缺失是聂绀弩衷情无政府主义的深层心理原因,它潜伏在无意识中。因为“人类的一切最美好的理想实际上都产生于母爱的感觉。道家的回归大自然,儒家的大同理想,佛家的涅槃境界,基督教中的伊甸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与人类关于母爱的向往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人与周围世界的完全和谐的关系。”[5] (P159)自幼母爱的稀薄是聂绀弩耿耿于怀、不能忘却的切肤之痛,由此产生对完整母爱的向往与追求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而母亲是不可重新选择的,母爱不能凭借强烈愿望重新获得,因而,对母爱的向往只能曲折地寄托在对与母爱具有同等和谐性的理想乌托邦之中。向往常常是双重的,既是对现存物的不满和反叛,又是对完美物的渴望与追求。因此,聂绀弩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既是对母爱缺失的补偿,也是对母爱缺失的反抗。
聂绀弩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衷情是相对短暂的,但经由无政府主义激发的自由意志却伴随了他的一生。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和庄子的“逍遥游”在聂绀弩身上是如何顺利接轨的。因为童年时的聂绀弩就受到老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生养绀弩的故园,本是浪漫主义楚文化的发源之地,又是滋生清净无为、恣肆逍遥的老庄哲学的山野之乡,以道家思想成分和楚文化圈中的神话传说构筑的中国大众宗教——道教的影响弥久广泛。在绀弩幼年的自学书目中,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各种野史、笔记小说,如他百看不厌的《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红楼梦》以及《笑林广记》等,但他最爱读、最醉心不已的是《庄子》和各种高人隐士特立独行的传记。这一方面既助长了他孤僻独行、任性而为的性情,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各种身心束缚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为青年时期倾心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作好了思想准备。但庄子的任性自然是在天下纷争、礼乐崩坏的时局下所寻求的一种个体和谐状态,它以自然状态为自由状态,通过心理的放任与超脱求得心灵的最大自由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的片面考察和逃避;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退守哲学。而无政府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异化人的背景下、针对现实中一切压迫人的机器,包括政府、警察、监狱、法律等提出的打碎一切的“破坏”方案。它的可贵之处是对强权的反抗,是在不自由中渴望自由,是以自由为理想争取自由。尽管理论本身漏洞百出,但它的眼光是向前的,是充满进取精神的。聂绀弩当初禁闭家中,在对前途茫然无望的灰暗心境下为庄子的心理自由沉醉,是一份潇洒自在,也是一种无奈解脱。而当踏上人生征途,对繁杂的社会有所了解之后,聂绀弩就转而更向往无政府主义所宣言的现实感很强的外在的形式自由。这种向往令他苦闷,但也正说明着他的壮怀激烈与踌躇满志。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制度自由”,但并不抛弃庄子的心理自由,聂绀弩同时揉合了二者的精髓,练就了体现和贯穿于他一生的心理气质和行为方式之中的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在聂绀弩身上不是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地存在着,尽管他从庄子的“自然自由”起步,又踏上了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也浇筑着他的自由、平等观念,但聂绀弩既没有从学理研究的角度接近自由主义,也没有从附庸时代风雅的方面附会自由精神,他几乎完全从生命直觉出发走向了自由意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开宗明义的对自由的精神领悟的记述,也没有塑造形象鲜活、特征显著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自由意志完全内化在他的精神品质之中,成为他的个性特点和心理信念,以曲折的方式表现为对正义的坚守和对侠义的发扬。正义和侠义是聂绀弩自由意志的双飞翼,这既是他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精神基础,又是他发论作文的立论支点和思想内核。
聂绀弩人生的最大转折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可以说,触发这一人生转变的思想动力就是正义。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压迫、更难堪的侮辱,带来了亡国的恐怖。当时聂绀弩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可谓身居要职。但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意识使他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真面目,绀弩冒着被缉捕的危险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宣传联俄联共、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回忆这个“质变”(聂绀弩语)时,他说:“那时,我还不是党员,也不知谁是党员,更不懂马列主义。……那叫我行动起来的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我呀,除了我,还有谁呢?”并且,他的叛逆之举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激励的思想斗争:“我面前的路并不只有一条,而我自己则确定是两个。两个我时常辩论打架,一个我命令做什么,另一个我又反抗;一个我说这样,另一个则说那样”。[2] (P153)一时的思想冲突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也说明聂绀弩抉择的慎重。要知道,聂绀弩是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下的,能冲破这种势力,迈出朝向正义的步伐,可以想象正义在聂绀弩心中的分量。聂绀弩对真理和事业有着绝对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认准就义无饭顾、坚持到底,有的是并不受别人命令、不顾个人利害的赤胆和义勇,甚至“劝以爵禄不肯移,俱以斧钺不肯止”。这种行为方式正是以强烈的正义感为精神信念。
作为知识分子的聂绀弩,主要是“在艺术里战斗,以艺术为武器而战斗”(聂绀弩语),他的全部杂文,就是他高歌正义的战斗诗篇。我们只要举出几篇,就可以窥斑知豹。《韩康的药店》是一篇兼有战斗性、讽刺性和寓言性的小说体杂文,它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鲁迅语)的艺术构思把汉朝的韩康和《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置于同一时空,以韩康的药店因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门庭若市,和西门庆的药店因欺行霸市、哄骗百姓而门可罗雀的事实相对照,在看似轻慢却内蕴深邃的故事背后隐现着正义超越强权、不可战胜的真理,说明专制者妄想以欺名盗世和专横跋扈的手段来扼杀正义的声音、压制正义的力量,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成为历史的笑料。《历史的奥秘》以历史上的岳飞和秦桧的行为、结局为例,揭示了这样一个奥秘:“一个人演了神圣的角色,他的一切缺点,一切过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尽的任务遮住,洗清了。不但这样,还有许多实际上与他毫不相干,而在当时是可能的神圣的传说,都全被加到他的头上,使他更为神圣……如果演的相反的角色,不言而喻,他的一切美德会被一齐抹杀,一切丑恶都和他脱不了关系。而父母妻子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一个好人”。[6] (P204)在这里,个人的神圣与否就看他是否站在正义的一方,是否维护了民族大众的利益。正义就不仅是判断个人品质、作用的尺度,甚至有了超越真实原则的价值。此外,在谈到《封神榜》时,聂绀弩指出其字句粗陋、章法呆板、结构草率,是不值一提的,但就因为它写出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表现了作恶多端、残害人民的“气数已尽”的旧势力的衰颓和灭亡,代表人民、反对独夫的“天命所归”的新势力的壮大和胜利而给予充分肯定。对个人成就的评价,他也取正义尺度:“所谓成就,不能离开真伪,善恶,是非,邪正而另有标准,即不能离开人群的祸福,历史的进退而另有标准。”[6] (P71)另外他在《从陶潜说到蔡邕》和《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中还宣扬“狷介”思想,所谓“狷介”说到底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消极的正义之举。
生逢民族危亡的战乱时代,从自由意识衍生的正义思想在聂绀弩身上是和民族意识相融共存的。民族意识是正义思想的根基和底蕴,正义思想是民族意识的脊梁和支撑;没有正义思想,民族意识会被金钱、地位、安全等利益考虑挤迫到褊狭的角落;没有民族意识,正义思想将虚空干瘪,缺乏现实的战斗力。二者的结合,使绀弩的正义行为带有时代的特征。
另一方面,在聂绀弩的自由意志中,总是或隐或显地闪现着侠义精神的光芒,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古代侠士的行为特征和人格观念的认同和欣赏中。取材于汉代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鬼谷子》,就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侠士形象——要离。要离本是鬼谷子的学生,他读书认真、表里如一,短暂的人生充分体现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承,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韩非子语)的侠士的行为特征。对这种行为品格,聂绀弩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聂绀弩还赏识要离那种超凡脱俗、蔑视平庸的英雄主义人格观念,他以赞同的笔调写道:“但是他(指要离)看不起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在权利面前,摩拳擦掌,个个是英雄豪杰;出了一点小事,马上变成了娇贵的闺女,心里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单是因为和这些家伙在一个世界上,人也会觉得很羞耻,要想什么时候显一点身手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止水似的情怀也波动这么一下的呀!于是挺身而起,自告奋勇去刺庆忌。”[7] (P71)但是,拥有独立人格的绀弩对古代侠士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债务意识是持批判态度的。债务意识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明了侠士的人格尚未独立,仍在封建等级制的钳制下苦苦挣扎。因而,对要离以生命的代价行刺庆忌的行为,聂绀弩是持否定态度的。
同时,在聂绀弩主体的个性行为中,也分明表现出一种游侠的傲骨与气派,他是一位勇武、敢拼的怪异文人。1945年底,聂绀弩正在重庆编辑《真报》副刊《桥》。一天,大家正在编辑部谈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情况,突然一位姓李的人冒了一句:“共产党这次可勇敢了。打日本鬼子是不是也这么勇敢?”正在埋头写作的聂绀弩听到此话,忽地拿起桌上带盖的茶杯连茶水一齐向那人头上打去,同时大骂:“操你娘,你知道共产党打鬼子不勇敢?”当时重庆是蒋介石统治的中枢,国民党的势力无处不在,那个姓李的人曾经是中央赈济委员会的雇员。聂绀弩的“暴行”并非武夫所为,而是遵循着内心道义价值的指引,在危难险阻面前不计利害、挺身而出,回荡着一种正气磅礴的侠义气概。在与朋友的相处中,聂绀弩常常仗义疏财、解人之危,事后又不以功自居,充满了古道侠肠的热诚。因而,尽管许多人认为他怪异、难处,但他的身边总是不乏肝胆相照的知心老友。
更为重要的是,聂绀弩的侠义精神,包含着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富于诗意地赞美人的力量和才智:“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样比人更奇异。”[8] (P16)文艺复兴时代,人道主义精神得到空前的解放与发展,上升为一种理性形态。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又使人道主义臻于体系化。在中国,人道主义以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小仲马、狄更斯等作品为载体传输进来,在“五四”运动时形成气候。对这种人本位的思想,聂绀弩是有理性自觉的。他在《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中正确地把鲁迅一生不变的东西概括为“战斗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操”,鲁迅“悲天悯人的情操”,也就是人道主义对人的尊重和爱护。聂绀弩是深得鲁迅精神真髓的人,在他的心灵天地中,“悲天悯人的情操”也是格外突出的,这表现为聂绀弩对普通人、尤其是未曾获得人的各项权利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关注与同情。如他的小说的取材视角就充分显露了他的人道关怀。进入聂绀弩小说画廊的没有任何具有英雄色彩的时代骄子,几乎全部是被灰暗迷蒙笼罩的小人物,有生性慧敏却婚姻不幸的青儿姐姐,有贫穷好赌又爱面子的金元爹,有遭遇水灾、难以果腹的老娼妓,还有风尘猎猎中被甩下火车的白发老人。这都是一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经受着生死考验的底层人民,他们要博取的只是“活着”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婚姻自主、人格尊严等最合乎人性的权利大都还无暇顾及。对这类人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观照,无疑是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在特定的选材范围内,结合作者的情感向度,才能完整地说明作者的思想情怀。聂绀弩在为他的小说集作序时曾说:“我的小说其实都不是小说,而是回忆,游记,散文之类。”考察具体篇目的内容,也可以得出如上的结论。因此,小说中的“我”就可以读解作聂绀弩本人。《天壤》是聂绀弩小说中广为传诵的一篇,它叙述了“我”的同学王龙曲折悲惨的人生经历。当“我”倾听王龙讲述他勇敢地顶住世俗压力、依旧爱护失去贞洁的妻子的故事时,“我”情绪激昂地回应:“我相信你对!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人应该像这样!要一个十六岁的,无知的,又没有人能帮她的忙的女孩子的命,不用说,那是极容易的,而且做了,不但没有人责备,反而有人称赞。可是仔细想想吧,那算什么呢?那算人做的事么?”[7] (P190)此处,聂绀弩用男女平权、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人道主义原则对王龙的行为加以评判,特别强调了具有现代思想的新人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的性别专制、历史惰性作出了无情的反叛。在《夜戏》中,作者明言:“我有一个贱脾气:不喜欢贵族,自然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贵族。”[7] (P66)从小说的内容来看,这种精神上的贵族气,就是等级制度的衍生物,是身居高位者对底层人民的轻视与嘲笑,是完全违背了无贵无贱、无高无低的生命平等原则。聂绀弩之所以对贵族气反感与憎恶,正是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
可见,正义思想中的民族意识、侠义精神中的人道主义情怀,使聂绀弩的自由意志超越了个人精神选择的狭窄界面,获得社会价值和群体认可的意义,完成了他人格存在的双重忠实:既忠实于自我生命的完整与独立,又忠实于社会环境,把自己纳入群体的参照系中,完成现代人格的塑造。
至此,我们清晰地展示了聂绀弩经由无政府主义走向自由意志的精神行旅,为聂绀弩最基本的人格品性绘出了大致的面影。这是一个顶天立地、追求完美公正、敢于反抗世俗的大写的人。这种崇高博大、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促成了尊重自我、注重个体的现代人格的完成,“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并且与其他人区别开来”。[9] (P5)其次,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精神原型之一。它是鲁迅精神的真正传承,是鲁迅之后的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风范,它以穿透历史的浑厚之音告诉我们:你应当拥有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非我的存在;你应是人类命运的沉重的承受者,而不是浅薄、轻浮的个人主义者。这大概就是聂绀弩给我们的人格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