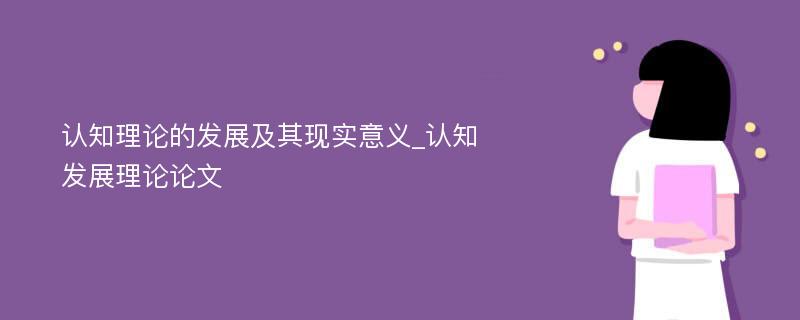
认知论的发展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认知论发展的简短回顾
1927年,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Jean Piaget(1896—1980 )领导的一个小组开始进行儿童认知过程的研究,并取得了杰出成果,为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iaget本人并没有直接研究语言习得〔1〕, 但他的学说却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为以后的语言习得认知理论指明了方向,所以现在人们提及语言学习认知理论,总把Piaget视为其代表人物。
本学派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J.S.Bruner(1915—),他也是最早把Piaget的著作介绍给心理语言学界的学者。
六十年代中期,另一位美国学者J.B.Carroll在美国倡导认知论,他说:“在美国外语教学中如此盛行的听说习惯理论,在十五年前或许与当时的心理思想状况一致,但如今已不再符合新近的发展。对它进行重大修正的时候已经到来,特别是应当使它与认知学习理论的某些合理成分结合起来。”〔2〕
Carroll还是第一个提出认知教学法的学者。 这一教学法的基本主张至今还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到七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认知论研究更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势头,一批很有建树的学者,如J.Anderson等,纷纷崭露头角。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关于思维图象表示法的论证》(1978),《认知心理学及其含意》(1980),《认知结构》(1983)等。1985年,他又修订并再版了《认知心理学及其含意》,对他早些时候的观点予以更新和发展。Anderson的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他成为这一学派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3〕此外,如J.O'Malley,A.U.Chamot,C.Faerch等,也是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成绩斐然的学者。现在,认知论内容比以往更加丰富,也更加系统化了。
认知论在这一时期得到新发展,大概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与交际教学法发展状况有关。交际法自1971年在英国问世以后,对促进外语〔4〕教学起了巨大作用。但经过大约十五年的实践, 这一教学法逐渐暴露出某些不足之处。其一,交际法固然在语言和学习方面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但其心理语言学基础却相对薄弱,因此在解释语言交际的心理活动过程方面难免力有未逮。其二,交际法( Communicative approach)更多地被看作是原则性的总的方法,而不是涉及学习、教学设计和程序的具体方法,所以比起其它教学法来,它给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实施方法留下了过多的余地,如M.Finocchiaro 和C.Brumfit的见解〔5〕与S.J.Savignon的见解就大相径庭。前者是传统的结构——情景法和听说法基础上的改良和发展,而后者却在锐意兴革,主张学生不必先掌握语法词汇等,从一开始就进行交流练习。〔6 〕又如Krashen的语言学习与习得和监检模式理论,既影响巨大, 又招致争议。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交际法的出现尚远未能为外语教学法研究划上圆满的句号,学者们的探索,包括对认知理论的探索,仍一如既往,孜孜不倦。
认知论研究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工智能这一新学科的影响和启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许多成果,被认知论学者所接受和采用,用之于语言习得研究,这就大大促进了认知论向更新阶段的发展。人工智能科学的影响,从认知论研究中所使用的众多有关概念和术语即可见一斑。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认知论本身的吸引力,在于它业已显示的以及潜在的实践价值。
认知论从开始就强调有意识的活动,智慧活动,理解、领悟。它强调“机体内部的活动”,〔7〕, 把学习看作是“包含许多积极心理过程的一种过程,而不只是简单的习惯形成”,它“重视学习者在语言使用和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语法规则的学习方面。”〔8 〕因此,这一理论比曾经盛行一时的行为主义理论及其教学法更少机械性,更符合人类学习的特点。
近年来,认知论研究把外语习得看作是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其理论框架的基础是复杂认知技能学习的一种综合性模式。持这一观点有几个好处:1.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信息处理等学科都对认知技能习得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果我们把这些学科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模式用之于外语习得研究,就能找到一个相应的综合性语言习得理论框架。2.技能习得模式的明确性及其过程方向性使我们能对外语习得过程有深入认识,而这是当前大多数其它模式所无法办到的。3.把语言习得视为认知技能为描述如何提高学习能力提供了一种机制,有助于外语教学方法的发展和使用,比如如何在不同认知阶段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等。
认知论学者们在把语言习得作为认知技能进行研究的时候,特别注意对认知和语言相互作用的研究,他们认为,只有对这种相互作用作出描述,人们才能完全理解外语学习和习得。
认知论研究包括心理语言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如说明性知识在记忆中的命题网络表示法,图示表示法,过程性知识的生成式系统表示法等理论,以及包括外语习得在内的复杂认知技能习得如何从有意识的规则为主的说明性知识学习逐步过渡到自动化处理过程的理论等,都是富有特色的理论,已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关注。这些理论,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述及。以下将着重讨论认知论在实践中的运用问题。
二、认知论的实践意义
认知论是经历了长期过程发展起来的学习理论。它在解释包括外语习得在内的复杂认知技能习得的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对心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独特的宝贵贡献,在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这两个领域中争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化理论,认知论的实践意义是多方面的。在W.Rivers看来,认知论有助于“促进在校学习,有助于尽量利用非正式的偶发学习。”认知论关于“输入处理和输出预处理”的理论“正是我们教授第二语言所需要懂得的理论”。〔9〕而在Robert Bley-Vroman看来, 在“成人外语学习的认知问题解决”方面及其相关的种种机制和过程中,“认知科学过去十来年的研究趋向于发展出非常丰富的认知模式,其特征似乎正合我们的需要。”他特别提到了图式理论,生成式系统等,并把Anderson称为他所“喜爱的学者。”〔10〕不同的学习者,均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从认知论得到启示和指导。这里限于篇幅,将只提及三个方面,即认知论教学法对现行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认知论强调的有意识认知处理是外语学习的特征,以及认知论的生成式系统在外语学习中的运用实例。
(一)认知论教学法的贡献
前文曾提及,认知论的教学法是60年代提出来的。它有点像是一种经过修改的语法—翻译法,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得到推广,“Longman 应用语言学词典”说它“没有形成特有的语言教学法”(P.44)大概就是指此。但不可忽视的是,认知论教学法的许多原则和主张在几年之后出现的交际法中得到了体现,所以Longman词典说, “交际法使用了认知论的某些原则”(同上)。
认知论教学法的基本主张〔11〕包括:
要从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出发传授新的知识。本族语是学习者共有的已有的知识,应在教学中广加利用,必要时可将本族语与外语作比较,以帮助学习者理解语言现象。没有必要排斥本族语。
要帮助学习者把新语言材料和他们本人的生活与经验联系起来,要选择最合适的真实的情景进行教学,反对那种只要机械的反应的情景。
口、笔语是互相促进的,应该同时发展,以加强学习者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像听、读那样的接受性技能的训练应该先于说、写那样的运用性技能。
强调语法形式的功能性用途,不要单学语法规则,而是要学会运用这些规则来表达和交流思想。要避免死记硬背的方法(词汇教学除外)。
利用形象(实物、图画、示意图、流程图)进行教学。
注意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多吸收他们参加语言活动。
根据不同情况使用归纳法或演绎法。
可以说,这些主张大都是我国外语教学界所熟悉、所普遍接受和采用的主张,只不过实行中可能因地、因校、因人而有所侧重。个别主张,如本族语的作用等,学术界可能有不同意见,但造成者人数不少。 Finocchiaro和Brumfit在把交际法和听说法进行对比时, 列举了交际法的22条特征〔12〕,其中“语言项目语境化”,“可以适当使用母语”,“可以采用翻译法”,“阅读和写作可以从第一天开始”等原则和认知论教学法主张一致。至于认知论主张的形象教学、提高学习者学习动力等,尽人皆知也是交际法的基本实践和主张。排除可能存在的学者们的“不谋而合”因素,认知论的主张对交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二)有意识认知处理是外语学习的特征
1995年10月,在重庆外文学会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全国大学英语指导小组副组长、重庆大学韩齐顺教授发表演讲。在指出当年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和8800多名硕士研究生外语考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语法、词汇等语言基本功问题之后,韩教授呼吁外语学习应“认知法和交际法并重”,“既要流畅,又要准确;既要交际能力,又要语言能力”,“要纠错”,从而含蓄地批评了当前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只重交际法,只要流畅,只要交际能力,不纠错的片面倾向,同时也就重申了外语教学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它表达了与会者的共同感受。
如前所述,认知论重视有意识的学习活动,重视语言学习,特别是语法规则学习中学生的积极参与。当前强调认知论具有普遍的意义。
O'Malley和Chamot(1990,P.ix)指出:“我们也已感觉到,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观点的影响下,有意识的认知处理如果不是受到贬损,也是被忽视了。人们似乎认为,第二语言的真正‘习得’是下意识的,有意识的介入反倒会减缓自动化过程。教师在教室中如果把精力集中到让学生理解输入上,‘习得”就会事半功倍。我们希望表明,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可能导致误解,导致教学上的不良后果,如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可理解的输入等。”
这里,O'Malley和Chamot没有提及的另一个不良后果可能是,学生片面理解,盲目接受“边玩边学”等主张,只注意“下意识”学习,不愿正视语言学习的复杂性以及为习得一门新语言而可能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和这类片面观点相反,认知论认为,外语习得在认知和元认知(metacognitive)两个层次上包括了许多有意识的活动。
在认知层次上,外语习得大致经历Anderson所阐述的复杂技能三阶段习得过程,开始是学习包括许多规则在内的说明性知识,再按照规则运用这些知识,使之逐步“过程化”,最后达到“自动化”。而要达到“自动化”决非易事。如果这里的“自动化”就是有些专家所说的“用外语思维”的水平,那么在“学科条件”下,这一过程需要6—13 年的时间〔13〕。没有资料表明,我国有多少外语工作者真正达到了这一水平,不过据Selinker(1972年)和Seliger(1978年)的调查, 外语习得的“成功率”分别为5%和6—8%〔14〕。而据Bley—Vroman 的估计,对成年学习者而言,如果“成功”的意思是达到本族语水平,那么“成功率”为零〔15〕。这些资料至少可以表明,要达到“自动化”费时颇长,且机会不多,程度不同的有意识的“认知处理”活动乃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此外,“自动化”还有相对性,对熟悉信息的处理可能自动化,但一遇到不熟悉的信息,其过程便成为有意识的。可庆幸的是,我们的许多外语工作,并不要求“自动化”水平。
认知层次上的一种典型的有意识活动是练习。认知论把练习视为实现知识性质转变的必要条件。“熟能生巧”已成为外语学习中的格言。除了课堂上教师指导下的练习外,课外的自觉练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课堂条件和时间的限制,学习者得到的语言输入和练习机会极为有限,必须有大量课外练习活动的补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语学习在学习者的内部认知结构、语言能力,学习条件等多方面不同于儿童学语,也在学习环境、师资条件等方面不同于第二语言学习,因此需要更多的学习动力的驱使,更需要学习者当“有心人”,随时都注意观察,倾听,思考,练习,决不放过任何哪怕是能学到一点一滴新知识的机会。
当前外语学习中存在的忽视基本功训练的倾向值得注意。这种倾向除表现在前文提及的笔头考试结果中外,还明显地表现在口语中,笔者在所在学院某系毕业班学生中注意到,不少学生由于在基础阶段没有下足功夫,单词念不上口、音节稍多的词和短语如“enthusiasm”(热情),“sovereignty”(主权),“territorial integrity”(领土完整)等,音素和重音掌握不好,拼读很吃力。念常用单词和词组尚且费力,当然就更谈不上句子和语段层次上的交际活动的“准确、流畅”了。
另外,在元认知层次上,特别是在元认知策略手段的运用方面,包括对学习过程的认识,学习计划的制订,学习时的监检,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估等,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更是显而易见的。善于学习者将不仅在认知层次上努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学习知识,操练技能,也将在元认知层次上竭尽所能,周密策划,在宏观上做好工作,保证自己的学习收到最佳效果。
总之,外语习得是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它不同于儿童母语习得,甚至与第二语言习得也有一定的差别,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认知和元认知层次上都要求学习者坚持不懈的有意识的认知处理活动。
(三)生成式系统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实例
Anderson的生成式系统理论是在近年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提出来的,这些研究开发出了成套的程序形式,用统一的表示原理,显示复杂认知技能在记忆中的表示模式。简单说来,这一系统就是逻辑中使用的蕴含式,即“If-then”式,人工智能学科采用了此式,并将其作为程序设计语言中最基本的条件结构。这一系统包含“条件”和“行动”,条件包括一个或几个“如果”引导的分句,行动包括“则”引导的一个或几个分句。Anderson把“过程性知识”包括在这一系统中。
以下是“O'Malley和Chamot根据Anderson的理论设计的生成式系统运用实例(PP74—75):Production System 1 (P1 )如果目标是与Sally会话,而Sally只会讲英语,则子目标是使用我的第二语言(L2)。
P2 如果目标是使用我的L2,则子目标是开始会话。
(社会语言能力)
P3 如果目标是开始会话,则子目标是说一句我所记得的问候套语。
(话语能力)
P4 如果目标是说一句记得的问候套语,而语境是非正式的,则选用适当的语体。
(话语能力)
P5 如果目标是选用适当的语体,则子目标是说,“嗨,Sally, 你好!”
(社会语言能力)
P6 如果目标是说,“嗨,Sally,你好! ”则子目标是注意尽量把音发得像英语民族的人那样地道。
(规范语音能力)
P7 如果目标是把音发得像英语民族的人那样地道,则子目标是检查自己的语音能否准确传达句子意思。
(社会语言能力)
P8 如果目标是检查我的语音能否传达我的问候之意,则子目标是仔细观察Sally的反应。
(社会语言能力)
P9 如果目标是仔细观察Sally的反应, 而她的反应表明她已听懂了我的意思,则子目标是等Sally答话。
(话语能力)
P10 如果目标是等Sally答话,而她说完之后又问了一个问题,则子目标是听懂她的问题。
(语法能力)
P11 如果目标是听懂Sally的问题,则子目标是把她的问题与我的英语知识和我在会话方面的常识相比较。
(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P12 如果目标是把她的问题和我的现有知识作比较, 而结果使我听懂了她的问题,则子目标是回答她的问题(社会语言能力)。
P13 如果目标是回答她的意思, 而我又想说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则子目标是在回答时注意语序以及名词和动词的结尾。
(句法及策略运用的语法能力)
P14
如果目标是注意语序和名词、 动词的结尾, 而我发觉(或Sally的反应暗示)我犯了一个错误,妨碍了理解, 则子目标是纠正错误。
(社会语言能力和语法能力)
P15 如果目标是纠正错误,则回到P13去。
P16 如果目标是把会话继续下去,而Sally的反应是问了一个我听不懂的问题,则子目标是请她重说一遍或解释一下。
(社会语言和话语能力)
P17 如果目标是请她重复或解释她的问题,而这次我听懂了, 则回到P12去。
P18 如果目标是继续与Sally对话,而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她做些什么事,则子目标是注意她的停顿和语言标记并适当插话。
(话语和策略手段能力)
以上实例体现了会话活动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包含一个层次结构,这一结构含有反映子目标(subgoal )的子程序(subroutine),而子目标依赖于某一转移机会(branching opportunity )作出的选择;另一方面,模式又含有许多转移和退出(branching and exit)的机会。某一次选择决定下一个生成组,这一生成组又产生出一组新选择,等等。如“sally”任何时候都可以说,“Well,I've got to gonow,”或“hey,it was great seeing you.”从而结束谈话。 但“I”可能听不懂或误解这样的话语标记的意思,于是不得不作种种猜测,而每种猜测都可能导致新的生成式,以及新目标和新选择。
像这样把生成式系统应用到语言学习中有非常实际的意义。语言学家们在考虑外语学习中成人认知问题解决模式特征或交流活动特征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其“目标导向”(goaloriented)〔16〕或“目标制导”(goal-directed)〔17〕特征, 生成式系统正是反映了这一特征。有些学习者在进行会话练习的时候常觉得无话可谈,教师也觉得口语课,特别是低年级口语课难上。在明白交流活动的目标导向特征以后,就可运用生成式系统,从任何“目标”,如购物,如借书,如乘车等等,产生出一系列的子目标,子程序,新选择,新生成组等等,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或许能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学习者可以从这样的交流活动中综合运用语法、话语、社会语言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从而全面提高交际能力。
按照Anderson等人的观点,在运用生成式系统的条件- 行动配对进行会话的时候,这样的配对开始的表示是说明形式,通过练习可逐步编译为过程形式,最终能精调到自动化点位。
注释:
〔1〕原指儿童学会母语的过程, 现在人们用它来表示“语言的学习和掌握”。
〔2〕转引自J.C.Richards and T.S.Rodgers,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Cambridge Language Teaching Library,7th printing,1991,p.60.
〔3〕J.M.O'Malley and A.U.Chamot,Learning strategies in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ambridge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pp13,19;
Robert Bley- Vroman,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in S.M.Gass and J.Schachter(eds.):Linguistic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tion,Cambridge AppliedLinguistics,2nd printing,1990 p.54.
〔4〕严格说来,“外语”与“第二语言”在概念上应有区别, 具体在学习环境、师资条件等方面也应有区别,但美国和加拿大用法中不作这样的区别。见注〔8〕,PP108—109。 国内学者似多采用北美用法,多用“外语”一词。
〔5〕M.Finocchiaro and C.Brumfit,A possible lesson outline in The functional-notional approach,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3,p.107.
〔6〕S.J.Savignon,Communicative compelence:theory and classroom practice,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83, p.31.
〔7〕W.M.Rivers,Communicating naturally in a second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6th printing,1989,p.95.
〔8〕J.Richards,J.Platt and Heidi Weber,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Longman,1985,p.44.
〔9〕同〔7〕,P.96.
〔10〕参见〔3〕
〔11〕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P.240。
〔12〕见〔5〕,PP.91—93。
〔13〕潘菽《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P.305。
〔14〕转引自Robert Bley-Vroman,见〔3〕,p.44,Footnote 2。
〔15〕同〔14〕
〔16〕见〔3〕,Robert Bley-Vroman p.54。
〔17〕见〔3〕,O'Malley,Chamot,p.76。
标签: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教学过程论文; 系统学习论文; 发展能力论文; sally论文; 语言能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