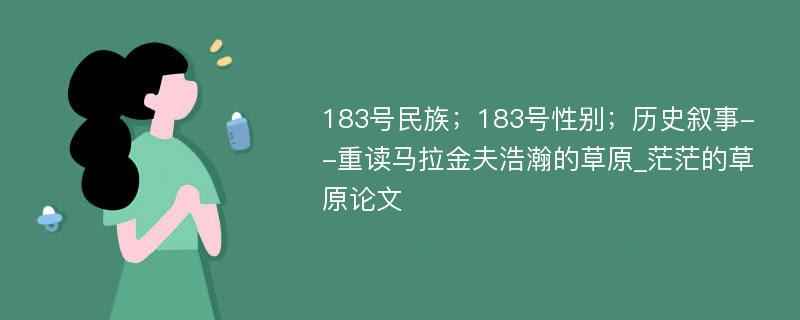
民族#183;性别#183;历史叙事——重读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草原论文,性别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玛拉沁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0-0175-06
《茫茫的草原》是当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代表作,也是其创作生涯中最具生命力的作品。长期以来,这部小说作为书写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之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具备了一定的经典性。《茫茫的草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反映蒙古族生活的长篇小说①,被认为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成就的好书”②,曾获茅盾文学奖提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文本的出现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与汉族文学不同的文学范型,也为其他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这部长篇分为上、下两卷。上部于1957年初版,原名为《在茫茫的草原上》,由于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一些“自然主义”的描写受到批评;1963年,经作者修改,更名为《茫茫的草原》再版。下部则由于“文革”等原因,直至1988年才得以出版。本文的考察对象是1963年修改版《茫茫的草原》(上)。
从作品表层结构看,这是一部相当标准的“革命回忆录”。它与同一时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有着类似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对蒙古族解放斗争历史的描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及经由这一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权、新社会,做出了合法性证明。然而,当我们在性别和民族的视野中重读作品、考察其历史叙事时发现,这一文本围绕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物形象的性别表述呈现出作家主体意识的复杂结构,也敞开了缠绕于叙事肌理深处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
一
一如其他“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茫茫的草原》也是一部以英雄成长为叙事主线的作品。作者在民族革命的大背景下,描写了察哈尔草原上特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从中揭示了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的历史命运。小说着重叙写蒙古族青年铁木尔接受革命的询唤,由一个粗犷、率性、散漫的草莽英雄,逐渐成为一名“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英雄的人生历程。在此过程中,作者的性别想象有着比较清晰的呈现。
首先,铁木尔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借助了“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在小说所提供的叙事语境中,男女之间最基本的性别关系具有“男性:解救、引导/女性:被救赎、追随”的内涵。它意味着故事中的男性人物因其所依靠的“革命”及“党”的意识形态权威的支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女性人物的引导者。传统文化中男女两性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被整合于“革命者/群众”的领导/服从关系中③。置身这一叙述框架的女性形象,客观上成为高大的男性英雄的衬托以及革命神圣的佐证。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斯琴正是如此。虽然这个女子的成长过程表现得有些仓促,但在“十七年”革命文本书写中颇具典型意义。她从最初作为“被压迫阶级历史命运的指称”④,到成为一个让共产党员官布都表示“真不敢相信”的孤身杀敌的女英雄,发挥了衬托铁木尔英雄形象、使之得以凸显的功能。故事进程中,是铁木尔及其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壮大,使斯琴在经历了血的洗礼(流产)后获得了自由;是铁木尔的一番革命启蒙话语,让斯琴意识到只顾“两个人安安乐乐地过日子”“就把受苦受难的牧民兄弟们忘掉”是落后的;是铁木尔的鼓励,让她在“夜黑路生”的情况下“两腿如风”奔走传信;也是“想着铁木尔教给她的射击方法”,她才开出了第一枪。最终,斯琴确如铁木尔所期待和要求的,在关键时刻变得“跟男人一样”,“学会杀敌人”。虽说斯琴的革命动机不那么“纯洁”(她之所以走向革命,与其说源自“有意义的生活的大门”的吸引,不如说更多的是因为受到铁木尔“只要我们一起闹革命,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的诺言感召),但铁木尔所代表的政治属性在此起到了弥补和修正的作用。
从叙事效果来说,斯琴的人生转变自然让铁木尔的英雄人生更为圆满,因为它从侧面写出铁木尔不仅自己“闹革命”,而且还有效地“发动了群众”,也获得了爱情。当然,铁木尔的强大感召力主要并非取决于个体的男性身份,而是来自支撑其形象内核的“党”和“革命”的政治权威。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中描写道,铁木尔在最初脱离“队伍”孤身回村寻找斯琴时,并未能如其所愿夺回恋人;而当他回归党的怀抱、投身火热的斗争,察哈尔草原再掀革命浪潮时,斯琴才终于在反动阶级慑服于革命力量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这样的情节设置不仅帮助斯琴实现了由女奴到女英雄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革命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除斯琴外,小说对另一个女性人物托娅的塑造也是耐人寻味的。初版叙事中,托娅身上表现出一些不乏负面意义的“性别特质”,比如喜欢唠叨、狭隘、任性。她不合时宜地向外人诉说生活的苦楚,还因为丈夫官布整天不在家“产生许多疑心”,时不时“给他点眼色看”(“卷一”第四节)。或许,如此“落后”的精神气质以及她那“一个瘸腿的虚胖的中年女人”的外在特征有丑化革命群众之嫌,不利于神圣的革命叙事,于是,在修改版中,有关托娅的外貌描写被作者删去,这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则被强化了。
说到底,托娅(蒙古语意为月华)可谓“人如其名”,她存在的意义只是停留在如同月亮般反射“革命”太阳似的光芒这一点上。小说描写“健谈的女人”托娅接受了丈夫的教育,又经受了革命的考验。她不再“信口开河”,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与一个伟大的整体有联系的人”,“从它那里得到了鼓舞和力量”。然而,这份欢欣鼓舞在读者看来很容易显得有几分空疏,因为叙事者并没有给托娅以相对充分的自我展现的叙事空间,而只是依赖外部讲述的方式。这样一来,托娅的内心世界被抽空,读者很难触摸到人物自身的感受和思维,托娅很大程度上也便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于是,她的缺乏内在逻辑性的思想提升与斯琴的“被解放”一样,只是观念化地体现着官布的启蒙成果以及革命的强大召唤力,却不曾昭示女性生命的内在律动及其对妇女解放的意义。
不过,如若将这一缺憾归咎于作家艺术功力不足,未免失之于简单。实际上,对“英雄”之外陪衬性人物的符号化处理,完全符合特定时期有关革命题材书写和英雄形象的书写理路;而作品中所流露的男性中心意识也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辨析。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确是从民族独立、阶级革命、国家建设等时代主题中获得价值定位和政治支撑的,而妇女解放对于女性自身的意义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等问题,彼时尚处于被忽略、被遮蔽的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其判定作家有意识地在这部小说中采取了男性中心的叙述方式,毋宁说,他的创作首先是自觉遵从主流政治话语的引导,追随当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模式的。小说艺术表现之得失背后,是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二
值得一提的是,玛拉沁夫的创作一方面受到特定的政治/性别意识形态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并没有放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力。《茫茫的草原》有关共产党工作队政委、女“蒙古八路”苏荣的性别表述,已然构成了一种个性话语与民族话语、国家政治话语并存乃至微妙博弈的场域。“尽管性别、族裔和阶级是具有不同本体论基础的话语,但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他们是纠结在一起的,彼此成为对方的表达形式”⑤。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苏荣,其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在这部小说先后出版的不同版本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其间隐约传达出作者的民族认同意识。
这要从1957年初版本《在茫茫的草原上》中曾经出现的一个人物——汉族共产党员洪涛说起。初版作品发表后,引发争议甚至导致相当严厉的批评的原因之一,即是小说中洪涛这个人物的塑造。在初版文本中,洪涛作为共产党派到草原领导革命的干部,由于不了解当地的复杂局势及蒙古族风俗文化,在工作中犯下许多错误,甚至影响到革命的发展。面对这样的情势,幸有英雄铁木尔力挽狂澜。于是,故事中的这两个分属于汉族和蒙古族的男性人物,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比照。其间通过具体情节从正面得到突出的,显然是小说主人公、蒙古族英雄铁木尔的形象。作品问世后,虽也有评论者从人物典型性的角度入手,以创作艺术方面的不足质疑洪涛这一形象⑥,但更多的批评者还是更为尖锐地着眼于他身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洪涛“作为党的领导形象出现,是失败的”;进而判定作者“流露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⑦。
在“文学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玛拉沁夫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改。一方面,他接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询唤;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放弃艺术家的能动性,而是在小说修改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的叙事策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小说初版与修改版对洪涛和苏荣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不同处理中见出。修改版中,当叙述者开始说到苏荣时,先是简单交代了其“雄化”的外部特征(如:“两条男人的粗眉”“迈着男人一样的步子”),继之便将更多的目光投注于苏荣身上的“女性特质”。例如作品几次提到,她像个“牧妇似的”熟练地从事给小羊羔喂奶、烧牛粪之类带有一定“技术性”的草原女性生产生活劳动,表现了“牧民妇女的勤劳传统”。而这个人物的性情也很符合传统性别文化中对女性的想象:她常常满怀柔情地思念丈夫、女儿,对同志亲和多于威严;在革命工作遇到困难时,她曾流露软弱;在有的同志对她不够尊重时,她深感委屈。然而,如若将这类叙述归之为“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⑧,恐怕并不恰当。因为从整个文本的生产过程来看,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恰恰有着创作主体面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规约,在文本中做出某种策略性回应的意味。
修改后的小说叙事中,洪涛这个人物被彻底删去,曾在初版“卷二”中出现过的骑兵师政委苏荣成为用以替代他的重要人物。这一改动关系甚大:草原上党和革命的领导人从汉族变为蒙古族;从男性变为女性。正是通过这样的变化,作者得以有效地回避了先前为一些文学批评所指摘的“问题”:一方面,苏荣作为在草原上生活过的蒙古族女性,与当地民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也便少了犯洪涛式错误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她是作为一名能够体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少数民族干部出场的,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不利于蒙汉民族之间的团结的迹象”⑨。与此同时,小说叙事对苏荣性别特质的强化和渲染,很容易让读者注意到其女性身份。于是,这一人物所具有的融合了民族、性别、政治因素的复合身份,显然使之更容易在草原蒙古族民众中获得亲和感和影响力;对于作者来说,也有利于避免因人物涉及不同的民族给文学叙事带来的风险,有可能出现的文学叙事上的“失当”或“狭隘”。
不过,小说中的女干部苏荣虽然在草原上拥有革命领导者的身份,但在革命进程中的关键时刻还是离不开官布、铁木尔等男性的帮助和支持。她对他们的钦佩和欣赏总是显得十分自然。比如在苏荣受到被敌对分子挑唆的战士们持枪围攻的危急时刻,是铁木尔果断地鸣枪示警,据理争辩,化解了一场风波(“卷一”第九节)。当革命局势恶化,队伍中出现重大分歧时,是官布三言两语就平息了纷争。苏荣不由得“钦佩地看了官布一眼”,深深折服于官布身上“那种神秘的力量”。而基于苏荣的政治身份,这种赞赏也便多少带有“党”的认可的意味(“卷二”第二节)。经由这样的叙事,官布、铁木尔的形象再次得到合情合理的映衬和彰显。
从洪涛到苏荣,由男性到女性,这一角色变动所具有的多方面功能在小说叙事中得到了发挥。作者不仅规避了先前受到批评者指责的“问题”,而且借助于对小说人物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置换,在叙事的缝隙间,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蒙古族身份自我认同的主体意识。不过这一变换并没有影响到传统两性认知的内核。
三
《茫茫的草原》从民族生活经验出发,以人道情怀和女性关怀意识观照处于历史边缘的蒙古族女性的境遇和命运。在作家笔下,除了苏荣那样的革命女性外,也不乏普通蒙古族女性的身影,例如贡郭尔家“最冷酷的人”“黑心肠的人”女厨师笃日玛、刚盖老太太以及其他牧民妇女。这些女子在喧嚣的民族历史舞台上或掩面行走于帘幕的背后,或只是一闪而过,甚至不过是无名的存在。她们处于传统政治结构的底层,映现着蒙古民族历史的沉重叠影以及传统社会中女子生命的卑微。
作者在描写刚盖老太太贫病无依的处境以及笃日玛被霸占的苦命时,无疑是充满同情的,但作为一名接受了革命启蒙的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她们的蒙昧。于是,“两眼全瞎”还绕蒙古包祈祷以还“心誓”的刚盖老太太,在铁木尔无声的质询下显得那样荒诞愚钝,而笃日玛的宿命论也被另一个苦命人斯琴的人生变幻击破。但小说并没有从叙述者的角度对这些迷信言行作出批判。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其说源自作者对这种带有一定宗教文化意味的民间信仰的认同,不如说最主要的是源于对蒙古族民间生活以及蒙古族女性历史命运的深刻理解。
蒙古族独特的生存环境及其曲折的民族历史使人们对生命苦难的感受尤为敏锐,尤为痛切。而蒙古族女性作为性别权力格局中的弱者,所承受的苦难往往比男子更多、更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她们对命运的呼告常因微不足道而被淹没,于是,她们很多时候转而求助于承诺来世的宗教,祈望从中寻求慰藉和指导。玛拉沁夫笔下为刚盖和笃日玛这两位普通女性所做的生命速描,正是基于对蒙古族女性传统命运的深刻了解。其中既有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也反映出作者的人道情怀和朴素的女性关怀意识。
《茫茫的草原》在故事讲述中,还隐约透露出作者对妇女解放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困惑和思考。“卷二”第七节,描写了那达慕大会上苏荣作为妇女“求解放、求进步的榜样”,被一群牧民妇女围住,回答各式各样的“妇女问题”。当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问起这位“能管男人们的女英雄”是否可以“打男人”时,人们哄然大笑,苏荣也忍不住大笑。而就在她想对那位妇女再说几句的时候,对方却已失望地离去。文本中,苏荣貌似没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而事实上,正因为作者没有安排她来回答,才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阶级革命创造了性别解放的神话,承诺给予妇女种种权利,但却未能触及男权文化的核心,无法解决“丈夫打了我几十年”这样的关系到妇女基本生存状况的问题。而蒙受家庭暴力,几乎可以说是传统社会草原深处的牧民妇女最为普遍的性别境遇,所以,她们迫切期待改变这样的关乎日常生活的命运。
如同有论者所指出的,在特定的意义上,叙事本身即是一种支配、甄别和操纵⑩。从整体叙事效果来看,小说中这一情境的书写,对故事的推进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并无明显功能。换句话说,如果设计如此这般的提问细节只是为了突出革命事业感召力的话,作者尽可以让人物提出另外的、更便于阐发主题的问题,然而他却让笔下的人物选择了性别话语。由此可以说,文本中无名妇女的发问以及苏荣的不曾回答,并不仅仅是作家人道主义情怀和女性关怀意识的自然流露,而是蕴涵着作者对人物的性别身份及其性别境遇的关注。
四
《茫茫的草原》中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女性形象——寡妇莱波尔玛。这个人物在作品初版发行后,曾引起颇多争议。小说发表伊始,就有评论者从道德批判的角度称:“这个形象比较追求的主要是肉欲的满足”(11),更有论者对作家在书写莱波尔玛这样有“乱糟糟的男女关系”人物时,“总是以客观的欣赏态度写的”表示强烈质疑(12)。然而,在1963年版的《茫茫的草原》中,玛拉沁夫虽然删去了对她的一些性爱描写以及抒情性的赞扬语句,但依然将莱波尔玛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去表现,以至于一些细心的评论者在肯定修改本比初版“更上一层楼”的基础上,仍含蓄地指出,相关“描写还嫌过多”;也有直率者明言其“过多地描写了她在性生活上的放任”。尽管文本中所谓的自然主义描写不过是对人的生命欲望的合理表现,但在那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语境中,玛拉沁夫的固执坚持显得相当特别。时过境迁,而今,当我们把莱波尔玛这个人物形象放置在蒙古族文化谱系以及蒙古族文学史的链条中加以观照时,不禁若有所悟。
翻开蒙古族文学的图卷,很容易发现对生命爱欲的热情渲染。事实上,在古老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英雄婚姻是最重要的母题之一。蒙古族的文艺创作在叙述英雄求婚情节时,总是会重叠复沓地歌咏女方矫健丰美的身姿形态;《蒙古秘史》中,亦有大量以欣赏口吻描述男女结合的语句;民间传唱的婚礼颂词中,更有许多对婚姻之于生命、人生以及族裔的重要意义的夸张表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对女性体态美的欣赏以及对男女之间两厢情愿的性行为的肯定,已经融入了蒙古民族深层的审美心理。
产生这种独特的审美心理,有生态环境的因素,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历史的生命记忆和心理积淀使然。世代游走于高寒地带,历经部族战乱,由兴盛到衰微的民族命运,清代喇嘛教对族群的变相削弱等等因素,使蒙古族民众形成了以种族繁衍为立足点的带有忧患色彩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内驱力的推动,促使当代许多蒙古族作家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具有一定独特性的审美风貌。某些时候,这种风貌可能与主流审美意识有所背离(13)。
《茫茫的草原》中玛拉沁夫关于莱波尔玛这个人物的“不合时宜”的艺术表现,一定程度上正可视为这种深层审美心理外化的表现。在这一审美想象图景中,人的身体本能属性获得了合法性。玛拉沁夫关于莱波尔玛的性爱描写,主要传达的是其对健康自然的生命存在形态的欣赏和生命机体活力的赞叹。性爱在一定意义上是生命激情的涌动以及族群繁衍的重要前提,在这一审美维度下,文本中性爱描写的文化意蕴与“十七年”主流叙事文本中意识形态化的身体叙事呈现出明显差异。后者往往将身体叙事整合在政治叙事中,通过两性关系的“非道德化”以及对女性躯体的“物化”修辞方式,描述女性的生命欲望,从而使性欲求与政治落后、道德败坏构成一定的对应关系,进而指认其负面价值。而玛拉沁夫为了保持其性爱描写的独特内涵,尽可能回避了类似的叙事模式。这一点从修改本对卡洛的性爱描写的变动中也可见出。与初版本相比,修改本关于卡洛的性爱描写篇幅少而抽象,与主流文学中处理“反面”女性形象时身体叙事的意识形态化保持了距离。
此外,值得称许的是,玛拉沁夫对莱波尔玛的描写并没有男性“窥视”的意味。自始至终,莱波尔玛的爱欲抉择都符合她自身的生命逻辑,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或许,与其他人物相比,身为女性的莱波尔玛不需要承载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因而作家有可能更多地赋予其理想的人性。莱波尔玛那因思念而流露的柔情,因爱而不得的纵情痛哭以及与情人相会时的率真表达,无不生动地展现着人性的丰富。在“十七年”文学中,这一形象具有特殊价值。
综上,《茫茫的草原》对主要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传统社会的性别定位;与此同时,作品对蒙古族女性形象的描写,有着多重话语的复杂缠绕,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诉求。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历史叙事别具蕴涵,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收稿日期:2011-06-15
注释:
① 特·赛音巴雅尔:《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② 王志斌:《〈在茫茫的草原上〉值得一读》,《内蒙古日报》1959年6月8日。
③ 参见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④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⑤ [美]伊娃-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秦立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孟和博彦:《动荡的草原,光辉的道路——评〈在茫茫的草原上〉》,《文艺报》1959年第24期。
⑦ 丁尔纲:《关于〈在茫茫的草原上〉的座谈》,《草原》1959年8月号。
⑧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⑨ 孟和博彦:《动荡的草原,光辉的道路——评〈在茫茫的草原上〉》,《文艺报》1959年第24期。
⑩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2页。
(11) 丁尔纲:《关于〈在茫茫的草原上〉的座谈》,《草原》1959年8月号。
(12) 魏泽民:《漫谈〈在茫茫的草原上〉的爱情描写》,《草原》1959年9月号。
(13) 例如,1960年扎拉嘎胡在小说《柳燕去过的地方》(《草原》1960年第2期)中,对牧民因性病被祛除而流露的欣喜情态展开描述,就与当时追求纯洁道德的时代审美导向格格不入。
标签:茫茫的草原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玛拉沁夫论文; 草原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蒙古族论文; 革命论文; 铁木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