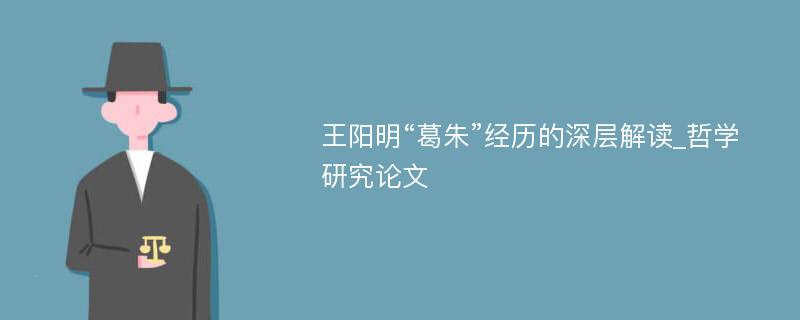
王阳明“格竹”经历的深层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阳明论文,格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即:他生平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往往会直接影响其思想的转变或发展进程。阳明早年的“格竹”经历及其由此引发的思想转向,就是其中的典型个案之一。据《年谱》记载,弘治五年壬子(1492),21岁的阳明随作官的父亲王华在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1223页;以下凡引此书,简称《全集》)阳明早年出入佛、道,思想面貌颇为复杂,然而透过其“泛滥无归”的表象,仍然有理由将阳明的思想立场定位于他心目中的“圣贤之学”亦即儒学上面。但具体言之,这里所谓儒学,当指程朱理学,尤其指朱子(熹)学说。朱子学说作为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凭借其特殊地位影响包括青年阳明在内的士人思想。在此背景下,阳明追随朱子学说,将其奉如“神明蓍龟”(《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第78页),便很自然地成为他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朱子一生对儒家经典《大学》十分重视,尤其重视《大学》中作为“八条目”之首的“格物”。他在论及《大学》时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朱子语类》卷十四)因而可以说,“格物”是朱子《大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不仅如此,实际上格物还是宋明新儒学者所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儒学内部思想争论的焦点。青年阳明当时集中思考的也正是格物问题,他对此问题的关注,恰恰是在程朱学派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的。弘治二年己酉(1489),18岁的阳明“始慕圣学”,并拜谒了著名的程朱派学者娄一斋(谅),一斋对阳明所述,便正是“宋儒格物之学。”(《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3页)弘治五年壬子(1492),阳明“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同上)他运用朱子的格物学说,于父亲官署内亭前格竹之举,也就发生在这一年。
格竹事件在阳明的一生经历中颇为引人瞩目,凡有关阳明思想的论著鲜有不道及者。对于阳明这次格竹经历的评价,在学界前辈和时贤中存在着肯定与批评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持肯定态度的代表人物先后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容肇祖、黄仁宇,以及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冈田武彦等人(注:康有为批评朱子不得《大学》格物其解,“宜来阳明格竹之疑也。”又说:“阳明因格物不可通,遂攻朱子。”参阅康著《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明国朝学派》,中华书局1988 年3月第1版,第7、280页。章太炎晚年对阳明甚推崇, 在言及朱子格物论时说:“阳明初信之,格竹七日而病,于是斥朱子为非是。朱子之语,包含一切事物之理,一切事物之理,原非一人之知所能尽,即格竹不病,亦与诚意何关,以此知阳明之诛朱子为不误。”参阅章著《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85页。胡适在《中国哲学的线索》、《先秦名学史》等著作中多次分析了阳明由格竹失败而开始怀疑朱子的格物理论,参阅《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91年12月第1版,第523—524、769页。相近的评论,还可参阅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1992年4月影印第1版,第74页;〔美〕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1982年5月第1版,第222页; 〔日〕岛田虔次著:《朱子学与阳明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82页;〔日〕冈田武彦:《阳明学之研究与受用》,刊于《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第7页。),他们的评论颇能切中肯綮,有的还不乏思想史分析的深度,但未及作前后连贯的深入阐释。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主要有刘述先、陈来、姜广辉等人(注:参阅刘述先:《论阳明哲学之朱子思想渊源》,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5卷(1984年);姜广辉:《阳明哲学的视角》,刊于《哲学研究》1993年第5 期;陈来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3 月第1版,第21、132、340页,及《朱熹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53页。),而其中以陈来的批评最为尖锐,评论亦最为详尽。对于阳明格竹的批评,其主要观点是:阳明亭前格竹穷理的故事,只不过是思想史上的一件“轶事”或“笑谈”;此事的发生和结果,完全是出于阳明对朱子格物论的“误解”,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阳明当时过于年轻,思想很不成熟,还不能真正了解朱子哲学格物论的全部内涵。
本文认为,在上述对阳明格竹的批评性意见中存在着两个有待辨析和考察的问题:第一,亭前格竹的故事,对于阳明的思想演变来说只不过是一桩毫无意义的“轶事”、“笑谈”,还是应当视为青年阳明的一次严肃、真诚的精神探索?第二,阳明格竹经历的发生和结果,是由于青年阳明的思想不够成熟而导致的对朱子格物说的“误解”,还是应当将其看作阳明从怀疑朱学开始、直至扬弃朱学并自创新说这一思想转向过程的契机和起点?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正是评价和阐释阳明格竹经历的症结所在。
二
对阳明的格竹经历持批评态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将其看作一桩对于阳明的思想演变历程并没有什么意义的“轶事”和“笑谈”,认为,“朱子格物之说出,数百年间更无一人误以‘面竹沉思’践之,何英敏如阳明,反有此亭前之笑耶?”(陈来著《有无之境》,340 页)据称,将阳明的格竹经历视为“笑谈”,其主要理由是认为阳明“误解”了作为格竹理论依据的朱子格物论。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集中加以分析。此外,视阳明格竹为“笑谈”,其理由可能还包括阳明格竹的动机和行为本身都是荒唐可笑的。那么,究竟能否将阳明的格竹经历仅仅定性为一桩“笑谈”?抑或能否换一个视角,将其看作阳明的一次精神探索?这里需要结合格竹一事的展开过程,以及当事人后来的自我评价进行分析。
嘉靖二年癸未(1523),阳明于江西平定宁濠之乱后归越。在越期间,其学已臻“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明儒学案》卷十)之境。阳明晚年居越讲学,格物问题是重点内容之一。阳明于讲学中相当详实地回忆和总结了自己早年格竹之事,他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120 页)
从阳明自己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与钱子“着实”实践朱子的格物说,把格竹当作“格天下之物”的出发点,其动机高远纯正(“与钱友同论做圣贤”),其态度和行为也很严肃认真,这里看不到任何玩世不恭的影子。当然,阳明自己是决不会把早年的格竹经历视为“笑谈”的,否则,他在思想已臻“化境”的晚年向门人重提这段旧事,岂不成了当众自我取笑?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阳明之所以于晚年向弟子重提格竹往事,是由于他对早年的这次特殊经历给自己造成的精神冲击很难释怀,因而特意于讲学中现身说法,向门人讲述自己当年格竹的切身体验及在夷中所悟的格物之旨,帮助弟子理解格物的真意,即:“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与那种把阳明格竹视为“笑谈”的观点截然不同,本文提出,应当把阳明的格竹经历定性为他早年的一次严肃、认真的精神探索。这主要是由于,青年阳明当时遵循朱子的格物论去格竹,并没有把朱子理论视为最终的真理,而是要以亲身实践去探寻一种真正有益于自己身心的精神锻炼方式。正因为如此,他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才能做到不苟从或依附于朱子思想,而是在尊崇朱学的同时以切身体验去印证朱子学说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实践朱子的格物论并不是他格竹的根本目的,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做圣贤”。在真正的儒家学者心目中,成圣成贤是他们的最高人格理想;如何“做圣贤”则是他们整个生命活动的中心。而格竹的结果使阳明感到,按照朱子的方法向外求理竟如此繁难,虽然自己的努力已达极限却毫无结果;而且,即使求得竹子之理,又怎样才能够与自家的安身立命和生命理想相联系呢?
青年阳明运用朱子的格物论难以达到“做圣贤”的理想,这标志亭前格竹的失败。这次失败,使阳明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一方面,格竹失败使阳明(及钱子)对朱子的格物论充满了失望和怀疑情绪(“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这实际上是青年阳明对朱子学说最早的一次质疑和挑战。看来,以主、客二分对峙为基础,把向外寻求某种客观知识作为提高道德意识之前提的格物方法,是很难适合于阳明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另一方面,这次格竹失败又顺理成章地成为阳明在精神探索过程中寻求新的格物方式的一次机遇,它后来转化为探求和选择新的精神方向时的动力源泉。同时也可以说,正是这次失败的经历,为阳明日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后来的事实表明,阳明所追求的格物方式决不是认识论的,而是道德论和生存论的。就是说,它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道德践履的完整方式,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以心性(“良知”)为本体论前提,以道德理性(“理”)为价值论依据,以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同一为哲学基础,以主体的内在决定(“立志”和“诚意”)为中心环节。这样,在阳明的心目中,格物的功能便不再是认识论的亦即获取外物知识的方法,而是以精神锻炼和道德努力为旨趣的修身功夫(注:参阅拙文:《王阳明“诚意”说的伦理哲学特质》,刊于《陕西师范大学报》1995年第4 期。)。阳明对格物的这种重新解释,实际上触及了一个为历史上东、西方许多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即:如何理解“理论知识”(客观知识)与“实践知识”(道德知识)之间的区分?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时指出:“道德的知识显然不是任何客观知识,求知者并不只是立于他所观察的事实的对面,而是直接地被他所认识的东西所影响。道德知识就是某种他必须去做的东西。”(《真理与方法》上卷, 洪汉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403 页)与朱子的格物方法强调以“客观知识”来解决人的信念和道德问题的企图相对立,经阳明重释之后的格物观念则着意强调了“道德知识”(“良知”、“德性之知”等)与主体道德实践之间的直接同一。这也正是阳明于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之后不久便提出著名的“知行合一”说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由此看来,阳明对朱子格物说的批评和对儒家格物观念的重释,是有坚实的哲学根据的,也是符合人类道德法则的普遍要求的。
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即:在前引阳明居越讲学时忆及早年格竹的论述中,他意味深长地将早年的亭前格竹与十余年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的龙场悟道相提并论,这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这两起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所周知,正德三年戊辰(1508),37岁的阳明赴谪夷中,在那里发生的龙场悟道一事,是他终于彻底摆脱朱子思想矩矱、转而自创新说的标志,也是他思想演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次精神事件。就阳明思想转向前后的长期探求所涉及的问题性而言,当主要关乎格物的实质,以及与格物直接相关的心、理之间的关系。从阳明思想转向的结果看,他于龙场“一悟至道”,可以说已经按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了格物问题和心、理关系问题,即所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8页)
龙场悟道的重要结果之一,是阳明终于找到了能够适合于自己精神和道德生活需要的格物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阳明经历中的亭前格竹与龙场悟道分别代表了两种路向不同的格物方式。这两种不同格物方式之间的矛盾胚芽,其实在阳明格竹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孕育。当然也应当看到,阳明并未因格竹的失败便立即否定朱子之学。阳明比较明确地对朱学提出怀疑,是在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27岁的阳明在实践朱子“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之后,仍不免心存疑窦,并指出了朱子“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4页)的理论矛盾。也正是在阳明对格物等问题的长期潜心探求和反复实践的基础,再加上他在政治斗争中身陷逆境等缘由,才最终发生了“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的龙场悟道事件。
综上所论,本文不同意将阳明格竹视为一桩不可理喻的“笑谈”这种轻率的断言,因为这既未触及阳明格竹经历的实质,也忽略了格竹事件在阳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三
由于亭前格竹事件的发生及其对阳明思想走向的影响,都与朱子的格物理论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为格竹事件的定位还需要以阳明与朱子格物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中心,作更深层、多视角的探析和阐释。
对阳明的格竹经历持批评态度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格竹的发生是由于阳明“误解”了朱子的格物哲学。所谓“误解”,是说阳明“不能真正了解朱子哲学格物论的全部内涵。”(《有无之境》第2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具体言之,是指“阳明把朱子的格物哲学了解为面对竹子的沉思”(第132页),“误以‘面竹沉思’践之。”(第340页)阳明为什么会“误解”朱熹的理论?批评阳明格竹的观点认为,此中有两条原因。第一条原因是,“阳明当时过于年轻”(第21页),“思想还完全不成熟。”(第132页)这种分析显得相当浮面化, 因为衡定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成熟,很难单纯用其年龄作为尺度(这里是指在成年人的范围内);而且,这种判断往往还要受到判断者的立场和视角的囿限。第二条原因是,阳明对朱子格物哲学的了解“是宋明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说,“除青年阳明之外,所有学者都能正确了解朱子的意旨”(第21页)。据此,便断定阳明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判断中,隐含着以多数人的理解作为真理标准的观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阳明格竹一事发生的真正原因,其实在前引阳明本人的回忆中已经陈述得相当清楚。阳明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这里,阳明揭示了一个易被忽略而又相当重要的事实,即:尽管众多的朱学追随者在口头上都表示格物一定要依循朱子的学说,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实意地去实践。然而阳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一反当时“只说”而不用的学风,对朱子的格物说是“着实曾用来”的。也正因为如此,阳明格竹才成了宋明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事。问题在于,并不能因为阳明格竹之举的罕见,就断言它一定是不能“正确了解”朱子格物哲学的结果。阳明按照朱子格物说“去用”,于亭前连续格竹七日,这恰恰表明:阳明当时虽然年轻,却是一位能够真诚地、甚至狂热地去身体力行的朱子学追随者。当然,阳明当时追随朱学,是企望它能够有效地指导自己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有助于自己去实现“做圣贤”的人格理想,而并非要以做一个朱子学者本身为目的。
那么,阳明格竹究竟是否“误解”了朱子的格物学说呢?这需要将朱子格物说的要点与阳明的理解作一个比较。如前所述,朱子一生中特别重视《大学》的格物思想。他训解“格物”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格物”之“物”,泛指“天下之事”,包括“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朱子语类》卷十五)朱子格物说所强调的,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考察和认知,因而其主体与客体二分对峙的认识论特点是显而易见的。经由这种认识论的考察和认识,才能达到“穷理”的目的。在朱子看来,一物有一物之理,格物就要象程伊川(颐)所说的那样,“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逐渐积累对万物之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朱子语类》卷一一七)就是说,通过上述真积力久的格物功夫,逐一积累有关各种事物之理的认识,最终便会“豁然贯通”,掌握“天理”这一宇宙间的最高原理。应当承认,朱子的格物说强调对经验知识和万物之理的积累,其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完善人性,提高人的道德意识。这诚如朱子所说:“物理皆尽,则吾之知识廓然贯通,无有蔽碍,而意无不诚、心无不正矣。”(《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
阳明格竹的直接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着实”“去用”朱子的格物说,“穷格竹子的道理”。作为以竹子为对象的认知活动,其方法当然也包括“面竹沉思”等环节。而阳明格竹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做圣贤”的道德追求,这从他格竹失败后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这一感慨中看得很清楚。这样,从阳明格竹的直接动机、方法依据和终极目的诸方面来看,都与朱子格物论的要求和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阳明当时对朱子格物论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偏误。
伽达默尔说过,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卓越的宽广视界,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2页)故我们在“观看”亭前格竹一事时, 应当将它置于阳明思想演进的链条之中,看作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仅仅视其为一起偶发的孤立事件。若断言阳明的格竹经历缘起于他对朱子学说的“误解”,则可能会遮蔽我们的视域,使我们无法看清格竹经历在阳明哲学思想演变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因而,从严格意义的哲学历史分析着眼,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察,包括解析和阐释阳明格竹事件的直接结果及其对阳明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格竹事件的直接结果有两个:一是阳明全力以赴地连续格竹七日却未能获得竹子之理,二是阳明深感运用朱子的格物方法很难实现“做圣贤”的根本目的。据此,我们可以断言阳明的格竹是失败的。阳明格竹的失败,暴露了朱子格物论中的两大难题:其一,一物(竹)尚且如此难格,更何况要“格天下之物”,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其二,即使能够从外界事物中格得“理”来,这外物之“理”又怎样才能转化为指导自己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准则?正如阳明晚年所总结的:“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119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阳明格竹的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也可以说格竹的失败其实正是朱子格物论本身的失败。阳明欲解决朱子格物论的内在难题,就必须扬弃朱子哲学,对格物观念做出新的阐释。
阳明批评朱子“错训‘格物’”(《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5页),阳明独发地将格物之“格”改训为“正”, 将格物之“物”改训为“事”。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第972页)这样, 阳明就将“格物”重释为主体调整和端正自身行为、“去恶为善”的道德实践活动。经由阳明的重释,就把朱子向外格物的方向扭转为向内“在身心上做”。应当指出,阳明强调格物当重内(身心),并不是看不到外界客观事物的存在,而是反对朱子那种把外物当作注视或沉思对象的认识论态度,主张作为真正的人(“大人”)应当是与世界万物无所间隔、融为一体的。这种宇宙论同时也是精神境界论,在阳明的成熟思想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其基础是主、客体之间的直接同一,其核心则是人心的“仁爱恻怛”。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也往往体现在对待自然环境包括花、草、竹、木的态度上。正如阳明所说:“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同上,第968 页)因而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格物等修身功夫又是达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境的重要方式。在阳明看来,由于朱子的格物论过分强调外在经验知识积累的优先性,故在实践生活中很容易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把本来只是作为主体自我实现中介环节的“物理”知识的获取,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这就必然会冲淡人性的道德自我完成的紧迫感。而且,有在外物知识积累的无穷环节与提高道德意识的终极目的之间的脱节,也很容易导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28页),亦即重知而轻行、甚至知而不行等流弊。质言之,阳明反对朱子把格物归结为外在事物的探究和经验知识的积累,主张格物应当是以先验的道德之知(“良知”)为基础的、主体自我实现的完整实践过程。
当然,阳明在格竹失败的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清楚地认识和完全解决朱子格物论的内在难题。阳明从实质上理解格物的内涵(“颇见得此意思”),是在格竹事件发生十余年之后的夷中(龙场)。尽管如此,我们评估亭前格竹事件在阳明思想演进中的地位和意义时却完全有理由将阳明对朱子格物之学的否定看作一个从比较朦胧到逐渐自觉,从起初失望、怀疑到最后彻底扬弃的长期酝酿过程。如果阳明对朱子格物学说的否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酝酿过程这种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酝酿过程的起点追溯至亭前格竹事件。从阳明格竹失败后发出“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的感叹声中,分明流露出了他对朱子格物方法与自己“做圣贤”的终极目的之间很难契合的失望情绪。正是由于格竹失败的冲击,阳明才对朱子的格物论产生了疑惑,才有可能逐步理解和解决其难题;也正是由于这次精神碰撞,才激发了阳明日后调整和重新选择致思方向的决心,转而另辟蹊径,探觅出一条不同于朱子哲学的新思路。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亭前格竹看作阳明思想转向的重要契机和起点,看作阳明逐步走出精神危机,扬弃朱学并开辟新的思想方向的转折点和推动力。因而完成可以说,早年的格竹经历对于阳明的思想演变进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若没有这段经历,也就不可能有日后的龙场悟道亦即阳明哲学思想的转向。
总之,作为一次重要精神探索的格竹经历,在阳明思想演变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意义也很深,它为阳明哲学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转捩点。阳明后来扬弃朱学和自创新说的学术历程,也都是基于此而逐次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