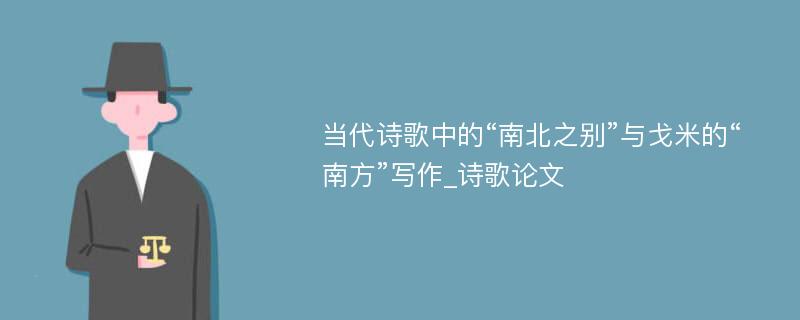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4-0060-0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9 墨西哥诗人帕斯在《百年佩索阿》的序言中说:“诗人们没有传记,作品就是他们的传记。”[1]对于中国当代诗人戈麦(1967-1991)而言,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用。在思索“那强大地把他(戈麦)推向诗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诗人西渡认为:“对像戈麦这样的诗人,要从他的生活传记中寻找这方面的原因的努力,也许将是一个错误。”[2]戈麦现存的生平资料是有限的,但他的诗歌作品却透露了更多关于他心灵的真实信息,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南方”情结。 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都在北方的诗人,诗歌也不乏北方之文“体峻词雄”[3]的特点,但在他的一些诗作中却出现了对“南方”的想象。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戈麦诗歌中所指认的“南方”,狭义上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南方地区,广义上则是指与戈麦所居住的北京这一地点相对的整个“南方”,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南方地区,还包括南半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戈麦生前所喜爱的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故乡阿根廷。据戈麦长兄褚福运、友人桑克、西渡所编《戈麦生平年表》来看,戈麦生前曾在1991年1月到上海访施蛰存,5月到四川访艾芜,这是目前仅有的关于戈麦与地理位置意义上的“南方”发生实际关系的两次记录。[4]由此看来,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有部分的经验来源,但他在南方停留的时间过于短暂,在诗作中显现出的生活经验相比于一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诗人而言是较为模糊和抽象的,所以其诗歌中的“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 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还与他所推崇的博尔赫斯有关。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是一个“打破现实/非现实二元对立”[5]、充满幻想特质的故事,诗作《南方》也具有梦幻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方”即幻想。而戈麦的“南方”书写也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从而与博尔赫斯的作品有着某种共通性。不仅如此,从写作日期来看,诗人对自己“南方”题材的诗作均进行过精心修改,从而形成了“一题两诗”的状态,这体现了戈麦对诗歌语言“精确性”的追求。因此,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不仅是深植在诗人心灵之中的“想象的经验”,也是对诗歌语言可能性的探索。 二、中国当代诗歌“南北之辨” 在出生于四川的诗人钟鸣的认识中,“朦胧诗”是“北方诗歌”,而“后朦胧诗”则是“南方诗歌”,他在随笔集《旁观者》中为“南方诗歌”的边缘地位感到焦虑,并深情呼唤和赞美“南方”:“谁真正认识过南方呢?它的人民热血好动,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于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却重义气,不惜一夜千金撒尽。固执顽冥,又多愁善感,实际而好幻想。……这就是我的南方!”[6]另一位川籍诗人柏桦也认为,自1978年来,中国“诗歌风水”发生了几次转移:北京“今天”派(1978-1985)是最先登场的,然而四川诗歌又以“巫气”取而代之,1992年之后,诗歌风水在江南[7]。柏桦还征引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的观点来证明“南”“北”诗歌之不同,刘师培所说的“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被柏桦引为同道。这些观点让人想到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为文学决定性要素的论断。诚然,对于诗人而言,他成长、求学、工作所处的地理环境或地理环境的改变或多或少会影响他的个人气质、创作素材和创作风格等。人们也可以在一些诗人的创作中指认出清晰可辨的地理特征来,如昌耀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他诗中的意象就多为雄浑壮阔的高山大川,呈现出一种“大”气象;而潘维的诗作,则以“江南雨水”作为关键词,体现了江南文化的清新秀美。就此看来,似乎“南方诗歌”、“北方诗歌”这种带有文化地理学意味的划分法是根据确凿的。 可是,当代诗歌是否存在绝对的“南北之别”,或者把后殖民话语应用到“南北”划分中(即北方为中心,南方为边缘)是否得当,是有必要详加辨析的。首先,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南北”差异肯定存在,但“南北”也只是一种相对的风格辨析,难以概括诗歌的全貌,诗人的作品风格也存在复杂性。所谓的“南北”之别,是整体风格上的概括,而非绝对。一位于“南方”成长起来的诗人可能会用北方歌喉歌唱(如海子),一位“北方”诗人也会在诗中书写南方(如戈麦)。其次,“南北”或许会存在政治意义、群体意义上的差别,但却无文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之分。即使是《南北文学不同论》的作者刘师培,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评价“南—北”之文时要用客观的眼光,否定绝对的“南北之别”:“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其所好而已。……一代杰出之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8]再次,虽然洪子诚先生曾提到:“朦胧诗运动的区域,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之后探索者的出身和活动地,则主要在南方。”[9]但运动的地点并不等于诗歌的艺术特质,因此绝对意义上的“北方诗歌”“南方诗歌”并不存在,对“话语权”的争夺并不能掩盖文学本身的特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南北方”并不应该成为划分“北方诗歌”“南方诗歌”的绝对标准。 戈麦成长于黑龙江,求学、工作于北京,可谓是一位地理意义上的“北方诗人”,他的诗作中也不乏“北国”、“冬天”、“冰雪”等典型的“北方意象”,在《冬天的对话》《一九八五年》《岁末十四行》等作品中,这些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并且,戈麦诗歌语言冷峻、坚硬的质地,也与“北方气质”相契合。但这并不影响戈麦在诗歌中对“南方”进行书写,尤其是在1991年2月,戈麦集中创作了一组以“南方”为题材的诗歌,分别为《眺望南方》《南方》和《南方的耳朵》,并对这些诗稿进行过反复修改,形成了“一题两稿”的现象。在这些作品中可以见到戈麦作为一位“北方诗人”对“南方”的经验与想象,既体现了戈麦诗歌中来自北方的“体峻词雄”的语言特点,又糅合了南方意象的精致与柔美。因此,戈麦对“南方”的书写可以视为一种“跨地域书写”。然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是他个人“南方”情结的集中体现,其现实来源固然可以追溯到戈麦短暂的南方游历,但那并不足以让戈麦成为一位地理意义上的“南方”诗人,戈麦对“南方”的情结更多是他心中深藏已久的“向往”。他的“南方”书写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三、戈麦诗歌中的“南方”情结 戈麦作为一位地理意义上的“北方诗人”,却对“南方”有着深切的向往,在他作于1991年5月的《自述》(此时戈麦已去过上海)中可见一斑:“戈麦寓于北京,但喜欢南方的都市生活,他觉得在那些曲折回旋的小巷深处,在那些雨水从街面上流到室内、从屋顶上漏至铺上的诡秘生活中,一定发生了许多绝而又绝的故事。”[10]这种对“南方”的眷恋,看似与戈麦成长于东北、求学于北京的生活背景相矛盾,但这可以反映戈麦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喜欢神秘的事物,如贝壳上的图案、彗星、植物的繁衍以及怀疑论的哲学。”[10]“神秘”这个词语可被视为理解戈麦思想的关键词,戈麦之所以崇敬博尔赫斯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给世界带来的是月晕和神秘的背景,而不是燃烧的花朵、火热的太阳”[11]。“南方”就是一个“神秘”的象征,诗人生前仅两次短暂地到过中国南方,不曾在南方长期居住过,现实意义上的经验可谓是浅薄的,“南方”对于戈麦来说更多的是一片未知、充满神秘感的地域。“南方”意味着一种“诱惑”,而这种“诱惑”来自于虚幻的想象。对于见惯黑土白雪的戈麦而言,“南方”无疑意味着一种新鲜、别样的经验。因此才有“身为过客却念念不忘”的“南方”情结。 从《戈麦诗全编》收录的诗歌来看,“南方”这个意象在1987年12月修改后的《刑场》一诗中首次出现:“枪声尚未响起/青色的狼嗥着南国的歌声”。“南国的歌声”在这首诗中显得比较突兀,因为前面的诗句一直在铺设寒冷、死亡、衰颓的场景:“从寒冷的尸谷走来/墨黑的冰河上/漂浮着天主教堂/沉沉的钟声//数以万计的囚徒/如亿万棵颓老的病树/从冰层深处/沉郁地呼唤着回声。”而“南国的歌声”无疑给这充满末世感的景象带来一种新鲜的血液和生命的气息。但“南方”在戈麦的诗歌中也不总是代表“希望”的,相反“南方”这种“想象的经验”也蕴含着“失望”的因素“可江南女子的青春/只是一只苦涩的微笑/苦难过去了倦容依旧”(《失望》)。在现实意义上的“南方”经验尚未形成的时候,“南方”对于诗人只是一种纯粹的想象,诗人在向往“南方”的同时也想到了可能的失望感,南方的美丽中可能也隐含着衰颓。这种对“南方”的纯粹性想象还表现在戈麦对南半球地理景观的幻想性书写之中。如“在南极这样一个冰雪的夜晚,/南十字星座垂在明亮的海岸。/世界,已滑到了最后一个狭谷的边缘。”(《南极的马》);“亚马逊平原,黄金铁一样的月光/流满这昂贵而青色的河/阿斯特克人灰白的废墟/远处,大森林,虎豹的怒吼一浪高过一浪”(《黄金》)等。在现实经验匮乏的情况下,戈麦的“南方”书写完全借助于幻想来实现,对“南方”幻想的来源也许来自诗人的阅读体验。正如诗人在其后期诗歌《南方》中所说:“我在北方的书籍中想象过你的音容”,或许由幻想而生的“南方”情结还过于浅薄,因此诗人此时并没有对“南方”这一题材进行集中书写。 戈麦真实的“南方”经验始于1991年1月。据《戈麦生平年表》和《戈麦诗全编》,戈麦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在十天之内(1991.2.3-1991.2.13)集中创作了《眺望南方》《南方》《南方的耳朵》等一批南方题材的诗,并对这些诗作进行过修改,形成了一稿、二稿并存的格局,可见戈麦对自己诗歌技艺要求之严格,也可见戈麦对这些南方题材诗歌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修改稿和原稿在诗句顺序、语言锤炼等方面有了较大改动,但诗句中最基本的意象却没有很大变化。如在《眺望南方》的两个版本中,都出现了“高原”、“草原”、“植物”、“冰海”、“星辰”等意象。与《眺望南方》想象中的南半球异国风情不同,《南方》和《南方的耳朵》更多的体现了秀美的中国江南风情,如“我在北方的书籍中想象过你的音容/四处是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南方(二)》);“我目睹南方的耳朵/开放在我洁净的窗前/开在水边/像两朵梦中出生的花瓣/像清晨,像菩雨,像丝绸的波光”(《南方的耳朵(二)》)。从“亭台”“越女”“菩雨”“丝绸”这些意象来看,戈麦所认识到的“南方”具有古典意味,是一个传统的“杏花春雨江南”。不过,从现实的观点来看,1990年代的中国“南方”却已逐渐离这种情调和氛围远去,现代化的世俗生活正在迅速蔓延,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悄然替代了“亭台”“越女”的存在。戈麦的“南方”,与其说是南方生活现实体验的描写,不如说是诗人的“心象”,这种具有幻想特质的“南方”在现实生活中是渐趋衰微的。 由此可见,戈麦诗歌中的“南方”情结的来源有戈麦为数不多的中国南方生活经验,但更多地是对“南方”的想象。所以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状态。同时,戈麦诗歌中的“南方”情结又体现了戈麦对南方生活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在“北方”诗人写作中,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930年代的北平“前线诗人”群中,就有对“南方”的“驰想”,这与他们身处“荒街”一般的现实环境形成明显对比,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诗作中都有对“南方”的歌唱,“南方”在他们的笔下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繁荣美好的未来,以及母亲胸怀般的温暖和安全”。对“南方”的呼唤也是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向往与渴望。[12]这与戈麦的“南方”情结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不同。卞之琳、何其芳都生在江南,对“南方”的呼唤多带有对旧日实际生活的怀想色彩,用来与现实的荒凉相对照;而戈麦是一位成长、学习、工作皆在北方的诗人,他虽有短暂的“南方”经验,但他的“南方”书写更多是基于对“经验”的“想象”,因而多了一层梦幻的感觉,现实与幻想的距离变得模糊和不真。这样的状态,恰恰也是戈麦所尊崇的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作品中追求的。 四、戈麦的“南方”与博尔赫斯作品的关联 在此可以探讨的是,戈麦的“南方”情结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影响之间的关联。博尔赫斯的作品自1986年之后被大规模地译介到中国,而这一时期也是戈麦开始诗歌创作的时期。戈麦曾在《文字生涯》中谈到博尔赫斯对其诗歌创作和人生选择的意义:“就在这样一种怀疑自身的危险境界之中,我得到了一个人的拯救。这个人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1]并且戈麦有过这样的断言:“如果说维多夫罗(智利诗人——引注)在某些方面还带着较为浓重的欧洲先锋文学的风范,那么博尔赫斯则更带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致与格调。拉丁美洲是一块巨匠辈出的新大陆。”[11]戈麦诗歌中对拉丁美洲这块南半球大陆的想象性书写,也时有体现:“亚马逊平原,黄金铁一样的月光/流满这昂贵而青色的河/阿斯特克人灰白的废墟/远处,大森林,虎豹的怒吼一浪高过一浪”(《黄金》);“在那曙光微冷的气色中/潘帕斯草原/你的茂盛有一种灰冷的味道/在这两块大洋,它佛手一样的浪花/拍击之下/你像高原上流淌下的铁”(《眺望南方(二)》)。这些描写无疑给人一种陌生感,它们更多与诗人的想象相关联,而非源于现实的场景。 或许是在博尔赫斯的影响下,戈麦的“南方”与后者笔下的“南方”发生了微妙的联系。博尔赫斯著有短篇小说《南方》,收入其《虚构集》中。博尔赫斯本人很看重这篇作品,并在《虚构集》的1956年补记中写到:“《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13]这篇小说记叙了“一个具有阿根廷和欧洲血统的男子胡安·达尔曼内心冲突的戏剧化”[5]。故事的灵感来自博尔赫斯本人受伤住院的一段经历——他在败血症的折磨下,一度出现了幻觉——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达尔曼也处在现实与幻觉的交错中:他被大夫宣布身体好转,可以去南方庄园休养了,于是坐上了去南方的列车;诡异的是,这辆列车停靠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在那里下车后,他决定做一次“小小的历险”,却莫名地卷入了几个醉酒年轻人的械斗之中,为了彰显自己的“南方”精神,达尔曼决定接受年轻人的挑战,“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小说在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坐上火车去“南方”的是现实中的达尔曼,还是达尔曼在病痛中的幻觉呢?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就此存在不确定性,经验和想象变得模糊,因而充满了开放性。而戈麦的诗歌《南方》则与博尔赫斯的这篇小说不仅在标题上形成呼应,内在肌质也有许多暗含之处。诗中,“像是从前某个夜晚的微雨/我来到南方的小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达尔曼坐火车到“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同时,“我”也同达尔曼所做的“小小的历险”一样,“在寂寥的夜晚,徘徊于灯火陌生的街头”,并且“我”也在对自己的这一经历感到怀疑:“我是误入了不可返归的浮华的想象/还是来到了不可饶恕的精神乐园”;“我”对自己经历的怀疑,与博尔赫斯《南方》的结尾带来的歧义性相类似,只不过戈麦诗中的“我”把博尔赫斯在小说中未明确提出的观念明确了。正如有论者指出:“在博尔赫斯那里,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心灵的罗盘,而它给出的向度则注定是形形色色的幻想。”[14]戈麦正是把博尔赫斯的“幻想”进行中国化、诗意化,两者在“幻想”这个层面上遥相呼应,形成了关联。 博尔赫斯还有一首题为《南方》的诗歌,勾勒了一幅他心目中的“南方”场景:“从你的一座庭院,观看/古老的星星/从阴影里的长凳/观看/这些布散的小小亮点/我的无知还没有学会叫出它们的名字/也不会排成星座;/只感到水的回旋/在幽秘的水池;/只感到茉莉和忍冬的香味,/沉睡的鸟儿的宁静,/门厅的弯拱,湿气/——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15]“星星”、“水”、“茉莉”、“忍冬”、“鸟儿”、“门厅”这些陌生的事物,究竟是“我”在现实中看到的,还是想象中的呢?诗中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并且诗人也没有明确肯定“这些事物就是诗”,而是插入“也许”一词,使得这些本来亦真亦幻的事物更添了一层不确定性。这样的“双重虚幻”也出现在戈麦的诗歌中,他在《南方的耳朵(一)》中写到:“我在一个迷雾一样的早晨/目睹了南方的耳朵/开在我的窗前/像两朵雨水中闪亮的贝壳/或是两朵清晨的梦中出生的兰花/这一景致并非寻常的幻象/幻象是一种启示/这一景致也非寻常的梦境/梦境是一种宫怨/但它不是”。“我”在“迷雾一样的早晨”看到的“南方的耳朵”,既像“贝壳”也像“兰花”,非“幻象”也非“梦境”,看起来它离诗人距离很近(“开在窗前”),却又是诗人“此生此世难以接近的纯洁”。“南方的耳朵”在此成了一个具有悖论性的超现实意象,从而比一般的想象更为神秘。因此,戈麦的“南方”题材的诗歌与博尔赫斯的诗歌《南方》在“幻想”这个层面也有着共通之处。 五、戈麦的“南方”书写所展示的语言探索 从更深层面来说,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以及《眺望南方》《南方》《南方的耳朵》出现的“一题两稿”现象,显示了他对诗艺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具体而言,即是一种严苛的对待诗歌语言的态度。 戈麦是一位高度重视诗歌语言的诗人,他在《关于诗歌》一文中这样说:“诗歌应该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16]这种对语言于诗歌之重要性的强调,类似于马拉美“将语言的无穷潜能作为自己诗歌的真正内容”[17]的主张。恰如西渡提出,将戈麦某些诗歌的一、二稿的差异进行比较,就会看到一首诗是“如何在艰苦的劳作中逐渐锻造成型的”,这也是“与传统的写作方式迥然相异的一种写作方式”。[18]戈麦书写“南方”的诗歌中“一题两稿”的现象,正是他对自己诗歌语言进行精心锤炼的结果。在戈麦的诗句中,“读者会经常听到一种清晰的挖掘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个神秘歌唱者的语言的暗夜融入了发现的新生”[19]。戈麦的诗歌时常迸发出一种警句般的震撼力量,词与词、词与句、句与句之间呈现出尖锐的张力,渗透进读者的心灵。戈麦这种对语言的重视使他对语言的使用更接近于波德莱尔所指称的“语言魔术”:“艺术地处理一种语言,意味着进行一种召唤魔术。”[17] 以下仅以两个版本的《南方》诗稿为例,分析戈麦对诗歌语言的严格要求和精益求精的语言探索: 南方(一) 那是前一个晚上遗落的微雨 我脚踩薄绿的青苔 我的脚印深深地印在水里 一直延伸到小巷的深处 这是一个不曾破译过的夜晚 我从早晨到达的车站来到这一爿屋檐 浅陋、迷濛,没有更多的认识 因而第一个傍晚 我仍然徘徊于灯火萧索的街头 耳畔是另一个国度的音乐,另一种音乐 那种柔软的舌音像某些滑润的手指 它在我心头抚起一层不名的陌生 我是来到梦里 还是被世界驱赶到经验的乐园 从此的生活是要从一种温暖的感觉开始 还是永远关闭了走回过去的径巷 南方,从更高的地方不可能望到你的全貌 在那雾一样的空气下层 是亭台的楼阁和越女的清唱 我还能记得这漫长的古国 它后来的几百年衰微的年代中 那种欲哭欲诉的情调 但我只能在狭窄的木阁子里 静静地倾听世外的聊赖 一缕孤愁从此永恒的诞生 它曾深深埋藏在一个北国人坚实的肺腑 今日我抑不住心中的迷茫 我在微雨中摸索,从一种陌生到另一种陌生 1991.2.3 南方(二) 像是从前某个夜晚遗落的微雨 我来到南方的小站 檐下那只翠绿的雌鸟 我来到你妊娠着李花的故乡 我在北方的书籍中想象过你的音容 四处是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 漫长的中古,南方的衰微 一只杜鹃委婉地走在清晨 我的耳畔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东方 我抓住它,那是我想要寻找的语言 我就要离开那哺育过我的原野 在寂寥的夜晚,徘徊于灯火陌生的街头 此后的生活就要从一家落雨的客栈开始 一爿门扉挡不住青苔上低旋的寒风 我是误入了不可返归的浮华的想象 还是来到了不可饶恕的经验乐园 1991.2.13 从篇幅来看,《南方(二)》明显对《南方(一)》(28行)进行了压缩(16行)。在形式上,《南方(二)》将《南方(一)》的不规则的4—6行一节,调整为整饬的4行一节,而且每行字数也大体相同,更体现出“句的均齐”,节奏感得到进一步突显,产生了良好的听觉效果。正如西渡所说,戈麦的诗体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句子长度大体相等,三、四、五行为一单元的整齐、匀称的音节,饱满、充盈的诗歌节奏。”[2]这样看来,戈麦追求的乃是马拉美式的“讲求智识的、形式严整的抒情诗”[17]。不仅如此,《南方(二)》在锤炼语言(表现为剔除冗余、精简词句)的同时,还凸显了语言的张力的运用,如该诗最后两句“我是误入了不可返归的浮华的想象/还是来到了不可饶恕的经验乐园”,否定词“不可”和自我疑问的运用,“想象”与“经验”二词的对峙,使读者更为深入地进入戈麦构筑的经验与想象交错的“南方”世界。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南方”世界呢?诗中的叙述者“我”在“夜晚遗落的微雨”中来到“南方小站”,来到在“北方的书籍”中想象过的地方,从“哺育过我的原野”来到“灯火陌生的街头”,所置身的无疑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国度。“我”徘徊于现实的“经验”和梦境中的“想象”之间,现实与梦境之间的距离变得模糊,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空濛与迷茫,但正是这种全新的“想象”中的“经验”,才让人向往,因为神秘的也是迷人的。这种神秘感正是其诗歌语言带来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南方(二)》较之《南方(一)》,抒情的成分少了许多:“我”不再倾诉,“我只能在狭窄的木阁子里/静静地倾听世外的聊赖/一缕孤愁从此永恒的诞生”。诗人把情感浓缩在诗句中,虽未言明自己的心态,读者却能够从“误入”与“来到”之间的犹疑和矛盾中感受到“我”的“一缕孤愁”。而正是在独处之中,“我”才能回到内心,进入灵魂栖居的空间,更好地倾听“另一个国度的音乐”。此种“孤愁”或许可与林庚《沪之雨夜》中的“幽怨”(“雨水湿了一片柏油路/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相提并论,二者都是通过“听”而产生的情绪,体现了置身于陌生环境中的孤独感。 此外,就这两个版本的《南方》中所包含的主要意象来看,也体现了戈麦作为一名北方诗人对“南方”的独特体认。虽然,戈麦是怀着某种古典情怀想象“南方”的,他笔下出现了诸如“青苔”、“小巷”、“亭台”、“越女”、“落雨的客栈”等富有典型“南方”特色的元素,但在这两首《南方》中,戈麦似乎更关注“南方”元素的组合所烘托出的具有朦胧效果的氛围,而并不在于具体的元素本身。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戈麦诗歌中“南方”的“经验”与“想象”边界的模糊感。 “那可能与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诗人穆旦曾在诗中如是说。对于戈麦而言,他似乎更倾向于“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无论是他的“南方”情结,还是他诗歌中的“南方”书写,都存在着经验与想象边界的不确定性。经验伴随着想象产生,而想象中又混杂着经验,但想象始终要胜于经验。戈麦正是试图用“想象”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心中的“南方”,而非单纯的再现。这种“想象”中的“经验”正如西渡所说:“戈麦在诗歌的诸手段中把想象力提高到独一无二的位置。他认为,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他相信,‘现实源于梦幻’、‘与其盼望,不如梦想’。”[2]因此,戈麦的诗歌“不愿再用人们通常所称的现实来量度自身,即使它会在自身容纳一点现实的残余作为它迈向自由的起跳之处”[17]。 戈麦的“南方”,是语言造就的“南方”,是他充满幻想的产物。这种“幻想”的成分也渗透到戈麦的众多“南方”书写之外的诗歌中,如《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南极的马》《帕米尔高原》等。这些诗歌中流露出的幻想特质,暗示他追寻着比现实更高远的生活,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俗世生活”。因为他声称“通往人间的路,是灵魂痛苦的爬行”(《空望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