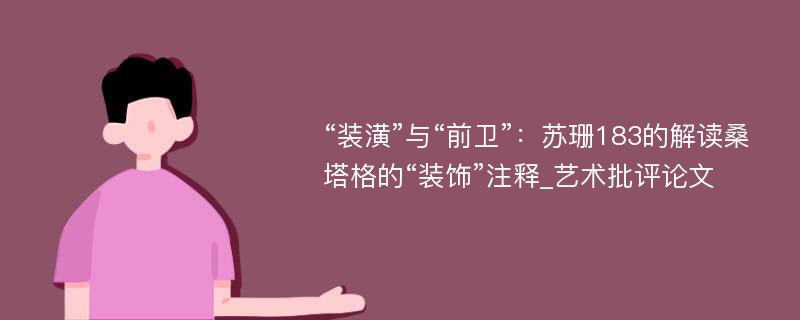
“矫饰”与前卫——解读苏珊#183;桑塔格的《“矫饰”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笔记论文,桑塔格论文,苏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珊·桑塔格于1964年在美国文学刊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秋季号上发表 《“矫饰”笔记》(Notes on‘Camp’),旋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效应。她之所以能在美 国文坛引起震荡,是因为她与从前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作品的纽约派耆宿不同:桑塔 格对60年代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毫无芥蒂之心,而是完全抱以认同的态度(注:Carl
Rollyson,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Chicago:
Ivan R.Dee,2001,p.vii,p.69,p.69.)。虽然她在文章中仍大肆评论和引用欧陆大师级 的经典文学和艺术,却同时也对好莱坞电影、摇滚乐表示青睐,并以当时的时髦话语称 自己为“嬉皮士”。综观桑塔格后来的文学创作,除了她近期的长篇小说之外,基本上 是她理念和批评思想的注脚。质言之,她的批评主张就是提倡冲破一切现成的艺术观的 禁锢,表现对生活的直接感受,放弃抽象的阐释,直抒情真意切的情愫。她认为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把艺术形式推至本体的极致,任何二元对立、把文本的形式和内容分割开 来的企图不啻把艺术的“诗性”剥离殆尽,是对文本的“翻译”和“改写”。她认为对 文本的阐释就是对艺术的无知,就是干涉作品。她响亮的口号式宣言是,“批评的作用 应该表现一样东西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甚或它就是这个样子,而不能表现它的意图 ”(注:Susan So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Octagon Books,1982,p.14,p.7.)。
显而易见,桑塔格的观念里还深深烙下了以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印记。 这种把养料建筑在欧洲的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之上的批评理论赞扬人类学、 考古学的新发现,欣赏人类共同创造的神圣礼仪、民间故事和神话的奇迹。它的特点是 不相信科技,追求精神上的理想意义,对人类的原初意义很感兴趣(注:参见杨任敬《2 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版,第604页。)。桑塔格对艺术真性和感悟性(sensibility)的张扬,以及对人类自科学启蒙运动以来对远古神话力量的消解和失去信 任的抨击都反映出她对尼采哲学的信奉,并站在现代西方文化病态的角度上呼唤着神话 的回归。科学性由于对世界采取了“现实”的观照,于是后神话时代意识中便固执地萦 绕着一个问题:宗教符号是否依旧合适。于是纯洁透明的古代文本不再被接受,阐释便 应运而生,成为古代文本和“现代”需求之间寻求折中之路的媒介;于是荷马笔下诸神 的行为便有了道德意义;希伯来的《圣经》亦成为精神的范本,为进入迦南之地而在沙 漠中展转四十年的出埃及故事被解释成个人的灵魂解放、受难和最终解脱的寓言。桑塔 格对用社会学的眼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挖掘文本的潜在意义的做法颇不以为 然,称其为“是智性对世界的复仇”,她称这样的“阐释会掏空并让世界匮乏,以便建 立起一个充满‘意义’的浅薄世界”。是为了把世界变成“这一个世界(好像还真存在 着‘这一个世界’)”(注:Susan So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Octagon Books,1982,p.14,p.7.)。
可以说,桑塔格的形式主义美学是建立在存在主义的本体怀疑论之上,即对世界的本 源产生怀疑,认为世界是荒谬而不可知的,人类的命运便是自我的丧失,因而文学无法 完成阐释生命深层意义的使命。传统的道德认识论批评已被她彻底摈弃,形式上升为审 美的主要对象。她的这种观点不免有失偏颇,但鉴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界普遍存 在的庸俗阐释之风,她的美学主张也确实能让人们把焦点转移到艺术的感悟经验上,用 生命的感受提高审美实践能力。
一、《“矫饰”笔记》的基本美学内涵
如果说桑塔格发表于1964年的《反对阐释》一文是她形式主义美学标志性的一声号角 ,她的《“矫饰”笔记》则如一曲委婉动听的行歌,详尽表述了她对艺术形式的认识及 种种定义,可以看作是《反对阐释》的进一步延伸。“矫饰”两字是用引号括起来的, 在桑塔格那里绝无贬义,而是一种时尚的称谓,指涉一种感悟能力。“‘矫饰’本质上 是对超凡脱俗、艺术性和夸张的热爱”(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 Susan Sontag Reade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Inc.,1982,p.105.)。 “矫饰”一词在英语中的起源含混不清,它大致在1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流行,20世 纪初特指英国的下层社会和“风流社会”(包括戏剧业、时尚业和演艺业),并且还囊括 了后王尔德(post-Wildean)时期的另类群体行为。战后时期掀起的流行文化的狂潮把“ 矫饰”文化变成边缘领域的一部分。总之,“矫饰”最初是作为一种卑琐的街头亚文化 语汇出现的,在文化的边缘占领着一席空间(注:See Fabio Cleto(ed.),Camp:Queer Aesthetics and The Performing Subject—A Reade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44.)。它是神秘的,是一种私有编码,一种体认的标识。桑塔 格又进一步说明“矫饰”是某种美学模式,是审美现象的一种方法,为此它并非是美本 身,而应从“艺术性和风格的度”的角度去理解。作为批评家,桑塔格的功绩在于她将 审美的视野扩展到了文学之外,囊括了摄影、电影、绘画、疾病乃至色情文化等领域, 艺术形式之美在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相互渗透和互动的,因此她列举了一些实例对“ 矫饰”艺术形式做进一步的阐发。当然,谁也不可能完全认同她列举的范例,但从中却 可看出,桑塔格的美学理论不仅为后现代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融合以及边缘艺术向主 流艺术逼压的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驱动力。
为了昭示艺术形式所能给人带来的感悟性,她特别强调“矫饰”主要体现在服饰、家 具、后摇滚、古典芭蕾、歌剧、电影以及所有视觉装潢上,“因为这些侧重的是质感、 感性表层以及摈弃内容的风格”。但音乐会不属此类,因为它本身缺乏内容,无法让丰 富的形式与滑稽可笑的内容形成对比。这里,桑塔格已把形式升华到本体的地位,试图 抵制后工业社会给人们情感和精神上造成的麻木愚钝状态。艺术美在桑塔格眼里是有意 而为之的,因此与自然无缘,而模仿则是西方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侧重模仿对象的 内容。桑塔格以为“矫饰”与城市的事物相对应,具有田园风格的宁静率真,即爱默生 所说的“城市田园”。桑塔格最为崇尚的是法国新艺术派的作品,因为这一派的任何实 用物品都被赋予了艺术形式:灯具成为花卉植物的造型,客厅俨然是石窟,连巴黎地铁 的入口都在19世纪末由吉马赫设计成了兰花茎的风格。贯穿在桑氏理论中的重要一点是 形式美感在观者眼中的延宕效果,为此她极力赞赏布莱希特的“间隔效果”电影艺术, 她还欣赏法国导演布莱森的影片,因为后者让画面“智力化”,将过多的情感介入抽离 ,并以重复形式的手法让观众直感画面的审美体验;而过多注入情感则会使美感瞬间耗 尽。同样,后拉斐尔绘画中的中性人、新艺术插图画中的性别模糊的人体以及影星嘉宝 美艳背后的性别剥离效果,都是“矫饰”的艺术形式。
桑塔格认为,上述这些形式抽绎了道德伦理指涉,可让审美体验在形式美上长久伫足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嘉宝的独特之处在于概念的层次,而赫本处于物质层次。嘉 宝的脸是一种理念,赫本的脸是一个事件”(注:Roland Barthes,“The Face of Garbo,”in Mythologies,trans.Annette Lavers,New York:Hill and Wang,1972,p.57 .)。相对于代表理念的嘉宝的脸,赫本的脸被巴特作为一种形式符号升华到艺术的本体 论高度,变成了一种形而下的在感官上追求美感的诉求,这与桑塔格的观点是不谋而合 的。具体落实在文学文本上,桑塔格认为“矫饰”类作家包括卡夫卡、阿托尔、萨德、 兰波等,因为他们创造的不是和谐,而是尽力拓展艺术形式的张力,创造出激烈和不可 解决的主题,如苦难、残酷和疯狂。这种感悟力所坚持的原则“只有‘碎片’的形式才 能成为可能”(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 ,p.280.)。桑塔格把感悟力一分为三,第一种是传统道德型,第二种是先锋派作品,这 类作品在道德和美感之间制造紧张感,第三种是纯审美型的。显然,她的立场是拥护第 二和第三种类型,因为用她的话说,“矫饰”代表“‘风格’对‘内容’的胜利,‘审 美’对‘道德’的胜利,以及反讽对悲剧的胜利”(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 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总之,《“矫饰”笔记》一文较全 面地反映了桑塔格的美学观点,她提出的“寓严肃于嬉戏,寓嬉戏于严肃”的观点正是 许多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所遵循的路数,这类观点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当然, 她理论的片面性及虚无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文本的艺术形式无论如何表现,其价值归 根结底还是在于表达的意义。
二、“矫饰”美学与前卫和大众文化的关系
二战之后的纽约知识分子仍把前卫艺术看作一种恪守艺术自律的活跃的思想和姿态, 桑塔格也对前卫先锋艺术很感兴趣,认为它是抵抗社会及知识层面自满自足的有利武器 。然而她更愿意探索和发现那些边缘和新生的“感悟”与“风格”,以挑战美国没有实 验性美学的保守观念;她的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先锋艺术已走入学院派的殿堂并被博物 馆驯化的时刻,希求探索一下前卫艺术是否能重新担当起批评的作用。
20世纪整个40和50年代期间,老派形式主义批评家格林伯格和麦克唐纳一直在把先锋 艺术与大众文化隔离开来,格林伯格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认为只有先锋艺术才能保证“ 文化的继续发展”(注:See Liam Kennedy,Susan Sontag:Mind As Passion,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27,p.27,p.33,p.34.) 。他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解读现代主义,将艺术的“纯粹”概念建立在艺术作品是独立 自足和自我合法化的理念之上,把现代艺术的美学标准看作是“最高的内在价值和终极 价值,其超越对象惟有自身”(注:See Liam Kennedy,Susan Sontag:Mind As Passion ,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27,p.27,p.33,p.34.)。据此,他将那一时期的抽象表现主义称为这种“非再现性”美学的最高旨归。桑塔 格对这种把精英文化象牙塔化并将大众文化排斥在外的做法不以为然,在对待诸如机遇 剧(happenings)等边缘文化的态度上,她与本雅明保持着相同的理念。本雅明对超现实 主义兴趣浓厚,认为这一流派在把“通俗”的日常生活物品并置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机 械复制生产时代对现实新秩序的“亵渎的澄明”;当艺术失去其“光晕”或崇拜性质时 ,他看到了新的感官经验乃至激进的政治意识被敞开的可能性(注:See Walter
Ba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n David H.Richter(ed.),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2nd edition),Boston:Bedford Books,1998,pp.1109-1114,p.1125.)。本雅明对“非光晕”艺术可以带来新的感官刺激的观点显然影响了桑塔格,后者还将这一影响与超现实主义的反艺术的游戏倾向结合起来,作为创造新感悟的“工具”(而在格林伯格看来, 超现实主义则是对与世隔绝的先锋艺术的一大威胁)。
在谈到“光晕衰退”时,本雅明曾指出其中一项重要的社会原因是“当代大众从空间 和人性角度把事物‘拉近’的欲望”(注:See Walter Ba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n David H.Richter(ed.),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2nd edition),Boston:Bedford Books,1998,pp.1109-1114,p.1125.)。桑塔格在美国“文化饱和”的状态下虽对这样的“拉近”抱有些许怀疑和忐忑不安的态度,却仍首肯本雅明的观点,并把“矫饰”列为她认为的三种“伟大的创造性感悟”之一;另外两种感悟是“高雅文化……(以及)严肃性和先锋艺术中情感的极致”(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矫饰是“失败了的严肃性以及经验戏剧化的感悟” ,是“持续不断地面对世界的美学经验”(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 91,p.289,pp.288-289,p.277,p.280.)。前卫或先锋艺术严肃性的标志是痛苦、残酷和 失常,而矫饰却表现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幽默与智慧,尤其是其对平凡的诗化”(注:See Liam Kennedy,Susan Sontag:Mind As Passion,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27,p.27,p.33,p.34.)。美国批评家大卫·伯格 曼把矫饰定义为一种崇尚夸张、造作和极致的风格,他指出矫饰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 以及消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而且能体验矫饰的人势必在主流文化之外。最后他还 把矫饰与同性恋文化联系起来(注:See David Bergman(ed.),Camp Grounds:Style and Homosexuality,“Introduction,”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pp.4-5.) 。同样,桑塔格也把“矫饰”附着于同性恋文化之上,认为“矫饰趣味”是同性恋者一 种自我合法化的姿态,“他们是以促进美学的方式溶入现代社会的”(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 ,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然而她又指出 矫饰远远不止限于同性恋情趣,因为“它是势利品味历史的一部分”,象征着坚持一种 “越来越独断和奇特方式的贵族姿态”(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这种趣味“大概只出现在富裕社会,在能经历富裕 心理病理学的社会或社交圈子之中”(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在谈到这一点时,桑塔格直接触及到了“矫饰”的 当代社会功能。在文化饱和及富有的社会里,“矫饰”提供了一种风格上的存活方式。 它并非完全等同于大众文化,而是一个可以透视大众文化的美学透镜,而且还是一个包 容兼蓄的透镜,因此“矫饰回答了下列问题: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做花花公子。矫饰的 品尝者……在大众艺术中发现了……奇特的乐趣。仅仅使用并不污损这一乐趣的对象, 因此他学会了在奇特的方式中拥有它们。矫饰……对奇特物品和大众生产的物品之间并 不加以区分。矫饰趣味超越了复制的作呕”(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矫饰可以担当一种反讽的智性抵抗体系,在 “大众艺术”中让人获得乐趣,但又通过设立一道品味的屏障而在大众艺术里“离群索 居”。
矫饰美学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人为状态以及“以牺牲内容为前提的质感、感性层面和 风格”(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 0.),因此它对桑塔格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她也承认矫饰是一种无形 的“比喻性感悟”,但显然与“新感悟”紧密相连。60年代初期,矫饰对大众艺术情有 独钟,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篇桑塔格对一部电影的评论加以印证。文章的名字是 《杰克·史密斯的<同性恋尤物>》(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收在桑塔格的 《反对阐释》文集里。她所评论的影片《同性恋尤物》充满了大量的淫秽镜头:疲软的 阴茎、弹性的乳房、手淫和口交、男人穿着异性服装与女人或同性嬉戏跳舞,在性感音 乐和广告背景的衬托下做各种淫秽动作,轮奸演变成性欲满足的高潮……凡此种种,不 一而足。然而桑塔格却认为这并非色情文学,因为它“充满了感伤和朴素味道,消弭了 性刺激。史密斯塑造的性形象时而幼稚时而幽默,没有淫欲”(注:Susan Sontag,“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27,p.227,p.229,p.229,p.230,p.231,p.231.)。这种作品历来就有其传统,称作“ 诗化的震惊影片”(the poetic cinema of shock)(注:Susan Sontag,“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27,p.227,p.229,p.229,p.230,p.231,p.231.)。影片没有情节,没有情节发展,因此也就没有顺 序。它既无思想也无象征,更没有对任何事情的评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对感 官的享受”(注:Susan Sontag,“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27,p.227,p.229,p.229,p.230,p.231,p.231.) 。它与许多法国先锋电影的“文学性”正好相反,对于影片中的寻欢作乐根本无从阐释 ;所能给予人的惟有“形象的直接性、力量及惊人的数量。与严肃的现代派艺术不同的 是,这一作品与意识的挫败感无关……”它只表现出了“一种被置于否定之上的拒绝思 想的感悟”(注:Susan Sontag,“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27,p.227,p.229,p.229,p.230,p.231,p.231.) 。桑塔格认为这部影片代表了一种少见的现代艺术,它表现的是欢乐和天真,虽说内容 不免淫秽,但却有美感和现代性。由于《同性恋尤物》的松散、“邋遢”、欢快、质朴 和“摆脱道德的自由”,桑塔格认为它属于“波普艺术”。波普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在 题材上放弃立场,桑塔格在这里并不完全反对道德立场,只是认为我们的生活经验中也 有一些不需要采取立场态度的题材,比如性,为此,她称那些认为波普艺术是崇拜地接 受大众文化创作的人十分愚蠢。她以为波普艺术开辟了各种态度混合体的新天地,因此 史密斯的影片出色地表现了性的戏仿,充满了性欲冲动的抒情激情(27)。
通过桑塔格对史密斯执导的这部影片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她心目中的“矫饰”美学 与“波普”相似,而“波普”又是解构现代派艺术深层结构,朝平面化、感官化的后现 代过渡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戏仿和游戏特征不仅反映出了桑塔格对新兴的边缘艺术的赞 同态度,也体现出了“矫饰”在60年代与先锋乃至大众艺术的血缘关系。从这一角度讲 ,《同性恋尤物》便具有了象征意义,用桑塔格的话说,就是“对世界美学视域的胜利 的范例”,并创造出了一个清晰的、由“日常歌曲、广告、服装、舞蹈,特别是从老式 的影片中吸取来的大量幻觉”而形成的人为的环境(注:See Liam Kennedy,Susan Sontag:Mind As Passion,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 5,p.27,p.27,p.33,p.34.)。按照桑塔格的解读,这部影片的“肌体”是由丰富的“矫 饰”拼贴构成的:“形象和肢体的语汇……包括拉菲尔前派的慵懒、新艺术流派、20年 代的异邦风格、西班牙和阿拉伯艺术,以及格外欣赏大众文化的现代‘矫饰’方式。” (注:Susan Sontag,“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27,p.227,p.229,p.229,p.230,p.231,p.231.)
桑塔格认为矫饰艺术尚未被美国发现或认可,因为美国批评家从传统的角度讲一直把 艺术置放在道德的空间,而《同性恋尤物》却是在美学空间中呈现。在桑塔格看来,艺 术“不仅有道德空间”,也有“快乐的空间”(注:Susan Sontag,“Jack Smith's Flaming Creatures,”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27,p.227,p .229,p.229,p.230,p.231,p.231.),而史密斯的影片便是这种美学/快乐空间中的一种 存在。
总之,矫饰感悟就是艺术的风格化,是艺术的自我看视,是浮华,是美学;它把一件 事物的重心从本质转移到形式,把事物的程序是什么移到了怎样操作。影片《巨猿》(King Kong)可以是矫饰,“因为它过于夸张,但却恪守自身的原则和看视世界的方式” (注:Carl Rollyson,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Chicago:Ivan R.Dee,2001,p.vii,p.69,p.69.)。电影明星嘉宝、梅·韦斯特以及戴高 乐公共演讲的风格及修辞是地道的矫饰美学,因为“这些人物已几乎变成风格的化身, 掏空了一切实质”(注:Carl Rollyson,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Chicago:Ivan R.Dee,2001,p.vii,p.69,p.69.)。矫饰是“大众文化时代的矫揉造作”,可以在“不顾及本体论焦灼不安的情况下体验高度风格化的方式”(注:Susan Sontag,“Notes on‘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287,p.287,p.287,p.287,p.290,p.291,p.289,pp.288-289,p.277,p.280.)。矫饰同机遇剧一样,都代表对内容的击败,而内容在桑塔格看来正是使当代文化的艺术概念贬值的罪魁。当下的艺术与科学一样,也在扩展和修饰人们的意识;之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当今艺术比科学理性低一等,是因为艺术已沦为一套道德说教。桑塔格认为当代艺术也在考验人们智性的极限能力,向感官提出挑战。大众艺术完全可以像科学公式似的呈现华丽的美的形式。她也承认有些先锋艺术和垃圾大众文化不可取,但具有多元性的新感悟应该是囊括所有艺术文类的,这便是桑塔格在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关系之间想要重新审视和促进一种新的批评意识的目标。
桑塔格对大众文化、波普艺术和“矫饰”美学的看重并不代表她已抛弃了现代主义, 而只是预感到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抱怨”;她处于多种感悟的边界,不能也不 愿意持骑墙态度,于是便“卸负”而前行(注:See Sohnya Sayre,Susan Sontag:The
Elegaic Modernist,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p.148.)。另一方面,面临 对艺术作品道德阐释之风,她不得不启用“病态”的艺术形式,矫饰、色情及灾难想象 力等等,企图还艺术以“澄清”的状态,其实从深层次说,这不啻是她对高雅文学所采 取的一种守卫姿态。矫饰成了桑塔格推广她的风格和艺术观念的手段,即艺术并非模仿 ,不是现实世界的翻版,而是艺术家的发泄,是一种奇幻。矫饰是对肌理、感官层面的 欣赏,而不是内容,不是主题。矫饰对中性、极度夸张和简单的形式感兴趣,因为它们 都代表着生活是个舞台、戏院,是构造本身的概念。总之,“矫饰是对世界的一种美学 观念,它希冀在常规的背后找到一些颇有意思的体验”(注: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pp.85-86,p.86,p.87,p.87.)。
1964年12月11日,美国《时代》杂志刊出了《“矫饰”笔记》的片段,该刊对这一美 学的评价是:“‘矫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大众文化的年代如何保持一流。桑塔 格不仅描绘矫饰,而且还指出了如何保持出色,她是一个知道如何捕捉当代感觉的思想 家。”(注: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 ,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pp.85-86,p.86,p.87,p.87.)美国批评家威廉姆 ·菲利普斯在《党派评论》也撰文说,桑塔格已经知道如何应付“大众趣味和娱乐世界 了,尽管她的手法较间接和有点嬉闹的味道”(注: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pp.85-86 ,p.86,p.87,p.87.)。诚然,在60年代初期,其他学者也发表过关于引起争议的大众文 化方面的文章,但他们都采取了一种冷漠旁观的态度。而桑塔格却全神贯注,因此“结 束了对大众和商业产品的敌对态度”。而且她的风格还超越了旧式的争论范畴,引入了 一种“看待我们文化产品的新方法”(注: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pp.85-86,p.86,p.87,p.87.)。从60到70年代,桑塔格都显示出了她能够超越一般性争论的能力,即包 容多种文化视角的折中主义,然而她所追求的“纯”形式的东西,多少有标新立异之虞 ,而艺术若一味偏离道德意义的所指,便将陷入虚无和自我圈地的境地,以致无法在科 学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达到审美救赎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