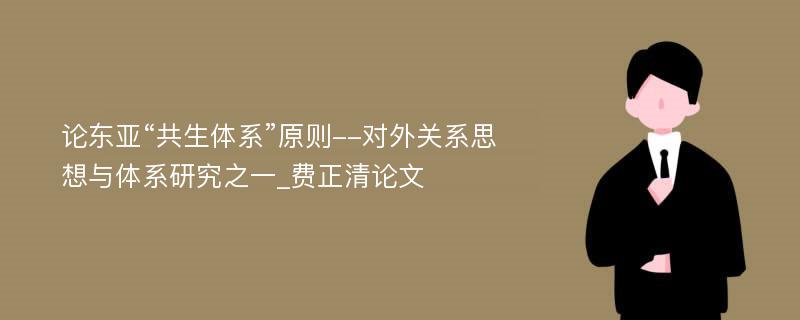
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原理论文,体系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7-0004-19
一 导言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撰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通常基于欧洲的历史和经验。在这方面,人们常会提及或追溯的是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及修昔底德以此为主题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①并常以其为国际关系的肇始,作为这一领域修习者不可或缺的知识和历史起点。这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对非欧洲或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国际秩序,若非视而不见的话,也是经常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仿佛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还有人把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说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除了低估思想史的意义之外,依然是无视欧洲以外世界的历史。出现于世界其他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孕育而生的思想、理论及地区性秩序,难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吗?这样做若非故意的无视,便是一种知识的欠缺或偏见。②
这一情形在近些年来有一定的转变,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重视比较历史。这显然是一种健康的趋势,隐藏于其后的是一种观念的树立,即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原是相互独立、并行生长形成的,比如亚洲,其绵延比之欧洲及其国家间体系历时更长。两大地区在许多个世纪中互不相闻和知晓,是分别存在和发展的。因此,非西方地区不是欧洲或西方的映射或延长,也不能用西方的经验来简单套用比附。于是,逻辑的结论便是,对这些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和秩序的研究工作应返归本土,从本土出发去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理由、根源及其内在理路。这样做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它并非只具有特殊性方面的价值,而是可能具有潜在的普遍价值。③在这方面,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④可谓发出了一个先声;亚当·沃森(Adam Watson)、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则把眼光投向广大的非西方地区及其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写出了视野宏大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康灿雄(David C.Kang)的《西方之前的东亚》则初步展示了他的发现之旅及收获的成果。⑤
与此同时,中外社会学家近年来对社会共生现象进行探讨,也收获了一些研究成果。⑥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社会共生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同主体建立共生关系,必须具备相应条件。要建立资源交换型共生关系,双方必须拥有对方需要的资源;要建立资源分享型的共生关系,双方必须同时需要这种资源,并且存在这种资源。对于两个都有选择自由的主体,要建立共生关系,必须彼此选择对方。在利益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建立共生关系-共生秩序,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便从混沌演化为有序。⑦以此来看国际社会或地区国际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类似的现象。
本文认为,传统东亚各国间形成的秩序可视为一个共生体系,这包括大国之间的共生、大国与小国的共生、强国与弱国的共生等,它们共同遵守若干规则,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规则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定的秩序。这一秩序是在东亚国家间历史地长成的,故谓之“东亚内生秩序”。本文强调,这一秩序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可能正因为如此,这种内生秩序和共生体系展现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了上千年乃至更长时间。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内生秩序和共生体系的原理。
二 对传统东亚地区秩序几种解释的质疑
东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若只以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地区国际关系而论,大约可从中国汉代算起,历经近两千年。
关于传统东亚的地区秩序,影响甚大的是“中华世界秩序”说,该学说通常与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名字联系在一起。⑧“中华世界秩序”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却未必是传统东亚国际关系的整体或本质特征。费正清本人的专长是近现代中国,他对“中华世界秩序”的认识显系由他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的研究发展而来。费正清注意到,参与“中华世界秩序”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同。指出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人们注意传统东亚秩序与欧洲秩序的不同进而原理上的不同。但对“中华世界秩序”本身,杨联陞曾提出过疑问:“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⑨这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论断,但可惜所论未详。
此外还有“华夷秩序”说。⑩其代表人物何芳川认为,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而且,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初具雏形的或比较成熟的、地区的乃至全球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一个有如“华夷”秩序那样源远流长,一以贯之。(11)这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何芳川按时间先后对其进行了描述。
香港学者黄枝连主张“天朝礼治体系”说,并著有《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三卷。(12)细究起来,其中所谓的“天朝”,本就是颇为自高自大、自鸣得意之语,因中国统治者自诩受命于天,是“天”之子,于是他的朝廷便也成了“天朝”。19世纪那个兴起于广西、后在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国部分地区建立割据政权的“太平天国”不也以“天朝”自况吗?南京不也被改名为“天京”吗?无非是主事者自称承受了“天命”,其实不足为训。关键在于“礼治体系”四个字。在黄枝连看来,东亚的地区秩序,那时是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的;这些做法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13)“礼治体系”概念抓住了这一秩序的表现形式和礼仪在其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然而,礼和礼仪毕竟只是表现形式,关键还在于礼仪内外所包含的内容和所反映的关系形态,它们是“礼治体系”说难以反映的。
以上几种解释各有其道理。而影响最大的,当推“朝贡体系”说。这个说法来自英文“tribute system”,汉语中原本并没有对应词。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指出,“研究者必须时刻牢记,‘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是为便于描述而创设于西方的一个词”。(14)这表明这个术语本非“产自”中国或东亚,而是源自于西方。现在的问题是,用它来指称传统东亚的国家间关系是否准确?它的来由如何?似未见有人做过详细的考证,但至迟在1941年就有费正清和邓嗣禹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主要研究工作当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论清代朝贡体系》一文,他们二人不是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应是沿袭而来,因为这个概念“19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出现”。(15)
费正清和邓嗣禹的长文陈义甚高,他们认为:(1)朝贡体系是早期中华杰出文化的自然长成;(2)它被中国的统治者用来为自卫的政治目标服务;(3)在实践中它具有一个非常根本和重要的商业基础;(4)它成为中华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工具。简言之,它是全部事情的一个构设,作为世界组织难题的一个历史的解决方案值得给予关注。(16)这里指出了朝贡体系所涉及或涵括的文化性、防御性、工具性和以经济为基础四个特点。联系到“美国学者卫思韩在其关于朝贡体系的著作中强调了‘防御性’的概念”,(17)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朝贡体系的“防御性”。费正清、邓嗣禹两人甚至视其为世界组织难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可见估价甚高。
逐渐地,每当人们言及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时,必以“朝贡体系”名之,几乎在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至于它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朝贡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常未得到深究,以致长期来成为了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东西乃至窠臼。实际上,“朝贡”一词很容易产生误导,有必要提出质疑、进行深究。
上文已经提及的杨联陞的质疑是针对“中华世界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言的,鉴于费正清是把它与“朝贡体系”等同的,因而也同样适用于“朝贡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一语恰恰暗含了单一中心的、向中国朝廷的“朝觐”和“纳贡”。
首先,“朝贡”一语表达的是一种单向的行为,“朝”是朝觐,“贡”是进贡,因此,该词表达的只是对方的行为,或被一方所认为的对方的行为。也就是说,“朝贡”一语传达和表现为一方的观念形态,而其实态却未必与其一致,或很可能不一致。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问题:如果朝贡关系只是出于一方的需要,或只对一方有利,为何它会延续那么长时间呢?也许会有人回答,是因为古代中国国力强大、文明昌盛。然而,国家都有国力衰微的时候,在不是强制性(非强制性)的条件下,朝贡关系却能源远流长,绵延存在若干个世纪,这难道不是一个需要很好解释的问题吗?我们有理由提出如下看法或曰假设,即只有在双方都有需要的条件下,这一关系才能建立、保持和延续,是双方的共同需要维系了这一关系的绵延。
其次,“朝贡体系”一语易使人误以为东亚秩序是单一中心的,即它以中国为中心。费正清以“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一语名之,根据这一思想,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论上的要求付诸实施。(18)但笔者认为这在准确性上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指出很多例外,譬如,强盛的唐朝就没有强迫或要求日本朝贡,明朝也把包括日本在内的15国列为“不征之国”,(19)还有很多时候中国朝廷主动要求外国减少而非增加“来朝”频率,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
至少更准确一些而言,一则它是中国统治者心目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与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有很大关联。在古代人(包括埃及、波斯等)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条件下,大都无不以自己为已知世界的中心,这在古代人那里或许是通例。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邻邦——从日本到越南——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思想。(20)王赓武则指出,在中国明代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国王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创建一种国家平等机制并运用于国际关系中。不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优越观有在同一历史时期并存的现象。它们的来源千差万别,包括爪哇和柬埔寨的印度教、泰国和缅甸的小乘佛教、越南的儒教、苏门答腊和满剌加的伊斯兰教等。(21)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傲慢自大。(22)这么来看,亚洲各国统治者处理相互关系的思想理念均不同于欧洲社会的主导性观念,他们所抱持的理念具有同构性,彼此之间相通,从而成为共同观念。共同观念是构成一个社会及其秩序的“水泥”。
二是中国人由己外推的思维方式。它与西方原子式的、因而个个“平等”的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平等”对个人是如此,对近代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观念则颇有类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而外,也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人。这不同于自我中心主义,甚或大异其趣,因为它讲究的是“人”与“我”之间的关系。许倬云认为,儒家的社会关系圈是“由己及人、由亲及疏的同心圆”。“这一社会关系圈,投射于中国对与四邻的关系,遂是理想中‘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的‘向化’,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23)没有绝对的他者,是因为“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可以转换的,转换的方式是对方的接受,这显示了一种中国文化的自信。只要对方表示恭顺,则什么都好说,这是一种颇有意思的心态,中国人曾为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
三是“名”与“实”的分际。“华夏中心”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话语”中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从中国的眼里看到的、记载于一些史籍中的内容,可能是实态,也可能是扭曲了的或实际并不存在的影像。
就以“中心”而论,这一东亚秩序实际是多中心的,越南就自成一个中心,在相当于中国清朝的时期,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周边藩属就包括万象(今老挝的一部分)、真腊等,其统治者也称“皇帝”,也奉行“厚往薄来”的来往之道。(24)阮朝曾在中南半岛上做“天朝”、“上国”,视邻近的国家为“属国”,构建起了自己的“宗藩体系”。孙宏年的研究表明,在越南封建王朝统治者心目中,中南半岛上的很多邻国、部族都是“蛮夷”,安南后黎朝、安南西山朝和越南阮朝都一直把邻近的南掌、万象、真腊、寮国(以上今属老挝、柬埔寨)及火舍等看成了“夷”,并推行向西、向南扩张的政策,多次同暹罗发生争夺地区霸权和领土的战争,又迫使邻近的“蛮夷”部族表示臣服。它们力图在中南半岛构建以越南为中心的“次宗藩体系”,后黎朝时期自称“大越”,阮朝时期自称“南国”,历代君主有其帝号、纪年和正朔。阮朝嘉隆、明命、绍治时期(1802-1847年),越南处于疆土最广、国力强盛的时期,在中南半岛上形成了一个以越南为中心的藩属体系。(25)
日本则曾经是另一个中心。它在很长时间里游走于边缘,没有进入“中华世界秩序”,后自成“中心”,要琉球等国向其进贡。也就是说,朝贡关系不仅存在于中国与外国之间,也存在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费正清承认,“上统下属的组织原则也适用于东亚异族政权之间,那是在中国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过问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满族与蒙古族、萨摩藩人与琉球人,甚至是在尼泊尔人与藏族人之间”。(26)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的、有大有小的中心又遵照相同的原则来处理彼此关系。这就属于共有观念,因为它们为诸国所共同认可和接受。
明史专家万明指出:朝贡关系的建立,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应该说是久已形成了东亚区域的共同观念。一旦作为一种共识被承认,它的实现就成为了国际原则。以往人们赋予朝贡概念明确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含义,是不确切的。如果说接受“朝贡”概念即是一种“文化认同”,那么朝贡关系凸显了东亚国际的共性。她援引的史实包括:日本曾将渤海国看做附属国;朝鲜《李朝实录》明确记载琉球国中山王“遣使来朝”,琉球国使“献方物”。由此看来,朝贡关系可视为一种区域国际社会惯例而存在。(27)其实还有更多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一点,例如日本与琉球之间、越南与它的一些邻国之间等。又如,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在哈奄·武禄王时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除了印度尼西亚群岛之外,还包括马来半岛的南部,而且这个帝国曾经要求对遍及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和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属国都拥有权力,要求这些地区的国家都向其纳贡。(28)这里的关键在于,“纳贡”的含义和实态需要从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只有实践才能反映出真实的关系样态,而非言辞或文书。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东亚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形式上或者称做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各国可以依旧保留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在内政上也一般不会受到干预”。(29)既然是“名义上”,就意味着不是“实质上”的,而只是“形式上”的。
最后,“纳贡”的虚实究竟怎样,里边大有文章。所谓贡物,通常是使节所携带的给对方的礼物,并有一套礼仪来体现上下尊卑。A国向中国纳贡,也可能接受C国向其纳贡。中国也不例外,如汉向匈奴进贡,宋向辽、金称臣等。因此,这是当时东亚地区一种普遍的、习以为常的行为。杨联陞就指出过如下事实,“在一些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把邻近的民族当做平等的‘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1138年,南宋的统治者为了与金人媾和,就曾接受过“臣”的地位。汉朝和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安宁,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首领,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就是朝贡。(30)这实际上是一种他者居上位,而中国居下位处理彼此关系的状态。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处理彼此关系从而达到“共生”效果的重要方式,它们之间固然有强弱之别,但这一方式的作用是平衡了强弱之间的关系。
已有论者指出,“朝贡或称为纳贡的物品,是作为礼品的贡物,与作为赋税的贡物有着本质的不同”。(31)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贡品是礼物而不是赋税。贡品的重点在于其象征意义,是为了关系的保持。这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朝贡的虚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从中国方面也可得到证明。明代中国朝廷对安南是“期以三年遣使以聘,所贡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坚,何在物之盛?”显然,中国统治者并不在意所贡之物的多少,他们所重视的是外国遣使来华本身及其所传达的含义。而且,中国朝廷常不要求甚至要对方不要频繁来朝。“中国外夷,若或有道,彼此欢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1390年,明太祖因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事,命礼部令广西遣还,申明“必三年乃来也”,表明这一次安南的朝贡在广西便已退回了。(32)
东亚的这种关系中还有和亲、联姻、质子、战争、贸易等内容,绝非“朝贡”二字所能涵括,而是远远超出了“朝贡”二字所能传达的意涵。有论者指出,一方面,有朝贡,也有不朝贡;有合作,也有对立。另一方面,朝贡关系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东亚区域国家共同认可的一种国际关系形态。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在强盛时曾要求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的众多属国向其纳贡,是同样存在以其为中心的朝贡关系的例证之一。朝贡关系中的对象也未必是单一的,而是可以多重的,例如琉球后来就同时向中国和日本朝贡。(33)
更为紧要的是,就实际看,关系的双方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待,同一关系在各自眼中看出来的是不同的,一方认为是进贡,另一方可能认为是平等的往来或者是开展贸易。中国朝廷和官员一概把“远人”的来华视为朝贡行为,其中颇多自欺欺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而在对方,却可能只是为了贸易,或者只不过是寻求与中国开展往来,也可能具有多重目的。“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34)把对方的交往行为一概视为“朝贡”行为,只能说是中国统治者和官员们的一厢情愿。
葛剑雄对中英双方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记载所做的分析,就颇能说明问题。当时英国迫切希望能打破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消除英国对华贸易受到的限制,争取能在北京派驻常任使节。为实现这一目的,英国找了一个堂皇的理由即向乾隆皇帝祝寿,派出了以马嘎尔尼为首的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节团。可是,在清朝方面看来,这些人是专程来向皇帝祝寿的“贡使”,他们的船队是“贡船”,所带物品成了“贡物”,但最终却遭遇了英使拒绝以属国使臣地位拜跪叩见中国皇帝。(35)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多数“四夷传”、“外国传”都得重写。也就是说,中国官修的史书,包含众多一厢情愿、属于自己想象的内容,这些是绝不能当做“史实”来看待的,否则势将被其误导。
因此,鉴于中国史籍上的某些所谓“记载”与历史的实相可能相差甚远,必须拂去蒙在其表面的灰层,而探究其内中之实。对于同一对关系,双方的认知却大为不同,这就大有文章。“朝贡”一事的成分如何,也是如此,需要打掉相当折扣才能恢复其本相。古代中国要的是外方的“恭顺”之意,而外方要的多半是实利,各有所需也各取所需,各自有各自的、并行不悖的理解。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为何常发生中国朝廷要规定以数年一贡为贡期,而外方却要想方设法缩短贡期的事情,例如,明代规定琉球“两年一贡”,而琉球却强烈要求“一年一贡”。中国要的只是外方显示“恭顺”或表示恭顺的态度,外方要的则是实际利益,恭顺为其表,迎合了中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这一关系得到维系的内里是实利和实利驱动,也即朝贡为表,谋利为里。朝贡有真的,尤其是来自费正清所谓“三圈”(即由内而外的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36)中的汉字圈国家,随着关系的由近而远,其真实性和真诚性相应递减,到第三圈后还有多少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颇有可能变成只是接受方的一厢情愿了。
这也再次回到问题的实质,即朝贡之表下面的真实关系是什么。这一关系也就是本地区国家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一种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旦这一关系形成,有关方就按照惯例或双方的定位,分别扮演各自的角色,相安无事,共生共处,也各自理解和表述之。由于相互间不是强加和强迫的,这一关系也就基本是和平的。对这一秩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来自日本及其统治者丰臣秀吉。日本长期游离于东亚秩序之外,14世纪建立的室町幕府(1336-1573年)直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时期才接受了明代册封,算是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贸易也步入正轨。16世纪末,基本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野心勃勃,试图挑战这一秩序,入侵亚洲大陆,是为壬辰倭乱。但他的狂妄企图最终失败。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即今东京)设立幕府后,日本进入了锁国时期,复归沉寂,直至19世纪明治维新后再次向外扩张。而在此之前,在欧洲列强冲击下,东亚秩序已开始发生转变。
三 “共生体系”及其原理
在论及中华文化圈及其特性问题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使用了“软结构”的说法,此说法与本文所论的东亚秩序可以说是吻合的。令沟口感到奇妙的是,在这种软结构下,一些稳定的小王朝(即日本、朝鲜、越南等)林立于中国周边,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该结构的内部有着具有融合性而非排他性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文化。这一点也对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维持这一文明圈的国际关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是一种松散的软结构,这一软结构导致了文明圈的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或周边的国与国之间保持了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37)
笔者认为,这种结构下的东亚内生秩序的特征是大小国家各安其位,小国尊大,大国容小,政治和经济上相互往来,基本保持了和平的地区秩序。这种秩序中的关系表面上看是不平等的,其实质却是相安无事,各主体根据各自的身份来定位自身和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共生体系”,而这恰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具体而言,构成这一共生体系和持久关系样态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多种形式的互动往来
东亚共生体系下国家间的互动往来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以清代为例,中华文化圈国家间的互动表现为以下五种形式:
第一,求封与册封。作为藩属的王朝、政权向中国的王朝、政权请求册封,表明它承认中国君主是“天朝上邦”的合法代表,中国对求封王国的统治者进行册封,也表明它承认对方在其境内的合法地位。
第二,奉正朔与颁正朔。也就是使用中国帝王的年号,采用中国的历书,这又主要体现为与中国的往来文书中使用中国君主的年号,在此之外则不一定。在奉中国“正朔”的同时,又常有自己的“正朔”,其君主也可能自称皇帝,各有自己的年号。其历法虽与中国的农历相同,但也有自己的历法。清廷对此一般有所了解,但并不过问和强迫对方。
第三,朝贡与回赐。朝贡包括岁贡(每年、每两三年或更长时间“遣使来朝”)和岁贡以外的其他朝贡(如谢恩、庆贺清帝登基、庆贺清帝寿辰)。
第四,告哀和谕祭。原国王去世后,新国王遣使告哀,奏称前国王已故。清廷一闻告哀,即遣使谕祭,经常与此同时完成册封仪式。
第五,朝贡贸易。这是宗藩往来过程中的经贸活动。(38)
另从琉球与中国之间互动往来的实际来看,从明洪武初年到清同治年间前后约五百年的时间里,琉球对华关系至少采取了如下四种形式:一是对中国的朝贡以及围绕朝贡而进行的贸易。二是“请封”,即旧王逝世、新王继位的时候,由中国的朝廷派人前往“册封”;很多时候该外国的新王早已继位,中国官方以皇帝名义派出册封使携带文书进行的“册封”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而已。三是派遣王子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到中国留学,所谓“肄业国学”。四是一般性的礼貌往来,如“入贺”、“入谢”等。(39)这四种形式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方面对琉球的往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册封,这是政治上的;二是贸易,这是经济上的。由于对方国家经济规模较小,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只占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因而具有不对称性。
(二)朝贡贸易
“朝贡体系”一语虽不确切,“朝贡贸易”却是共生体系中真实的要件。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概括。例如,孙宏年认为朝贡贸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狭义的朝贡贸易的内容,也即献贡物和赏赐;二是使团随带贸易,即两国官方允许的使节代表国家开展的国际贸易和使团成员私人的贸易活动;三是派遣、接待的费用。(40)这里的“派遣、接待费用”,因非交易行为,似不应视为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
万明认为,明初的朝贡贸易有互惠交换和市场交易两部分,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朝贡给赐贸易。其他国家来朝贡,随后明朝皇帝颁给赏赐。“正贡”与赏赐,实际上相当于中外礼品交换的性质。二是由各国国王或使团附带而来的商品的贸易。这部分物品,明廷称为“附至番货”或“附搭货物”。它在所谓的“正贡”之外,是外国带到中国来进行贸易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分别于京师会同馆和市舶司所在地进行贸易。三是遣使出洋直接进行的贸易,这以郑和下西洋为典型事例。四是民间的私人贸易。这也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官方管理下的民间对外贸易部分。(41)
在上述四种朝贡贸易中,第一种其实不能算是一种贸易,但根据中国朝廷“厚往薄来”的政策,对方得到的常常多于它们所进贡的,这就成为一种收益,是以政治上表示谦恭所换来的。外方获得无本之利,成为保持朝贡关系的一种动因。不过,这部分“贸易”在整个贸易中一般只占很小的部分。除去这一种,就变成三种类型,也即随派遣使团开展的官方贸易、官方允许或管理下的民间贸易以及遣使出洋开展的贸易。清代中越间的贸易往来也有体现,越南阮朝时期,其使团的重要任务是奉命为国家或皇室采购物品,代表国家或皇室开展对华贸易,它们把肉桂、豆蔻、燕窝等越南特产带到中国,又从中国购回人参、药材、书籍等物品。(42)
还有中国人对外方开展的“册封贸易”。对中国统治者来说,册封是证明其为“天下共主”的重要体现。对于册封使来说,这是接受朝廷委派的政治任务,使命光荣。由此附带而产生了“册封贸易”。册封使团携带的物品由于要在当地消化,则可能对小国产生负担。根据黄枝连的研究,“册封贸易”对于一个经济恶化的琉球王国,确实可构成一种负担,“尽买则财不足,不买又恐得罪”。尽管如此,琉球王国还是自愿地、主动地一再向中国“恭求册使而锡封”,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用以维持“朝贡贸易”;二是由于政治上的安排,对内可以提升新政府的威望,对外则可显示琉球的国际地位,即“依中华眷顾之恩,杜他国窥伺之患”。(43)幸好两次册封之间一般都会相隔较长时间,其所引起的问题就不那么受到注意。而琉球的朝贡贸易,相隔时间较短,相比起来获利更多。
(三)交往的自愿性
由于建立和保持关系的双方都是自愿的,这便形成了一种资源交换型的共生关系。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指出,诸小国接受纳贡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属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44)既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都能获得收益,外方愿意建立和保持这一关系就很容易理解了。
比如,从历史上看,琉球是积极主动的一方,是琉球积极要求“入贡”,而不是中国。在明太祖洪武年间,琉球中山王朝对明朝的朝贡多达24次,几乎每年一贡,有两年还“两遣使”贡马、硫磺及方物。(45)热衷于推动中琉关系者,是琉球方面而不是中国方面。“恪遵典制,奉表请封”,是由琉球国王屡次三番主动向明廷和清廷提出来的,而且远比中国方面所希望的更为频繁地朝贡。(46)原因即在于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中国和琉球王国关系中的贸易是在明朝初期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朝贡贸易”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琉球王室对中国朝廷及官府的;二是随贡使来华,在泉州等地分别从事活动的私商。琉球人开展“朝贡贸易”,无论官商还是私商,既然是“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当然就是合法的活动。从明洪武初年到清同治年间,中国和琉球之间虽然有大国和小国、天朝和藩国之分,但基本上双方的关系是和谐的、正常的。(47)
关系的另一面是,中国统治者从来不借口册封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他国的政治体系之内,以便对其进行操纵、利用。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方面为何愿意付出代价保持这类关系,所求的又是什么呢?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48)这指出了它的安全功能,以期求得一方平安,所谓“羁縻”之道,或安全上的“守在四夷”,即以臣服或藩属的夷狄为边陲之藩篱,命其谨守其地,抵抗外侮,为封建国家的安全提供屏障。(49)不过,这仍然并非问题的全部,还有理念上的原因。不能不指出的是作为驱动力的中国朝廷政治上的虚荣,幻想做“天下共主”,一种“万国来朝贡,四夷率来宾”的“天朝意识”。然而,这多半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可就是这种虚幻的东西,却在很多个世纪中影响着中国统治者的思维方式,乃至到20世纪都余绪不绝。
于是,这便形成了一种两相情愿的、资源交换型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个前提,即关系的有关方各安其位,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个适当位置。构成这种秩序的规则,本质上是中国社会政治原理的延伸,正如同个人都按自己的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社会和国家就会安宁,天子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一样。
(四)和平共存,礼尚往来
这一共生体系具有程度很高的和平性。根据康灿雄的说法,从1368年明代建立到清朝后期的1841年,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些东亚国家之间只发生了两次征服战争,(50)即1407-1428年中国明代年间的中越战争和1592-1598年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的壬辰战争。康灿雄所依据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年表》(51)等。这部年表分上下两卷,共一千多页,在该主题下可谓收罗殆尽。另一位研究者罗伯特·凯利(Robert E.Kelly)使用了更为严格的标准,认为应计入1788-1789年的中越之战(为时不到两个月)。(52)假如把眼光越过四国之间,实际还应包括1766-1770年的清缅战争。(53)
但即便如此,总体上我们仍可以说整个东亚在漫长的时间内基本保持了相安无事的局面。从欧洲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战争和冲突更为频繁,战事不断。根据杰克·列维(Jack Levy)的研究,1648-1789年间,在欧洲基督教各国之间有92年处于战争状态并牵涉至少一个大国(其中还不包括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54)主要的战争包括:法国-西班牙战争、北方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三次继承战争(西班牙、波兰和奥地利)、七年战争和北美的独立战争。通过比较希腊世界、阿拉伯地区、欧洲基督教世界和东亚儒家地区,凯利发现欧洲的战争和冲突最为频繁,而东亚地区国家间战争甚少,和平程度最高。对于这种和平性的体认,在研究者中基本是一个共识。
(五)共同合法性
这一共生体系是一种相互认可合法性的安排。由于中国朝廷的册封,一些较小国家的统治者得到了国力较强的大国中国的承认,有助于其在国内地位的巩固。而“远人”来朝,对中国统治者来说是对其所想象地位的认可或确认,满足了其自尊心和虚荣心。
因此,这一共生体系中的东亚地区各国之间是相互认可的。“如果行为体相信他者没有吞没自我的意图,也不会出于利己的考虑,采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吞没自我,那么,自我就会比较容易相信,与他者认同会使自我的需求得到尊重,即便是在没有外部制约的情况下也会如此”(55)。这就为行为体之间共有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是东亚大小国家处理相互关系之道使然。较大国家因较小国家的“诚服”而获得合法性,较小国家则因为较大国家的承认而获得合法性;这种承认,从中国方面看是以册封方式表现的,有时则可能是默认。对于某些违背政治道德的行为,如弑君夺位,也会产生异议,或决定却贡,但一般最终还是承认现实,或授予印玺,加以册封。这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是一种不干涉行为,体现为彼此恪守疆界,互不侵扰。
也就是说,这一共生体系中的行为体对各自的身份有一种自我意识。身份即是位置,是关系中的定位。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看来,身份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56)身份指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内容,利益则以身份为先决条件,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57)
这里涉及东亚国家间相处和往来的独特方式及其中包含的智慧。在这种方式中,大国并不恃强凌弱,甚至侵占吞并小国;小国则有自知之明,多表诚敬恭顺。简言之,表现为大国克制,小国识相。大国展现仁厚,不仅不以大欺小,而且提供公共物品(例如贸易中的市场),给予政治上的认可和经济上的好处;小国不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尽谋好处,或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大国不是一味使用蛮力、逞强好斗,小国不是心怀鬼胎、以小搏大,从而在相互间取得了平衡。
在讨论传统东亚秩序时,人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影响和传播甚广的把东亚传统秩序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或等级秩序问题。王赓武曾指出过类似的问题:“传统中国对待异民族的态度常常被描述为是以等级原则为基础的。我认为,这样理解朝贡体系是不适当的。”(58)历史学家“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过去的所有外交关系都曾涉及程度不同的平等和程度不同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关系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常态,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59)西方人之所以形成东亚秩序是“等级秩序”的观点,很可能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来看待和衡量东亚传统秩序的缘故。
那么究竟什么是等级制或等级秩序呢?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等级制(hierarchy)是一个有地位或权威上下排序的体系。(60)在西方学术界,康灿雄将等级制定义为基于特定属性的排序。因此,一个等级秩序是指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而对人们、群体或机构做出的某种安排或排列。这一定义的关键是等级制的社会性质。等级制本身可以是强加的,也可以是被接受的。也即,它可以被行为体视为合法或非法。尽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由形式上平等的单位组成的,即便今天也能看到大量的等级现象。(61)
康灿雄提出的另一个看法是,基于合法权威和物质力量的结合,朝贡体系提供了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秩序,它也包含了中国的可信承诺即不会剥削接受其权威的次等国家。这一秩序是显性的和形式上不平等的,但它也是非正式地平等的(informally equal):次等国家不能认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与中国是平等的,然而它们的实际行为具有可观的自由度。中国处于这一等级秩序的顶端,不存在对于游戏规则的思想挑战,直至19世纪末和西方列强到来为止。朝鲜、越南甚至日本的精英有意识地复制中国的制度和话语实践,部分地是为了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而不是挑战之。(62)
戴维·莱克(David A.Lake)将等级制分为地位等级制和权威等级制。地位具有关系性(relational)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最终是由体系中承认其地位的他者赋予的。正是地位的这种关系性和主体间性要素使得这一概念区别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所界定的国际结构概念。在权威等级制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对外安全和经济政策行使合法的权力。像地位等级制一样,权威等级制也是关系性的和主体间性的,但进一步强调合法性。这意味着居下位者不仅承认诸国的不同地位和角色,而且接受这些不同为公正的和自然的。(63)
以此衡量,能否认为东亚内生秩序是等级制的,或者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呢?若是依照力量大小来上下排列,则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等级秩序或等级制,正如权力转移理论所主张的那样。(64)但这并非中国人传统看待对外关系的方式。中国更经常地是以由内而外的同心圆方式看待自身和外部,并以国内的社会政治原则或曰“礼”来适用之,这有异于等级秩序观。由是观之,这种等级秩序或等级制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观念的产物。
与此相关的是平等/不平等问题。一般而言,在古代人那里,把文化上不如自己发达的民族或人群视为“野蛮人”,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古希腊的学问家或思想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都曾将非希腊人视为“野蛮人”。(65)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非例外和独此一家。
东亚秩序中所谓的“不平等”,较突出地反映在朝贡和册封关系中的表文以及贡使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比如,中国皇帝与朝鲜国王之间文书往来,前者以“朕”自称,后者以“臣”自称,就好像是国内的君臣关系一样,而君臣之间是上下关系,不是平等关系。可是细究起来,国内的君臣之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中国与外国统治者的“君臣”关系则不然。例如,明代神宗皇帝就曾对朝鲜国王说,“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尺寸之土,朕无与焉”。中国与外藩的关系,其形式和性质,在于后者对前者的“朝聘礼文”,体现为一套礼仪。除了这套礼仪之外,中国对藩邦并无所求。这一关系既以“朝聘礼文”为主,中国不要它们的“尺寸之土”,藩邦自己就得负起治国安邦之责,所谓“存、亡、治、乱之机,在王,不在朕”。(66)由此可见,那只是形式上的君臣而已,形式上不平等,而有实质上各自的自主和相互的平等之实。即使是在藩国遭到侵略而再三请求下,中国出兵救援,也始终念着事毕即归,不想“自费兵饷而代外国戍守”,实质上是各自独立,而分别行使统治权的。
由于两相情愿,这套礼仪和文书表述等在东亚秩序下的国家之间似乎不成问题,因而运行了多年而不坠。然而,在讲究法律平等的欧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就出现了问题。这恰恰是18世纪英使马嘎尔尼使华过程中出现的情形,是东亚和欧洲两种体系、两种秩序之间的碰撞。
四 结论
东亚“共生体系”是在长达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内生而非外生的。从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秩序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与众不同而独树一帜的。它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久维系和存在,有其内在根由。多年来,研究者努力以不同的术语名之,这些术语在不同程度上各有效力,其中尤有影响的是“朝贡体系”说。这一名称来自于西方,后来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然而,这一术语却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它是单向度的,把东亚的传统秩序描绘和理解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原本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尤其是其内在的原理。本文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存在很大缺陷的术语,应该由更准确的名称来取代。
在东亚长期存在和延续的这一内生秩序,有其内在理路。行为主体间的互相接受和共同需要,使双方都愿意保持并以相应方式往来和共生,使得这一秩序延续了上千年乃至更长时间。假若只是一方需要,或只满足了一方的需要,它是不可能存在和延续这么多年的。在相互关系中,一方看重的可能是“远人”政治上的恭顺,而“远人”则出于诚敬慕义外加可预期的物质利益,或者仅仅就是出于实际利益的驱动,双方各有所需也各取所需,形成了对这种关系的共有观念。
本文认为,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之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成为在若干个世纪中这一共生体系运作的条件。这一体系又是多中心的,从其辐射状看,可以画出若干个圆圈,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各种交叉,并非单一中心的等级秩序。
构成东亚内生体系的框架以及这种内生秩序运作方式的诸多要素中,主要包括多种互动方式、朝贡贸易、自愿交往、和平共生以及共同合法性,其中每一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们是构成和维系这一共生体系的原理,也是东亚内生秩序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秩序的特征,值得今人认真加以探究,从而在比较中丰富我们对国际秩序问题的理论认识。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收稿日期:2013-06-03]
[修回日期:2013-06-16]
注释:
①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颇有学术成就的韩裔美籍学者康灿雄就坦承在自己所受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从未听闻过历史上的东亚曾发生过“壬辰战争(Imjin War)”,参见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reface",p.XII。
③可参见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87-98页。
④保罗·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例如,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92;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2010。所谓“国际社会的扩展”(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不过是近代以后的事。
⑥阿兰·图海纳著,狄玉明、李平沤译:《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胡守钧:《社会共生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金应忠:《国际社会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
⑦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61-62页。
⑧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⑨Lien-sheng Yang,"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20.
⑩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0-45页。
(11)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0页。
(12)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前言”。
(14)Mark Mancall,"The Ch'ing Tribute System: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译本《中国的世界秩序》遗漏了很关键的“Western invention(西方的发明)”。参见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张锋:《解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3页。
(16)John K.Fairbank 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No.2,1941,pp.135-246.
(17)张锋:《解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44页。
(18)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2页。
(19)据明太祖的《皇明祖训》,此15国为: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浮泥国。这些国家大致都在明朝时人们认为的东洋范围,也即今天的东亚地区(除了西洋国在今天的南亚)。参见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5页。
(20)张锋:《解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47页。
(21)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60.
(22)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 p.36.
(2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页。
(24)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25)孙宏年:《越南阮朝的邦交理念及其演变初探(1802-1885)》,载《〈东南亚古代史〉出版暨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2013年4月26日,第192-204页。
(26)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8页。
(27)万明:《重新思考朝贡体系》,载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25页。
(28)万明:《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重新审视》,载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该文称“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费正清和邓嗣禹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朝贡体系论’”(第4页),似有误,因费正清和邓嗣禹的《论清代朝贡体系》长文发表于1941年,该文被误认为载于费正清主编、出版于1968年的英文《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
(29)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14页。
(30)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18-19页。
(31)万明:《重新思考朝贡体系》,载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第128页。
(32)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153页。
(33)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20页。
(34)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3页。
(35)葛剑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和“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载葛剑雄:《往事与近事》,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要是世界上只有英文”,可能也一样。感谢匿名审稿人提示这一点。
(36)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2页。
(37)沟口雄三著,王瑞根译:《中国的冲击》,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2-94页。
(38)参见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第二、三章。
(39)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186页。
(40)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第118-119页。
(41)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第14-15页。
(42)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第157页。
(43)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219页。
(4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45)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188页。
(46)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253页。
(47)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201-210页。
(4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5页。
(49)方铁:《论中国“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治边思想》,载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8页。
(50)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pp.83-84.
(51)《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52)Robert E.Kelly,"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3,2012,pp.407-430.
(53)任燕翔:《乾隆朝对缅政策述论》,载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4)Robert E.Kelly,"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pp.417-418.
(55)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448页。
(5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页。
(57)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290页。
(58)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61.
(59)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57页。
(60)The Oxford Paperback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75.
(61)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pp.17-18.
(62)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p.2.
(63)David A.Lake."Great Power Hierarchies and Strategies in Twentieth-First Century World Politics," in Wai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bury Park:Sage,2013,pp.563-564.
(64)例如,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65)Robert E.Kelly,"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p.416.
(66)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论》,第487-488页。
标签:费正清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朝贡贸易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共生关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