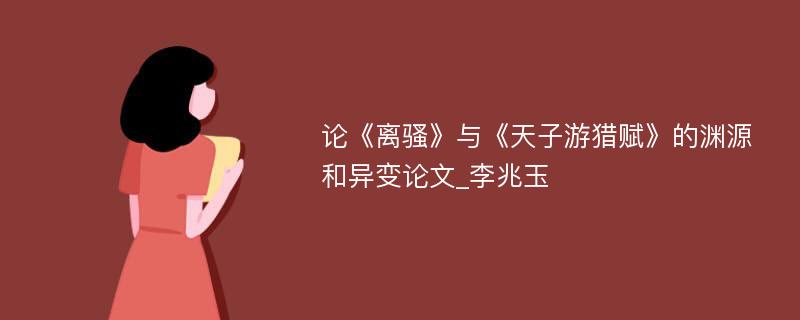
李兆玉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在中国文学史上,《离骚》与《天子游猎赋》分别代表了楚辞与汉赋这两种文体既有密切相关而又大相径庭的文体。前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而后者亦是盛开在辞赋史上的一株奇葩。从屈原到司马相如,从楚辞体到汉大赋,二者之间的渊源一直是治骚者及赋作家孜孜不倦所探求的。
关键词:屈原;《离骚》;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渊源;异变
《离骚》是屈原呕心沥血之作,是中国古代最瑰丽的一首抒情长诗,而开启一代恢弘富丽的美学范式的《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在吸收其精华基础上的气势恢宏之作。诚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二者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一、《离骚》与《天子游猎赋》的渊源
(一)以“爱国主义”情怀为终归
《离骚》所蕴含的“屈骚精神”是极其丰富而有生命力的,对“屈骚精神”的探讨自古以来就是治骚者的主流,其争论的焦点始终在个性精神与爱国精神两个方面,正如潘啸龙所说“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其实统一的‘屈骚精神’,即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抗争精神’和不为任何摧残而移易的‘忠贞精神’。”他在《离骚》这篇绚丽多姿、气势雄伟、情意真挚的抒情长诗中,抒写了他对恶草奸佞的痛恨之情,对美政的追求和热爱,以及对祖国及自身的忧患,而这些复杂个人情感产生最主要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司马相如,他的爱国情怀亦体现在他“尤著公卿者”的赋作中,《天子游猎赋》既是对大汉统一帝国高唱的赞歌,又是对汉武帝时期美政的彰显,这些都与国家强大密切关联,这种强烈的自豪感均来自他对大汉帝国深深地爱。相如描写了子虚所炫耀的宫廷奢华之美,乌有所宣扬的君德之厚,虽未达到讽谏的效果,但是也不能抹灭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作品最终的旨归都是他们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是他们的作品,也是他们人格中最耀眼的闪光点。
(二)以“大”为美的审美倾向
《离骚》是楚辞体无可比拟的典范,它在先秦诗歌史上开拓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体制之大。《离骚》中写屈原的几次漫游,漫游队伍浩浩荡荡,场面神奇壮观,充分体现了骚体这种以“大”为美的特色。在他上天入地的探索中,有大量的铺陈、夸张和想象的运用,它们把以“大”为美的审美倾向发挥到了极致。幻境中塑造的仙境同自然景物、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现实人事构成一个绚丽多姿的庞大意象群,它们不断地变幻组合,把读者引入一个神秘莫测的奇妙境界,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美轮美奂、绚丽多姿的世界中。
汉赋也以鸿篇巨制,气势恢宏盛名于后世。汉赋不仅篇幅宏大,所描写的场面富丽、全面、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还包含了蕴育于其中的雄奇气势。相如《天子游猎赋》虽写的是诸侯、天子的游猎,但是赋中所写天子上林苑景物华美,声势浩大,场面惊人。这个苑囿已难用“大”来形容,它已不是现实中的上林苑了,而是赋家再现“大”和追求“大”的统一体。《西京杂记》载相如语云:“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内,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他的“赋迹”、“赋心”说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汉赋“以大为美”的倾向。
二、从《离骚》到《天子游猎赋》的异变
(一)从极具“悲壮美”到“巨丽美”的异变
“以大为美”是源自于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屈原在他的上下求索中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奇幻的世界。秦汉大一统之际,华夏民族以“大” 为美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加强并在汉大赋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
《离骚》是屈原人生悲剧的再现,作品中展现的真善美和伪丑恶的冲突,既是他的人生悲剧,也是社会悲剧。陈炳良先生指出“他被两种力量所撕扯——一方面是行将崩溃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他内心的难以抑制的要建立新秩序的要求。”屈原最终的选择是投江而死,以死来明志,以肉体的毁灭来求得精神的永生,这是人格的悲壮美。他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和苦难,他绝望、愤慨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借《离骚》抒发自己的一腔热血,其中具有难以言说的悲壮美。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不同于《离骚》美的“悲壮”,汉大赋的美是“壮丽”、“巨丽”的。这里的“丽”,指的是一种鲜明而强烈地诉诸人们感官的美,让人产生一种愉悦。这种“丽”首先表现在体制的宏大上,其次是表现的内容和描述的对象弘大而广泛。汉代的赋区别于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自觉地讲求文词的华美,以穷极文词之美为重要特征。同时,汉赋的“丽”总是与汉代博大、宏伟的气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汉代大一统的王朝气象所决定的,而汉大赋也恰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完美地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汉代的宏伟的气魄,在文化艺术上的高度成就。
(二)人物承载身份不同
人物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屈原的《离骚》中,作者是以第一人称来论述的,是屈原内心的自我独白,他在文章中直接陈述自己的感情,饱满而又激越。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祖国真挚的爱,和愿为祖国奉献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
而《天子游猎赋》中子虚、乌有、亡是公则是相如虚构的人物,他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全知全能的视角讲述这一故事的始末。在三人的对话中,文章的主旨层层递进,逐步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既是对齐、楚诸侯国夸夸其谈的批判,也是对大汉天子威仪的弘扬。实质上,子虚、乌有先生的对话,看似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以不相同。子虚、乌有是以使臣的身份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是使臣身份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国家的。他们的一言一行,荣辱之感已同国家的荣辱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言谈之中时时注意维护的国家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代表个体形象,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和意识。
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的形象,一般地说是组成艺术形象的主体、核心。《离骚》和《天子游猎赋》中正是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不同角度,以及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二者显然是具有显著不同的。
三、《离骚》与《天子游猎赋》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战国纷乱到汉帝国一统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正是对《离骚》和《天子游猎赋》存在差异的最好阐释。《离骚》的创作时代是战国时期,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楚国由极盛走向衰败的时期。这个时期诸侯之间战乱不息,作为楚国的贵族,一位深爱祖国的楚人,屈原心系祖国,他时刻期盼自己能被重用,美政理想得以实施。而现实却是奸佞横行,楚王昏庸,他的美政理想还来不及实施便被小人陷害。他空有一身治国的本领却无处施展,面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现状,内心极度的苦闷、抑郁促使他唱出了“千古绝调”的哀歌。
《天子游猎赋》之所以具有后人难以企及的壮丽的精神气韵,主要仰赖于司马相如对这个时代所涌现出来的精神气韵的敏锐感应——这一时期西汉王朝正走向鼎盛,这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给予了赋家巨大的情感冲击。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家统一、版图广大,使汉民族充满了自信、喜悦和自豪感。篇幅狭小的诗、骚已不足以表现大汉帝国的气象和魄力,不足以再现汉人昂扬向上的气概。于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以大为美”的大赋应运而生。
(二)创作者的身份与主观创作动机:从独抒性灵到代天子立言
陈世骧称赞《离骚》道:“这是一首英雄诗篇,而所表现的却是一般人的处境。”这种英雄悲剧,跟个人的思想、感情、性格有关。屈原是与楚国同姓的大贵族,也曾“与王图议国事”、“接遇宾客,应对诸候”,但楚王却听信谗言,对他由最初的信任变为疏离、排斥,屈原却不能背叛他。他满腔的凄苦无人言说,于是乎借《离骚》抒发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苦闷与忧愁,并最后“以死明志”。所以,《史记·屈原列传》称:“《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正是他“独抒性灵”的产物。
而司马相如,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使他创作出令汉武慨叹“不得与此人同时”的《子虚赋》。对自己的准确定位,使他看清自身身份之低微,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准确把握帝王的心态,时代的脉搏。于是乎,追求壮丽的审美观念和向外征服的时代心理成为其创作的出发点,他的文章便具有了恢弘的浪漫气势。他以独特的审美视野,以“欲明天子之义”的气度,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度与风范。随着《子虚赋》、《上林赋》的渐次展开,这种为天子代言的特质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相如笔下,《上林赋》堪称是英雄史诗性的作品,激荡在大汉英雄时代的精神上空,雄奇闳大,令人仰之、壮怀激烈。
结语
《离骚》与《天子游猎赋》作为两个时代文学的典范,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明显的看出汉大赋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祖述,以及它站在新时代的基础上的独特审美眼光和艺术技巧。千百年来,他们被无数人传诵与赞扬,他们深刻的内蕴和使命感激励了无数的文人,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
参考书目:
【1】赵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 [M]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章沧授.论汉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4.
【3】曹明纲.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J] .社会科学战线,1987:3.
作者简介:李兆玉(1990.5.7——);女;汉;河南;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论文作者:李兆玉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6/17
标签:离骚论文; 屈原论文; 天子论文; 司马相如论文; 汉赋论文; 楚辞论文; 精神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1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