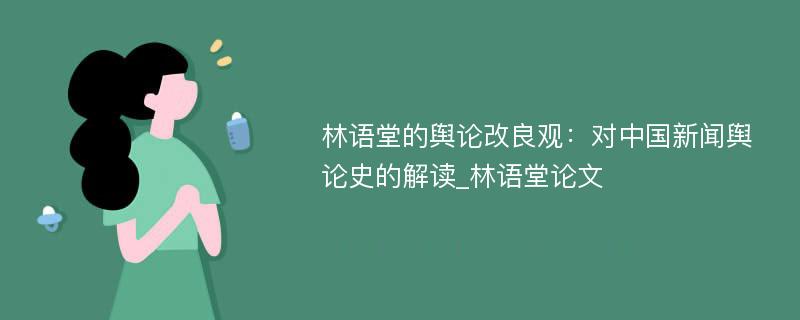
林语堂的舆论改良观——关于《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中国新闻论文,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1)4-0041-05
1935年,上海著名小品文杂志《人间世》第28期上发表一篇署名阿苏的特写《记者生涯》,文后有一篇叹息中国记者“文人腿脚太坏”的按语,称赞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一游俄,即能将俄国政治经济文学人生抉微导窍报告于美国国民”,与此同时,直接批评民国著名记者戈公振“驻俄多年,未见有同类文章发登报纸,吾不能不怪戈公矣”。文章对于戈公振批评很重,迫使后者立刻写了自辩,以《戈林通信》的名义发表于上海报纸①。
按语的作者是林语堂,就是当时《人间世》的主编,而该杂志能够为远在海外驻俄大使馆的戈公振所知,可见该杂志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
林语堂(1895-1976)是众所周知的著名作家、学者,同时还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民国报人。他最重要的办报经历是在1930年代的上海,创办并主编了文学史上颇具盛名的三大小品文期刊: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高谈“幽默”。而后因和老板章克标不和,林语堂一气之下离开,在1934年4月5日,另起炉灶办了上文提及的《人间世》,取法晚明的公安派,强调“独抒性灵”,提倡“自我为中心”、“闲适为格调”的清俊议论的小品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②,在上海当时影响很大,为“论语派”主要人物,引起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极大争论。可惜该刊也不长久,到1935年12月20日出版第42期后终刊;随后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再创《宇宙风》半月刊,后改为旬刊,销量一度达45000份,仅次于《生活》的12万份与《东方杂志》的8万份,位于杂志“探花”的位置。此后他漂流海外,还曾于1952年在美与人创办《天风》杂志等。
林语堂,属于中国报业史上的“文人办报”,报业与撰稿生活是他人生的一大半。“文人办报”有两种,一种是“报人而文人”,先是专职报人,以报章立世走向文人,如最初梁启超、邵飘萍、戈公振等;一种是“文人而报人”,往往是学者文人兼职为报人,或阶段性“触电”从事报刊业,如严复、章太炎、章士钊、胡适之、周氏兄弟、徐志摩等。林语堂显然属于后者,往往带着个人志趣和信念办报,形成鲜明的报刊风格。其报人经历最早是从1923年做北大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始,作为“五四”期刊《语丝》、《莽原》的重要撰稿人、旗下一个著名的干将,及至上海方为专职报人。
可见,林语堂的办报经历远非一般文人可比,而学识宏博渊深也远非一般报人能及。林氏因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报业思想,尤其是对于新闻舆论的研究,是其重要却长期被错过的贡献,这一点集中体现于《中国新闻舆论史》。
《中国新闻舆论史》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继承和发展
1936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新闻舆论史》,由上海别发银行出版,“最早对新闻舆论进行系统研究,建立最早的舆论史学专著的框架结构和理论体系,是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开山之作”③。此书是在吸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般的报学史、新闻事业史走向专门史、舆论专题的研究。两著都密切地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与公共舆论,但是观点却大相径庭。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认为新闻不自由的要害是新闻法制,是新闻立法本身不合法。他较早地讨论中国新闻法制,在第六章中专门划出一节论述《关于报纸之法律》,认为应在立法方面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刑律外不另有限制言论出版之法律,或其类似之法律④。林语堂却认为,新闻自由在中国的缺乏,其根源不是法制,而是更加经常、直接起作用的新闻审查制度;尽管新闻审查有时候是根据法制来进行的,但是新闻审查却更加微观具体;新闻法制一般是事后惩罚,而新闻审查固然可以惩罚于事后,却常常作用于事前,干预新闻报道流程中的任何环节,实际上就是戈公振“随政府或立法者之意思为伸缩”了。
至于新闻审查制度于新闻自由的影响,戈公振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希望除刑律外不另有限制言论出版之法律,或其类似之法律”⑤,显然他把新闻审查自然地划分到“类似之法律”中了。他在《中国报学史》中列举的晚清到民国的新闻法律法规,从《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受规则》、《大清报律》、《民国暂行报律》到袁氏当国时期出台的“命令式之法律”的《报纸条例》以及“动辄得咎、非常危险”的《出版法》、《戒严法》、《治安警察法》,直到“安福系专政,为压制舆论计”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其中主要的还是涉及新闻法制,而不是新闻审查的范畴。
但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然没有涉及到1927年之后中国新闻自由问题。而林语堂在1930年代办报,遭遇了一个不幸的时代,“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鲁迅语)。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新闻审查从此开始。1928年当局颁布《著作权法》;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等;1930年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出版法》,规定书刊在创刊前申请登记批准出版,如有违反“党义”,拒绝注册,还须交中宣部审查;1934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付印前送审(翻印古书也不能例外),如不送审,即“予以处分”。据国民党中宣部及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审科文件表明,1929年至1934年间,查禁发行书刊约887种;1936年一年通令查禁的社科书刊达676种。所以鲁迅愤然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对于上海各大报馆,国民党则坚持派员审查,开始一度被大报抵制,但在1934年军统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后,各报万马齐喑,一片肃杀,审查员大摇大摆纷纷进驻。鲁迅发现:“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⑥他的文章,经常是“删得连骨子都没有……七八千字,只删剩了一千余字”,只能不停地换笔名,在1932至1936年就换了80多个,占他一生用过150个笔名的一半多。
林语堂既为报人,当然备尝新闻出版检查的摧残荼毒。1934年7月6日《申报》发表微风出版社对他和鲁迅的声讨:……(乙)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丙)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出版及广告。(丁)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面对如此明火执仗的封杀和打压,林语堂只能叹息:“在此制度下,像我们这等独立思想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了。”⑦
林语堂不是鲁迅,他当然不能如后者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成“匕首”、投枪刺向敌人,但却可以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愤懑和不满:“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⑧《中国新闻舆论史》正是林语堂的对于国民党新闻审查的抗议,当然同时也是对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发展。
新闻审查自古而然,而在现代尤甚
在《中国舆论发展史》里面,林语堂试图证明“新闻审查是一个可以明辨的概念”⑧。
林语堂首次梳理了中国三千年来舆论发展及其压迫的过程,指出古代舆论压制与现代新闻审查的内在一致代表了不断加深的压制程度。“文字审查的历史并不明确,我们没有必要把文字审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徒劳地焚烧朝廷禁书的时代……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当代对于书籍、杂志和报纸的新闻审查。”⑨事实上,从封建时代到民国,这种审查制度越来越完备、严格,它是专制的一种重要标志,而并不是近代与古代的简单差别。林语堂还论及中国古代的三次舆论高峰,同时也是三个失败事件,即汉代的“清议”运动引发的两次“党锢”事件、宋代的太学生运动及明代的宦官新闻审查和东林党运动。认为这三次高潮表现了代表舆论的文化公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说明只要中国的士人被正确地领导和组织起来,就能有很大的勇气去代表正义,即使冒着一批又一批被杀的危险。但是,在专制统治下的惨败,只能导致后来国人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对于这种古代舆论的惨败,林语堂总结说:“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士人和作家,拥有一个正常和固定的舆论势力是不可能的”⑩,因为“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我们所想象的被杀死的编辑和被处死的汉代大学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11)。但是他很快发现一个更大的困境:拥有近代法律的保护,并不能保护记者免于迫害。
林氏指出共和时期报刊的衰落是从袁世凯开始的,当时500多家报纸只有几十家保存下来;反动军阀张宗昌不加审判就射杀了《京报》的编辑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的编辑林白水。迫害新闻记者的不仅仅是军阀,“国民党……也讨厌嚼子和笼头”(12)。相比于蛮横粗鲁的北洋军阀,后者建立更为成熟严密的新闻审查和特务制度。加上国民党的“紧急法”和“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对报刊,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舆论、行为进行合法的扼杀:1931年五位左翼作家被关押;1933年丁玲被绑架;1934年成舍我《民生报》揭露汪精卫集团一个官员贪污案遭到关闭、逮捕;1935年《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影射日本天皇,总编杜重远被判刑。林语堂只能悲哀地做出结论:“从1895—1911年……这段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911年之后就开始退步。”(13)林语堂认为新闻审查就是万恶之源:“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当代对于书籍、杂志和报纸的新闻审查,因为它独立地解释了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迟缓,也独立的证明了它今天成为这种状况的原因。”(14)“假如新闻审查机构决定了一家报纸应该倒闭的话,它必将倒闭,而不管它是否站在正义的一边”(15),要避免迫害,新闻媒体就要友好亲善,“意味着对这个国家真正重要的政治运动保持沉默”(16),结果就是“中国的报纸通常只把官方发布的消息作为报道的唯一来源”(17)。
新闻审查的本质:政府需要
林语堂无法像戈公振一样做出轻松的判断:新闻审查一切都不需要。因为现实的新闻审查已经存在,不可能被取消——甚至比法律更难取消。因为其存在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理由就是:“政府需要”。林氏试图给予新闻审查一个理性的视角,他认为新闻审查制度的实施表明政府认为它有能力担负起国家管理的职责而无须新闻界或人民的“干预”……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统治者总是要求人民“沉默”(18),这种对于人民干预的讨厌就是新闻审查的实质,这和清朝的文字狱、禁书、迫害作者的行为是一致的。林氏雄辩地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当代新闻事业倒退包含着一个“悖论”,即越是“强大”的政府,其新闻事业越弱小,反之亦然。换言之,双方消长互现……(19)而比较起来,国民政府比清政府要更为强大。其结论是:新闻事业反而比前清时期更弱势,因为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新闻事业贯彻了某种真实有效的东西,因为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的中国新闻,整体而言,“已经成为有关公共信息和教育的一个相对不自由、不公正的媒介”。
林语堂认为新闻审查的存在,其实是一个政府极端自私自利的结果,因为“任何民主制度的最终检验标准就是,人民的意见能够多大程度地影响或者直接引导和控制政府的政策,现代新闻的重要意义依赖于这个界定被接受的程度”(20)。长期压制的后果就是人民普遍笼罩着愤世嫉俗和沮丧的感觉,“不允许中国人民对影响主权、领土和国家全部生活的事说一个字”。诚如鲁迅所言:“党国究竟比贾府聪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厉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21)
中国新闻审查:可以寻求改进吗?
在进行严厉的批判之后,林语堂用完整的一个章节从理性视角寻求对于新闻审查的改进可能。“因为,如果有好的新闻审查制度,有更自由的标准,只限于查禁攻击政府的反叛言论,国家就可能认识到目前的政治局势是他们本身失职造成的而承担部分责任。”(22)
首先,希望新闻审查制度能够科学明智。“现在审查制度最坏的特点是它缺乏科学明智性、独断和过于敏感等”(23),“中国的审查是偶发的,不一致的,没有日本的审查那么系统和有效”,审查官心中无数,编辑们也没有准则可依,结果是“审查的间接影响大于它的直接影响。作者和编辑常常不敢批评政府”,“所以审查的罪恶比实际上的增与删还要隐蔽”(24);当时中国的新闻审查思想和条款比1900年之后还要严厉和僵化。“我们必须牢记,除非新闻审查制度是科学明智的,否则的话,它不但是无用的而且还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经常违背其终极目标”(25)。
其次,希望产生“更加明智的新闻审查官”。新闻检查的混乱往往表现在“缺乏协调性、系统性和一致性……新闻的剪辑经常依赖于个别审查官一时的兴致和异想天开的怪念”(26),而缺乏智能是那些审查员的资质问题,他们大多是外行、没有知识但却掌握了报刊的命运,经常胡乱运用审查的条例来查禁报刊,在一个城市禁止的新闻在另一个城市可能被通过;在对日本等外国列强的问题上过分敏感,不管他们如何在中国走私、侵略、胡作非为,报刊都不能报道,更不能报道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侵略的舆论和斗争,这样形成了一个现象:从报刊上你根本看不到日本已经侵略到东北、华北,而实际上战火已经燃起。
林语堂希望必须从新闻审查工作者的视野来理解其工作性质——换言之,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使其成为专业人员,至少比非专业新闻审查官更有容忍度——即他们需要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新闻审查的形式(27)。
关于新闻审查的“改进”论述,明显暴露林语堂的“调和主义”倾向,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和勉为其难。一方面证明新闻审查就是不自由、不民主的产物,同时又期望有更加自由的审查标准;一方面说明审查官总是外行,一方面期待有理想的内行的审查官,然而新闻审查官的职能决定欣赏从来不是目的,而在于把关、威慑;除了直接影响,还有间接的吓阻,“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让任何媒体和编辑放弃批评政府的企图。
所以,新闻审查的标准不可能科学明智,而模糊从来就不是简单表象,而就是一个目的——因为一旦科学明智,就势必走向法制化,言必有据,不是捕风捉影;事后惩罚,而不能事前敲打;依法执行,而不是为所欲为。同时,新闻审查官本身也不会科学明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鲁迅曾多次勾画其嘴脸:“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28);“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29)。
林语堂的舆论研究,在开始的冲冠一怒之后还是走上了“劝百讽一”的调子。这与他主张“幽默”、“闲适”,而不是讽刺、批判的小品文文风有着密切关系。他用英语,而不是用中文直接写这本书,其实就是满足于做“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30),所以鲁迅曾批评他的小品文“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文雅人的摸挲”罢了(31)。
“林语堂问题”的现代价值
林语堂主张的新闻审查的改进,反映出他在政治酷压下的一种顺变的倾向,其实质就是一种舆论改良观。这种顺变的改良观,跟他的经历有关。1927年他在武汉外交部做秘书,亲眼见证大革命的失败和血腥,从此“寄悲愤于幽默”,而“勇气没有了”。他厌倦政治,走向一种“政治不沾锅”的立场:一方面“不反对革命”(《论语社同人戒条》),一方面也“不做政治家”,寻找一个“清者自清”的个人话语空间,“我将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党,任何政党,苟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统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32)。这实际上已经接近一种政治犬儒主义了。林的选择是无奈的,但这无奈同样是政治和“新闻审查”打压的结果。在左翼和国民党俱不见容的情况下,他于1936年开始海外漂流的撰稿生活,其实也是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敬政治、革命、政党而远之的态度。在他的书中,“新闻审查”终究是个学术概念,当然找不到根本解决的政治出路。
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提出了“新闻审查”是可以明辨的概念的问题,在当时当然是难于明辨的,但对后世却并非如此。同样,林语堂认为新闻审查对于新闻法制的破坏,通过改进“新闻审查”、保障言论自由的看法,也并非一无是处;林语堂为之设定的答案是寄托于宪政和法治,“在宪法的指导下,现代的公众舆论……会得到更好的组织和保护……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执行下去,将会使人们的心理和公众态度有根本转变”(33)——这当然是正确并且有远见的。
新闻审查总是存在,并不仅仅是1930年代的特殊产物。这一关于新闻审查改进的“林语堂问题”,不仅仅属于林语堂,也属于今天的时代,对于当代的新闻法制研究者们,自然具有启发和镜鉴的价值。
注释:
①戈宝权:《关于戈公振致林语堂的公开信》,见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②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见《文学运动史资料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③刘家林:《中文版序言》,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⑤戈公振:《新闻报学史》,三联书店(北京)1955年版,第316-317、352页。
⑥(28)(29)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5、203、370页。
⑦《申报》,1931年(民国20年)7月6日号。上海书店1931年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⑧林语堂:《祝土匪》,《莽原》周刊第1期,《京报》1926年1月10号。
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38、63、35、99、97、138、140、116、137、138、97、98、146、144、146、144页。
(21)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3页。
(30)林语堂:《论幽默》,见《文学运动史资料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3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
(32)(33)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