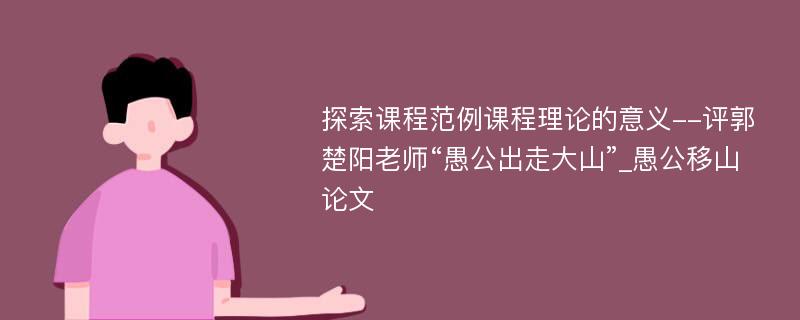
探求课例的课程论意义——评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愚公移山论文,意义论文,老师论文,课程论文,课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初阳老师执教的《愚公移山》,是一堂很富于冲击力的课。这不仅仅指课堂教学的现场效果,对语文课程与教学来说,《愚公移山》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正面直对。对这堂课,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评议:关于文本解读;关于课程实施。
一、关于文本解读
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第四章,我专章讨论了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取向问题。在我看来,语文课程不但在总体上有个“面向何方”的总取向问题,而且其中的构成元素——听、说、读、写,分别也有一个“哪种方式”的取向问题。具体到阅读,取向问题也就是阅读的方法论问题,按照伽达默尔理解与解释一体化的观点(注: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也就是文本的解读方式问题。“哪种方式的阅读”,或者说“哪种阅读”,我以为是阅读教学的前提性问题。在该著的另一个地方,我论述道:目前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至少混杂着四种取向的“阅读”:一是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寻求“思考与练习”“正确答案”的“作业者”取向;二是以分析课文形式方面为主,归结为生词、语法、修辞、章法(结构特点、语言特色等)的语文教师“职业性阅读”取向;三是遵循2000年《大纲》,以“诵读”为主要样式的“鉴赏者”取向;四是2001年《标准》所倡导的“感受性阅读”,在教学中表现为对“讨论法”的倚重。相信在目前实验区的阅读教学中,不少语文教师正在经历着“鉴赏者”取向与“感受性阅读”,乃至与习惯了的“作业者”、语文教师的“职业性阅读”方式激烈争斗的煎熬;而许多学生正在学习着相互冲突、相互干扰的阅读姿态和方式,因而正在形成一种混杂的、无所适用的“阅读能力”。(注: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写作《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时,我的立足点是“课程”,着重讨论的是语文课程目标的分析、语文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的关联、语文课程内容的教材呈现。取向问题,当时是作为蕴涵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中的一个成分提出来的,它与“教育政策”“文化意识”“知识状况”等成分胶合,而在研究状态中予以相对的分离。因而在讨论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取向时,我主要关注的是“能力”的培养问题:“在讨论培养能力的教学之前,我们有必要事先查明,希望学生现在或将来所从事的,是哪种方式的听、说、读、写活动;这样,我们才能明了,要培养学生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接下来去研究怎样去培养这些能力等一系列的课题。”(注: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也就是说,在讨论听说读写取向这一章里,我没有凸显取向的意识形态性。尽管在该著的其他地方,我反复申明听说读写的“方式”乃至所有的语文知识,同时需要从教育政策和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观照:比如阅读教学中所训练的按一定套式“归纳中心”的技能、写作教学中所练习的按一定套式“构思作文”的策略,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在练习着对待语言文字、对待人生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认识方式。“技能”“知识”,这些通常被指认为“工具性”的东西,在语文课程与教学,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工具”。(注: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在我看来,学生以何种方式阅读,是被我们的阅读教学所“构造”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教师阅读方式,尤其是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所体现的阅读方式。学生被语文教师所教的“阅读”是特定方式的阅读,其中蕴涵着意识形态。
但是,取向问题长期被遮蔽,甚至被有意地隐瞒了。语文教师对自己的阅读,对自己在备课时的阅读,对自己在教学中实际对学生实施“构造”的阅读,对它具体所体现的“能力”因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对它所蕴涵的特定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说的“人文性”,木然而不知。人们似乎以为大家在谈论的都是同一种听、说、读、写,更经常地,是把当下的取向或者自己所主张的取向,视为理所当然。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捂住两耳、蒙住双眼的人,在到处蛊惑什么“自然阅读”“原生态阅读”等等。
我写书、写文章,是想唤起语文教师、语文教育研究者乃至全社会来关注听说读写的取向问题,我认为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中,包括课程目标的制订、教材编撰和教师的教学实践,应该把取向问题放在桌面上来讨论、去审议。但现在看来,写书、写文章声音是微弱的。我说郭初阳老师执教的《愚公移山》很富于冲击力,其中有一点就是指它把长期遮蔽的甚至有意隐瞒的阅读取向问题,生动地、尖锐地抛在了众目睽睽之下。是哪一种阅读、主张哪一种阅读、能容忍哪一种阅读等等问题,现在终于被大家看到了,或者说,再也不能假装不看了。
然而取向问题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被“看见”的。正如心理学告诉我们的,你想看什么才能看见什么,“看见”需要先有“思想”。据说,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与他所执教的《珍珠鸟》《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以及干国样老师执教的《斑羚飞渡》等课一样,引起了剧烈的争执,有慷慨激昂反对的,有欢呼雀跃拥护的,也有充满同情宽容的。但种种见解似乎都围绕着课文的解读结论:一方说,“愚公”不能被丑化;一方说,“愚公”就是有点毒辣和可怕;另一方说,《愚公移山》反映了中国人的“老人崇拜”,这好像也有点道理。对一堂富于冲击力的课,仅仅在其解读结论上就事论事,我以为是很不到位的;何况正如我下面要分析到的,老师未必要坚守什么结论,老师的解读结论在课堂教学中也未必一定能够转化成学生们的观点。我们需要严肃面对的,是郭老师以何种方式来解读《愚公移山》,是其解读方式是否符合学理,是这堂课所体现的阅读取向。
为了评议这堂课,我上网查了相关的资料,键入“愚公移山教学”,发现居然有四千多个网页,还不包括相关的搜索条目,打开了几个教案或教学实录,才知道让学生“讨论”愚公该移山还是该搬家,早已有之,而且愚公是好人还是坏人那种没谱地打打闹闹似乎还挺有市场。但郭初阳老师执教的《愚公移山》是有谱的,而且是“语文”的谱,它是执教者所主张的“另类”文本解读方式自觉地、系统地实践。这从课例的教学设计(尤其是对学生思考线路的诱导性提问)和执教者精心准备的“阅读材料”,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这“另类”方式,他们归于“解构”的名义。不过根据我对解构主义和德里达著作的初浅理解,我觉得郭老师们所张扬的“解构”,其含义可能仅仅借此名义来表明自己的一种姿态,正如德里达所说(注:[法]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解构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从这个角度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具体到语文课程的阅读教学,郭老师们所主张的是:“必须对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谎言(如《珍珠鸟》)进行解构”。(注:干国祥.成为课程开发者——语文教师专业化之路思考.中学语文教与学(人大复印资料刊),2004.12)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对“解构”这个词保留必要的敬畏,而另寻其他的说法来更贴切地描述那被主张、被实践着的“另类”解读。
也许可以借用韦内·布斯的“过度理解”。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卡勒转述了韦内·布斯的见解(注: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文学批评可以区分为(适度)理解和过度理解,(适度)理解就是去问一些可以在本文中直接找到答案的问题,比如“从前,有三只小猪”这句话要求我们问的问题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为什么是三只?”;过度理解则是去问一些作品本文并没有直接向“标准读者”提出来的问题。布斯认为,去问本文并没有鼓励你去问的问题,这一点对诠释(即理解、即阅读)来说可能非常重要,而且极富于创造性。为了探究“过度理解”的意义,对“从前,有三只小猪”的故事,布斯问道:你想用这个关于三只小猪与一只恶狼的、看来完全是讲给小孩们听的天真小故事来表达关于那个保存了你、并且与你心心相印的“文化”的什么东西呢?关于创造了你的那个作者或民间集体作者的潜意识的梦?关于叙事悬念的历史?关于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之间的关系?关于大人物与小人物、有毛与无毛、瘦与肥?关于人类历史的三合一模式?关于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关于懒惰与勤奋、家庭结构、民用结构、节食与减肥、正义与复仇的标准?卡勒总结说,如果认为(适度)理解只是对“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是两个概念)的重建,那么上述这些问题想问的是“本文做了什么”“它又是怎样做的”:它怎样与其他本文、其他活动相连,它隐蔽或压抑了什么,它推进着什么或与什么同谋。
《愚公移山》以及《珍珠鸟》等课例,从阅读方式上来看,有点像“过度理解”。也就是说,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以及《珍珠鸟》等,所实践的阅读方式,是把教材里的这些选文,当作我所界定的“用件”,是把《愚公移山》《珍珠鸟》等当成“引起议题文”来用,通过“对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谎言进行解构”,表达“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郭老师在这堂课最后所说的那句话,尤其是我在引用时加黑体的两个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愚公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引发我们的思考和讨论”。
当然,将郭老师的《愚公移山》及《珍珠鸟》所实践的阅读方式与“过度理解”相类比,未必能够完全描述出郭老师们所主张的“另类”阅读,也有拔高之嫌。
那么与阿尔都塞的“征候式阅读”联系如何?在《问题式、征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张一兵介绍了阿尔都塞的“征候式阅读”(注:张一兵.问题式、征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是从“无辜的阅读”和“有罪的阅读”这两个概念进入讨论的,所谓“无辜的阅读”(或者译为“清白的阅读”),指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那种理想化的“直接”阅读(有点类似现在有人鼓噪的“自然阅读”“原生态阅读”),假设在阅读中将不加任何外来因素地直接“看到”作者所表达的全部东西。阿尔都塞认为,“凡阅读必定有罪”,无辜必是虚妄,这就是阅读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也就是说,任何人的阅读只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或生活阅历中负载自己主观投射地“看”,“没有一种阅读不包含着(至少是含蓄地)决定阅读性质的一种理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与我所说的“阅读总是特定取向的阅读”有一致的含义。)任何阅读都是“有罪的阅读”,阿尔都塞说,他所求的是一种“有道理的罪过”,并且还要证明它的必然性,以此来捍卫它。阿尔都塞所说的“有道理的罪过”,指他所主张的“征候式阅读”,即把本文明确的论述与本文未曾言明的论述——那些“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沉默之处”,结合起来读,本文的“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沉默之处”,这些就是“征候”,它们往往是作者所无意识的,而征候式阅读“意味着把隐匿的东西表现出来”。
《愚公移山》以及《珍珠鸟》所实践的阅读方式,看来比较像“征候式阅读”,尽管阿尔都塞的观点属于“结构主义”,而将三五个课例与阿尔都塞并列,显然是拔得贼高了。
那么“必须对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谎言(如《珍珠鸟》)进行解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呢?或者,《愚公移山》《珍珠鸟》仅是特例,执教者所追求的其实是“如何新翻杨柳枝”(郭初阳《项链》教案导言)?其实是“来重新打量这首诗”(郭初阳《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教案导言)?其实是“文本解读的别的可能性”(郭初阳《愚公移山》教案导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自觉、系统的“另类”文本解读方式,动机其实只是求新、求异(相比较“教学参考书”或“平常”的教学),因而执教者读出“新义”的每篇课文,其实都是个案处理的,因而我们也需要个案地审议其处理的合理性、合法性。
我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事业,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取向必须加以显彰,而对取向的任何主张,我们有权利要求主张者作出学理的陈述。这种要求,不仅仅针对郭老师的《愚公移山》,而且包括所有语文老师所执教的所有语文课。也就是说,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取向,是必须“有道理”的,并且必须证明其“有道理”。
二、关于课程实施
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观点看,问题还不仅仅是显彰被遮蔽、隐瞒的取向,或者要求对主张做出学理的陈述;我们还必须考察这种或那种取向与课程目标的关系。事情本来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即使是能够做出学理陈述因而是“有道理”的阅读取向,也不是全部都能够进入中小学的语文课程。然而,要考察取向与课程目标的关系,前提是语文课程目标——尤其是阶段目标的相关条目,有确切的解释。这样的前提我们目前似乎还不具备。因此我无能分析《愚公移山》这堂课所体现的阅读取向与语文课程目标的关系。因此我也不能认同对这堂课所体现的阅读取向任何赞赏或者反对,除非他们能进行上述的分析。
语文教学大纲过于笼统,早已为人诟病;条目可以随意解释,导致过去的语文教学大纲几乎失效(许多语文教师从来没有见过大纲)。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语文课程标准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新课程标准的宣传和教师培训也很有力度。但是,许多条目的本文含义尚缺乏确切的解释,理解因人而异的现象乃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相关条目无确解,致使人们在许多时候难以判断什么能够进入什么不能,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难以把握所实施的教学内容是否合理、是否合法。
事实上,我们的语文课程,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语文教师“我认为”“我喜欢”甚至“我就这样”的课程。在评述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魏书生老师的一篇文章里,我指出(注:王荣生.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其实,将个人性的“师之法”移交给学生,本来就是现行语文课程中的常态,只不过多数语文教师是不自觉地在做,由于不自觉,多数也做得相当糟糕。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语文教学改革实践中,许多优秀教师创立“教学模式”的路子,也是自觉地用自己的“师之法”来改造占主流的教师们的“师之法”,出发点也多是“我喜欢”“我觉得”,尽管在后来不断添加进理论为其佐证,像魏老师对“六步法”“四遍八步阅读法”一样。关于个人性的“师之法”,过去我们用“语文教学的个性特点是很突出的”来解释。但这种解释是不对头的,而且制造了一个陷阱,使我们想不到要去问:学生学的到底是语文课程里的“语文”,还是语文教师的“语文”?
在我看来,这一提问至关重要。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确定无疑。语文教师当然是教语文课程!学生当然是学语文课程里的“语文”!所谓教语文课程,所谓学语文课程里的“语文”,也就是教学的内容要“有道理”并且足以达成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目标。但正如关注听说读写取向的呼吁一样,我这两个“当然是”的认定,声音是微弱的,至今还很少有人把“谁的语文”作为问题来研究。现在,郭初阳老师富于冲击力的课,他所执教的《愚公移山》以及《珍珠鸟》等,鲜明地、尖锐地呈现出了“谁”这个问题,并且迫使人们去思考语文教学中的“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
在教学内容这个含义上,“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指的是教师对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创生,即语文教师对教学内容所做的创造性开发,或者说,是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显现。显然这里有两面性。在当前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研制严重落后甚至空缺的情况下,应当鼓励语文教师的创造性开发;即使在课程与教学内容研制相当齐备的情况下,也应该大力张扬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教师即课程”,无论是导向还是现实,我们都应该把这作为基点。但是开发和张扬,是有界的;教师并不能代替课程,或者篡改课程。有界,意味着“有道理”,意味着对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达成;不能代替或篡改,意味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开发需要审议,意味着语文教师的“实践性知识”需要反思。即使是在教学方法这个含义,“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也不是“我是这样我就这样”,也有个“有道理”问题,也有适应具体学生学习风格的问题,也需要审议,也需要反思。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相当棘手。一方面,语文课程内容的研制严重落后乃至空缺(不知道该教什么),另一方面,课堂里的语文教学内容随意性过大(不知道在教什么);一方面,语文教学内容的“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显著而需要对其合理性、合法性审议反思,另一方面语文课程标准的阶段目标,许多条目的本文含义尚缺乏确切的解释。在我看来,出路在于语文课程目标和“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语文课程内容研制和语文教学内容审议反思,双向或多向的互动。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用体现“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的“好课”来确解课程标准的目标乃至修正目标。也就是说,把过去和现在的一堂堂“好课”当成一个个“判例”,用哪些“好课”符合目标、哪些与目标有差异但应该进入的、哪些不符合目标但可以接受的、哪些违背目标等等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从而使课程目标得到相对确切的解释,或作必要的修正。
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个“判例”,因为它满足一堂“好课”的标准。语文“好课”的标准,我称之为“语文课成功的最低标准”(注:王荣生.语文课成功的最低标准是要有合宜的教学内容.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5.1),也就是在不考虑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关联性的情况下,就课论课而提出的“好课”(区别于“坏课”)标准:(1)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要有意识,即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教这些内容。(2)一堂课的教学内容要相对集中,因而使学生学得相对透彻。我是从语文教学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语文课堂教学的,提出“最低标准”,是鉴于我们语文教学中的“坏课”实在太多,尽管有些课似乎相当生动甚至十分机巧。但“最低标准”,只能满足于对教案、教例静态的、定性的分析;由于立足点是教师的“教”,因而还不足于描述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张力以及“教”的种种复杂情况。我想借《愚公移山》,将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郭老师的《愚公移山》,显然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并且为什么教这些。但在我看来,其中也有些含混的地方,需要提出来讨论:这堂课,是教《愚公移山》这篇课文呢,还是教《愚公移山》的一种“另类”的解读方法?换句话说,学生是“学”教师对这篇课文的解读结论呢,还是学习一种“另类”的解读方法并据此由自己去探询本文或者“引发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还可以从课堂当中学生活动这个角度来提出:学生的口头应答和反应,是以回答老师所组织或诱导的问题为主呢,还是努力采纳一种“有道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体验?
阐释结论与解读方式,在那些频频上出“坏课”的老师身上往往是分裂的,而对上出“好课”的语文教师来说,它们则胶合在一块,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因为能上出“好课”的语文教师对文本的阐释结论,是自觉地用一种“有道理”的解读方式得出的。但是,对语文课程与教学来说,教师在课堂中所关注、所展现的是结论这一侧面还是解读方法这一侧面,实际上会构成不同的课程与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学习来说,由于很难同时注意到教师所呈现的侧面和所隐蔽的另一侧面,在还不能熟练地运用教师欲教的解读方式之前,阐释结论与解读方式在他们身上往往也是分裂的。我们就《愚公移山》来作点具体分析:
内容1:从“山”“人”“过程”“结局”这四个抓手,把握课文的总体内容,了解民族的硬朗精神。课堂所展现的显然是结论这一侧面,因而学生的学习活动就是回答老师所组织的四个问题。为什么要思考这四个问题呢?这就牵涉到解读方式了,大家知道,这四个问题指向记叙文的要素,因而是阅读这篇文章的抓手。解读方式处于背面在这里是好理解的:一则学生已经学过,二则这个步骤主要是个预热,以引出下面重点要教的内容。
内容2:指出《愚公移山》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共同点,从“人数”“外援”“结局”三方面比较它们的不同点。所关注的仍然是结论的侧面,而将“征候式阅读”十分注重的“比较”方式隐藏在背面。为什么要从这三方面作比较呢?对此不予追究在这里也是可以理解的。
内容3:澄清“愚公是怎么认为的”,而将视点引到“亡以应”的智叟。这是一个过渡的片段,尽管为什么要把视点落到智叟也许本来是应该讨论的。
内容4:仿拟智叟,在两个地方继续“反对”的“发言”。为什么要仿拟智叟“永远做一个反对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切入了“征候式阅读”的关键,赖以揭示本文“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沉默之处”所“隐匿的东西”。然而教师把增补的两次发言机会,理所当然地赠送给了智叟。因而,学生也理所当然地应答老师所诱导的问题。在这里,学生的阐释结论(观点)与解读方式(思考方式)明显地呈现分裂。学生的仿拟,与其说“有道理”,毋宁说是按照教师所规限的“反对”要求而进行的比较随意的即兴发言。有碰巧与教师的构想合拍因而教师点头并重申的,比如教师重申“第一,血缘的不断。第二,思想的不变。”也有与智叟的智商明显相距甚远因而教师也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比如“不要忘记地球还在不断地进行造山运动”,比如“掠夺性开发”云云。
内容5:按张远山(智叟?)的立场来“评价愚公这个人”;以当事人(受害的现代人?)的身份来“评价愚公这个人”。为什么“假如智叟来做总结”?为什么“假如愚公早就料到帝会‘感其诚’”?为什么“假设‘时至今日,尚未休矣’”?为什么“而今的你”就一定是这幅样子?为什么继续挖山就必定是“受罪”?如果不交代这些,而只是让学生沿着教师所规划的线路应答教师所诱导的问题,就像一家当地报纸对《愚公移山》的现场采访录所说,此时“学生的回答更加天马行空”(注:金璐.愚公移山与语文变法——我市初中语文优质课展示现场实录.金华日报,2004.10),那么在教什么呢?学生在学什么呢?将基于现代生活的学生与“愚公”的“对话”,跟后面所展示的那两位外教凭借西方文化来解读愚公移山的言论相比较,当可以看出“有路数”和“没路数”的区别。是不是本来就想让学生不顾路数地“思路打开来了”?我们是不是先要教点“路数”,而不只是用下发材料的观点来影响或暗示学生的思考?语文教学是不是要凸显解读方式这一侧面,哪怕是“另类”解读?文章解读的关键,难道不是该问问题的地方会问问题吗?
内容6:参考两位外教对《愚公移山》的评议以及下发的“阅读材料”“探究愚公移山故事的文化内涵”——“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疯狂的愚老人津津乐道?”
这个片段的教学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讨论,因为出现了新情况:第一,学生似乎忘记了刚才关于一系列“假如”的讨论。许多学生乃是按“励志故事”的解读方式来展开自己的“探究”,就像郭老师所感觉到的,“回到了我们这节课的开头”。第二,与前面一系列“假设”的讨论相比较,学生的论述系统性突然增强了许多。如果排除事先准备的情况,有理由推测是前面两位外教“讲道理”的论述方式影响了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并没有认同外教的观点,郭老师在引文上打黑体的词语,比如“指望他的家人”“运用的是体力,而不是脑力”“愚蠢的老头”“疯狂的老头”等等,这些词语及其所蕴涵的意思,学生在后面的陈述中均未提及。第三,有些学生有选择性地参考了下发的“阅读材料”,而所选择的点与教师所意图的有差异。比如一位同学说到“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孝字当先”,子子孙孙努力帮助完成老人的遗愿“很符合常理”,郭老师紧接着就按自己的解读方式(从强调处读出意味)牵引到“我们都喜欢儿孙满堂”,“中国人注重血缘”。再比如学生提到“愚公是个老人”,郭老师马上就牵领到“他一说话,下面的子孙就没有人表示反对意见”,而学生对“老人崇拜”的理解却认为“更有教育意义”,因为“在人一生中最弱的时期去移山,可以显出他志向的远大”。
上面三个情况很有意思,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再做更细致的研究。我以为,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对研究来说是个很理想的课例,它鲜明而生动地呈现了语文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张力以及“教”的种种复杂情况。这堂课给我的感觉是:教师按自己的解读理路阐释文本的意图非常明显,但似乎在学生身上没有显效;教师在这节课设计最巧、用力最猛的地方,即由一系列“假如”牵引的讨论,也许对学生的阅读行为并无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内容4和内容5的教学,按高标准看很可能是不成功的,它根本就没有实现郭老师在教案里所允诺的“懂得真理的相对性”——在这两块里学生的应答甚至很难说与“真理”发生了关系。
阅读《愚公移山》实录,我一直试图想象上课的情景。我关注学生的现场感受,尤其想知道他们在若干天之后心中所驻留的体验。我希望今后的课例研究能够延伸到学生;我认识到,联系学生现场感受和之后体验,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课例研究。这是《愚公移山》这堂课给我的启发,为此我要感谢郭初阳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