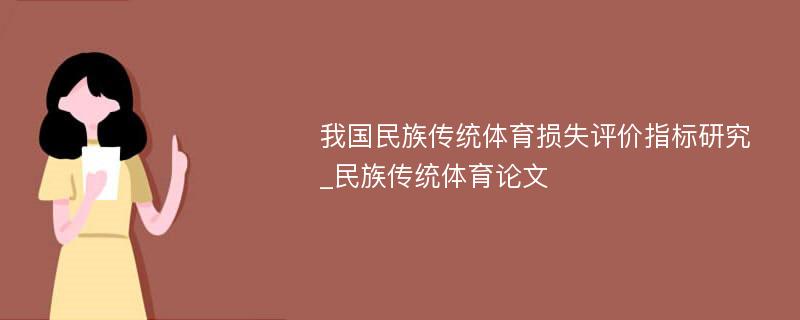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评价指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指标论文,民族传统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08-06-30
l 引言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防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流失。根据保护和发展方式的不同,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建国之初到70年代末期为第一阶段,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模式以西方体育文化为标准进行改造和改编。其间,有1953年在天津召开的民间体育运动会以展示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有1956-1958年政府组织专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如武术等项目进行改造、改编、简化和套路化。而自1981年开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入了以整理改造、开发利用式保护为特点的第二阶段。这期间,我国在响应国家体育总局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政策下,恢复了全国民运会;全国各级体委和民委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民族民间体育进行了广泛普查,开展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整理改造工作。在整理改造的基础上,汇编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其中,收录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977项。以后国内大量体育学者也一直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发展的研究,希望能够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健康传承。
然而,回顾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一直以来,我们的行为不是跟着西方走,就是盲目开发、利用,我们整理改造的行为方式是功利性、工具性和短期化的。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拯救工作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我们的拯救行为缺少规范,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失范频频发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断裂、流失堪忧。因此,通过个案动态地跟踪研究,利用失范理论分析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指标,拟弥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行为控制的残缺。这将在社会转型时期调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目标、优化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机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论文主要是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平安村和三江县富禄村两个自然村社会变迁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分析,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概念以及失范的指标。当然,这种个案比较、分析的说服力一般会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使得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但全文力求通过个案以解剖麻雀的手法,关注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大环境下生存这一现实问题,关注点落在弄清引起民族传统体育失范与规范背后的真正原因,从而从实践措施上升到理论规范的角度去寻找它的普适性。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与理论分析方法
通过阅览馆藏图文资料和网络图文资料等方式,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社会学理论、社会转型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保存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存研究等文献资料。
2.2 田野工作法
在2001年7、8、9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富禄村和龙胜县平安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5年之后又进入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即2006年2月至7月,驻扎在当地张新忠家、廖翠杨家、廖淑嫦家和地方旅馆考察。2006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又因核实调查数据和补充研究资料的需要再次回访考察地区。考察方式一般是深入到村民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研究他们在经济、生活、生产、观念方面的变化,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
2.3 小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需要对不同年龄层人群进行小问卷调查,小问卷的发放都是自己亲自发放和回收。
2.4 访谈法
对一些了解掌握了大量民族传统体育史料,但又由于无法进行小问卷沟通的村寨老人,采取登门拜访或邀请他出来吃饭的方式进行访谈,补充所需资料;对一些小问卷调查的结果,也采取随机访谈的方式求证并检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2.5 典型个案研究法
对广西三江县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抢花炮和广西龙胜县平安村多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个案调查研究,较详细地了解了不同时期两个村寨民族传统体育的保存状况以及发展路径。
3 研究结果
3.1 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概念前提
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失范”这一概念,可能一些学者会产生质疑,“失范”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一般只听说“社会失范”,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失范”是否妥当?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首先从“失范”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失范”一词首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奥提出来的,认为“失范”是一种社会混乱状态,提出了“社会失范”的概念。而后杜尔凯姆在分析迪奥“社会失范”的基础上,认为“失范是所有道德的对立面”和“人类行为的天性就是逾越限制,企盼不可及的目标”[1],提出了人的“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发展了杜尔凯姆“失范”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人们越轨行为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2],提出了“文化失范”和“价值失范”的概念。特别是当代中西方社会学学者随着时代的变迁,将失范的范畴与内涵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如“教育失范”、“诚信失范”、“学术失范”、“管理失范”、“政府行为失范”等等举不胜举。“体育”本身属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传承”是作用在“体育”上的一种行为,故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从社会发展变化来说,我国的社会转型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却在社会发展中举步维艰。如笔者个案研究了广西龙胜县平安村,发现每当社会发生较大变化,或村民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依附于社会土壤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没有在社会变迁中找到新的结合点,而是彻底消失。打扁担活动,这种原始意义是驱赶野兽,提高村民生存安全的活动,却随着村民生存能力的增强而没有了其存在的基础,并从村民的生活中消失;打师公活动,原始意义是清理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是村民们为了生存向死神抗争的活动。然而,一段时期,它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并被禁止,使得这种活动不久也从村民的生活中消失;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打着以旅游促发展的旗号,在迎合一些游客的低级趣味的情况下,被改编成黄色节目或舞台艺术等等。这一切人的主观行为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上后带来的文化遗失,带来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畸形发展不是民族传统体育失范是什么?所以说“民族传统体育失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普遍存在的事实。
那么,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失范呢?结合中西方学者对失范的理解,以及论文中个案考察的社会事实,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失范主要是指在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因社会内部诸因素的相互矛盾,产生的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约束力失效的状态。具体表现在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上的行为目标与手段之间缺少平衡、行为目标与意义之间缺少平衡、行为冲突、组织混乱、意义匮乏、核心形式丢失等方面。
3.2 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失范指标的依据
孤立地谈论“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范”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一深入民族传统体育的组织活动过程或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研究其秩序性的判断标准,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范就会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便也会产生价值判断的意义。
既然提出“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范”,也就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你是以什么标准来探讨其失范的?也就是说,谈论失范前必须首先要清楚与失范相对照的标准问题,没有标准,失范是无从谈起的。而论及标准,又会附带产生另一个问题,标准的惟一正确性。你选定的标准就一定正确吗?你是以传统时期的人们的体育价值观为标准还是以现代人们的体育价值观为标准,你选择的标准合理吗?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自身交往关系结构、秩序;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群体,也具有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及其关系结构、秩序”[3]。因此,标准的选择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标准的选择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流动的变量。20年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高度综合化走向项目分化,这种行为也许是规范的标准。可是20年后,由于民族传统体育过度的分化使它远离了其依附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土壤,民族传统体育被架空了,这一行为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同时也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平衡,它则变成了失范的标准。另外,在考察标准合理性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清楚,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对社会生活秩序起支配与主导作用的,总是那个时代在经济、政治上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那种价值要求。而人们思维的惯性往往是把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那种价值作为标准,其他行为价值与它进行比较,把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相冲突或背离的行为状态视为失范。这里我们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就完全正确吗?完全合理吗?如果完全正确与合理,那么,社会应该是良性的运行与发展,而不会出现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李强等所说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诸多的负面的社会问题”[4]。因此,我们在选择标准时,也必须同时考虑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同时,更要以文化进化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深入到个案研究的第一线去考察,去发现,去聆听最底层的声音。本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论指导原则,这样才能使制定的指标具有生命力和实践应用价值。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利奥·斯罗尔(Leo Srole)就“失范”理论的应用研究而言,在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基础上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他第一次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社会失范尺度的主观状态下的5个指标。随后,伯纳德·兰德在通过对美国某城市8项特征的考察分析中,发现了一个“失范”的变量群,此变量群虽粗略地衡量了失范的因素,但它却给客观状态下的失范指标的提出,开了一个好头。因此,本研究拟以前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在个案比较的情况下,探究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指标。
3.3 民族传统体育失范指标的探究
3.3.1 组织因素
美国社会学家利奥·斯罗尔(Leo Srole)在归纳个体层面上失范的特点时划分了第一种失范维度。即“个体是否感觉到社区领袖离他们很远,并且对他们的需要漠不关心”[5],这是斯罗尔在考察了美国城市社区人组织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可能引起社区人行为失范的一个因素。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广西三江县富禄村和龙胜县平安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政府组织行为角色转变的情况,也能发现组织因素是探究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一个出发点。
3.3.1.1 富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组织行为的转变
1.个体行为与政府的进入
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得以恢复并蓬勃发展得益于一个关键的政府进入的组织行为。“文革”期间至1982年间,富禄几乎所有的集体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被禁,原因于在那个“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跑步前进,大搞生产的时代,搞体育活动或庙会活动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破坏生产。就这样集体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被禁,而仅留下支离破碎的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偶尔开展的个体性体育活动。如跳多耶、打泥脚、跳芦笙、跳皮筋、爬坡杆、打草球等,并且,这些活动也慢慢由于活动意义的缺乏,玩的人越来越少。
1982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抢救、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行动。当地政府在响应政策和确实感觉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遗失危机的情况下,委命当时任富禄居委会书记的王仁生组建抢花炮活动组委会,借助当地三月三庙会活动恢复当地的集体性体育活动。1982年恢复的三月三抢花炮活动是由政府出面领导和组织的,在探讨如果政府不出面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能不能恢复这一问题时,当时任花炮组委会主任的王仁生说:“如果当时政府不出面,抢花炮是不能恢复的,因为当时人们不敢搞啊!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能不能搞(抢花炮活动),但是村民还是不敢,害怕受迫害,那个时候如果走错一步会搞死人的。再说,有权力的人说话村民才会听的,那个时候还是很信权力的,没有权力的政府的领导就是一盘散沙……”应该说政府的进入,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从临危到复活,而国家和政府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则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当地蓬勃发展。1982年国家体委领导通知王仁生带领富禄抢花队到全国第二届民运会上去表演,并亲自从富禄做一个花炮带到第二届民运会的举办地呼和浩特去。1986年将抢花炮活动列为第三届民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并由当时任富禄抢花炮组委会副主任的张新忠任比赛的裁判。在与张新忠老人讨论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对当地抢花炮活动的影响时,张新忠说:“那影响可就大了,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老百姓的热情特别高,而且还去参加全国运动会,全国人都看得到我们富禄人的表演,村民们特别有满足感,你不知道仅1984年那届三月三‘抢花炮’从全国各地来了10多万人,这两岸的河沙坝都站满了人,各个村子的人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地来……以后历届花炮节都突破了传统时期的参与人数,一般都有4~6万人。”因此,当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展成个体的行为时,由于个体的行为不定因素很多,波动性大,当感觉到行为的目的和意义不明显时,民族传统体育便存在消亡的危机。而这一阶段,政府组织行为的进入,并合理地引导激发村民的集体意识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关键。
2.集体行为与政府的退出
在富禄抢花炮活动恢复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都在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使抢花炮活动上升到村民的集体意识,并进而形成一种新的习惯(说其为新习惯是区别以传统商会组织的抢花炮活动),三月三抢花炮活动成为了集体行为。逐渐地,村民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组织有依赖心理,政府一味地统包会减弱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活力,在进一步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只有是民间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后,政府慢慢从抢花炮组委会中退出,放手交给村民委员会和乡村精英去组织。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在以后的每一届民族传统体育抢花炮活动中,政府领导担任抢花炮活动组委会的顾问,帮助村民解决一些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如交通调度与安全维护等,并每年从政府办公经费里拿出一部分资金赞助给当地花炮节,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经费。同时,每年政府领导必亲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场给予村民们节日的祝贺。放手交给村民委员会和乡村精英去组织的抢花炮活动,在有了政府的适度关注后,真正成为了村民们自己的活动。村民如今可以群策群力,根据自己的需要大胆地改革与创新抢花炮活动的仪式过程,并且活动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表面上看政府似乎离场,但他们始终觉得政府在扶持他们。
当村民们的体育活动从集体意识上到集体行为的时候,政府组织角色的及时转变是引导这种行为良性发展的关键。
3.3.1.2 平安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组织行为的转变
平安村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辉煌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由龙脊团组织或“寨老”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的颇具规模。村寨间的联谊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村寨里的打师公活动,依托民俗社开展的体育活动等等丰富多彩。传统的延续,形成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并上升到村民的集体行为。只要“寨老”或政府一组织,他们就参加活动。如两次有代表性的政府进入行为:一次是在反对派别运动时期,村寨联谊式体育活动被认为是村寨间拉帮结派活动,有聚众闹事的嫌疑,当地不组织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村寨联谊式体育竞赛活动便也马上消失;另一次,村寨内的打师公活动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有违科学精神,延续很长时间的村寨大型体育活动打师公也销声匿迹。
在改革开放后,平安村搞旅游开发。村寨中在原来集体体育活动基础上分化出来的活动项目,成为了村民闲暇时间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个体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表演也成为了村民用来吸引游客的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种活动发展有一定规模,如很多家庭旅馆以家庭为单位组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表演来吸引游客。但是此做法没有被很好地引导。几年之后,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了引发村民旅游开发恶性竞争的根源,极大地破坏了村民的团结和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自此,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村寨中彻底地消失了,随着它的消失,村寨中也就没有了任何体育活动。
3.3.2 意义因素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失范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的社会成员能够对行为不断产生意义匮乏的社会系统状态,失范的根源不在于这些成员缺乏获得他们所需的能力和机会,而在于他们对这些需要没有明确的认识。”[6]用帕森斯的理论来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失范,则表现为其失范的根源是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社会成员对他们的参与行为“不断产生意义匮乏”,没有认识到他们有这种参与需求。在这个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又回到平安村和富禄村的两个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个案中来求证。
3.3.2.1 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意义的丰富
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在无意识中强化了活动的意义。即,目前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意义是在保存其原始意义(原始意义,主要指“原本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包括精神价值和部分社会意义)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以当地抢花炮活动为例,该活动的原始意义是以举办抢花炮活动来营造节日氛围,吸引周边地区群众聚集富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参与者也通过自己努力拼搏,证明自己的能力,增强对自己和对生活的信心。随着活动的发展,该活动也必然赋予了一些社会的主导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赋予了它时代内容(时代内容,主要指“解决现在面临的相似问题”或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如传统时期,活动附加了一些迷信的内容,如抢花炮活动,抢得第一炮者,神灵会保佑他发财;抢得第二炮者,神灵会保佑他生儿子;抢得第三炮者神灵会保佑他吉祥如意。然而,如今随着科学的传播,已经没有什么人信花炮的神灵效应,它在那个时代赋予的意义也就匮乏了,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被剔除了。但是该活动的原始意义还在,只不过是它在不同时代赋予的意义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旧时代赋予的意义的淘汰和新时代赋予意义的产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的。只要活动的原始意义被保存下来,该活动就不会消失,因为母体存在,新的衍生物才能附着在上面,如抢花炮活动在旧时代赋予意义淘汰的基础上,新时代赋予意义又不断出现了。如当地传统的择偶方式是对歌,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唱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择偶依托的基础便也消失,再加上现代村寨年轻人出外打工后,很少有时间聚在一块谈朋友,因此,年轻人择偶成家成了老大难问题。抢花炮活动自然地为男女青年相聚提供了新舞台,承载了在活动中取悦异性,在活动中寻找对象的意义。
3.3.2.2 平安村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意义的缺失
平安村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消失都是源于其活动意义的匮乏,或者说是源于其时代赋予意义的匮乏,并且,又没有保存好其原始意义。如传统时期村寨中的“打扁担”活动,其起源于村民用扁担在傍晚敲打板凳,发出巨大响声,驱赶在村寨附近出没的凶猛野兽,以避免村民在睡着的夜晚被野兽偷袭。害怕偷袭的东西主要有丰收的庄稼、家畜、甚至人类。以后这种活动又演变成丰收的庆典。其原始意义就是村民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也是表达一种不向生活屈服的抗争。同时,它也是村民寻求村寨安全、生活安全意义的表达。尔后,当村民们的生活保障有所提高之后,村民们则将这种活动的原始意义抛弃了,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即用“打扁担”这种活动来庆祝农业丰收。扁担成了神物,村民们觉得家中的稻谷都是扁担挑进来的,希望扁担能给他们源源不断地挑进财富。同时,也通过“打扁担”活动中,那悦耳的“打嘟打,打嘟打……”的声音来传达内心对农业丰收的喜悦心情。当村寨在以后的社会变迁中,改变了村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业已经不再成为村民的主要产业,农业丰收成为了村民的负担而不是丰收的喜悦。在这种情况下,“打扁担”活动旧时代赋予的意义便也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一种行为如果没有了意义,这种行为就将结束。故在村民以旅游业为谋生的主要方式的情况下,“打扁担”活动消失了。
村寨中“打师公”活动的消失也是源于同一道理。“打师公”活动起源于村寨中出现疾病、疫情,在当地人们的土方、土法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村寨中出现的一种集体活动。即,村寨的寨老请来会做法的道士(当地也叫师公),在全村寨画符打醮后,清理生病人的衣物进行焚烧。全村大扫除,以除出瘟神,同时村寨人带上面具在道士的带领下围着火堆跳着驱魔舞(有点像南方的傩舞),以驱赶村寨的瘟魔,使村寨人不再生病或死亡。活动结束后,家家户户在自家大门口挂上一面镜子和一把剪刀,以照妖和威吓妖魔,使妖魔不敢进入。无从所知其迷信的意义是不是后来人赋予的,但整理其原始意义则是村寨人加强环境卫生,保护生存环境,提高自身免疫力的活动。而当科学的现代人没有保存其原始的积极意义后,又对赋予的迷信的驱妖避邪的意义产生匮乏时,打师公活动便也消失。
3.3.3 目标因素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认为:“当过于强调了文化的目标而与制度性手段相脱节的时候,欺骗、腐败、不道德、罪恶,简而言之,一些社会所禁止的行为,就会成为日益普遍的行为,失范也就产生”[2]。默顿这里所指的文化目标在我们民族传统体育里面就可以理解成为比赛的结果。默顿随后在解释他的失范的理论时,便也用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强调比赛结果的失范行为作为例证。他说:“在竞技性的体育项目中,当胜利的目标摆脱了制度性装饰时,成功则被解释为‘在比赛中获胜’而不是‘在比赛规则条件下获胜’,这是对使用不合法,但技术上效率高的手段给予的含蓄教唆。敌方足球队的明星暗里遭人伤害;摔跤运动员用巧妙,但犯规的技术使对手失去战斗力;大学校友会私下资助体育‘特长生’。过分看重目标便减少了纯粹参与竞争活动产生的满足感,以至于只有成功的结果才能提供满足感”[2]。我们还可以从平安村和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情况来进行证明。
20世纪90年代末,平安村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活动的内容主要有抛绣球、跳竹杠、板鞋竞技和一些民族舞等。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各自家中的家庭旅馆门前或大厅内几乎每天都开展,搞得十分热闹。如果把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看成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的目标则是吸引过往游客入住自己的家庭旅馆。
正如默顿所说的,当过分强调这种文化目标时,这种文化便出现了失范行为。平安村家庭旅馆在过分重视吸引游客入住的情况下,出现了拉客源、争抢客源的恶性竞争事件,并引发多家搞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家庭,因发生客源争执,竟抄起活动的器材相殴打。由于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引发了村寨各家庭旅馆的恶性竞争,破坏了村寨间的团结,不久便在村民家庭中消失了。
另外,据富禄村的老辈们讲,传统抢花炮活动,也曾经由于过分重视比赛结果而发生村寨间的群殴事件,影响了抢花炮活动开展的规模,并差点就取消了抢花炮活动。旧时,抢花炮活动的迷信色彩特别浓,花炮的每一炮都带有神的生息,而且村民也特别信花炮的灵验,如第一炮是发财炮,第二炮是添丁炮,第三炮是如意炮。人们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是为了比赛结果,为了抢到好运气而去的,而阻碍他们运气的人都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比赛中为达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最后,引发打群架,甚至,村赛之间的冲突和械斗,抢花炮活动也继续不下去了。
而富禄周边省(市)在端午节期间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龙舟竞赛就更能说明问题,由于过分重视了龙舟竞赛的比赛结果,每年必引发村寨之间和宗派之间的大型械斗。以湖南叙浦为例,2003年6月14日,由于各村过分重视龙舟竞赛夺标的结果,比赛一开始两只龙舟队就打了起来,后来引发群体械斗,300多人受伤,7人死亡。这种事件,就湖南叙浦来说,不是第一次,他们每举行一次“爬龙舟”,群体械斗就进行一次。而其他省(市),如广西、江西、湖北也不例外。最后,周边省(市)没有什么地方敢组织民间的端午龙舟赛。地方政府便在端午节期间强行禁止民间组织的龙舟赛,如江西鹰潭在2006年端午节到来前夕,政府在花200多万元赔偿费代价的情况下,砸了一千多艘龙舟,禁止民间“爬龙舟”。事件的起因也是当地龙舟竞赛因特别看重夺锦标而导致群体械斗,打死、打伤很多人,最后被禁止。如果事态如此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则生存危矣!
3.3.4 动机因素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失范是因为社会无力约束人们无限的欲望和要求,因为个体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规则系统一旦解体,则人的欲望就会无限制的扩张”[7]。杜尔凯姆的理论在本文中的理解则是,当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动机是基于物质和金钱的利益时,由于物质、金钱等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这必然带来人们行为的矛盾。矛盾表现在:“其一,活动的组织方用于提供体育活动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活动组织方的期望和要求是无限的,存在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的矛盾;其二,活动组织方所能提供的物质和金钱的服务是有限的,而人们的生活需求逐渐多样化,并不断变化,存在服务有限与需求无限的矛盾”[8]。矛盾的存在是失范产生的前提。我们再来看个案发生的情况:
据调查,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动机有一个变化过程,如村寨抢花炮活动,传统时期,村民参与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因为花炮灵验,人们为争取神明的福佑而积极参与。如今,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传播使得村民对神明的信仰产生怀疑和感觉不切实际,村民参与抢花炮的主要动机则变成了对抢花炮的奖品物质的追求。从抢花炮活动组织者使用奖品物质刺激的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出,传统时期,花炮每一炮的物质奖励为一头猪,100个红鸡蛋,100个糯米粑粑和一坛酒;随后演变为一头牛,100个红鸡蛋,100个糯米粑粑和一坛酒;最近3年,则变为一台29英寸大彩电,200~500元红包,100个红鸡蛋,100个糯米粑粑和一坛酒。以前,本届获得花炮的村寨在下届还得“还炮愿”,得交一定的物质和180元钱“还炮愿”;如今,由于大家更看重金钱,要人家“还炮愿”,人家就不参加你的活动,故“还炮愿”也取消,不用“还炮”了。而听2006年花炮组委会主任赖江民说:“……以后如果集资到更多的钱,还要增加奖励,根据村民的需要把彩电改为摩托车。这样就更具有吸引力了,来参加的人就会更多了……”这显然是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一个因素,正如默顿所说的“我们将那种不能够整合的以金钱上的成功的一种动机作为是产生失范的因素”[7]。但看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社会事实,某些程度的失范行为并非对民族传统体育不利。就拿富禄抢花炮活动中用物质刺激来增强人们参与活动的动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失范行为对抢花炮活动的保护是有利的,是带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在价值观转型时期,“这种失范表明,旧的价值体系在日益变革的社会中已失去其原有的社会效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健全,它揭示在克服这种社会失范中,实践的教化比简单的说教更重要……有时,失范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内容”[3]。这种积极意义的失范,我们说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和源于“实践的教化”,如富禄村抢花炮活动采取物质的诱惑来扩大其影响,就是源于村民处于价值转型时期和各村寨的实际情况而定的。正如村民所说:“采取这种行动总比不采取这种行动好”,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采取这种行动,抢花炮活动就会萎缩,甚至消失。只有首先保存了这种活动的形式,你才能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合理的引导,皮之不存了,毛将焉附呢?失范虽然有时也带有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社会学上说是“非常态发展”,这种发展在民族传统体育里面是属于边缘性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形式及时调整这种失范状态。
3.3.5 形式因素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由于社会是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的,它的各个器官和组织相互协调地发生联系,可以为各种需要提供必备的功能,社会机体在相互匹配的结构模式中,始终处于正常的周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社会事实都是普遍的和规则的,都把社会本身作为自己的起点和目的。然而,失范却意味着对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分解和破坏。”[9]用杜尔凯姆的理论可以解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状态。以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以单个项目的状态形式存在的,而是依附于一定社会民俗节日或民族社日,以多种活动形式综合存在着,并且,是以一个有机体的形式存在。这个有机体相互协调地发生联系,自我组织、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始终能正常地从一个无序的混乱状态不断地过渡到有序状态,不断地从一种有序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有序状态,而提供整合动力的则是这个综合模式的自组织结构,也正如杜尔凯姆所说的,这种综合模式的失范就是意味着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分解和破坏。换句话说,就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展从综合的形式走向了分化。同样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认为:“个体所处的特殊环境可以被看作为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是指普通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失范被看成是文化结构的瓦解。”[2]依据默顿的观点,民族传统体育在特殊环境中传承的那个综合形式,可以看成是文化结构的话,那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式从综合走向分化,则可以看成是这种文化结构的瓦解,它也包括这种价值标准的瓦解,那么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范也就产生了。我们再从理论到实践中去求证。
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是依附于当地的传统民俗节日三月三举办的,如当地的三月三抢花炮活动,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仅参与抢花炮比赛而已,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日活动。这个活动中,人们不但参与抢花炮,还参与逛庙会、赶圩、斗牛、斗鸡、赛芦笙、民俗歌舞表演以及寻找心悦的异性等活动。总体上来说,它是以抢花炮活动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综合性的民族节日欢庆活动,同时,它也承载了很多社会的东西,在为社会服务,如为村民与商人之间提供农产品交换的场所,为年轻异性相识、相知提供平台等等。然而,自1982年抢花炮活动进入民运会之后,广西体育局的领导便对抢花炮活动进行规范化,他们仿照篮球、足球和手球的竞赛规则给抢花炮活动创立规则和竞赛秩序,把抢花炮活动从综合化的模式中分化出来,成为了单个竞赛项目。广西体育局为普及这个项目,还在全区内组织了专门性的分化后的抢花炮比赛。在开始的一、二年,由于人们赶新鲜,觉得好玩,参与的人数还很多。可是过后不久,便觉得这个项目玩厌烦了。以后除非是政府花钱请他们去玩,否则没有谁再去玩它,这个分化后的抢花炮活动逐渐便在人们生活中消失了。为什么人们新鲜劲过后会觉得它厌烦了呢?原因于分化解析后的民族传统体育,它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相互整合的模式,同时,它也瓦解了那种综合的价值标准。更确切地说,就是分化解析后的民族传统体育变成一个纯粹的身体活动或竞赛,不符合村民的审美习惯。
而平安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完全走的就是从综合到分化的道路。传统村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如在春节期间举行的村寨联谊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民族社日鬼节(也就是农历七月半)举行的打师公活动都是综合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的转型,综合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因缺乏人们的主观引导,没有传承下来。在一种传统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情况下,这种综合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被割裂分化出来,成为一个个单项走进了村民的生活,如分化出来的活动项目有抛绣球、跳竹杠、师公舞、板鞋舞等等。但是,这些分化出来的项目因缺乏社会基础,或者这些单个有机体的器官免疫力太弱,当社会一有风吹草动的,它们便受不了,便自动死亡了。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分化后的独立个体在出现状态无序时,不能进行机体系统相互间的协调,从而自动调节,变无序为有序,就好比如人的各个内脏器官一样,平时他们是协同工作的,当某一器官出现暂时的毛病,其他器官便会部分地代替它的功能,不会导致机体的迅速死亡。而如果各个器官都是独立个体时,一旦个体出现问题,这个系统就瓦解了,失范就产生了。平安村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是传统综合性活动分化的产物,当这种活动被质疑为导致村寨间旅游开发的恶性竞争和破坏村民间、村寨间团结时,这种分化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便迅速失去了其“抵抗力”,在村民的生活中自动消亡了。
4 分析、讨论与结论
1.平安村与富禄村的两个个案说明了组织因素在民族传统体育问题上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平安村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问题介入甚微。正如当时富禄花炮组委会主任王仁生所说的,没有政府的组织或政府的在场,村民就是一盘撒沙,不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恢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按道理来说,平安村传统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远比富禄村丰富,而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平安村寨目前没有传承下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是,富禄村则不一样,不但以前被禁止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恢复了,而且,形成了以抢花炮活动为主打项目的民间习惯性节日“花炮节”,同时,又依托“花炮节”带动了其他村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本村落地生根。这两个个案表面上看似乎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代表全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组织行为,但是,这两个个案又无不是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缩影,具有普适性。所以,组织因素是考量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失范的一个维度。
2.一般来说,意义因素导致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范,主要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意义的匮乏,也可以说,是不同时代赋予意义的匮乏,或者是其意义不符合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存活就会存在问题。如平安村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断地消亡,就是由于其活动意义的匮乏,使村民觉得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一种无用感”[2]而导致失范。富禄村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不断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新的时代意义后,其发展则表现为生机勃勃。这两个案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是同样具有普适性的,因此,可以认为,意义因素是考量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失范的又一维度。
3.一系列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过分强调比赛结果的实例,说明了强调结果会减弱活动过程的娱乐性,将参与活动过程的满足感会转移到获胜的满足感上,从而导致人们行为转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此,便使得制度性手段与活动目标不协调,甚至相脱节。事态发展的最后结果是活动在“内力”和“外力”的作用下逐渐消亡(这里的“内力”指由于活动自身制度性手段与活动目标相脱节,导致活动无法组织下去;“外力”则是指外来的干预因素,如因活动产生更坏的社会影响,政府将出面禁止活动)。可见,目标因素是考量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失范的一个重要维度。
4.提出动机因素,如“民族传统体育行为动机是在于物质和金钱的追求”,作为考量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失范的指标,目的就是为了给民族传统体育提出预警,说明这种行为已经存在潜在的危机,应该合理地引导人们行动的动机发生转移。否则,任由这种人们参与活动只是对物质和金钱感兴趣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你今年提供彩电是满足了村民的物质需要,明年提供摩托车也能满足村民的物质需要,当村民们彩电、摩托车都有了,已经不稀罕了,你还能给他们提供什么物质,况且人的欲望的增长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是无止境的。因此,事态发展到最后必然是民族传统体育组织的“崩盘”,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消亡。
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模式被解析或割裂这种现象,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它都是一种系统平衡态的打破,但这种打破又不同于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所提出的非平衡系统的耗散结构类型[10]。普利高津的非平衡系统的耗散结构的存在,首先必须是这个系统没有被瓦解,它是系统内部与外部不断进行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和沟通,进而使这个系统不断地自我组织、自我生产,不断地克服系统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并将系统的混乱无序过渡到统一有序的状态中去。相反,长期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综合性形式正是普利高津的非平衡系统的耗散结构的典型。因此,形式因素也是考量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失范的重要维度。
标签: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