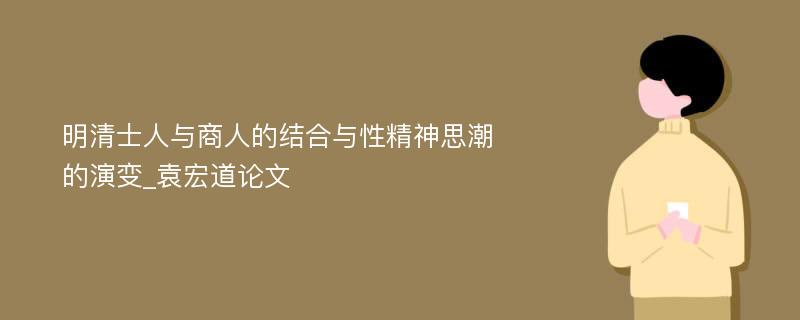
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思潮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性灵思想的活跃,其背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复苏,还有反对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扬等。但是,论者往往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商贾的活跃及士与商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明清时期性灵思潮的演变,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明中叶的孕育期,晚明的高峰期,清中叶的集大成期。这三个时期性灵思潮的生成与发展,都与商贾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密切相关。换而言之,士与商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明清时期性灵思想活跃的一个重要动因。
一、明中期商贾之风影响下的转变——由格调转向性灵
性灵思潮孕育于明代中叶。明代中叶,尤其是正德(1506-1521)以后,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十三中曾经分析正德前后的情况:“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这种弃农经商、活跃商品经济的势头,以南直隶(南京)、浙江等地区发展较快。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有很大的转变。例如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在《节庵方公墓表》中为苏州府昆山商人方麟作传,塑造了一个弃去举业而经商的典型,并且一反重农轻商、重士轻商的传统观念,对士、农、工、商的价值作了新的评价: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1](p.941)。
在“尽其心”和“有益于生人之道”的前提下,肯定士、农、工、商的平等地位,这与中唐时期韩愈有关士农工商的论述同中有异。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又说:“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相生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2](pp.12-19)显然,韩愈从儒家仁义的角度论述士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价值,而王守仁则是从“以求尽其心”即心学的角度,论述士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价值,后者为心学及尔后出现的性灵思潮与商贾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中业商贾之风对王守仁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哲学思想(心学)的层面,而对前七子中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和康海的影响则主要侧重于文学思想的层面。李梦阳(1472-1530)的祖父为商贾出身。他的《空同集》中,不仅有《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3](卷45)、《梅山先生墓志铭》[3](卷45)、《明故王文显墓志铭》[3](卷46)、《鲍允亭传》[3](卷58)等碑传文,为兰阳商人丘琥、徽商鲍弼和鲍允亭、蒲商王现等商贾列传,而且有为士而商、商而士者的诗文集所写的序记等,如《潜虬山人记》[3](卷48)、《方山子集序》[3](卷51)、《缶音序》[3](卷52)等,这些都是李梦阳重要的文论。例如,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引王现语云:“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与王守仁一样,以“同心”沟通了士与商之间的关系。又如《潜虬山人记》与《缶音序》是分别为徽商佘存修、佘育父子诗集所写的序与记,在《潜虬山人记》中较多地记述了李梦阳对徽商佘育诗学思想的影响:“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而在《缶音序》中侧重叙述了徽商佘存修的“作诗本旨”,可见徽商佘存修诗歌创作对李梦阳的影响。但这两篇为徽商诗人所作的序记中均体现了李梦阳宗唐抑宋的格调说与“情以发之”的情感论并存的特点。如《潜虬山人记》中有云:“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又如《缶音序》中,一方面从主调或主理的角度强调唐诗与宋诗的对立,反对所谓“主理不主调”的宋诗;另一方面,强调“感触突发,流动情思”,追求“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显然,李梦阳与商贾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倡言格调上的复古,二是强调“流动情思”、“情以发之”的情感论。也就是说,以士与商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李梦阳的格调论中孕育出性灵说的某些因素,因为性灵说中以情为核心内涵。
康海(1475-1540)受商贾之风的影响,有与李梦阳大致相同的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家庭方面,李梦阳的祖父曾为商贾,康海的叔父康銮为“长安人言善贾者”[4](卷39);二是康海也曾为商人作传,如《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4](卷38)等。当然,康海也有与李梦阳不同的方面,那就是他曾亲自参预商业活动。在他因党附刘瑾而谪居家乡之后,“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男女长幼来观者数千人”[5](《闲居集》卷10)。正是由于谪居生活与商贾之风的直接影响,他后期的文论如《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跳出模拟汉唐的窠臼而主张因情命思,缘感自鸣:“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兴会者,诗之道也。”[4](卷32)。将“情思”与“兴会”提升到“诗之实”、“诗之道”等文学原则上,较之于李梦阳在格调说中孕育情感论因素,则是向性灵说跨近了一大步。
后七子中的代表人物王世贞(1526-1590),是明中叶在商贾之风影响下转变心态,并由格调转向性灵的一个典型。王世贞被视为明中叶复古文坛上的巨子,文主秦汉,诗主盛唐,倡言格调,崇尚古雅。但是,他在明代中叶率先提倡性灵说:
顾其大要在发乎兴,止乎事,触境而生,意尽而止。毋凿空,毋角险,以求胜人而刿损吾性灵。(《湖西草堂诗集序》)[7](卷46)
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邓太史传》)[7](卷73)
从与“工于色象雕绘”(即在格调尤其是文辞上刻意修饰)的对立面来论述发抒性灵,既是王世贞对七子派宗汉崇唐、追求典雅格调等复古理论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这种转变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王世贞与商贾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王世贞是明代中叶与商贾交往最多,受影响最大的名士。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340篇,为商人所作59篇,约占17%。其实,《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还有多篇为商人所作的传记。这其中有浙江、山东、广东商人,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与苏州商人。据《古今奇闻》(卷三)等记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流行着“钻天洞庭(指苏州府洞庭商帮)遍地徽”的谚语。在这种背景下,家在苏州府太仓又在全国各地做官的王世贞深受徽州、苏州(包括洞庭东西山)商人的影响,往往与他们之间有某些契合处,如在《程汝义诗小引》中说徽商诗人程汝义“好以吟咏自适”[6](卷69)。又如《张隐君小传》云:
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遴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揳琴,揄袂,跕屣,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6](卷84)。
显然,明代中叶徽州、苏州等地商人畅舒心志、吟咏自适的思想作风,与王世贞的性灵说有契合的一面。从文学思想演变史的角度来看,王世贞是明中叶由格调转向性灵的桥梁,其转变的动因之一是他注重与商贾相互交流,深受“从耳目,畅心志”等商贾之风的影响。
二、士商心灵上的契合与晚明性灵思潮的高峰
经过明中叶较长时期的孕育,到晚明时期性灵思潮形成了高峰。其主要标志是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竟陵派钟、谭的抒写“幽情单绪”以及郑元勋的“文以自娱”等。袁宏道(1568-1610)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苏州吴县作《叙小修诗》[8](pp.187-189),其中大胆地树起“独抒性灵”的旗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标志着晚明性灵思潮高峰期的出现。
袁宏道虽为湖广公安人,但此时正在苏州府吴县任县令。显然,吴县是晚明性灵思潮高峰的发祥地,而吴县乃至苏州府则是明代中后期商贸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时活跃于全国的十大商帮之一——洞庭商帮的据点在吴县的洞庭东山和西山。袁宏道曾于万历二十四年游览过洞庭东、西山,有《西洞庭》、《东洞庭》[8](pp.161-164)等游记,其中记述了他对洞庭东、西山“民竞刀锥”等经商风俗的直接体验。袁宏道在苏州府任县令期间,与当地的商贾多有交往,其中最为频繁的是与苏州府长洲商人张冲之子张凤翼、张献翼的交往。袁宏道作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锦帆集》之一中有《张伯起》、《张幼于》诗(张凤翼字伯起,张献翼字幼于),《锦帆集》之二中有《识张幼于箴铭后》、《识张幼于惠泉诗后》,《锦帆集》之四中有《张幼于》尺牍三封。尔后的《解脱集》之四中也有《张幼于》尺牍二封,写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张凤翼、张献翼兄弟作为商人之子的身份。这主要依据是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十一中《张季翁传》、王世贞的《明故处士云槎张君墓志铭》[6](卷92)、李攀龙的《张隐君传略》[9](p.486)等。后者云:“隐君张冲者,其先钟离人,徙金陵,再徙吴门,家世服贾云。”其中又云:“王生(指王世贞)往为余谈,隐君家仲子献翼兄弟,故奇士也。”商人张冲之子张凤翼、张献翼以及张燕翼,有“吴中三张”之名,其中以张献翼为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太学献翼》中云:“献翼……好游大人,狎声妓,以通隐自拟,筑室石湖坞中,祀何点兄弟以况焉。晚年与王百榖争名,不能胜,颓然自放。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袁宏道也在《张幼于》诗中写道:“家贫因任侠,誉起为颠狂。”,[8](p.145)显然,张献翼是当时苏州地区一个“颓然自放”、“越礼任诞”、“任侠颠狂”的商贾子弟的典型。在吴县任县令期间的袁宏道与他在心灵上颇为契合,往往以不能与他倾肠一吐为恨:“吴中无足系去客者,独大小何君(以南朝梁何求、何点兄弟喻张凤翼、张献翼兄弟),经年末得倾肠一吐为恨耳。”[8](p.282)他又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指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最引人注目的是《解脱集》之四《张幼于》尺牍中的一段话: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子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8](pp.501-502)。
显然,袁宏道与商贾子弟张献翼交流的心得,与他在《叙小修诗》中力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精神是一致的。袁宏道之所以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高标,从相反相成的角度来说,有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0](p.7348)等复古思潮的反作用;从相因相生的角度来说,有“雅不与时调合”[8](卷19)的徐渭,强调“至情论”的汤显祖和力倡“童心说”的李贽的先驱作用。而徐谓又是商贾之弟,其伯兄徐淮是“足几遍天下”、“散其赀数千金”的商人[11](p.633)。汤显祖也亲自目睹海外贸易,他在《香岙(今澳门)逢贾胡》诗中写道:“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12](p.428)李贽的远祖从事过商业活动,有的还远航海外。他在游江汉时,手书张居正《泊汉江黄鹤楼》并改题为《江上望黄鹤楼》:“枫霜芦雪净江烟,锦石流鳞清可怜。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九秋槎影横晴汉,一笛梅花落远天。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13](p.128)对于袁宏道来说,他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直接的动因之一,是苏州地区商潮的影响,尤其是苏州商贾及其子弟的“越礼任诞”、“任侠颠狂”的精神,使得他在任吴县县令时思想更为解放:“为吴县日,倡为觞咏,遍排名流,历诋往哲,举当世所奉盘帨而插骚坛者,悉掊而仆之,虽众怒弗忌也。”[8](p.1663)
徽商的影响,也是公安派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的一个重要动因,《广陵集》中有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所写的《饭王太古馆中》、《王太古令郎有父风,即赋》[8](p.546)诗二首。王太古,即王野。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山人野》中云:“野,字太古,歙人。从祖仲房,以称诗有闻。太古儿时,习为诗,稍长,弃博士业,从其兄贾江淮间……久之,诗益有名,游于金陵,不轻谒人。贵人慕其名,访之,累数刺,始一报谒。蹇驴造门,称‘布衣王野’,投刺径去……子儒劭,字彦纶,亦能诗,早卒,有《胐明草》。……人谓得乃翁衣体也。”又如袁中道(1570-1623)的《吴龙田生传》为徽州商人吴文明作传[14](pp.738-739),塑造了一位儒商(“公贾也,而行实儒”)形象。这位儒商不仅与袁中道相交颇深,而且也乐于和袁宏道交游:“中郎(袁宏道,字中郎)游广陵,公乐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也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贽从游。予校新安,长君竟入新安校。”其实,袁宏道、袁中道等人所结交的徽商,不仅是上文所提到的吴文明,又有如吴元询等,袁中道有《新安吴长公墓表》。其中所谓“爱其(指墓主吴元询)贞淳,有先民风”,爱其“为真人”云云[14](p.772),与公安派“性灵”说的精神相通。
竟陵派的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提倡“求古人真诗”,抒写“幽情单绪”[15](p.236),将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深化也有异化,其动因之一也是儒商精神。上文提到的与袁宏道交往的徽商诗人王野,与竟陵派的关系也相当密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山人野》中指出:王野“晚年诗颇为竟陵熏染,竟陵极称之,为评骘以行世。”其实,这也与钟惺商贾家庭出身的背景有关。钟惺的祖父钟山,曾经商。据钟惺撰《家传》云:“祖虽勤俭,耕商作业,然意度落落然常出于其外……尝经商远归,囊可数百金,偶陈诸案而笥之。”[15](p.371)钟惺的《程次公行略》[15](pp.516-519)、《司城程公墓志铭》[15](pp.535-538)等,分别为徽商程道庚、程敬弘等立传。程道庚的父亲程嗣勋是位名儒,又有经商意识,视货殖为大道,曾经教导儿子程道庚说:“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程道庚继承了父亲的儒商精神,经商江淮,栖游金陵,又入赀南雍,为国子监生员。如果说程道庚是“商而儒”的一个典型,那么,程敬弘则是“儒而官,官而贾”的典型。钟惺称赞程敬弘说:“公负至性,内行醇备,儒而官,官而贾,皆有条理,而以诚心出之。”以“诚心”赞美儒商,可见儒商精神与竟陵派的“真心”(钟惺《诗归序》:“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说有某些相通之处。这也有力地说明:徽州等地区的儒商精神是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崛起并演变的动因之一。
明末郑元勋(1604-1645)集士、商于一身,将性灵说演变为“文以自娱”说。郑元勋,字超宗,号惠东,盐商出身,侨居扬州。其祖父郑景濂业盐于扬州后,遂占籍江都,据陈继儒《洁潭郑翁传》说,他“独谓盐策可能起家,饶智略于局,坐筹贵贱赢缩之征,如指掌上”。自郑元勋的祖父起,几代人业盐扬州,成为明代两淮地区的巨商豪贾。郑元勋商而士,天启四年(1624)中举人,历官兵部职方司主事。著有《影园集》,并辑有小品文集《媚幽阁文娱》。他在《文娱序》中说:“文以适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侠客、忠臣、骚人、逸士,皆能快其臆而显摅之,故能谈欢笑并,语怨泣偕……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16]显然,“就诗文批评本身而言,文娱说产生的基础是性灵说。创作上独抒性灵的自适态度,与鉴赏上以美为宗的文娱说是相辅相成的。”[17](p.546)
当然,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实行恐怖统治,是郑元勋“文以自娱”说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而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兼有士商双重身份的郑元勋的生活情趣。我们读一读他的《影园自记》,[18] (卷首),便更为清楚:以性灵说为基础的“文以自娱”说,其形成的基础之一是士商共同的自适情趣。
三、士商的互动与清中期袁枚等集性灵思想之大成
康熙末年,清朝开始进入中期。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诗坛上也流派纷呈:有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赵翼等标榜性灵,集明中叶以来性灵思想之大成。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侧重考察的动因之一,是士与商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袁枚(1716-1798)是清中叶性灵派的主将,他的身上较多地体现了当时士与商契合的风貌。他与洞庭商人有直接地接触。乾隆四十四年(1779),袁枚曾游吴县洞庭山,与洞庭商人蔡璘之子相见。十四年后,又为蔡璘作传,这就是《吴县文学蔡君勉旃传》[19](p.1869);又分别为徽州商人鲍宜瑗、汪孟翊撰写传记或墓志铭,即《鲍竹溪先生传》[19](pp.1904-1906)、《汪君楷亭墓志铭》[19](pp.2078-2080)。后文中记载汪孟翊屡试不第后说:“子贡废举,亦称贤士。”子贡(端木赐)在拜孔子为师之前曾经商,是先秦儒商的典型人物。汪孟翊所云,旨在继承与张扬子贡的儒商精神。在此,袁枚以记其言表示对徽商汪孟翊的肯定,而《林君毅庵墓志铭》[19](pp.1828-1829)则以记其行表示对福建龙岩商人林嘉俊的赞许:“生有干略。父克旋服贾折阅,家无担石之储。群持钱负贩,权其子母,走闽、粤、齐、鲁、晋、楚、吴、越间,渡海越山,滨死者屡矣,卒以诚信勤敏,累至万金。”其实,袁枚对商贾的推许,还表现在他为商贾所作的传记和墓志铭之外的诗文中,如《与卢转运书》中说:“其利市三倍者,惟商耳。”[19](p.1508)又如《真州竹枝词》其一云:“流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族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19](p.678)
袁枚交往最多的,还是迁居扬州的徽商如江春、马曰琯、程晋芳等。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徽州歙县江村人,他是乾嘉朝显赫一时的盐商代表。关于江春,袁枚有《扬州康山诗为主人江春作》[19](p.609),又有《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19](pp.1862-1864)等。后文深情地回顾了他与江春交往的情况:“乾隆己未(1739)冬,余恩假归娶,路过扬州,初识江公颖长。余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时两淮司禺荚者侈侈隆富,多声色狗马、投焭格五是好;而公独少年渊雅,与王己山、程午桥诸先生游山赋诗。余洒然异之。”马曰琯,徽州府祁门人,字秋玉,号嶰谷。自祖父马承运业盐两淮,始迁入扬州,入江都籍。马氏家庭为清代两淮著名盐商,马曰琯好结宾客,丛书楼藏书甲于东南,著有《沙河逸老集》。关于马曰琯,袁枚有《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诗[19](p.687),又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记述了马氏玲珑山馆名士群集,“争为诗会”的盛况。程晋芳,字鱼门,号蕺园,徽州府歙县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召试,授内阁中书,三十六年(1771)成进士,官吏部主事,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改编修。“程鱼门家世业盐,拥资巨万,晚岁家中落。”[20](p.843)袁枚与程晋芳的交往最为密切,有《余正北上而鱼门来宁应试,治行已具不能小留,路寄此诗》[19](PP.150~151),诗云:“高唱骊歌路正遥,忽逢旧雨过蓬茅。尽拼此夕同君话,难改行期把客抛。芳讯叮咛千里寄,奇书交易两家抄。临歧双枕殷勤赠,要我时时梦故交。”士商之间的友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又有《寄鱼门舍人一百韵》[19](pp.415-417),还在《仿元遗山〈论诗〉》[19](pp.688-691)中论赞程晋芳云:“束发愔愔便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尤其是有多篇文论,与程晋芳交流文学思想,如《答程鱼门》[19](p.1520)、《与程蕺园书》、《再与蕺园书》,[19](pp.1563-1566)、《与程蕺园书》、《答蕺园论诗书》[19](pp.1800-1803)。正如袁枚在《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中所说:“君交满海内,而与余尤昵。”[19](p.1714)当然,袁枚与程晋芳也有分歧,例如程晋芳劝袁枚“删集内缘情之作”,袁枚断然拒绝,坚持“诗者由情生”的观点(《答蕺园论诗书》)。
清代中叶性灵派的副将赵翼(1727-1814)与商贾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乾隆十五年(1750),他以直隶商籍应试而中举。据孙星衍《赵瓯北府君墓志铭》中云:“以直隶商籍入学,中乾隆十五年庚午科北榜举人,补义学教习。”[21](p.1432)又据阙名编《瓯北先生年谱》中记载:“先生年二十四,以南籍生员,不能试北闱,会有族人在天津业鹾,招往试。商籍运使叶公昱得先生卷,叹为奇才,拔置第一。学使吕公炽按试,取入泮。秋应顺天乡试,以五经卷获隽。”[21](p.1393)对于这次冒商籍应试北闱而中举,赵翼在当时有《赴津门》诗自述其事其情:“西笑到长安,求官拟唾手。岂知一青衿,易地成弃帚。南庠试北闱,令甲所不受。闻有牢盆籍(即商籍),游客借已久。入作黉舍生,可列乡射耦……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21](p.39)在赵翼冒商籍中举之中,商籍运使叶昱起了关键作用,赵翼有《津门呈叶东壶运使》诗感其恩德:“也随土著入胶黉,失一兵仍得一兵。唇舌换如儿学语,姓名变岂客逃生。鹏当北徙贪风便,鹊不南飞羡月明。说与先生应笑绝,几同火迫酂侯成。”[21](p.40)赵翼交往最多的,还是迁居扬州的徽商如江春、程晋芳等。关于江春,赵翼《瓯北集》卷三十有《江鹤亭方伯招同松崖未堂蘧庵松坪棕亭春农游康山即事》诗,卷三十三有《江鹤亭挽诗》等。关于程晋芳,《瓯北集》卷十二有《竹君述庵蕺园来殷耳山璞函小集寓斋即事》诗,卷二十七中有《寄蕺园》诗等。
在袁枚、赵翼与迁居扬州的徽商以及其他商贾的交流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情为先,性灵自适。如袁枚《扬州康山诗为主人江春作》诗中有云:“青山如高士,不肯居城中。难得邗江城,中藏一华峰。相传栖息者,昔为康武功。于今属江淹,规址增穹隆……君今继前徽,风雅有同调。”[19](p.609)康武功,是指康海,陕西武功人,号对山。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二《状元康海》中说,明中叶的康海谪居后“尝贾于维扬”,又在扬州康山与客宴饮弹琵琶,缘情而发,放荡形志。赵翼也在《江鹤亭方伯招同松崖未堂蘧庵松坪棕亭春农游康山即事》诗中写道:“鹤亭特借对山名,自写胸中丘壑情。对山翻藉鹤亭力,风流从此垂徽声。”[21](pp.673-674)江春继承了康海等人性情自适的传统并有发扬,所以说“君今继前徽,风雅有同调”。袁枚常与“家世业盐”的程晋芳以书信论诗,其中有《答蕺园论诗书》,书中写道:“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19](p.1802)“情”或“性情”是性灵的核心,男女是真情的本源,所谓“提笔先须问性情”[19](p.73),又所谓“自把新诗写性情”[19](p.323),所谓“情之最先,莫如男女”。显然,袁枚、赵翼与商贾在性灵说的核心——情性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显现出士商契合的深度。
二是士商群集,争为诗会。袁枚在《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中赞扬徽商马曰琯云:“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并注云:“吾乡厉太鸿,陈授衣诸君皆主于其家。”[19](p.687)又《随园诗话》卷三写道:“马氏玲珑山馆,一时名士如厉太鸿、陈授衣、汪玉枢、闵莲峰诸人,争为诗会,分咏一题,裒然成集。”继马曰琯之后,江春又发扬了这种风气,他亦好交游文士,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载,江春对于“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奇才奇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又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中说,程晋芳亦“性又好客,延揽四方名流,与袁大令枚、赵观察翼、蒋编修士铨为诗歌唱和无虚日。”无论是士商“争为诗会”,还是巨商豪贾“供养文人过一生”,都加大了士商交流的力度,增强了士与商之间的影响。
三是领袖风范,老成气度。马曰琯既为巨商,又以诗名,著有《沙河逸老集》。其丛书楼藏书甲于东南,四库馆开,进书七百余种,可见其儒雅博学。而江春在盐商中更具有领袖风范、老成气度。江春在其父去世后,被推为两淮总商,一时群商多趋下风,受其指麾。袁枚《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中写道:“亡何,鹾务寝削,商中耆旧凋谢。恭遇国家大典礼、大徭役,大府无可咨询,惟公是赖。公阅历既久,神解独超,辅志弊谋,动中款要。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19](p.1862)每当两淮巡盐史上任前,在接受乾隆皇帝的训示时,乾隆总要说:“江广达(江春行盐的旗号为“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赵翼《江鹤亭挽诗》也写道:“须髯皓白地行仙,领袖淮纲数十年。”[21](p.759)从袁枚、赵翼为江春所作的墓志铭和挽诗中,可见江春等盐商的领袖风范、老成气度,其对袁枚以诗古文主东南文坛及赵翼成为性灵派副将,不无影响。
四是亲睹内外贸易,心目超旷。袁枚曾亲睹江春等扬州巨商豪贾“神解独超”的风采,赵翼则亲睹边境贸易与对外贸易,更是大开眼界。乾隆二十五年(1760),赵翼扈从出塞,途中见到蒙古风物与行事,有《扈从途次杂咏》组诗三十首[21](pp.143-149),其中有《买卖街》(贾人随营设街贸易)写边境贸易。乾隆三十五年(1770),赵翼奉旨调守广州府,亲自目睹沿海与对外商贸,有《南珍》、《番舶》等,皆目击成诗,有感而发。《南珍》诗中云:“凡百瑰玮负奇质,咸不胫走来羊城。天宝既征孕育厚,人巧亦见工力精。不惟其产惟其聚,奇彩耀市目欲瞠……合浦六地产有几?贩自番舶来重瀛……伊余一双书生眼,乍睹不觉适适惊。”[21](pp.333-334)《番舶》诗中则写道:“峨峨百丈船,横潮若山嶂。一载千婆兰(番语三百斤为一婆兰),其巨不可量……不惜九死行,为冀三倍偿。重利而轻生,举世因同恙。伊余过虎门,适遇碇五两。梯登试一观,心目得超旷。”[21](pp.344-345)显然,亲睹国内外贸易的盛况,使得袁枚、赵翼等人也“神解独超”、“心目超旷”。
总而言之,以性情为核心的士商契合,以及群体的交流、领袖的风范、老成的气度、超旷的心目等,促进了袁枚及赵翼等人性灵说的成熟与完备。诚然,袁枚与赵翼等人性灵说的成熟与完备,还有其它动因。比如清代乾嘉时期具有在丰富的历史积累上集大成的时代特征,还有袁枚等人在反对程朱理学,批评乾嘉考据之风,批评翁方刚的肌理说,尤其是在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之中,不断地弘扬与完善性灵说。因而,乾嘉时期的袁枚等人集明中叶以来性灵思想之大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性灵说[22](p.394)。在此,我们要重申的是袁枚等人集性灵思想之大成,其动因之一是士与商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动力作用于明中叶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性灵思潮的高峰期和清中叶性灵思想的集大成期。总而言之,士商契合是明清性灵思潮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