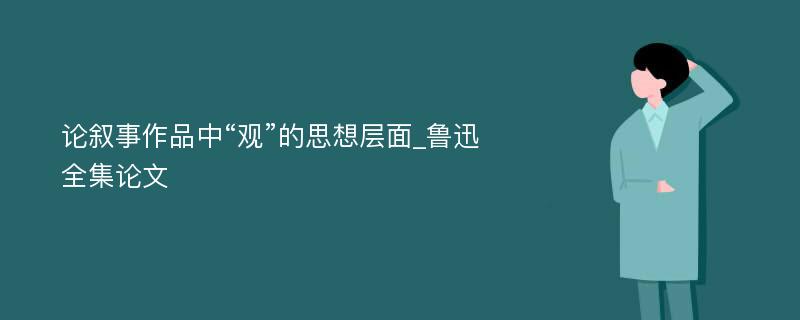
论叙事作品中“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视点论文,层面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叙事作品中,必定存在着一个或多个故事的讲述人,即叙述者,将故事叙述出来。而在叙述的过程中,无论所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如何表现出来,都一定会经由一个特定的“视点”(point of view),也就是一个观察点。通过这一特定的观察点,叙述者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在对叙事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1905年,威特科姆(S.L.Whitcomb)在其《小说研究》一书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叙述者,其观察点”的问题,他声称在这里所涉及到的是“语段或情节的统一大大地依赖于(叙述者)位置的清晰和稳定”(注:Norman Friedman,"Point of View in Fiction:The Development of A Critical Concept."The Theory of the Novel,Ed.Philip Stevic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p.114-115.)的问题。此后,卢伯克(P.Lubbock)在《小说技巧》中所说的话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观察点问题,也就是在其中叙述者相对于故事所站的位置的关系问题所制约。”(注:Percy Lubbock.The Craft of Fiction.London:Jonathan Cape,1966,p.251.)
人们逐渐注意到,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说”,与其所置身的某一“观察点”的“看”,二者既可以统一,也可以加以区分。原则上,一个人可以说出他或她所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看与说。这时,“看”与“说”是一致的。但是,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一个人可以说出某一个特定的人物所看到的东西,以另一个特定人物的“视点”所见来进行讲述。因而,就叙事作品的叙述者而言,讲和看,既可以归于同一个媒介,也可以归于不同的主体。在这里,叙事分析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谁说?”——这是确认叙述本文的叙述者及其叙述声音的问题:“谁看?”——即谁的视点决定叙述本文的问题。热奈特据此区分了叙述(说)与聚焦(看),并由此区分了聚焦的诸种不同类型;米克·巴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叙述者与聚焦者。在巴尔看来,只有叙述者在讲述,即说出可以被称为叙述文的语言。而聚焦者则属于这一叙述者讲述的故事的层面。它属于经由感受的独特行动者、视点的秉持者所表现出来的给予素材的“着色”。(注:见[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页。)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不论叙述者所说出的是他或她本身所看到的,还是说出经由其他人物的“视点”所聚焦的,在叙事作品中都一无例外地存在着通过一个或多个特定“视点”叙述者进行讲述的事实。
“看”或者“聚焦”,尤其是后者,由于热奈特在阐述时选择了一个摄影与光学上的用语,并隐喻性地使用了“叙述投影”、“视点决定投影方向”(注:见[法]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等说法,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经由“看”或“聚焦”所涉及到的视点,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巧或形式层面的视觉问题,而与其他层面无涉。实际上,“看”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视觉的眼光,而这只是就强调观看的角度而言,它并不只含有视觉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感知、感受、体味所“看”或可能“看”到的东西,而这当中也可以包含价值与道德判断等更深层次的意义。由“看”所脱胎的“聚焦”同样如此。率先采用“聚焦”一词的热奈特,后来实际上也意识到“聚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纯视觉”的“看”的问题,而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比如,按他所说,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索多姆Ⅰ》中,透过马塞尔所聚焦的夏尔吕和朱尔安之间的那一幕的结尾,属于“听觉的聚焦”。因此,在提出“聚焦”这一看法11年之后,热奈特在1983年出版的《新叙事话语》(这是作者针对学界对他的《叙事话语》所提出的批评所作的回答以及补充与修正)中提到,他本人对这一用语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运用了一个纯粹视觉的、因而过于狭隘的用语”。他认为,我们“显然可以用‘谁感知’(who perceives)这个涵盖更广的问题来取代‘谁看’的问题。”(注: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64.)而巴尔在她对于“聚焦”的阐述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她指出,聚焦是“视觉”(即观察的人)和被看对象之间的联系,并这样对“聚焦”进行定义:“我将把所呈现出来的诸成分与视觉(通过这一视觉这些成分被呈现出来)之间的关系称为聚焦(focalization)。这样,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就“感知”而言,她认为,它是受到众多因素影响的,诸如一个人对于感知客体的位置、光线、距离、先前的知识,对于客体的精神心理态度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影响着一个人形成并传达给他人的图像。(注:[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由此可见,在对叙事作品的分析中,与叙述、聚焦、叙述者、聚焦者等联系在一起的“视点”这一概念,超出于纯粹视觉的或形式的层面,而与其他层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可以在几种不同的意义上对它进行研究。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其中一个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层面,即“视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二
所谓意识形态,是一个含蕴十分丰富、而又引起广泛争论的概念。本文不准备对这一词语自法国人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开始使用以来所产生的种种不同看法展开讨论,而只是就其一般的意义上采用它。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它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表明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见解和评价。意识形态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艺术中也不例外。通常,人们注意得更多的是它透过作品内容的展现,而往往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形式层面上所具有的意义。后者虽然不象前者那样明显,但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比较而言,在作品的形式层面上,与意识形态层次的关联可以说是形式研究中难度最大的,但是,对它的研究恰恰可以更为有效、更为敏锐地接近文学艺术作品,从中探寻某些带本质性意义的东西,因而,在叙事理论的研究与文本分析中它日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在涉及到“视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什么是所关注的呢?我们知道,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叙事作品,都由具体的作者所创作。其中叙述者的确定,“视点”的选择,可以说,都是由实际意义上的作者所决定的。而在这一选择中,无疑包含着作者希望传达给读者、观众或听众故事的含义,希望读者如何以及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所传达出的信息、意义、价值规范等。这样一来,“视点”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是否主要表现为与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相联系呢?
不容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往往成为作者自身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的表露。作者也往往借助作品中的叙述者、人物、事件等实现与读者的交流,即布斯所说的相互间错综复杂的隐含对话,这种对话同样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任何阅读经验中,都存在着作者、叙述者、其他角色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隐含对话。四者中的每一个在涉及到其他任何一个时,都在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甚至是身体的轴线上,可以从同一到完全对立而变化不一。”(注:Wayne C.Booth:"Discourse and Point-of-View."The Theory of the Novel,Ed.Philip Stevic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97.)然而,在涉及到“视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它与作者自身意识形态的对应联系,但研究的结果却显示出,它往往超出了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对叙事作品阅读与分析的实践中,往往会不时出现读者、甚至于研究者将叙事作品的叙述者与作者本人混为一谈的情况。(注:以鲁迅小说为例,捷克著名学者普实克认为:“在鲁迅的作品中,故事的叙述者常常是一个确定的人物,或是作者本人(如在《祝福》和其它一些作品中),或是某个其他具体人物:《孔乙己》中酒店里的男孩,《伤逝》中的鳏夫,等等。”(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原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也说到:“应当充分肯定,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在大多数场合就是作者自己,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观点和作者相近的人。”(见谢曼诺夫:《鲁迅和他的前驱》,李明滨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这种情况在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出现时显得更为突出,它甚至于对作者本身造成了某些困惑。(注:作家严歌苓曾说,能写好性爱的作家是最懂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她自己早就希望以最不保守、最无偏见的态度去写一部爱情小说,这正是她在写她的长篇小说《人寰》时的态度。但是,出于对读者将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自己联系起来的担心,她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得不作了某些调整,她说:“《人寰》这个作品在开始写作时是不保守的,可我感到读者可能会把小说中的‘我’和我联系起来,所以作了些割舍。不然,它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一个女人对一个心理医生讲自己的感情史和心灵史,应该更坦诚些。所以我意识到,即使有艺术形式的保护,艺术家做到坦诚也是不容易的。”(见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又如,李长之在谈到鲁迅的小说《伤逝》时说:“无疑地,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的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故。”“涓生,也就是作者鲁迅自己,有的是高傲和倔强。”(见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83、90页)。在当时,将《伤逝》看作为鲁迅的“自叙传”是很时髦的。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写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20页)。)而我们知道,在叙事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真实作者和叙述者的区分。前者是写作主体,后者则是叙述主体,前者是一个或多个具有真实身份的个人,后者则只具有语言主体的性质。正如父母在给孩子讲故事时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必须放弃成年人的理智,而相信他们眼里的世界和奇迹都是真实的一样,对于叙事艺术来说,类似的变化就是作者开始叙事时必须经历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叙述者从来就不等同于作者,而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一个由作者蜕变而成的虚构的人物,一个“施动者”。(注:参见[德]沃·凯瑟:《谁是小说叙事人?》,白钢,林青译;载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在这一点上,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对我们很有启发。布斯称“隐含作者”为“作者的第二自我”,作者的一个“隐含的替身”。作者在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然而,一个作者可以有各种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件,可以根据与每个通信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而会有他的自我的不同替身一样,因此,作者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表现自己。(注:参见[美]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1页。)这样,就造成了作者与其所创作的作品之间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复杂关系。
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心理复杂性。布斯认为,隐含作者在智力和道德标准上常常远远高于真实作者本人。也有人认为,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不必要、事实上也往往不是同一个人。一个作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信念、规范、感情可以和他在实际生活中所抱有的思想、信念、规范、感情不一样;当然,二者之间也可以不同程度地同一。这样一来,通过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视点去追寻真实作者自身的思想规范与意识形态,其可靠的程度就大大值得怀疑了。当然,尽管一个作者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不同的思想、信念与规范,但是,一般说来,在同一部作品中,隐含作者却往往被看作一个隐含的、稳定的实体,在作品中表现得合乎理想地始终如一。但是,这也并不表明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完全一致,而只意味着:一部特定的作品,其自身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存在着内在的、自成一体的思想、价值规范,它构成一部作品的内在机制,这与叙述者的视点并无必须联系。
将叙述者与真实作者加以区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割断叙述者与实际意义上的作者之间的关系,客观地说,在许多作品中,叙述者往往是承担作者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层面的最为便利的载体,他们与作者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我们无需像传统的叙事理论那样,将叙事作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而把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绝对隔绝开来。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分,意在强调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对具体作品作细致周密的分析,从而避免简单化,避免先人为主的趋向。
在叙事作品中,意识形态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品中的叙述者及其讲述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并经由他们的讲述与行动加以渗透的。因而,就“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值得关注的主要是叙事作品内部意识形态视点的载体,即叙述者与主人公的功能,及其在不同的视点中所表现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三
叙述者在叙事作品中的功能,首先就在于叙述,只有叙述才能成为叙述者,只有讲述故事才能形成为叙事作品的叙述者。这种讲述,就是叙事作品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将叙述者看作为既不是作者,也不是那个虚构的、常常一上来就亲切感人的人物,而是一个“面具”。在这个面具后面,是小说自己在叙述,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精神在创造世界。这种精神通过其本身的形成、叙说,运用创造性的词汇,构造并展现出一个绝无仅有的新世界。而“小说的叙述人,从明显的类比角度看,就是这个世界的神秘的创造者。”(注:[德]沃·凯瑟:《谁是小说叙事人?》,白钢,林青译;载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至于人物,既是小说的叙述者所讲述与创造的,同时也可能与叙述者发生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叙事作品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叙述者从哪种视点出发,在作品中评价并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他所描写的世界。原则上说来,这可能是作者本人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提供出来的视点,讲述者的视点(这一视点与作者并非一致),任何一个出场人物的视点等。(注:参见[俄]鲍·安·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彭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我们知道,在区分不同的叙述者的种类时,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就存在于叙述者仅仅充当一个纯粹的讲述者、自外于故事之外,还是同时也参与故事事件、成为一个作为故事人物的讲述者,即人物叙述者这两者之间。两者分别提供了不同的视点,而这不同的视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在作为纯粹的故事讲述人的视点下所出现的叙述者,通常称为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这样的叙述者的眼光完全不受限制,他的视点可以任意转移,超越时空,知晓古今,将他的聚焦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从一个场景转向另一个场景。他可以深入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看到他们心中所蕴含的一切。正如巴特所概括的:叙述者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既知道所有人物身上发生的一切而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认同)。由这样的叙述者所产生的视点通常在一部作品中贯彻始终,并成为作品中惟一的叙述者。这样的叙述者,一般说来属于权威的叙述者,同样也是一个“看”与“说”、聚焦与叙述合而为一的叙述者。正是以这样一个叙述者的视点为核心,构筑整部作品以主人公为中心的关系网络,而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评价往往就出自于这一权威的、看与说相结合的叙述者。
从单一视点出发的权威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对于相应的作品的意识形态显现与评价,通常不会出现在整体意义上看来所产生的内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这并不意味着,在一部作品中不会出现不同人物之间以言语和行动所显示的意识形态交锋;而是说,当出现这样的交锋时,在不同人物从各自的视点出发、从而产生相互之间的对立与不同评价时,最终将经由叙述者所作的叙述安排、人物关系网络之间对立统一的协调,也包括直接出自叙述者自身的叙述者干预等方式来对整个叙事作品加以调整,使不同的评价在作品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在作品整体的层面上保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评价的整一性。一如乌斯宾斯基所言,当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评价由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视点出发被给出时,“这个惟一的视点使得作品中所有其他视点都服从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部作品中出现另外一个视点,而它又与前者不相一致,譬如说,从某个人物的视点出发而作的对某些现象的评价,那么这种评价的事实本身首先则要接受源自这一基本观点的评价。”(注:[俄]鲍·安·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彭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这样,就不至于在同一部作品中任由对立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评价信马由缰、各行其是,而使读者无所适从、以至产生矛盾与困惑的状况。下面将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为例,以作进一步的阐释。
《阿Q正传》一开头便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年了。”(注: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以下所引该文不再加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以第一人称身份“我”介入到故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人物。细观之下,其实不然。整篇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与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保持距离的权威叙述者所进行的讲述。作品的中心人物是阿Q,而阿Q的个性既通过叙述者,也通过阿Q自身,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眼光传达给读者。在这里,经由叙述者的视点,展现出阿Q强烈而又盲目的自我认同与周围的其他人物对他的否定性认同的尖锐对立,这一对立形成了人物之间意识形态的巨大张力,它不仅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也成为人物性格、尤其是阿Q这一中心人物性格形成的基础。在赵太爷对阿Q关于阿Q是否其本家、阿Q是否姓赵的詈骂中,在未庄的闲人们对阿Q的戏弄中,在阿Q和王胡、小D的打斗中,以及阿Q对更为弱小的小尼姑的欺侮、对吴妈的调戏中等等,无一不显示出阿Q与其他人物在视点上的巨大差异,在行动与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对立,同时也通过这众多人物的眼光、经由他们的不同视点将阿Q的性格提供给读者。比如,阿Q很自尊,因他头上的癞疮疤而忌讳人们说“癞”,推而广之甚至于“光”、“亮”、“灯”、“烛”都讳。开头阿Q一听到人们说便骂、便打,但吃亏的时候多,便改为怒目而视。而未庄的闲人仍不放过他,以至于相互间冲突不断。吃亏之后的阿Q,开头在心里念叨、后来每每说出口的是“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说出之后却也和胜者一样,“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样,阿Q性格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开始凸显出来。它经由叙述者的视点,在更高的层面上以“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一画龙点睛般的解释加以提升,使阿Q性格中的一个主导层面得以形象化的定格。此后,在阿Q与人的冲突中,更将之推向极致。当有人扭住他,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阿Q却宁肯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而在被打之后,又以从叙述者的视点所作的描述深化了这一思想:“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由此可以看出,在作为作品意识形态载体的不同人物之间,可以出现几个不同的意识形态视点,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人物从各自的意识形态视点对其他人物进行评价,而叙述者则在更高的意识形态视点层次上进行叙述与评说,构成一幅错综复杂、对立统一的人物与故事图景。
在叙事作品中,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与话语层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中的叙述者、尤其是惟一的权威叙述者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位置,每一个人物也从各自的视点出发,表现出自身的立场,而所有这些,都会通过叙述者对人物的性格特征标记、对于人物话语的直接引述以及叙述者的干预等,在作品的话语层面展现出来。如我们所知,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诸如褒义词、贬义词,雅语、俗语,书面语、口语,以及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等所形成的习语和各种独特的语言。除此之外,在语言的运用中也包含着幽默、讽刺、反讽、反语等种种语言修辞手段。在叙述者的叙述与人物的语言运用中,常常可以或隐或显地感受到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味,而这都是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关的。仍以《阿Q正传》为例,在作品的话语表达中明显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从阿Q这一视点出发的是出自下层无业农民、流浪汉的毫无遮掩而又略带狡黠的语言;而与之产生明显对比的是出自高踞于贫苦农民之上的乡绅、权势者与有产者的语言。这些语言由其主体从各自视点出发的日常表达中表现出来,隐含着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阿Q在戏弄吴妈遭到秀才痛打时,牢牢记得的是秀才一句骂他的话:
“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
这里,“未庄的乡下人”与“见过官府的阔人”,二者在语言层面上意识形态的对立昭然若揭。而在二者的交往、对话中,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们构成两个平行的、判然有别的话语世界,在从各自的视点出发时,其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立场清晰可见,不可避免地打上各自价值观念的烙印。
在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讲述中,叙述者通常以外在于故事、不露面的内隐形式表现出来,叙述者的视点不仅通过对事件的描述、对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展现、话语的选择等透露出意识形态的观念与价值评价的态度,而且它具有在作品总体背景上起到某种超越人物与事件意义的作用。读者在阅读中尽管看不到一个人格化的叙述者在作品中露面,但却会或隐或显地感受到其视点所汇集的意识形态网络的力量。这种力量贯穿在作品中,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对于故事的理解。权威叙述者这样一种居于优势地位的视点,连同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会无形中对读者的价值判断起到一种导引的作用。
经由叙述者的视点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也可以不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此前已经提到布斯采用的“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在巴尔看来,布斯采用“隐含作者”,目的正是想讨论与分析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立场而不必直接提到真实意义上的作者的情况。它有着可以从叙事本文中推断出来的总体意义的意味。因而隐含作者是叙事本文意义的研究结果,而不是那一意义的来源。只有在本文描述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解释以后,隐含作者才可能被推断并加以讨论。(注:见[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通过对具体叙事作品的分析,人们可以对一部特定作品中所内在的隐含作者进行推断。在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中,人们将会发现,经由隐含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立场与真实意义上的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千差万别的。就《阿Q正传》而言,我们知道,鲁迅曾经谈到,他创作《阿Q正传》是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同时他也意识到,“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在中国实在算是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81-82页。)。此后,他在一篇以笔名写的文章中,再一次说到:“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144页。)。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之后,对隐含作者所凝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进行探讨之后,应该说,作者创作这一作品的意图,已通过作品中权威的全知叙述者对阿Q性格的描述而得到了实现。叙述者由表及里,从行动到思想,将阿Q这一人物种种可笑而可悲的行为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将“国民的弱点”以形象化的手法暴露在世人面前。这种对“国民的弱点”的暴露,全知叙述者利用他居于故事之外的地位,以纵观古今的无所不知的犀利目光给予了透视,并以各种叙述者干预与评论进一步加以深化。可见,在这一作品中,经由权威叙述者的视点所显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立场,大体上是与真实作者相一致的。
在叙事作品中,还有另一类叙述者,这类叙述者不仅充当故事的讲述人,同时叙述者也作为故事中的一个特定的人物参与到故事的进程中,并作为一个故事人物而活动,这就是所谓人物—叙述者。人物—叙述者,由于是以故事中的某一个特定人物身份来讲述故事的,叙述者的视点必定要受到限制,而无法如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那样对一切了然于心。如热奈特所言,在这种情况下,叙事可以不通过均匀过滤的方式,而依据故事参与者(人物或一组人物)的认识能力调节它提供的信息,采纳或佯装采纳上述参与者的“视角”或视点,好像对故事作了这个或那个投影。(注:见[法]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在涉及到视点时,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叙述者的视点必定带有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判断的态度,他或她必定按照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视点去看待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并与之发生与其独特身份相符的种种关系,同时又讲述自己程度不一地参与其中的故事。人物—叙述者既可以成为一部作品中唯一的叙述者,像许多以每一人称“我”出现的人物—叙述者自始至终地讲述由自己所参与的故事、尤其是回顾性的故事那样;另外,也可能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现多个人物—叙述者,各自从其视点出发,站在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讲述。后者的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其中有可能充斥着不同人物从各自视点出发的相互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且,在许多叙事作品中,正是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立与交锋,由人物—叙述者自身来完成对于人物的描述与刻画的。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任由人物—叙述者各自在叙述的舞台上自行表演一番,而不存在对他们作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与评价。只是这种价值判断与评价,可能来自于其他的人物—叙述者,甚至于在作品中还有可能出现一个参与或不参与故事的权威叙述者,经由这一叙述者的视点,更多地体现出作品中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后面在对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叙述者的分析中,我们会注意到这种情况)。
在叙事作品中,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区分最早由布斯提出。按照布斯所说,“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也就是说,经由叙述者的视点所显现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思想规范与隐含作者不相一致。同时,布斯也指出:“应该将不可靠一词保留给这样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注:Wayne C.Booth,"Distance and Point-of-View:An Essay in Classification."The Theory of the Novel.Eed.,Philip Stevic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p.100-101.)说到底,不可靠的叙述者,其核心在于叙述者的视点所显现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立场与隐含作者、从而可能与真实意义上的作者不相一致。这里所说的“不可靠”,不见得是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不“真实”,更多的是叙述者的“视点”对于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带有某些意识形态“偏见”,经由这些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视点的过滤,使读者对于不可靠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形成某些疑虑,反过来又使其讲述造成某种独特的叙述张力。
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视点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与道德评价“偏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道德意识上的差别,这样导致对事件、人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可以是智力上的,如果叙述者在智力上出现问题,他或她所讲述的一切就可能带来疑问;可以是年龄上的,一个年幼的孩童叙述者可能会在对事件与人物的描述中与隐含作者有别;可以是性别上的,一个男性或女性叙述者在故事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可能与作品中特定的隐含作者不相一致等等。
在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透过对那个虚构的密西西比州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描述,可以看出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缩影。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与奴隶制所留给后代的种种罪恶有关,透过作品可以看出,隐含作者对这种遗留的罪恶持反对态度,而且力图对人性如何被摧残、人与人之间如何难以沟通、精神如何得到挽救进行探讨,以寻求解决之道。作品分为四章,分别有三个人物—叙述者,依次为康普生家的三个孩子班吉、昆丁、杰生,以及从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迪尔西的视点出发、表现出迪尔西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叙述者。四个叙述者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视点。前三个叙述者都属于不可靠的叙述者,因为他们分别在智力、精神、道德、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与隐含作者不相一致。班吉的叙述,是在他三十三岁的生日那天进行的。他在叙述中常常回想起过去不同时期的事。但是,班吉几乎是一个白痴儿子。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智力却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他的叙述全凭一时的感觉和粗浅的印象,甚至分不清事件的先后顺序,恰如痴人说梦,读者不得不费力地加以揣测。昆丁的叙述发生在他决定自杀的那一天,这时他的精神已经处于半崩溃状态。由这样一个人物所讲述出来的见闻显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杰生则是一个偏执狂,他的自叙恰恰是他的邪恶与残忍的自白,一个满怀仇恨的虐待狂的自画像。一开头他就说出这样的话:
我总是说,天生是贱坯就永远都是贱坯。我也总是说,要是您操心的光是她逃学的问题,那您还算是有福气的呢。我说,她这会儿应该下楼到厨房里去,而不应该待在楼上的卧室里,往脸上乱抹胭脂,让六个黑鬼来伺候她吃早饭。这些黑鬼若不是肚子里早已塞满了面包与肉,连从椅子上挪一下屁股都懒得挪呢。(注: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无论从价值规范到语言表达上来看,前三个人物—叙述者都与隐含作者大相径庭。尽管他们所叙述的都是这个家庭的事情,但都是从他们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立场、从各自的智力、思想与道德规范角度出发的。这样,在最后一章,出现了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这个可靠的叙述者从黑人女仆迪尔西的视点、通过他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立场来进行叙述。福克纳自己曾说:“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注:转引自李文俊,“前言”,载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第7页。)从这样一个仁慈、宽厚、充满同情心的黑人女仆独特的意识形态视点出发,对她自己所经历和目睹的这个家庭作最后的叙述,显然具有独特的意义。由于她所具有的特定的意识形态视点,使她的叙述显得公正、客观,具有她自身的判断力,可以匡正前三个人物—叙述者的某些不可靠叙述,从而使读者能够对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一切做出整体把握,并且将前后不同的叙述加以对照,更好地了解每一个人物。
不可靠的叙述者有其自身的独特意义,他们可以起到一种可靠的叙述者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尽管他们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不相一致,但是,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与视点的不一致,使读者得以深思其产生的原因及裂缝所在,从而揭示出在这种矛盾之下的深层意义,有利于对作品思想意义的把握。一个作为人物的不可靠叙述者,往往可以成为有意义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就以《喧哗与骚动》中的三个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来说,他们作为作品人物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杰生是恶的代表,他的邪恶是公然的、毫不隐晦地表现出来的。对杰生的恶的揭露,也恰恰是通过他自己在他的叙述中所做的自我表白与自我辩解得以完成的,正是他自身的叙述造就了这个人物。班吉,这个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以其近乎白痴的愚蠢语言使他带上了十分明显的印记,但是也使这个人物具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品质。尽管他一点也不能理解发生在他周围的种种事件,但作为一个目击者,他却能将他所看到的某些事件十分准确地报道出来。因而,他成为一个极为单纯的人物,也是十分感人的人物。他是如此脆弱,几乎成为别人供奉的祭品,因而格外引起人们的同情。(注:参见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3页。)
由上述对视点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视点决非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它与更深层次的意义,即与意识形态层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视点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意义与价值判断在作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着作品的价值意义以及读者对它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由于叙述者的不同类型而变得错综复杂,对它的探讨不仅会变化人们对视点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密切关系的了解,同时也将深化对具体的叙事作品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