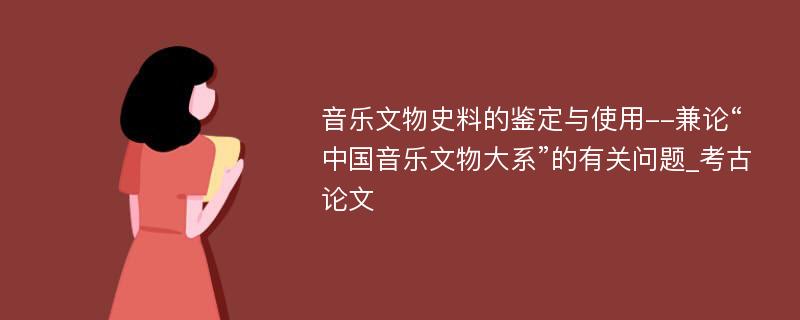
论音乐实物史料的甄别与使用——兼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系论文,史料论文,实物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文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10)03-0023-06
中国的音乐历史源远流长,在深厚的史学传统下,历代留传的文献典籍汗牛充栋。一直以来,音乐文献史料不仅是后代了解前代音乐状况的主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研究的首要材料。随着考古学传入中国,田野考古不断深入和拓展,大量文献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音乐实物史料惊世显现。在以文献为主的史学研究成果不断被新实物史料修正、补充、创写的情势之下,科学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逐步成为了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互证互补的两种重要的证据和材料之一,它与历史文献被史学家喻为历史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轨”。
对于历史文献史料中存在的主观因素和局限性,古人早有认识,对历史文献的鉴别和考订也由来已久,清代乾嘉时期已成大势。直至近代,系统的文献学学科逐步形成,并在历史研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的合理鉴别和使用渐而为学术界所关注,有学者前瞻性地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就必须借鉴中国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建立和健全独具特色的中国实物史料学。”[1]可见,实物史料的甄别和使用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课题。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纯一就曾指出了正确分析音乐考古材料的问题,并对出土乐器、图像和文字三类材料进行了扼要论述。[2]有鉴于此,笔者拟延续前人提出的研究思路,针对目前所见各类音乐实物史料的特殊性与局限性逐一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甄别、辨析的角度和方法,此外,还将结合当前学术界使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相关情况做进一步阐述。
一、音乐实物史料的类别及其特殊性
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音乐实物史料是古代人类音乐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对其进行眉目清晰地分门别类是我们深层了解研究对象的必经之途,也是深化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众所周知,任何分类都必须根据一定的目的拟定明确的分类标准。在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鉴于文物监督与保护的实际情况,文物被分列为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大系》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资料性重典,其分类当以为据。《大系》采用了二级分类:一级分类以“器类法”为据,分为乐器与图像两大类,类外文物就近归入其中一类,其中,乐器类以“材质法”作为二级分类标准,在此类别之下,再以“种类法”作为三级分类,图像类则视文物构成的实际情况适当划分次级分类。①这种多级别类别的划分主要缘于《大系》编纂的需要。由于本文将论及音乐实物史料的特征、局限及其使用情况,故拟依据其基本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差异进行细分,大致归列为如下几类:
(一)乐舞用器
主要指古人音乐文化活动遗留下来的乐舞器具实物或实体,其中包括乐器、律器、舞器等,八音之属皆为乐器,律管弦准均为律器,羽龠干戚当为舞器。除了这些实物本身之外,与之配套的附件或装置(如放置器具、演奏工具等)、乐舞实物制作用具、调试工具等也应包括在内。
(二)乐舞图像
指反映音乐及相关内容的图像,大致分平面、半立体和立体三种。平面音乐图像多为表现乐舞相关内容的绘画、壁画、岩画及各类器物绘饰等。半立体音乐图像则主要是表现古代音乐生活内容的浅浮雕等。立体音乐形象主要指乐舞俑像等。
(三)乐类文本
主要指记写有关音乐内容的文字资料,多见于甲骨文、钟磬铭辞、简帛文字等。所记录的不仅有叙事性的音乐文献、乐律乐调理论的相关论述,还有古代音乐思想观念等内容。此外,一些书刻于乐舞器具实物上的文字也被纳入研究视野。
(四)古代乐谱
指考古出土或传世的古代乐谱,它们是古代音乐的符号化、书面化记录。目前发现的古代乐谱凤毛麟角,最具代表性的可能要数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乐谱。
(五)音乐遗迹
即音乐文化遗迹,主要是古人礼乐文化活动和进行音乐事项的空间环境、场所、残迹、设施等,包括出土乐舞用器的墓葬环境、乐器陪葬坑、乐器制造遗址及古戏台等。
音乐既是一种时间艺术,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一方面,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年代,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可逆转、不可驻留;另一方面,音乐又会或多或少地以某种特有的方式隐匿于各种形式的物质载体与音乐文化遗存中,所有这些便成为了我们追寻过往音乐及其发展历史的主要依据。上述五类古代音乐物质遗存所提供的音乐信息形式多样,各有不同,它们可以互证、互正、互补,使史料信息更加立体、多棱,是我们探寻古代音乐蛛丝马迹的首要物质依据。
考古出土的乐舞器具实物一般可以直观地展现其质地材料、形制结构及装饰组合。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古代乐器由于其材质耐于保存,至今还存留有宝贵的古代音响,它们不但是唯一能够保存古代音响的史料,还是古代音乐的重要载体。正如黄翔鹏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
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的古代音乐,其本身早已不复存在了。也许,它以不可察觉的方式,融汇在我们民族音乐传统的中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把它们的原始形态一一指认出来。唯独有条件的,只是它们的音阶结构的规律可能保存在某些幸存的乐器实物之中,可供我们今天来进行研究。[3]
从乐器制作的角度来说,“烧结、镂刻、熔铸可看作古代的录音技术。”[4可见,考古出土的乐器实物当为古代“有声”音乐研究的核心材料。
就乐舞图像的表现形式而言,它仍隶属于美术作品范畴。作为一种较为直观的视觉审美艺术,它们一方面为相对静态化的乐舞器具实物提供了一定的演奏方法和表演场景,营造了相应的音乐文化氛围,使其呈现出“动态”、“立体”的画面;另一方面,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与乐舞器具的形制组合和乐队编制等内容相对证、互补。此外,一些乐舞图像还蕴涵着古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内容。与乐舞相关的文字资料是我们研究乐器称谓与功用、古代音乐理论、古代音乐思想等的重要史料。它们不仅可与其他音乐实物史料进行对照,还可与历史文献中的同类记载进行比勘校正,补“脱”删“衍”,纠“讹”正“倒”,理清“错乱”。古代乐谱作为音乐表演的文本,所包含的音乐本体信息将有助于我们对前三类研究的综合验证。音乐遗迹是我们研究古代礼乐文化的必备材料,有助于古代音乐文化的活态再现。出土乐器的墓葬或遗址的空间环境及音乐表演场所可以从某一侧面真实地折射出古代礼仪社会中的音乐生活,乐器制作的残迹则为我们进一步掌握乐器材质及其制作的技术流程提供了有力证据。
对于古代音乐,尽管我们不可去亲听、不能有实感,但潜藏有丰富音乐信息的各种音乐实物史料却为我们提供了追溯古代音乐的可能性。这正是音乐实物史料与一般实物史料的相异之处,即它不像一般考古实物史料能够“直接”呈现古代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社会文化状况,而是以一种“间接”、“含蓄”的方式来展现古代音乐文化的各方面内容。
二、音乐实物史料的局限性
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是古代人类社会生活中各项活动遗留下来的遗物,因而它们大多被认为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讲述”历史。然而,“并不是说文献资料描述的历史就容易出问题,引用出土资料就可以反映真确的历史了:出土资料并没有这种特权”[5],这类史料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它既不能完全等同于史实,也绝非“天生”客观。
一般说来,造成音乐实物史料局限性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音乐实物史料自身的局限性
如前文所述,任何音乐实物史料的历史信息都是有限的,也是不完善的,某些原始材料就可能与史实存在一定差距。
音乐实物史料大多出自于墓葬或窖藏,多为古人丧葬及各种仪式中的礼乐用器,尽管古人“事死如事生”,但当时还是存在“有意排除活文化的现象”[6],即随葬乐器并非当时使用乐器的全部,随葬乐器也不一定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匹配等。同时,还会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出现事死不同生的情况。例如,可能在受墓坑空间大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未按照日常生活或一定仪式中的规定摆列乐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群二号墓的王孙诰钟出土时大小相套横卧于墓中,不同于实际使用时悬挂于簨虡之上。在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中,“许多大件遗物由于自身形体过大,为节省空间以放置其他随葬品,在下葬时曾作过精心的计划和安排”[7],其编钟编磬的陈放就是如此,钟磬架被置于最下层,横梁被取下,除少量小件纽钟悬挂在拆下的钟架横梁上,其余大多数纽钟集中堆放在东室南部。此类现象并不鲜见。
乐舞图像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乐舞图像只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音乐实物史料的外部特征(如乐器外部形制等),其内部发声构造之共鸣腔体、音乐音响等则无法表现。另一方面,图像更多的是带给人们一种视觉审美,音乐场面只是其表现的内容和题材之一。音乐图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美术作品,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反映真实,即便是写实类作品,也未必会完全按照音乐器物的原始状态和情景来绘制。此外,音乐图像制作者的知识局限也会造成音乐图像与音乐史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现存音乐图像中,琴的头尾颠倒、琴瑟弦数和排箫管数不计等现象普遍存在。英国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大部分图像在被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被历史学家所使用。图像制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8]这就是“图像证史”的最大弊端。可见,我们在“不可尽信书”的同时,也不可尽信图。
(二)客观因素造成了音乐实物史料的局限性
1.年代久远导致音乐实物史料的残损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历史的不断磨砺中,古人的音乐遗存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例如,石磬经过数千年的地底珍藏,因腐蚀失去全貌,更不能敲击发音;琴、瑟、笙、排箫等以丝、木、匏为主要材料的乐器,出土时鲜见其完整形态,即使有,也是“残疾”之身,聆听其声,实为奢望;有些出土乐器存留的音响也会留下岁月的“痕迹”。
2.自然环境对音乐实物史料保存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地下材料的保存。众所周知,北方气候干燥,地下水较少,不适于保存漆木器;而南方气候湿润,地下水丰富,具有保存漆木器的良好环境。学术研究“说有容易说无难”,尤其是在判断某实物史料的出土与分布时,必须将其材质的耐存程度及其在地底保存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也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南方出土瑟的数量多而北方几乎未出,就武断得出瑟是古代南方特有乐器的结论。
(三)人为因素造成了音乐实物史料的局限性
1.古人对原始音乐实物的重组与改造
就拿古代青铜乐钟来说,由于其制作原料稀少昂贵,制造技术含量高,它们一旦被铸造成功后就不会被轻易废弃。不仅如此,青铜乐钟是器主贵族身份的标签式象征物,也是供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的传世宝器,更是古代礼乐社会中的国之重器。即使后人以各种方式获得了前人之钟,通常也不会弃之不用,而是进行合理的重组或重调,以满足不同时期的礼乐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先秦时期青铜编钟拼凑、增扩成套的现象屡见不鲜,多次锉磨调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西周时期的16件晋侯苏编钟就“并非同时设计,一次铸就,而是数百年间拼合发展而成。”[9]拼凑成编后的乐钟虽然已不再是最原始的编列状态,但古人对编钟的重组与改造也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音乐文化活动需求来进行的,改造之后的乐钟仍可作为又一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的真实反映。
2.提取史料信息的研究者及其方法和理念是决定音乐实物史料客观性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一大差别在于,它不可直接解读,而需要研究者运用各种方法从中获取历史信息来进行分析和解释。在此过程中,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治学观念、分析过程等都会影响到史料挖掘信息量的大小和阐释的有效性。
目前,音乐实物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主要由专业考古人员承担,由于他们专精于科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而对音乐理论知识和乐器构造知识较为匮乏,因此,曾出现过在发掘清理音乐实物时误失研究材料和历史信息的情况。通常,笙簧、瑟弦、琴弦这类微小却重要的乐器部件较容易被损坏和丢失。测音是提取古代乐器遗存音响的重要手段,测音结果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不仅有湿度、温度等环境因素,还有诸如测音方法、操作过程、操作者的素质等人为因素,有学者曾撰文就音乐考古测音中的主观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10]。
各类音乐实物史料所提供的信息不尽相同,未必能直接反映历史,因而需要经过研究者的分析与阐释。例如,就古代音乐文字类资料而言,由于先秦文字迥异多样,文字辨识是首当其冲的工作,其次需要对字面意义和内涵进行挖掘。曾侯乙钟磬铭辞的释读不仅是多学科专家共同协作的成果,还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但仍不乏未解之谜有待解译。古代乐谱无论在表述方式、记录手段上都大大不同于今,因此乐谱的解译便显得尤为艰难。古代音乐遗迹虽也不能直观地展示历史面貌,但它们却是古代音乐文化制度和音乐文化语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见,音乐实物史料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们因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或被无形地改变着初始面貌,或被丢失重要信息。除了自身的局限和难以避免的自然环境因素以外,它们从制造产生之初到发掘出土之日,再到科学研究之时,经过了多人之手,多重复杂的主客观因素都可能导致它们被不断“整容”。
三、音乐实物史料的甄别与使用
材料是研究立论的基础,随意使用未经鉴别的材料,可能导致研究成果成为“豆腐渣工程”。音乐实物史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拿来就用,我们理应带着一定的“疑古”精神去辨析和鉴别,用科学的方法拨开蒙附其外的层层面纱,对其提供的史料信息进行严谨的多重论证,之后还应深入挖掘,最大限度地获取可靠、有效的历史信息,为历史研究所用,从而更接近于历史之真。
一般来说,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史料分为实用器和明器,其中实用器又有成品和半成品。
明器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中,有关明器的系统阐释见于战国至汉代的相关文献中,但古人使用明器及其概念的传统却由来已久,并逐步演变。尽管明器均“貌而不用”,但它们的形式却各有不同。巫鸿将西周末期至战国中期所见明器统计为7种:(1)微型,形制同但体量小;(2)拟古,即非忠实模仿而是创造性发挥;(3)变形,即刻意简化或蜕变乃至整体改变;(4)粗制,形同但制作粗糙;(5)素面,即纹饰朴素甚至无纹;(6)仿铜,仿青铜礼乐器之形而采用陶、木或铅制作;(7)重套,即大墓中对应的礼器和明器。[11]明器作为礼仪之器被用于丧葬,象征其拥有者的身份和等级,它们有礼仪之“名”而无使用之“实”,即明器亦以“藏礼”,也仅“藏礼”,对于乐器明器来说则是其音乐功能丧失而仅存其礼仪功用了。实用器与明器大多较易区分。首先表现为它们的选材不同,制作精良程度不一。一般而言,乐器明器的制作较为粗糙,选材简易,例如有良好音乐性能的编钟采用青铜合金而制,而所见编钟明器则多为陶质或木质。其次,乐器明器的体量大多比同类实用器小,外形上不讲求与实用器完全一致,装饰纹样也常被略去。
实用器之成品与半成品之间,一般不存在制作材料上的差异,其主要不同在于制作的精良程度,以及主要制作程序是否完成,尤其是关系到其实用性或实用功能优劣的工序。还是以青铜乐钟为例,编钟实用器,除少数乐钟铸造出来就基本符合音列设计的要求外,大多都必须进行调音锉磨,而半成品则只铸造完成,进一步的精良和调试工作均未进行。但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是,有的古代编钟音律不调并非因为它们是半成品,而是由于铸调乐工不具备能够“齐其声”的高敏锐度的耳朵而导致音律乖张。如此复杂的情况,研究者不得不拭目以辨。
早前已有学者指出:“音乐考古的材料,包括各种各样的‘测音数据’,也应该象文献材料一样进行认真的、严密的、科学的整理考订”[12],我们不妨尝试借鉴文献学的相关方法和理念来对音乐实物史料作对应的分析讨论。
首先,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小型墓地的报告多以简报形式发表在考古类核心期刊上,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于资料繁多、情况复杂,则大多先以简讯或简报的形式向学术界通报,然后再做进一步系统整理并编写大型考古报告,短有历经几年之时,长则逾十年之久。按惯例,考古报告由发掘该墓地或遗址的考古发掘单位负责整理编写,一般没有多种版本,重印的情况也不多见。因此,实物史料不存在版本问题。需要提到的是,有同批史料先后发表简讯、简报和完整发掘报告的,常以发掘报告著作为准,但仍有必要查实相关简讯和简报。
其次,可从史源的角度对音乐实物史料的等次与级别做以下分析。
第一级:指第一手资料,科学考古发掘的材料属此级别,考古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就是第一手材料。偶然发现或被盗出土的实物史料,即非科学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它们大多失去了相应的地层时空关系,在经过专家的研究类比并确定其相对年代之后,也属于此级别。辑录的传世实物史料等也可视为第一手资料。
第二级:研究者因学术研究需要对第一手资料所作的分类整理和辑录,或根据上述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后撰写的论文、论著,均为第二级资料。
学术研究注重材料的客观性,讲求掌握第一手资料,这在音乐实物史料的使用上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第一级资料较为可靠,但也还需要核查、比勘和考证,前文对此已有所论述。第二级材料的价值也不可忽视,它们不仅是研究的重要参照,也是收集资料的“中介”,便于按图索骥,找到所需实物史料的“祖本”。
音乐实物史料同文献一样,也需要进行校勘。校勘音乐实物史料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是:通晓古代音乐历史和古代的基本音乐理论,具备与古代乐器相关的常识和考古学的基本知识,最好具有一定的考古实地调查经历。
陈垣总结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此法在音乐实物史料的甄别中也是可资借鉴的有效手段,现根据音乐实物史料作适当推演。对校,可将发表于不同时期或以不同形式发表的(如:简讯、简报、报告、论文、论著等)同一音乐实物史料进行对比研究,找出矛盾,辨析校订。本校,可对音乐实物史料的获取方法、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比照。他校是用出土的同时期同类音乐实物史料进行合理互校。理校,则需要运用所具备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分辨和校正。针对各类音乐实物史料的局限与弊端,四法的灵活运用应更为有效。
此外,对于考古界就音乐实物史料所阐发的结论,我们需要从音乐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以证明、修正、或补充其观点。就拿编钟的年代考证来说,考古界主要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来进行分析判断,而从音乐学角度为编钟断代的方法已日臻完善。黄翔鹏首开从音列设计发展的角度进行编钟断代之先河,为古代青铜编钟断代提供了新视角。王子初提出以编钟内部调音锉磨方式的变化来断代的方法,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些都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断代“反哺”的具体体现,也是音乐考古学的学科价值和特点之一。
还需提到的是,在对音乐实物史料的甄别和使用中,其客观程度、科学程度以及对史料的利用程度与研究者的知识水平、分析能力,以及对包括实物史料、文献史料等在内的史料综合驾驶能力及其研究的敏锐程度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同样的史料在不同研究者的手中常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体现完全不同的学术价值。
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合理使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迄今为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套专业音乐资料性典籍,也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部重典。
1977年四省音乐文物普查后,在曾侯乙墓乐器、舞阳贾湖骨笛等一系列重大音乐考古发现的推波助澜下,吕骥于1985年提出编辑《中国音乐文物图录集成》(多卷本)的倡议,得到了考古学家夏鼐以及有关单位和专家的赞同与支持。1988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定名并申报纳入了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指第Ⅰ期工程)。第Ⅰ期工程历时14年,1996年开始陆续出版,先后完成了湖北、北京、陕西、天津、江苏、上海、四川、河南、甘肃、新疆等12个省卷,共10册。1997年10月,《大系》第Ⅱ期工程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并于2006年12月出版了首卷本《湖南卷》,随后又出版了内蒙古、河北、江西等省卷,目前有福建、广东等省卷正在编辑校订中,同时还在对若干省进行音乐文物普查工作。
全面掌握分布于中国各地的音乐文物资料不仅是当时的一项迫切学术任务,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作为中国音乐文物资料的集成性典籍,《大系》的宗旨是对各省音乐文物进行全面普查和地毯式收集,正如《大系》第一任总主编黄翔鹏所指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性质是“集成”,而不是“精选”![13]因此,《大系》普查与资料搜集的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博物馆,下到县市文物管理所、文物保护站和文管会,对所藏与音乐相关所有遗物的各种信息进行全面搜集,包括文字资料、图片拍摄、音响采录和相关检测等。
音乐实物史料是古代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材料,看着其他音乐史料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散存于全国各地的丰富音乐文物并不为坐在电脑前的研究者所了解,《大系》的贡献即在于将这些史料予以系统化搜集整理,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展示它们的历史信息,这不仅使学界获得了对中国古代丰富的音乐物质遗存的总体认识和感观,同时也为研究者了解和查找实物史料提供了线索。
毋庸讳言,《大系》是一本可供学术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工具书,更是研究古代音乐、古代历史的必备工具书。遗憾的是,笔者注意到目前学界在使用《大系》时出现了一些误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有学者在使用《大系》收录的史料及相关历史信息时都未经查索和核实“史源”。以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王孙诰编钟的测音数据为例。这套编钟于1978年出土,其详细资料发表于1991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据考古报告介绍,这套编钟曾先后经过四次测音并均附录有测音报告②,第一次是1978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用自制测音器测定,第二次是1980年由哈尔滨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用电激励共振仪测定,第三次是1984年由河南省歌舞团用电子调音器测定,第四次是1988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响实验室用Stroboconn闪光频谱仪测定。[14]《大系》对其中的资料进行了转载。出于对测音数据科学性、可靠性的考虑,《大系》选载了来自哈尔滨科技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两家学术机构的数据资料,并在该条目下的“文献要目”中提供了资料出处,即原始考古报告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及年代等。此法对于一部资料性总集来说,应当无可厚非。遗憾的是,《大系》在转载这套编钟的测音数据时出现了4处错误。王孙诰钟因其外部特征不甚统一、出土时呈现的编列不明晰,而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音乐界所使用的测音数据多来自《大系》,如:有论文直接抄录了《大系》转载的测音数据[15],虽抄录无误,但重复了《大系》的错误。有论著中的“数据采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16],但在转载过程中再次出现错误。究其原因,或许是学界对《大系》性质及资料来源的不甚了解,也可能是在音乐实物史料甄别和使用上出现了误区。故以下有必要对《大系》资料的基本情况予以介绍和说明。
众所周知,《大系》工程巨大,而且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大多来自各省市基层,他们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搜集、分析、整理材料的水平和科学程度均各有不同,因此材料出现错漏难以避免,各卷本水平也参差不齐。笔者近年来也参与了《大系》的编纂和校订工作,深知其资料浩繁,工作量极大,虽然工作人员都秉承科学认真的态度,反复进行校对、核查,力争将错误率降到最低,但仍不乏缺憾之处。尽管如此,对于一部涉及地域广及全国、收录资料全面崭新、参与人员为数众多、历时将达几十年之久的宏大工程来说,偶有疏漏在所难免,略有错误也情有可原。然而,对于使用《大系》的研究者来说,对资料进行甄别和辨析不仅是研究成果科学性的首要保证,也是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环节。
据笔者了解,《大系》收录的音乐实物史料大致有两种情况:
1.已发表的音乐实物史料
(1)发表信息齐备的史料。对于已发表的,信息全面而完备的音乐实物史料,《大系》多采取转载的方式予以呈现,且均在“文献要目”中附有资料来源及主要参考文献。
(2)发表信息不全的史料。由于这些资料此前均由考古界发表,其音乐方面的信息恐提供不全,因此《大系》收录这部分材料时,补充了诸如测音数据等音乐方面的信息,此外,专设的“文献要目”一栏也提供了资料的文本来源。
2.未发表的音乐实物史料
这部分史料在《大系》中所占比例较大,它们中有发掘品,有征集品,还有回收品。这些资料在《大系》出版前均未发表,此前均隐匿于各文物收藏单位。它们首次展现于《大系》中,无疑都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这部分资料的收录正是《大系》资料全面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作为资料性总集的独特价值所在。
根据前文对音乐实物史料等次和级别的划分,《大系》中收录的未经发表的音乐实物史料当为第一手资料,可以直接采用。《大系》中收录的已发表的音乐实物史料则为第二手资料,在使用时应如引用文献一般,需追溯“史源”,即根据条目下的“文献要目”找到其“祖本”,以获得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大系》中收录的已发表资料的补充材料,也属于第一手信息,可以直接使用。
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和实物史料的日益丰富,音乐实物史料势必在音乐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众所周知,史料是研究之本,其科学性、客观性是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各类音乐实物史料的情况并不乐观,它们或多或少由于自身原因、客观环境及人为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理应与文献史料一样,需经过仔细的甄别、比勘、“正本清源”后为学术研究所用。
注释:
①参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卷“凡例”。——笔者注.
②附录五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测音报告,附录六为哈尔滨科技大学测音报告,附录七为河南省歌舞团测音报告,附录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测音报告。——笔者注.
标签:考古论文; 编钟论文;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乐器制作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