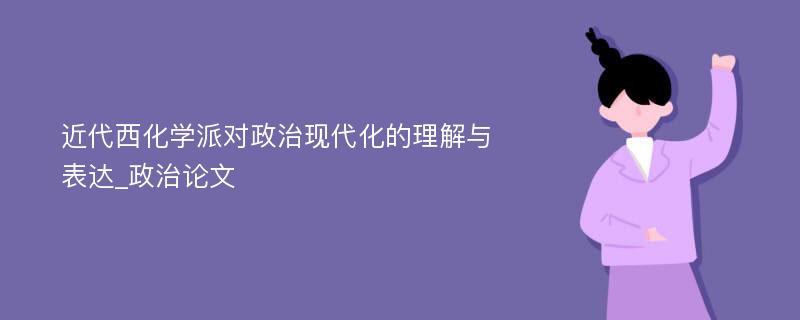
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及其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晚期论文,派对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洋务派是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数十年洋务活动的岁月中,他们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以促进,然而却在政治现代化上毫无建树。但是,如果我们不否认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洋务运动的终结,从甲午之后到清末新政启动客观上有一段洋务运动复兴,即晚期洋务运动的话,那么便不难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晚期洋务派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对那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需求是有认识的。尽管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认识公诸于世时既不如资产阶级改良派那么具体明确,更不如资产阶级革命派那样慷慨激越,但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却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即他们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和表达,既反映了洋务派思想命运的历史走向,更折射出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艰难。本文对此进行论述。
一
所谓政治现代化,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农耕社会向以机器力为主要动力的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时,社会政治制度等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有两条,即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打破既存政治体制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或主要利用既存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以完成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就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来说,当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将政治现代化的需求摆上中国现代化的议事日程后,那时对这一历史课题最深刻的体认者和倡行者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无论是从国情考虑还是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紧迫感出发,都将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放到尽快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上,并认定最快捷和可靠的施行方法,是通过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威利用传统官僚机构自身来完成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实现政治现代化,完成救亡图存的根本任务。应该说,这就是那时的时代认识水平,也是我们评判晚清洋务派有否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及这一认识达到何种水平的出发点。
从历史的时序看,晚期洋务派的形成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是共时的。而当维新派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愈来愈鲜明地表达了政治现代化的主张和要求时,其时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亦逐步有了认识。这一阶段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恰恰也最为集中地表现在被视为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集大成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当我们循上述基点予以分析时,这种思想便凸现出来。
就那时中国社会改造的理想目标君主立宪制而言,所谓政治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继军事、经济上的“师夷之长技”之后迈向更高层面的向西方学习。这就是说,作为形成政治现代化的认识第一步——认识与了解君主立宪制本身的优劣高下,或说了解君主立宪制的范畴,首先就与主体的西学观有关。纵观《劝学篇》对西学的涉及,可以看出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基本上是与时代水平同步的。在该书中,他将西学分为“西艺”和“西政”两大类,其纲目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所概括的内涵中,所谓学校,从他在书中仿行西方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设计看,不单单是单个的学校,而是以科举制的三级功名与西方三级教育制度的结合,即整个的教育制度。同样,度支、赋税、律例、武备、通商、劝工,指向的也是整个的财政、税收、法律、军事及工商制度。因此很显然,如果说“西艺”概括的是那时中国人所知的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话,那么“西政”则是西方的社会科学且指向是涉及各方面的国家制度,若非此,他也不会以“政”名之了。不唯如此,在“西艺”与“西政”的关系上,他一反早期洋务派谈“艺”不谈“政”的传统,称必须“政艺兼学”,而且进一步更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②]。之所以“西政为要”,从西学本身而言,是“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③],即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其经济的产物,为科学技术服务的,无此,现代科学技术将难以发挥最大功效。
当把目光聚焦在西学的制度层面并给予了如此的重视,在维新派开议院的政治改革声浪中,张在《劝学篇》中顺理成章地讨论了议院制问题。他的讨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议院制在西方政治运行中效用的分析,他说西方实行议院制后,“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议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④]。从书中看,这一讨论表面是为了证明西方亦有“君臣之伦”而说的,但显然表达的却是议院制这一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当此时,维新派要求开议院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中国政治的一大弊端是上下不通,君民相隔,而仿行议院制可以克服,如郑观应就明确说:“中国病根在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脉阂隔,寝成痿痹,势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开国会设议院不可。”[⑤]可见,张通过实际上的中西政治对比而阐述的西方议院在政治运行中使君与民“相去甚近”、“好恶易通”、“亲爱过之”等对议院制的赞许,并不逊于维新人士,价值倾向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这种议院制与中国的圣道的关系,如说“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国君可散议院之议”,在中国的《周礼》、《论语》等书中均有,也即议院制这种政治形式在中国古已有之,时下的议院制“皆圣经之奥义”[⑥]。应该说,张的这一论述无论是正统的“西学中源论”也好,还是托古改制的政治谋略也好,在打开政治变革从理论到实际的通道上效果是同一的。
那么,这种实际上包含了政治制度的“西政”之于那时中国改革的关系如何呢?无疑,在了解了“西政”在西方为优后,要回答在中国是否也为优,从广义的文化层面上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固有文化的认识评判,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而在根本上,决定于历史观水平,因为那时的改革无可否认地是要进行现代化,而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发展,一种对传统的变革。众所周知,在《劝学篇》中,张明确称:“天不变,道亦不变”,显示出停滞不前的历史观,但同时,他还展现出这样的认识,他说:“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又说:“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⑦]无需多言,这是十分明确的“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表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他具有一种矛盾的二元论色彩。既然圣人不能“尽泄”、“尽知”,而“西政”在实际上与中国的对比中又有如此的优越性,故他一反早期洋务派只承认技不如人的习惯,认定“政”亦有不如人之处。于是他说“西学”、“西政”之于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⑧]“西学”、“西政”取舍的限度,是:“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⑨]
显然至此,就“西政”尤其是内含于其中的议院能否在中国仿行,就取决于能否使中国富强和“无损于圣教”,所谓“圣教”,即封建的道德名教。如上所述,“西政”可有益于中国在他这里是肯定的,因而问题的关键是“圣教”的保护与维系。无庸讳言,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出发,张充满着极其强烈的卫道意识,他同样明确地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待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⑩]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纲常名教确是封建圣人头上的光环,是封建中国的显著特征。从政治层面看,这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正是封建政体得以存在的思想和道德基础。换言之,在总体上封建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的议院制是非此即彼的,要仿行议院制,必“损”圣教;要保圣教,必弃议院。张给自己摆出的是一个政治改革中难以解脱的二难困境。由于张公开表达的中体西用模式和强烈的卫道意识,论者一向因之论定张所要维护的是封建政体,并无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但必须注意的是,那时谋求变法的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将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相分离的思维模式与倾向,如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最为激烈的康、梁,就并未在政治文化方面对封建道德予以批判。须知,将变革的目标深入到文化心理和伦理的层面,这是此后二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因此,如我们不曾以此看待康、梁等人的政治现代化要求,那么也不应就此否定张之洞对议院制的肯定与赞赏。这样,当我们注意到张不无急迫地称:“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1]时,也就可以认为他不仅对西方的议院制有了解,而且不存在仿行的思想障碍即政治文化的抵捂。倘若他就此提出立即仿行,也并未超出其思想逻辑。
然而,最终在回答是否立即实行议院时,张却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他说:中国“此时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12]即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是未来之事。显然,这一答案与上述思想似不尽完全合拍。为了弄清这是某种考虑更深思想的表达,还是谈议院制仅仅是应时之作,如他所说的要折中新旧中的抚新,虚晃一枪最终不得不临阵而逃,有必要将考察越出对《劝学篇》思维逻辑的分析,从更广的层面进行审视。
政治制度的更替,归根到底要受社会经济、文化程度和社会意识的制约。就政治现代化之一的民主立宪政治而言,上述三个因素中民智、民力开发,即民众知识水平、现代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提高尤显重要。中国那时政治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由经济的发展而引发,而是由民族危机的压迫,在思想超前的导引下被推上改革议事日程的。这样,对施行政治现代化来说,如果经济基础已显得不足的话,那么,在民质民力上则欠缺更多。可以说,正是由于对这一民质民力状况的认识与重视不同,使得同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完成政治现代化的人们在何时实行上产生了分野,其中的一派人主张缓行议院而首先专注教育以提高民质。如严复,他在维新之际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认识的全面与深刻,对封建专制政治批判的辛辣与尖锐,在那时无有出其右者,但他最终还是将政治变革转换成教育变革,在教育思想领域里展开了革命[13];又如郑观应,他历来持有中国应尽快仿行议院的看法,但随着维新运动的展开目睹了变革的现状后,便在修订其《盛世危言》时,将原来的议院“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改为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14]。当然,从政治斗争的层面看,这种缓行议院而专注教育,无疑是一种临阵的退步抽身,但同时这种选择却展开了更为艰巨的人的文化心理的变革。历史证明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思想及实施同样有价值。
那么,张之洞的整个政治现代化思想是否从属于上述思潮呢?答案是肯定的。不难看出,张“今非其时”的整个表达,无论是最终目标的设定,还是施行方略和途径,与上述严、郑等人都是同一的。不唯如此,在该书中他还不无深刻地指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15]。所谓“习”,即民间习俗,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众文化心理的反映,民质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赖于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社会政治制度的真正变革和确立,又有赖于民众素质的提高。他将整个变革的基点和成败的关键放到了民质能否得到改造上。应该说,他如此重视民质,与他曾做过多年学官并久任封疆大吏对地方实况的了解不无关系。正是认识到改变这一民质状况的重要性与艰巨性,使他在作为改革实施纲领而非理论著作的《劝学篇》中,在认可并选定了议院制这一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后,设计了相应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意识等的以“学”为手段,以提高民质为目标的过渡性变革方案。一个“劝学”揭示了希望之所在。所以,他的“今非其时”,缓行议院,本质上是一个更为深远的变革方案的必然表达。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那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特别是“百日维新”的开始,表明政治改革者们所认定并实施的变革路径,是依靠皇帝的权威和既存官僚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而皇帝的权威和官僚们的“官质”更显重要。然而恰恰在此情况下是不容乐观的。于是随着“废八股”等改革的展开,特别是詹事府、通政使司等裁汰,观念的冲突挟带着利益的维护,使得守旧者被彻底激怒,新旧斗争趋向白热化,甚而康有为等人也有了缓行议院的意向。议院制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这样,如果说张政治现代化思想由于本身的特性,在将目标高悬一格后就转向了他方面的设计,从而缺乏对议院制明确、系统和集中论述的话,那么,在新旧斗争达到高峰之际推出的以调和新旧为己任的《劝学篇》,使在政治现代化的表述上又多了不少人为躲闪的色彩,使整个思想零散和难以索解。这也正是人们长期以来忽略其政治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维新变法之际,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亦形成了政治现代化思想。这一思想与康梁等人相较,相同之处在于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不同之处则是康梁等希望立行,毕其功于一役;而张则寄希望于教育的普及与民质的提高,将政治现代化放到了不定的将来去完成,从而不乏深刻的同时与急切的历史需求产生了距离。
二
时至1901年清末“新政”行将启动之际,晚期洋务派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又有所长进。如果说此前他们对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虽有认识但却要缓行的话,那么这时则希望通过某种变通方式立行了。而且还相应扩张着与议院互为表面的诸如民权等认识。
他们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导源于那时政治进程的演进。1901年1月29日,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冲击和八国联军入侵重创,且仍未从内扰外患所激成的统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清政府,发布改革上谕,宣布实行变法,并要求内外臣工“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各抒己见[16]。无疑,这是清中枢认识到了非在一定程度进行改革不足以化解统治危机。而且,将以往不能触及的朝章、国政等也列入了“当因当革”之列,还要“参酌中西要政”来变革,似乎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更新了。这种态势和氛围的出现,对在政治现代化上有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深化并陈述自己识见的不曾有过的良机。
还在1900年之际,中国政坛上以“东南互保”的筹施为标志,崛起了一个以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实际上是包括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内的整个南方督抚集团。当此时,这一集团不仅宏观上为清王朝保有了大半个国土的基本安定,在经济上支撑着整个“西幸”的朝廷,而且还在诸如惩凶、回鸾等事上频频向朝廷施加压力。正是看重这一特殊的政治资源,“新政”上谕一下达,刘即电告张及集团的主要人物袁世凯、盛宣怀等人说:“变法须有次第,是一成不易办法,由浅入深,方可推行尽利。香帅胸罗全局,能先拟大纲,俾各省行效,建议相同,庶易采择。”[17]即主张由对改革有识见的张之洞设计,各省督抚统一口径上奏,以促进最高当政者按督抚们认可的方向变革。应该说,督抚们这时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但希望清廷行“新政”以对内政做一定的变革则是他们共同的愿望,故刘的建议很快得到响应,如袁世凯称“不厌雷同”,盛宣怀更发挥说:“臆见直以为能合五、六公折,方足以破主司之惑。”[18]在此基础上,刘进一步提出了南方督抚联衔上奏的方案并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督抚们为此开始了往返电商。
庚子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说与封建政治运行中的上下不通和缺乏一定的制衡机制有关,这就不能不促使谋求变革的人们将目光集中到政治体制的变革上。在督抚们往返协商中,已有政治现代化认识的张之洞首先涉及了这一问题,并力图将政治体制的改革向现代化方向导引,提出了非常大胆的思想。他说:“其实变法有一要紧事,实为诸法之根本,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如何仿行?他还具体拟定了督抚由司道府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依此类推,最后县由“通省绅民公举”,朝廷中外部院堂官也依这种层层推举产生的方法[19]。很显然,这表明经历了庚子年间的社会大动荡后,张之洞也将政治现代化看作了改革中“要紧”的“根本”之事,更加突出了政治现代化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将此直接作为了整个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而且鉴于局势的紧迫,已不待民质的提高,而是要通过变通——先设上议院并公举官吏,将政治现代化由两年多前的缓行纳入实际操作了。
张之洞此议一出,马上得到了刘坤一的认可与称赞。他说:“议院意美法良”,张的设计“极为精当”[20]。刘的这种表态并非官样文章,实际上刘对政治现代化在维新之际亦有所认识,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即众所周知的他被光绪皇帝斥责之后,他通过具体行动反映了这种认识[21]。因而同样是经历了庚子之乱的强烈刺激后,他的认识也在发展。而且,他不仅认可议院制,还加深着对民权的认识,如他在论为学之序时说,在获取知识上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必须有“西政丛书、经世文续编、三编、新编等书,阅之可知欧洲学术政治及中西交涉本末。《泰西新史览要》,记泰西百年变法兴利尚民权等事,阅之可扩识见”[22]。这样,如果说张的“公举”是对自己《劝学篇》中“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内在的否定的话,那么,刘对“民权”明确的推崇,则与之共同加深了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
那么,张、刘两位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在往返电商中和师友信札中所表现出来的已进一步提高的政治现代化认识和要求,是否见诸奏章而公开表达于世呢?显然,有必要对他们最终完成的以应“新政”要求而撰的“江楚三奏”进行考察。
“江楚三奏”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拟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联的奏章组成。它是由张之洞主稿、但却经两人字斟句酌的讨论后,由刘坤一领衔上达朝廷的。纵而观之,通过人才培养、整顿中法和整顿西法方面所设定的破与立的变革,实质上涉及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新式文化教育和确立新的社会风尚等[23]。这也就决定了刘、张对在本质与这些变革紧密相连且已被视为整个改革“根本”之事的政治现代化不能不在其中有所反映。这方面至为明显的是他们说:“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日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途径,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新;度我筋力,以为径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24]这即是说,西方的政体学术是经过数百年研究和施行,在强国强民上成效显著的东西,是可以“转相仿效”的人类精神文化财富,它正可以“相我病证”,是治我顽症的极便利的“药剂”,是走内政改革坦途的“途径”。言下之意,就是那时中国非实行西方的“政体”——议院制不可了。无疑,这正是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政治现代化的表达。从是否施行的角度看,显然较之以往的“今非其时”前进了一步。
但亦不可不注意到,他们的上述表达不仅较为隐含,而且是一种泛论,即没有从笼统的西方“政体”深入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制,以及民权等问题,更没有展现在谋划过程中所主张的那种结合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国情所作的变通。这样,就一个设计整个社会变革方案及步骤的奏章而论,尽管以特定的方式表达了中国要富强非仿行西方政体不可的主张,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如何施行的具体构想,从而这些建议只不过是给最高当政者一个认识上的参考和向导,政治现代化并不是要立即施行。这样,他们最终的指向仍然首先是社会环境和人的文化心理的改造,所谓“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然后同时并举的是中法的整顿和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乃至法律制度的采纳等,从而无可否认的又回到了施行议院制“今非其时”的基点上。
刘、张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与公开表达何以存在如此的距离?实际上,从认识到公开表达即向当政者建言,即对认识是否反映、怎样反映,是一个交织着多种因素与矛盾的复杂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较之认识政治现代化的必须更为困难。当我们把刘、张谋划“江楚三奏”的过程置于那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进程中考察,便可发现刘、张上述状况的出现,主要在于:
其一,从自己对社会状况的体认出发,刘、张希望以一种平稳的方式完成这一次“参酌中西”的内政变革。
如前所论,对那时欲进行的依靠现存官僚机构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现代化而言,民质的高低和能否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资源,破除来自体制内阻格,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维新变法业已从某种角度表明,那时无论是民质还是官僚体制,以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绳之,其景况是不容乐观的。而作为任封疆大吏数十年、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刘、张二人,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即对朝廷内部和地方实况,有相当的认识与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艰巨性的认识远远超过维新之际的康、梁等人。因而张才会有“今非其时”之论,而刘则是在认定维新的步伐过于急促后,一方面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按兵不动,另一方面“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勿涉急遽。”[25]
这种思想认识,基本上框定了他们可能选取的变革路径。尽管在急迫的民族危机下,张似想在政治现代化上向前走一步,但刘却坚决不同意。刘虽然认定“议院意美法良”,对张的设计“曷胜钦佩”,但又怕这一在当时是“骇人”的行动在实际中“多阻格,未能照行”[26],反而因过激过快招致反对,影响了刚刚起步的“新政”。刘认定变法“必须从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坚定不摇,乃有实济”[27]。从而主张政治现代化即议院之事不必直言。正是有上述的思想基础,张很快同意了刘的看法。此后,两人即是以这一思路撰稿的,从而有了上述的表达方式。他们称作是“布告天下,不至于骇俗”[28]。
其二,刘、张对最高当权者在政治现代化上态度的了解,制约着他们在奏稿中对政治现代化要求的表达。
对规模较大的政府主导型的变革来说,最高当政者的态度与意志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政治现代化而言,倘若最高当政者意识到必须并着意于此的话,他往往可以发现并依托可用的政治资源,针对现实采取通过某种变通的政治制度,然后以法令的形式推行,同时辅以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和提高民质与改造民俗的措施,推进整个现代化进程。从世界现代化的实际看,这种例子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并不鲜见。
那么,那时清王朝的最高当政者对政治现代化之于中国的认识如何?刘、张对此又有多少了解?纵观整个清末“新政”,历史证明清最高当政者在政治现代化上始终无真心,更无诚意。如果说1905年之后在社会压力下清政府还搞了一场君主立宪的真戏假演的话,那么应该说在1901年之际,清最高当权者与政治现代化是水火不容的。从这时刘坤一对最高当政者的概括“内间之意,过新之事不行”[29]来看,刘、张对之在政治现代化上的态度是了解的。因为经历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对清政府也不是新事,所谓“过新”,显然就是还“骇人”、“骇俗”的政治现代化。由此他们认定,若提“过新”之事,最高当权者“必以为骇人听闻,置之不理”[30]。反而影响整个改革进程。可以说由于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表达。
其三,刘、张欲借用督抚联合体向最高当政者在变革方向上施加压力计划的流产,也制约着他们在奏章中对政治现代化要求的表达。
在政治变革进程中,当统治阶级内部意见相左时,往往会出现一方或一派凭借一定的方式如政治、经济实力压迫另一方甚而最高当权者,以选取自己认可的变革方向的情况。或许正是认识到实行政治现代化民质的不足,走政府主导型的变革最高当权者又无意于此,刘、张实际上从清廷征询变革意见时一开始,就试图借用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如前面所述,经过刘的发动谋划,至1901年2、3月间,一个由南方督抚上奏言“新政”压迫清中央政府按地方之意行新政的计划开始实施。
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看,应该说若这一督抚群体言变革的奏章形成,对促进最高当政者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乃至对政治现代化的宏观进程是不无益处的。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倘若上述计划实现并促使清政府如此变革,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即限制最高当政者,而且会造成某种行“新政”上地方言中央行、地方成为重心,进一步加剧已经出现的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况且,又会对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一场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运动而必须保持和加强的中央政治权威产生侵蚀,这当然为一直汲汲恢复皇权绝对权威的清廷所不愿。这样,到了4月下旬,鉴于已超过规定的“限两个月奏到”的期限而“各疆吏使臣多未奏到”的情况,实际上也即得知了南方督抚群体将联衔上奏后,清廷采取了行动。先是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罔、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张二人虽然得到了“遥为参预”,名列参政的荣耀[31],但清廷却由此握定了“新政”的大权。接着,令“某老嘱达”督抚们在陕西的“耳线”,要督抚们“各举所知,勿联衔上”[32],力图消除南方督抚们自“东南互保”形成的以东南为重心的督抚们联手对付朝廷的状况。
善于见风转舵的袁世凯见此首先变计,很快单独上奏。盛宣怀见状也称:“慰帅来电,以两帅现列参政,与他省分际不同,拟改为分奏,如分奏而大意相同亦妙”[33]。如此,以刘、张为核心而联南方督抚会衔言“新政”的计划宣告流产,“东南互保”以来客观存在的东南政治中心走向解体。此后,虽然由于刘的坚持,刘、张仍然会衔上奏,从而形成了“江楚三奏”,但老于官场的刘、张二人在失却了督抚群体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后,很难在奏章中直述“骇人”的且被认定最高当政者不会同意的政治现代化建议了。
可见,1901年之际,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在不同程度上都深化了自己的政治现代化认识,从即将开始的一场清政府不得不进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作为那时权要人物的刘、张有此认识,无疑较一般资产阶级人士通过舆论影响传统政治结构更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然,这一可能性的前提首先在于必须将所识明确地公开地表达。但令人遗憾却又必然的是,由于诸种矛盾的交织,这一前提始终未能出现。众所周知,“江楚三奏”是整个清末“新政”的理论基础,其实之所以能成为理论基础,主要在于所设计的具体变革适合最高当政者的需求。倘若刘、张在政治现代化上直抒其意,等待“江楚三奏”的必定是另一种历史命运了。
至此,可以对文章所提出要考察的两个问题做出如下的概括:
所谓晚期洋务派,是甲午战后统治阶级由内部推行洋务复兴,即在实际中仍然变器不变道的政治派别。但晚期洋务派在筹施洋务复兴的同时,却形成了并步步深化着政治现代化的认识。这一状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经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通过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行特别是百日维新中注入生命与热血的阐扬,终于伴随着庚子年间民族危机对中国人的重创而推展到了统治阶级内部以至其权要人物。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进程看,由于其特定的政治现代化思想的表达方式,使其认识并未对中国早期的政治现代化予以促进。而从洋务派自身的历史发展看,如果说1902年总理衙门的取消标志着洋务运动结束的话,那么在此前,随着晚期洋务派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与深化,洋务派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历史命运已经完结。
通过晚期洋务派政治现代化认识与表达之间的距离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艰难之处在于,当愈来愈重的民族危机将政治现代化推上历史舞台之际,中国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民质,甚而是“官质”,最高当权者对这一历史需求更无认识。某些封疆大吏在此的认识虽然高于清中枢,但在封建中央政治权威总体上仍然十分强大的态势下,这些地方督抚不得不试图借用一种非常态下的政治构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压迫清廷接受自己的建议,从而使政治现代化的要求与封建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掺杂在一起,这种建言方式首先就为清廷所不容,使这种可能出现的明确的政治现代化的表达胎死腹中,失却了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对政治现代化的促进。这样,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政府主导型的以自身为变革对象的政治变革不能成为现实,当经济、文化等等步步迈向现代化之时,政治现代化始终处于停滞之中。
注释:
① ③ [11]《劝学篇·设学》。
② [15]《劝学篇·序》。
④ ⑩《劝学篇·明纲》。
⑤ [14]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322页、316页。
⑥ ⑦ ⑨《劝学篇·会通》。
⑧《劝学篇·循序》。
[12]《劝学篇·正权》附言。
[13]参阅拙著:《严复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
[16] [23] [24] [28] [31]《光绪朝东华录》总4602页,参阅总4722—4771页,总4753~4754页,总4767页,总4655页。
[17] [20] [26] [33]《愚斋存稿》卷50,电报27,页23;卷50,电报31,页10,卷54,电报31,页10;卷54,电报31,页25。
[18]盛宣怀:《庚子亲笔函稿》。
[19] [27] [32]《张文寰公全集》,卷171,电牍50,页38;卷171,电牍50,页30;卷172,电牍51,页11。
[21]刘坤一在“百日维新”后一段是积极的,甚而是遵令进行地方官制改革的极少数人之一。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清末近代化中的地方督抚》中有专章研究。
[22] [25]《刘坤一遗集》(五)第2294页,2233页。
[29] [30]《刘坤一遗集》(六)第2625页,26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