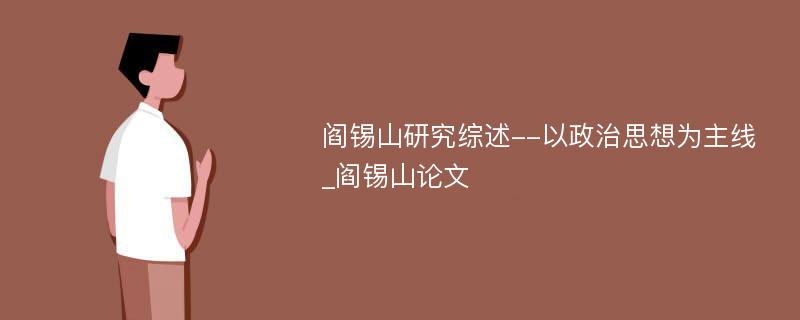
阎锡山研究综述——以政治思想为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主线论文,政治思想论文,阎锡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初期,全国百废待兴。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更是造成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惟独山西与其他省不同,军阀混战不仅没有造成多大的侵扰,地方经济反而有所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也有了某种程度的提高。分析其细节,无不与阎锡山的治理措施息息相关。因此,阎锡山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军阀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目前海内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和成果都为数不少。其中,对阎锡山本人成长过程、政治生涯以及晚年生活感兴趣的颇多。概而言之,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综述性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王树森的《阎锡山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蒋顺兴、李良玉的《山西王阎锡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等。这些研究主要讲述了阎锡山一生的历史。它们一般都是以叙事为主,稍加一些评论。
二是断代性的。即截取阎锡山政治生涯中的一段时间进行研究,具有时代的特点。如台湾研究者曾华璧的《民初时期的阎锡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2年),就把时间限定在1912年~1927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军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大三角中的阎锡山》(济南出版社:1991年)等,则是详细阐述了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李茂盛的《阎锡山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主要讲述了阎锡山晚年在台湾生活与工作的一些具体情况;董江爱的《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又是把侧重点放在了1917年~1927年阎锡山在山西的政治管理与军阀统治。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时间段比较短,应用史料比较多,对阎锡山的政治举措或军事行动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述。
三是专题性的。这方面的研究著作颇多。它们主要是从阎锡山的言论、思想、经营诀窍以及治晋方略等角度编写或著述的。如《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1937年)、《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1939年),就是以阎锡山的思想言论为主线、稍加或不加评论编纂而成的;《阎锡山的经济谋略与诀窍》(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与《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把侧重点放在了阎锡山的理财能力上;《治晋政务全书初编》(山西村政处:1928年)与《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则主要叙述的是阎锡山治理山西的措施与成果。
就具体内容而言,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类问题:
其一,对阎锡山的基本评价。解放前,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以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仍把阎锡山作为反面人物,在研究过程中以批判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研究者虽然还侧重于对阎锡山的批判,不过,也开始有了一些比较客观的具体分析。如蒋顺兴、李良玉在《山西王阎锡山》一书中就指出,阎锡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做过一些好事,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辛亥革命做出过历史贡献;民国初力主抵抗沙俄侵略外蒙;华北事变后主张守土抗战和联共救亡;为发展山西经济做了不少事”;另一方面,他在民国史上也干了不少坏事,概括为三点:“反对共产党直到老死;抗战期间进行降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参与发动新的内战。”(注:蒋顺兴、李良玉:《山西王阎锡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和态度也逐渐趋于客观。在这种背景下,阎锡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评价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杨树标、宋振春的《阎锡山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对阎锡山的政治思想和所作所为就有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阎锡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军阀。”(注:杨树标、宁振春:《阎锡山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而台湾研究者对阎锡山的评价则无限拔高,如台湾研究者吴文蔚认为阎锡山是“近代的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及哲学家,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完人。”(注:《阎锡山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以阎锡山是否可以称为“伟人”,我们权且可以不做评说;但称他为“完人”,显然是言过其辞。这样鼓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是正确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
总之,对阎锡山的评价存在很大的歧异,由于时间不同、角度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研究者各有侧重,评论者各有定论,目前还难以达成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客观而公正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因此,还阎锡山以本来面目,将成为研究阎锡山本人的重点。
其二,有关阎锡山政治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多数研究者们认为,阎锡山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其成长经历对他的个性与价值观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家庭环境、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的经历使阎锡山一步步走向成熟,逐渐有了追求的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研究者普遍认为,阎锡山幼年丧母对他的个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王树森即指出,阎锡山从小顽皮淘气,母亲的死和外祖母家的溺爱,“更使他养成了一种喜怒无常的性格”(注:王树森:《阎锡山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另外,多数学者认为,阎锡山的思想形成与他少年受到的儒学教育和武备学堂上学的经历有关。如有人指出:阎锡山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封建儒学典籍的熏陶,特别是“封建后期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浓重的朱陆之学”,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武备学堂的学习则坚定了其“军事救国”的信念(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研究者们大都认为,阎锡山的留日生涯是其思想成形的关键,也为其治晋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如王树森在描述阎锡山登上赴日轮船,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情形时,说:“他那颗在山区呆惯了的压抑的局促的心豁然开朗了。”(注:王树森:《阎锡山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这就似乎预示着,留日期间将是阎锡山一生事业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对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的评价,研究者基本持肯定态度。如李茂盛就认为,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纵观山西辛亥革命的部署、发动、起义及最后成功,都与阎本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在山西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注:李茂盛:《阎锡山在山西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其三,对阎锡山政治思想实践的研究。1917年,阎锡山赶走了山西原任省长孙发绪,自己独揽军政大权。为了在军阀混战中取得主动,阎锡山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帜,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积聚实力。其中,阎锡山提出的“用民政治”是山西建设事业的思想总根源。为了落实“用民政治”,阎锡山还推行了“村本政治”。对阎锡山的“用民政治”与“村本政治”,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如蒋顺兴、李良玉认为,阎锡山的“用民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山西的社会经济,“适当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是有利的”(注:蒋顺兴、李良玉:《山西王阎锡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而另有学者则从阎锡山长期控制山西的角度,分析了他的这一政治措施,认为阎锡山的“用民”是为了“安民”,而“安民”的用意是利用人民求安的心理,以便驱使人民为他创造割据山西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所以“安民”只是“用民”的“代用语”(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因此,“用民政治”实质上就是“利用当时人民渴望安定富裕生活的心理,驱使人民去为他割据山西所需要的军国主义政治效力”(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于是,1922年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的“村本政治”,就成为玩弄权术的“新花招”(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有关阎锡山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实用”的核心。有研究者认为,阎锡山“总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试图来为自己的观点找到落脚点”(注:王树森:《阎锡山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也有研究者指出,阎锡山认为一切事情都不能作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又要准备剿共”,这些都被称为是阎锡山的处世反动哲学,也是阎锡山“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则(注:赵瑞:《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山西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还有研究者认为,阎锡山曾经致力于“经世致用”的经学,成为“实用主义”的实施者(注:杨树标、宁振春:《阎锡山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更有研究者指明,阎锡山的真理标准就是对自己有利,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标准(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阎锡山的一生由于用“中”的哲学指导实践活动,“得到了比其他军阀存在较长时间的实际效果。……阎锡山‘中’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是把真理和效用混为一谈,认为对我有用就是真理,他们否认客观规律,尤其否认社会发展规律。”阎锡山的“中”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存与自固”问题的(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其四,关于晚年阎锡山的研究。大陆有研究者认为,阎锡山在台10年,仍然被“反共”事业充塞得满满的。他处处事事都没有离开“反共”两个字。这说明阎锡山在大陆失败后,“对共产党的仇恨更加深了”(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而且,阎锡山提倡的“大同主义”只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杂烩,具有十分反动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扼制共产党的发展,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完全是反动的”(注: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484、488页。)。王树森也提出,阎锡山的晚年始终眷恋着他永远失去了的政治权势,顽固地坚持着复辟的幻想(注:王树森:《阎锡山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页。)。台湾研究者则对阎锡山晚年持歌颂态度,认为:“民国三十八年,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主持政府,……,其爱国精神,受到全民钦佩。”(注: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2年版,第2页。)研究者李茂盛则是在《阎锡山晚年》一书中,对阎锡山晚年的著述给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些著述中固然有许多反共的内容,应予以批判,但也有不少可供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研究之处,比如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分析是有见识的;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系统的;对社会教育的设计是翔尽的;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独到的,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决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它束之高阁,置之不顾,而只能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批判地去研究、鉴别。”(注:李茂盛:《阎锡山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2页。)
从现有的对阎锡山的研究来看,尽管著作和论文都有一定数量,不过,其共同的薄弱之处是重史料而少评价,重批判而少肯定,因而实事求是的学术性分析比较欠缺,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明显不足。如若具体言之,我以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就内容而言,研究者常常以史料铺陈,叙述阎锡山的活动或事迹,一般主要表现为叙事的研究方式,几乎没有人对他的政治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的《阎锡山评传》、王树森的《阎锡山这个人》、蒋顺兴与李良玉的《山西王阎锡山》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在有些论著中,偶尔也有涉及到阎锡山政治思想的描述,但研究者显然只是点到而已,并没有梳理出阎锡山政治思想的主线,既缺乏系统性,也难抓住重点,显得有些零乱而浅显。
其次,对阎锡山的“村治”思想与政策研究偏少,实施过程、效果和经验研究更少。有关阎锡山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提到阎锡山的村治思想,但就村治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效果等问题,则语焉不详,令读者有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有些著作在对村治的评价上,将其定性为“实现军阀统治的手段”,这种认识的对错姑且不论,仅就这种认识方式而言,显然就是“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至于阎锡山村治思想的历史定位或实际价值等等似乎成为研究禁区,令后学者望而生畏,裹足不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村民自治普遍实施的情况下,沉寂多年的山西村治研究变得活跃起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了村治的现实价值。如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就认为阎锡山的村治“开创了民国村治的历史”,并且“因受‘五四’以后民主思潮的影响而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特征,以及他所开创的乡村财务公开与村务监察制度,在当今都对我们有启迪意义”(注: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给山西村治以很高的评价。而董江爱的《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一书,用23万字对1917年~1927年的山西村治进行了剖析,是目前对山西村治研究最详细的一本专著。不过,这两本书还没有突破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研究模式(注: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很难从山西村治引发对21世纪中国农村建设的具体思考。
再次,就方法论而言,前贤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基本局限于历史学,研究者多以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作为主要的方法论,而缺少新的视角,这样就使得有关阎锡山研究的学理深度受到了某种限制。例如,北京大学硕士生孟令梅的毕业论文《民国时期山西村本政治述评》(2000年5月完成,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描述了山西村治的一些情况。
鉴于以上研究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选择新的视角将研究推进一步。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阎锡山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可归一点,即“实用政治理念”,村治则是阎锡山实用政治理念的典型表现。
阎锡山不仅是个政治实践者,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在研究阎锡山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如果能找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就可以突出重点并避免认识的散乱或无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实用政治理念”始终是阎锡山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一理念凝练在他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即“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注:《阎锡山日记》,1942年7月23日,手抄本,年代不详,现藏山西省档案馆。)。
为了深入研究阎锡山的政治思想,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村治——作为典型,以充分展示阎锡山的实用政治理念。这是因为,阎锡山的实用政治理念在“村本政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以村为基、以治为本是阎锡山治理山西省的重要环节,也是他能够统治山西长达38年的根基。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最大成就在于,他着眼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在以民为根本的传统思想体系中演化出“用民政治”,在基础稳定的乡村实行“村本政治”。在“保境安民”的前提下,阎锡山建立并推行“极密之行政网”,以为“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达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注:《山西村政汇编》序言,山西村政处编印,1928年,第1页。)。基于这种理念,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村——闾——邻——农户四级村组织管理体系。村治的推行,使山西建立了上下贯通而应用自如的行政网络,为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而且,村治在现实中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仅得到了当时人的好评,也被以后的人所肯定。
其次,对阎锡山村治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阎锡山的实用政治理念提供切实的个案依据,而且,能够为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
美国学者冈内尔(Gunnell J.C)曾说:“历史的态度倾向把过去作为有内在研究价值的客体看待,而现实的态度则从过去与当前的关系中研究过去。”(注:[美]约翰·G·冈内尔著、王小山译:《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所以,深刻的研究必然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换言之,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以古鉴今”,通过研究历史以获得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以村为本的治理规范并不是阎锡山首创,不过,阎锡山在山西普遍推行了村治并取得成功,这在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史上无疑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通过研究我们看到,阎锡山实行的山西村治在制度设置方面是颇有章法,相当细密的,而且他具有明显的重视村级选举的意识。虽说村级选举在阎锡山看来只是维系山西统治的某种手段,不过,这也恰恰表明,阎锡山作为一代军阀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政治的重要性,在统治思想方面不仅深邃,而且是颇为复杂的。从历史借鉴的角度看,阎锡山村治思想、制度设施以及有关的政治意识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不无参照意义。
再次,在延续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采用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以扩展研究的视角。
一般而言,历史学方法指的是通过史料收集和分析,形成研究的结论。以往有关阎锡山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大体属于这一类。研究历史人物,历史学的方法论仍然是采用的主要方法。此外,也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不过,为了开拓视角和推陈出新,也有必要选用政治学的方法论,如政治思想、现代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社会化的方法论,从思想观念、政治理念和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分析阎锡山的思想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