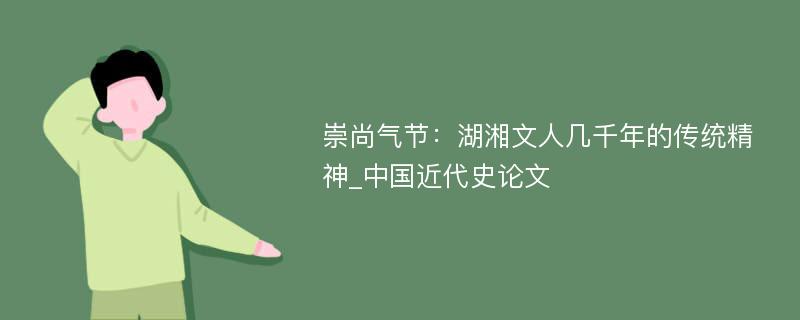
崇尚气节——近千年来湖湘学人的传统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节论文,学人论文,近千论文,年来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建湖湘文化的湖湘学派和由湖湘文化孕育的一代代湖湘学人,大都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于学、于政、于人品均卓有建树,令人瞩目。因此,近千年来,湖湘学人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影响深远。本文仅就湖湘学人“崇尚气节”传统精神作一番探讨,使之能永远沾溉湖湘学林,启迪湖湘后人。
一、近千年来湖湘学人留下来的有关“崇尚气节”的传统精神遗产,内涵十分丰富,而且明显地显示出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
“崇尚气节”,“砥砺情操”,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个人修身和人格精神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精华。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千劫不灭、万难不屈、危而复安、弱而复强、衰而复起、仆而复振、生生不息、永不沉沦,至今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铮铮铁骨者将正义、真理、气节和浩然正气世世相承,代代相传,维系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崇尚气节”、“砥砺情操”的优良传统,不仅培育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作为区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极大地影响着湖湘学人。湖湘学人对“崇尚气节”、“砥砺情操”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出了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展示了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湖湘儿女重气节、不屈邪恶的传统美德。
近千年湖湘文化史告诉我们:两宋之际湖湘学派气节明著;明清之际湖湘学者代表人物民族意识十分强烈;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的代表,在致力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过程中,表现出“崇尚气节”、“砥砺情操”的可贵品质。下面,拟就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湖湘代表人物在“崇尚气节”方面留下的传统精神遗产进行阐释和论述。
1、两宋之际的湖湘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在治学、从政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崇尚气节”和“匡世扶艰”的精神。
两宋之际,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胡寅父子及张栻等人,或因躲避战乱,或因拜师求学,先后从福建、四川等地辗转来到湖南,在湖南创办书院讲学、著书立说,形成了以“湖湘”称名的地域学派。当时的学术界就将这一既有授受关系、又有相同学术思想的学者群体称之为“湖湘学派”。他们创建的湖湘文化,他们的学术思想、学风特色等对后代湖湘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在治学、从政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崇尚气节”和“匡世扶艰”的精神。
胡安国一身骨气和正气。他走上仕途,就一直严守士大夫操守,不趋炎附势,在为太学博士期间,“足不蹑权门”〔1 〕。胡安国入仕之初,正值权奸蔡京当道,一手遮天,权势显赫,一切“向权看”的官僚士大夫们极尽阿谀巴结之能事,可他不但不受蔡京的笼络,还敢于冒犯他,因而受到蔡京等人的无情打击〔2〕。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 宋高宗赵构欲起用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只因朱胜非过去一则“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即是说高宗一味南逃,胜非难逃其咎;再则“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即是说中原沦丧之事,胜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胡安国极力反对。宋高宗只好改任朱胜非为侍读,但胡安国仍坚持己见,并卧家不出,表示与投降变节者誓不两立的抗战立场。这件事不仅得罪了宋高宗和朱胜非,而且也得罪了在朝的一班权臣,所以胡安国不久即落职〔3〕。正由于他不阿权势,表现出一身骨气和正气, 曾先后得到了许翰、侯仲良、谢良佐等名家的赞许。许翰称许他“鹤立鸡群”:“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4〕侯仲良表彰他把功名富贵看得很淡:“吾以为志在天下、 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5 〕谢良佐赞颂他为严冬的青松翠柏:“胡康侯(安国字)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6〕
胡宏是一个志在“立身行道”,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功名利禄为他“志学以来所不愿也”,更不愿意同腐朽的现实政治势力同流合污。史载胡宏曾以荫补为右承务郎,“不调”〔7 〕,即不愿堕身于黑暗官场之中而不赴任。绍兴八年,投降派秦桧当国,被宋高宗任命为右相。在秦桧奸迹没有暴露以前,胡安国早年曾与他有过一段交往,胡安国死后,秦桧就想笼络、召用在家的胡宏、胡宁兄弟。史载秦桧曾“贻书其兄(胡)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其结果“胡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8〕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投降派势力受到打击,汪应辰、 张浚等人纷纷向朝廷推荐胡宏,“宏被召”,只因朝政十分腐败,他“以疾辞”,“终避不出,竟卒于家。”〔9 〕他这些毕生追求“立身行道”,不愿做官,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的事迹,确实表现了他的一身骨气。他声称自己志在做一个不随俗浮沉而有气节的大丈夫〔10〕;时人亦赞誉他为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
胡寅志节豪迈。初擢第时,媚金乞和的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他坚决拒绝。靖康初京师陷,张邦昌被金人册立为帝,僭号“大楚”,他弃官归家〔11〕。胡寅洞悉南宋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气节与廉耻不彰,寡廉鲜耻,甚而认敌为友,认仇作父。徽、钦二帝被金北掳,导致北宋灭亡,这本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而时人却视为“是以为适然耳”,即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胡寅一方面怨恨朝廷,对国家之事极为忧虑,批评宋高宗不去集合义师报仇雪耻而忙于登基;另一方面又痛恨权奸,对秦桧等权奸执意罢战议和深怀其恨。因此,秦桧当权,他不愿与其为伍,“遂与之绝”,辞官不做,“乞归湖南衡山家居。”〔12〕
张栻身为朝臣,有很强的洞察力。他所看到的是“危机”、“失败”和“困境”。决不象有些人那样,本是山河破碎,却一味粉饰太平,沉缅于歌舞升平之中;而是屡以危言规劝皇帝,希冀重整山河,中华奋起。张栻的一生始终站在反对女真氏族贵族集团发动的对南宋侵略战争的立场上,每每上疏痛陈国失,指出“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勉励朝廷自今以后“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济哉!”〔13〕史称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14〕
总之,两宋之际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崇尚气节”、“砥砺情操”的品德,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湖湘学子。
2、明清之际湖湘学者代表人物民族意识强烈,民族气节昭著,对近代湖湘学人民族意识的激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呼唤着一代思想家和学术巨人的产生。这一时期的王夫之,既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历史上著名的湖湘学家,是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他那“崇尚气节”、“砥砺情操”、“不阿权势”的品质,不仅在湖湘文化演变过程中比较突出,就是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界亦很典型。王夫之既反对汉族统治者“万里兴师”,“勤远略”,无故侵凌少数民族;更痛恨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动掠夺性战争,并认为在这种掠夺性战争面前,必须坚决予以抵抗。他特别强调“夷夏之防”,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固我族类”,即把保卫民族生存视为“古今之通义”,作为永恒的政治原则。正是从“夷夏之防”的民族思想出发,王夫之一方面痛斥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族投降主义者,尽情鞭挞历史上缺乏民族气节的人,表现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极大。比如怒斥石敬瑭“称臣称男”,“名为天子,贱同仆隶。”谴责桑维翰为石敬瑭策划是“祸及万世”,犯下了“覆载不容之罪”,是“万世之罪人”。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夫之还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对于东晋桓温北伐和南宋岳飞北伐,他就理直气壮地提出桓温、岳飞如能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即使取东晋司马氏和南宋赵氏的皇位而代之,也无可非议。这种议论,在封建时代胆子是够大的了。另一方面,对现实中的满清贵族入主中原,首则举义兵于衡山,英勇抗击清军,只是因力量薄弱而“战败兵溃”;继而历经险阻,奔赴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坚持继续抗清,只是眼见事不可为,遂绝望于南明永历朝廷而被迫遁回湖南,开始了“屏迹幽居”的生活;三则在清廷占领湖南并下令“薙发”之时,王夫之拒不“薙发”,改换姓名,变换衣著,浪迹于荒山野岭之间,“常匿常宁徭洞,变姓名为徭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著述;四则于1675年居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称为“湘西草堂”,终日孜孜矻矻,刻苦自励,完成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著作,为祖国的思想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
总之,王夫之“夷夏之防”论中所蕴含着的民族自卫思想、反对民族投降路线、提倡民族气节精神,是对祖国历史上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阐扬。
3、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的代表, 在致力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过程中,表现出“崇尚气节”、“砥砺情操”的可贵品质。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湖南涌现出的几大人才群体,他们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进程。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崛起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他们在致力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过程中,表现出“崇尚气节”、“砥砺情操”的可贵品质。
魏源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和近代史开端的两个时代。他既是鸦片战争前后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又是湖南在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批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杰出的代表。鸦片战争失败后,他痛定思痛,立志制订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抵抗外国侵略的方案。他所作的《圣武记》就反映了他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振兴中华的进步思想,并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希望战败之后举国同仇敌忾,能重振国威。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主张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则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当时顽固派竭力反对学习西方,认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淫巧之为,荡人心志”,学习西方是“示弱外夷”。魏源却十分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明确指出他所编撰的《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15〕他斥责顽固派借口“奇技淫巧”而盲目排外的错误,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学习西方技术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使中国也能和列强并驾齐驱,而不受其欺侮,这和“示弱外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魏源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和坚持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洋溢于《海国图志》的字里行间,并为后世湖湘学者所继承和弘扬。
左宗棠既是一个“心忧天下”、“志在康济时艰”的出类拔萃的湘籍士大夫,又是一个“崇尚气节”、“砥砺情操”的湖湘学者。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割据和沙俄强占伊犁,新疆有沦为英、俄殖民地危险的紧要关头,在祖国统一遭到严重破坏的危急时刻,左宗棠对内力排众议,独任其难,严斥“放弃新疆”的谬论,坚决主张出关西征;并排除李鸿章的阻挠和破坏,坚韧不拔地为西征大军筹饷、筹粮、筹运,运筹帷幄,表现了一身正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对外他在向天山南北的进军中,不为英国侵略者的阴谋所惑,除恶务尽,勇往直前;他在收回伊犁的斗争中,不为沙俄帝国主义的威胁所屈服,秣马厉兵,殊死决战。所有这些,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谭嗣同既是一个我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爱国志士,又是一个“砥砺情操”、“崇尚气节”的著名的湖湘学者。说他“砥砺情操”,是指他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清醒认识到,只有无私,方能无畏,要能“不为所困”,不被一切恶势力所吓倒,就得视个人的“功名货利”于不顾,做到“得失利害,未足撄我之心!”他认定一个人的“块然驱壳”,“除救人外,毫无他用”;“除利人外,复何足惜!”说他“崇尚气节”,他不仅在口头上发誓虽“杀身灭族”在所不惜,为变法维新、振兴中华服务,而且确实以他“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谭嗣同那激烈的言词,勇敢的行动和高尚的民族气节,是当时其他一些改良派人士所望尘莫及的。所以梁启超在评价他时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君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
二、近千年来湖湘学人坚持“崇尚气节”的传统精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和启迪的宝贵经验。
近千年来,湖湘学者崇尚气节、重视情操、不阿权势、正道直行的一面十分突出,而且积淀而成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了湖湘人文精神之一。
1、近千年来湖湘学人坚持“崇尚气节”所积淀的传统精神,表明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要真正做到“崇尚气节”、“砥砺情操”,就必须正确对待富贵贫穷与生死祸福。
胡安国为人处世,以古代圣贤为榜样,重操守,讲忠信。生活贫困,却口不言贫,手不书贫,表现出可贵的安贫乐道、不求利达的个人品格,并以此谆谆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学生。自父亲胡渊逝世后,他就几乎完全断绝了仕进的念头。正因为他能正确对待富贵贫穷,所以被时人称赞为“视不义富贵如浮云”〔16〕。胡宏终身布衣。在受到中年丧子、丧妻的痛苦后,仍然坚持隐居治学不动摇。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隐居治学决不是为了个人的“独善其身”,而要象古圣人那样在穷窘中“兼善万世”;特别是在当时“道学衰微,风教大颓”的关键时刻,他决心“以死自担”〔17〕。与此相联系,胡宏还无情地批判那些执迷于富贵利达、醉生梦死者,指出这些人虽然当时也的确是“快胸臆,耀妻子”、快活了一阵子,但过不了多久,便会“声名俱灭”,为世人所不齿。因此,他从年青时起就鄙视利禄之途,而力求真正做到安贫乐道。张栻之父张浚,虽为南宋“中兴”名相,但居官廉洁。所以张栻在当时虽然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却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相反,其父张浚这种为官清廉的作风,极大地影响了儿子张栻。张栻一生以圣贤自期,以匡扶社稷为志。因此,象这样一位堂堂的宰相公子,却自幼以清贫自居,以孔门高足颜回自期,把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信条,为此作《希颜录》上下卷,力图使自己作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颜子式圣贤。他的业师胡宏称赞他“稽考之勤”,对他的安贫乐道、好学不倦倍加赞赏,并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王夫之为时势所迫,最后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这是一个“良禽过而不栖”的穷山恶水地方,赭色的山冈,稀疏的草木,干涸的溪流,四周杳无人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王夫之安之如素,“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面不变”〔18〕,终日孜孜矻矻,刻苦自励,完成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著作,为中华文化和湖湘文化增添了新的瑰宝!左宗棠生于贫苦之家不忧贫,从小就养成勤俭朴实的生活习惯,熏习于朴拙的家风〔19〕。他日后在事业的成就,实因长期的俭朴生活磨练和良好家风所促成;他日后发迹得意后,仍不改原来勤俭朴实的初衷。
2、近千年湖湘学人坚持“崇尚气节”所积淀的传统精神, 表明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要真正做到“崇尚气节”、“砥砺情操”,就必须正确对待荣辱功名与权位爵禄。
胡安国在湖湘学派中是能正确对待荣辱功名与权位爵禄的典型。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 实历不及六载”〔20〕。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为官,或“遍触权贵”, 或“同投降变节者誓不两立”,或“足不蹑权门”〔21〕。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满于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权贵的腐败,表现出难进而易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一再辞退了朝廷任命的尚书屯田员外郎(宣和末)、太常少卿(靖康元年)、起居郎(靖康元年)、徽猷阁待制知永州(绍兴五年)等职〔22〕,执守自己由来已久的“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生信条。胡宏一生未入仕途,并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比如他在年轻时就曾以荫补右承务郎,可他从没去履职做官;后来投降派秦桧执掌朝柄,想网罗“故家子弟”而意图启用胡宏,胡宏不愿与其为伍而坚决拒绝;秦桧死后,胡宏再次被朝廷征召,他“又以疾辞”〔23〕。胡宏正是这样把荣辱功名与权位爵禄看得很淡、很淡才布衣终生的。胡宏这种不求富贵利达、不阿权势,同南宋社会钻营利禄成风因而政治昏暗的官场成了鲜明的对比。胡寅虽则毕生从政,但后来秦桧当国,投降派头子的嘴脸逐步暴露,“寅遂与之绝”〔24〕。正由于他得罪了奸相秦桧及其爪牙刘旦之流,因而落职,二十年没做官”〔25〕。张栻不仅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而且是个政治上的治国良臣,曾居官十余载。他为官不计较荣辱功名、权位爵禄和个人得失,而是志在报国。他对国事久有谋虑,只要有机会便要报国忧。张栻在其位,固然谋其政,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黑暗,敢于同情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随着国势之艰危亦无法使他安静,仍不忘国家之忧。王夫之在政治上以东晋力挽危局而壮志未酬的刘越石(即刘琨)自比,在学术上以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张横渠(即张载)为依归。在满清统治湖南以后,王夫之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终生不剃发,拒绝清王朝的威胁利诱,不应聘,不做官,呕心沥血地写下了许多杰出的学术专著,为中国文化思想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左宗棠眼见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当时的士大夫又失去了操守和忠信,曾一度产生过“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的思想,企图走“重操守”、“崇尚气节”的隐士田园生活。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过隐士田园生活决非他的真心,但他的出仕的确是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目的,而不是热衷于功名利禄。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时年已65岁,于奏稿中不免嗟叹年事已高,然思及国事,却掩不住一片丹诚〔26〕;任两江总督时,左宗棠又以72岁高龄奋勇而起,图谋中法问题的了结。左宗棠不但毕生不注重荣辱功名与权位爵禄,相反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都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
3、近千年湖湘学人坚持“崇尚气节”所积淀的传统精神, 表明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要真正做到“崇尚气节”、“砥砺情操”,就必须正确对待人己与家国。
胡安国公而忘身、国而忘家的道德思想境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湖湘学派中都是比较突出的。比如靖康末,宋钦宗任命胡安国为中书舍人,赐三品服。但由于在抗金这一核心问题上,在抗金名将李纲被罢免这一政治事件中,胡安国均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因而遭到了既有个人宿怨、又坚持投降路线的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的排挤与打击,迫使胡安国离开京城。就在胡安国离去不久,金军就包围了京城。这时,其子胡寅尚在京城供职,有客为之担扰,但胡安国能正确处理“家”与“国”的关系,考虑得更多的是朝廷、国家的安危。他说:“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27〕史书还记载胡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密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28〕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胡宏虽然终生布衣,但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使得胡宏既对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又在努力探寻社会政治改革方案,企图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风俗等各个方面推动改革。这对一个终生布衣的儒学知识分子来说,其祖国和人民在他心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张栻在家教和胡师的影响下,以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重也委典型。比如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奸相汤思退用事,朝廷罢战议和,同金人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这时张浚已被谗去位,饮恨逝世于江西余干。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张栻心中无限悲愤,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就连夜草疏上奏,一腔爱国激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奏疏开门见山地说:“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紧接着提醒朝廷过去对金战争之所以失利,乃在于当局和战不决,动摇不定,他说:“异时朝廷虽尝兴缟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忱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29〕直至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忧患成疾,一病不起,处于弥留之际,仍不忘危难中的国家,“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30〕王夫之一辈子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都与反清复明的斗争相联系。在亲自组织和参加抗清斗争失败,投奔于南明永历政权又绝望以后,遂“决计林泉”,“力疾而纂注”〔31〕。此后,他改为以笔墨作武器,从思想上总结王朝失败的教训。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亦研读和著述不辍。162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杀害于昆明,王夫之在悲痛之余,立志修一部反映永历政权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当代史——《永历实录》。这部书以相当完整的体例记述了永历政权的始末,一方面对永历政权失败的内在原因全面加以披露;另一方面又为李过、高必正、李定国、李来亨等联明抗清的农民军将领作传,记述他们抗清斗争的历史功绩。左宗棠“先人后己”非常有名。有一次他要上京会试,没有盘川,他夫人在自己的奁产中设法为他筹措了100两银子,这时恰值他大姐遭灾穷得没饭吃,他便把这100两全数送给了大姐。家乡有两年连续两次大水,他毫不迟疑地捐出他当时全部教书的收入,还到处向亲友劝募,散米煮粥,救济难民。他这种“先人后己”、“乐于助人的作风和品质,直至后来发迹之时仍坚持不变。他后来飞黄腾达、官高禄厚,依然乐于帮助亲族,帮助师友,帮助僚属,帮助地方义举。左宗棠在“先国后家”方面亦有着不同于当时一般儒家学者和士大夫的地方: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反对侵略而积极筹谋;他比较务实,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痛感当时政治的败坏,企望国富兵强;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之时,他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重重困难,毅然承担规复新疆的重任;在中法越南交涉时,他先备战两江,后督战闽、台,已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他历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至于自己的家庭和身体却不怎么去经营它、考虑它!
注释:
〔1〕〔2〕〔3〕〔4〕〔5〕〔6〕〔16〕〔20〕〔21〕〔27〕〔28〕《宋史·胡安国传》。
〔 7〕〔8〕〔9〕〔10〕〔23〕《宋史·胡安国传》附《胡宏传》。
〔11〕〔12〕〔24〕〔25〕《宋史·胡安国传》附《胡寅传》。
〔13〕〔14〕〔29〕〔30〕《宋史·张栻传》。
〔15〕魏源《海国图志·叙》。
〔17〕《宋元学素·五峰学案》。
〔18〕〔31〕王敔《姜斋公行述》。
〔19〕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6页。
〔2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