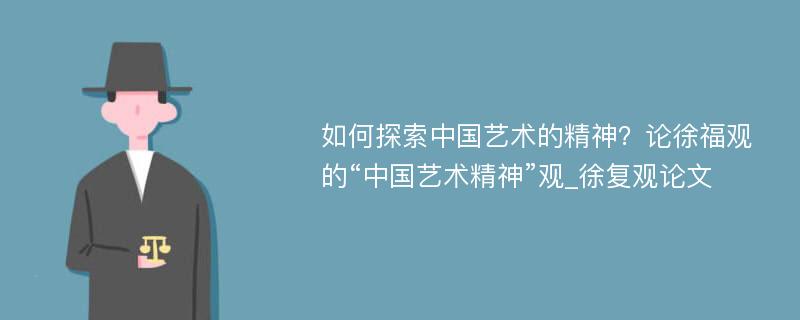
怎样探讨中国艺术精神?——评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几个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艺术论文,精神论文,几个论文,观点论文,评徐复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2—0021—08
艺术精神是指一种艺术独自具有的、内在的品质或气质。譬如,中国画不同于日本画,中国古诗不同于日本俳句,不是它们的物质媒介不同,而是内在的精神不同。西方艺术也是如此,近代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的绘画,人们都可以看出具有不同的精神。当然,东西方艺术精神的不同,则更是十分明显的。由此可见,艺术精神中蕴涵一种文化的根本理念。因此,探求这种艺术的精神不是一个艺术上的难题,实质上是一个哲学难题。这个难题是属于哲学的美学学科研究的真正对象。(注: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艺术中宇宙观、哲学观的研究,就属于这种对艺术精神的探求。)因为,一种艺术所体现出的精神,不可能来自艺术本身,而应该是源于民族文化中最核心处的东西——哲学或宗教。就像体育运动虽然是一种身体的运动,但体育的精神——比如“奥林匹克精神”之类,一定是属于人文的精神一样。
中国艺术的精神是什么?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他认为中国艺术精神(或纯粹的中国艺术精神),是庄子的精神(注:徐复观先生也说过:“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P5)但是, 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音乐,而且更重要的,儒家是“为人生而艺术”。[1](P21)而“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1](P5)。同时, 徐复观先生还认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和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1](P5 )(该书第三章以后专论中国绘画)所以,中国之纯艺术精神是渊源于道家,尤其是庄子。故本文只从《庄子》的角度来辨正。):
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1](P118)
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1](P5)
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1](P41)
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1](P49)
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1](P3)
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1](P44)
徐复观先生的这些观点,可以说发前人之所未发,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线路。(注:宗白华先生说过:“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倾向。”[2](P187 )他还认为,《庄子》中的人物,都成了宋元人画的范本,但他没有由此从整体上论及中国艺术的精神。)这种首创之功,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无疑都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于“中国艺术精神”这样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臻于完满,非一人一书即可了断,徐先生书中自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谈谈一些粗浅之见。
首先应该要说明的是,徐复观先生的著作在关键问题的表达上出现了一些混乱。虽然他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绘画的内在精神,并试图由此伸展为探讨中国艺术的精神,但他常常把“中国艺术精神”,与“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以及“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精神”混为一谈。例如上文中“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显然不是指“中国艺术的精神”,而是指“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精神”。当然,“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以及“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精神”,与“中国艺术的精神”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和逻辑上,它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这些问题的混杂使得徐先生的论述不仅零乱,而且常常有悖逻辑。
本文不想讨论“中国艺术精神”与“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以及“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精神”之间的关系,而是集中就徐复观先生书中涉及《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关系的论述,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庄子》的“道”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最高意境是否相同?
从根本的思想和观念来说,“道”是《庄子》全部哲学的核心。谈论《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庄子》的“道”。因此,徐复观先生书中专设一节“道家的所谓道与艺术精神”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徐复观先生也说:对于老庄的“道”,“假使起老、庄于九泉,骤然听到我说的‘即是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必笑我把他们的‘活句’当作‘死句’去理会”[1](P43),但他仍然认为:“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而“道的本质是艺术精神,乃就艺术精神最高的意境上说”。[1](P49)
让我们看看《庄子》的“道”是否属于一种艺术的精神,或艺术精神的“最高意境”。在《庄子》看来,“道”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本源:“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3 ](《知北游》)“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在时间和空间上,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故存”;它始创万物,“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3 ](《大宗师》)正是由于“道”,宇宙万物,无论大小、巨细,其生成、发展以及衰亡的运动,才有规律:“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愍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本根”就是本源。“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3](《知北游》)“道”主宰一切,“无不将也, 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3](《大宗师》)
从创生论来说,“道”是“物物者”。“物物者非物”,“道”是非物质性的,而且,“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3](《知北游》)“际”即边界、关系之意。所以, “道”决定万物的盈虚积散等变化,本身却没有变化。“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3]《知北游》“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3 ](《大宗师》)“道”又无所不在,在蚁蝼、稊稗、瓦甓、屎溺。而且,“道行之而成”,是在事物的自然运动之中,“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3 ](《齐物论》)在事物的千变万化中,“道”则始终如一:“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3](《齐物论》)
我们从《庄子》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道‘神鬼神帝’,说明比鬼神更根本;道‘无为无形’,说明道没有情感和意志,所以不同于上帝之类的神灵。道‘自本自根’,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道又‘不可受’‘不可见’,是神秘而不可感知的”[4 ](P105)。
因此,简单地说《庄子》的“道”与中国艺术家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相同,或者说“道”的本质是艺术精神最高的意境,实在是牵强附会,不能成立。徐先生本人也意识到这里的背谬,所以他又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庄子把它当作人生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 1](P44)就是说, 只从《庄子》“由修养的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1](P43—44)。这些话的含义实际上是,中国艺术精神是体现在《庄子》中的得“道”者身上,也即徐先生所说的:“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1](P3)
那么,《庄子》中的得“道”者,或者说《庄子》理想的人生,是否具有一种艺术的精神或境界?
第二个问题:《庄子》中的得“道”者是否具有一种艺术的精神或境界?
《庄子》的“道”是非常神秘的:“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3 ](《则阳》)言语和思维都不能表达“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3](《知北游》)当然, “道”有时可以体验。能够体验到道的人则是非常不一般的人:“夫体道也,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今于道,秋毫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3](《知北游》)比如, “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3](《大宗师》)除了天地、日月、 星辰,得“道”的几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除此之外,《庄子》中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对得“道”者的描述,大体说有三种。第一种是能够无待而逍遥,即绝对逍遥者。《庄子》认为,像大鹏鸟那样,“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不算绝对逍遥;“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的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也不是绝对的逍遥;甚至“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的列子,仍然不是绝对逍遥。因为,“此难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绝对的逍遥是“无待”。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这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是绝对逍遥。[3 ](《逍遥游》)能够这样逍遥的,只有“神人”、“至人”、“真人”、“圣人”。
何为“神人”、“至人”、“真人”、“圣人”?《庄子》说: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3 ](《达生》)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3](《大宗师》)
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3](《大宗师》)
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3](《齐物论》)
这种“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可以说,就是后来道教中的“太上老君”、“太白金星”等神仙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方士卢生向秦始皇说:“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可见战国时的方术也与《庄子》此说相通。
《庄子》中得“道”的第二种人是混沌无知的人,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像南郭子基、伯昏无人等。成玄英疏曰:“伯,长也。昏,黯也。德居物长,韬光若黯,洞忘物我,故曰伯昏无人。”《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3 ](《养生主》)知识是无限的,而人生是有限的。所以企图去穷尽知识,是会陷入迷途不能自拔的。《庄子》还说:“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成玄英疏曰:“率其所能,止于分内,所不能者,不强知之,此临学之至妙。”否则,“斯败自然之性者也。”[3 ](《庚桑楚》)“天均”在此意为自然之性。如果强求为知,则必然碰壁、失败。《知北游》通篇讨论的,就是能否认识“道”的问题。结论是:“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就是要人们取消求知的欲望和行为。
因此,《齐物论》把古人的“知”分为几类:“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这是第一等,即知道“未始有物”之前的世界状况为知识之极;其次是“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就是只见其物,而不作区分;再次是“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即对事物作出区别而不判明是非;最下一等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就是把什么都弄得清清楚楚,道也就破坏殆尽了。最高的认知就是与天地浑然为一。
《庄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道”是为语言和思维不可及的:“夫大道不称”,“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3 ](《齐物论》)我们一般的逻辑和理性是不能把握世界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3 ](《齐物论》)而语言也不能表达真理之思:“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以轮扁斫轮为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3 ](《天道》)真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其次,就具体事物来说,它在发生和生成意义上,我们是不可究其根底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3 ](《齐物论》)就是说,事物生成在时间上不可追溯,同时,“有”与“无”在绝对的意义上也不能追问的。
因此,《庄子》走上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立场:“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豪]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3](《秋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无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3](《齐物论》)“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3](《知北游》)真知似乎在是与非,无可与无不可之间。
于是,《庄子》指出了一条与一般逻辑和理性认识不同的认识之路:“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3 ](《齐物论》)“天均”在此意即天然均衡。冯友兰说:“休乎天均,即听万物之自然也。”[5](P291)这里的“天府”、“道枢”、“天均”、 “葆光”,都是要人们超脱是非,以不知为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3](《大宗师》)
不能否认,《庄子》提出了认识论中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比如,语言与事物的关系问题,最终真理性问题,以及真知的可说与不可说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然而,《庄子》的立足点和结论是极端相对主义的,它在对待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态度上,又是消极、被动的,甚至是麻木地听任自然。
此外,《庄子》中还有得“道”的第三种人,即庖丁、梓庆等“寓道于技”者。
徐复观先生论述的主要是第二、第三种人。他认为这两种人与第一种人实质是一样的:他们“修养的过程及其功效,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梓庆由此所成就的是一个‘惊犹鬼神’的乐器;而女偊由此所成就的是一个‘闻道’的圣人、至人、真人乃至神人”。[1](P49)而在他看来,《庄子》中的神仙和圣人、至人、真人等,是一种艺术的理想人格:“庄子所要求,所期待的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如实地说,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1](P49)“庄子之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可以说都是能游的人。能游的人,实即艺术精神呈现了出来的人,亦即是艺术化了的人。”[1](P55)他还说:“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1](P47)而“《庄子》书中所描写的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无不可从此一角度去加以理解”[1](P87)。
这些看法,粗略地看,似乎有理,但若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似是而非。首先,《庄子》中这三种人的区别自不待言,不能笼而统之加以混淆;其次,像第一和第二种人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取消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而混沌无知的境界,本质上不是艺术的境界。《庄子》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与认识论上的极端相对主义是一致的,这与艺术化人生中的基本精神,可以说完全不同。(注:此外,徐复观先生把《庄子》中“心斋”、“坐忘”等同于审美的精神状态:“达到心斋与坐忘的历程,……正是美地观照的历程。而心斋、坐忘,正是美地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最后根据。”[1](P63)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把《庄子》的“心斋”、“坐忘”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还原”(Epoche中译为“悬置”)相比较,认为:“现象学的归入括弧,中止判断,实近于庄子的忘知。不过,在现象学是暂时的;而在庄子则成为一往而不返的要求。因为现象学只是为知识求根据而暂时忘知;庄子则是为人生求安顿而一往忘知。”[1](P68)“凡是进入到美地观照时的精神状态,都是中止判断以后的虚、静地精神状态,也实际是以虚静之心为观照的主体,不过,这在一般人,只能是暂时性的,庄子为了解除世法的缠缚,而以忘知忘欲,得以呈现出虚静的心斋。以心斋接物,不期然而然地便是对物作美的观照,而使物成为美地对象。因此,所以心斋之心,即是艺术精神的主体。”[1](P69—70)徐复观先生这一观点为大陆很多学者接受和转述。我认为,第一,现象学的“悬置”与《庄子》的“心斋”、“坐忘”,具有根本的不同:“悬置”所达到的是“纯思”,“心斋”和“坐忘”所达到的是“离形去知”的“混沌”;第二,二者都不能构成审美的条件。因为审美观照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人生和艺术经验作为基础和背景,并在审美的“当下”活动中发生作用。)
宗白华先生曾说:“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 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2](P59)宗先生这里对艺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以及其他境界的区分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艺术的境界是主于美的话,我认为《庄子》中得“道”的第一种人的境界是神仙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境界;第二种人的境界,类似于气功的境界,无论如何不是艺术境界;第三种人,可以说有一种艺术境界,但这在《庄子》中根本不是最高的得“道”之人。因为他们不能无待而逍遥;也不能像第二类人那样“离形去知”。而且,这类人也不完全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技艺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并非能证明他们的人生态度也是艺术的和审美的。因此,《庄子》的理想人生和得“道”者的最高境界,可以说不是艺术的精神或境界。
第三个问题:《庄子》有自然美的观念吗?
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知北游》有“圣人者,原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语,说明《庄子》的“‘美’与‘理’、‘全’、‘纯’,都是对道术本身的陈述。因此,可以了解庄子认为道是‘美’的,天地是‘美’的。而这种根源之‘美’是‘理’,是‘全’,是‘纯’。美、理、全、纯,这几个概念,对庄子的思想而言,是可以换位的。……道是美,天地是美,德也是美;则由道、由天地而来的人性,当然也是美。由此,体道的人生,也应即是艺术化的人生”。 [1](P51)
我们上文已经论及《庄子》“道”的实质含义和基本特征,以及得“道”者的精神或境界特征,故“道”与美的问题与得“道”者是否艺术化的人生,已无须赘述。这里集中讨论《庄子》对于“天地”与美的观念和思想,实际上涉及的是自然美的问题。(注:《庄子》关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说法,也被大陆的一些学者引用,作为《庄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证据。例如,李泽厚、刘纲纪[6](P242—247)。)
从《庄子》的整个思想可以看出,“全生”、“保身”是其人生观的核心。《史记》和《庄子·秋水》记载一个大致相同的故事:楚国王派人请庄子(注:本文中之“庄子”与“《庄子》”不完全相同。《庄子》一书的作者应该是多人,而庄子则专指庄周。)做宰相。庄子对使者说:“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7 ](《老子韩非列传》)可见在庄子看来,相对于生命来说,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是次要的。这是因为《庄子》的作者生活在诸侯争夺异常惨烈的战国时代,征战和杀戮司空见惯,人们随时会遭杀身之祸。所以,《庄子》关注的焦点是人怎样能在乱世中苟全性命。
在这种“全生”、“保身”的人生观指导下,《庄子》教人们不要关注所谓仁义、是非之争,认为:“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故“圣人议而不辩”。[3](《齐物论》)此外, 也不要去争辩世界上的其他事物的真假善恶。因为,这些争论往往是战乱的导火索,也常常是每个个体遭遇灾难和杀身之祸的原因。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取消一切差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这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内在含义。所以,像“世界究竟怎样?”“自然界究竟如何?”这类问题,《庄子》认为人们没有必要去关注。甚至自然界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庄子》也没有兴趣讨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在哲学认识论上的这种极端相对主义,为古今学者所公认,是学界不争的事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至少在认识论上,《庄子》就根本没有重视和关注自然界。也可以说,在《庄子》的哲学中,自然界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认识对象这一前提并未确立。
基于对自然界的这种本质观念,《庄子》也根本没有关注自然界的美和丑。所以,在《庄子》中居于最高地位的“道”,被认为无所不在。“道”不仅存在于灿烂的日月星辰、雄壮的山川、奔腾的河流、鲜花小草、鸟兽鱼虫等人类喜欢的、被认为是美的事物中,同样也存在于“蚁蝼”、“稊稗”、“瓦甓”、“屎溺”等人类不喜欢、甚至极其反感、厌恶的所谓丑的事物中。《庄子》所谓“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表达的就是这个思想。[3 ](《齐物论》)在《庄子》看来,自然界就根本无所谓事物的美与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也可以说,人们不需要关注自然世界的这些美和丑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庄子》理想的人格,与美丑都是没有关系的。《庄子》中很多人物,在生理上都是有缺陷的“跂者”(如佝偻丈人等)。所以,在《庄子》的思想视野中,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自然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所以,把《庄子》的“道”与美扯到一起,实在有悖于《庄子》的基本思想和观念。(注:《庄子》各篇的作者不同,这是学界的共识,这也是《庄子》中出现思想、语言和语义上矛盾的一个原因。故应该对现存《庄子》所有文字有所区别,把握其基本思想进行论述。)而把《庄子》的一些个别、零星的句子串联起来,游离《庄子》全书的根本思想,得出所谓《庄子》关于自然美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美不是《庄子》所宣扬和赞赏的东西(注:《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肯定一种最高的美,在这一点上与《庄子》不同。),中国艺术的精神与《庄子》的思想和境界也不能简单等同。因此,徐复观先生由此来论证《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其论点和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作这样论证,并非完全否认《庄子》乃至道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产生的深刻影响。徐复观先生所认为中国艺术中“虚”、“静”的精神和境界来源于《庄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是徐复观先生在提出问题之后,逻辑和思维游离了主题,论述本身过于直接、简单,有些则十分牵强。甚至可以说,徐复观先生著作的逻辑混乱,几乎掩盖了其中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此外,徐复观先生还忽略了《庄子》与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中介——魏晋玄学。(注:当然,徐复观先生也提到玄学:“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1](P3)但是, 他的全书主要是论述庄子与中国艺术的关系的。比如从道与技、虚静、游等方面来阐述庄子对中国艺术内在精神的影响。)在郭象的哲学中,《庄子》思想得到一次根本的改造和转换。(注:这并非意味郭象哲学比《庄子》深刻,而是指郭象对《庄子》的改造活动而言。)故有“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之说。[8](P16)而这些都是讨论中国艺术精神所必须涉及的问题,必须浓墨重彩,不能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然而,要论证这个问题,则是另一篇论文的任务了。
收稿日期:1999—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