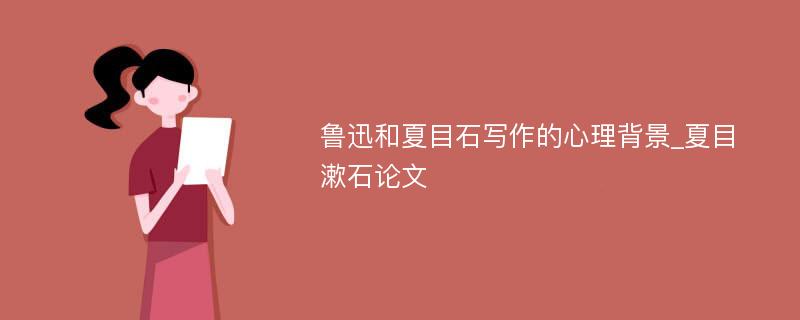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背景论文,心理论文,夏目漱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意义上的联系
20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然而,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P1644)。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其实岂止是在日期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他还在大力搜购夏目漱石作品全集,这可从鲁迅的岁末书账中看出。在1935年末的书账中,他购得了《漱石全集》的第4、8册,共2册。在1936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夏目漱石全集的搜购收藏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该年的书账中,可知他陆续购得《漱石全集》的第1、2、5、6、10、11、13、14、15册,共9册。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的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如吟哦‘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也许是有失礼貌的,然而并非不道德。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漱石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后来被周氏兄弟大段引用过的夏目漱石为高浜虚子《鸡头》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不把娱乐作为小说的目的不能成立’,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2](P494—495)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鲁迅的确受到了夏目漱石影响,也许这种说法有些武断,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3](P231) 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1](P1739) 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 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4](P826),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如果这还说明不了鲁迅受夏目漱石的影响的话,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则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5](P441) 周作人还具体讲到鲁迅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与显克微支来也”[5](P505)。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 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道:“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理和显克微支。”[6](P86) 他们的说法又与鲁迅的自述十分铆合,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自云,“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4](P792)。从周作人和增田涉的眼里来看,鲁迅文章中“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即使受影响,也仅与笔致相关,单纯是表现技术上的问题”[6](P86)。这也许为鲁迅的写作技法和讽刺艺术的理论渊源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参照。
至于鲁迅为什么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如此感兴趣,日本学者桧山久雄认为这是他们对当时文坛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义的做法反感所致,这也是才识卓著的文学家的成熟之处和基本素质。自然主义手段固然带来了新的文学气象,但也许很难适应东方独有的“低回趣味”的文化氛围以及注重直觉和感性经验的体悟方式,所以自然主义很难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成大气象。桧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在当时“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的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这里也许有一个不算小的理由,起码可以说明青年的鲁迅……反对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改革方向,而开始有了一种模糊的认识:要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这时的鲁迅,遇到了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漱石的文学,他自然会很倾心。这样的推想大概是很自然的吧”[6](P74—75)。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从以上一些当事人、研究者的回忆和研究中可以看出,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思想上的确发生了某些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鲁迅的一些文学理念和写作手段与夏目漱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联系呢?以下,我们将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来探析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二、“后进”国家变革:失败的五四运动与轻率的明治维新
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两位作家都生活在本国由自我封闭的封建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转折期里,经济、文化、政治、思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新奇和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文化先锋的紧张和痛苦。
五四运动与明治维新相同之处都是两国现代化起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西方文化的压逼下,他们都曾经历了一种由盲目自大(“不服”)到全面膺服(“不得不服”)的心理过程。这种“不服”都是表现为“东体西用”或“道器说”这一点上,中国人说,“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中国与欧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行之西洋则有效,而行之中国则大乱”[7](P1),“欧洲之无形文明,各种思想,各种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优于中国固有,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怀疑矣”[7](P2)。而在日本自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后,类似的提法不绝于耳,如桥本左内语提出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横井小楠提出的“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等。这种“服”则表现在他们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即在不触动东方文化根柢的情况下,要进行国家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加之中国半殖民化的加剧带来亡国的危险以及日本面临要被半殖民化的危险的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在精神方面的发达,并不得不奉之为变革的楷模。
然而,中国与日本的这两次变革又都是“后进”国家目的性极强的变革。“相对‘后进’的国家的近代化可以称作‘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这一点,是与相对‘先进’的国家的不同之处。比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是‘自然成长’的近代化的典型。在那里,近代化并不是目的意识性的。也就是说,不是按实现近代化的意愿去推进近代化的,其近代化是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来推进近代化”[8](P18)。在近代化进程中,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其实都是有着以西方为模板,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的心理,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文明”国家(欧美),一类是“半开化”国家(中国、日本等),一类是“野蛮”国家(非洲、澳洲),他认为日本应当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这种非内发性的、目的性极强的变革会带来文化引进的盲目和浮躁。“幕末维新期的‘开国’是急剧的、单方面的(输入过超的)文化接触。西洋文化从大开的闸门奔涌而进。于是翻译和传播这种异质文化的使命,便落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仅日本是这样,朝鲜和中国在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8](P15) 这时西化成为一种时尚而忘记其引进的本来目的,鲁迅曾抨击过那些稍沐欧风美雨,“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1](P1731),开口闭口ABCD、细胞、元素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也存在着以西学为时尚的知识分子,“明治以后的日本,为了改变长期锁国造成的落后状态,便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这种风气至今未变。特别有这样一种倾向,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不是根据他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他懂得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9](P100)。
虽然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加之鲁迅与夏目漱石分别在这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不同,这都决定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分别写作《野草》和《十夜梦》时所产生的抑郁和苦闷的原因个个不同。
五四运动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在陆续经历了器物(“洋务运动”)、制度(“百日维新”)而觉醒并发动的一场思想革命。它是在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由知识精英所主导并推动的不全面的思想革命。所以说,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的,仅局限于思想界的一次革命。
正因为是自下而上的,所以不会是彻底的,不会是全方位的,也注定是不成功的。鲁迅曾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出来”[10](P25)。“涂饰的新漆剥落”,鲁迅这个真切体会可以移用到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这也是自下而上思想革命的结果。
鲁迅以新文化思想运动主将之一的身份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转眼间又面临着新的失败,“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4](P774)。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写《野草》,自然沉痛而抑郁。
186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四艘大船打破了日本二百余年的封闭视野,“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从此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国难”。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经过一系列的倒幕战争之后才争取来的自强机会,“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是他们的口号,在这场变革中,明治政府广派使团到欧美等国考察,重金雇用外籍技师、教师,普及义务制教育,使得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以西化为时尚,以西化为荣。所以说,明治维新是由政府主导的一个自上而下,波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一次变革。
正因为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几乎是彻底的,全方位的,也注定是轻率的。一个德国医生贝立兹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黄遵宪在《驻日观感》中写道:“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全面向西方文明国家学习的谦卑的维新运动,以至日常生活中,“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人、警察、学生纷纷穿西洋制服。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红砖洋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于大街闹市。男人纷纷剪掉头发,竞相‘文明’,以至民谣中也说:‘敲敲剪发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允许和尚吃肉娶妻”。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肤浅的文明开化”现象,“如有人主张日本应使用英语,甚至主张和洋人结婚以改善日本的人种等等;还有一些破坏日本固有文化的现象发生,如烧毁古代佛像,五块钱出卖兴福寺五重塔等”[11](P39—40)。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即明治维新(1868年)前一年,五四运动虽比明治维新晚五十余年,但夏目漱石在1905年写他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时,已是明治38年了,他也已经38岁,不同于鲁迅的当事人身份,夏目漱石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观察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时明治维新“肤浅的文明开化”恶果已有所呈现,在夏目漱石的眼中,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维新后的日本处处是丑恶和堕落。
先看社会生活层面,按理说,明治维新可称得上是日本国的一次凤凰涅槃,但夏目漱石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一个封建主义余毒与资本主义恶瘤交叉感染的社会。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主宰了人的尊严和情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2](P274—275) 在小说《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借代助之口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一片黑暗”进行了反思和抨击,“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13](P101) 在夏目漱石看来, “日本这种急于跻身于一等强国之林、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忘却精神文明重要性的国家,正像一个虚张声势的店铺一样,门面很宽而进深极短,这种可怜的现象是出于硬要与西方列强比高下的结果。它必然会像伊索寓言中所讲的那样,是青蛙与牛竞赛,最后以鼓破肚皮而告终,而这种与西方竞争的影响,势必要涉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来。其结果是,人人都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生活难’”[14](P13)。一种失望和忧惧占据了夏目漱石他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心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就借猫眼对明治以来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揭露,小说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15](P341)
再看思想文化领域,福泽谕吉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16](P207) 维新先辈们认为西方文化是文明的、先进的,日本要从半开化状态进入到文明国家,就必须向西方全面学习。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西周是西方哲学在日本的移植者,“他更指出西方哲学高出中国及日本之上”[16](P175)。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明治维新多少具有些自轻自贱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福泽谕吉对此有所反思,他说,“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17](P74)。相反,西田几多郎在信浓哲学会作《现实世界之伦理的构造》中谈到东西文化的区别及所持的态度就显得相对合理些,他说,“西洋文化是大体以有形为本的文化,东洋文化是以无形为本的文化。西洋文化是以知为本的文化,东洋文化可说是以情与意为本的文化”,“认为东洋文化是未发达,发达时即为西洋文化,那种看法是错的。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是在各自独立的立场发达着的”[16](P1325)。早年留学英国,对东西文化有所把握的夏目漱石也反对自轻自贱的民族虚无主义,他认为,“日本总是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性,不见得要模仿西洋。西洋能成为模范,我们也能成为模范”[13](P57)。1911年, 夏目漱石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外发式的畸形发展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18](P3)。夏目漱石显然希望建设一种内发的成熟的日本文化,而现实又不能。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夏目漱石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写《十夜梦》,自然苦闷而迷茫。
从客观方面来说,鲁迅与夏目漱石同样生活在各自所在国近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五四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带来的不全面性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结局,从而构成了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鲁迅的心理阴影。而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形式造成全方位的颠覆的同时,也带来轻率和片面,这给以后来者身份审视维新成果的夏目漱石带来了一种思想困境。
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之一。
三、困境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击与遁逃
“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4](P1089) 社会转折期的知识分子向来不轻视他们的作用和责任,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这种具有高度责任心、独立品性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注重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分为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领域里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点滴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地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正良俗的形成。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己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走出一己之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鲁迅与夏目漱石正是属于这种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究竟是敏感人物”[4](P355),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1](P1819)。这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然而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其大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认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激情”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他否定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现实冲动,主张应当像知识分子的“模范”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用抽象的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这固然有其合适的理由,但如果知识分子所有的思考和智慧都存放在抽象名词堆砌的“象牙塔”里,并以之来对社会进行“批判”则无异于痴人说梦。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很值得参考的,他们“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9](P85)。至于吉罗笔下“抵抗的知识分子”,则要“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知识和实践。抵抗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将对于被压迫情境的改革性批评作为出发点的人们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19](P85—86)
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相对,还有一种“流氓知识分子”。冯雪峰回忆鲁迅时说过:“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20](P749) “他以为Lumpen性的知识分子,表面上好像很革命,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也崇拜外国人的主子,只要有势力。”[20](P750) 这和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致,所谓没有一定的主张,一贯是骑墙的姿态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的。类似的话他还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21](P685)。因为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4](P1191),“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4](P1168)。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独立特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所谓“漱石”即取《晋书》孙楚的巧辩“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砺其齿”,这里面除有一种野鹤闲云式的仙风道韵之外,更有一种“漱石欲砺其齿”的桀骜不驯的气骨。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写作目的相同,早年的夏目漱石从事写作时是“用维新志士那种拼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22](P567)。他在其代表作《我是猫》中以猫眼看人的角度对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种种丑恶和堕落做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赴英留学时,夏目漱石就声称自己是一个“自我本位”主义者,他说,“自从以自己的双手紧紧把握住了‘自我本位’这个词之后,我变得异常地坚强起来。一种傲视一切的豪迈气概油然而生:他们算什么东西?可以说,站在茫然若失的我的面前,给我明确指出从今往后的前进道路的,正是这‘自我本位’四个字。那时候,我心中的不安完全消失了。我以轻快的心境眺望着阴郁的伦敦”[23](P130)。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品性使得夏目漱石为文为人显得独立卓行,这可从其以下的行略中略窥一斑。
早在1907年,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设宴招待知名作家,明治初年作家尚属于一种不甚被人瞧得起的“下贱职业”,一般能被邀请的人自然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然而,有三个人毅然拒绝出席,他们分别是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和夏目漱石。
1910年5月,日政府借有人暗杀天皇为由,将搜捕的26人以“大逆罪”起诉, 并判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0人死刑,这就是当时的“大逆事件”,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夏目漱石对此非常愤慨,1911年,他断然拒绝文部省授予的博士称号。然而文部省声明,这是敕令,不能辞退。夏目漱石固执地说,“总而言之,文部大臣表示不取消授予,我则表示不取消辞退。社会承认我的辞退呢,还是承认文部大臣的授予呢?这要根据社会的常识以及社会对学位令所加的解释来决定。但是,无论文部省如何,社会如何,我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肯定自己的自由”[13](P114)。在“博士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夏目漱石就发表了《文艺委员是做什么的》的文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设立文艺院并制造官选文艺委员,其实质是为了文艺仅仅适应行政上的需要,而使作家失去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
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在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
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之二。
总之,我们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进一步地了解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人和为文呈现出一些相似风貌的原因之所在。
标签:夏目漱石论文; 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读书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野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