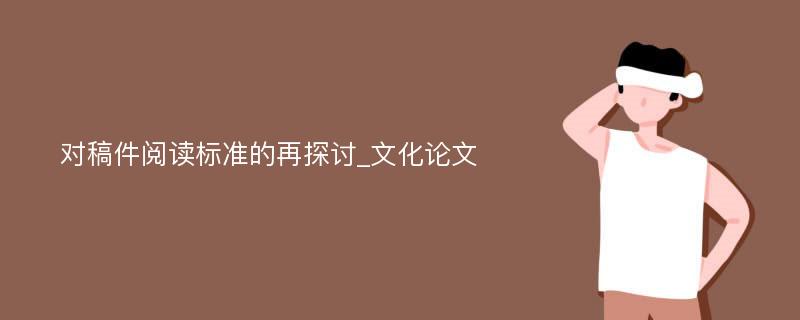
再论稿件的审读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稿件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书、一本刊物的生命在于质量。质量要靠编辑通过审稿来把关。因此,稿件审读的标准至关重要。太紧了,不利于百花齐放;太松了,又难免泥沙俱下。要恰到好处,也真不容易。
有的编辑家提出,对书稿要进行“三看”:从同类作品相互对比看,从一本书的整体要求看,将立足点放在更高处看。①《科技编辑工作概论》根据审稿中常遇到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政治性问题的审定。(二)是否符合编写大纲或出版意图。(三)科学技术性。(四)书稿的结构和文字质量。(五)稿面是否整洁清楚。也有提出“两点要求与三项考虑”的,有提出材料、论证、见解、创新、探索、办法、分寸、风度“八有”标准的。说法不一,标准各异。
我们认为,除了某些出版物的特殊要求以外,稿件审读的标准一般有四个,即:创新性、思想性、科学性和可读性。
一、创新性 为什么要将创新性放到第一位来谈呢?因为文化出版活动,说到底,是一种创造活动,写文艺作品,称为“创作”;有独到见解,称为“创见”。都与“创”字有关。敢创,才能出新。
初学者可以依样画葫芦,可以模仿,但要将其重复别人的东西拿出来发表就有问题了。纯粹的仿作,再好也是赝品。唯有作者自己创造的、有独到之处的作品,才有出版价值,才能长存于世。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天大约出版图书一千四百种,发表论文一万四千篇。一个学科专家仅仅浏览一遍本学科当年发表的论文,就需要花费四十八年的时间。②有人认为过多的信息已经“泛滥成灾”,使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当然要精益求精,出版部门也要好中挑好。
某个稿件,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学术上也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但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新的观点。什么都不错,什么都不是自己的,人云亦云,算不算是好文章?茅盾当年主编《文艺阵地》时,在一篇启事中曾经提出他的审稿标准:“作品呢,或题材把握有独创之处,或形式上有新的尝试;论文则不患其立论之无懈可击,而患其庸俗与公式化,缺乏新知灼见。”注意,茅盾将成语“真知灼见”中的“真”换成了“新”。一字之改,却道出其中真谛。
艺术贵在创新。创新即意味着超越他人,超越自我。真正的艺术家是从来不去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在征服了一个艺术高峰后,又不断地去攀登新的高峰。我们在用“创新”尺度来衡量稿件时,应该审视它对作者本人原有作品的超越程度和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超越程度。如果它在现有作品的一般水平之下,就说明创新价值不大或没有创新价值。如果它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人,就说明它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价值较高。可能是内容新颖,开拓了新的题材;也可能是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段独特,开创了新的形式。
科学也贵在创新。一篇学术论文,如能在解决问题上提出新的途径,那当然最好。如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分析问题上有新的见解也好。再退而求其次,在提出问题上应有新的贡献,最起码要在观察问题上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否则,便无新意,也没有发表的价值。
新和旧是相对的。怎样才算“新”?这就要比较。前人未写过的,新;前人已写过的,就要看手中的稿件是否在观点、材料、方法上有突破,如有突破,也就有新意。这需要当编辑的经常看书看报,掌握各种信息,至少要了解所编范围的新动态。一旦作者抄袭,马上就能识破。作品有无新意,也能一目了然。
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作者可能会担心创新原则将他们的稿件排斥在外,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且不说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戏剧融进了现代人的审美观,推陈出新,就是纯粹的考古研究,也有许多新技术的引进和新材料的发现。流传很久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不是被新出土的文物证明是《触龙言说赵太后》吗?原来触詟系触龙言之误。还有,电脑分析古代文学名著更是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视野。
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现代,各种新名词、新概念纷至沓来。文理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的崛起以及高新技术的运用等,也为这些新名词、新概念的繁殖提供了舞台。于是,许多新符号、新名词纷纷登上各种文化媒体。如伴随电脑而来的“软件”、“硬件”已广泛运用到管理学中,日本人发明的“软科学”一词,已被大众接受,用来专指处理信息资料的科学,生发出来的“软饮料”、“软着陆”等经常见诸报端,最近又在晚报上看到了“软装饰”。我查了一下词典,“软饮料”、“软着陆”已被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说明这些新词已被权威认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新词汇,注意它们蕴含的新概念。编辑不能因为不合自己的口胃、看不懂而拒之门外,因为语言是概念的载体,人们往往能够从新的词汇中了解新的概念,接受新的思想。
成语“标新立异”,原谓特创新意,立论与众人不同。后多指提出新奇主张或创造出新奇的式样。如果不是从贬义的方面来理解“异”的话,我们觉得“标新立异”的提法还是不错的。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有事实根据,能自圆其说,应当允许作者标新立异。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等,不是一下子就被众人所接受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就被人看成是异端邪说,但历史证实了他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否定新生事物,而要热情支持作者的创新精神,即使这些新的还太嫩、还不够成熟,但只要有一定的探索价值,也可以帮助修改,使其脱颖而出。抛砖引玉,引起争鸣也好。很多新学科、新理论是在碰撞中产生、在争论中成熟的。编辑肩负着促进新学科发展和培养新人的双重责任。
当然,我们也不能被无病呻吟、哗众取宠的“新名词”所迷惑,天真地以为一切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有的新词是生造出来的,谁也看不懂,连他自己也未必真懂。有些时髦的新词大量堆砌,叠床架屋,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意。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曾写过一篇幽默小说《饱学之士》,讽刺那些爱玩弄新词的“诗人”。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书店里对着书架说:“浅表层次信息载体积淀于框架深层之书的群落耗散无序之网络淡化现象之走向致使文化消费呈现危机氛围”。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新名词,谁知道他在说什么呢?旁人只能从他的语气和态度上推断他大概是在说书摆得不好,所以找不到。很简单的意思,干吗不直说呢?七里八拐,弄得别人如坠云里雾中。这种现象,在某些“新潮”的稿件中也时有发现。这就需要我们编辑来认真分辨,哪些新名词是蕴含着新概念的,哪些新概念是有价值的。
我们所提倡的“新”,是科学合理的“新”。它可以逆向思维、侧向思维,但不能违背逻辑。它可以超出人们已有的认识水平和经验范围,甚至违反常规,但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我们应该坚持辩证法,坚持唯物论,实事求是地把握创新性原则。
二、思想性 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写的东西总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即使是科技类的稿件,表面上看似乎与政治不搭界,但在深层次上也有一个是否对人民有利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思想性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不管作者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稿件中总要流露出一定的思想倾向。
社会科学类的稿件,观点鲜明,论点突出,政治态度明朗,思想性直露。文艺作品,借助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态度,思想性较含蓄。科技类稿件的思想性,是间接反映出来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出版方针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目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审稿的时候,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为人民服务,是否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符合这个条件的,就说明思想性是好的,可以考虑出版。反之,则不予通过。
也许是因为过去对政治问题强调过了头,使得一些人存有逆反心理,故对“思想性”的提法至今感冒,认为现在再来强调思想性,是否有这个必要?
其实,审稿的思想性早已有之。孔夫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都有政治标准。比如:“不语怪、力、乱、神”。犯上作乱,在孔夫子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这类文字,孔子要严加防范。能删则删,不能删就改。《春秋》中有周天子被晋文公挟持的记载,但到了孔子笔下,却成了“天王狩于河阳。”③明明是被挟持去的,却改成是狩猎去的。因为天子被人挟持,太失面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实太令人难堪了。孔夫子用他的政治标准来审稿改稿,所谓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乃春秋笔法也。
从出版史来看,不朽的传世之作,一般都是思想性较强的作品。有些思想,当时是进步的,开明的,现在看来,未必正确。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它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有些思想,至今还是进步的。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天仍被人广泛传颂,《岳阳楼记》也因此成为不朽名作。而有些思想性较差的作品却显得苍白,缺乏生命力。试看历朝状元的考试文章,有几篇留传至今?状元的文笔应该是不错的吧?但他们的考试文章是应景之作,思想性差,不值得编辑出版,也就不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了。
所以说,编辑审稿时重视思想性,不是今天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
再看国外,除了强调商业性外,思想性政治性也是很突出的。日本文部省编的教材,就把侵略我国的历史轻描淡写地改成“进入”,而非“侵略”。很明显,这是为他们的军国主义政治服务的,思想性很强。为此,我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两国打了几年官司。
看来,古今中外都很重视思想性,只是所持的标准不同罢了。总之,一篇稿件,总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示个什么观点或引导人们去做什么,这些就是它的政治内容、它的思想性。
对思想性的问题,编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在文字技术上出了问题,虽然也是问题,但有时还无伤大体。思想政治内容出问题就不同了。
这里还有一个政策问题。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指导各方面工作的准绳,宣传要力求准确,不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更不能唱反调。政策涉及的范围很广,有经济方面的,有外交方面的,有民族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等等。这些政策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也可能作某些调整。编辑人员要注意及时学习,了解精神实质,掌握宣传口径,以免发生错误。
例如,有的出版物把香港、澳门和世界各国并列时不加注“国家和地区”的说明,使我们在涉外工作中陷于被动。因此,来稿中如提到世界各国而又必需列入香港、澳门时,必须加上“国家和地区”的字样。在称呼港澳中国居民时,应称“同胞”,不要称“侨胞”。因为港澳地区是我国的领土,除了从国外回到港澳定居的华侨外,对其他港澳同胞不应称为华侨。
还有,刊登中国全图和广东省地图时必须包括南海诸岛,不能省略,因为南海诸岛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地图上如何表示南海诸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维护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斗争。
国境线不能划错,否则要引起邻国抗议。有的古代史稿件,论及古代国界,审稿时也要慎重对待。因为古代国界是现代国界的渊源,有的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涉及到外交政策。
还有民族、宗教问题,也相当敏感。有些出版物在论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时不够慎重,造成不良影响。如说伊斯兰教“把猪奉为神明”,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引起了事端。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编辑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缺乏政策观念。要知道,有些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到推行党的宗教政策,而且影响到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对于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书籍中一些关系民族问题的记载和说法,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党的民族政策加以分析鉴别,用是否有利于今天维护民族团结的标准加以衡量,有所取舍。不要去猎奇、炒热点、爆冷门。
诸如此类,都涉及思想性、
三、科学性 科学性是指稿件能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由于稿件的种类繁多,科学性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我们在审稿时应有所侧重。
新闻作品,要求事实的完全真实,并能客观、全面、公正地将客观事物反映出来,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新闻稿在报道客观真实事物时,可以议论,也可以对比,甚至可以抒情,但绝不能脱离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稿件科学性要求的基本要素。希特勒分子曾经叫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谎言重复一千遍仍是谎言,它可能欺人于一时,但不能得逞于永久。历史迟早会还其真面目的。我们编辑新闻,实际上也是在编历史。如果将编发的新闻稿件接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便是一部真实的编年史。
科学,容不得半点虚假。任何添枝加叶,或者“合理想象”,在新闻稿中都不允许。这就要求我们编辑基础知识扎实,信息渠道畅通,避免犯常识性的错误。例如,有篇新闻稿报道边疆地区电视机销量大增,一个季度达到多少多少万台。编辑居然信以为真。其实,只要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个数字有误,那个省的人口就这么些,一个季度中人均买三台电视机,要那么多电视机干吗?都去跑单帮?作者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宣传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报道失实,不仅未达到原来的宣传目的,而且还影响到出版物的声誉。所以我们编辑绝对不能马虎,吃不准的东西,要翻资料,作调查,仔细核实。
文艺作品,要求来自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具有典型意义。这里虽然也讲真实,但与新闻真实的概念不同,新闻真实是指生活真实,文艺真实则是指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容许虚构,可以提炼,可以浓缩,可以发挥,这与科学性的原则并不矛盾。
学术论文,要求对科学的某一领域有所突破,所提出的观点要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材料真实典型,论证严密。我们所说的“某一领域”有很大的伸缩性,它可以是一座森林,也可以是一棵树,一根枝条,一片叶子。科学上的贡献不是以研究范围的大小来划分的,你能研究整座森林,提出保护它发展它的总体规划固然很好,但有时候研究一张叶子上的病虫害,找到防治它的办法,也可能因此救活一大片森林。研究“叶子”领域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研究宏观领域的作用,而一些大范畴大体系的根本变化往往从一些“叶子”领域开始,由小叶子形成突破口,波及整棵大树、整座森林。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以研究领域的大小来评估来稿的价值,关键是要看它有没有突破,是不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学术研究是从已知求未知、从必然求自由的探索性工作,一些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来确定。编辑人员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代替客观标准,只选用自己认为观点正确的稿件,而不选用自己认为观点不正确的稿件。在学术问题上,编辑应该开明一些。只要作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就应当允许其持不同观点。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争论双方一视同仁,不要只选用一种观点的稿件,而要适当选用双方观点不同的文章,让争论双方都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在审稿时,不能以作者的地位、声望为标准,不能“唯书”、“唯上”。一个作者可能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有建树,观点正确。但不等于他在其他方面的观点也正确。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有些来稿,尽管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但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探索价值,对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有益,编辑也应热情扶持,帮助修改利用,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或争鸣,促进科学的发展。
一种观点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材料的真实和典型。材料不在多,而在典型。典型的材料,能以少胜多。典型的材料,最具说服力。
有了观点,有了材料,还要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如果逻辑结构不合理,推理呆板,逻辑证明不充分,那新观点还是立不起来。我们在审稿时,不仅要注意某些具体问题上的逻辑是否背谬,而且要分析通篇的逻辑体系,看它是否一以贯之。这些都是科学性的要求。
四、可读性 编辑是第一读者,一稿在手,是不是值得一读?有没有引人入胜的地方?怎样使它更加贴近读者?我们需要从编辑的角度看问题,更需要从读者的角度看问题。书刊报纸等出版物,最终是给读者看的,人家不要看,就达不到出版的目的,白白地浪费了人力物力。
稿件的可读性取决于稿件内容本身和表现的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形式为内容服务,反过来又影响内容的价值。我们发现,来稿一般有四种组合:1.深入深出;2.深入浅出;3.浅入浅出;4.浅入深出。
第一种,深入深出。专业性很强,学问深奥,着重研究某学科的高精尖问题,专用术语很多,一般外行看不懂。出版数量有限,主要供学术交流之用。属“阳春白雪”,虽高深但却货真价实。多见于科学论著、考古文章等,有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有特定的读者面。
第二种,深入浅出。将精深的大道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文章或书稿最受欢迎,读者面也较广。除了本学科本专业的人能读懂,一般读者也能接受。出版物交流信息、传播知识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某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也因此得到养料。社会发展到今天,学科门类越来越多,划分越来越细。在古代,正式学科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和哲学四种,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逐步分化发展出许多学科。目前的学科分支数已达两千多种。同时,学科的交叉综合性也越来越强,特别是新学科的开发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会战。如研究编辑学,就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一个人,即使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同时在许多学科中都研究得很深。因此,深入浅出的读物是最合适的了。一方面,读者不会被很深奥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所困扰;一方面,又可以及时得到有关学科的有关信息,便于学习和研究。这有点象大学里上大课,既要给研究生等个别尖子以启迪,又要顾及一般学生,让大家都听懂。
第三种,浅入浅出。多见于通俗读物、普及知识的书稿,虽然道理浅,但让人一目了然,获得一些知识。这样的稿件,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目前,我国一般大众的科学文化程度还不高,需要大量出版“浅入浅出”的读物,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编辑活动应该朝“真正地拥有大众”的目标努力。就当前情况来说,我们的出版物离“真正地拥有大众”还有距离,应该多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平易浅显的读物,争取更多的读者,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这方面《新民晚报》、《读者》杂志等做得较好。
第四种,浅入深出。这种稿件最可误。明明没有什么东西,却要藐似高深,摆架子来吓唬人。比如,吃饭,他不直接说吃饭,而说是“营养物质由外部向内部渗漏”;赏花是“调动自身的感知力、理解力和想象力,是视觉内在的审美能力和植物外延部分的美紧密地亲和”。故弄玄虚,弄得别人看也看不懂,还有什么可读性呢?真正好的文学家不以艰深为贵,司马迁写《史记》就改了《尚书》中的好多古字。而有人就偏偏爱用一些冷僻的、谁也看不懂的字,好象是跟读者过不去,故意要难倒读者。北宋的宋祁就有这个毛病,他和欧阳修合修《新唐书》时,常用一些稀奇古怪的字。欧阳修对此很有意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门上写了“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个字,请宋祁来看。宋祁看不懂,欧阳修趁机批评道,这就是你修《新唐书》时用的笔法。换成今字,就是“夜梦不祥,书门大吉”,意思很明了。现在古的不时髦,洋的吃香,有的作者就顺应“潮流”,变食“古”不化为食“洋”不化,把一些自己也未好好消化的洋概念洋名词硬塞在稿件中,弄得大家都看不懂。这样的文章,深是深了,可惜却没人看了。我们反对空架子,主张言之有物。我们的出版物应该让读者读后感到有所收获,有所启迪,或学到很多知识,或获得很多信息,没有浪费时间。
上述是一般稿件的审读标准,各种出版物还有其特殊的要求,如书籍要求稳定性,新闻稿要求时效性,教科书要求系统性,普及读物要求通俗性等,这由另文论及,此处不赘述。
注释:
①《编辑与出版基础课程》,P108。
②《决策思维学》,P20。
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