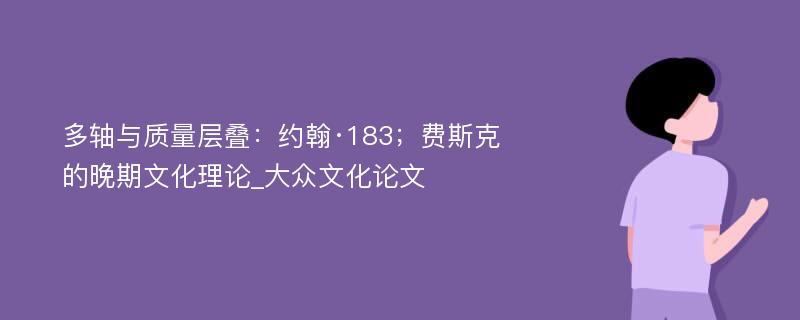
多重轴线与大众层理:约翰#183;菲斯克的后期文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轴线论文,大众论文,后期论文,菲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3)08-0053-07
在其早期著作《理解大众文化》、《电视文化》中,菲斯克提出了“大众层理”这一概念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主体。在晚期的《权力运作权力操演》和《媒介事件》中,菲斯克提出了多重轴线、拥有者和没有者、在地抵抗等概念以阐释后结构主义社会的斗争策略,发展出完备的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本文以菲斯克后期著作为中心,结合其他论述,呈现菲斯克文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
尽管在冷战中获胜,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陷入不安之中。当美国被推向单极化世界中的史无前例的领导者位置上时,人们对其领导能力和赋予他们权力的体系失去了信任。各种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华盛顿弥漫着幻灭感。这种幻灭感的表现之一是,政治竞技场广泛存在于政党体制之外:洛杉矶的街道、流产诊所的门口、法院和学校课程等等,这些代替了投票摊成为主要的政治行动据点。与此对照的是,对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无论是投票还是激进主义,都充满着冷漠的态度,这不是因为人们对政治冷淡了,而是表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斗争发生在传统政治还没有认识到的领域。
结构性社会能够以稳定种类的固定关系去理解,这种社会包含深层结构,这一结构组织了那些种类并在社会经验的所有领域再生产自身,理解深层结构也就理解了它所生产的社会现实。欧洲和美国的早期资本主义比当代资本主义更适合于定位为结构决定的社会系统,以结构性理论解释它更为合适。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复杂精密,不能以某一结构模型去理解,阶级不再占据着理论核心的位置,而是必须与其他的组织社会身份和社会体系的轴线一起发挥作用。虽然阶级已经失去了在传统社会理论中的优势地位,但传统阶级分析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经济不平等这一阶级理论的核心变得更为突出,而且是沿着所有社会轴线分布。比如,孩子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最贫穷的社会种类,但黑人和拉丁小孩比白人小孩更穷,单亲家庭的小孩比双亲家庭的小孩更穷,黑人和拉丁单亲家庭的小孩比白人单亲家庭的小孩穷。因此,贫穷是按照年龄、种族、性别、阶级和婚姻状况分布的。再比如,那些观看影片《难以控制》的无家可归者是白人男性,种族和性别轴线以特殊的方式配置其经济被剥夺状况。他们成为弱势者的方式是特殊的,对于一般的无家可归者并不典型,因为他们是白人男性,是优势种族。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缘由不同于其他的性别和种族,但是在经济层面则是类似的。阶级仍然起作用,但与突出的社会轴线时期相比,它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阶级差异常常结合到其他轴线之中。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权力已经代替意识形态成为理解晚期资本主义运作的关键。权力通过在特殊条件下围绕着特殊问题的社会利益群体的联合而运作着,这些联合体的流动性可能横切社会范畴或阶级,或与这些范畴相一致,但一种建基于范畴差异的社会理论如意识形态理论忽视了其流动性,而纯粹的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可能排斥这种流动性之中的斗争。菲斯克发现,一些团体,其特征是黑人性,但他们的黑人性并没有把他们与所有的黑人连接起来,也没有排斥他们与非黑人结成联盟。大众的联合是临时的、流动的,传统的社会范畴如阶级、性别、种族无法与之完全对应。社会范畴如种族、年龄、性别和阶级仍然起作用,但只是在联合体的形成中作为引导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发挥作用,它们不能决定社会经验的结构。围绕问题和具体语境展开的联盟之间的斗争是后现代政治的主要表现。
随着资本主义变得高度复杂,葛兰西看到了流动性发展的迹象,预见其结果是阵地战(wars of position)(不同强度的、多前线的、延长的)将取代游击战(单一前线的、集中在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口)。霸权理论更适合于后结构状况,它不同于福柯的权力理论,它的斗争是在可识别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而不是反抗与社会群体分离的权力体系。福柯的权力理论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有些利益集团从权力的操作之中获益更多。权力集团这一概念缺乏对等的概念,这就削弱了福柯的理论,导致他缺乏对抵抗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中的大多数抵抗更容易为霸权理论所理解,而不是后结构权力观。菲斯克对反抗性力量的寻求,是一个葛兰西化福柯的尝试。
二、多重轴线
后结构主义社会不再能够以单一的社会轴线如阶级来理解,多重轴线(multiaxiality)把任何分类的稳定性转变为权力的流动性。种族轴线和阶级轴线在各种条件下混合着运作。种族差异是策略性地构造的,部分为经济权力所构造,同样的,阶级优先性是色彩化的。种族和阶级不是分别应用的权力轴线,而是种族权力能够沿着阶级轴线实施,阶级权力能够沿着种族轴线伸张。性别轴线参入之后问题更为复杂,但没有改变相关图景。阶级和种族权力沿着性别轴线实施,如同性别权力与之随行。性别差异在不同的种族和阶级层理中被不同地体验和操作,此外,年龄、宗教等也是权力的轴线,所有社会范畴纵横交错在一起。黑人作为一个群体与白人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分割开来,但在黑人群体之内,又有阶级之分,又有性别主义操作其中,底层老年黑人妇女被种族主义、男权主义、阶级控制和年龄歧视所害。
多重轴线意味着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权力的布局不能被事先预知。某些社会利益主体沿着轴线形成联盟和身份以推进和维护其利益,为其目的去策划合适的战术和策略,权力就运作其中。菲斯克借用德赛都的术语战略(strategy),指的是权力集团部署策略以提升和保证其利益,而战术(tactics)则是指弱势者保护和提升其利益的操作。沿着社会权力轴线,战略部署其中,战术实践其中,它们是斗争的领地。社会轴线即是社会种类,它们的稳定性为其战略或战术的使用所打破,战略性权力能够为战术性权力所转向。根据情况的急迫,人们组成社会联盟以协商其生活。联盟可能与社会种类(如阶级、年龄、性别等)的边界一致,或者横切它们。社会联盟可能相当稳定并长期存在,或者是流动地形成、分解和再形成。多重轴线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形成处在过程之中,而非稳固的绝对的结构。因此,菲斯克指出,我们应放弃社会种类(social category),而以社会层理(social formation)代替之,后者指的是社会联盟构成的过程性,它把种类差异理解为领地,在这些领地之中,联盟形成了,策略应用其中。
多重轴线的政治既面临困境也提供了机遇:多重性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层理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社会层理是相交叠的,这样,广泛的政治联盟就可能形成。比如性骚扰,无论是发生在工厂,在街上或家里,对于妇女都是共同的经验,虽然这种经验在不同的种族和阶级位置中会有不同,它能够构成性别共同体,能够便利地在跨种族和跨阶级之间构成联盟。权力集团的宰制性联盟具有漫长的历史,影响深远,其结果是,白人、男性、上等阶级、老年人能够容易地接合在一起,他们的利益相关性使得他们相互交织,实际上,他们的多重轴线变成单一轴线了(monoaxiality)。从属性的社会层理比主导性的社会层理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他们的历史也更为多元,几乎无法消除他们之间的差异,结果是,从属性的社会层理的联盟比权力集团的联盟更难以形成和维持。菲斯克说,“在后结构主义政治世界中,我们必须发展构造和维持联盟的技术。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单一的超级权力的危险就会变成全国性的,如同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现实。”①传统阶级视角在今天的局限,一是阶级并非唯一的社会轴线,社会斗争也沿着其他轴线展开;二是阶级并非固定的结构性存在,一个在经济上是统治阶级的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是被剥夺者,是弱势。
社会轴线的纵横交错导致了文化领域斗争的新形态,具体表现为某一事件的歧义性阐释。比如,在《媒介事件》中,菲斯克以接合(articulate)这一概念谈到安妮塔·希尔的案例被放置在不同的甚至是冲突性的联盟之中所产生的歧义性阐释效应。听证会之所以具有争议性,部分原因是,这些联盟的政治是复杂和冲突性的,依据牵涉其中的社会轴线是如何接合的,它可以获得不同的解释:政党政治围绕着民主党对共和党、进步对保守、左派对右派接合它们;在性别政治中,它显示的是一个孤独的妇人对抗男人;在种族政治中,它显示的是白人对付黑人;在民粹主义政治中,它显示的是“我们”对“他们”,普通人对“华盛顿”的模式;在阶级政治中,它显示的则是职业阶层与较低阶层两者之间的斗争。“每一轴线能够与任一或所有其他的轴线相接合或解接合(disarticulated),不同轴线的交叉点就是一个接合之点:它是一个铰链之点,从此个人能够言说和界定自身,界定其盟友和敌人。每一个接合具有每一个权力轴线所负载的意义,比如女性(femininity)可能是所有妇女之中的统一的轴线,但它与种族和阶级的交叉产生的差异可能扰乱了这种统一。”②沿着某些轴线形成的统一和联盟必然压制其中个体性的差异,而且为了联盟的有效性,任何对差异的压制必须被所有人赞同。在任何一个交叉之点形成的社会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它构成了社会联盟得以进入的那一点。话语和社会联盟的多重性意味着它产生的身份是流变的,因为基于具体问题而策略性地形成的联盟政治是流动的、冲突的和不确定的。菲斯克总结说,“在多重轴线领域展开的政治;围绕在可识别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其中得到常常需要付出作为代价的政治;形成于场合和问题的牵涉到战略和战术的联盟的政治;这些流动性的相互冲突的不确定的政治,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必须面对的。”③
菲斯克对多重轴线所产生的大众层理的界定受到拉克劳的影响。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和墨菲论述了后结构主义世界的社会联盟和斗争,他们指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动理论相反,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完全有可能认同同一种政治斗争符号,并成为一个思想一致的联合体,为特定的政治变革而斗争。“有效的”政治团体并不必然是由来自同一个阶级的人组成,政治团体也不一定是整体性的、完整的或“自然的”:它们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话语和表意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指涉物”是被生产出来的,这意味着政治身份和政治团体是局部地、暂时性地跟某个政治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不会是完整的、完全的或永恒的,一旦事业(政治对抗)失败、取得成功或消失,政治团体将立刻消失,因为这种团体身份是围绕着这种对抗、相对于这种对抗、在这种对抗中构建起来的,它们在对抗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此,他们提出,不应该把政治主体和他们名义上的指涉物等同起来,政治身份应当是在与某个政治事件的关系中形成的。④
三、拥有者和没有者
如福柯斯指出,权力是通过一套科技和机制而不是社会阶级来操作,它分散在整个社会层面而不是一个阶级强加给另外一个阶级。权力是操作在人民之上的一套系统,它的运作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维持并保证其通畅地运转。那些从这个秩序中获利最多的人与这套体制合作以便润滑其运行,这是权力集团的核心策略。人民则是那些获得最少的,被权力系统规训最多的那些人,他们也应视为一套社会力量而非社会种类。人民由不同的和变化着的社会联合体所组成,其常量是他们的弱势,相对于权力集团,他们被剥夺了经济和政治资源。人民没有接近权力系统的便捷的渠道,不能把它转变为其自身的优势。但他们有自己的权力形式,虽然比较弱势,但远非无影响。人民不能以社会范畴如阶级、种族、人种、性别等定义,但它与这些范畴交叉,不能从其中分离。人民这一概念的流动性穿越了社会种类,它也分裂了个体的种类,比如,一个蓝领白人男性与一个黑人男性形成了社会联盟,他与后者共享其技术和从属的工作条件,而在他闲暇的时候,他会与其他白人男性在种族控制中组成联合。第一种联合是与人民的联合,第二种联合则是权力集团的联合。当从属男性以暴力对待妇女的时候,这种权力是帝国化的而非在地化的。从属群体可能沿着其他的社会差异轴线与权力集团结盟,男性从属者在阶级或种族上是被剥夺者,但能够沿着性别轴线伸张帝国权力,从属性的白人可能伸张种族主义权力,因此,“权力集团不是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个策略性的社会集团。”⑤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新变化,菲斯克提出了拥有者和没有者(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⑥这一新的分类范畴。对于美国普通大众来说,华盛顿就是拥有者,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存在于大众的影响之外,脱离了大众的生活。拥有者和没有者这对范畴不同于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或者黑人和白人,它不是客观的社会种类,而是流动的社会轴线,只是在其具体使用中形成。在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可能是拥有者,但在其他情景中,她可能是没有者。洛杉矶的韩国店主可能被本地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人视为拥有者,但当把自己比较于白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把自己定位为没有者。拥有者这一范畴只在社会下层的使用中才有意义,它是没有者的建构之物,因此也就是策略性的而非客观性的术语。
“拥有者”和“没有者”是基于具体情境中的权力和利益冲突而提出的界定范畴,菲斯克又把从属群体称为“社会利益行为者(socially interested agents)”。近年来西方文化理论中的行为者理论(agency)和主体理论(subjectivity)争论不休。主体理论把重点放置在宰制性力量的运作,意识形态理论、物化理论(commodity)、精神分析理论是其要者;而行为者理论则把焦点集中在人们如何对付这些力量上。因为宰制和规训的力量是相当同质化的,主体理论倾向于强调特定社会秩序中的所有主体的共同的东西,特别是其意识和无意识。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多样化的,行为者理论倾向于强调多元性。行为者理论和主体理论都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复杂社会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群体。主体理论集中在宰制性力量,其极端形式暗示从属群体被剥夺了任何抵抗的能力,而行为者力量则强调,正是从属群体的抵抗使得控制性的实践需要不断运作以获得其宰制性,他们强调,从属群体的不妥协的反抗、颠覆或规避宰制性的权力直至这种权力显得无效。
社会行为者并非自由主体(free agents),因为他们受制于不是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条件。他们只能凑合着使用他们所有的,而他们所有的通常是权力集团所提供的。权力集团也在操练其主体性(agency),他们有强大的能力去控制社会资源,其主体性经常是体制化的,常常在诸如教育、法律和媒体等机构中形成。权力集团试图最小化对社会差异的感知,并强调共识(consensus),因为减少冲突意味着保证其地位。而人民的利益由对社会差异的认识和产生其中的社会冲突而得到提升,通过伸张某种区别于从上面强加给他们的社会身份而得到保证。人民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差异的感知,是通过不断地把自己比较于那些权力者的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获得的。被剥夺从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民的控制日常生活的意愿从来不因为其困难而消失,其主体性产生于控制的欲望和社会限制之间的张力。
四、大众层理
在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亚文化,而认为大众是无差异的同质性的,要么是精英的蔑视大众的立场,要么是商业机构的功利性立场。在后者眼里,大众是以人口统计学公式可以计算的人数,是卖给广告公司的商品。菲斯克的观点与此对立,认为大众性意味着“民有”。大众性来自大众,符合大众的利益,菲斯克的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异质性的、具有明确对抗意识的被剥夺者。在大众文化的创造中,文化工业所能做的,是为形形色色的大众层理制造文本库存(repertoire)或文化资源,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对之加以利用或拒绝。菲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在于,他深入到文化接受者的层面,借助学界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发现了大众文化在使用中创造的一面,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忽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菲斯克本人就是大众文化迷,他在大众文化的欣赏中创造着自己的意义,这是他区别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原因之一。在菲斯克看来,大众并非静态的乌合之众,并非与传统的社会学范畴如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对应,大众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它不是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着,大众“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它们跨越了所有的社会范畴;而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时常在各层理间频繁流动。”⑦被支配群体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allegiances)中,大众是可感觉到的集体性(felt collectivity),他们横切社会轴线诸如阶级、性别、种族等组成了大众层理。个体的身份和认同极其复杂,依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时间地点构造着不同的主体,组织进不同的大众层理。个体在某一消费活动和创造自己的意义的过程中与某些人结盟,但在另外的活动中又与另外一些人结盟。菲斯克的大众层理这一概念深刻地推动了对于大众复杂性的认识,因为作为实体性的大众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是个体的人,而个体的人在不同的语境关系中,因为身处的位置的不同,会交错于不同的社会轴线,菲斯克借用了瓜塔利和德鲁兹的游牧主体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在复杂的社会机构之中穿梭往来,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而所有这些重组过程都是在种种权力关系的结构中进行的。所有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都存在着对抗性和差异感,正是种种共享的对抗(shared antagonisms),在即时性的效忠从属关系中认同谁,反对淮,造成了身份的流动性,而流动性乃是复杂社会中的大众的特征。大众层理错综复杂,各种各样,其主体是行动者(agents),而非消极的消费者。他们穿梭往来于各种社会范畴之间,根据临时性语境,可以同时采取显然是相互抵牾的立场。菲斯克说,“这些大众的效忠从属关系是难以表达的,它们既难以概括,也不易于研究,其原因在于,它们由内部产生,并在特定时间、特定语境中,由大众决定。它们乃以语境和时间为基础,而不是‘结构性地’产生的:它们是实践的事,而非结构的事。”⑧因此,在大众文化中,“权力的诸多轴线可以相互支持、抵牾或者彼此平衡。所以,阶级宰制可以与性别统治共存,种族优越感可以与阶级自卑感共存,或者种族臣服可以与性别狂热共存。在相对断裂的领域里,人们在社会层面或话语层面体验和行驶权力。”⑨比如电影《第一滴血》,被蓝领阶层所接受,在种族和阶级政治层面,它可能是进步的,但在性别政治中,它可能就是反动的。大众层理是临时性的,语境性的,因个体在地(locale)所面对的问题而组成的联盟,因此,大众文化必须关系到大众切实的社会经验,正因为这种相关性,才能联系自己的状况产生或抵抗或认同的意义,原住民观影所产生的意义与快感只有在白人宰制并在反抗这种宰制的过程之中才能产生,电视剧《蜗居》的热播,是因为所反映的问题契合了当下大众的切身体验。菲斯克说,社会层理这一概念应视为“一种由不断变化的、相对短暂的结构形成的组合。这个概念既不统一,也不稳定,它在与支配阶级的辩证关系中被不断重新定义。因而,在文化领域,大众艺术是一种短命的、多样的概念,建立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行为的多种不断发展的关系之上。”⑩
在菲斯克的理论中,大众文化是大众自己创造的服务于大众利益的,它是对宰制力量的反抗,不可能是宰制力量的一部分或共谋,但这不意味着宰制性社会群体的成员无法参与大众文化。权力阶层的个体成员在改变其效忠从属关系的时候,与那些社会权力者保持距离的时候,他就参与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是多轴线的,临时的,语境化的,比如一名商人脱下正式的经商服装,在体育馆的露天看台,为他喜爱的当地球队摇旗呐喊时,他就参与了大众文化,他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从经济权力的宰制集团转变为与其他社会大众具有相同趣味的共同体。大众文化的核心是对抗权力,个体可能是权力集团的一分子,但在具体的环境中可能成为权力之轴线的对抗者,因为权力的轴线沿着性别、阶级、种族、年龄、教育分布,这些轴线组成了社会的复杂的权力之网络,个体成员可能是某一轴线的权力者,但处于另外一个权力轴线时,他可能成为边缘者,从霸权的共谋者到霸权的抵抗者的转变,取决于他自身境遇的必要条件以及宰制性的战略能为他提供什么机会这两者的综合考虑。大众文化见诸于具体的实践,而非见诸它的文本及其读者,这种实践产生于文本和读者互动的时刻。同一社会范畴如阶级,不能等同于大众,无产阶级与大众是相互重叠的概念,而非同一的概念,在无产阶级之中,又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大众层理。但无产阶级和女性是大众文化的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女性和无产阶级都是被剥夺了权力的从属者,所以很容易把自身与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大众文化所生产的主要是快感和意义,这些快感来自对权力控制的逃避、抵抗、抵制等。大众层理是交错性存在的,不同的个体对于大众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正是其不同效忠从属关系的体现,比如对于麦当娜现象的不同理解和立场,是基于个体的差异性的年龄、性别、种族、宗教、阶级等状况。
在社会中,权力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任何一组社会关系都必然涉及权力与抵制,存在着支配与服从。布尔迪厄揭示社会的文化资本的分布如它的物质财富的分布一样,是不均衡的,而且也像财富一样,起着鉴别、推动阶级差异并使之自然化的作用。比如对高雅艺术的欣赏是权力阶级才可能的,因为这种欣赏需要长期的教养和训练,而这需要经济资本,但权力阶级却以不能欣赏高雅艺术指责大众缺乏品味,把标明阶级差异的文化品味建立在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人性的基础之上,这就掩盖了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权力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要有效地控制文化,其核心战略就是不断贬低电视这类大众文化,说它无益于个人和社会。大众文化的意义不是根据主流价值体系得出的,也不是要人们甘于处在受支配的地位,它们确认的是受支配者的社会体验,而不是他们的受支配地位。发掘大众文化的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揭露大众文化编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阴谋是菲斯克电视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和视角是由斯图亚特·霍尔开拓的。
五、帝国权力与在地抵抗
菲斯克把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称为帝国权力(imperializing power),弱势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称为在地权力(localizing power)。帝国化的权力尽可能地伸展自身于物质现实、人类社会、历史和意识之中,它竭力把其领地延伸到它能够控制的外部空间,特别是人民的俗世的思想和行为。帝国权力系统为权力集团开发得最多,因为他们要获取最多而让出最少。相反的是,从属群体不控制其他的社会层理,不扩展其领域,而是把兴趣集中在加强对其即刻的日常生活条件的控制上,这些条件包括思想、情感、信仰和行为,以及从社会物质条件中获得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在地权力生产一种为从属群体控制的空间,这一空间具有四个维度:它是内在的(interior),是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被体验的场所;它是社会政治性的(socio-political),存在于某种社会秩序之内;它是物质性的(physical),就在人民居住、玩耍和工作的地方;它是临时性的(temporal),仅仅存在于那些构造它的人息居其中的那一时刻。这一内在的、物质的、临时的政治性空间,菲斯克称为在地(locale)。(11)在地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关系到内在和外在,关系到意识、实体、时间和地点之间的持续性(continuities)。在地是自下而上的在地权力的产物,它常常对抗着帝国权力。构造在地意味着面对、抵抗或逃避帝国权力,因为帝国权力试图控制其社会成员,它通过给他们提供据点(stations)试图去阻止人民生产他们自己的在地。据点是在地的对立物。据点既是物理性场所,其中社会秩序强加给个体,它也是社会性场所,其中个体建立其社会性的关系系统。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是一个据点,它是物理性场所,社会安置他们,自上而下的规训应用其中。如果他们如帝国知识(imperializing knowledge)所认为的,是慈善的脆弱的客体,需要他者化(othered),那么,他们的安置就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对电影中弱势者抵抗权力者的欢呼是他们的在地权力发挥作用的时刻,它把休息厅、电影和他们的意识转变称为在地。在地是从属者反抗宰制集团安置权力(stationing power)的场所。
菲斯克的名言是:“结构安置,实践在地化(Structure stations,Practice localizes)”。(12)这里的结构和实践类似语言理论中的语言和言语,一个是权力集团的控制性的单一化的、总体性的体系,另一个是具体的抵抗的、扭转式的、临时性的运作。实践是人民在社会斗争之中投入最多的,因为它是他们的在地权力最有效的地方。在宏观层面,权力集团的利益通过对结构的控制而得到提升,而人民在微观层面对实践加以控制以获得在地。结构在社会层面实施控制,但是无权者总是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以在地化的方式予以反击,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以他者的语言言说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大众文化是社会斗争的领地,其语言是社会结构之物。虽然是社会里的成员都能够获得的资源,但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均衡地分配的,它是斗争的关键场所。语言常常是多重音调的,它具有为不同的音调所讲述的潜力,这就把意义契合于不同社会层理的利益。帝国式语言试图压制多重音调,试图以权力集团的利益建立单一的音调,并以之作为唯一的、中立的、正确的。与之相反,在地权力开发多重音调。比如一个无家可归者在电视新闻中说,我不是精神有问题,我只是你们所说的经济不稳定,他是在开发多重音调,把他们关于他的观点转变为他自己的观点。语言的多重音调使得从属群体能够投入语言里的社会斗争。比如《难以控制》里的溅满屏幕上的CEO的鲜血对于权力集团来说是危险恐怖的,但是无家可归者把它转变为胜利的象征,他们的欢呼同时是他们的宣言,是对宰制性话语的拒绝。话语可以负载权力集团的意义,但话语也把权力暴露给挑战。如福柯指出的,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矛盾的:当话语实施权力时也使得权力变得可见。权力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伪装和操作的能力,可见性是其弱点,从属群体常常利用这一弱点。
人民与权力集团的关系是多样化的,日常生活不可能是不断的对抗,把某个人的利益纳入权力集团以获得舒适是必要的,即使是为了矛盾的短暂的缓和,重要的是出入这种关系的控制权在人民手里而非权力集团手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可能采取对抗的、逃避的、容纳的或者任何其他的之于权力集团的关系。人民战争是阵地战,其中失败从来不是最终的,胜利也从来是无法保证的。人民战争需要战术的流动性,不能把自己固定于某个社会范畴,或者一套力量的结合。对于社会问题,不存在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但是最终解决的缺乏不应该阻止我们沿着改善之路采取小的步骤。“不可能去设想一种对所有人都完全公平的社会秩序,但是,去构想一个比我们当下的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能够辨识我们需要转移脚步的方向,而不必预见我们的最终目标。”(13)
任何朝向这一社会秩序的移动,有赖于权力集团抑制住其帝国权力,并允许从属社会层理拥有更大的在地权力去延伸其控制的领地。如果他们无法做到,赞同之点可能变成冲突之点,和平的可能变成暴力的。暴力滋生于物质上的和社会性的自我控制空间的缺乏。后结构社会中的政治是从一种权力制度(regime of power)转变到另外一种权力制度。权力如它应用的据点一样是多样化的,因此,变化在权力的不同领域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着。不像革命性的变化,它没有提供给历史学家关键性的点,从这一点可以说新的代替了旧的。权力的变换极其复杂,冲突、前进和后退混合其中。在一个权力制度中是边缘或者是被压抑的,可能在继起的权力制度中是更为中心的,或者相反。一种同质化的、中心和边缘之间是完全对抗的强权制度可能为一个更为多样化的所取代,其中,位于中心的力量更为公平地向弱者扩散。无论新的权力制度可能采取何种规划,变化常常牵涉到去中心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所有领域。解构主义就是把边缘的运动到文本中心,告诉我们文本的关键部分存在于边缘,边缘意味着未来。权力制度的变迁重新规划了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历史没有提供给我们变化的方向,什么将在边缘被重新发现,什么仍然保留在那里,这是无法确定的,新的制度形式是什么样的也无法确定。当某个权力制度到达了某一时期的效率的最高点时,其权力集团会以更大的紧迫性和绝望,通过中心化其利益回应危机,同时,它对边缘的压制会变得公开化和严酷,这样,边缘的再发现变得更为重要。
菲斯克批评福柯的在地权力的缺乏,导致了对大众的抵抗和斗争力量的忽视。福柯认为,官方历史的宏大叙事忽视了经验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经验,历史才是被生活过的,而非被叙述的,这种特殊性扰乱了叙述的权力,这一点为黑人的反记忆(counter-memories)所证实。但是,因为福柯缺乏在地权力的概念,他低估了再秩序化(reorder)这些碎片成为一个反历史(counter-history)因而对于当前来说是反知识(counter-knowledge)的力量,其理论的局限在于,“扰乱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有效的解构主义运动,但在其本身并不够:它能够逐出当前权力制度的某些确定性,但它对于提升下一个权力制度所做甚少,除非进一步的步骤能够被采纳。”(14)反历史有助于产生反身份(counter-identity),更重要的是,产生是一个相反的未来(counter-future)。反历史是在地知识反对帝国知识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反知识去产生反现实(counter-reality)。
分而治理(divide and rule)的原则被帝国权力广泛运用。从属社会层理越是能够被分离,人民就越是能够被个体化到规训、控制性的身体和身份之中,他们就越是能够被更好地控制。不让被压迫者知晓权力操作的程序对于权力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权力必须只能被自己的知识所认知。权力集团对它不需要的知识的压制不仅对于生活在这种联盟之中的人有利,而且这也是权力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广播、工厂、课程设置、街道都是知识的控制和反抗的据点,权力集团在这些对抗中从来不是完全胜利的,因为被压制的知识是如此牢固地根基于人民的物质社会条件和历史经验。菲斯克乐观地指出:如果“没有者”能够抵抗帝国权力,能够在奴隶般这样的控制中获取少量的空间反对它,他们就能够在任何地方这么做。他们已经展示了其绝对的不可战胜性。弱势权力的“弱势”仅仅在其当下与强权的关系中。经过长期的运转,弱势权力将证明比强权更强,他们的力量在于其持久性。(15)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步入后结构主义阶段,传统的结构性的社会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的政治斗争。在今天,社会权力沿着多重轴线分布,人民因具体问题和利益而结成联盟并与权力者斗争,后结构主义社会中的身份政治是流动的策略性的,大众层理构造在地以抵抗帝国权力,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意义。斗争无处不在,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斗争也展开在伦理、审美、仪式、日常生活实践等领域,菲斯克的文化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新形式,为当代大众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概念和阐释视域。菲斯克提出这种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近期横扫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英国的骚乱,似乎印证了菲斯克的理论预言。
注释:
①②John Fiske,Media Matters:race and gender in U.S.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96,p.93.
③⑤⑥(11)(12)(13)(14)(15)John Fiske,Power Plays,Power Works,Verso,1993,p.260,p.28,p.6,p.12,p.31,p.270,p.289,p.312.
④Paul Bowman,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17.
⑦⑧⑨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162页。
⑩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7页。
标签:大众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