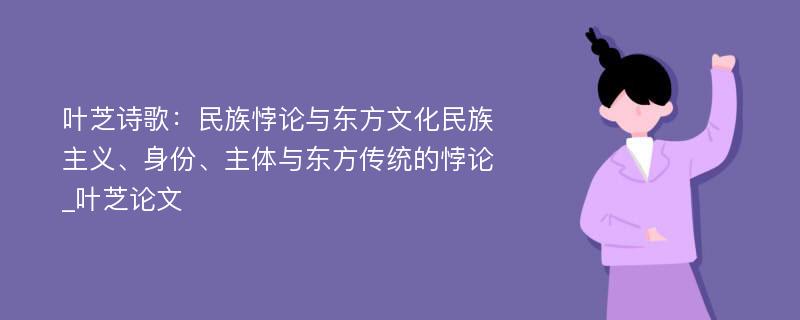
叶芝诗歌:民族的吊诡与东方的悖论——论其文化民族主义、身份、主体与东方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芝论文,悖论论文,民族主义论文,诗歌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3-0039-09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7 虽然西方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东方传统对叶芝诗歌创作的影响,但至今还并没有给予这一影响以应有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叶芝仍然被视为西方文化框架内的现代主义民族诗人[1-3]。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讨论叶芝与东方的文章[4-9]。这些文章试图挖掘叶芝诗歌中东方文化影响的价值,然而却往往透露出这种影响的有限,导致近来的某些研究虽显努力却略有牵强。究其原因,这些研究往往囿于东—西影响论的窠臼,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民族主义这一核心议题对于“民族诗人”叶芝的重要性。本文拟通过对叶芝诗歌中民族主义这一颇有“问题”的问题梳理,来探讨叶芝对东方文化的挪用和误读,试图解释为何东方这个叶芝诗歌中历久弥新的主题却构建了诗人西方的、现代的、民族的身份。 一、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尔兰文学复兴的修辞策略 在叶芝诗歌研究当中,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来探讨其诗歌中身份、主体、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这几个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叶芝与民族主义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0-11],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爱尔兰性”(Irishness)——或“盖尔性”(Celticity)——对于叶芝来说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潜)意识,诗人对其想象性的构建贯穿了他整个写作生涯;其二,“爱尔兰性”与叶芝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从个人的爱情到其文化观、历史观与哲学观等等——的冥思交织在一起。其中与本文研究最直接相关的是民族主义与叶芝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身份之间难以厘清的种种纠葛。 叶芝始终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在爱尔兰“有一种可辨认的、广为各种族所共有的种族成分,那便是‘爱尔兰性’,它表现为与现代世界的敌意”[12]95。但是叶芝很清楚,这样一种广为种族成员所共有的成分不可能简单地建立在种族一致性的基础上,因为他自己作为盎格鲁—爱尔兰人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盎格鲁—爱尔兰人与天主教—爱尔兰人之间的激烈斗争。那么,他所找到的那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构成基础就是麦克尔·诺斯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13]387-393,这成为了叶芝建构爱尔兰民族根性的一贯策略。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引导了本研究的两个相互交织的方向:第一,在叶芝建构爱尔兰文化以及他意识中这种理想化的文化反过来影响其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他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身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第二,叶芝对于神秘的东方文化的挪用。 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英主义。他所说的文化能够统一和代表一个民族,但这种文化却并不是广大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大众文化。叶芝从其创作的初期,便开始建构理想的“爱尔兰性”的概念。此概念主要根植于原始的、非理性的、女性化的爱尔兰乡间,但这并不表示普通的爱尔兰民众在叶芝那里具有道德上的优势。相反,该概念进一步确认了叶芝对高雅的贵族文化的信心——他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精神性的拥有者,这与诗人对于精致的日本能剧的兴趣是一致的。在一篇写于1890年的文章中,叶芝谈到,“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伟大的文学”,同样“没有文学也就没有的伟大民族”。[14]74这其中传达出两个思想:其一是叶芝对于民族文学创作重要性的确认;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在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中美学所起到的绝对重要作用的肯定。许多评论家都特别指出了叶芝思想中所表现的精英民族主义。例如,约易普·里尔森写道: 对于格里夫斯和其原著民主义的新芬党的理念来说,民族的对立面是“国外”;而对于叶芝和他的集体来说,民族的对立面则是“地方”。对于格里夫斯和拥有相似理念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建立民族戏剧是指培养自己的、根植于民间的、不受外国污染的文学。与之相对应,允许国外的影响进入艾比剧院就意味着抛弃了自身的国内价值观,迎合国外的异乡情调,将爱尔兰置于欧洲颓废思潮的困境之中。相反,对于叶芝及其圈中人士来说,民族的则意味着超越地方性以及阿林汉学派伤感主义的浅薄。他们的目标是将爱尔兰带出维多利亚地方主义的漩涡,将其提升至一个成熟的水平,使得其能够与欧洲其他民族并列于民族之林。为了这个目的,将勃迦丘以及欧洲传统中的其他伟大人物作为比照对象也是可以接受的。[15]219 加里·史密斯同样强调了两者间的差异:“民族主义……产生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诗歌,而非民族(national)诗歌。这一点给叶芝、约翰逊和其同僚批评家带来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对于盎格鲁—爱尔兰有着实用意义。”史密斯接着论述道,许多“青年爱尔兰”爱国诗人,如托马斯·戴维斯,都怀有这样一种“问题性的民族主义”,它“激发了一种大众主义的、缺乏复杂性深度的文学,并不适合代表一片新近被想象为充满传奇和英雄、质朴与精神的土地。”[14]74正如我们所见,在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史密斯所言的该词在词义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差别),“文化”,特别是高雅文化,是该词的核心因素。 另外,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曾经使得叶芝相信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贵族倾向,源自于他作为盎格鲁—爱尔兰人的那种“介于两者之间”(in-betweenness)的身份。在叶芝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内在的要求——他对于爱尔兰自由国家的政治、天主教会、爱尔兰民主以及由现代性所带来的庸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不满和恐惧等等——驱使着他走向精英主义。这样一种要求一直刺激着叶芝去创造一种“爱尔兰性”,支持着他“反文艺复兴”倾向的斗争。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要求下的叶芝对于自身身份问题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执著探寻。他在这个问题上与自己和他人的不懈斗争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关切与焦虑。特里·伊格尔顿曾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盎格鲁—爱尔兰复兴主义者求助于“现代主义者为人称道的形式主义与美学主义”,是对于“他们自身无根性的境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且具有抵触性的合理化举动[16]300;也如麦克尔·诺斯所言,文化统一是“强制性的”(coercive)[13]390。 如果我们将叶芝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执著看作是对自身身份问题采取的一种防御机制,那么很明显,他的复兴主义立场则是挪用爱尔兰古文化来确立盎格鲁—爱尔兰中心性的一项策略。所谓的民族性格仅仅只是一种建构和创造,缺乏坚固的核心理念。在考察爱尔兰文学复兴中的冲突中,诺斯指出,叶芝民族主义所依靠的文化是基于“人为的、武断的(arbitrary)概念”[13]390。叶芝与天主教的国人间的身份认同危机构成了他民族主义斗争中的裂隙,同时也促使他去弥合包括此裂隙在内的种种断裂。 格利高里·卡斯特尔对“爱尔兰式的人类学现代主义的修辞、想象力量”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于这种策略理解得更加清晰: 这种[现代主义的文化代偿(cultural redemption)]美学是凯尔特复兴运动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成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背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权威性使得它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有一种表现传统、试图用理想化、本质化的爱尔兰乡间“原始的”社会境况来使得爱尔兰文化获得救赎,这种权威性既与该传统合谋,又与之为敌。这在叶芝和辛格等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真实。他们对于爱尔兰文化的思考运用了文化差异理论并借用了(类似于)人类学的话语手段和策略。英国或欧洲的现代主义者将人类学作为将非西方的感受和视角纳入西方参照框架的一种手段,而爱尔兰复兴主义者一定为能够与这种学说合谋而感到满意——该学说在极其重要的方面,通过生产认识被殖民人民的具有权威性的知识体系,而巩固扩大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17]3 卡斯特尔对于英国、天主教—爱尔兰和盎格鲁—爱尔兰之间复杂关系的勾画,加深了我们对于叶芝挪用古代本土爱尔兰文化的理解。这种挪用是真诚的,用以建构他心目中理想的“爱尔兰性”,既区别又平等于其他欧洲民族。而“人类学”这一措辞深刻又昭然地揭示,这种理想化的古老爱尔兰文化并非叶芝所在文化中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的”一部分。叶芝以一种超然的视角将其视作一个原始的“他者”,虽然他的眼光中也不乏真挚的温情。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一措辞也同时损害了该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用“人类学”一词无异于将叶芝简单地与帝国主义者并列(叶芝的对手“青年爱尔兰”者便是如此批评他)。正如叶芝的朋友莱昂内尔·约翰逊所说,“‘艺术’成了‘英格兰性’的诅咒,而非‘爱尔兰性’的赞美”[18]93。在这个问题上,里尔森的论断似乎更为接近要点:“一方面,叶芝求助于爱尔兰想象来激发他的创造力,逃避英国主流文学的颓势;另一方面,他将欧洲大陆象征主义的所有自以为是的、萎靡不振的颓废注入爱尔兰文化,产生当代都市性的道德两难与复杂,使得爱尔兰乡间生活的简单真理复杂化。”[15]218英国的文化遗产对于叶芝来说,既是祝福,又是诅咒。 二、强力诗人的“自我”主体 叶芝的写作生涯也是不断探讨他命途多舛的国家命运的过程——爱尔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现代性、帝国主义的占领和宗教冲突等种种威胁。在叶芝的写作中,交织在一起的身份问题与民族主义问题不仅仅在他诗歌创作的内容之中,同时也在他诗歌表达思想的方式里有所表现。叶芝是一位自我意识很强的诗人,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诗歌中,牢牢确立着“我”这个概念。他将自己作为祖国和一个确信的“自我”的代言人,这个立场似乎是无需证明的。但是,为了这个强力的“自我”主体,叶芝使用了各种手段以实现其合法性。首先,“介于二者之间”的诡谲身份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立于双方而又不被任何一方所约束。 以叶芝早期诗歌《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为例,这首诗是他于1892年出版的诗歌集《玫瑰》中的第一首诗①。该诗总起全集,是叶芝走向诗人之路的宣言书。起始两行为:“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请来到我近前,听我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诗人在此呼唤爱尔兰缪斯赐予他诗情的灵感,誓言“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这朵柏拉图式的、永恒的、神秘的、女性化的玫瑰是精神性的所在,很明显,它象征着爱尔兰民族间以及基督教的手足之情。在此呼唤中,诗人从古老爱尔兰乡间文化里获得了诗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从他的盎格鲁继承身份中积累了文化资本:读者很快就被他极其浪漫优美的诗句所吸引(如第7行:“脚趿银屐在海面上舞蹈”)。作为强力诗人的主体,叶芝既与爱尔兰民族传统紧密相连,又有着盎格鲁的美学特征,在两者中同时获得了合法性证明。如卡斯特尔所示,盎格鲁—爱尔兰复兴主义者占据着一个十分模糊的社会地位,既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又作为民族主义者自我确认的反对派。在伊格尔顿所说的、由古老和现代所构成的张力所统治的社会里[17]2,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身份在政治和美学上似乎更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 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叶芝的一个无法化解的困局——“民族排他性与民族自我充实间的冲突”[15]218,认为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史密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解构主义的解读。他在“补充性”(supplementarity)的意义上分析了冲突双方的关系: 真实的民族经验必定为一种“补充性”所占据,这种“补充性”将为盎格鲁—爱尔兰在当代爱尔兰中确保一个位置。在政治意义上,这种补充性被认作是都市的一个必要维度,以抵制地方性和孤立性的邪恶。在美学意义上,它意味着与风格、技巧和真正的艺术——道(例如与戴维斯式的宣传鼓吹相对立),批评(criticism)被列为真实民族经历的组成成分。该概念中的根本矛盾在于,叶芝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艺术应该等同,而另一方面却否认源自于批评对象的批评的真实性。或否认引起自身批评的艺术。批评一定通过与其文化客体发生关系来确认盎格鲁—爱尔兰经验,这既统一又有差别。[14]75 在叶芝民族特性的建构中,“自我完满”的(基于乡村的)爱尔兰身份的中心性却诡异地需要由“都市的一个必要维度”来补充。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鉴于其介于二者之间的身份,叶芝自我确认的主体也需要有其他外来资源作为“补充”。如上所述,他既有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忠诚,又从盎格鲁都市美学中得到了主体合法性的确认——从后者中获得的诗学文化资本“补充”了他对建构真实的“爱尔兰性”的执著追求。 在哲学层面上,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中的内在二元性不仅可以追溯到他模糊的身份,也可以上溯到从柏拉图以来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主义,古代哲学中本质与形式间的张力转化为现代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张力②。这种本质上的二元主义深深地系于西方思想中对主体的根本确认。叶芝的矛盾同样源于他自我意识强烈的身份与主体问题,它只是这种分裂一种特例的展现而已。 三、强力主体与东方神秘主义的挪用 叶芝似乎也从一开始意识到这种潜藏的分裂,他试图通过从非西方的文化中寻找灵感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似乎从古老的印度哲学中发现了慰藉,来寻求自我与宇宙本体(梵)的同一。如约翰·里卡德写道:“被困于现代爱尔兰国家给他带来的痛楚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越来越不信任之间,叶芝建构了一座想象中的印度文化的山峰,以建构一种未受现代性污染的、有近似于他认为是盖尔和印—欧文化本原特性的哲学和种族”[12]110。 叶芝寻求于印度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行为,一直被认作是对面临现代性来袭的真正的“爱尔兰性”的救赎——“对于原始的回归受到欢迎,同时也是已然被确定的——它被当作是18世纪理性主义和19世纪物质主义的解毒剂”[19]153。叶芝在两种文化间所发现的共同点——包括精神性所依托的古老的原始性、受英国殖民者的共同压迫——可以解释叶芝对印度文化的兴趣。但是主体性在现代西方思维中的——特别是在叶芝的事例中的——中心性,使得整个问题变得复杂化:一方面,叶芝寄希望于东方文化能为民族主义和身份问题的危机找到一条出路,不仅仅通过给他提供精神性的神秘文化作为类比,而且还给他展示一条通过降低并最终消除自我来绕开西方哲学中裂痕的途径;但在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些“他者”文化同时也加强了他自我肯定的主体性。 我们可以看到,上文中里卡德对印度文化在叶芝诗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评价,同时也暗示了叶芝挪用古代印度文化来作为爱尔兰文化对抗现代性的拯救策略。如果我们能理解叶芝处理古代爱尔兰文化中的想象性、挪用性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对待古印度文化中的类似态度发生误解。对于叶芝来说,后者在地缘政治和心理上是更加遥远的客体。这种对印度文化的挪用(而非与其产生共识),包括主体走向客体的过程,反过来也证明了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我”在叶芝诗歌中的重要分量。另外,叶芝所挪用的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也是额外的却有效的方式,以对他自我肯定的主体性进行合法化。印度的情人、玫瑰、星辰,日本的宝剑,中国的雕刻、佛教、禅宗——所有这些神秘的、异域的、具有异国风情的文化“他者”象征,都强化了叶芝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自己文化的合格代言人。如果叶芝确实从盎格鲁这个“(半)他者”中获取了文化资本,那么他对东方文化的诉求不也可以作为他确认自己为有良知的爱尔兰文化代表的另一种尝试么? 在下面部分中,我将着重考察叶芝是如何在他解决自身问题的议程中利用东方文化象征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或许也曾试图去把握这些文化的本质,以从消除自我的视角提供给他对付自身危机的道路,但是他对东方的强力误读却重新确立了他的主体性,加强了他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地位。 叶芝与东方传统的经历已有多种论述,此处不赘[4、6]。叶芝早期以印度作为主题的诗作《印度人致所爱》(1886年12月)便反映出他对印度文化的殷羡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这首田园爱情诗是欧洲抒情诗歌传统和诗歌形式与印度主题的有趣结合: 诉说世俗中惟独我们两人 是怎样远远在宁静的树下藏躲, 而我们的爱情长成一颗印度星辰, 一颗燃烧的心的流火。 带有那粼粼的海潮、那疾闪的羽翮 (第11-15行) 除了说话的印度男子和作为他爱情象征的印度明星,全诗没有任何特别意象将印度展现为独特的文化参照。在此,印度被用作一种神秘主义的符号,而叶芝相信有一种永恒的美藏身于此。总体上来说,这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化的印度。 叶芝曾于1908年写道:“我写作之初,是阅读引导我四处寻找创作主题,我倾向于所有其他国家,如雅卡迪和浪漫的印度,但现在我说服了自己……我不应该在除我自己国家以外的任何地方寻求诗歌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叶芝诗歌本质上是爱尔兰的,年轻浪漫的避世主义者叶芝通过创造一个梦幻之岛印度,将自己乌托邦式的爱情之土投射过来——这片热土远离“不平静的土地”,梦幻之岛也是抽象的、普适的。 在写于1923年的《内战期间的沉思》一诗中,一柄远古的仪式用剑成为了在现代性物质主义的变动不居中永恒不变的高雅文化的象征(“就像这剑一样不曾变更”)。此剑是日本外交官佐藤纯造1920年赠与叶芝的,在此成为东方文化的又一代表。它被当作高雅文化的真正拥有者(“一件不朽的艺术品”)以及不变的精神性(为了“一颗疼痛的心”)的象征;它将灵魂带入天堂,“可以儆戒/我的日子免于无目的的虚抛”(第三章《我的桌子》,第4-5行)。 这柄剑在写于1929年的《自性与灵魂的对话》一诗中再次出现: 横在我膝上的这神圣的剑 是佐藤的古剑 (第9-10行) 依然像从前一样, 依然快如剃刀,依然像明镜一样, 不曾被几个世纪的岁月染上锈斑; 扯自某位宫廷贵妇的袍衣, 在那木制剑鞘上围裹包缠, 那绣花的、丝织的、古老的锦缎 破损了,仍能保护,褪色了,仍能装饰。 (第10-16行) 但是叶芝对于该剑象征的取舍在这六年中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处所强调的不变的部分是剑的“物质性”而非以往所拥有的“精神性”。当“我的灵魂”宣布精神之塔的垮掉,“我的自性”却在肯定这柄利剑仍熠熠生光的物质层面: ……它周围躺着 来自我所不知的某种刺绣的花朵—— 像心一样猩红——我把这些东西 都当做白昼的象征,与那象征 黑夜的塔楼相互对立…… (第26-30行) 叶芝不仅解释了该剑的历史与外形,而且还将它的物质性(“像心一样猩红”的刺绣)与塔楼的精神性相对立:“我把这些东西/都当作白昼的象征,与那象征/黑夜的塔楼相互对立”。在这里,此剑不再是精神与仪式的象征,而成为物质与世俗的象征。它赞颂了世俗的英雄主义,并暗示着男性的权威。该剑象征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逆转——伴随着诗人思想的发展。 在这里,同一件事物(一柄日本古剑)作为象征的巨大转变(尽管它本质的稳定性没有发生改变),使得诗人对该事物的掌握与挪用意图更为明显。东方的象征物被作为一个符号,可以灵活地用以指征。通过使用异国之剑的象征,“我的自性”在与“我的灵魂”的对话中实现了它决定性的地位。在与“我的灵魂”的争斗中,诗人的自性通过带领灵魂进入物质性的话语之中而取得了上风。“我的灵魂”无法发言,因为当它一旦使用了(“物质性的”)声音,就已经落入了“我的自性”的话语之中了。因此,“我的灵魂”之舌从第一节结束便成为了“石头”,在接下来的诗节中完全保持沉默。那个曾经是决定性的灵魂失去了对神秘宝剑的支配,将自己的中心地位交于了“补充性”的自性。但在这场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中,除了叶芝,并没有最终的胜利者。他是本诗的作者(author),也是人类内心斗争权威(authoritative)的代言人。“我的自性”与“我的灵魂”之间的对话便傲慢地普适化为《自性与灵魂的对话》,诗人英雄化的主体在此得到充分地展现。 尽管“我的灵魂”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沉默不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受佛家思想的影响: 想一想祖先留传下来的夜, 只要想像藐视凡尘世界, 理智藐视其从此到彼 又到其他事物的游移, 夜就能使你脱离生与死的罪恶。 (第20-24行) 对于“我的灵魂”来说,超验的精神性可以类比于永恒的涅槃,超越生死轮回与尘世间的孽。根据佛家教义,到达涅槃之理想境界,需经过仪式性的冥思以求得自我意识的消除、欲望的泯灭。但是灵魂认为,人类过于受制于尘世间的事物,不再能够辨识“‘在’与‘应在’,或‘能知’与‘所知’”(第37行)之间的差别,这使得他们无法升入天堂。“惟有死者能够得到赦免”(第39行),因为他们已从悲剧性的无限轮回中解脱。 但是“我的自性”因为拥有话语权,沉溺于当下、自我和此世世俗的无限可能性: 我满足于在行动或思想中追溯 每一事件,直至其源头根柢; 衡量一切;彻底原谅我自己! 当我这样的人把悔恨抛出, 一股巨大的甜蜜流入胸中时, 我们必大笑,我们必歌呼, 我们备受一切事物的祝福, 我们目视的一切都有了福气。 (第65-72行) 和灵魂的世界形成鲜明反差,这里“活者”得以宽恕。更重要的是,此宽恕的过程也是自我合法化过程,反之确证了主体的确然性。 或许叶芝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他无法把握佛家之道,通过降低直至最终消除自我的意识来解除自身的痛苦——“他几乎已经触摸到了真谛!”但他选择了入世、作为和介入,而非避世主义,是由于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与责任感不允许他超然于这个世界之外。换而言之,他选择了确证、斗争与痛苦。 叶芝对于东方哲学情有独钟的更为明显的例子是他哲学中的“目光”和“旋回”(gyre)。在他的哲学理念里,月亮的圆缺对应着人生的起伏,“旋回”的开放与收缩循环往复,对立成分相互包容,这都与佛家的轮回和道家的阴阳形成类比。不同的是,佛家与道家都以宣扬“无我”的状态于世,而叶芝的哲学却强调特别阶段与时刻的实际效用,因此,更为确证后者中自我作为行动的主体。 说到佛家和道家,《天青石雕》一诗(1938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该诗在不经意中运用了道家哲学来阐述诗人“悲伤的快乐”这一哲学思想,而超越了外在的灾难。诗的一开头故意使用了非正式的、随意性的描述来减轻社会灾难所带来的沉重,然后策略性地将“悲伤的快乐”的事例由西方转向(精心挑选的)希腊——因为它横跨东西的文化地理位置,最后到达中国/东方——精神之都: 天青石上雕刻着两个中国佬, 身后跟着第三个人, 他们头顶上飞着一只长腿鸟, 那是长生不老的象征; 第三位无疑是仆人, 随身携带一件乐器。 (第37-42行) 前面几行诗句介绍了作为佛家哲学精髓之一起起落落的永恒轮回[“一切都倾覆又被重造,/重造一切的人们是快乐的。”(第35-36行)]。有了这几行作为转承,本节这一描述性的诗节似乎是以把握中国艺术之精髓为目标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本节的确传达了一些传统中国画的精神和韵味:白描的、非聚焦的,或者说多点聚焦的描述特点正是道家绘画的特色。道家绘画尽量降低人的作用,表达他们与外在世界合而为一的境界。但是本诗中主体性的“目光”/“自我”(eye/I)却得到了某种暗示:“无疑”一词十分突兀,暗示了观察者由外部强加的判断。 叶芝本人从未企图掩盖他对这件艺术品注视的目光,他十分明确地宣称:“……我乐于/想像他们在那里坐定”(第49-50行,笔者的强调)。同时,该描述也被证明是想象性地重新建构:那“熏香了半山腰上那小小凉亭”的“杏花或樱枝”实际上是一棵松树。另外,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山中隐士很少是英雄式的人物③,而叶芝则在这东方的艺术品中看到非常西方化的“绝望中的英雄的呼喊”[21]116。这种对中国雕刻叶芝式的“创造”说明了诗人先入为主的“悲伤的快乐”的概念。 叶芝对东方艺术的兴趣同时也见于1938年的另一首诗《仿日本诗》。正如诗人对友人所说,该诗的灵感来自于一首赞美春天的日本俳句[13]116。叶芝确实在音步与节奏形式上模仿了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影响的日本俳句,但是他却不愿深究。就拿最为方便寻找却又最为重要的一首西方俳句——埃兹拉·庞德的《在地铁车站》(1913年)——作为比较和对比的对象: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我们在这两行诗句里读到的,或者说看到的,是好几个叠加的意象,用来传达特定的感觉与感受。此叠加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连接词(辅助语)的少用或不运用。这样一来,诗人给意象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它们彼此自由联系,在读者脑海里产生各种可能性,以达到制造足够多义的目的。或者说,诗人根本就无意说明和确定任何实在的意义,只是想通过意象间的张力来传达一些可触摸的感觉而已。这与道家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另外,自然中的无我境界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特点④。我们可以说,庞德的这首意象诗把握住了传统东方诗学的这些要点,但是叶芝的模仿却没有: 极其稀奇一件事, 我已活了七十年; (欢呼春天繁花开, 因为春天又来临。) 我已活了七十年, 没做褴褛讨饭人; 我已活了七十年, 七十年来少与老, 今始欢乐而舞蹈。 从句法上来说,叶芝过于依赖助词,让诗中的逻辑联系显得十分清晰——这是由于中文和英文在语言学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相比较而言,庞德的努力在“模仿”的意义上来说似乎更有成效。另外,叶芝没有试图通过纳入更多的意象而使这首短诗更加丰满和具有诗意,而是在这种形式所允许的有限空间内,颂歌般地为他生命之泉的“第二次降临”近乎奢侈地欢呼。而这个极其中心化的“我”确然占据了诗歌空间的绝大部分,没有给读者留下太大的空间。 诗人所表现出的确然的主体似乎成为他真正“进入”东方文化的障碍。换而言之,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对民族主义和身份问题的执著,使得他无法真正地把握东方哲学。诚如许多论者指出,叶芝抓住了东方传统中“实用”的部分,为其民族诗歌的现代表达所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叶芝平生的诗学追求不允许他去消除自我,他需要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介入性的知识分子;他对东方文化的强力借用与误读使他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强力诗人的地位,使他能够以他自己的方式应对爱尔兰问题、解决哲学上潜在的分裂——尽管他的这种诗学在许多方面引起各种矛盾和悖论。 四、叶芝的诗学暴力/诗歌美学 如我们所见,叶芝深潜于西方传统之中,拥有过强的个性,虽然他试图从东方世界寻找灵感,但还是无法解决其自身的哲学问题。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强力诗人,叶芝英雄化的、却又未能完成的斗争,赋予他的诗歌一种悲剧性的气息和永恒的魅力(如他的诗集《最后的诗作》、特别是其中《不尔本山下》一诗中所表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美学上通过诗的破格和诗学暴力所建构出的他孜孜以求的统一性。他早期诗歌中呈现出对立状态的意象和力量,在他晚期诗歌中神秘地实现了统一,或者说暧昧地交织于一处。 麦克尔·特拉特纳论述道,叶芝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是早期和晚期集体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桥梁——连接着对大众的恐惧和对大众的融入”,他作品中“由个人主义者向集体主义者”的转变可以从他的“暴力诗学”来解释[20]135。叶芝本身真正集体主义者的立场值得怀疑,这也是特拉特纳论述中潜藏的逻辑矛盾。但是我认为,他的“暴力诗学”的观点确实很有洞见地指出了叶芝试图克服各个层次的裂隙与矛盾所采取的策略。特拉特纳将“暴力”解释为对垂死的男性理性毁灭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昭示着由失落、痛苦甚至恐怖所带来的具有女性精神性的新世界。特拉特纳的该“性别化”论述在何种程度上合理,需要另文再讨论,这里只想说明的是,特氏所指出的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暴力倾向,有助于我们对其诗歌产生新的认识。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该暴力理解为诗歌美学,在叶芝的诗歌中转化了众多矛盾,形成了矛盾的统一,那么这种解释将更富有建设性。 在叶芝的许多诗歌中,一些概念和思想彼此矛盾对立,但它们又会在诗人的长期思索中同时成立;或者在另外的情况下,它们会共存抑或被强行拗在一起,形成极其复杂的意象。例如上面所说的日本宝剑,通过互文性解读我们知道,纯粹的物质性或者精神性都不足以构成民族建构的充分条件,或许文化根性与英雄举动的结合可以共同构成所需要的条件。自我与灵魂间的对话也是一样——尽管在第二诗章中“我的自我”通过话语权力使得“我的灵魂”完全沉默,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此世界”过于傲慢的确认,反而会使得其让对立面的完全隐退更加困难,这样就暗示了同样重要的、一个相对立的立场,那就是对“彼世界”的认可。“彼世界”的暂时隐形仅仅只是因为它与当前的话语不协调,而此话语又是当前唯一存在的话语,因此留下的空白在一种反讽的意义上——或者在道家的意义上——却显示了一种别样的力量。 叶芝的诗学暴力更加明显地体现在那些具有统一性和已经统一的意象之中。特拉特那写道:“意象是暴力转型(violent transformation)的同义词:和柏拉图哲学不同,意象创造非连续性”[20]161。叶芝许多晚期的诗歌作品都运用了意义模糊、晦涩的意象,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书写上的政治暴力,更重要的是为了用诗歌美学来克服业已存在的断裂。最诡谲的一个意象是经常被提及的“舞者”。她最早出现在写于1919年的《麦克尔·罗巴蒂斯的双重幻视》一诗中,是一个女子的雕塑,在一个“生着女人胸脯和狮爪”的斯芬克斯和“一手安住/一手举起祝福”的佛陀间起舞。这个特殊的位置处于一个象征智慧的女性形象和一个象征情感的男性形象之间,暗示着二元对立的沟通的可能性——这对于诗人来说极为重要。他(或者说是叙述者)在月亮升起的“第十五个夜晚”思考,认为:“我有生之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坚实”(第26行)。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舞者呈现为一个完美的组合形象,因为他/她是一个统一的、思考的个体。《在学童中间》(1927年)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诗歌是这样结束的: 呵,栗树,根须粗壮繁花兴旺, 你究竟是叶子、花朵还是枝干? 呵,身随乐摆,呵,眼光照人, 我们怎能将跳舞人和舞蹈区分? (第61-64行) 在这首诗当中,前面几节在年老与年轻、男性与女性、盎格鲁—爱尔兰人与天主教信徒、过去与将来等关系之间构成了张力。在最后一节里,这种紧张非常诗化地,或者说非常暴力地消解于两个有趣的意象中:作为无法分割的整体的核桃树,和一个无性别的、无种族的、不老的舞者,象征着主体与客体的结合。 在复杂性方面,这种结合更为晦涩的表达是在《拜占廷》(1930年)一诗的结尾: 舞场铺地的大理石 截断聚合的强烈怒气, 那些仍在孳生 新幻影的幻影, 那被海豚划破、锣声折磨的大海。 (第36-40行) 那些意象是如同“那被海豚划破、锣声折磨的大海”一样没有被净化,还是它们是属于已被净化的精神性的世界,如同“舞场铺地的大理石”?抑或两者都是?另外,作为精神性象征的拜占廷在这里值得质疑,因为其中的许多意义模糊的意象,例如皇帝的酒醉的士兵们,以及充满人类血脉的怒气和淤泥的世界等。正如特拉特纳写道:“这首诗非常暧昧,因为它本身就是关于暧昧这个话题的——这是一个以消除意义来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20]163。正因如此,我认为叶芝所使用的意象跨越两个对立却又同时成立的范畴,因此,其中的对立被转换成为二律背反。 五、结语 东方传统时而彰显时而隐灭地贯穿于叶芝的写作生涯。或许诗人从未“特意转向东方寻找创作题材和灵感了,而只是偶尔利用东方的感性形象来象征他的抽象理念”[4]56;或许是他所处的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情境、他父亲的哲学影响、他自身的诗人气质和追求以及他政治、情感、交友经历等各种因素共同造就了他与东方剪不断理还乱的遭遇[6]。另外,爱尔兰与东方同作为“他者”的地位,于叶芝而言也有着某种情感上的同构性[22]。印度哲学和东方文化中的整体统一性确实给予了叶芝灵感的瞬间及自信,来克服一直困扰他的、深潜于西方思维中的断裂以及其不同形式的变形。但是,诗人未能也无法把握东方传统的本质,而只能是挪用它们和对它们进行误读,这样只会强化诗人本身的主体意识,又恰恰与东方哲学中的“无我”的概念相悖。这种悖论显现于诗人对东方传统追求的各个方面,如其所追求的世俗人生之永恒而非超脱六道轮回之永恒,以及科学实证的神秘学信仰等。 叶芝在构建自己个人哲学的过程中触摸到了东方这一蹊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和民族主义的诗人,且拥有强健的个性与美学诉求,叶芝自信无法放弃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责任。因此,他对东方文化的诉求只能限于一种颇具良知的、英雄性的挪用行为,这使得他确证而非消除自己的主体性,与其梦寐的东方南辕北辙了。如此,(当然还有通过其他途径)叶芝获得了他作为一位强力诗人的地位,拥有了合法性的主体,得到了行使诗学暴力而可被豁免的权利。在艺术创造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叶芝的创作生涯起始于想象(imagination),而结束于想象性的意象(imaginative images)。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收稿日期:2014-10-17 注释: ①本文叶芝诗歌译文均选自傅浩译《叶芝诗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②阿多诺写道:“如果说一切决定性(determinants)——也就是那些决定某事物成其为某事物本身的因素——确实是由‘形式’(form)所发生;反之,如果‘实体’(matter)确实是不确定、抽象的,那么,在这种前主观(pre-subjective)、本体论的思维之中,早已包含了后来的唯心主义信条的精确轮廓。根据该信条,认知实体是绝对不确定的,要从它的形式之中,也就是主观性之中,获得它一切的决定性和内容。”参看Adorno,Theodore W.Metaphysics:Concepts and Problems.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49. ③该资料感谢讨论课上谢文姗女士的论文"Recreating a Stone:Yeats's 'Lapis Lazuli'"中提供的信息。她参考了O'Donnell,William H."The Arts of Yeats's 'Lapis Lazuli'." Massachusetts Review 23(Summer 1982),pp.353-67; Chung,Liang."A Humanized World:An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Lyrics." In Literature of the Eastern World,edited by James E.Miller,JR.,Robert O'Neal,and Helen M.McDonnell.Illinois :Scott,Foresman,and Company,1970. ④叶维廉在中国诗学和东西方比较诗学方面做出过许多深富洞察力的研究,参看Yip Wai-lim,ed.and trans.Chinese Poetry:Major Modes and Genr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Yip,Wai-lim.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Yip,Wai-lim.Between Landscapes.Santa Fe:Pennywhistle Press,1994.